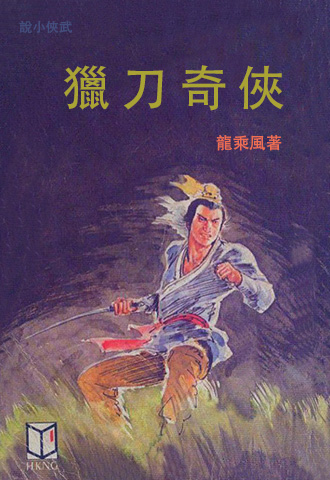朱玲听他们一问一答,心中急得什么似的,眼巴巴就希望他们快放了自己再谈别的。
陈雷正要回答金穆关于宫天抚怎样了,一转眼忽见朱玲露出焦急之色,便疑惑地问道:“石朋友你怎么啦?急什么呢?”
他们一动疑心,麻烦可就大了。朱玲的心儿突地一跳,但不敢露出丝毫慌张之色,苦笑道:“陈兄你是在为难在下么,在下哪敢心急?只不过听你老提起那姓宫的兄台,一时有点好奇。”
陈雷一听这解释有理,任何人处此景况,也会想多听一点儿消息。当下颔首道:“好罢,你们夫妇千万记得出庄别多嘴多舌。”
金穆这时暂且不问宫天抚的情形,却转身走到桌子边,抚抚她们的包袱,这两个包袱中,都包着一口宝剑,故此都是长方形。他道:“像你们夫妇,何必带着两把剑,启人疑窦?下一趟只带一把也就够了”
朱玲又暗惊起来,想道:“我的太白剑不是凡品,他们要见到此剑,必定不肯放过我们!”随即她又恨恨想道:“我这叫做虎落平阳被犬欺,凭你们这两个东西,就把我弄得胆颤心惊,等你们放开机关,我不杀了你们,我就不是人!”
她暗自发狠,人家可不知道。陈雷却道:“这些人便是这样,老是在替自己找麻烦。”
恶樵夫金穆也摇头道:“这一番不知是他们晦气抑是我们?你看我们可不是也多了许多麻烦。”
说着,忽然把包袱打开。朱玲大吃一惊,只见金穆取起内中的长剑,道:“陈兄你看,这剑敢情真不错哪!”
陈雷过去一看,口中啧了一声,道:“这可是百炼精钢的好剑呢,我猜一定是那位小娘子用的!”
金穆笑道:“何以见得呢?莫非你已瞧见包袱中的女人衣物么?”
陈雷道:“不是,这等好剑当然是这位懂武功的小娘子使用呀!”
“猜得好,这个包袱果真是小娘子的!”
朱玲闭上眼睛,心中自语道:“你们这两个混蛋,算了罢,还看什么呢?”
她自然怕金、陈两人再解包袱来看,只因那柄太白剑非是凡兵俗器,落在这两个老江湖眼中,还能猜不出她身负绝艺么?
上官兰半晌没作声,这时忽然道:“求求你们两位让我们走吧!”
他们闻言一齐回她一眼,陈雷大概耳朵较软,容易听女人的话,便道:“马上就放你们走,你不必慌。”
金穆一言不发,回头又打开另一个包袱。
那太白剑古朴的形式,已足够教他为之一愣,伸手取剑一按弹簧,“呛”一声全剑出鞘,顿时满室白气蒙蒙。
陈雷惊噫一声,道:“这是什么剑?”
金穆把玩一忽儿,才道:“此剑名为太白,真是好剑!可惜……”
“可惜什么?”
“可惜教主不是用剑,其它也没有谁是用剑的!否则这不是件上佳礼物么?”
陈雷点头道:“不错,奇怪那厮怎会藏有这等好剑?”
朱玲道:“这是寒家世代相传的一宗宝贝,寒家屡代都用这剑镇住家宅,邪魔不侵!”
她答得够快,陈、金两人一时便没想到可疑之处。金穆问道:“你这剑可肯出让?”
朱玲眉头一皱,露出为难之色,心中却骂道:“可恶的混蛋,等会儿连本带利,慢慢细算”
金穆哈哈一笑,道:“此剑如给碧螺岛主于叔初或者石轩中得到,可就上了天啦!他们都是使剑的一等名家,得到这等神物,有如猛虎添翼……”说着话,便走向暗间,去按枢纽放开她们。
他走进暗间,陈雷忽然叫道:“金兄且慢!”
金穆的手已摸到机钮上,只要往下一扳,朱玲和上官兰都立刻恢复自由,这时却中止了动作,问道:“什么事呀?”
陈雷直接问朱玲道:“你怎么啦?”
朱玲惘然寻思,直如不闻,原来她一听到有人提起“石轩中”三个字,登时心灵大震,迷迷惘惘!
陈雷问了一声不应,便耸肩自语道:“书呆子,没办法。”
金穆见没有什么事,颇怪陈雷冒失,心念一转,向朱玲道:“现在我想起一件事,故此得屈你们夫妇的驾,暂留在本庄一两日!”
朱玲雄心忽起,只因她听到这恶樵夫金穆居然把石轩中拿来与天下第一位剑家的碧螺岛主于叔初相提并论,心波为之荡漾不息。对于石轩中这个名字,她熟悉得不能再熟,但她纵然在心中叫千万遍,也及不上听到别人口中提起那么刺激心灵。
她的确因石轩中之故而骄傲振奋,抬眼道:“方庄主之命,愚夫妇岂敢不从?”
这时她已立定主意,哪怕仍旧锁在椅上,但只要一时三刻不露出马脚,她仍可以争取时间挣脱枷锁,那时节她非放一把无情火,把整个方家庄烧为平地不可。
金穆走到暗间,扳动机钮,“啪”的一声,圈手椅上的四道钢箍都放松缩回椅中。他道:“你们到指定的房间歇宿,只要规规矩矩,不离那院子一步,便没有一点危险!”
朱玲赶紧站起身,心中忖道:“现在我可不怕你们了,混蛋的东西们,总要教你们晓得我的手段!”嘴里却恭敬地道:“庄主你老放心,愚夫妇一定听从指示!”
金穆随即命人来把她们带到一个院子里,指定她们住在北上房中间的一间。
朱玲等人家走后,登时吁口气,跟着又冷笑一声。上官兰忙对她眨眨眼睛,向窗外嘟一嘟嘴巴。
朱玲把她拉过来,搂在怀中,悄悄道:“我怎不知外面有人,但今晚之事,我决不肯和他们善罢罢休,先教他们狐疑一下也好。”
只听步声又响,有人敲门道:“小的奉庄主之命,把两位的衣物带来。”
朱玲忙忙出去接了,一眼瞥见自己的包袱中还有长剑,心中暗喜,也甚是惊奇。
回到房中,赶快拆开包袱一看,太白剑赫然尚在!上官兰大惑不解,趴在朱玲耳边问道:“玲姑姑,他们为什么不取这柄宝剑?”
朱玲先关好门,吹熄灯后,把她抱上床去,放下帐子,然后在她娇嫩的面颊上亲一下。
上官兰禁不住咭咭而笑,但她立刻便记起当日在仙音峰上,宫天抚曾经抚爱她的一幕往事!是以立刻怔住,朱玲轻轻道:“外面的人听到你的笑声,该不会怀疑了吧?”
但上官兰可没有听到她的话,心中千般幽怨,万缕愁思,郁结不解!最后,她自个儿轻叹一声,想道:“我此身已非完璧,纵使将来遇到如意郎君,但人家一定不肯原谅我的过失,同时我也将愧对良人!唉……”
朱玲诧问道:“兰儿,你想什么?”
“玲姑姑,你要嫁给宫大叔么?抑或是找到石大叔再决定?”
她自家也不知何以忽然问出这么大胆的话来,这是数年来她都不敢触及的问题!这时蓦然发觉自己问得太突兀,赶快吶吶地补充道:“我……我是在想……假如玲姑姑你两个都不嫁的话,我便永远跟随奉侍你。”
朱玲呆了半晌,叹口气,翻身向内,枕住自己的手臂,没有作声。
她迷惘地怅思许久,忽然想道:“兰儿已经长大了,她已经开始关心婚嫁的问题!不过她并不要紧,因为她还有足够的青春和完整的感情,可以献给她喜欢的人,我呢?”
不知不觉已是三更时分,朱玲轻轻坐起来,上官兰也睁开眼睛。朱玲道:“咱们可以动手了!”
“去救宫大叔?他真的被困得无法可施?”
朱玲微笑一下,道:“单靠勇武决敌不过智慧,你得记着我这句话。”
她迅速地爬起来,好在都是和衣而睡,同时以她们的身手,也不须换夜行衣。
两人下床,把包袱斜系在背上,宝剑则交叉着也插在背后。朱玲轻轻道:“这个庄内一定甚多巧妙埋伏,你要加倍小心,咱们如今出去,擒贼先擒王,只要把那两个首脑擒住,还怕找不回宫天抚么?”
房外静寂如死,万籁无声,大概天气转暖,故此连北风也停止吹刮。朱玲又道:“这是你第一次真个与人动手,心中不免会惊慌。但你只须沉住气,下次你就好得多了。”
上官兰道:“姑姑,我真有点害怕……”她的声音也有点颤抖。
“别紧张,那些人并没有什么可怕的!告诉你那个庄主外号是恶樵夫,姓金名穆,以前是碧鸡山总舵的副总舵主。现在调出来独当一面,这家伙如果知道是我,准保弃械而逃。”
上官兰听了胆气一壮,道:“姑姑一会儿让我先动手,你好在后面接应!”
朱玲伸手抚了她的秀发,道:“只要你不紧张就成了,动手时最好别使出我教的招数。”
且说那宫天抚自个儿坐在一间密室中,一方面冷静地筹思脱身之计,一方面却怒气冲天,只因这一趟太过丢面子,第一次和朱玲等踏入江湖,便自遭了暗算,自己枉有惊天动地的武功,哪知却一筹莫展!
原来他已瞧出这个密室四面尽皆是极厚的钢板镶壁,他要破室而出,势比登天还难。同时他仍坐在椅上,四个钢箍纹风不动地箍住他四肢脉门。
闷坐了好久,对面钢壁上响动一声,开了半尺大的窗口。同时在侧面也开了一个半尺的窗口,一道黄色的灯光射进来。宫天抚把眼睛一闭,一方面不让敌人看出他的精神如何。一方面免得被灯光照花了眼睛,等会儿看不见东西。
大概外面是恶樵夫金穆和陈雷两人交换着瞧完他,然后听到他们窃窃私语道:“这厮大概是装死。”
“他的武功真高,一路上我已细察清楚。”
“但他挣不出咱们的神仙椅呢,那包袱仍在背上么?”
“是的,咱们必须问出他的来历,然后才好动他的东西。”后面这一句声音较大,分明想他听见。
宫天抚忖道:“这两个狡猾的家伙,想问出我的师承来历,然后好摆布我,哼!我的来历怎能教你们知道?”
只听他们又道:“算啦,一旦问出有渊源的,咱们这笔财岂不是落了空?”
“我以为还是问清楚好些,别替玄阴教惹下不明不白的仇敌。”
这可是金穆的声音,只听他跟着大声道:“朋友你尊师何人?”宫天抚睬也不睬。
恶樵夫金穆又问了一声,室中仍然一片寂然,陈雷冷笑一声,道:“干脆宰了算啦!”
金穆道:“朋友你可别自误,本庄这个钢室,总共方圆不过丈半左右,本庄主只须下个命令,或水或火,取你性命不过举手之劳!听这位陈兄说,你武功已得真传,并非俗士,是以本庄主多问这一句。”
宫天抚为之一惊,忖道:“我打算等他们进来,这才暴起伤敌,自信这四个钢箍虽不能一齐绷断,最少也能腾出双手,那时节只要擒住一个,还愁出不了此室?可是人家若是用水淹火烧之计,我宫天抚今日便得丧身此庄。”
然而他想过又想,却不知玄阴教和武林哪一派有渊源,故此他想假报也不成功。其实他纵然说得出假话,却正好堕入圈套。原来金穆和陈雷来时商量过一阵,陈雷坚持说这个宫姓美书生身手之高,不容忽视,一路上他曾屡次细察,证明此人武功远在自己之上。
金穆一听可就不敢大意,商议好设法骗他说出师承来历,不管他说的是哪一派,都装出有交情的样子,进室去说是要放开他,冷不防把他穴道点住。此计定得甚毒,宫天抚只要一报出人名,势必中计无疑。只因宫天抚绝想不到以这两人还会使用这么卑鄙的手段,故此一定防备不及……
这时宫天抚既然答不上来,金、陈两人反而疑心大动,金穆拉了陈雷到一旁,道:“这厮的师门说不出来,定与本教有仇,以我之见,一把火烧死这厮,干手净脚,岂不最妙。”
陈雷道:“火烧么?不太好吧,珠宝之类可架不住火烧呀,不如用水淹死他!”
金穆摇首道:“内功真好的人,能够伏在水中十天八天还不死,夜长梦多,咱们要干的话,就得彻底一些!免得由这厮身上引来了能手,把他救了出去,咱们以后还有面目见人么?”
陈雷这时不好坚持,以免金穆说他贪财,想了一想,道:“那厮如挣不出神仙椅的钢箍,咱们便不须费事!”
金穆道:“咱们如何能够知道?”
陈雷道:“请看我的手段。”
两人走到钢室外面,陈雷暴声道:“庄主,这厮不敢自报姓名,必定包藏祸心,一把火烧死,倒也干净!”
金穆大声道:“好,来人呀!”
宫天抚大吃一惊,也不知是诈,暗中运集全身功力,蓦然吐气开声,四肢一震。
暴响一声,四个钢箍完全炸碎。他跳起来,运动三阳功,举掌一拍。
外面两人闭窗不迭,只听“轰”然一响,房屋摇震。
陈雷咋舌道:“好厉害,这厮是谁?功力之高我陈某委实平生未见。”
钢室内只响了一声,便没有第二下,金穆冷笑道:“那厮也许怕耗损元气,不敢再胡乱出手。”
只见一个身手矫捷的壮汉冲来,道:“启禀庄主,有两个夜行人已闯入内宅……”言犹未毕,又有一人报导:“那对夫妇已经失踪。”
原来此庄内到处都有消息埋伏,是以有人掠过布有讯号网的屋顶,庄中便已知道。又有一人来报导:“那两夜行人在内宅徘徊一阵之后,似因听到刚才声响,已回到此处上面的屋顶。”
恶樵夫金穆冷笑道:“陈兄咱们都走了眼啦,你且在此监视这厮,立即用火烧死他。我上去将那两人擒住。”
陈雷道:“金兄请便。”眼见金穆走了,便下令放火。
宫天抚在室内咬牙切齿,十分愤怒,但早先试过一下,情知钢壁极厚,凭他未练成的三阳功,势难击倒钢壁,只好站在那儿瞪眼睛。忽然嗅到一阵油味,定睛一看,敢情钢壁四面现出好些小孔,这时汩汩流出火油来。眨眼工夫,整个地面都流满火油,然后屋顶和壁间都开了小洞,抛下一束束的柴木。他觑准时机,一掌击出。一个小洞传来一声惨叫,原来他的掌力穿洞而过,把那塞柴木进来的人击伤。
但这一次之后,人家已有防备,小洞口一开即闭,已落下一束木柴。宫天抚无可如何,正在生气,眼前一亮,原来一道火光,直射进来。这道火光可是一种火药,燃着之后才喷进来,因此他无法击灭,转眼间地上已燃着一大片。火光熊熊,照映出这个俊美书生面庞。烈火蔓延得甚快,晃眼间已成了火海。
恶樵夫金穆出了地窖,大马金刀地走出院子,手中托住那枝旱烟管,还在抽着。风声飒然,一条人影电射下来,落在他面前四尺之处。金穆举目一瞧,便冷冷道:“小娘子你夤夜持剑乱闯,究有何意?你丈夫呢?怎不现身下来?”
来人正是少妇装束的上官兰,她可想不到人家一张嘴,便说穿了朱玲隐伏在一旁的事,不由得一愣。
但朱玲并没有现身,因此她只好不作答复,娇叱一声“看招”,一剑刺去。
金穆暗中一凛。敢情这个美貌的少妇已得能人真传,剑上力量不比等闲,出招便是武当派的九宫剑法,当下浓眉一皱,极快地盘算好必须尽力拾下这个女人,然后再对付另外一个,否则胜败尚在未知之数。当下手中镔铁旱烟管起处,使出一手怪招,脚踏奇门方位,烟管尖端似左实右,疾取对方右肩“气户穴”。这一招又快又怪,乃是鬼母指点他的几招杀手之一。
上官兰一迈步,恰好反欺到他左边,刷刷刷连发三剑,顿时把恶樵夫金穆迫到墙根。金穆这一惊非同小可,敢情上官兰连发三剑,却没有一剑是武当派的招数。
那恶樵夫金穆身经百战,阅历丰富已极,这时已看出这个清丽如花的少妇,头一剑是峨嵋剑法,第二剑是少林招数,第三剑乃是昆仑派剑法。三剑俱都真力外溢,显然不是偷招之流可比。
这三剑本已够奇,但最使金穆骇然的是他使的一招,乃是鬼母亲自指拨的数着杀手之一,最厉害在于脚下方位,出乎敌人意料之外,极难脱出他招数威力范围。哪知这个少妇一迈步,轻轻易易便事先趋避了以后的险窘,反而连发三招,把他迫得差点儿贴在院墙上。其实上官兰乃是朱玲亲自传授技艺,对于鬼母的路数脚法,如何会不晓得?
金穆惊骇之余,旱烟管一捧,使出成名多年的关东索家十二路旱烟管手法,只见他“斜阳封”、“锁喉箭”、“沙鸟独飞”一连三大绝招,竟把上官兰迫退三步。
上官兰拆了这三招之后,胆气陡壮,清叱一声,剑上光华倏盛,一招“登山赶月”,剑尖一滑,直指敌人大腿上的“伏兔穴”。
金穆又是大吃一惊,敢情上官兰这一招,乃是崆峒派阴阳剑法中的妙着。他真不知这个少妇识得多少派的武功,忙忙撤身横闪。猛觉剑尖嘶风之声,追袭右胁,疾如陀螺般一旋身,故意露个破绽。果然剑光如练,分心刺入。
他大喝一声,猛可一卸步,手中旱烟管挟着猛烈风声,直砸向上官兰头颅。这一招虽快,但上官兰剑势已成,本可刺穿他的肩头。不过若是这样,却怕也难躲对方旱烟管迎头一击。纵然因稍占优势,避开要害,但伤势总不能免。
上官兰可不能和他换命,撤剑一架。“叮”地微响,两般兵器粘在一起。金穆斜眉一笑,运力下压,上官兰内力逊他一筹,嗳了一声,长剑下沉尺许,但居然挺住不再下沉。
一条人影倏然跳下院中,脚下弄出一点儿声息,金穆一看这人正上唇留着小胡子的书生石灵,便冷笑一声,不把他放在心上。黑影中钻出两人,各持兵器,恶樵夫金穆大喝道:“尔等守在一旁,不必过来。”
朱玲冷笑忖道:“好个老江湖也中了我的计谋,等会见你就尝到滋味了。”当下呛一声撤出太白剑,黑暗中闪起一道白虹,冷气森森,侵人肌肤。
金穆道:“好剑,合该换个主儿啦!”原来大凡名家撤剑,自有风度。朱玲却手颤身歪,分明不是材料。
朱玲猛一伸剑刺去,金穆旱烟管一移,登时又把她的太白剑粘住。上官兰本以为可以透一口气,谁知朱玲却不发力,只帮一点儿忙,故此她仍然觉得沉重不堪!
朱玲愤愤骂道:“今晚一定要荡平你这一家贼巢,如今升平世界,居然敢胡作乱为,你们有王法没有?”
恶樵夫金穆嘿嘿冷笑,道:“酸丁闭嘴,大爷就是王法!”
朱玲恨声道:“你把那个宫兄怎样了?”
“嘿嘿,他武功果然高明,但他焉能逃得过天罗地网,现在也许已给火烧死啦!”
朱玲一听心血上涌,差点儿挥剑真打,但她一向心计绝工,猛一转念忖道:“我不能轻举妄动,只因我不知机关在什么地方,纵然杀死这厮,我还得找个大半天,这样宫天抚必死无疑!还是另想计策救他眼前灾难。”
恶樵夫金穆的旱烟管逐渐得势,缓缓压下去。上官兰气力已竭,娇喘呼呼。
他得意洋洋地道:“那厮叫什么名字?喂,小娘子你可知道他是哪一派的?”上官兰有口难言,心中直在怪朱玲不赶快出力。
朱玲蓦地灵机一触,直着嗓子骂道:“你们这些贼人总有一天遭报,那个被你们烧死的是石轩中大侠,小心他的朋友们替他报仇。”
金穆为之一愣,上官兰乘机反攻,把旱烟管托高大半尺。他道:“小子胡说八道,那厮怎是石轩中?”
朱玲记得当日在碧鸡山上,金穆没有在场看到石轩中真面目,于是冷笑一声,道:“他就是石大侠!”
恶樵夫金穆这一下可惊得呆了,上官兰乘这机会,剑尖一颤,“嗡”地轻响一声,金穆旱烟管直跳起两尺之高。
朱玲暗暗恼那上官兰不懂事,只因她是个心窍玲珑的人,一看金穆吃惊之状,便明白他说架火焚烧宫天抚之事不假。这时正应该放松一步,好让金穆抽身传令停止火攻,假如还来得及的话。
只见上官兰剑光如虹,连攻三招。金穆急忙招架,竟现出凌乱的样子。要知石轩中乃是玄阴教第一个大对头,今日若是金穆擒捉到此人,不但立刻得到鬼母重用和厚赏,在江湖上他金穆可就算得一鸣惊人,名扬寰宇了。故此他立刻现出心神不属的样子。
这刻正好是宫天抚甚为危急,满地皆火之际,性命悬在指顾之间。可是上官兰剑发如风,每一招无不精妙异常。金穆到底是个老江湖,马上已收摄心神,运足内力,硬架两招,把上官兰震得剑势一挫。
上官兰又急又愧,她本以为朱玲刚才故意拿话哄得对方心神分散,以便让她把敌人收拾下。但她却没有办到,如何不愧急交集?
只见对方旱烟斜捣腰胁大穴,身形微侧。当下已知敌人要踏什么方位,暗自银牙一咬,左手伸出去推开敌人旱烟管,右手剑疾如毒蛇般刺出,配上脚下方位,妙到毫巅地递入敌人胸前。
金穆使的正是鬼母所传诛杀着之一,这时不但被破,还惹火上身,危殆无比。万般无奈之下,疾的滑步侧身,猛觉剑斜掠,已到了后颈,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
朱玲恰在这时,冲过来举剑劈下,无巧不巧反把上官兰撞了一下,剑势稍歪。
恶樵夫金穆为之大喜,乘机避开这致命的一剑。饶他躲得快,头皮一凉,已被长剑削断一绺头发。
他心中虽怒不可遏,但事情有缓急轻重,此刻纵然让这两人逃走,料他们也逃不了多远。当机立断,马上一跃入室,大声传令道:“请陈总巡立刻停止火攻!”
屋内有人噭然应了,朱玲登时又喜又忧,喜的是自己妙计已售,敌人已下令停止火攻。忧的是时候已耽搁了不少,只怕宫天抚早已被火烧死。
恶樵夫金穆又跃出院子,冷笑自语道:“除非是这小子,哪能有这等功力?”
原来当日制造这批“神仙椅”时,经过多次试验,六堂香主当中,没有一位能够把四个钢箍一下震碎。外三堂三位香主都只能震碎一个。内三堂的三位功力较深,也仅能震碎两个。
当年石轩中大闹禁宫,孤剑纵横往来,连大内群雄之首的乾坤子母圈诸葛太真也抵挡不住,石轩中自经这一仗,名扬天下。除了他出现之外,当世之间,还有哪个年纪如此轻的人,具有这等身手功力?金穆越想越对,不由得仰天长笑。
朱玲因不知详情如何,只好继续装佯,故意道:“哼!你们敢把石大侠怎样?他的朋友过几日便来取你首级。”
金穆大怒道:“你少胡说八道,石轩中这刻不知已化了灰也未!”
上官兰一听真个急了,过来狠狠举剑就砍。金穆记恨剑削头发之仇,更不多言,施展平生技艺,那支旱烟管使得有如毒蛇出洞,凌厉无比。
眨眼间上官兰已狼狈异常,险状百出。朱玲心中为难之极,这刻她若一露真相,因而被敌人惊觉,宫天抚性命可虞,但她不出手也不行,只因上官兰情势危殆,她岂能眼睁睁地由她被人杀死?上官兰经验不够,故此能赢而不能输,现在一落在下风,便心散神乱,手中剑破绽百出。
朱玲咬牙叱喝一声,挺剑上前,剑招还未发出。屋内一个人蹿出来,问道:“金兄是你传的命令么?”
金穆立刻收回旱烟管,退开几步,回顾道:“不错,这可是大功一件,你……”
他说话时,朱玲已揽住上官兰香肩,在那耳边道:“我们听完他们的问答,知悉宫天抚生死之后,便立刻跳上屋顶,若然他已死了,嘿……”她冷嘿一声,阴森无比,杀气腾腾,听得上官兰也为之打个冷战。
“那厮已烧死了没有?”金穆继续问道。
这句问话,正也是朱玲、上官兰两人的心声,是以她们都睁大眼睛,静听陈雷回答。
陈雷耸耸肩头,道:“你的命令来得太迟了,我虽立刻停止再加火,同时开放气孔,好教那厮不至于闷死,但我看八成儿活不成了。”
朱玲这一下有如扬子江畔失足,又似万丈高楼坠下,脑中“轰”的一声,但觉昏昏沉沉。
恶樵夫金穆也十分着急,匆匆道:“那厮可是石轩中哪,咱们快去瞧瞧。”
“什么?”陈雷大叫一声,但身形已随着金穆闪入屋去。
上官兰想跟他们进屋,但朱玲身形摇晃,她得先扶住玲姑姑,眼看那两人闪入屋后,便无声息。她低低叫道:“玲姑姑,玲姑姑,你怎么啦?”一面问她,一面替她推揉胸口穴道。
朱玲猛然清醒,四顾道:“他们呢?”
上官兰答道:“他们已进屋去看宫大叔了。”
朱玲喝声“追”,身形一晃,已入了屋子。她施展这种类似内家移形换位的上乘功夫,忘了反震之力甚强,竟把上官兰震得哎一声,弹开四五步。
上官兰打个千斤坠,稳住身形,然后发力欲追,猛觉运力之时,真气腾涌,暗自大惊,知道自己气力用尽,复又被朱玲震了一下,虽然不是受伤,但真气不调,必须调气养息,过一阵才能恢复。
一抬眼朱玲已隐去踪迹,这时她可不能慌忙,原式站在地上,暗自运气。
屋上跳下一人,只见此人其貌不扬,窄额尖腮,两眼如鼠,可是武功却不错,落地时声息毫无。
他咧嘴l奸笑一下,蹑足走到上官兰背后,慢慢伸手指着她背上穴道,直到离她后背不及半尺,然后闪电般戳去。
上官兰猛可一旋身,右肘撞将出去。那人哎了半声,小臂疼痛欲折,原来已被上官兰一肘撞着,但上官兰也被他点了穴道,身形直跌下地去。
因这院子中的地面乃是三合土所筑,坚硬无比。上官兰跌下去,可能鼻肿头破,花容月貌变成丑罗刹。
那人猛一伸臂,揪住她的臂膀,上官兰身躯一转,滚入他的怀中,却好碰着他的痛臂。此人疼得又哎了一声,额上冒出热汗。
但此人仍不放手,硬是挺住疼痛,单用左臂把她拦腰抱起,口中喃喃道:“大爷若不是为了你的容貌,管你跌死呢!”
黑夜中只见此人挟着上官兰,跃上屋顶,一径出庄而去。
书中交代,这人姓燕名亮,有个外号是粉燕子,大江南北闻名痛恨,只因这粉燕子燕亮早年出身下五门,后来不知怎的学了一身绝艺,轻功特高,同时囊中三十二只特制喂毒银燕子,手法奇妙非常。是以近四五年来崛起江湖,虽是采花杀人,无恶不作,但至今逍遥法外,连侠义中人也找他不着。
最近半年,他从北方来到湖南,闹了两件案子,使得荆楚派高手云梦双侠刘兼和张浦两人,率领门下数弟子,到处搜捕粉燕子燕亮。这些人淫贼燕亮俱都不怕,独独怕那云梦双侠中的老大刘兼一个弟子,姓罗名章,外号飞猿。罗章因为得到衡山派猿长老传授绝艺,一手猿公剑独步江南,为近年后起之秀中的佼佼者。同时玄阴教也放出风声,要捉拿这个江湖不齿的败类。粉燕子燕亮见势头不对,他可认识那恶樵夫金穆,是以立刻来找他,希望玄阴教对他网开一面。
今晚刚刚来到,还未见着恶樵夫金穆,便发生了这遭事。刚巧他碰上了上官兰独立院中,她那花容月貌登时令他神智昏迷,便下来把上官兰劫走。
且说朱玲闪入屋中,一看这个厅子并无异状,便直闯二道门。转出这道门,赫然一条长廊,不知通到哪里去。廊边露天空地,植着不少花卉,当中还有一座小亭。
她张望一下,不知何去何从,这时她心急如焚,便仗剑从长廊直奔过去。长廊尽处是个月亮门,出去一看,花木扶疏,亭阁楼榭隐现其间。偌大的地方,到哪儿去找秘密机关的入口?
朱玲银牙一咬,想道:“如今已无法子,不如闯入内宅,找到金穆的内眷,便用这些妇女要挟金穆,逼他供出实在详情。”放眼一看,所有的屋子都黑沉沉,地方又大,如何能在短时间内找到金穆的内眷?不觉为之踌躇起来。
忽地想起上官兰没有跟来,甚是奇怪,忖道:“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且找到兰儿,才和她一起入内宅搜寻。”
于是又转身奔回去,这时她只要出到院子,一见上官兰失踪,势必登高瞭望,便还来得及见到淫贼挟她出庄的身影。但她刚奔到廊畔那座亭子时,忽听“喀登”一响,从亭子中传出来。
朱玲的反应何等灵敏,蓦然一提气,身形飘飘飞起,贴在亭上檐边。
只听亭子中传出异声,似是有人掀起石板的声音,跟着便听到金穆的口音道:“我的确是太兴奋了,故此匆匆忙忙的,其实应该先把那对夫妇捆住再看也不迟!”
朱玲在亭顶忖道:“走着瞧吧,看毕竟谁捆住谁。秘密机关的入口既已找到,但他可没说出宫天抚的生死呢。”
蓦然自家怔了一下,只因她忽然想到这次一闻宫天抚的凶险消息,登时便急成这个样子。现在居然连兰儿也丢下不管,难道他在她心中的地位是这么重要?
记得昔年她回天碧鸡山,不久便听到石轩中葬身南连江泉眼的消息。那时候她虽是肝肠寸断,但似乎还不及如今表现得热切激动。那么难道说,石轩中也比不上宫天抚?
这个自我反省的念头,使她苦恼无比,连陈雷对金穆说些什么话也没有听到。
那两人转眼已是出二道门,转出大厅。
她苦恼地想道:“我可不能够这样啊,我怎能对他这么好?日后又如何解决了?咳,他现在如果死了,那也好,让我来替他报仇……”想到这里,心中异常悲哀,彷佛宫天抚已经真个死了似的。想是这样想,但她总得下去瞧瞧呀!
忽见一个人从外面进来,幸亏她眼快,早一步窜到亭子那边的顶盖,来人敢情是两省总巡查陈雷。他望见亭子毫无异状,便大为放心,咕哝道:“真是石轩中的话,虽是大功一件,可是那一堆珠宝却不是我的了。”
原来这时他们也不知钢室内的人死了没有,只因早先他们匆匆一瞥,却因室中烟雾弥漫,根本看不到什么。他们料想那假石轩中纵然不死,但也得熏昏,便下令把那半尺方圆的洞也打开,好把烟雾放出来。不过,纵使石轩中仍然活着,这半尺方圆的小洞,也逃不出来。之后,他们便又匆匆上来,打算把朱玲、上官兰这对假夫妇擒捉住。
哪知上来一看,人影全无。恶樵夫金穆立刻决定自己追赶那两人,由陈雷留在庄中,看守石轩中。
陈雷走入亭中,正在咕咕哝哝,弯腰把一个石圆墩向右一扳,喀喀一声之后,便又向左方扳去。地面响了一声,却无动静,只见他把另一个石圆墩推开半丈,地上有个铁环。
他一面弄,一面还在想着石轩中到底死掉与否?忽听身后有人问道:“合字请问那石轩中可曾死了?”
他道:“还不知道……”蓦地一惊,回首瞧看。只见那对夫妇中的书生,正站在他身后。
“别忙!”朱玲道:“咱们都是在线的,规矩是见者有份,我倒不管那石轩中是生是死,主要还是怕那些珠宝都让火烧坏了!”
须知黑道上真有这种规矩,不过玄阴教早就独行独断,不管这一套。不过陈雷出身绿林道,习染已久,其次这小子一向财迷心窍,要论起他如今的积蓄,何止巨万!但他仍然见钱眼开,总是不嫌钱多。
这时陈雷一怔,道:“好哇,敢情你早就吊住这厮了!但这一回你我都别想沾沾那些珠宝!”
朱玲心中好笑,踏前一步,道:“为什么呢?”
“唉!若然那厮是石轩中,此事可得上闻教主,谁还敢动他的东西?”
忽见朱玲眼中射出凶光,这陈雷虽然一时之间吃她蒙住,但到底是个老江湖,蓦然退纵出亭外,在这一纵之际,抽出白森森一道光华,却是柄软得可以盘在腰间的缅刀。朱玲忖道:“这厮真精灵,我决不能放过他而下地道救人。”
同时见陈雷使的乃是削铁如泥的缅刀,这才明白他何以不贪自己宝剑之故。她含笑道:“合字别慌,我见你使这桩兵刃,忽然想起一个人,我提一下,看看是否攀得上交情!”
陈雷冷笑道:“你说吧。”
“我提的那位,也是使缅刀的名家,昔年在关外时,我们结为忘年之交。此人姓邓名牧,外号雪山雕,听说如今已在贵教中效力,又曾有一段时间,在大内当差。”
陈雷啊了一声,道:“那是敝教外三堂香主之一,噫,他老人家前两天经过此地,如今却不知去向。”
“你看,这就对了,我也得到他的行踪消息,准备在衡州与他会面!”朱玲这叫做打蛇随棍上,她堆起满面笑容,走下亭去。
朱玲的打算是不惜用任何手段,冷不防把陈雷弄死,决不让他有机会报警,然后悄悄进入地道营救宫天抚。眼看对方已经中计,她只要走到他面前,倏然剑掌兼施,当然可以立毙敌人。因为根本上她的技艺比陈雷高出一大截!
陈雷果真被她哄住,最低限度他不能用强横的态度盘问朱玲,当下也堆笑道:“原来尊驾和邓香主相识,说起来咱们算得上是自己人啦。”
朱玲一直走过去,面上堆满笑容,一面道:“可不是吗,我现在正焦虑一会儿怎样向庄主解释误会哩……”她向他挤挤眼睛,故作豪放地笑起来。当然她不能走得太快,免得人家生疑,是以这刻还离着陈雷半丈之远。
她只要再迈两步,便可一击毙敌。正在此时,陈雷忽然脸色一变,横跃丈许,戳指喝道:“朋友你实在是什么人?”
朱玲被他突如其来的动作弄胡涂了,含含糊糊地道:“我是什么人?你不知道么?”
陈雷面罩严霜,冷冷道:“你识得邓香主的名声,有何奇怪,莫非我这样便可相信你?”
朱玲心中暗喜,想道:“原来你仅仅这样疑心起来,这还不易么?邓牧加入玄阴教时,你还未曾入教呢!”
陈雷又道:“请你先回答我两个问题,第一,你真实姓名是什么?第二,你今年尊庚若干?”
朱玲故作从容,并不走过去,道:“我的确姓石,名灵,往年多在关外混迹,是以识得邓兄。今年算起来年纪也不算太小,已是三十二岁的人了。”
陈雷面上掠过一丝冷笑,道:“好极了!”
朱玲一听,不觉疑惑想道:“这厮声调诡异,难道已听出我话中有假?”
“那么邓香主的身量约摸多高?面貌上有什么特征没有?”
朱玲眉头略皱,道:“他……他身量颇为高大,面貌却没有什么特征。记得昔年在关外,他老是爱穿一袭暗青缎面皮袍子,气度甚觉威严。”
陈雷也为之皱皱眉,这分明是朱玲已说得十分确切,证明无讹。
朱玲便又含笑走过去,一面道:“寨主可相信了我的话么?”
陈雷倏然举刀道:“你说得太对了,反而教我不能相信。”
“这是怎么啦?”朱玲愕然问道,这次她的惊愕神色,倒是出乎真情。同时她也有点气恼,若不是为了怕被他发讯报警,根本就用不着啰嗦。
陈雷冷笑道:“你说你三十二岁,但我怎样看都不像!呔,你还不从实招来,本总巡可不再留情。”
朱玲举手摸摸上唇的胡须,猛可一愣,也情她早先装笑容装得太厉害,以至那一抹胡须歪下来,差点就要掉下地上。这时她才知道人家早在她须歪之时,便明白她乃是诳语,后来多问几句,不过是套多点线索而已。心中一阵羞愤迸发,怒嘿一声,倏然疾冲过去。
她的身法快得异乎寻常,陈雷为之一震,疾忙挥刀虚架一招,斜纵开去。
朱玲激起一腔怒气,左手扯掉假须,大喝道:“你不是想擒捉石轩中报功么?先找我好了!”喝声中,剑光如虹,电射而去。陈雷蓦然缅刀撒手,直扔过来,跟着纵出围墙外。朱玲暗自叫声不好……
原来陈雷这一刀力量刚猛之极,又是把削铁如泥的宝刀,挡她一挡,自无问题。同时他跳进墙去的身形落得古怪,竟是贴墙而坠。故此朱玲立刻想到围墙那边定有逃走之路,可以立刻隐蔽身形。
如此一来,朱玲便势难把他杀了灭口。好个朱玲!不愧是碧鸡山玄阴教一凤三鬼中的突出人物,只见她抢前半步,左手一绰,巧妙绝伦地绰住那柄缅刀。
这时陈雷已贴墙而坠,刚好头颅从墙上消失,已看不见他一点踪影。
朱玲清叱一声,运足全身功力,聚集剑上,以大摔碑手法,太白剑脱手,力掷而去。一道白虹劲射而去,“嚓”地微响一声,整柄宝剑完全没入墙中,那边传来一声惨叫,然后便一阵寂然。
朱玲在惨叫声起时,已跃到墙上,俯首一看,便冷笑一声。只见陈雷贴在墙上,双脚离地尚有尺许。
在他脚下的地面,一块薄薄的青石板已掀开来,露出一个入口。原来这个入口的机关和亭子中的入口机关相连,那边只要一移动石圆墩,这边的青石板便自动掀开。倘若陈雷真个跳落入口里,地下复道重迭,朱玲再也找他不着。
却见陈雷身形一沉,噗通连声滚下地道,溅得满地鲜血。原来朱玲一剑掷出,那太白剑锋利无匹,居然透墙而过。陈雷的身形正好贴墙而坠,冷不防有利剑从墙壁中刺出来,恰好刺在胸口上。顿时惨叫一声,立刻丧命。到朱玲上墙瞧看结果时,因太白剑过于锋利,陈雷的尸身吊不住,破开一道口子,尸首跌坠地道入口。
朱玲纵回这边墙下,先把缅刀扣在腰间的衣服底下,然后把自己的太白剑拔出来,左手倒持着,一径跃到亭子里。她弯腰抓住地面那个铁环,运力一拉,“咔嚓”一声,一方石板应手而起,露出黑黝黝的洞口。她静静倾听一会,四下俱无声响,便从石阶走下地道去。
转一个弯,赫然从前面透来微弱的灯光,于是她瞧清楚四壁俱是大石筑的甬道,只有七尺来宽,一丈来高。暗忖道:“只要前后都掉下一面钢板,便是神仙也得束手被困。”于是不免怀着戒心,十分谨慎地往前走。
幸好走了数丈,还没有什么动静。转一个弯,只见一面钢板挡住走路。她走近去,只见这块巨大的钢板上有好几处半尺方圆的小块,突将出来。
当下停步在这块阻路钢板前,细一思索,忽然发觉这儿正是三人中伏被困的厅的下面。心中一阵惊喜,想道:“宫天抚掉下来,不正好被困在这块钢板里面么?”
于是举手去掀那些突出的小门,但不论她掀或推,都纹风不动。又试着向左右移,仍然不动,往上一推,却应手而起,露出一个洞口来。
洞口中立刻冒出烟来,不过并不十分浓厚。她的心大跳一通,现在马上可以知道宫天抚是生是死之谜了。她先低声叫一声“宫天抚”,里面毫无声息,于是提高嗓子又叫了一声。
里面静寂如死,连呻吟声都没有。朱玲的心直往下沉,急急凑到洞口一张。只见里面犹有余火,一阵热流扑面。她眼光一扫过这间只有一方丈大小的钢室,室中一切纤毫毕露。她闷哼了一声,呆住不动。
敢情在钢室角落有具尸体,衣服已完全烧毁,身躯也焦黑了大半,面目完全看不出来,头发更加不存。她彷佛嗅到肉焦香味,熏得她一阵恶心,想呕吐又呕不出来。看这个人惨死之状,不用说也知是那文武全才、潇洒倜傥的宫天抚!
室顶烟气昏腾,兀自未散。朱玲打个冷战,眼泪有如江水滔滔而流!这时她才明白那金穆、陈雷两人不知宫天抚生死之故,敢情是早先火烟太浓,是以瞧不清楚。
好些年来她已没有眼泪可流,如今才让泪水畅快地洒滴下来!然而世事是这么残酷,天道如是不仁,老是教她在噩梦似的人生中,尝遍生离死别的痛苦!
泪光模糊中,她举剑乱斫,那么厚的钢板,也被太白剑斫缺深深的裂口。
她忽然发觉自己这种下意识的行为,是太过愚蠢了。当务之急,还是赶紧找到敌人,把他们屠宰清光,然后再把这个庄院付诸一炬。
于是她返身直奔,岂知转个弯,陡见前面一扇钢板挡住去路。扑到切近,用剑柄轻击,不禁大吃一惊,原来这扇钢板不但甚厚,后面像还有石壁,因此声音沉闷。
正在发急,身后轰隆一响,震耳欲聋,朱玲不必回顾,也知另有一扇钢板掉下来,封住去路。
她不必去动身后那扇钢板的脑筋,只因纵然破得开这一道,但再过去还有困住宫天抚的钢室拦路。
现在看来她已变成瓮中之鳖,插翅也难以飞出樊笼。她长叹一声,眼光惘然地落在手中那柄宝剑上。不祥的血腥的阴影,笼罩在她心头。
这一回她不会像上次那样,因全身无力而放弃了自戕之念。相反的在这暗无天日的地道中,谁也来不及挽救她!在顷刻间,她已下了决心。生命原无足恋,往昔屡屡挣扎,不过是有点不甘心罢了!
好几只蚂蚁爬上她的脚面,她轻轻一抖,便把那几只特别大的蚂蚁抖落地上。她也懒得弄死这些可厌的东西,幽幽苦笑一声……
就在朱玲决心自杀之时,在五六里外的湘潭城边,一座已破落残败的神祠中,这时散布着昏暗的烛光。
上官兰心中明白,但全身瘫软,躺在破旧的长供桌上。她虽是睁大眼睛,但只能看见蛛网尘封的屋顶。
粉燕子燕亮蹲在地上,一面在解开自己的包袱,一面狞笑道:“那么你是那方家庄被困的石轩中的小老婆子,对么?”
原来这淫贼把上官兰一直背到此地,便问她和什么人一同到方家庄。上官兰这刻已知石轩中在江湖上真是威名赫赫,便说出他的名字。
燕亮当时真的有如当头被浇了一盆冰水,但俗语说得好,所谓色胆包天,没有其它的胆子会比色胆更大。
这粉燕子燕亮自我沉吟一下,忖道:“我横竖要托庇玄阴教下,那石轩中再厉害,也敌不过玄阴教主鬼母的黑鸠杖,管他娘的,干了再说。”
于是便蹲下去解开包袱,一面狞笑着说了上面那句话。上官兰悲恨攻心,却又不能转动,连自杀也办不到。
供桌下有人咿唔一声,好梦方醒地打个呵欠。粉燕子燕亮大吃一惊,想道:“我真荒唐,竟没想到这等所在,多半有叫化子盘踞!”抬眼见那供桌还垂着破幔,故此无法看得真切。便大声道:“喂,什么人躲在桌子下?”
那破幔一掀,钻出一个头颅,燕亮见了暗自一骇。原来这个头颅上的头发梳得油亮,眉浓鼻挺,气概轩昂,年纪尚轻,并非蓬首垢面的花子。
那人怒道:“你是谁?把大爷好梦吵醒!”
上官兰在供桌上心急起来,只因这人问这么一句,已表示出他并不知道供桌上面有人。她想弄出一点声息,这么一来,那人发觉了,粉燕子燕亮这淫贼总不能立刻奸淫她!
燕亮左手摸出一只巧制喂毒银燕,冷冷道:“给我滚出去!”
那人见他凶残异常,哎一声,反而缩回桌底。燕亮久经大敌,见那人动作甚快,不敢大意,退回几步,扬手发出一只银燕。桌底黑漆漆一片,他看不见那人躲在哪儿,但供桌下能有多大地方?他以特异手法,发出那只银燕作个弧形穿过供桌底。
银燕上的毒极为剧烈,见血封喉,淫贼打算弄死那人,省得多言。谁知银燕打入供桌之下,毫无声息,也不绕飞出来。
只听供桌底那人哎了一声,道:“这是什么?嘴巴好尖,把大爷蜇了一下!”
燕亮眉头一皱,奇怪那人何以还能说话。只见破幔呼地劈面卷来,他挥掌一劈,那破幔布面拂着他的臂膀,登时疼痛之极,如被棍子击了一下,心中大大凛骇。那人跟着钻出来,现出全身,向他嘻嘻而笑!
欲知此人是谁,以及朱玲上官兰和宫天抚三人后事如何?请看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