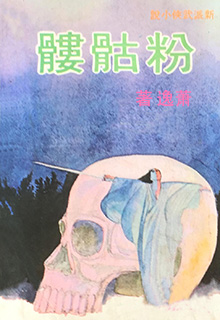皂班头张四把下剩的大部礼物押送回衙,向过于执禀报之后,因隔夜奉命应差,忙得连早点也没有顾得吃,“偏偏遇到这位老厌物(指况钟),会把那么好的上等酒席给退回来”,连他准备空着肚皮,分吃一点剩菜的想头都未如愿。
回完话出来,饿得肚子里直咕噜。知道本官辛苦了一天多,这一睡,至少要到黄昏后才起,便朝同伙差役招呼了一声,借着回家换衣服为由溜了出来。本意想找一个常去的小饭馆来顿白吃,填饱肚子回衙,再寻刑房书吏冯承谈心。
谁知刚到街上走不多远,道旁小巷内忽然低着头走来一人,脚底既轻,来势又急,不是闪避得快,差一点没有撞上。看出来人正是以赌博为生的小流氓娄阿鼠,脸上带着喜容,衣服也比以前整齐。连忙一把拉住道:“你这只‘小老虫’⑴,这样钻头不顾尾巴,阿是要去赶头刀?”
娄阿鼠见是张四,忙把脚步收住,随口答道:“我们是老弟兄,你为啥要‘触’我的‘霉头’?”
张四把眼微微一瞪道:“小贼不要和我装腔。我看你这样高兴,这两天一定得了不少彩头。你不请爷叔吃两顿,当时就给你看颜色。”
娄阿鼠把嘴一撇,诡笑道:“这半年多,我只是在白相场台(指赌场)给人家帮帮忙,拿点份头,啥地方来的油水?吃一顿没有关系。走!跟我到鸿源楼去,请你做一个饱死鬼。这样红眉毛,绿眼睛,我见得太多,用不着!”边说,边拉张四往城隍庙走去。双方口里不三不四,连说带笑骂,显得很近乎。
鸿源楼在城隍庙附近街上,南面临河,专卖酒菜和点心小吃。张、娄二人因还不到吃饭时候,叫了两个冷盘、一笼烧卖和两壶酒,边吃边谈。
娄阿鼠原因昨晚在茶馆里听书,听人传说熊友兰、苏戌娟一斩一绞已成定案,“钉封”一到就上法场。幸时心里一松,认定从此可以无事,就算多带上这两条命债,且等自己死后再说,不去管他。因说的人也是出于传闻,语焉不详,旁边还有两个乡邻均说此案判得冤枉,并说有人还要劝梁大嫂到苏州去上控等语。
娄阿鼠虽然常和差役们相交,早就打听出过于执办的案从来没有什么驳回。连经三审,都照原判,告到哪里去都是无用。到底事不关心,关心则乱,一面虽为自己庆幸,一面却想打听出一个真实消息。特意提前起床,往衙门口来寻相识差役,不料遇见张四。
知道这厮狠的是张嘴,除了倚势欺人,掉不出什么大枪花,三杯酒—下肚,什么话都肯说,今天身边又恰带得钱多,正好先灌他一个够,再问虚实。上来不住劝酒劝菜,等张四把一笼三十个烧卖吃完,又灌了半斤花雕,脸涨得和猪肝一样,才拿话引他道:“辰光业已不早,难道说你早起一点物事也弗曾吃?看你这种吃相,阿要狼形?”
张四把醉眼一翻道:“你晓得啥?断命的况钟老贼来了!我忙了—夜天,到这辰光连口茶都没有吃过。阿要气人?”
娄阿鼠心中微微一动,并未在意。接口又问:“这个老头子不是在苏州府吗,跑到我们无锡作啥?”
张四气道:“瞎,这个专管闲事的老贼,有啥说头!你应该晓得,他就是为了旧年冬天尤葫芦这件命案来的。”
娄阿鼠听到“尤葫芦”三字,心里便似着了一重锤!—向吃酒不上脸的鼠脸,立时涨得通红,脑子里直嗡嗡,前额上的两条青筋也凸了起来。等听完末两句,更是从脊梁骨起往上直发麻,刚端起来的酒杯也拿不稳。
张四见娄阿鼠抖着手端着一满杯酒,往下巴颏送,酒洒了好些在桌上,连忙一手接过,随口骂道:“猪猡!这样好酒,留给爷叔吃吧。你不会吃酒,偏要吃酒,醉得连酒杯也端不牢,阿要作孽?方才你还说我吃得狼形,你才真是贼腔……爷叔,起……起码还可以吃两斤……”张四劈面把娄阿鼠多半杯酒夺过往口里送。本来酒已过量,这一大口喝得又急,酒顺口角往下流,淋漓满胸,舌头也有点发短。
娄阿鼠听张四虽说他事情应该晓得,对他尚无疑意,觉着光怕不是事,假装镇静,抖着手把冷盆中吃剩的一块酱鸭骨头夹起,放在口里乱呷。赔着一脸诡笑问道:“这个老贼骨头不是苏州知府么?无锡县不归他管。我不相信有这种事,你倒讲给我听一听?”
张四酒醉之后,心也糊涂,便把昨日由过于执亲信人等口中得知犯人临刑呼冤和况钟深夜往击抚衙堂鼓,非要重审此案不可的经过,随问随答地一一说了。
娄阿鼠不等听完,二次心又发抖,毛骨悚然。暗中叫不迭的苦,心想:“我的老天爷!况钟是有名的活包公,什么事也瞒不过他。这件事我一定不得了!”继一想:“况钟虽然绰号活包公,从来没听说过他会日断阳,夜断阴,到底比真包公差得多。我杀人并无人晓得,身上既无血迹,家中又无凶器,怕他作啥?”自作宽解,心方略定,忽然想起那两粒灌铅的骰子!二次又急出了一身冷汗。暗骂:“这真是我的致命一伤!本来也曾打算半夜里撬开尤葫芦家的排门,到里面去把这两粒骰子偷出来扔掉,以防万一。
偏偏冬天太冷,稍微耽搁了几个月。热天人都在门口乘凉,有的小家小店还露宿在外,无从下手。秋后仿佛容易,斜对门又开了一家猪肉铺,比尤葫芦会做生意,本钱又足,每天半夜里,照例开着门在那里宰猪,直到天亮前后才洗剥干净,想在它对面撬门,决办不到。有时打算白天先去做好手脚,等肉铺刚一‘打烊’⑵,就去下手,偏又遇见那个‘小赤佬’倪阿根。他就住在尤家隔壁,我只一走过,他表面假客气,暗中好像对我很留神。再要遇上郑家那个大媳妇,她还要瞪我几眼,和别人唱隔壁戏,说上几句戳心话。秦家老鬼也是一见我就仿佛有气。再一想起事后去看验尸时所见尤葫芦的惨状,心里也是害怕。门户又被县里木条钉紧,加上封条,稍微露出一点马脚,更是自寻死路。并且行凶以后,虽因事前当众丢丑,不能再‘做生活’吃人,仗着脸皮老,会巴结,赌场老板又不肯得罪我这样深知他们根底的人,‘俸禄’照样有份。偶然下上两次冷注,也难得有一次输过。长年在赌场里过日子,吃好的,喝好的,还不断有钱进账,这是多么便宜舒服的事!每日天明回家,过午才起床就惦着往赌场里跑。人是越来越懒,什么都不想干。日子一久,胆也更大,又听说案情都照原判,只等熊、苏二人一死,万事皆休。没想到一时疏忽,这乱子恐怕还是要出在这两粒断命骰子上。”
越想越怕,越怕越后悔。胡思乱想了一阵,再看张四业已伏在桌上沉沉睡去。知道对方昨夜没睡,这一酒足饭饱,决喊不醒,并且此人酒后无德,强要把他喊醒,准发脾气。刚想溜走,忽然想到:“未来事情难料,不能省这一顿酒饭钱,和这疯狗做冤家。”便把堂倌唤来,一同连喊带拍。
见张四果然不醒,暗中伸手衣袋内,把所带的钱取了—半,再一把抓了出来,笑道:“这位老兄约我吃老酒,偏吃得这样醉,喊他不醒。我姓娄的不能不讲面子,白吃你们。可惜身边银钱不多,现在都付给你。如有富余,给你作小账。如果不够,给我记上一笔。我说话算数,到时准还。”说罢,把钱递过。流氓光棍对付公门中人照例要留一手,决不肯随便得罪的,虽然他把身边的钱藏起了一半没拿出来,并且心情太乱,走得非常慌,连有些场面话都没有顾得说。
堂倌把钱接过一数,照二人所吃点心酒菜价钱,差着一半还多。但这两个顾客,一是公差,一是流氓,都惹不起。对方居然付了一半钱,就等于是白拿。非但没有话说,反而连说:“足够,足够。”一路赔着笑脸,把这位顾客送走。
过于执以为凭自己的判断才能,这件凶杀案决不会有什么漏洞。就算有人挑剔,打算翻案,此事关系太大,两位最有力量的上司(指常州府和江苏臬台),也决不容它翻过来。先断定不会出错。忽然想起:“对头官声甚好,办事精明细致而有魄力,并且不畏权贵。如果没有一点把握,决不会这样冒失。莫要真个发现线索,却是可虑。”心又不安起来。刚愎任性的人,往往犯了罪恶而不自知。一旦事关切身利害,到底不能无动于衷,虽然他自以为是的信心比所疑虑的一面要强得多。
过于执一回无锡,和师爷商量了一阵,仍觉他办的案无懈可击。为防万一,密令心腹暗中布置,并派皂班头张四等四名干役以应差为名,去往况钟行馆坐探消息。只要对头行事稍有不合,便可给他一个难堪,再向抚、藩、臬三大宪去密禀。不料所送礼物大都璧还,连派去的耳目也被退了回来。几次传询南门地保,都说:对头从未出过门,也不许随从人等外出,接连几天,只见到一个姓况的老家人上街去买了两三次药,人很老实,也来见他向当地人交谈等情。先打算以参谒请示为名往探口气。两次请见,对方均说因病挡驾,改日再请。暗中又托同城文武官借故前往,也无一人见到。似这样点水都泼不进,不知对头生病真假,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这日,想起:“对头来了好几天,尚未着手办案,就算他关防多么严密,决无不见原审官之理。
案经三审,他的疑心病纵多,也不能凭空捏造出一些证人证物。期限这样紧迫,他却挨着。岂非怪事?他真要病上个把月,就有现成反证,也必误期,难于交代,何况断无此理。我若小心太过,反使生疑,还是‘以不变应万变’,听其所为,比较妥当。只要两个月期限一满,我便拿了抚台的委札往苏州府走马上任,非但叫他丢官、丢人,还要想法子使他多担一些罪名,才能出这一口恶气。”过于执专往好处想,自信心也越来越强。
这日想到再有两个月就要升官,正在得意,忽见心腹师爷匆匆赶来,手里拿着一封公文,说:“况大人来文,今天要往西门外复查尤葫芦被害一案。请东翁速派刑房和当时的仵作人等前往启封,并请东翁午前往现场尤家肉铺相见。晚生亲自赶出去打听。来人答说,况大人病快复原,等吃完早上这遍药就要起身等语。晚生管见,况知府这件事虽是胡闹,决无损于东翁日月之明。到底抚台派来查办的委员,官阶又高了一点。似乎去一趟,比较使他无话可说。因此斗胆代东翁回复,告以一切遵办。特请东翁示下,如不打算去,吩咐原案刑房仵作人等前去敷衍一下也可以。”这位跟随过于执多年的老师爷,明知此案东家不到场不行,并还表示忠心能干,代他做了主。事后请示,所说的话却极委婉中听,照顾到这位东家刚愎好胜的性情,内容也富于伸缩性。
过于执一听,数日来的怒火立被勾起,接过公文随便—看,往地下一掷,气忿忿道:“好,我就去一趟。看他怎么在鸡蛋里找骨头。”
师爷忙答:“东翁真个髙明,去一趟更对,省得他无中生有地找毛病,也显得东翁的为人公正,落落大方。”师爷明知况钟不好说话,此案必有文章,万一闹翻,东家就不得了。但在这件事还拿不定的当儿,仍是照着一向的奉承比较妥当。
过于执冷笑道:“先生说得有理。我又不是三岁孩子,不管他多么刁难,这些过节是不能错的。来人哪!”
师爷忙即驰出,长随立即传命,依言行事。过于执回到内宅,换上整齐衣冠,匆匆上轿,往西门赶去。因来文说是午前复验,至少也在巳刻光景况钟才能到,想赶在前面。哪知刚出西门,便见前导长随引了老地保前来禀报,说:“况大人现在尤家右邻借坐,静等县太爷带了人来启封复验。”过于执把头一点,挥退地保,暗骂:“这老家伙果然讨厌得厉害!约我午前复验,此刻就到!你便是头天晚上来,凭我断的案,也扭不过去。这管什么用!”越想越气,不觉轿已停住,长随下马赶将过来打帘。出轿一看,尤家肉铺门外并未停有官轿人役,只右隔壁郑家门口条凳上坐着两人,都是寻常打扮,也未穿着公服。
地保顾四当街跪禀:“况大人方才步行而来,只带了两个从人,都是便服,等把小人传去,才说出来历。因不许在街上设公案,小人无奈,才和他从人商量,引往郑家暂坐。请太爷示下。”
过于执点了点头,见左近住户商店的人们渐被惊动,纷纷赶出,立在道旁交头接耳,有的还往尤家对门一带凑近。忙命差役遣散闲人,再命长随先到郑家投递手本禀见。
况钟开头只认定熊友兰无罪,对于女犯却颇怀疑,并且还想不用刑求,由她身上找出真凶。经过路上和连日仔细考査,非但熊友兰完全无辜,连苏戌娟也是冤枉。最感棘手是,此女嫌疑重大,并无其他反证可使脱罪,怎么深思熟虑也找不出一点线索。熊友兰纵然无罪开释,不将真凶缉获,她仍长禁监中,成为疑案,永无出头之日。再要遇到一个糊涂而又多事的后任官,使她重受屈刑,甚而牵连到别的无辜,均所难免。因曾为官多年,深知民间疾苦,心想:“一个兴讼,全家受累,一人被押,四邻不安。如嫌麻烦,救一个不救一个,良心上怎么问得过去?”况钟这几天的日子,实在比过于执还不好过,操的心也更多。第五天晚上,听完况福密禀众干差所说访查情形,仍想不出好的办法。
睡梦中惊醒,忽然想起:“过于执就因刚愎狂傲,自恃能干,才致冤枉好人。我只顾先听舆情,寻访线索不经亲自查看,岂不和他也差不多?像他这样粗心大意,就许凶手在现场留有形迹,被他忽略过去。我怎么疏忽起来?”心念一动,半夜里起身,唤起老简房,令其备好公文,饬无锡县令派人启封,会同复验。次日一早,刚把公文发出,忽又想起:“日前探望苏戌娟的郑家媳妇杨氏和倪阿根,人前背后,口口声声都说昏官冤枉好人。暗中命人去向他们探听,偏又说不出个道理。”意欲提前起身,就便先寻这两家近邻,亲自探询其中有无难言之隐。照预计布置停当,连官轿都没有坐,带了况福和一个干差便先起身。到时,天还未过辰刻。知道微服查访,不是事先准备得好,有时遇到当事人的对头或是仇家,如其偏听—面之词,更易留下成见,颠倒黑白。一到先传地保明言身份暂时不许张扬,再拿话引话,由地保自动引往郑家暂坐。随命退出。
郑家婆媳一听来人是况青天,人又和气,肯和她们平起平坐,惊喜非常,当然有问必答。杨氏更是抢着代戌娟诉冤不已。
况钟问知戌娟平日为人,倪阿根上街卖菜未回,秦古心尚在西门内茶馆里同人喝早茶,正想命人去唤,忽报无锡县禀见。便命郑家婆媳暂退,传话请进。
过于执见况钟独坐郑家堂屋,含笑起迎,忙以下属之礼拜见,执礼甚恭。同坐之后,谈不几句,过于执便起身请示:“是否就在此时启封,追陪大人复验?”
况钟命:“先将封条和门上所钉木块拆去,门上锁暂不要开,只要钥匙呈上。”
过于执不知何意,强忍着一肚子的恶气,诺诺连声。依言传命将钥匙交上。装出一副笑脸,陪了况钟一同起身,刚走出门,见尤家肉铺已在启封,街旁看热闹的人也站满。想问,“这锁是否大人亲启?”没好意思出口。
况钟一到尤家门前,便道:“带熊友兰!”
“有!”熊友兰立由两个便衣差役引着,由人丛中挤了出来,赶到况钟面前跪下。
过于执一见,由不得怒火上升,暗骂:“老鬼又不是初次为官,怎么如此糊涂?就算你看出此案有什么疑窦,在还未判明以前,竟将朝命处决的凶犯身上刑具连囚衣都去掉!分明认定我是冤枉好人,当众使我难堪。就这一件,也是你将来的罪状,人在屋檐下,暂且让你一头。”想到这里,把满腹怒火强又按了下去。不等熊友兰开口,故意笑道:“‘杀人凶犯’熊友兰带到。”
况钟装没听见,随手由袖内掏出大把钥匙,往熊友兰身前一扔,正色说道:“据女犯苏戌娟的口供,她临逃以前,有一把切肉的快刀随手丢掉,不知放在什么地方。你开锁进去,把这刀先找出来呈验,不许迟延!”
熊友兰连声应“是”,拿了钥匙便去开门。
过于执断定况钟此举必败,只是冷眼旁观,心中暗笑,连气也平了下去。
从人早奉过于执之命,在当街设了官座。况钟并未拒绝,由于执一旁陪坐,等候开锁入内査看。熊友兰虽料自己冤枉可以昭雪,但是这些天来押在—间小屋里面,既无亲探望,又得不到一点消息,那个拼死为他喊冤的苏戌娟已不知道下落。听况钟在船上对她的口气,大是不妙。她死虽非自己牵累,眼看这样一个好人冤遭横死,救她不得,心实不安。东家陶复朱也不知道寻见没有?万一寻他不到,自己是否能够脱出监牢,也拿不准。以上这些想法,全都使他非常愁急。这日早起,被两个便服差役带往现场,一路留神,都没有看到苏戌娟。事前受有公差嘱咐,什么话都不敢问,只随二差挤在看热闹的人堆里,等候传唤。认定戌娟凶多吉少,心里头甚是苦恼,并不因为本身已有生机而自慰。及听况钟口气,苏戌娟好似还未处死,好生代她庆幸。当时也未想到别的,拿了那一大把钥匙就去开锁。
这锁从未开过,看去大同小异,拿不准是哪一把,锁又生了点锈,连试了好几把,均未打开。人本忠厚,恐官久等见怪,正急得头上冒汗,无意中用力一捅,竟将那锁捅开。旁边一名干差见锁一开,忙将锁和未拔出来的钥匙一齐要过,呈向公案。况钟接过一看,转交过于执,随口说道:“开锁的不是原钥匙,贵县请看!”
过于执见原钥匙被况钟杂在一大串钥匙内,开锁的是另一把钥匙。男犯不知怎的一个猛劲,将锁捅开,钥匙也被锁簧卡住,拔不出来。暗骂:“老鬼!你以为熊友兰连原钥匙都不认识,也算是反证么?慢说平日尤葫芦和女犯苏戌娟未必让男犯开过锁。何况这类‘刁民’多狡猾,还看不出你那点鬼把戏?”心里有气,正寻思间,见锁一开,便有几个苏州的差役由人丛中抢出,把所有排门全数去掉。熊友兰当先走进。况钟把手一让,也自离座而起。过于执只得忍着气忿,跟着走进。
排门一去,尤家肉铺的半间店房全被阳光照得一览无遗。这地方熊友兰从未到过,更不知那把切肉刀放在何处,在外屋东张张,西望望,忽然发现切肉案板下微微露出两个刀柄,连忙拔出呈上。况钟知道苏戌娟用来自杀的切肉刀,是因行前扎手指时匆忙遗落,多半还在屋内。这两口刀形式尺寸均与所说不同。熊友兰从进门起就摸不着头,看去很生,也没到里间屋去。
便命差人带下。先仔细把里外间査看了一过,见满屋布满灰尘蛛网,肉案上那盏孤灯,灯油已干,灯碗中心黑腻腻地剩下薄薄一层油底,还有两根烧残的灯芯微微搭在边上。死尸早已埋葬,熊友兰走过的脚印中有一块地面微微隆起,土色不匀,似有一滩千凝了的血迹,被灰尘蒙住。方才命寻那把切肉刀已在里屋小桌上发现。
因过于执仍和没事人一样,表面恭敬,在作旁观,一言不发,暗忖:“你这个把人命当作儿戏的昏官,早晚叫你难逃公道!即使陶复朱传不到,熊友兰常坐夜航船,认得他的船夫有三个,已曾传来由窗外暗中指认,都证明尤葫芦被杀的当夜,熊友兰尚在船上,并有悦来店簿可对,决不怕你到时狡展。不过,老査不出真凶线索,这另一个无辜的被害人,叫我怎样救法?”正寻思间,忽然发现西床脚边斜搁着一枚制钱,因钱上布有灰尘,地又背光,先前不曾看出。心想:“尤葫芦父女那么穷,怎会把钱落在地上不管?”过去拾起,果是一枚“正德通宝”,旁边灰尘中也横着一枚同样的制钱。心中一动,忙请过于执一同退出,吩咐无锡县的差役到屋里面轻轻扫去灰尘,搜寻地上有无余钱。
一会工夫,差役呈报,又在床后壁角一带土内搜出三十多枚同样的制钱,还有半截粗红头绳,长约二寸,一头打着绳结,像是串钱所用。
况钟故意笑道:“尤葫芦开个小肉铺,竟会把钱随便扔在地上不管,难怪他要穷了。”
过于执听出语有深意,越发有气,忍不住起立,躬身说道:“回大人的话,凶犯劫去的十五贯是白麻绳。这二三十个散钱定是女犯逃时匆忙,遗留下来的。”
况钟气他不过,正想开口,忽见另二差役呈上两粒骰子。接过一掂,比寻常骰子较重,里面分明有铅。侧顾过于执说完话归座,已偏过头去,口角上还带着一点冷笑。立命:“将尤家的门钉好,另上封条,传原案证人往行馆问话,不许惊吓他们。锁和钥匙连同査出来的制钱、切肉刀等一齐存案备査。传轿回去,以免看热闹的人太多,致生事端。”说罢,朝过于执略一拱手道:“贵县请先回衙理事,等本府查出一点眉目,再请会审。”
过于执见况钟说时笑容全敛,话也没有先前客气,虽早瞥见搜出的两粒骰子被他揣入怀内,以为当地流氓较多,赌风颇盛,好喝酒的人十九好睹钱,骰子上又没刻有名姓,这和钱一样,难道说都是凶手遗留的凭证?当时答道:“卑职回衙待罪。请老大人先回行馆。有何吩咐,随传随到。”过于执虽然几乎气破了肚子,说的话也颇负气,表面上仍装出一脸笑容。老州县官对于上司,在任何情况之下是不肯失去应有的礼貌的。
官轿早已随后跟来。况钟在过于执恭送如仪之下率众起身。过于执也带着他们全班人役和一肚子的怒火回转衙门。
人们一听况青天前来复查命案,越认为苏戌娟是冤枉。当时轰动,纷纷赶来看热闹。这时,天已傍午,秦古心固早回家,倪阿根刚卖完菜,听人一说,也匆匆赶来,和郑家婆媳同立人丛之中。听说要传原案证人,不等官差挨家传唤,便一同争先上前报名,跟在况钟的轿子后面,高兴非常。
况钟闻报众邻居和证人随轿而来,知道他们贪看热闹,没吃午饭,自己也正腹饥。立时传话开饭,给众邻居证人也各吃饱,并命况福、任健,借着送饭慰劳,分别探查他们辞色,只不许熊、苏二人与其相见。
吃完饭,况钟拿着那两粒骰子和半截断头绳,仔细想了又想,忽然把手一拍道:“真凶定与这两粒骰子有关!连这半截红绳也是苏戌娟脱罪的反证。”随命从人速往通知苏戌娟的姨母梁大嫂带了她另藏的十贯钱来对质,但要好言安慰,免使惊慌,并且为她雇轿同来,不许泄露。遣走从人之后,便命传询邻证。
注:
⑴江南土语,称鼠为小老虫。
⑵店家关灯上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