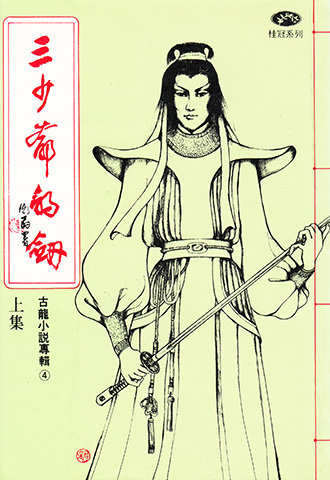前文桑老人祖孙、沈鸿、姜飞老少四人由龙眼崖童天保寨中起身渡江,忽遇异人暗中警告,说前途有一水寇,外号铁臂江猪,在黄松岭山脚下开有一家黑店,此去必须留意,并令四人第三日早晨到了孔家湾左近再行分手。老人途中谈起康家场翰林庄土豪康氏弟兄种种恶迹,过时并还避开这两处地方,准备去往庄西的康前镇上打尖,走到黄昏觅地投宿,半夜起身,到了孔家湾恰巧天明,再行分手。四人正在镇上酒馆之内用饭,先是姜飞发现有五六个身带兵器的壮汉走往雅座里面,同时瞥见隔扇外面醉卧着一个穿得极旧的酒客,仿佛哪里见过。先当过土山时所见穷汉,一问盆子答说不对,穷汉左肩上补着两块,脚上也未穿着这样藤鞋,此人衣服虽旧,洗得也较干净。正谈论问,桑老人忽然示意催走,会账起身。刚刚走出,便听内里喝骂之声,由雅座内纵出三个壮汉,前堂酒客当时一阵大乱。
因那酒馆孤立在一座土墩上面,三面空地,一面临河,后窗外面还有凉亭水阁。里面一乱,街上的人也都惊动,纷纷赶来,内有十余人并还拿着刀枪棍棒。柜台上那个满脸横肉的胖子也赶了出来。三小弟兄心中一动,姜飞因先那几个壮汉曾对自己这面注目打量,神情鬼祟,疑有恶念,刚把手伸腰间戒备,忽被老人示意止住,故意笑说:“此是是非之地,也许有什歹人被他们看出,你们要看热闹也立远一点。”说罢,四人正由人丛中挤出,猛瞥见胖子一手指着里面,正在唾沫横飞,口中喝骂喊打,忽然发现四人走出,刚回转身来,指着桑老人急喊得一个“老”字,忽听叭的一响,声甚清脆,胖子立时捂着半边肥脸急着暴跳起来。原来内里三个壮汉刚刚纵出,朝着醉汉厉声喝骂喊醒,准备盘问,将他绑起吊打时,胖子见有人来,凶焰高张,由柜台里面抢出,正向那几个壮汉指手画脚,说那穷汉方才如何说话无礼,并还打伤两人之事。忽然想起先前进来的老少四人形迹也是可疑,因在怒火头上,只顾盘算同党到后如何打那醉汉出气,不料人已溜走,想起这老少四人脚底沉重,身边金银财物必不在少,只要问不出个来清去白,或是认得有头有脸的人物,立可随便加上一个罪名,发他一笔横财。想骂伙计不小心,令其追赶,一眼瞥见人刚出门,心里一急,方想说这四人均是贼党,话还不曾出口,醉汉看去年约三四十岁,先来饮酒本没打算多事,只为店伙倚势欺人,定要先钱后酒;同时发现胖子出身绿林,现受土豪豢养,表面是开酒馆,实则用他接待江湖中人和自家同类一时高兴饮酒取乐。休看乡村中的酒馆,因那胖子外号双料易牙,本是厨房出身,做得一手好菜,所请厨师又都名手,菜肴十分精美,比寻常城市中还要考究,便门口散座卖与土人吃的包子之类也都味美,价也不算甚贵。远近富户只与主人相识,或是有事路过,也都带了保镖的人,来此大吃一顿,生意颇好。还有那些带了金珠细软避难投奔,仗着官亲官友情面、想靠土豪保护。寄居附近的中上人家,每日游手坐吃,不事生产,也把这家酒馆当成惟一饮食消遣、会聚之所。里面两间静室和后窗外面的凉亭水阁并还设有赌局,从午到夜热闹非常。
四人方才所见前堂酒客看去虽极整齐,并不一定都是土豪首恶爪牙。醉汉也是坐定之后听旁桌上人低声议论,得知胖子外号,想起昔年那伙漏网的贼便有此人在内,不料吃得这么脑满肠肥肥猪也似,心中好笑,这才故意和他为难,先用言语挖苦,对方自然不吃,当时动手,便有两个吃了苦头。双料易牙是个老江湖,看出不妙,立将伙计喝退,亲自赔话,命人送上酒菜,把人稳住,再去喊人。当地离后庄场坝往返十多里,沿途虽有他们自己人,因知来人虽是孤身,决不好惹,又防打草惊蛇,事前嘱咐,非等所请武师到齐不可轻动,一面却当无事人一般,暗中留神察看。本意想等几个能手一齐赶到再行下手,不料对头酒吃大猛,一口气吃了五六斤,吃完便自醉倒。想起前事,觉着就将此人擒住打死,这顿酒菜也被白吃了去,心正痛恨,请的人已陆续来到。先被打伤的酒保见那人睡熟,又沉不住气,偷偷抢前一说,来这几人虽然也是江湖出身,但都年轻性暴,方才得信业已气极,到后正想查问,一听是那醉汉,不禁怒火上撞,未等胖子招呼便抢先下手。上来骄敌,还想喊醒再打,表示光棍。胖子知这三人本领不弱,闻声追出,正在喝骂,说那经过,醉汉好似睡得甚香,听人喝骂刚刚惊醒,偏着一个头,望着面前三贼微笑。内一壮汉见他若无其事,伸手要抓,猛觉眼前人影一晃,叭嚓连声,一手抓空,同时桌上菜盆盘碗一齐飞起,内中大半碗残汤恰巧扣在他的脸上。旁立二贼也被菜碗打中,闹了一个通体淋漓,一身华丽短装全是油污狼藉。同时门口叭的一声过处,胖子业被那人打了一个嘴巴,半边猪肝脸当时肿起老高,痛得暴跳如雷,猛扑上前想要拼命。不知怎的,被醉汉朝胖脸上又是一个大嘴巴,这一下打得更凶,非但顺嘴流血,人也翻倒在地。
三贼明见醉汉身手之快从来少见,微一抬腿先将桌上盘碗连桌一齐打飞,打得他们周身淋漓。就这晃眼之间人已到了前面,接连两掌把胖子打了一个晕头转向,倒在地上爬不起来,急怒攻心,哪知厉害,仍想以多为胜,由酒保手里抢了一块抹布,稍微一抹头脸,便同怒吼抢上前去。室中还有六七个武师打手,本要出看热闹,见状大怒,各自甩脱长衣,拔出兵器,一窝蜂般怒吼追出。醉汉招手笑说:“莫要误伤别人,是好的和你前面空地上打去。”声随人起,人和箭一般斜飞出去。这时外面的人正纷纷赶来,内有十余个早已得信,因胖子暗中嘱咐,不听号令不许上前,一见里面动手,拿了棍棒刀枪齐声喝打,同往里拥,一丈多宽的门口业已被人挤满。醉汉竟由那离门只两三尺宽的人群头上惊燕穿帘斜蹿上去,离地两三丈,再化作一个大鹏展翅侧身而下,口中大喝:
“不相干的人快些散开,各自走路,免得多遭麻烦!”
老少四人见醉汉动作轻灵,宛如飞鸟翔空,轻功内功全都到了上乘境界,不在独手丐诸老侠之下,可是都未见过。桑老人也看出那人甘肃口音,决非来路所料简氏弟兄,生平从未见过,否则对方就能改易年貌,也瞒不过自己这双老眼。心中惊奇,呆得一呆,忽听这等说法,知其暗中示意警告,催令速走,心想,凭此人的功夫,再多几倍敌人也非他的对手,所说必有深意,忙装惊慌,拉了三小弟兄往前面树林中走去。外面的人见此声势也都吓得纷纷奔避。胖子的话不曾出口,一班打手又想群殴,谁都不曾留意,群贼也刚追出,三小弟兄一听真走,还不愿意,同说:“这位好汉只得一人,我们如何袖手旁观?”老人笑答:“盆子年幼无知,二位贤侄曾得高明传授,如何这样小看人家?
敌人再多几倍也无用处,这位异人必知我们来历,业已示意催我上路,分明其中有事,守在这里无益有害。我料前面必能见到,还不快走!这真奇怪,这位必是昨夜那两位异人之一,但决不是简氏弟兄,我真不曾见过。你两弟兄可听师长说过吗?”姜飞闻言,首先想起昨夜渡江时头目郎三所说借口渡江卧在船头后又失踪的那位异人,仿佛这样身材打扮。沈鸿。盆子也都想起,老人一说并非简氏弟兄,又在催走,也就放开。
四人途中回顾,来路镇上锣呜犬吠、呐喊喧哗乱成一片,相隔已远,又有树林挡住,看不出来。只见锣声起后,附近村落中的居民一齐响应。跟着便见各地田岸上的丁壮成群结队拿了刀枪棍棒呐喊喧呼而来。桑老人深知远近村落中均是康家产业,设有联庄会,那伙贼党决非异人对手,难免全要惊动。恰巧前途是片土坡,偏在路侧,便由坡上穿行,遇见有人经过,便装回头眺望。仗着镇上均有暗号,村民听出敌人就在镇内,这老少四人均像一家由此路过,相隔行处最近的也有两三丈,再听镇上锣声紧急,忙于应援,谁也不曾留意,就此对面错过。老少四人对面察看,见这一带联庄会果然布置周密,登高遥望,不消片刻,远近人家村落俱都拿了兵器,四方八面飞驰而来。来路侧面一带并有烟尘蓬起,隔着大片树林看不见人,估计还有马队成群飞驰。鸣锣敲梆吹哨之声远近相应,震撼田野,声势甚是惊人。估计康家土豪党羽众多,便他手下种田的农人也都受到长期训练。方才所见异人只得孤身一人,本领虽高,到底势孤可虑。这方圆一二百里以内都是康家势力,另外几处村庄大寨连同水陆两路的贼巢和他兄弟又有勾结,一声令下,遍地皆敌,岂不讨厌?互一商谈,连桑老人也有一点惊疑起来。正想假装旁观,立在坡上相机而行,如其醉汉真有险难,立时出手往援。停了一会,正商量间,忽见镇上两处火起,远近各村落中的丁壮也都相继赶到,一时浓烟蓬蓬,火光照耀,喧哗之声比前越发热闹。先前所见远方涌起的那一条尘雾也由远而近,渐渐现出人马影子,果是一群马队,转眼赶到镇上,锣声人声和呐喊救人之声乱成一片,分外显得乌烟瘴气。大闹酒馆的异人却始终不见出现。
三小弟兄正担心事,欲往窥探,桑老人一面劝止三人,一面定睛朝前注视,仔细看了一阵,方说:“这位朋友决不妨事,我们走吧!”忽听身后坡下有人低喝:“那几个狗教师业已赶来,你们虽然无关,何必多费手脚!老桑,你也是个老江湖了,如何看不出来?你们前途事关紧要,还不快走!我往那面调虎离山,省得麻烦你们,还可和他再开一个玩笑。你们如再不走就要妨碍我的事了!”三小弟兄见那发话之处就在身后生满野草的土崖之下,又要跟踪往看,刚一探头,便被老人伸手拦住,再把手一拱,笑答:
“谨遵台命,老朽无关,这两位贤侄初涉江湖,此去前途十分艰险,他知阁下是他尊长,拜见心切,前途请赐一见如何?”说完未听回音。老人料知对方行踪飘忽,匆匆说完便自离去,忙催三人快走。姜飞途中笑问:“这便是那位异人吗?如何口音不十分像,老前辈为何不令我们探看?”老人答说:“这还看不出来,此公暂时不愿我四人相见,业已露出,何苦使其不快!照我猜想,也许他们另有事情,我们适逢其会,无心巧遇,走成一路。因和二位贤侄师长至交,只在暗中就便相助,并不愿露出他的形迹。如我料得不差,定必关系机密,所以口音都变。你二人也许暂时还难见到,你只照他所说走法,到了黄松岭多留点心便了。”
四人原是顺着一列土崖,借着崖上树木遮掩加急前进,边走边往来路土坡那面察看,见镇上火已快要救灭,人烟杂乱中忽然连骑带步涌出数十个手持兵器的壮汉,正往自己这面追来,业将赶到方才所经土坡前面。为首两人手指自己这面,已在厉声发话,似要喝令停止。相隔颇远,人在上风一面,虽未听清,全都看出不妙,料知后面贼党看出破绽,对这四人生了疑心。桑老人忙催快走,一面准备应付。猛瞥见坡侧纵起一条人影,由那为首两人面前箭一般横飞过去,纵出两三丈高远方始落地。马上两人虽然拿有兵器,似因跑得太急,骤出不意,不知怎的一来全部翻身栽落。一个本领较高,就地一个倒翻便自立定,怒吼一声,朝坡侧纵起那人追去。另一一同伴竟似受了重伤,翻跌地上,被人将马抢前拉住,上马扶回。当时又是一阵大乱,所有人马同声呐喊,转身往侧面追去。
镇上后赶出来的敌人也自警觉,锣声又起,分头追赶。人是越来越多,看意思是想三面合围,不料那人身法绝快,纵跃如飞,时东时西,出没无常,还未追到,人已蹿向镇旁树林之中。等到贼党将那树林包围,忽又接连几个隐现,回向镇口,立在房脊之上,等到敌人看出反扑过来,人影一闪,又复不知去向。
四人也将那一带土崖走完,相隔已远,后路已看不见,各自加急朝那隐僻无人之处飞驰过去。一口气跑出十多里,走进一条山口,掩往高处一看,来路镇上黑烟蓬勃,烈焰上升,虽然看不清楚,估计四人走后异人将马上两人打倒,重又赶往镇上到处放火,又闹了一个乱七八糟。这类事如在三更半夜也不足奇,当此大白日里,又是孤身一人,竟在大群仇敌围攻之下连放了几次火,闹得这等厉害,伤的敌人想也不在少数,非但本领高强,从来少见,单这机警胆勇也是从未见过,全都惊佩不止。沈。姜二人因从未听师长说起,对方口气却是一位师门至交,求见之心自然更切。本来沿途无此平安,仗着桑老人深知地理,善于闪避,知道康氏兄弟虽然人多势盛,到处都有耳目党羽,但这康前镇临江一带都是山地,只有两条樵径,形势险峻,轻易不见人迹,过去不远乃全境最荒凉隐僻的所在。山那面虽有一片村落,也是康家外围农村,风景较好之处,内中结有两个小寨,但可不由下面行走,如由靠近江边的危崖童山翻越过去,再绕走二三十里,走上孔家湾的一条山径小路,便不归他所管。湾口大镇又是各路土豪约定交易停泊之所,号称三不管,往来商船均知当地水陆要冲,远近土豪恶霸、往来客商的货物均要由此起运,非但谁也不肯破坏,反倒随时有人相助防护。镇上又住着两个有名人物,本乡本土自不必说,便对水旱两路的绿林中人也有交往,哪怕中途发现贼船尾随,一到当地便得平安,还可设法求那两人保护,代向来贼求情,怎么也不至于人财两亡,身遭惨祸,故此镇上繁盛已极。
照着渡江时异人之言,也应是在当地分手,不过这条山路虽极难走,路却近出不少。
初起身时并未打算,只为路过康前镇,看出形势可虑,临时改道掩来此地。仗着各有一身好功夫,连那两条樵径俱都避过。入口不远便即攀上崖顶,往前进发。桑老人笑说:
“按照预计本想从容起身,赶过两处打尖站头,再往镇店中宿上一宵,明早到了孔家湾再行分手,以防万一有什事情,未照这位异人所说,无心错过。谁知发生波折,前途俱是童山石崖无人之地,连我也只为了寻访仇敌踪迹,前后来往过两次,中途并无宿处,越过此山偏巧又是康氏弟兄的势力之内,这厮平日那么骄狂自恃,镇上发生这大乱子,定必怒发如狂,决不甘休。贼党已对我们生疑,此时想已发出信号,沿途堵截,盘问虚实,休看我们脚底迅速,他那传递消息的方法只有更快。何况我们俱是生人,只要将那旗花信号一路传达过去,不消几个时辰,非但这面境内可全知道,便是和他通气的那些土豪贼党也都得到信息。我们决定追他不上,说不得只好连夜起身,在天明以前越过大小康场和十八里沟边境,抄小路直达孔家湾,索性去往相识人家投宿,睡到预定分手之时再行起身。这样未了一段虽然要绕不少的路,仍照预计分手,却是一点不差。我想和二位贤侄日落以前便寻住处,舒舒服服谈上些时,吃饱睡足再行起身,顺大路走出两三里便是孔家湾了。”三小弟兄自无话说,四人边说边走,穿山过涧,纵跃如飞。还未走到黄昏,山前村镇人家业已在望,知道此时下去容易被人看破,便先觅地休息,取出于粮吃饱。候到天快入夜,然后往出山路上绕去。经过大小康场天只初更,十八里沟就在小康场的附近,河沟不宽,四人一跃而过。
沈、姜二人问知康氏弟兄最是好名,这方圆一二百里以内的地名都喜带上一个康字,心正有气,月光忽上,同时瞥见对面小径上走来两人,桑老人忙喝禁声,刚往侧面坟堆后一掩,想等来人过去再走,以免相隔来路太近又生枝节,不料那两人走过面前忽然回身,刚喊得一个“桑”字,老人已抢先赶出,匆匆相见,便随来人往前走回。原来那是老人两个相识的后辈汪大、汪二,在当地耕田为生,日里听说老人祖孙还有几个帮手大闹小沙湖,冲破截江锁,君山吴枭叔侄传令沿江各地大小水寇与之为仇的信息,不由大吃一。惊,无奈自身本领不济,爱莫能助。弟兄二人由孔家湾镇上回到家中,正在相对愁虑,夜饭后忽然有人隔窗发话,说老人祖孙同了两个少年已在途中,转眼就到,四人形貌已被贼党看出,此去荆门、洞庭等地到处危机密布,步步皆险,可将这四人引到家中,非但同行少年,连桑氏祖孙的形貌装束也须改变,最好假装客商,搭一得有吴贼保护的商船,索性出其不意径由洞庭回转,到后带了家中妇孺再往荆门山中暂避,反较稳妥。并说,商家隐居的渔村对头至今尚未发现,只知他是祖孙二人,专一注意那条附有铁桨的快船。现正乱发急令,并派许多能手沿江搜索那条快船的下落,还想不到别的。
只管在孔家湾搭船回去,形貌已变,再和盆子装不相识,另外寻一相识的人与之做伴,就遇见贼党上船查问,也认不出等语。初发话时不令汪氏弟兄出去,听完出看,所居是片旷野,竟未发现人影,料是老人好友,心中关切,忙照所说引来,果在途中相遇。同时谈到对岸来路方才还有两个相识的人在黄昏前见面,似还不曾得到信息。
近来康家弟兄自在康庄开河之后,觉着大小康场地土大薄,又隔着一座山,已将他那亲信的人搬了回去,另外招些苦人为他耕种,共只派了有限几个爪牙掌管,兼做他的耳目,就被知道也不妨事,何况内有两人是旧相识。四人来路并未出手,敌人在后喝止,相隔又远,可装未闻,稍微分说,只要本来面目不被认出就可无事,无须多虑。这两弟兄人颇义气,全家种着三十多亩土地,又在镇上开了一个口袋铺。当地人家均是依田而居,只两户自耕农。天近二鼓,农家俭节早起,已早安眠。路上月光如水,一个人也未遇见,桑老人料知又是那两位异人所为,也许令其孔家湾分手都是为了自己方便。仗着途中业已吃饱,一面劝止主人不要费事,一面打听镇上停泊的商船,果有两条大船,非但平日得到君山照应,并还常代吴贼就便采办各地需用之物。船老大交情颇宽,人最义气,桑老人和汪氏弟兄均与相识,匆匆议定,忙托汪大连夜赶往镇上,偷愉与之商量,允与不允均速回信。人去之后,汪二夫妻恰将面水饮食端进,老人推谢不掉,随意吃了一点,便由沈、姜二人取出易容丸,照齐全所说如法施为,面容立变。老人见所带易容丸甚多,共只用去两个半粒,合起来不过黄豆大小,连皮色也都变过,连声赞妙,间明用法,讨了三丸藏起,再将二人所剩九药如法涂在祖孙二人脸上,也将形貌换过。姜飞另取出一小包药粉倒在水里,将老人须发全都染黑,分了一些解药交与老人收下,可备随时可以复原之用。老人问明易容之后不用解药,至少要经两三个月方始逐渐退去,否则怎么也洗不掉,越发高兴。沈、姜二人见汪二在旁赞不绝口,两次欲言又止,知其想讨两粒,也送了三粒与他,加上一小包解药。汪二外号小白条,武功不甚高,水性却是好极,彼此谈得十分投机。睡前汪大赶回,说事已办妥,船老大非但一口答应,并还早就关心,日里便在打听,回转洞庭、湘江恰又必走之路,此船连来带去君山方面全都知道。就是形貌不变,同时上船,只不被人看见,到了船上便可藏起,船头插有君山的旗,沿途贼党均通信号,更不会上船查看,尽可放心等语。四人闻言大喜,又谈了一会,便各安眠。天明起身,沈、姜二人见只盆子在旁,问知老人天未明前业已上船,因盆子不舍分手,又恐二人途中劳倦,不肯惊动。本来预定祖孙分走,盆子假装船上新招的小伙计,守在旁边,想等二人醒来话别再走,不曾跟去。行李、兵器老人已先带走,并嘱二人紧记途中之言,以防有失,尤其黄松岭黑店更要留心等语。二人见盆子那样依恋,同声劝慰,匆匆洗漱。汪氏弟兄早已准备酒饭相候,汪二并还固执要送二人一段,推谢不掉,只得听之。吃完分手,汪大自送盆子上船,沈、姜二人便由汪二引路,往乐乡关进发。汪二一直送出三十里外,沈、姜二人再三辞谢,方始答应在前途相识镇铺中打完了尖再行分手。
快到前面山镇,姜飞无意中听汪二说不久要往岳州访友。为了当地种地受气,两三面均是有势力的土豪恶霸。靠近孔家湾一带的田地均要强行收买,敌是敌他不过,房后那家自耕农已快成交,如今只剩自家这三十多亩田地。差役常时下乡骚扰,越来越凶,卖与一家姓张的土豪多少还能得点田价,以免闹翻被其强占了去更是冤枉。听说岳州这家是个大家世族,近来为了年景荒乱,结寨自保,平日只管作威作福,财势大得惊人,连地方官都当他祖宗一样看待,但对他手下的人却较宽厚,这位朋友又是他得用的武师,目前安分种田的人简直无法立足,说不得只好前往混上些时。因其不喜单身汉,仗着家无幼童,也许弟兄全家均往投奔,暂时先拿力气换钱,等到天下太平,再用新旧两起积蓄另外设法买田耕种。此去虽是好友相招,自知本领不济,决不想出人头地,再吃江湖上饭等语。二人闻言心中一动,再一细问所去人家,正是沈鸿昔年杀父夺妹之仇、外号烟花太岁小霸王的钱耀祖。
钱贼一子承挑两姓,本是湖南首富王廷诚的第三子,从小过继钱家,父兄都做大官。
长兄王耀宗少年科第,年纪轻轻做了一仟外官,贪污荒淫,闯了乱子,看出风头不顺,仗着朝中有人,也未受到处分,年未四十便告了终养,人却不曾回乡。因在开封城外置有大片园庄,加上续弦妻子十分得宠,又是最有权势的亲贵人家之女,母家就在汴梁,于是留了下来。因其性最贪淫,在外面偷偷立了两处外家,常时背了续弦妻子,带上两个保镖的和几个心腹恶奴前往淫乐,倚仗财势,无所不为。姜飞之父生前便种王家的田,虽因所种的田归王耀宗新纳的爱妾所有,是个开封城里的土娼,人最妖淫,颇有几分姿色,王耀宗爱如至宝,每月必要想出许多花样,或借查看所经营的农商为名,背了爱妻前往欢叙,住上几天。起初往来十分隐秘,后因性喜结交当道,作威作福,饮食用度又极豪奢,王妾最善撒娇献媚,耀宗为她所迷,百依百随,除代置许多田产而外,又在当地建了一片园林精舍作为自己别墅,以及应酬达官显宦之用。王妾娼妓出身,只管骄狂任性,平时对人尚不刻薄,因此姜氏夫妻虽代人忙上一年,衣食还能保住。本来相安无事,并还小有积蓄,眼看别家种田人过得那等苦法,自己夫妻子女五人居然过得满好,非但知足高兴,对田主人也极忠心。因其祖传种花手艺,无论什么花树,经手立活,相隔又近,王妾先不知道,后来听说,将他喊去,一试果然。连做了两年,王妾对他极好。
姜父彼时人才三十来岁,生得十分精壮,正感激主人待他的好处,不料王妾水性杨花,早就与人私通,并将旧情人引去,表面做他粮柜上的账房,日常晴中幽会,仗着平日肯用钱财,收买人心,事情并未泄漏。因其天性淫荡,又到如狼似虎之年,原有奸夫之外还不满足,耀宗每次来时故意装得一脸正经,所居上房前面的院落连三尺之童都不许其走进,耀宗一去,非但男女上下一概不分,随便说笑,全无避忌,并喜常时偷偷出外走动,去往娘家勾引外面男子,不知怎的,姜父竟被看中。先借花种得好为名赏了两次酒食银子。隔不几天忽命心腹丫头将其喊往上房密室之中,当面调笑。彼时绅权至重,稍有财势的官绅杀害个把家奴佃户毫不足奇。姜父人颇机警,性又方正,夫妻之情更厚,知道事如泄露全家遭殃,当时借故推托,不等对方言明,便打好脱身主意。王妾虽觉他不知好歹,心中有气,还不放松,正待纠缠,总算事情凑巧,被管粮柜的奸夫得信掩来。
姜父虽得勉强脱身,回家便装了几天病,正在提心吊胆,夫妻愁骇,不料王妾并未喊他人园种花,再一打听,花匠也换了人。姜父原恐淫妇恼羞成怒,从此结怨,于他不利;无奈所种的田又肥又好,每年出息甚多,交完租粮还有盈余。起初为了种花得宠,虽做花匠,田并不曾收回。恰有一个远房兄弟田被主人强行收去,无衣无食,夫妻二人一同投奔,相助耕种,连长工都无须雇。觉着王妾虽然行为不正,别处还寻不到这样宽厚的主人。又想,这类妇人固是心毒,她做这类事也不怕我张扬,虽然怀恨,不要我再做花匠,别的还有顾忌,只是还不放心。正想如何可以察看风色,前引他去的心腹丫头忽然背人寻来,说那日主母实是酒醉,幸而你还明白,现虽不便再喊你到园中种花,但党委屈了你,命我赏十两银子。但是此事如敢泄露休想活命,莫怪她狠。只要能守机密,所交租粮以后均可由你的便,另外还有好处等语。
姜父安土不舍重迁,竟为所愚,全没想到这两个狗男女一个心生妒念,不能奈何淫妇,却把怨毒种在他一人的身上。一个更是恼羞成怒,恨之入骨,表面买口,暗中阴谋陷害。本就放他不过,加以王耀宗日久胆大,乘着王妻怀孕,居然整月不归,宿在王妾那里。王妻早有风闻,只当丈夫同了一般官场中的押友在省城寻欢取乐,井没想到这等大举。等到耀宗回家,办完满月,又要借故出门,王妻借回家为由,带了心腹使女下人去往城内,本就有心查访,偏巧亲戚人家请酒,主人姓吴,也是一个大绅宦,新近被参回来。虽是风尘俗吏,因其出身望族世家,受了习染,颇喜附庸风雅。家中妻妾甚多,又爱和内亲女眷说笑,王妻又是他的表妹,无话不谈,一时疏忽,酒后失言,吃王妻连哄带激,竟将丈夫隐秘之事探听出来。当时不动声色,回到娘家住了两天,突然带人亲自前往查看。也是姜父应该晦气,那所别墅离城虽近,又在官道旁边,但有一条小径,外有树林遮避,主人又是当地有财势的人家,外人向来不许入庄一步,不知底的人不易寻见。事有凑巧,王妻到时,正命下人往前访问,为防泄露机密,事前并未明言,那娘家叫去的恶奴连想送信讨好都办不到。又知姑太大的脾气,只能倾向一面,正悔平日未向对方下人探询明白,多费口舌,姜父恰巧迎面走来,因是王家多年佃户,近年每逢年节,王耀宗见他花种得好,常命担花送礼,并告对方种花之法,到岳家去过两次,还代剪接了两天花木,所以双方相识,立时唤住探询。姜父不知后面还有母老虎的大队人马,立为引路,等到发现,业已无及。王妻大家出身,耀宗当日又正接待两位路过的贵官,高朋满座之际,当时虽未发作,爱妾却被强行接走。回到家中自然又是一番大闹。耀宗对这悍妻又爱又怕,对她母家更是不敢得罪,赔了无数小心,连闹了多少天才得无事。
爱妾却是苦极,平日放荡已惯,哪受得住正室折磨管束,始而背人哭诉,寻死觅活,最后还是在王妻阴谋运用之下,逼得逃了出去。
耀宗问明经过,本就迁怒姜父,那爱妾又疑心姜父,先下手为强,暗向夫人告发,几次暗中进谗。耀宗先因悍妻警告,还不敢公然报复。爱妾一逃,越发勾动前恨,暗中命人瞒了悍妻,先将姜父的田强行收回,连自建的房子也都迫令拆掉。姜氏全家仗着历年辛苦有点积蓄,以为对方出完了气拉倒,不种他家的田当无他虑,便在附近买了十多亩田,再祖上十来亩,准备辛苦数年,再将所租的田买下,便可安身立命,保得丰衣足食。谁知过了不到一年,姜飞年才两岁,先是耀宗寻到逃妾,另筑金屋,重修旧好。因有前车之鉴,不再招摇,想起以前风光那么称心,恨毒姜父。旧好夫自从逃出便在一起,为知耀宗余情未断,想要讨好,推说本是亲兄妹,昔年穷苦,不得已让妹子落了火坑,恐怕丢人,所以始终不敢明言。耀宗居然相信,仗着悍妻不知外间的事,仍令管理旧业。
对于姜父自然恨透,耀宗因狗男女日常絮聒,非要报仇不可,随便借一题目硬污姜父偷他庄上的瓜,打了一个半死。后又由狗男女连命恶奴生事,打骂凌辱,无所不至。姜父才知不妙,匆匆把所种的田用贱价偷偷卖掉,逃往城内,想做小本经营;无奈几次毒打,冤苦太甚,人已受了内伤,小生意做不了两天又与对头巧遇,将担踢翻,不是旁人力劝,几乎还吃官司。因此悲愤成疾,活活气死。未年所受罪孽简直惨痛到了极点,同住的堂弟夫妻早被对方打跑。姜飞还有一兄一姊,也因乃父被打,在旁跪哭求告,一个被恶奴踢伤,一个吓病。姜父死后不久相继死去。
姜母含着满肚皮的悲愤,受尽艰难苦痛,好容易抚得姜飞还未成年,人便病死。生前看出爱子性刚疾恶,如知杀父之仇,难免惹出祸来,始终不肯明言;后虽露了一点口风,并非真实详情,连姓名也不肯说。直到后来乐游子暗中前往周济,姜飞恰巧睡熟,因听来人口气和那来势,以及平日所闻贾先生待人之好。想起以前所托的人不如远甚,当时跪在地上,悲声哭诉,并请在姜飞未成人以前,就是自己老死,千万不可泄露一字,乐游子点头答应,安慰了几句,连姜飞都未喊醒,便自走去。跟着独手丐去往姜家赴约,姜母又在暗中乘机拜托,说自己体弱多病,决不久于人世,务望恩师照应孤儿,等他年长告以前事。不料独手丐早就得知,不等姜飞取柴回转,便令住口,笑说:“你那仇人因见中原年景荒乱,业已迁往岳州,贾先生教读之家便是他的亲戚,比你所知还要详细。
只管放心,恶人决不能久,此仇也是必报。不过此子年太幼小,你托人所写的那封遗嘱不是时候,不可泄露。”姜母原有深心,虽看出这两位异人,仍不放心,临终以前依然托人转告,并将遗嘱交与姜飞,令其见到师父再行开看。可是仇人的底细和真实地方还是下山以前才听师长同门说起。
沈鸿先只知道钱耀祖是他杀父夺妹之仇,还当人在湘阴原籍,没想到二人的仇敌都在岳州,仗着此去奉有师长机宜,一切均有准备,事关机密,连对桑氏祖孙都未明言。
这时一听,汪二说他全家也要搬去,所投的正是钱家,暗忖:听师父说,妹子心痛父仇,见我久无音信,行刺未成,被仇人擒住,正要加害,不知怎会逃走。妹子如在,此去还可假装亲戚,方便得多。虽然此时形貌已变,昨夜也未当人说出去向,名姓却未隐瞒。
师父原说名姓随意,形貌一变,便用真名也不相干,到了岳州再看事而行,另外还有一层用意,但没想到汪二也会寻去。我虽先到王贼的太平洲福全庄去作内应,但是钱贼所居与之邻近,两家又是骨肉至亲,汪二前往投奔定必相遇,万一走口,岂不露出破绽?
心中盘算,正打主意,打算托他几句,姜飞已先开口,低声说道:“汪二哥,我知你是个好汉子,人最义气,我有一事相托,还望原谅。”汪二也是一个心明眼亮的人,昨夜沈、姜二人睡后,已听桑老人说了一个大概;加上初见面时所闻,对于两小弟兄万分钦佩。原是有心结交,又早料定二人所去之处,故意借话试探。闻言四面一看,离村已近,往来行人渐多,惟恐被人听去,彼此不便,忙即低声接口答道:“你我弟兄一见如故,有事均可心照。今日你我亲如弟兄,自不必说;但是目前到处恶人横行,洞庭君山和太平洲三姓土豪勾结自不必说,便这一路上的土豪恶霸、水旱绿林也把吴家叔侄奉为神明,与之通气,准备依附,以为将来保全身家之计。我们弟兄和这班人都合不来。小弟此去投奔原是出于无奈,又是朋友好意,不便辜负。如今人心难测,贼党耳目甚多,前途分手之后,无论何处,我弟兄再如相遇,最好重新结交,作为以前全不相识,还望二位兄台不要见怪才好!”二人一听,双方心意不谋而合,连忙谢诺,姜飞虽觉汪二言之有因,分明前途相见已被知道,惟恐自己多疑疏忽,被外人听去,将话点醒,彼此都不再提,心中一动。前村已到,汪二笑指道旁酒家让进,也就不再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