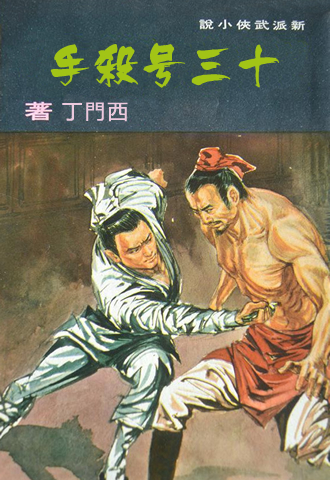前文凶僧因忿三姑说话难堪,欲向文麟猛下毒手,冷不防朝前扑去,不料窗外一股掌风迎面打来。凶僧本要跌倒,身往后退,心再发慌,忘了身后还有一席残肴,一下撞将出去,连桌椅带人一齐翻倒,劈哩喀喳,乒乓叭嗒,满屋杯盘乱飞,残看狼藉,凶僧也跌倒在地。
恶道正往前纵,三姑虽未把他放在心上,但一想尚有文麟在旁,对方人多,身居虎穴,虽有大援在后,对方怒发如狂之际,也颇危险,心里有些发慌,待要抢前迎敌,耳听呼的一声,又是一股掌风由外扫来。
恶道发动稍慢,也不至于受伤,只为素性阴险,以为凶僧性暴,必朝三姑扑去,似此劲敌,不乘此时合力夹攻,冷不防下手,万元取胜之理,又因人较机智细心,看出主人与三姑嫌怨颇深,于是新仇旧恨同时引发,上来便下杀手,满拟凶僧性如烈火,受此奇辱,必和三姑拼命,不料凶僧心有顾忌,又知三姑不是庸手,难于取胜,上来想拿文麟出气,两下心意相左,等到瞥见凶僧往扑文麟,方自暗骂:“秃驴真个废物!你杀穷酸有什用处?”耳听窗外哈哈一笑,一股掌风已由侧面打来。
恶道武功高强,久经大敌,长于应变,耳听呼的一声,便知来敌不是寻常,百忙中往旁一闪,本来不致受伤。无如对面还有三姑一个劲敌,见凶僧、恶道双双飞纵过来,惟恐文麟受伤,打算将恶道架开,抢向文麟面前,把人护住再行应敌,刚一掌朝前架去,正赶恶道临时变招,往旁闪退。三姑情急之下,为防有失,单臂用力,“金龙探爪”,当胸就是一掌。
恶道本在收势旁闪,见对方一掌打到,知道厉害,改向后纵,不料窗外那人因恐误伤三姑、文麟,原是双掌同发,由侧打来,恶道不躲,不过和凶僧一样,打中半边肩膀,还不至于送命,这一躲,恰将三姑避开,由侧面变成正面,觉出掌风又猛又急,仗着闪躲得快,虽未打中,右肩头仍被扫中了一点,其痛彻骨,同时凶僧已重伤倒地;心正发慌,暗道“不好”,猛觉面前又有一股重力压到,情知遇见内家能手,中了千斤大力神掌,内腑已受重伤,惊悸亡魂中忙把身子往后一仰,打算仰跌在地,避重就轻,免将脏腑震断,保住残生。谁知遇见照命凶星,恶满数尽,他这里往后倒退,那股真力也随同下压,当时胸前一紧,逆血上行,口里发甜,两太阳直冒金星,啊的一声,连一口气也未透转,就此肝肠断裂,七窍流血,死于就地。
这原是同时发生转瞬间事,双方连念头都不容转,晃眼之间,胜败已分。三姑一心专顾文麟,并没想到身后异人的武功这等高强,一见凶僧倒地,惟恐敌人翻脸,忙抢向前,急把文麟拉住,令其快走,恶道已惨死地上,凶僧也受伤惨重,倒地未起,心胆立壮,刚拉文麟越窗而出,忽听门外步履之声,冯婉如又在大喝:“三姑留步!这位朋友尊姓大名。”话未说完,一条黑影已由窗外飞进,落地先向三姑说道:“你二人可用套索仍由原路下去,这里的事由我发付便了。”三姑应诺,带了文麟便往崖边跑去。贼党也纷纷赶进。
婉如见来人是个头戴面具身穿紧身黑皮衣裤的少年,因是身材瘦小,所穿紧身短衣似皮非皮,不知何物所制,紧贴身上,更显得皮包骨头,又瘦又小,通体纯黑,所戴面具又是人皮所制,色作灰白,青渗渗的,看去和骷髅一样,身手矫捷,动作如飞,那么厉害的凶僧、恶道,竟吃他一掌一个同时葬送,心虽惊惶,但因乃父全家多年威名,今被来人谈笑之间把人劫走,并还伤了两个有力同党,如在平日已是难堪,何况此时各路英雄纷纷到达,将与强敌恶斗之际,这人怎丢得起?即便不敌,也应有个交代,强笑问道:“这位朋友,素昧平生,何故上门欺人?请道其详。”黑衣人见外面跑进四个贼党,均被女贼挥手止住,发话询问,哈哈笑道:“我黑骷髅近年本不愿多事,只为有一朋友撞见几个贼党,拿了雷四先生的铁木令正在说笑,问出是由周文麟身上取来,以为尔等明知故犯,有心抗命,前来问罪。先想他们也许事出无知,只要把人交出便可无事,中途发现蔡三姑同了一人赶来。我知此女为人尚好,互相谈了几句,同来窗外。先用铁木令警告你们,见你不曾抗命,正要令人退走,谁知这两个贼僧道不知死活,意欲暗算二人。我生平最恨恃强欺人的狗贼,周文麟一个文人,你们无故将他欺凌已是该死,而这雷四哥铁木令所到之处,照例不容违抗,顺他者生,逆他者死,既敢违抗,当然不能容他活命。我知你们近日约了不少隐迹多年的老贼,好好日子不过,想要自寻晦气。此时你们人未到齐,本不值与你计较。说得分明,我决不走,无须用什缓兵之计拖延时候。
不问你们多少人,我只孤身应敌。如其不知厉害,想要一分高下,只管把人喊来,我等在这里便了。”
婉如一听,来人竟是昔年与雷四先生齐名的黑七煞中神行无影黑骷髅查牧,这一惊真非小可,初意敌人狂傲凶横,情面难堪,丢人太大,欲借问答为由将其绊住,以便贼党闻信赶来,以多为胜,合力夹攻,不料被对方叫破,先进来的几个同党虽非庸手,武功还不如凶僧、恶道,如何应敌?急切问正打不起主意,老贼和那几个有名人物又不知何往,心正为难。忽听门外有人笑道:“主人不在,哪位朋友光降?待我看来。”婉如一听来人乃是老贼昔年至交,有名的矮韦护、铁掌铜拳沙镇方,心中一喜,忙喊:“沙老快来!”人已走进。
另一面三姑带了文麟到了崖口,正待用绳索把人缒下,猛瞥见老贼冯越同了许多党羽和恶兽黄猩子由峰后跑回,下去难免撞上,自己无妨,文麟却是可虑,心中惊疑,不敢就下,一听婉如高呼“沙老”,猛想起此人也是父执;日交,成名多年,本领甚高,幼年曾经见过两次,暗忖:“老贼最怕张扬他丑事,何不将机就计,索性等老贼回来,当众明走山正路出去。”主意打好,便停了下来。
回到窗前一看,那沙镇方乃是一个须发如银、根根见肉的红脸矮胖子,手中拿着两个茶杯大小的铜球,由门外缓步走进,见面笑道:“我当是谁,竟是黑七煞弟兄么?今日光降,有何见教?凭这一僧一道,何值阁下动手?”黑衣人接口哈哈笑道:“老东西少说俏皮话。今日我本无心至此,因见我雷四哥的铁木令被人盗去,问出雷四哥将它赠与文人周文麟,现被老贼擒来。好些无耻的事不必说了,依我本意,只要对方无心冒犯,如肯服低,将人交我,使可无事。不料贼和尚他们见了铁木令仍想暗算伤人,杀害善良,我才出手将其打倒。如不服气,不妨连你一齐算上。”
沙镇方闻言,哈哈笑道:“老兄年已不小,为何还是这大火气?即便你我有什难过,也不是当时的事。何况这里人多,我老沙生平从不以多为胜。真要讲打,不久这里便有一场约会,到时一决胜负存亡,岂不光明得多?不过你说的那周文麟却请留下,日内自会送他回去,决不伤他一根毫发。雷四先生的铁木令也由我交还,向他领罪。所有过节都由我老沙一人承当,任凭雷四先生和贤昆仲处置,刀山剑树当前,我老沙也无二言,你看如何?”
黑衣人笑骂道:“放屁!我向来不懂情理过节,任你成千成万的人,也只一人应敌,有本领只管施展过来。”说时凶僧身受重伤,倒卧在地,一面装死,一面静听,暗中咬牙切齿,一想成名多年受此重伤,同党又遭惨死,以后成了残废,如何在外行动?无奈仇敌来历太大,不敢妄动,正在暗中咒骂,沙老一到,觉着有了仗恃,心胆立壮,一面咬紧牙关,强忍奇痛,再把身旁暗器五毒核桃钉偷偷取出,握在手内,运用真力,用内家真气,侧目偷觑,见敌人趾高气扬,朝着沙老和婉如等贼党从容发话,旁若无人,越发有气,冷不防把手一扬,照准对方上下穴道,似一蓬寒星打去。
那核桃钉乃凶僧独门暗器,形如核桃,长约寸半,前头凸出一钉,约有寸许长短,另外还有五个棱角,纯钢打就,锋利无比,并有毒药喂过,中人必死,无论多坚厚之物,中上必碎。凶僧原仗着一身武功,生具神力,以前所背铁木鱼,重有上百斤,拿在手上运转如风,周身炼得和铁一样,刀斧所不能伤,纵横江湖多年。极少遇见对手,生平共总两次败在异人手内,余者所遇全非其敌,这类暗器直用不着,又因棱角锋利,无论皮革衣服均易划破,已有多年不曾携带。
自从去年向简冰如寻仇,受袁和尚戏侮,把随身招牌铁木鱼失去,心中恨毒,连夜赶回,重炼三月苦功,把手法炼熟。此次赶来,并还约了好些同觉,待寻敌人拼命,只和仇敌稍微沾亲带故的,见面便即杀死。事前访出文麟、沈煌均是冰如门下,上次受那奇耻大辱又由二人而起,越发愤怒,不料在蔡家树林内无心发现,正下毒手,被三姑出头救去,反受了一场恶气,为了三姑内外功均臻绝顶,更有一口削铁如泥专破武功的宝刀和三只神铁镖,又是老贼冯八公的义女,不得不忍气吞声,负愧而去,事后越想越恨。
这日正由外接了两个能手赶回冯家,进门听说文麟在此,想起前仇,.心中大怒,欲往杀害,后间出老贼以客礼相待,此仇难报,正生闷气,偏巧女贼冯婉如因日前蔡家席上嫌三姑神情强做,说话牢骚,目射凶光,暗中怒视。被文麟瞥见,警告三姑,令其留意。三姑本恨她平日阴险淫凶,助纣为虐,最喜长舌,拨弄是非,再听心上人这等说法,先又吃了几杯闷酒,回到席上便借题发挥,将她平日和朱、刘二人通奸,淫荡无耻,好些不堪的恶迹,指桑骂槐挖苦了一顿,对于老贼自然不无微词。
席上群贼全都愧愤,但因老贼法严心狠,三姑是他命中克星,平日百依百顺,任其当而侮辱讥嘲,仍是片面相思,爱之如命,向不计较,万一翻脸动手,不问胜败,老贼只一偏袒对方,谁都禁受不住,只得强忍怨毒,回到路上互一商量,觉着老贼老不收心,自寻苦恼,调戏三姑,以致把柄落在人的手内,任其骄横狂傲,目中无人,稍不遂意便以恶声相报,冯氏全家那等威名,竟无一人敢于发作,好容易两下疏远,断了来往,大家少受好些闲气,不料老贼表面痛恨,心仍不死,一有机会又去命人引来,帮了她的忙还受恶气,实在难堪,越想越痛恨,便由女贼为首,回去造些谣言,添枝加叶,朝老贼进谗。后将文麟擒来,便在一旁偷听,满拟不能奈何三姑,好歹也将她心爱的人杀死,稍微泄恨,不料冯大夫妇较识大体,又知他这五妹最是阴毒,所说未必可靠,先向文麟问出三姑并未泄漏老贼阴私,人又正直光明,和老贼一说,父子二人全起爱才之念,意欲釜底抽薪免得将事闹大,对于文麟毫发未伤,反对客礼相待。
婉如因想老贼喜怒无常,说话算数,看那情势,分明知道自己所说,不甚可靠,少时三姑赶来,再要把话说开,害人不成,反要吃亏,暗忖虎毒不食子,反正弄巧成拙,不如把事闹大,把文麟杀死,等三姑赶来,定必翻脸,迫得老贼不能不下毒手,永除后患,正打主意,忽然听出文麟不识抬举,说话强傲,刺中乃父心病,老贼已被激怒,只为有言在先,不便发作,恰巧前山有警,赶了出去,不曾在屋,知道凶僧对这两人切齿痛恨,正好利用,便往怂恿。
凶僧果然一点就燃,当时赶来,结果仇未报成,吃黑骷髅一劈空掌把左肩骨打碎,痛晕倒地,数十年形影不离,同恶相济的党羽也被打死,早就横心,欲用暗器拼命,先恐敌人和雷四先生一样炼有罡气,仇报不成反为所杀,不敢妄动,及见敌人大意,心中暗喜,以为共只两个强敌,自己这面虽多能手,听沙老口气,似借口自己这面人多,另约时地再决胜负,表面大方,不愿以多为胜,实则还是畏惧黑七煞的威名,又怕雷四先生铁木令,惟恐一成仇敌,难于收拾,就此下台。暗忖:“我数十年威名,如今落成残废,以后江湖上已无立足之地,你们这些老贼平日何等狂妄自大,为何一遇强敌如此怕事?人家已欺上门来,还说这类无耻的话。我且给你闹个大的,凭我手中五毒核桃钉,便是一块铜板也必打穿,黑鬼武功多高,骤出不意,只要打中穴道,断无不死之理。”
主意打好,乘着双方问答之际,猛一翻身,扬手便是大把发出。
凶僧武动也实惊人,这类四面均有尖角、锋利非常、触手即碎又具奇毒的暗器,寻常武家连一枚也无法把握,他却大把拿在乎内,全是锋尖朝前,互相凑合,并在一起,合成一根三四寸长两三寸方圆形如铁钉之物,同时发将出去,出手分散,化为十余点寒星,并还照准敌人上下穴道,似暴雨一般打去,端的又猛又急,凶毒无比。凶僧百忙中瞥见敌人不曾防备,为了仇深恨重,上来便将真气屏住,暗器出手方始发声怒吼,满拟一发必中,沙老不足恃,即便对方还攻,不能逃命也拼得过,正待忍痛纵起,以防仇敌受伤回手,能逃得过终是便宜。
说时迟,那时快!凶僧卧处偏在黑骷髅的后侧面,沙老虽看出他在装死,但知黑骷髅炼就玄门罡气,扬手便可制他死命,以为无法逃走,起身只更受辱,故意装死,挨到仇敌走后再行起身,不料会把多年未用的核桃钉发出拼命,准备借此报仇,方才匆匆相见未听说起,事出意外,心中一惊,又见婉如和众贼党均在身旁,惟恐遭了波及,仗着久经大敌,武功高强,连念头都不容转,慌不迭刚把婉如往身旁一拉,扬手一掌朝前打去,准备把旁立贼党护住,免受误伤,忽听连声惊叫,人影微闪,群贼纷纷惊避中,一股又劲又急的掌风已在身前闪过,如非先发一掌挡了一下,自己或者无妨,旁边贼党必有两人被那掌风扫中,休想活命,随听了当夺夺一阵乱响和怒吼之声,地板上叭的一声大震,凶僧已横尸在地,死于非命。
原来黑骷髅查牤为当年中条黑七煞中第一能手,天生异禀,炼就玄门罡气,耳目尤为灵警,能在隔墙百步之外打人要穴,著名的嫉恶如仇,手狠心黑,凶僧对他暗算,分明自寻死路,尤其所穿黑衣乃蛟皮所制,刀剑不入,那十余点寒星即使打上也无用处、早就看出诈死,疑要闹鬼,艺高人胆大,暗自好笑,也未放在心上,初意凶僧内外功夫均非庸手,至多暴起暗算,情急拼命,心中暗骂贼和尚一动必死,如何能够近身?后来听出凶僧手在移动,并有金铁微微相触之声,才知想用暗器猛放冷箭,暗忖:“自己内家气功已然出神入化,黑七煞的威名,贼和尚多年老江湖,断无不知之理,就说身穿黑蚊衣靠,外人不知底细,这一身刀斧不入的皮骨,岂是暗器所能伤害?”正自奇怪,忽然脑后风生,十余点寒星已如暴雨打到,因见前面还有男女贼党,又料凶僧必是想用独门暗器来打自己的七窍和身上要穴,立时就将计就计,把身一侧,装着抵御,右手一扬,“怀中抱月”之势,一面朝身后反击,顺势横扫。经此一来,女贼冯婉如仗着沙老拉开,又用劈空掌勉强挡了一下,不曾受伤,那十来个核桃钉经黑骷髅掌风反击,多半击退回去,来势更快,连具有内家罡气的劈空掌一齐打到凶僧身上。凶僧左肩负伤,本就奇痛彻骨,加以用力太猛,越发痛苦难禁,正待翻身纵起,猛瞥见所发暗器被仇敌反震回来,心中一慌,再想逃避如何能够?又当张口怒吼之时,内中一枚核钉恰巧打中口内,直通咽喉,连舌根和牙齿一齐打断,已然见血致命,那重逾千斤的内家罡气再同向胸前猛力压到,当时肝肠震裂,死于非命。
下余还有五枚核桃钉,黑骷髅有意借刀杀人,避开内中三枚,使由身旁飞过去打贼党,伸手一撮先抓住了一枚,恰巧第二枚迎面打到,更不避让,张口一股罡气照准来势噗的一喷,那寒光耀眼比箭还急的毒钉立时倒退回去,夺的一声钉向侧面横梁之上,深陷木内,无影无踪,然后低头朝手上一看,笑道:“贼和尚人虽万恶,论他武功,并非寻常,却使出这样下三门的玩意。老沙,你也曾在江湖上奔走多年,有点名头,和这类无耻恶贼为伍,也不怕丢人么?”
沙镇方见那么又狠又准、为数又多、厉害无比的毒药暗器,来势何等猛急,对方只把身形微闪,右手一扬,左手略抬,晃眼之间便全回敬过去,将敌人打死;百忙中还借刀杀人,几乎把身前逃避的同党伤了两个;下剩两枚核桃钉,一枚被其张口反喷出去打向梁上,一枚被他接到手内;眼看十余点寒星迎头飞舞已快上身,共只一眨眼的工夫,竟被从从容容避的避,打的打,无一沾身,神色自如,若无其事,不特动作神速,手法轻灵,那姿势的美妙和神态的安详,更是平生仅见,由不得又惊又佩;情知不是对手,想想自己年已八十,数十年盛名得来不易,黑七煞只一人出场,便这样落花流水,再要结成仇怨一齐引来,如何能敌?就算姜、冯两老友约有两个会剑术的异人,不久就要来到,照此情势,吉凶胜败仍是难料,大援未到,凭自己的威望,不出手不行,出手又是必败,何苦老来丢人?与其平白身败名裂,不如乘着凶僧妄发毒药暗器这点过节,就此下台,在主人与来敌未破脸以前,由自己出头把对方引开,身家既可保全,还使主人因此少掉一个强仇大敌,自己也由此退隐不再出世,免得日后又有江湖老友纠缠不清;心念才动,耳听脚步之声由远而近,料知主人父子同党已同回转,连忙大声说道:“黑老兄此言有理,且请宽坐,容老朽一言如何?”
黑骷髅还未答言,窗外蔡三姑遥闻楼梯响动,料知老贼父子已回,忙拉文麟越窗而入,朝着沙老下拜道:“沙叔父,你还认得苦命侄女蔡三姑么?”
沙老原和三姑之父同盟至交,三姑幼时也曾见过,只为隐居福建莆田,相隔大远,等到听说蔡父已死,事情已隔了好几年,退隐年久不愿远出,知道孤女家财甚富,又有老贼照应,不足为虑,也未前来访看,有时想起,还觉自己大懒,不应这等疏忽,这次为了姜、冯二贼与简冰如等异人为仇,三次专人约请人川相助,姜贼又曾亲自登门,迫于情面不便坚拒;谁知到时听说老贼正在宴客,平日谦和随便不拘礼节,武功又高,突然登门,正赶上贼党多半外出,自说:“姓沙,远道来访。”未提赴约之事。这类江湖朋友,冯家常有来往,本不足奇,老贼事前拿不准他是否肯来,未向子女徒党提说,一班后辈多未见过,便将他送往宾馆安置。还是婉如由外赶回,听出来人姓沙,年纪甚大,想起乃父昔年老友,忙即赶去,恰巧凶僧、恶道两人回来,认得沙老,见面惊喜,当即由婉如陪同上山,先到楼下客厅款待。两次要往禀告老贼,均被沙老止住,说:“多年老友,无须拘礼。现正宴客,听说又是敌人一面。此来还要多住些日,不愿张扬出去,贤侄女何必忙此一时?”婉如勉强陪了一会,终恐老贼怪罪,力言:“去往书房看看就来,如与穷酸话未说完,决不禀报。”等人走后,正想探询故人之女近况,婉如忽然回转,说:“附近山中发现敌人踪迹,父亲已然赶去。”一面和凶憎说起文麟话不投机,词色强做,乃父已是愤怒,如杀穷酸,正好下手,随将凶僧恶道引走。
沙老暗忖:“文麟一个文人,又是敌人一党,以老贼为人,怎会对他如此重视,盛筵相待,礼若上宾?其中必有原因;又觉三狗男女恃强行凶,于理不合。”忽然心动,独自赶来,想要问明情由相劝阻止,不料到晚了一步,贼党这面已一死一伤,而对方竟是昔年名震江湖、中条七煞中的第一人物黑髓髅查牤,并还持有雷四先生的铁木令,料知不妙,其势不能坐视,进门发现还有两个少年男女正往外走,十余年不见,三姑已然成了少妇,又未对面,强敌当前,全神应付黑骷髅,无暇顾及,也未在意。冯婉如知道沙、蔡两家多年至交,未和沙老商量以前,来人不曾询问,乐得不提。
沙老事前本不知道,及听这等称呼,低头一看,三姑幼年形貌还能认出,忙答:
“贤侄女请起,我正想打听你的踪迹呢。你和这位查老前辈是一路么?那太好了。先前不知铁鱼和尚会用那等下作暗器,黑老兄事前又未明言,出手就是一死一伤。我虽老朽无能,数千里远来,到此老友家中,遇上这类事情,中条七友虽只丁三老侠昔年曾有两面之缘,见面匆匆,不曾领教,别位更是素昧平生,但他七位英名早已如雷贯耳,彼此强弱相差,不是敌手,何况又有雷四先生的令符在此。无如黑老兄逼人太甚,声势使人难堪。明知不堪一击,但愿负伤回去从此杜门,也无坐视之理。未等请教,铁鱼和尚乱放冷箭,几乎连自己人也误遭毒手。这等行为和所用暗器,均与老朽平生信条有违。黑老兄如其有什过节,有意为难,不必说了。如是疾恶太甚,为这一僧一道恶迹太多,不按昔年雷四先生所说条款,轻视他的令符,一时激怒将其打死,事出无心,这类惯用下三门毒药暗器的黑道中人,便主人冯八兄事前知道,也不会容其登门。他固自寻死路,也与近日双方争斗之事无干。我想中条七友成名多年的英侠,无缘无故决不犯于恃强偏袒一方。对方如是高明之士,也不会借着他人旗鼓来壮自己声威,倚势逞强。真要不行,便由我老朽另约时地,单独请教。胜自无望,只要保得残躯,从此隐迹深山不履尘世,今日之事,也只算我和黑老兄一段小过节,与他人无干。主人同了几位老少朋友,为了门人子侄当时在外受人欺凌,新近访出对头隐居本山,意欲互约时地作一了断,我便是受人之约而来。黑老兄方才曾说无心经过,方始来此查问。现在恶人已被打死,雷四先生的令符仍和昔年一样威力,已犯不着多事再有枝节,正要开口请教,不料贤侄女会与黑老兄一路。此事再好没有。我与令尊原是骨肉之交,死时我未在场,得信已晚,相隔大远,又知冯八兄有托孤之任,故人之女得他照应,自无话说,因此未来看望,每一想起,深觉愧对良友。老朽年已八十,已将人士之人,名利之心早已消忘,为了朋友原是无法。现因贤侄女与此有关,无论有何委屈丢人之事,均由老朽一人承受。黑老兄如不见谅,老朽情愿伏低,请大驾回转中条。老朽在此,也只与昔年几位好友聚上些日,无论情势如何,只作旁观。过了月底,立即专程登门,负荆请罪如何?”
说时,老贼冯越也率子侄从党带了满腹气忿匆匆赶回。因老贼所居,除几个心腹徒党而外,连下人不奉命也不许入门,法令最严,子女如有违犯,也不加以宽贷,服役的人也都是些相随多年的贼党,当日接连发生事故,又有远客到达,这班人都正忙于约人相助,来去无常,子女贼党不是奉命他出便在宾馆陪客。老贼因连日发生拂逆之事,虽然强敌当前,例有文章,当着外人接连失利,终是难堪,表面上仍作镇静,不肯惊动宾馆中人,方才发现强敌扰闹,知道自家人少,又当怒火头上,亲自赶去。残余徒党见老贼亲自出场,纷纷随往助威,剩下有限几个,又都听见楼上有了响动,赶进屋来由峰脚起直到二楼,并无一人。
老贼只在途中听说老友沙镇方前来赴约,别无所知;多年未见,又是一个本领极高的人物,心还暗喜;刚进楼门,便听凶僧怒吼和倒地之声,还以为文麟独在房中,被凶僧走来撞见,将其杀死,方觉这等杀他正合心意,免得自己话说在先,难于下手;迎头发现蔡三姑正向沙老行礼起立,互相问答,后面站着一个头戴皮面具、形如骷髅的小黑人,所穿黑皮紧身衣裤看去松紧如意,黑中透亮,隐有鳞甲之纹,柔软异常,头上黑皮套和上衣相连,双手双足也是同样皮套皮衣皮鞋,除一片灰白色的人皮面具紧绷脸上,露出那一双黄光四射的怪眼而外,从头到脚均是纯黑,不见一点皮肤,周身装束好似天然生成一样;刚想起昔年那几个怪人的怪打扮,心中一动,目光到处,发现凶僧恶道横尸在地,酒席桌椅多半翻倒,残肴剩酒狼藉满地,到处都有核桃钉的痕迹,地板屋梁打穿了好几个洞,凶僧七孔流血之外,脸上还被核桃钉打穿了两个窟窿,凶睛怒突,头前汪着一摊鲜血,似由口中狂喷而出,死状更惨;僧道两人武功高强,硬功更有根底,天生神力,刀斧不伤,敌人未带兵器,暗器又是凶僧所有,曾听说过,来人必凭一双空手将人打死,又死得这等惨法,同时敌人来历也自想起,料已知道一切底细,不禁大惊。
再见三姑立在沙老面前,一面说话,只朝自己面带冷笑,毫未答理,知其心中恨毒;沙镇方是乃父至交,此女突然会在此时赶到,两下对面,万一说出以前丑事,多年英名付于流水;沙镇方为人又是外和内刚,机智绝伦,一被知道,甚或反脸成仇,向赴约诸人声明自己罪状,由此身败名裂都在意中,势又无法阻止;对面还立着一个戴面具的凶神恶煞,也不容自己妄有举动;宾馆中虽有几个有力同党,为首一人又因约人,天明前带了徒党二人离山他去,下剩诸人即便来此相助,也未必是今日强敌对手,何况这些人多半都是沙镇方的后辈,万一事情闹翻,丢人更快。当时急得手足发抖,脸红心跳,脊梁上直冒凉气,万分惶急之下,心神皆乱,连江湖上照例的过节都忘了交代,呆在当地,做声不得,众目之下,又不便向三姑服低告饶。
正打不起主意,忽听沙老那等说法,知道所料不差,来人果是中条七煞中的第一能手,正在暗中叫不迭的苦,心想:“这七个凶神现虽只剩四个,如同出场相助敌人,再加上雷四先生,全是有名的心黑手狠,赶尽杀绝,尤其雷四和二侠黑骷髅神行无影查忙,疾恶如仇,丝毫不肯容让,未来这场恶斗不特败多胜少,连身家性命也莫想保全;自己这面所约异人如肯来助,也还有点指望,偏又事隔多日尚无音讯。”越想心越寒,正打不起主意。
后来听出沙镇方借着凶僧妄用黑门暗器和蔡三姑与来人相识为由,想要化解此事,并将事情揽在他的身上,表面情愿向敌人服低,实则是想保全自己威名身家,和来人一同跳出圈外,不问这场争斗之事,一面去掉几个强敌,并还把雷四先生这一关一同交代过去,使对方在好高好名之下了结此事,措词不亢不卑,十分巧妙得体,在双方未破脸以前息事宁人,顾全江湖义气,不令与此无干的人加入争斗,互相树敌结怨,经此一来,自己个人少掉好些危险,他也由此袖手,回转家乡置身事外,并还借着老友叙渴看望故人之女,候到事完再去,并不当时就走,以显得他对友忠义热肠,委屈自己,乃是中有好些顾虑,为要顾全大局,不是真个怕人,只管表示对方较强,本身仍有不屈之概,分明洗手多年,此次迫于情面是不得已,再在途中听说对头方面能手大多,一世英名惟恐丧失,但又无法推谢,恰好机缘凑巧,立时就此下台,威名无损,还为朋友暗中解围,落一个面面都到;偷觑小黑人,也在微微点头,知已为其感动;方想此人由十余岁出道,纵横江湖数十年,现在年已八旬,从来不曾失过一次风,除练就极好武功、有名的铁掌铜拳外,因其足智多谋,机警绝伦,一班老朋友都叫他双料张良,果然不差。
心方一定,忽听三姑在叫“沙叔父”,猛想起沙老虽是一番好心,为人为己全都妥当,就算有心取巧,自己也实阴受共福,但是眼前还有一个活冤孽,只要当众揭发自己丑事,休说无地自容,沙老也必就此绝交,反助此女一同为仇,如何是好?当时心头乱跳,愁急万分,迫于无奈,只得颤声唤了一声:“三姑娘。”三姑理也未理,慨然说道:
“这位黑老前辈,以前并不相识,只为义弟周文麟乃雷囚先生记名弟子,知其为人良善,品学兼优,为一亡友托孤,护一孤儿入山从师,恐受人欺,将他老人家的信符铁木令赐作防身之用。因他为人正直,从不倚势招摇,平日带在身旁,从未向人炫弄,连侄女以前也未听说。后在侄女家中,被冯八公误信长舌妇拨弄是非,以为侄女对他诽谤,勃然大怒。其实八公当初原受先父托孤,身为义父,听到谣言挑拨,纵不能分别是非,是否侄女言而无信,理应随便命一人来相唤,当面对明以分曲直。即便侄女今日这等度日如年的遭遇全出他老人家所赐,心中不无怨恨,但侄女从先父去世便蒙他接到家中住了好几年,那遗弃我的昧良丈夫也是他老人家苦劝强迫力为作主而成,日常相处,性情为人当所深知,何至劳师动众,由满山云雾之中,派了许多门人子女前往擒拿,侄女恰巧前山有事,不曾相遇,于是把我义弟劫来作押。实不相瞒,先父遗命招赘丈夫,欲生子女承继蔡氏香烟,不料遇人不淑,受了好人离间和淫妇勾引,弃我而去,并还寄来休书。
本心不愿再嫁,因去年先父托梦,有好些话不便出口,想起蔡氏香烟自我而断,山中难择佳婿,又不敢再请他老人家作主,一误再误。正打不起主意,忽与义弟周文麟无心相遇,见其人品文才无一不好,原有嫁他之意。谁知生来薄命,又是弃妇,而义弟文麟虽是世家大族,也和侄女一样,伤心人别有怀抱,早已立志独身,等把他爱如性命的世侄门徒学成文武,立即披发人山,决不娶妻。不怕叔父见笑,侄女对他以前实是情痴,也曾费了许多心力,只是羞于明言,不曾出口。后被文麟看出心事,他不好意思明言相拒,却把他的心志与难言之隐婉言说出。人各有志,不能相强,他的心意又极坚绝。侄女自知福薄命浅,虽得遇到一个对心思的人,偏又固执成见,而他这人心地极好,虽然不改初衷,却极感我情义,昨夜月下谈心,双方各自拿话暗示,结为骨肉之交。侄女已然拿定主意,去向先父坟前痛哭告罪,从此不再嫁人。我把文鳞当成兄弟,问心无愧,也就不再顾忌嫌疑。天明前文麟自往暖房沐浴,无缘无故,梦中被人绑来。那铁木令系在旧衣之上,行前侍女去往浴室洗衣才得发现,与侄女看过。因旧衣已经文麟自己洗过,便命侍女送回原处,等其醒来自取,不料去的人命恶兽黄猩子把人背走,再由同党拿了他的衣服另走一路,自不小心被我迎头发现,已然打过一阵,正在途中谈说此事。这位黑老前辈与四先生至交,问明经过,知道他的门人决无庸流,再说四先生的令符也不容人违抗,才同了来。侄女年幼无知,对于冯八公的照应已然受够,以后经过不愿多言,除非万不得已、生死关头,也极不愿在人前提起一字。当着叔父在此,侄女情愿背那忘恩负义的恶名,从此决不再提冯家一字。义弟周文麟由我送他回转茅篷,从此两不相犯。
至于八公和简老前辈争斗,本来与我无干。他们多是前辈英侠,自不值与后辈弱女计较,至多为了文麟生出误会,现已明言心志,也不致再生枝节。这位黑老前辈,侄女虽是初见,幼时也曾听先父说起七位老侠的威名,和三老侠并还相识。先父昔年全家归隐便是听他所劝,家中还存有他老人家一面银符。侄女因是孤女山居,不在江湖走动,与人无仇无怨,从未用过,对谁也未提起。先父遗命曾说昔年中条山群英盛会,在座三十七位英侠为了不久都要退隐,曾将各人信符取出,传观以后,见符如见人,所到之处全有照应,如其有人故意为难,得到信符的人不妨就近寻访在场诸位英侠随时求助,只要情理上讲得过去,或受强仇大敌欺凌侵害,无求不允。先父虽未在场,隔了一月便与丁三老侠相遇说起此事,见先父听劝归隐,特意相赠,我想黑老前辈当知此事。侄女情愿凭这银符向黑老前辈求说,了却今日这场过节。那铁木令仍交文麟带走,作为今日之事全是贼道贼和尚所为,已然伏诛,便不相干如何?
黑骷髅查牤接口笑道:“你便是昔年小白旗金弓银弹子蔡天章的女儿么?三弟坐化以前,曾说他七十三面银符现均收回,只有一面留在一个姓蔡的江湖朋友手内,因其归隐多年从未与人伸手,不曾用过,尚未交还,当初答应过他,只能改行向善,以后无论有何难题,我弟兄七人和九侠、六友、四先生,当初群英会上这班好友,一见此符必以全力相助;后来此人隐居峨眉便无音讯,近年听说人已死去;此人颇有心计,必将银符传与子女,请我随时留意,发现此符,设法向其取回,另以别位弟兄信符相赠,使其平生所发七十三面令符完璧归赵。当时因事耽搁,又去海南走了一趟,历时数年方始回转。
这次来游峨眉,一半访看两位老友,一半便是访查三弟银符下落,刚到后山便遇此事。
因当初群英会一班老友曾经约定,无论何人,只一发现各人令符,便须追究来源,出力相助,不容坐视,因此赶来。既是蔡天章之女,事前听你和同行侣伴谈论,人也颇好,周文麟的事我已得知大概,此时各位老友对你也颇相谅,不致见怪,后日午前,可将银符送往金顶,我当在彼相候,见面再谈也是一样。”
随对沙老笑道:“你这老头儿,果然狡猾得有点意思,不必绕弯,我无故决不伸手。
你也趁早回去,莫要膛这浑水。他们双方争斗,我原是无心遇上。只有一贼道,我已寻他多年,因其阴险刁猾,长于隐避,始终不曾寻见,如若在内,我决放他不过。此是个人的事,与众无关。至于近在寒萼谷聚会的那班人,虽有几位老友在内,凭人家也用我不着。不必多虑,就照此女所说,我们走了。”老贼听三姑口气虽然难听,且喜丑事不曾泄漏,并知以前也未对人宣扬,又见沙老不曾追问,心中略定,见黑骷髅说完要走,照那口气,并非是应敌人之约而来,虽听出寒萼谷这面敌人甚强,少此一个异人到底要好得多,方欲就势拉拢,交代几句过场,刚把手一拱,还未开口。
黑骷髅把话说完,只朝着老贼鬼脸微动,龇牙一笑,把手一摆。三姑早有准备,取回铁木令,同了文麟当先越窗而出,正把套索拿起,想把文麟缒下,猛瞥见恶兽黄猩子独立楼下崖石之上,正在昂头向上仰望,一见文麟崖前露面,一声厉啸便纵身朝上飞来,深悔方才因气老贼不过,不愿他以客礼相送,故意抢先,改由原路退走,没想到下面还有恶兽潜伏,心方一惊,忽听耳旁喝道:“把人交我!你随后下来。”声随人到,一股疾风带着一条黑影,已由身旁闪过,捷如飞鸟往崖下射去,微闻文麟失惊之声,定睛一看,正是黑骷髅从窗中飞出,脚不沾地,直飞崖下,由身旁闪过时,就势一手挟了文麟往下飞落,同时恶兽黄猩子也张牙舞爪由地上奋身飞起,眼看两下对面就要撞上,方觉黑骷髅本领虽然极高,但那恶兽生具神力,身轻如燕,两条长臂坚逾铜铁,双方势子全是又猛又急,万一骤出不意被恶兽扑中,或是抓上一下,黑骷髅固然无妨,文麟不死必受重伤,心念才动,忽听一声惨号,就在双方快要撞个满怀之际,黑骷髅右手挟着文麟,左手凌空一挥,恶兽一条黄影已似断线风筝,往斜刺里连声厉啸,四爪乱舞,由离地十余丈处翻滚下落,比起先前势更猛急,快要倒地,喀喳一声,低头下望,原来崖边一株老树吃恶兽一把捞住,折为两段,恶兽跌在山石之上,也似受了重伤,当时爬不起来,号叫不已。黑骷髅已轻轻落向地上,把文麟放下,自行走去。随听老贼身后怒喝,似令婉如传令同党不可阻挡,并将恶兽喝住,知其有意做作,心中好笑,为防异人走远,不易追赶,忙喊:“老前辈请留贵步!”随用套索飞身援下。
那一带山崖共分三段,都是上下壁立好几十丈,三姑轻功虽好,赶到山脚,黑骷髅人已不在,只文麟一人立定相待,闻知黑骷髅行时曾说司徒兄妹先对文麟颇有误会,今已冰释。料知老贼不会追来。见日色已快偏西,二人略谈两句便从容前行。
文麟原不认路,以为三姑送他回转茅篷,感其关切之情,方才又曾当着贼党明言心事,恐其多心,也未询问,并未觉出路行已远,三姑好似有意延宕不肯快走,知其钟情太甚,想和自己多谈一会,这等痴心也实可感可怜,自然不便露出不愿之容。沿途风景又好,不是山高水深,涧谷幽寄,便是风光黛泼,松杉夹路,时见各色山禽好鸟飞鸣往来于花树之间,到处春花乱开,灿如云锦,树色泉声绵亘不断。三姑人既美艳,情又缠绵,二人并肩同行,宛如一双神仙美眷置身画图之中,外人眼里看去固然容易引起妒羡,便这一对局中人,当此春和景明之候,并肩游行在这等溪山胜处,也由不得生出一种亲密娱快之感。彼此指点烟岚云树,飞瀑流泉,悦目赏心,兴味无穷,越谈越投机,再一想到各人的身世处境,更生同情之感,一边观赏美景,渐渐倾吐心事,也就忘了行路远近。
走了一阵,不觉月影西斜,晚烟欲生。文麟见前路方遥,尚无止境,定睛四顾,觉着所行之地和四山形势均无一处见过,笑间三姑:“今早我被恶兽黄猩子由睡梦中背来,因其奔驰迅速,也不知走了多少路,离我茅篷多远?现在走了好些时候,还看不见茅篷影迹,途中地形也未见过。天已快黑,不知还有多少路才能到呢?”三姑巧笑道:“你忙什么!到了地头,包你喜欢就是。我因来时匆忙,只顾救你出险,去和老贼拼命,忘了这条路。如由前山绕来,要费不少的事,等你到后如不见人,难免多心,故此缓行。
我们走到,你苦想的人也先到了,你当是有别的用意么?”
文麟以为沈煌已回茅篷相待,三姑知道自己惦念,故意如此说法,又见三姑说时星眸微睬,似乎略带嗔容,恐其不快,忙笑答道:“我实是惦记煌儿,想回茅篷看上一下,明早便往寒萼谷一行,向司徒兄妹道谢,并看师父和各位老前辈是否在彼,为了何事与冯村争斗,因见夕阳已快落山还不见到,所行途径从所未见,以为相隔尚远,随便请问,并无他意。”三姑笑道:“你不必问,到后自知。此是后山盘蛇谷,为山中最隐僻之区,四围均有深沟高崖阻隔,休说香客游人,连久居前山的和尚和樵采人也极少有人来过。
但这一带气候温暖,风景清丽,尤其春来到处繁花,一片青碧,加上许多清溪映带,越发引人入胜,自来便是高人奇士隐居之地。那茅篷就在前方,转过崖去不过半里来路,就可见到你那想念的人了。”
文磷仍当是指沈煌而言,暗忖:“我那茅篷高居半山,左右峰岭森列,而前大片盆地,还有许多森林,与寒萼谷遥遥斜对,无论由哪面走,相隔都不止半里来路,三姑不是戏言便是另有捷径小路可以穿行。”正在回忆茅篷前面山形地势,觉着不对,人已转过崖去,前面乃是一片峭壁危崖,崖腰上面现出一片平地和数百竿竹林,林中果有一座茅篷隐现,但非原住之处,猛想起自己所住茅篷三姑并未去过,必是把路走错,到了另一隐士家中,忙呼:“三姊!我那茅篷不是这里,我们走错了吧?”
三姑闻言惊道:“那崖上住有两处人家,均是世外高人,内有一位,与老贼平日所说简老前辈行径相仿,也有一个幼童在彼习武。我只听传说不曾到过,还以为是在这里呢,不料把路走错,岂非笑话?此时天色已晚,回去还有许多的路。你在冯家只吃了几杯寡酒,由早起来还未用饭,又走这远一段山路,难免饥渴,便我一早出山,为办一事忙了半日,刚把事情忙完便接家人报信,说你被老贼擒去,忙即赶回,也是一天水米不打牙,此时想起内中一家女主人与我交厚,事已至此,只好先到她家,吃饱之后再送你走吧。”
文麟一清早便被黄猩子擒去,冯家虽以盛筵相款,无如心中有事,正以全神观查主人心意,筹思应付之法,无心饮食,未等用饭,老贼闻警走出,跟着凶僧寻来,遇救上路,空着肚子走了半天,也觉腹饥,此时对于三姑又无疑虑之念,人家好意相送,把路走错,又非故意,如何怪人?闻言笑答:“本山地理我全不知,难得有此相识高人。或行或止,全听三姊吩咐便了。”三姑笑道:“想不到你居然信我,可见天下事往往出人意料。同是一个茅篷,也许你想见的人就在里面,不是好么?”
文麟人本聪明,闻言心又一动,暗忖:“三姑久居此山,地理甚熟,听连日所说口气,不应把路走错,莫非煌儿和简老师、各位前辈高人,有两位在此不成?”方说:
“三姊不要取笑。”猛见瞥崖上有一女人影子一闪,也未看清,三姑已领文麟走入崖下山洞之中。文麟见那洞高只丈许,洞中石地平坦,甚是高大整洁,前面地上现出一团白影,静荡荡的,光景甚是昏黑,心中奇怪,便问:“三姊,到此作什?”三姑微嗔道:
“这大一个人,莫非还吃了你不成?只跟我走,包你喜欢。”
文麟不知何意,暗影中偷觑三姑,走着走着,往后退了一步,举起衣袖,似在拭泪情景,语声也微带凄苦,与沿途谈笑风生神情迥不相同,不便再问,只得随同前进,再走两三丈便到白影之处,这才看出顶上现出一洞,白影乃是天光,上下相隔不下二十余丈,靠着右侧洞壁奇石错列,左右盘旋,似与顶上出口相连。
三姑随引文麟,沿着洞壁那些上下错落的怪石,左右盘旋,手足并用攀援而上,一面悄声说道,“这家女主人姓晏,是我新交至好,无须客气。她那房舍便在对面竹林之中,外观是一茅篷,内里却有两层房舍,共住两家,东边屋内住一异人,脾气古怪,无人引进,经其允许,不可入内。进门可往西边房中走进,主人如在,自会接待,否则照直入内,无须客气。”
文麟因听主人是一女子,初次登门,如何可以冒昧走进?忙问:“三姊不是同路么?”三姑凄然答道:“我么?”话到口边又复忍任,改口说道:“我还有我的事。此非外人,只管走进,多问作什?”文麟以为三姑走了半日有些内急,笑答:“三姊有事,我在这家门外等候,事完同行。免得冒昧登门,好些不便。”三姑气道:“有我一路才不便呢,怎么不听好话,莫非我还给你当上么?”文麟见她生气,只得勉强应诺。一会绕道洞口,走了上去,又经过两条山径,便达前见平崖之上。三姑便令文麟照她所说,往林中走进。文麟还想询问,三姑已面带急怒之容,低声悄说:“我还有事,事完再见不是一样?”说罢匆匆转身,往来路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