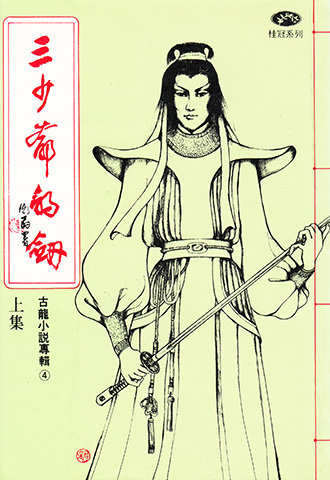话说牛子听了灵姑的吩咐,忙穿上皮衣,接过宝珠,暗取刀弩,掀帘走出,踏了雪滑子,飞也似地赶往小洞。寻了一根生竹扁担,一头挑一具贼尸,再绑上两枝石油浸透、外包篾皮的大火把。绕过横崖,径朝前山昔日长臂族猎取马熊之处驰去。火炬光强,夜间持以行路,十丈以内,本可纤微悉睹。这时还是白天,因雾气比昨日还要浓重,火在雾中看去,只是两股暗红色的焰影突突荡漾,依稀辨出贼尸和脚底一点雪地影子,首尾都不能照见,端的昏晦已极。加以沿途冰雪太厚,崩坠之处又多,地形好些变易。牛子虽然路熟,也不能不加小心,只好默记途径,试探着缓缓向前滑去。
灵姑又因牛子孤身一人在昏雾中奔驰山野,惟恐那天蜈珠奇光外映,招来怪物仇敌,抵挡不住,将珠放在一个装药的水瓷瓶内,外面还包了几层川绸,只令贴身取暖,不许取出。牛子先时颇守主人之戒。及至走了半个时辰,一算途程不过走了六七里,距离弃尸之地三停才只一停,冰雪崎岖,浓雾晦暗,不能疾驰滑行,洞中还有两尸,似此几时才能完事?越走心越发急。走着走着,微一出神疏忽,忽被地上乱冰绊倒,横跌了一跤,后半挑贼尸又吃冰崖挂住,扁担也脱肩坠落。牛子忙爬起寻视,还算好,火把有油,落在雪里只烧得吱吱乱响,不曾熄灭;脚上雪滑子也未折断;周身皮裹,伤更轻微。可是那两具贼尸弃置小洞地上已一昼夜,牛子恨透这伙恶贼,为想使其早膏兽吻,挑起特又把全身皮兜裤一一剥去,自然越发冻硬,稍用力一撅,便能应手而折,哪禁得住比铁还硬、比刀还快的坚冰去挂,人头立即脆折,离腔滚去。前半挑贼尸正是阎新,又把那只没断的左臂碰断失去,都没了影。牛子心眼最实,向来做事做彻,又恐日后老主人发现怪他,急得忙将火把取下,满地乱照。火光为雾所逼,二尺内外便难见物,找了一阵没找见。忽想起那粒宝珠光能照远,便取了出来。珠才到手上,立见紫气腾焰,奇光焕处,四周浓雾似潮水一般往外涌去,和昨晚越溪追贼时情景一样,虽不能照出太远,数丈方圆以内景物已能洞见无遗。所遗贼尸首、臂俱在冰堆附近,相隔不远,一眼便已看见,忙取了来,重新绑扎停当,挑起上路。
牛子起初只想取珠暂用,行时仍旧收藏瓶内。事后借着珠光一看前路,所有山石林木俱被冰雪封埋,除零零落落有些大小雪堆外,地甚平阔。如能照见,避开雪堆不往上撞,极易滑行,只不知再往前是否一样。试用珠照路前驰,果然一滑数十百丈,顺溜已极,景物地形也都相似,照此滑去,转瞬可达,不禁大喜。灵姑交珠时,当着老父,原未明言。牛子暗忖:“小主人不叫取珠照路,分明是怕我粗心失落。却没想到这珠红光上冲,就是失手落地,一看红光,立时可以找到。与其在黑雾里跌跌撞撞,一步一步慢腾腾受罪,还是用它,一会工夫把事办完回去的好。反正这样黑雾,狗贼绝不敢来,别的还怕什么?”念头一转,便擎珠在手,加速往前驰去,其疾如箭,不消片刻,便已到达。
那地方原是危崖之下的一片森林,平日草莽没肩,古树排云。以牛子的眼光、经历,早看出那一带必有野兽出没。一则地势较偏,吕氏父女轻易不去;二则洞中肉食无缺。
又因以前凶徒曾在那里猎杀马熊,后来发现凶徒踪迹系由死熊而起,这类兽肉膻臊,山人视为异味,汉人却不喜吃;灵姑经过当地几次,并未发现兽类,因而无意及此。牛子知道崖上下有无数大小洞穴,尤其崖阴一面崖形上凸下凹,像一口半支起的大锅。内里怪石磊砢,有天生成的盘道。洞穴俱在上层,离地又高,多大冰雪也封堵不了。哪怕平日因洞大黑暗,寒冷当风,野兽不居,这时却是它极好的避寒过冬之所,怎么也藏有几只在内。
及至寻到崖下一看,凹口果然还有两丈没有被雪填没。牛子便将火把点旺,用力投了一枝进去。凹外积雪虽高,凹内原是空的,这次是雾浓而沉滞,不甚移动,没有侵入,只近口处有些,已被宝珠光华荡开。凹洞聚光,火把落处,照得清清楚楚。牛子本心想将野兽引出再抛贼尸,看了一会没有动静,拿不定有无野兽潜伏,恐万一料错,弃尸在此,开春雪化,被人发现。方一踌躇,忽听轰隆大震,和着浓雾中崖壁山野沉闷的回音,兀自不息,牛子忙舍死尸,循声赶去,见是一株半抱多粗的老杉树不知怎地断折在地。
乍看还当是树顶冰雪凝积过重,将树压折。继一寻思:“杉树都是直干,这么深厚的冰雪,还高出地面好几丈,身粗根固,可想而知。上半枝叶不密,不曾多积冰雪,就算是雪压倒,不应该断了上半截,怎断处离地才二尺上下?四外松杉好几十株,怎么也一株没断?”心中奇怪,不禁目注地上,见那树干上有好些巨兽爪痕和蹭伤迹印。再一细看,不但别的树上也有同样痕迹,中有一株老松,因是枝叶繁茂,将雪承住,下面围着树干陷出宽约二尺一个空圈,圈旁冰雪还有好些深裂爪印,看神气好似野兽向树干上蹭痒,失足陷空,死命抓爬上来留下的残迹。牛子这才明白,当地雪后实有野兽盘踞来往,适才所断之树,乃是它们日常擦蹭所致。既发现在此,早晚必来,何必费事把死尸往崖凹里塞?忙回崖前,将二尸取来弃置地上,匆匆便往回赶。有宝珠光华照映,归途又是熟路,加急滑驰,一会便到。将余下两具贼尸绑在扁担上面挑起,二次往弃尸之处驰去。
沿途无事。眼看滑到崖前树林之内,牛子正觉滑行顺溜,心中高兴,忽听前面林内似有猛兽咆哮扑逐之声。心方一惊,珠光照处,瞥见两团蓝光,一只牛一般大的野兽嘴里衔着东西,还有一只张开血盆大口追逐在后,首尾相衔,由斜刺里急蹿过来。牛子忙于事完回洞,滑势迅速非常,又是明处,珠光以外不能辨物,肩上又挑着尸首,人、兽都是急劲,等到发现相隔已近,回转已经来不及了。牛子见状,刚喊得一声:“不好!”
脚底早顺前溜之势,朝头一只野兽冲去,一下撞在后股上面,撞得脚骨生疼,上半身朝前一扑,连人带肩挑尸首,径由兽股上跌翻出两三丈远。随听两声震天价的虎啸,眼前一花,连吓带震,就此跌晕过去。
牛子醒来,闻得群虎怒吼之声近在身侧。睁眼一看,离身不远,珠光之外暗影中,连大带小,竟蹲着三只斑斓猛虎,俱在光圈边际磨牙伸爪,咆哮发威,各竖身后的长尾,把地打得山响,激得寒林树干簌簌振动,碎冰残雪乱飞如雨。牛子不禁胆裂,忙即纵起,往后逃遁。才一回头,谁知身后和右侧还蹲踞着四只大的,也在发威欲噬,怒吼不已。
左边又是危崖,简直无路可逃。刀弩已于跌时失去,只有一珠在手。方在惊悸,忽瞥见四虎齐都怒吼倒退,并未扑来。百忙中再一回看,前三虎却似走近了些,蓝睛睞睞,凶光如炬,只现虎头,后半身仍隐光外暗影之中。先还不知虎俱宝珠,一时情急无计,妄想往左攀援崖壁逃避,便试探着缓缓往左横退两步。牛子一退,这大小七虎也跟着进了两步,可是与前一样,并不逼近。似这样人退虎进,快要退到崖上。牛子回顾冰崖百切,冰凌如刀,莹滑陡峭,难于攀升。下面崖凹又是虎穴,恐要再有虎由内冲出,四面受敌,先前主意只得打消,不敢再退。正站在那里惶急害怕,虎本隐身光外,只七个虎头在光圈边上出没隐现,见牛子站立不动,互相怒吼一阵,内中一只大的倏地暴啸一声,往光圈里一探,前爪抓起一尸,便掉转跑去,下余六虎立即吼啸连连,相率隐退。晃眼虎头一齐没入黑影之中,随在附近林内扑逐咆哮起来。
牛子见那抓去的正是一具贼尸,先前似在自己身下压着,逃命匆匆,没有理会。经此一来,方始醒悟虎畏宝珠,因贼尸在宝光圈内,不敢逼近。等自己退出,贼在光圈边上,才行攫取。否则自己适才撞虎跌晕,早被虎吃下肚去了。虎吃死人,可知饿极。另一贼尸不在光内,早落虎口无疑。欣幸之余,胆力顿壮。查看身上,且喜平跌,没有撞在坚冰。树木之上,只手、臂、腿、膝等处有些疼痛,并不甚剧,走动也还如常。再看脚上雪滑子,一只前半折断,尚可绑扎;另一只却在跌时脱落,不知去向。心想:“冰雪满山,没有雪滑子怎能走回?还有腰刀、弩筒与扁担等物也须寻取到手才行。”反正手有宝珠,虎不敢近,便借珠光照映,满处寻找。雪地平滑,不多一会,全都找到。只跌时势太猛急,弩筒甩出时正撞坚冰上面,将筒跌散,一筒十二枝弩箭只找到九枝。牛子忙于回洞,懒得再往下找。一听林中群虎尚在争食未完,匆匆将雪滑子断绳接好,绑扎停当,试了试也还勉强,便自起身回转。
走不多远,忽听身后山风大作,虎啸连连。群虎想是没有吃够,见人一走,又复不舍,从后追来。此时牛子虽然胆比前大,但二次被虎一追,拿不准宝珠是否真有御虎功效,终不免胆怯心慌。脚底雪滑子一好一坏,滑驶吃力,再加之长途往返,奔驰了半日,人已有些疲乏;跌时所受的伤,惊慌惶遽中不觉怎样,跑起来便觉到处酸痛,腿脚也没以前灵便:因而比初来时滑行速度差了好几倍。耳听啸声越近,回顾身后,虎影已在离身三四丈处隐现,好生惊惧。离洞尚远,无法求援,只得咬牙忍痛,拼命向前疾驶。牛子逃了一半途程,忽然急中生智,改用扁担支地,单脚滑行,居然要快得多。虎在冰雪地里原跑不甚快,遇到险峻之处也常常滑跌,约有半盏茶时便落了后,但仍是穷追不已。
牛子听出啸声渐远,一看途程已将到达,心始稍安。快要转过洞前横崖,猛见一道银虹照耀洞前,跟着有人呼喊他的名字。越发心定,忙赶过去。
原来灵姑久候牛子不回,惟恐被贼党寻来受了暗算,借故赶往小洞。一看四具贼尸已无踪影,别无朕兆,雾也较前更重,不似贼党来过神气,料是牛子埋尸未归。方要回去,才出洞口,便见天蜈珠红霞宝气上冲霄汉,知牛子背地擅用宝珠照路,不禁生气,正待数落。及见牛子气急败坏跑来,皮衣裤上好些破裂之处,神情惊慌,甚是狼狈,心疑遇变,便问:“你怎么这个样子?”牛子喘吁吁答道:“老虎追来了!”灵姑呸道:
“你真废物,一只老虎也值得这样怕法?”牛子道:“哪止一只老虎,多着呢。”随将前事说了,只把存心弃尸的私见隐起。
话没说完,便听虎啸之声自崖前传来。灵姑猛然触动心事,暗忖:“洞中失盗,正缺肉食,这雾不知几日能退,又没法往寻贼巢。如能打着一只大虎,表面不说,暗将腊腿、香肠供老父一人之食,嘱咐别人专吃虎肉,怎么也能度完明年正月,事情就好办得多了。”念头一转,忙喊牛子快跑,同往崖前追去。
那虎原本不止七只,先后发现四具尸体,群虎争夺之下,前两尸已被几只大虎一阵抢夺分裂,衔回洞中大嚼,下余好些没有到嘴,正好牛子二次送食上门,滑势猛速,撞在虎屁股上,死尸脱肩甩落,人也跌晕过去。一尸落在光外,被两只大虎备撕一半衔回洞去。下余七只,因见一尸落在宝珠光里,虽然猴急,却不敢走近。直到牛子醒转退避,盗尸快出光外,才行抢去,七虎都是饿极,纷纷扑夺。这次虽得各尝一宵,仍因大虎霸道,小虎吃亏,到嘴有限。想起还有一个活人,味更鲜美,虎目本锐,长于暗中视物,又惯嗅生人气味,加以极强宝光照耀,于是相率望光追来。重雾迷目,连遭滑跌,依旧不退,反更暴怒。可是宝珠辟虎,虎虽馋饿情急,一到追近,却又不敢往光里冲人。稍一落后,便又紧追不舍。
灵姑放出飞刀本为照路,牛子一到,便已收起。及至迎向崖前,虎也恰好赶近。灵姑因听牛子说虎似畏珠,意欲试它一试。刚把牛子刀、弩要过,就有四只虎追来,果在光圈之外咆哮,磨牙张口,只露前头,后半身隐在雾影里看不真切。灵姑见状,忽起童心,用刀砍了些冰块,向虎投掷,又用刀伸前撩拨。激得虎越发暴怒,发威狂吼,只不敢冲进。牛子也学样用冰乱打。
二人逗了一会,灵姑猛想起离洞太近,时候久了,恐老父闻声出视,泄露失盗机密。
又不愿多伤生物,只想挑一只大些的杀死带回。左手按定弩簧,右手握刀,纵向前去,照准内中一只大虎一刀砍去。这时牛子站立未动。灵姑因逗弄了一会,觉虎无甚能为,一时疏忽,看事太易,又想将虎皮剥下铺地,留下虎头,自恃身法灵便,用刀横砍虎颈,身便出了圈外。忘却虎乃山中猛兽,矫健凶猛已极;况且下余三虎虽未与这虎并立,却是一扑即至,而且又都红眼,早恨不能搏人而噬,丝毫大意不得。刀刚砍中虎颈,虎负痛大怒,用尽天生神力,狂吼一声,往后一跳。以致刀嵌虎颈未能拔起,灵姑虎口也几被震裂。这一眨眼的工夫,旁立三虎为宝光所阻,本是情急无奈,见人出圈,立即纷纷怒吼扑到。灵姑正想用力将刀夺回,猛觉左右风生,雾影中两对拳大蓝光朝自己冲来,知虎扑到,当时情势又不宜于退回。幸好她心灵敏捷,纵跃轻巧,见势不佳,就着前虎嵌刀人立之势,脚尖点地,两脚先已朝天凌空飞起,同时右手握刀一按劲,随即撤手,向前面雾影之中倒翻出去。翻起时百忙中没有留神,左手臂微微下垂,竟被虎爪尖挂了一下,尚幸身穿厚皮,未受重伤,那左臂皮袖却已被抓裂,臂骨也撞得生疼。虎仍怒吼追来。牛子瞥见灵姑翻出圈外,三虎怒吼追去,好生惊急,也赶了来。虎见珠光,又复纵避。灵姑又把飞刀放出,微一掣动,便将一只小虎斩为两段,另二虎望见银光,才知厉害,惊窜逃去。
灵姑还欲追杀,王渊在洞中闻得崖前虎啸,持火赶来。灵姑忙问:“爹爹知道也未?”王渊说:“伯父闻得虎啸,怕伤洞内牲畜,想出来寻你问问。我说大洞既然都听得见,姊姊、牛子不会不知,此时必在打虎。娘又从旁劝阻,我才跑出寻你。这虎怎会到此?听叫声还不止一只呢。”二人说话一耽搁,虎已逃远,不闻声息。先受伤的大虎负痛疾窜,跌向大树下面虚雪窟里。那把腰刀,因灵姑纵时左臂受伤失惊,撒手稍慢,竟被巧劲带出,落向一旁。三人匆匆寻找,见地虽有虎血,大虎却已不见,刀则在远处寻到。以为大虎将刀甩落,带伤逃走,不愿穷追,合力将小虎抬了回去。
吕伟问虎伤了小洞牲畜没有。灵姑说:“虎在雾中一点不能视物,先是在远处吼叫,牛子想吃虎肉,闻声往寻。虎见珠光跑来,又怕天蜈珠,不敢走近。现在杀了一只小虎,还有三只,女儿不愿多杀,已然放它们逃走。虎连崖都未过,怎会伤害牲畜?况且牛子昨日已然防到雪后野兽乱出寻食,将小洞口加了木栅,就来也进不去,爹爹放心好了。”
吕伟信以为真,便不再问。灵姑进洞时,便将虎爪抓裂的上衣脱去更换,好在受伤轻微,稍敷自制伤药,即可痊愈;便没提起。
说完,大家合力开剥虎肉,先将虎皮揭下,后将肚肠取出弃掉,洗涤干净,切成薄片,围火烤吃。那虎也有骡一般大,肉颇鲜嫩。灵姑因洞中肉食将罄,正在为难发急,不料有兽可猎,心里略宽。
这场雾直下到除夕半夜,方始逐渐减退。灵姑和王妻既要瞒住吕伟,山中头一次过年,还得像个样儿。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只得就着大洞平日余存的一点东西配合筹划,费了好些心思,勉强把年供;年食备办停当。可是这样竭泽而渔,吃一样少一样,预计过了正月十五,只有蔬菜还多,食粮也仅敷二月之用,余者还有一些雪前未及运藏小洞的干果、种籽,肉食就没有了。
贼党自从乘橇逃走,终未再来。灵姑每日盼着雾退,除夕半夜出洞祭天,火光照处,见雾已稀薄好些,料雾一退,贼必来犯,这次好歹生擒他一个活的,只要说出下落,就能夺回失物。当晚借词守岁,私往小洞烧香,暗中守伺,以防贼来。快到天明,一阵大风刮过,残雾全消。虽还不见星光,天色迷蒙,东方已有曙色。到了天明,居然出现晴空,东方渐渐涌出一轮红影,天际寒云浮涌其间,隐隐透映出一层层的霞彩,衬着万峰积雪和灰蒙蒙的天色,静荡荡的山林原野,越显得景物荒寒,境地幽寂。三人在浓雾中沉闷了好些日,乍见天日,好生欢喜。
祭神祭祖之后,吕伟听说天晴,也要出视。灵姑苦苦劝说:“天冷冰滑,风又太大,天不转暖,定不放爹爹出门。”吕伟只说自己一病,爱女成了惊弓之鸟,怜她至性,也就罢了。
当日不见贼至,灵姑满以为除夕元旦,也许贼正忙着过年,不愿出来争杀,至多过了初五必来无疑,谁知到了初六仍毫无动静。雾住之后,寒风又起。日光只在初一早上露了片时,此后终日愁云漠漠,悲风萧萧。只正午偶尔在灰云空中微现出一点日影,也是惨淡无光,天更奇冷透骨。鹦鹉灵奴平日遇事总喜自告奋勇,背地已对它说过,迟早要命它去探贼巢所在,但俱未答话,可知畏冷难禁。又恐平日里飞去为贼毒弩所伤,想了几次,俱不放心,也未遣去。
一晃快到十五,灵姑不由着起急来。屡和王渊、牛子商量,渐渐觉出贼党虽与后山尤文叔所投之贼来路相反,但这类积年为害山寨的匪徒素来勾结,即便不住在一起,也必通气。况且玉灵崖形势险要,除却尤文叔,素无外人足迹,文叔走后不久,便出这事。
可惜伤贼已死,没有问出口供,弄巧还许是文叔勾引前来也说不定。王渊想起那日往小洞寻药遇贼情景,虽恐灵姑怪他,不敢明说,也极力在旁怂恿,欲往探看。无奈后山贼巢道阻且长,尤其那座高峰是个天险,平日还是攀藤附壁,横峰而渡,目前冰封雪固,如何得过?崖后危壁下面那条石缝通路地势凹下,料被冰封雪埋,也没法出入通行。
为难了两天,未了牛子道:“贼终有个路走。那晚过溪追他们,半路上不见雪地橇印就跑回来,离绝壑还有一段路也没去看,怎知不是绝壑被冰雪填满了呢?那大雪橇我也会做,比他的还好。年前缝洞帘剩皮还有,别的木料、竹竿贼没有偷,更是现成,何不做一个,顺他来路前后左右细细查看一回?”灵姑称善,随命赶制。当晚制成。
灵姑以为老父自从病起,便照仙人所传练气之法,日常打坐习静,几次想到洞外游散,俱吃自己劝阻,近日一意打坐,已不再提出洞的话。自己去这半日,想必他不会走出。万一走后,恰巧贼党来犯,凭老父的本领,足可应付。一面暗嘱王氏夫妻随时留心贼来,老父如出,务须力阻;一面假装游戏,给灵奴做了一件棉衣,暗告灵奴:“我知你难禁酷冷,不带你去。但我走后,如贼突然来犯,事关紧要,你无论如何均须飞寻我们报警,不可胆怯。”灵奴只说:“贼怕飞刀,现时决不会来,主人放心。”灵姑一想也对,否则那日逃贼见同党遇敌动手,早进小洞相助了。
嘱咐完毕,随即借题起身。走到小洞一看,牛子所制雪橇果然灵巧结实,三人同乘甚是舒适,只是没什么富余地方。王渊笑问牛子:“怎不做大一些?如把贼巢寻见,那么多东西怎么运得回来?”牛子道:“这群猪狗偷我们东西,到时还不逼他们运还,要我们费事么?”灵姑道:“那么多的东西,不知要运多少次才完。这么多天来糟蹋掉的还不知有多少,真气人呢。”牛子道:“这群猪狗既然在这山里打窝子,他们平日不是偷就是抢,还有从各山寨里明夺暗骗弄来的东西一定不少。今天寻到贼窝,都是我们的,回来只有加多,只不能原物都在罢了。”王渊道:“那还用你说,先前被狗贼杀了的那些牲畜就没法还原。”灵姑催走,三人随将大橇运向洞外。除随身兵刃、弩箭、干粮和应用器具外,走前牛子又急跑进洞寻了一条坚韧的长索出来,以防遇见高崖峻壁,可以悬缒上下。
那雪橇形如小船,与雪滑子大同小异。前端向上弯翘,正面钉着一块雪板,板后尺许有一藤制横板可以坐人。两边各有一个向后斜立的短木柱,上嵌铁环,环内各套一柄枣木制成长约三尺的雪撑,撑头有一寸许粗细的握手横柄,另一头装有三寸来长的锋锐矛头。板后尺许又有一个皮制靠座,同样设置,只比前高些。座后便是橇尾。靠背底下有一块横大板,边沿随橇尾略为上翘。两边各有一舵。底部粗藤细编之外,还蒙上一层牛皮,铁钉严密,再加上三根两指宽的铁条。三人两坐一立。滑行起来,两人双手各握一柄雪撑,后一人先站橇外猛力向前一推,跟着纵向靠背后面,手握舵柄一站,同时前坐两人用雪撑向后一撑,那橇便在冰雪地里向前驶去。
一切停当,牛子因掌舵的事不大费力,却极重要,生手做不来,便叫王渊坐在橇头,灵姑居中,自站橇尾掌舵。橇长连两梢不过八尺,通体只用一块木板,三根铁条和六根长短木棍,余者俱是山藤牛皮,轻而坚韧,一旦滑动,其疾如飞。灵姑、王渊初乘这种雪橇,又有宝珠御寒,毫不觉冷,俱都兴高采烈,快上还要加快,各自用力,不住地将手中雪撑向后撑动,两旁玉山琼树,闪电一般撇过,端的轻快非凡。还是牛子因雪后地多险阻,恐怕滑太快了撞翻出事,再三大声喊阻。灵姑见已滑到乱峰丛中,为要查看贼踪才滑慢了一些。贼留橇印尚存,看了一会不见端倪,又往前驶。
走不多远,仍和那日一样,橇印忽然中断,沿途也不见有弯转痕迹。三人想不出是何缘故,仍旧照直驶去,顺着橇印去路,滑行迅速,也未留神查看地下。不消片刻,忽见大壑前横,深约数十丈。对面又是一座峻崖矗立,又高又陡。两边相去,少说也有十来丈远,照情理说,贼橇万不能由此飞渡,三人更过不去。灵姑终不死心,又沿壑左右各滑行了二三里,两岸相隔竟是越来越宽。左右遥望,那崖一边连着许多峰峦,一旁是峭壁高耸,浓雾弥漫,望不到底,而且越往左右走相隔越宽。因去贼橇来去途向已远,毫无迹兆可寻,以为再走远些也是徒劳;又疑贼党故布疑阵,也许中途还有弯转之处,适才滑行太速,看走了眼,便今回转。到了贼橇印迹中断处,缓缓滑驶,沿途细加查看,一直滑回乱峰丛中,仍是除了贼橇来去迹印外,什么也未看见。那数十座石峰俱是整块突立的石笋,尽管灵奇峭拔,千形万态,并不高大,决无藏人之理。三人失望之余,没奈何,只得回向玉灵崖驶去。
归途细查贼踪,橇行本缓,又绕着群峰乱穿了一阵,连来带去,加路上停驶,差不多也耗了两个时辰。快要驶抵洞侧小溪,忽听两声虎啸。灵姑心动,抬头往对岸一看,老父手持宝剑,足底好似没踏雪滑子,正在崖那边绕向大洞走去,虎已跑没了影。王守常拿了把刀正好迎上,两人会合,一同回转,互指小洞,似在商议甚事。灵姑不知离洞这一会工夫机密已泄,只当老父闻得虎啸追出,吃王守常拦阻,没有走往小洞探看,心还暗幸。恐老父看见自己乘橇疾驶,盘间难答,悄嘱王渊暂停,等二人回洞再滑。不料吕伟已经瞥见爱女回转,遥喊:“灵儿立定相候。”
灵姑见瞒不住,一面盘算答话,一面应声,催着疾驶。晃眼过溪到了洞前,见老父面带深忧之色,正在心慌,吕伟已先开口问道:“洞中失盗这等大事,灵儿为何瞒我?
贼党被杀,决不甘休。你三人远出寻贼,我如知道,还可预防;你只顾怕我忧急,万一贼党乘虚而入,有甚失闪,岂不更糟?此行可曾发现贼党踪迹么?”
灵姑本因肉食将完,余粮无多,最近几天如不寻到贼巢,早晚必被老父看破,心中焦急,左右为难;如今事已泄露,自然不再掩饰,婉言答道:“女儿见识不多,爹爹不要生气。外边天冷,请进洞去细说吧。”当下老少五人一同进洞,为备后用,把雪橇也带了进去。父女二人脱去皮衣、兜套,各说前事。
原来三人走时,吕伟正在开始打坐。王、牛二人当他已然闭目入定,藏挂兵刃之处又在左侧不远,一不留神,有了一点响声。吕伟何等心细,听出在取毒弩,偷眼一看,二人果向弩筒内装换毒箭。爱女满面愁容,正和王妻附耳密语,好似有甚么要紧事情似的。暗忖:“二人说往小洞清扫,带这齐全兵刃则甚?即便雪后打猎,也可明说,何故如此隐藏?女儿又是向不说谎的孝女,其中定有原因。”疑念才动,猛瞥见牛子小屋中探出一个牛头,又听小鹿哟哟鸣声。吕伟忽然想起:“年前女儿说牛、马、小鹿有病,带来大洞调养,后来查看并无疾病。素性好洁,恐遗污秽,屡命牵回小洞,女儿总是借口推托。说到第三次上,意是怕我嫌憎,竟藏向牛子房中喂养。因怜爱女,也就由她。
现时一想,小洞还有不少牲畜,怎单这几只怕冷,无病说病?是何缘故坚不牵去?再者,自己只要一说要出洞,众人便齐声劝阻。近来女儿脸上又时带愁容。许多都是疑窦,难道出了什么事不成?”思潮一起,气便调不下去。勉强坐了一会,越想心越乱,决计赶往小洞查看。
事有凑巧。王氏夫妻知吕伟这一打坐,少说也有一两个时辰,没想到他会走,也就一个人房更衣,一个在牛子房中喂饲牲畜,以为一会即可毕事。直到吕伟穿着停当,掀帘将出,出声招呼,才行得知。忙赶出劝阻时,吕伟已走到洞外,纵上雪堆了。王守常匆促追出,没戴皮兜,刚一掀帘,猛觉寒风凛冽,扑面如刀,逼得人气透不转。又自暖地骤出,当时手僵体颤,肤栗血凝,机伶怜打了一个寒战,其势不能禁受,连忙退了回来。王妻更是怯寒,才迎着一点帘隙寒风,便觉冷不可当,哪里还敢出去,在自焦急。
手忙脚乱帮助王守常把寒衣穿上,赶出洞外,吕伟已然穿上雪橇,滑往小洞。
吕伟先进小洞一看,见各栅栏内所有牲禽一只无存,地下留有好些血迹。细一辨认,中有两三处竟是人血,新近经过扫除,尚未扫尽。料知洞中出了乱子,已是惊疑万分。
回身再赶往二洞,恰值王守常追来,见吕伟面带愁容,由里走出,知失盗之事已被发现,无法再瞒。吕伟关心二洞存粮,忙于查看,只问:“这事老弟知道没有?”不等答话,便往前走。王守常虽知小洞牲粮被盗,王妻恐他忧急,并未详说,想不到失盗得如此厉害,也甚骇然。便答:“我不深知。”说完一同赶往二洞一看,见平日众人辛苦积聚,连同入山时带来粮米食物,以及文叔所有存物,俱都荡然无存,只剩下笨重东西和一些田里用的农具没被盗走。灵姑、王渊、牛子三人一个不在。
二人这一急真是非同小可。吕伟生平多历危难,比较沉得住气,王守常则急得跳足乱骂,脸也变色。吕伟反劝他道:“看老弟情形也不知晓,事己至此,愁急无用。前洞遗有刀斧、铁条和新砍裂的竹竿、生皮;牛子昨日来此一整天,今日吃饭又甚忙,丢下碗筷就走;适才他们走时俱都带上兵刃暗器;分明年前贼来次数甚多,被他们每日守伺。
遇上杀了两个,问出巢穴,雾重不能前往;雾开想去,又因冰雪梗阻,才由牛子做成雪滑子一类的东西,今日乘了,同往贼巢搜寻。怕我两个发急,意欲寻回失物之后,再行明说。记得那日弟妹曾给他们送那宝珠,回洞时带去牛、马、羊、鹿及很多菜蔬,年下用的一物没有带回。以后我每想出洞,必遭灵儿苦劝。二人又不时背人密语,从此便不闻再令人往小洞取东西。我还恐弟妹体弱,残年将尽,准备年货实在劳累,既能将就也就罢了。此时想起,竟是别有原因,弟妹定知此事无疑。可恨灵儿只顾怕我病后不宜气急,却不想想此事关系我们食粮日用尚小,虽然全失,本山有兽可猎,野生之物甚多,还有菜粮、种籽,只一开冻,便可设法,至多白累了这几个月,决不致有绝粮之忧,可是盗党来者不善,善者不来,盘踞荒山绝域的能有几个庸手?况且这等冰雪,远出行劫,历经多少次,没有本领,如何敢来?敌人不犯大洞,只来行窃,可知并无仇怨,为何一动手便将人杀死?从此结下深仇,乘隙相报,不特防不胜防,对方再有高人,岂不关系全洞安危,成了我们一桩隐患?去时又不说一声,我们留守的人一点防备没有,真个荒唐极了。”
王守常答道:“侄女走时倒对内人说过。”刚说到这里,王妻已经到来。原来她催王守常走后,忽又想起丈夫也只知大概,恐二人相对愁急,丈夫又答不出详情,忙即穿着停当,冒寒赶来,便接口说了前事。
吕伟一听,盗党被杀的竟有四人之多,余党因怕飞刀,并未再来。这类无恶不作的土匪虽然有余辜,偏没留下活口问他巢穴所在,冰雪茫茫,崎岖险阻,何从查找下落?
想了想,觉着此事一日不完,一日不能安枕。便叫王守常送王妻回去,自在洞外忙看橇迹,忽听虎啸之声。心想洞中肉食将完,正好行猎。忙赶回大洞取剑赶出,那虎已由崖角探头缓缓走出。吕伟不知那虎后面还有一只大的蹲伏在崖前转角处,又因灵姑嫌年前所杀之虎皮不完整,为博爱女欢心,想用剑刺中虎的要害,以便开剥整皮,见虎立即赶去。偏生那小虎从别处深山中蹿出,初次见人迎面跑来,觉着奇怪,吕伟气又特壮,虎更有些疑惧,只管四爪抓地,竖起虎尾,龇牙发威,却不敢骤然前扑。吕伟看出是只小虎,暗自得计,随把脚步放慢,意欲身体靠近,再故意反逃,诱它追扑,然后用生平最得意的回身七剑去刺虎心。等走到双方相隔不过丈许远近时,虎仍未动。吕伟身刚立定,目注虎身,正待假装害怕,返身诱虎。这类野兽何等猛恶,本已蓄势待发,起初不过暂时惊疑,略为停顿,及见敌人举剑迫近,倏地激怒,轰的一声猛啸,纵起便扑。吕伟知虎是个直劲,一见扑到,并不躲闪,只把身子往溪侧略偏,让过正面,迎上前去。
那只大虎最是凶狡,听小虎在前发威,由石凹里掩将出来,悄没声一纵两三丈高远,朝着吕伟飞扑过来,来势又猛又急,和小虎只差了两头,落处恰在人立之处。吕伟剑才举起,方欲让过虎头,由横里进步,回向正面,由小虎腹下上刺虎心,忽觉迎面急风,猛瞥见一只斑斓大虎当头扑到。还算身法灵巧,武功精纯,久经大敌,长于应变,一见不妙,地方正当溪岸窄径,一边是崖,此时已顾不得再刺小虎,百忙中把身子一矮,径向溪中斜纵出去;同时反手一剑,朝虎便刺。纵时大虎已经扑落,双方几乎擦肩而过,稍迟瞬息便会被扑中。这一剑原想去刺虎头,不料那虎落得大快,竟被错过。剑往右刺,人却往左横退,双方方向相反,虽然劲要差些,剑只刺中虎的左肩,没有深中要害,可是虎也吃了太快大猛的亏,剑又锋利,竟被剑尖由深而浅,从左肩斜着向上划伤了尺多长一条伤口,鲜血四溅。大虎负痛着地时再往前一蹿,正撞在小虎左腿股上,小虎吃不住劲,又被斜撞到危崖上面,右额角被坚冰撞破,几乎连眼都撞瞎。两虎受伤俱都不轻,疼痛非常,才知人比自己厉害,不禁胆怯。
吕伟因见了两只虎,不知崖前还有没有,又因匆匆赶出,忘携毒弩,恐虎尚多,防受前后夹攻,只得追到崖后。刚刚纵落,两虎己然掉转身子向来路逃去。吕伟想不到虎会知难而退,连忙追赶。偏又脚底没踏雪滑子,过崖口时还得留神,稍一耽搁,虎已一跃数丈,连蹿带蹦,逃出老远。等王守常持了兵刃暗器赶出相助时,早没了影。灵姑等三人也已回转,父女二人见面说完前事。
众人商量了一阵,只想不出贼橇遗迹半途中断是何缘故。灵姑因老父年迈,好容易千山万水来到此地,辛辛苦苦费尽心力筹办劳作,才积聚下这许多物事,忽然一旦荡尽,虽然耕具尚存,牛还有两只,开冻即能耕种,大洞所剩食粮加上行猎所得,不至便有绝食之忧,但比起平时百物皆备,那么舒适充裕,终是相去天渊,老年人的心里岂不难过?
那贼又是鸿飞冥冥,不知道何时才能寻到他的巢穴,夺回失物,不禁焦急起来。
吕伟心中自是忧急,只没显在面上。见爱女发愁,便安慰她道:“灵儿无须忧虑。
那贼如用妖法行路,尽可直落洞前,何必只空一截?我想他绝非由对壑照直驶来,必是另有途径,将到达时故意变换方向,来乱我们眼睛。只不知用什么法儿掩去迹印。你们年轻人心粗,只照橇迹追踪,不曾仔细查看。明早我和你带了牛子同往查看,许能找出一点线索,好在洞中尚有月余之粮,菜蔬尽有,至多缺点肉食,何况还有野兽可猎。事有命定,忧急无益。”
灵姑道:“适才见那橇迹,到尽头处连宽带窄只两三条,并无错叠之痕,好似来去都循此迹一般,可是越往这边来迹印越多。听爹爹一说,才觉此事奇怪。贼党来往小洞少说也十几次,沿途俱是广阔无比的冰雪平野,贼来有时又在黑夜之中,既是那么大举来偷,如入无人之境,况已留有迹印,还有什么顾忌?怎会对得如此准法?听爹爹一说,才得想起,真像贼党从侧面远处乘橇驶来,等到离洞不远,再改为步行,将橇抬到正面,重又乘橇滑行,使那所留橇迹正对绝壑,叫人无从捉摸。那绝壑又宽又深,对岸危崖,人力万难飞渡,照情理说,橇迹应由壑岸起始才对,怎又离壑里许才有呢?”吕伟道:
“灵儿真个聪明,这话有理。照此猜想,贼党十九是由侧面驶来,不是对岸。你问怎不由壑岸起始?不是嫌远偷懒,便是无此细心。橇迹左边尽头与玉灵崖后峭壁相连,中间山石杂沓,崎岖难行,料他不能飞越。只右边远出二十里,危峰绵亘,森林蔽日,我们从未深入,贼由此来居多。明早去时多带千粮、弩箭,就料得对,恐也不是一时半时能寻到。如仍无踪,就便打点野兽也好。”灵姑应了。当日无话。
次早起身,吕伟因王渊从向笃学过几种障眼法儿,大敌难御,尚能吓那不知底细的人;加以近来武功气力进境神速,寻常足能应敌;那雪橇只能坐三人,离了牛子不可:
便把王渊留在洞里。并教王氏夫妻父子三人各备毒弩,以备随时取用,万一贼党突然来犯,与己途中相左,没有遇上,不论来贼多少,可利用洞口形势,藏在两侧石凹里,隔着帘缝向上斜射,切忌出敌。自带灵姑、牛子,循着贼橇遗迹,乘橇查看前去。
果然沿途迹印交叠,不下数十条之多。过了峰群,渐渐归一,甚少散乱。到尽头处只剩了三条六行,中有两行还是大橇所留。这里小橇迹印甚深,好似由此起点。在上面划过多次,来时都循故道,走时随意滑行。过峰以后,因为峰群中有两峰矗立对峙,恍若门户,是条必由之路,所以过峰才得归一。三人细一查找,只贼橇起点正当橇迹中心,有二尺许深、茶杯粗细一孔洞。雪里还有少许竹屑、几滴冻凝的蜡泪和一些被冰雪冻结,没被风吹走的引火之物。灵姑笑问:“爹爹看出什么没有?”吕伟不答,只管在当地左近盘旋往复,定睛寻视。约有刻许工夫,灵姑见老父时而点头微笑,时而摇首皱眉,自言自语道:“不会。”一会又道:“贼党竟非庸手,人更狡诈,我们着实不能轻视他们呢。”灵姑未及发问,牛子本在左侧面相助查看,忽然失声惊叫道:“这不是雪滑子划过的脚迹么?”
吕伟因料贼来自右,不会在左,闻言赶过一看,相隔贼橇起点约有二十来丈地上,竟有好些雪滑子划过的迹印,俱都聚在一起,前后左右都无。再前数十丈有一斜坡,过此,肢陀起伏,路更难走。吕伟想了想,便命牛子回去驾橇,自己和灵姑往坡前缓缓滑去,沿途滑迹更不再现。
牛子滑行迅速,一晃将橇拿到,说道:“前面山路不平,这么大雪橇怎滑得过去?”
吕伟道:“滑不过去,橇并不重,我们不会抬么?”灵姑忽然省悟道:“贼橇中间还抬了一段,真想不到。左边山石崎岖,没有住人所在,除非贼巢是在后山。但有那么一座危崖,休说冰雪封住,便平日也难飞渡,回时还偷我们那么多的牲畜粮肉,他们是如何过的呢?”吕伟道:“玉灵崖后那座危崖,我以前仔细看过,只有崖夹缝一条通路,别无途径可行,崖又高峻,无处攀援。可是左边许多乱峰峭壁挤在一起,我们好几次往前查看,无论左折右转怎么走法,走不几步,不是遇阻,便是无法再下手脚,也就没再往下追寻,焉知那里没有藏人之处呢?”
说时三人已到坡前,首先人眼的便是坡上面散乱纵横迹印甚多。除了贼橇滑过的划痕和残余火把、人手脚印、蜡泪肉骨之外,旁边还有一摊烧残的余烬,倒着几根烤焦的树枝,地面的冰雪已然融化了一个大坑。颇似贼党人数甚多,一拨入往玉灵崖偷盗,一拨人留在当地打接应,野地奇冷,支起树枝,作火架烤肉,饮酒御寒,等盗运人回,会同回去。照此情形,贼党不但人多,住的地方定远无疑。
贼踪二次发现,有迹可寻,三人重又乘橇前进。那橇迹竟是一个大弯转,一气滑行了二十余里,接连越过两三处雪坡高林,到一峻岭之下,橇迹忽又不见。吕伟见那峻岭被冰雪包没,来势似与玉灵崖后危壁相连,除却上面突出雪上的大树而外,什么迹印都没有。尤其橇迹断处,左近岭脚更是陡峭,万无由此上下之理。以为贼党又施乱人眼目故技,舍了原处,沿岭脚走不远,为绝壑所阻。左走约五六里,便到玉灵崖后危壁之下昔日寻路遇阻所在。到处危峰怪石,丛聚星落,加上坚冰冻雪,有的地方休说雪橇通不过去,简直寸步难容。三人吃罢干粮,脚上换了雪滑子,分头在乱峰中苦苦搜寻了半天,一任细心查看,也看不出贼党怎么走的。时已不早,灵姑见天色昏暗,恐降浓雾,老父病后不宜过劳,便婉劝回洞,明早再来。吕伟无法,只得上橇回转。途中恐有遗漏,吩咐缓行查看,终无迹兆,俱都懊丧不置。
其实贼党通路正在岭脚之下,除了头一回橇迹中断是盗首听了一人苦劝,有心做作外,这里本未掩饰。只因那晚逃走三贼想起飞刀厉害,恐怕万一被人发现橇迹追寻了来,故意做了一些手脚,将通路掩去。吕伟只见那岭壁陡滑,无可攀升,千虑一失,竟未想到这里也和玉灵崖后一样,岭腹中还可通行;贼党利用崩雪,掩饰又极巧妙,竟被瞒过。
三人回洞,天已近暮。又商量了一阵,自不死心,次早又往搜索。连去三日,白费心力,仍无所得,天又奇寒。后来灵姑把去年后山牛子报仇之事告知乃父。并说:“那伙俱是南疆中积恶如山的匪徒,尤文叔不辞而别,竟与同流,可知不是善类。此老贪顽狡诈,决不舍弃那些东西。贼来多次,未犯正洞,只把小洞中金砂、皮革、牲粮、食物和一些精细的用具盗个精光。照此推想,十九是他勾引外贼来此偷盗,否则不会如此知底。他久居本山,地理甚熟,不知从何绕来,所以我们竟未找着。”
吕伟惊问:“既有这事,怎不早说?”灵姑道:“彼时女儿和渊弟、牛子早看出他不是好人,爹爹怜他身世,偏极信赖,心又慈厚,如知此事,势必寻他回来。那伙匪徒再用些花言巧语和我们亲近来往,岂不引鬼人室?牛子又用毒弩射死一贼,恐爹爹见怪,再三苦求女儿答应不为泄漏,才说的实话,不便欺他。明知这是隐患,原意把爹爹劝住,三五日内带牛子前往后山查探。牛子已然起誓,决无虚言。这类恶人死有余辜,看他们那日鞭鹿的惨毒便可想见。到时先寻文叔究问:不辞而别,一去无归,是何原故?一面用飞刀将贼党全数圈住,逼吐罪状。问明以后,文叔如早入贼党,或是有甚诡谋要暗算我们,便连他与众贼一齐诛戮;如实因追鹿遇贼,被逼入伙,便带了回来,开春遣去,以免生事。谁知当日变天,接着爹爹和众人一病,无心及此。加以大雪封山,后山高峰阻隔,贼我俱难飞渡,万想不到会出此事。等女儿病起发觉失盗以后,既恐爹爹忧急,又怕贼党为患,见那雪中橇迹与后山去向相反,只猜贼由对壑而来。虽然牛子认出那伤贼与后山之贼是同类。但没等问出详情便已自尽。牛子又说上次后山报仇,这四贼俱不在座,他们平日互相疑忌攘夺,虽是同党,时常此离彼叛,情如水火。女儿当时心念微动,以为另是一伙,说也无益。近日二次发现贼橇去路的峻岭,竟与洞后危崖相连,把前后情形细一推敲,颇似贼由后山而来。否则贼党那么凶暴骄横,人数又多,有甚顾忌,既来必犯大洞,连抢带占,何必避重就轻,来去又做下那么多伎俩,分明是早就知道女儿手有飞刀,难于抵御。这不是尤文叔引来,还有哪个?只不知他用甚方法飞越岭崖罢了。”
吕伟道:“女儿说得颇有道理。这几次我们差不多到处寻遍,全没影子,可见贼已受挫,未必再来。我们又没法去;天气大冷,灵奴也难于远飞。为今之计,说不得只好熬到开山,再往后山一行了。”主意打定,便不再搜寻贼踪。
过了几天,吃完上次打来的小虎,肉食已无。所余牲畜俱留后用,不能宰杀。更恐旷日持久,积雪难消,无从取食,剩点余食,哪里还敢多用,只得把三餐改为两顿。众人平日享受优裕,一旦搏节,还得虑后,俱觉不惯。牛子更嘴馋,淡得叫苦连天,终日咒骂狗贼。
背晦之中,天也似有意作难,自最后一次吕氏父女寻贼回洞,又连降了七日大雾。
盼到晴天有了一点日光,这才开始分班出外行猎。头一天是吕氏父女和牛子做一起,离洞不远,便发现雪地里有了兽爪迹印。三人方在心喜,以为不难猎获,谁知那些兽迹俱是前番遇虎时所留。虎本有些灵性,见人厉害,当地又无从觅食,早已相率移往别处,更不再在附近逗留。在发现满山兽迹,空欢喜一阵,什么野兽也未猎到。
牛子先还恐吕伟父女发现老虎吃剩下的弃贼尸骨头发,嗔他说谎,没敢领往虎洞。
后来无法,拼着受责,同往年前弃尸所在。一看,崖前林内到处都是虎爪迹印,故意狂喊引逗,虎却不见一个。知虎多喜昼眠夜出,也许藏在崖洞里面,仗着灵姑壮胆,便请灵姑将飞刀放进去照亮,兼作后备,自持腰刀、毒弩人穴寻虎。如若虎多不敌,出声一喊,说出方向,上面灵姑便用飞刀斩虎。吕伟说:“飞刀虽是神物,这等冒失行事,万一将人误伤,如何是好?”力持不可。最终仍是灵姑随了同下。纵落洞底一看,与上面雪地虽差有数丈,侧面却还有一条盘道,尽可缓步出入。虎穴便在盘道当中离地三丈的洞壁上面,牛子闻出膻味甚浓,洞底还有虎斗时抓裂的残毛,心疑虎已睡熟。怪叫两声,除了空洞回音嗡嗡绕耳,别无响应。及和灵姑纵上盘道,深入虎穴,剑光照处,一个大敞洞,比外洞还要宽大数倍。石块甚多,都有丈许大小,西壁角崩塌了一大片,碎石堆积,裂痕犹新,似是新崩不久。除虎毛外,又发现许多兽骨,四贼残余骨发也在其内,虎却遍寻无踪。牛子算计虎已外出觅食,入夜始归,只得一同退出。
三人又往别处搜寻一阵,归途绕往碧城庄查看,在左近小崖洞中发现了一窝兔子。
灵姑见那兔子大小三对,雪也似白,不忍用飞刀杀害,意欲生擒回去。兔洞大小,人不能进,孔穴又多。忙到天黑,费了不少的事,仅仅捉到两大一小。灵姑心慈,见大兔是只母的,洞中还有一对小兔,动了恻隐,又将大的放回。有此一举,虽然提了点神,仍然于事无补。
接连三日,换了好些地方,俱无所得。料知后山野兽必多,无奈通路为冰雪填封,无法通行。后来牛子想了一个主意,择了一处有兽踪的林野,掘一雪阱,下铺厚草,上用粗竹交错虚掩,将两白兔放在里面为饵,想将野兽引来。吕伟虽知无效,情急之际,也自由他。牛子隔日往视,竟在阱旁发现了一种从未见过的兽迹,推测身形甚是庞大。
可是竹子未毁,两兔也在其内。这日因那地方就在碧城庄侧,相隔甚近,吕伟父女知是徒劳,没有前往。只王渊比灵姑还爱白兔,昨日经牛子再三苦说,抱去为饵,今天恐怕冻死,想抱回来,相随牛子同往。居然发现兽迹,不禁大喜,当时便想跑回报信。牛子道:“你先莫忙,满山都是虎爪印迹,虎却不见一个。主人们白累了多日,再要扑空,又是心焦。看这东西把冻雪踏得这么深,身子一定又蠢又大。我们有刀有箭,还怕它么?
真要厉害,打它不了,跑也容易,它怎么也没有我们雪滑子快。莫如等它一回,来了便打;打不成,引到玉灵崖去,再喊他们,省得不来又跑个空。”
王渊一想也对,先和牛子在阱侧树杈上坐守了半个时辰,没有动静。枯守无聊,纵身下树,刚将脚上雪滑子扎紧,待寻兽迹,往来查探。忽听猛的一声厉吼远远传来,紧跟着叭喳叭喳一片兽蹄乱踏残冰之声由远而近。二人忙把腰刀拔出,手握弩筒,闪在阱侧树后。只见前面通往山阴森林的大路上跑来两只怪兽,身子粗壮,和大象差不许多,也有两牙翘出血唇之外,只是没有那条长鼻,比象要矮得多。通体雪白,生就扁头凹脸。
怪眼突出,其红如火,凶光四射。一张半月形的血盆大嘴微微张着,露出尺多宽一条鲜红舌头。再衬上一身极丰茸的白毛和那两尺来长的一对刀形的獠牙,端的威猛无匹。
这东西名为雪吼,产于云南大雪山背阴冰谷之中。蹄有吸力,不会滑倒,多么高峻的冰山,只要不是直立的,都能上下,其行甚速。性最耐冷恶热,终年在冰雪中奔驰逐突,不是冰堆雪积奇冷之地,从来不去。加以嗜杀好斗,喜怒无常,专门同类相残,非到重伤力竭,同归于尽不让。因此种类不繁,极其少见。吕伟壮年送友人藏遇过一只,苦斗了好些时辰,终于用计,才得弄死,同行的人不是吕伟在场,几乎无一能免。这次雪吼系由极远荒山中踏着冰雪乱窜而至,如非本山降此大雪也不会来。群虎离洞远避,一半也是为此。牛子生长云贵山寨之中,从未见过。此兽还有一样长处,身子虽大,食量极小。不发怒时,走在冰雪上面,脚步极轻,甚少留下痕迹,等人兽都对了面,才会发觉。一发怒,重蹄举处,冰雪粉碎,声震山谷。常因发怒暴跳,震裂了冰壁雪峰,倒塌下来,将它压死。所以兽迹只阱旁有,难找它的去路。
二人所遇乃是一公一母,本来彼此相斗时甚少。公吼不知怎地将母吼触怒,一逃一追,晃眼到了二人面前平地。公吼在前,边跑边往回看,略一停顿,吃母吼追上,将头一低一歪,悄没声地用那长牙便照公吼腿肥问撩去。公的虽然有点俱内,吃母的追急已然犯性,再被拥了一下,负痛暴怒,拨回身子,用长牙回敬,立时斗将起来。两兽都是以死相拼,只见两团大白影带起四小团红光,在雪里滚来滚去。所经之处,冰雪横飞,全成粉碎。哞哞怒吼之声远震山野,脚底冰裂之音更是密如贯珠,相与应和,越斗越急。
此兽皮毛经水不湿,最能御寒。只是骨多肉少,味作微酸,如善厄制,也还能吃。
二人如若等它们斗疲两伤,力竭摔倒,照准咽喉一刺,便可了账。王渊偏是年小好动,不知厉害,见二兽苦斗不休,想早点弄死,拖回洞去,博众人惊喜。以为兽舌外垂,一中毒弩,见血便可了账。也没和牛子商量,径举手中弩筒,瞄准母吼舌尖射去。谁知此兽耳目最灵,并且一遇外敌,不论自己斗得怎么凶,也会立即迁怒,合力来犯。此时二人藏身树后,本是险极,不去招惹,被发觉尚且不容,何况又去伤它。王渊箭到,母吼只把头微偏,便用大牙拨掉,怒吼了两声。公吼也已觉察,一同停斗,厉声怒吼。
王渊见未射中,方欲连珠再射。牛子看出这东西厉害,一见它们停斗,回身朝树怒视,便知不妙,忙即拦阻,低喝:“万惹不得,快往那边躲去,莫被看见。”二吼本不知树后有人,正望那树犯疑,牛子出声虽低,竟被听去。双双把头一低,狼奔豕突,直蹿过来,双方相隔才只两丈,眨眼即至。还算牛子话才出口,人便纵开,王渊身子又极轻灵,没被冲着。二吼来势既迅且猛,二人藏身的是一株大杉树,下半截埋在雪里,仅剩上半枝干,粗才半抱,竟被公吼一下撞折,冰柯雪干一齐纷飞。牛子几乎挨了一下重的,见势不佳,拉了王渊滑雪就跑。二吼看明敌人,益发风驰一般追来。王渊见怪兽驰逐如飞,来势凶猛,转折也甚灵便,仍不十分信服,边跑边用连弩回射,晃眼将满筒弩箭射完,除有三四支吃二吼长牙撩开外,其余支支射中,可是全被振落,一支也没射进肉里。反逗得二兽怒吼如雷,势更猛急,紧紧追逐不舍。遇见阻路的树木,也不似人绕转,一齐前冲,头牙比铁还硬,撞上就折。沿途半抱左右的树木,连被撞折了十来株,碎冰断干打在身上,只略停顿瞻顾,仍然急追,恍如不觉,声势端的惊人。王渊方知厉害,不敢迟延。仗着滑行迅速,二吼又吃这些树木作梗,略一停顿,二人便滑出老远。
虽然未被迫上,人兽相隔也只半箭之地。
始而王渊欺它身子长大,专打林木多处逃跑。一晃逃到碧城庄,猛想起:“此兽人力决不能制,何不把它引往玉灵崖,用飞刀杀它?还省得撇运费事,多好。”念头才转,忽见灵姑由前面转角处滑雪驰来,老远高喊,“渊弟、牛子莫慌。我来杀它。”二人未及还言,灵姑飞刀已应声而出,一道银虹由二人头上掣将过来,迎着二兽一绕,眸眸两声厉吼过去,同时了账。牛子、王渊二人见银虹飞出,知道二吼必死,宽心大放。刚停步转身,意欲看个明白,不料二吼急怒攻心,如箭脱弦,就这晃眼工夫,已被迫近了些。
二吼并驰追人,忽听飞刀自天直降,往下一剪。母吼身略落后,将头斩去半个,余势冲出还不甚远;公吼性最暴烈,驰得正急,恰被飞刀拦腰斩成两段,后半身带出丈许,即行扑倒,那前半身死时负痛拼命,奋力往前一挣,竟冲出了十来丈远近。二人骤出不意,王渊眼快身轻,才一回身,瞥见血花迸涌,一团白影冲来,忙用力把牛子往侧一推,同时往起一纵。总算见机得快,吼尸前半身径由王渊脚底冲过。到头处原是一株古柏,下半树干已没人雪里,上半枝梢露出地上,雪积冰凝,越聚越多,朔风一吹,全都封冻,成了一个丈许高大的雪堆,不见一点树形。恰当吼头对面,来势既猛,雪堆里又是空的,一下撞个正准。只听轰隆一声,整个雪堆立即崩裂,残冰碎雪带着断折了冻枝满空飞舞,纷坠如雨。
三人见死兽余威尚且如此猛恶,也觉骇然。相率滑近前去一看,雪堆散裂,现出一个新崩散了的残梢。那兽头冲到,余力已衰,整个被嵌夹在一个本干的老树权中,半截身子仍悬在外。一颗象一般的大自头,圆瞪着一双火也似的凶睛,突伸出两枚三尺来长的獠牙,两尺半宽的血盆大口。再加上鲜血乱喷了一地,雪是白的,血是红的,互一映衬,越觉凶威怖人。那母吼只斩半头,如马爬地上,从头到尾几及丈许,死前急怒发威,身上柔毛一竖立,格外显得庞大肥健。
三人看完,牛子拿腰刀一试,竟砍不进。便请灵姑用飞刀斩成数段,运回洞去。灵姑一摸,兽毛丰茸柔暖,想剥下整皮给老父做褥子,商量如何开剥。刚才灵姑闻声赶来时,吕伟闻得兽吼之声,觉着耳熟,灵姑走后忽然想起,”也穿了雪滑子赶来。认出是两只雪吼,知是难逢遇的珍奇猛兽,“贮止住三人,说了此兽来历。并说:“这东西四蹄有天生滑雪之用,运送回洞,无须人力,只消用索系好吼头,拉了就走。只那两截断吼,前半不能倒滑,须头朝前,后面用人抬平,方能滑动罢了。”当下便由牛子先驰回洞,取来绳索、扁担。如法施为,果然顺溜,那么蠢重之物,一点没费事,分为两次全运入洞。
牛子虽听吕伟说吼肉无多,不大好吃,仍是馋极,一到洞内,不等开剥,便就断处用刀割肉,那吼看去虽极肥壮,全身骨节无不粗大,肉只薄薄一层,牛子割剔了一阵都是碎块。灵姑见他猴急,就和老父商定开剥之法:先将断的两截翻转,用飞刀由肚腹中间割裂,又将四蹄斩断。量好了五六尺方一块整皮,吼兽脊骨两旁的肉有两寸来厚,颇为细嫩。余者连前后脚都是厚皮包着粗筋大骨,即便有肉,也极薄而且老。牛子也不管它,先取=块脊肉放在架上烤起。余肉一点不剩,连筋剔下。毕竟吼身长大,居然剔割了一大堆。灵姑见吼腿甚粗,皮更厚软滑韧,剥下来足有二尺见方,两方吼皮用做床褥再好没有。取下一试,果然合用,便分了一方与王妻。骤得珍物,俱都心喜称幸不置。
吼肉极嫩,一烤便熟,人口还有松子香,只是味带酸苦,不大好吃。二次再烤,吕伟想出了吃法,命牛子先用盐水擦洗两次,再切薄片,用酱油加糖浸过,随烤随吃,果好得多,但仍不似别的牲禽之肉味厚丰腴,因断荤多日,慰情胜无,众人都吃得很香。
吕伟因存粮不多,肉更难得,吩咐将余下的收起。牛子意犹未足,又讨些带软筋的吼腿碎肉去烤。腿肉本老,又带着筋,一经火烤,又干又韧,休说不能下咽,简直无法嚼动。
吕、王诸人看他生吞了两块,馋得好笑,又从肉椎里挑了好些给他。腿肉煮也不熟,而且和肚肠一样,还有难闻的怪味,不能人口,只好一齐弃掉。
这一来,只剩下两块脊肉和一小堆能吃的碎肉,算计不过吃四五顿便完,再加上那只母吼,至多能吃七天,还不能任意大吃。王妻说起野味难得,来日大难,又在发愁。
牛子道:“我看这东西太厉害,老虎忽然跑没了影,定是见它害怕,逃到别处去。老巢还在,迟早虎要回来。过几天就有野东西打了,焦急什么?”正说之间,忽闻远远传来一声虎啸。王渊笑道:“真有这样巧事,才一说虎,虎就来了。我们快打去吧。”吕伟道:“这些从未见过生人的虎,人气旺时,有的见人还怕。此处已闻虎声,想必虎穴距此不远,先不要打它,免得见人就逃,无处寻它们。最好晚打两日,等它归了巢,要打就多打两只。这里死吼还有一只不曾开剥,有好些事做呢。”王渊忽想起两只白兔尚在阱中,无人在彼,难免不落虎口,忙喊:“姊姊、牛子快走!兔儿忘了抱回,莫被虎吃了去。”灵姑一边穿着,一边说道:“虎声甚近,今日想不至落空,爹爹也同去散散心吧。”王妻巴不得多打些野味存储,以免到时发急,从旁怂恿道:“那死吼只要灵姑娘用飞刀把肚皮和腿切开,我们自会开剥,大哥去吧。”
吕伟当日本不打算再出行猎,经众一劝说,虽然应允,随同穿着,心里兀自发烦,明知需用甚切,只不愿去,也说不出是何原故。容到老少四人匆匆穿好快要起身,那随身多年的宝剑原悬壁上,忽然当啷一声,掉了下来。众人都忙穿着,灵姑又在用飞刀相助王氏夫妻分裂吼皮,全未留意。只牛子一人仿佛看见那剑无故出匣,自行振落,并非木撅松脱坠地,急于想起身,便过去拾起,看壁间挂剑木撅业已受震倾斜,随手交给吕伟佩好,就此忽略过去。
那鹦鹉灵奴平日最爱饶舌,自吕伟一病,忽改沉默,也极少飞出。除人有心调弄,还肯对答外,终日只伏在牛子房中鸟架上面,瞑目如定,一声不叫。等四人事完行抵洞口,灵姑在前正待伸手去掀皮帘,灵奴忽然飞出,落在石角上,叫了一声:“姑娘。”
灵姑停手,回头佯嗔道:“蠢东西,喊我啥子?自从天气一冷,你就不愿出门,连话都不多说了,我不信会冷得这个样子。”灵奴睁着一双亮晶晶的眼睛,偏头注视灵姑,又看了看王氏夫妻,好像在寻思说什么话,被灵姑一说,仿佛害羞,心又好胜,只叫了声:
“我不怕冷。”将头一点,便即飞回房去。
灵姑回头,见老父正转身取镖囊,笑道:“爹爹,看这东西多么好强,明明想随我们同去,心又怕冷,还要强嘴,真比人还好胜哩。”随说随伸手去揭皮帘。不料外面风大,皮帘有搭绊扣紧还不觉得;这一揭开,风便猛扑进来。灵姑偏脸和老父说话,毫不留神,风狂力猛,呼的一声,大半边皮帘立即朝内卷来。洞门高大,帘用许多兽皮联缀而成,并用长竹对开,钉有十来根横闩,以备扣搭之用,分量不轻。天蜈珠虽有定风御寒之功,偏巧灵姑恐行猎时万一四人走散,不在一处,就将珠交与老父带好,以防受寒,没在身上。吕伟行时又想起有毒的弩箭只可防身,用以行猎,要割弃许多兽肉,虎豹之类的猛兽常弩又难致命,意欲将镖囊带去,回身往取,没有在侧。灵姑帽兜未戴,骤出不意,竟被皮帘横条将脸鼻割破了一条口子,流出血来。众人俱都慌了手脚,纷纷将灵姑唤住,坐向一旁。吕伟自更心疼,忙着看伤势。还不算重,只刮破了些肉皮。当下取来清水和自配创药,将伤口洗净敷上,用布扎好。吕伟方说:“灵儿受伤,明天再去猎吧。”话才出口,又听虎啸之声,灵姑因众人俱已穿着齐备,仍欲前去。吕伟疼惜爱女,见她兴致甚好,不愿强留,便命灵姑稍为歇息,套上帽兜再走,以防伤口受风。灵姑应诺。
老少四人一同出洞,纵到洞前积雪上,侧耳静听,虎声已息。再滑向前崖,登高四望,到处白茫茫空荡荡的,哪有一点虎的影子。适听虎啸似在碧城庄左近传来,便往庄前赶去。到时一看,已然来晚一步,阱前满地虎迹,阱被虎爪爬碎了两面,两兔不知是被虎吃去,还是跑掉,已不在阱内。气得王渊顿足大骂。牛子看出有迹可寻,笑道:
“渊少爷,你不要气,这回我们打得到它,你跟我走好了。”于是四人便循虎迹滑去。
先还以为虎归旧穴。及至滑了一阵,越滑越远,细查地势,竟是去往山阴一面。四外冰封雪盖,地形已变,这条路从未走过,不知怎会到此。
吕氏父女恐走得大远,途径与贼常来路相背,恐万一来犯,不甚放心。牛子却因沿途虎迹尚新,接连不断,又只有去路,并无来路,力主前往。说:“狗贼害怕飞刀,夜里都不敢来,何况白天?山阴本是野兽聚居之地,往日嫌远没有去过。洞中粮少,既然误打误撞走到这里,莫如乘机看上一回,野兽如多,、日后也好再来打猎。何苦半途回去,白费力气?”几句话把三人说活了心。灵姑又看出那地势仿佛昔日亲送向笃闭关修道时曾经走过;记得再行十来里,越过两处高山野林,便是所居崖洞。久已想去看望,因路甚远阻,没有前往,此时冰雪封冻,滑行迅速,一会即至,即便虎猎不到,也可乘此相见,向他道谢,就便请他占算贼党踪迹和异日休咎,岂非绝妙?便向众人说了。于是一同脚底加劲,赶紧滑行,向前驶去,片刻工夫,滑出二三十里。
吕伟见大小雪堆乱坟头也似,为数何止千百,一眼望不到底,堆旁不时发现又深又黑的洞穴。方疑途径走错,想唤灵姑询问,忽听来路高崖侧面人虎呼啸之声。刚听那人一声暴喝,仿佛耳熟,猛觉脚底一沉,轰隆一声,存身雪地忽然崩陷了一整块。四人因为防冷,俱都挨近吕伟而驶,前后相隔不出两丈,所陷之处恰与四人立处大小相等。四人俱都身轻矫捷,长于纵跃,雪地陷落虽然骤出不意,也可纵开,不知怎地都觉身似被地粘住,一个也未纵出圈去。
那地底当初原是盆地森林,千年古木,虬枝交互,结成一片,绵延数十里方圆不见天日。雪落上面,越积越多,逐渐冰冻凝固,看是雪地,下面却是空地,先见空穴便是原来树问空隙。冰雪厚达两丈,被成千累万的林木枝干托住。这还不说,最奇的是崩雪之下,本有两边大树的枝干相互托住,落时竟就四人立处往下沉坠。先沉之势极速,过了上面雪层,忽然改为缓缓下沉,不偏不斜,稳沉至地。不特人未受伤,冰雪也一点没碎。倒是上面四外冰雪齐往陷处崩聚,却不再坠,晃眼便将陷孔填满。森林地本阴黑,吃上面层冰积雪之光一回映,反倒清明起来。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