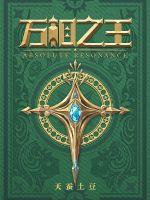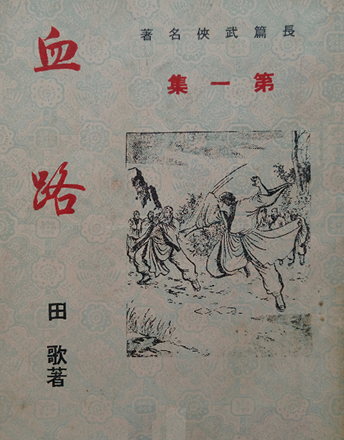君不畏爬上船的时候已经是精疲力竭地直喘大气。
他比任何人都惨,先是与姓田的女子折腾,又碰上那个水洞中的人妖,他便是铁打的汉子怕也生锈了。
苗小玉十分紧张又关心地拉住君不畏,道:“你的面色苍白,莫非生病了?”
君不畏摇头苦笑,道:“病倒是没有,元气大伤,我需要睡一觉,千万别来叫我。”
苗小玉道:“我叫他们安静,你快进舱里歇着吧。”
君不畏往舱里走,包震天对苗小玉道:“苗姑娘,咱们大伙把船顶入海中,慢慢地往上海去,还来得及把银子送到。”
苗小玉吩咐小刘等十一个人,等到潮水升高,立刻把船往大海推。
苗小玉关心君不畏,特别命黑妞儿弄了许多吃的送进君不畏的舱内去。
君不畏这一睡就是一整天,等他醒过来抬头看,他发现镖船已经行驶在大海中了。
回头瞧,鱼山岛不见了。
君不畏急忙去找苗小玉,苗小玉正站在小刘身边认方向,因
为船上的指南针也被海浪打坏了。
苗小玉发现君不畏走来,忙着迎上去,道:“你睡了一天一夜,应该吃些东西了,我扶你进舱里面去。”
君不畏笑笑,道:“苗小姐,我并没有病,倒是要问问你,怎么船就这么开走了?”
苗小玉道:“包老爷子的主意,镖银要按时送到,否则他有责任。”
君不畏道:“白白放弃发财的机会了。”
苗小玉道:“怎么说?”
君不畏道:“咱们既然上了鱼山岛,又知那地方乃田九旺的老巢,他一定在岛上藏有宝物,这么多年来他们在海上打劫,也必然发了财,如今田九旺又不在岛上,正是咱们找寻他宝藏的好时机,就这样走掉,岂不可惜?”
苗小玉道:“君先生,我如今心情很乱,我们另外的两条护航船不见了,我哥哥他们生死不明,你想想,我哪有心情再去发那意外之财?”
君不畏道:“说得也是,且等把镖银送到,我自己雇船再赶来。”
苗小玉吃一惊,道:“你一人?”
君不畏淡淡地道:“一人干也干脆,我非杀田九旺不可!”
苗小玉道:“你们之间必有大仇。”
君不畏道:“我与任何人都没仇。”
“可是你却一定要杀田九旺。”
“不错,我杀田九旺是有原因的,你是不会知道的。”
苗小玉道:“如果你告诉我,就知道了!”
君不畏道:“我又何必吓你一跳?你还是不知道为妙,苗小姐,可有什么吃的?”
君不畏把话岔开,苗小玉自是不便追问。
她笑笑,对外边的黑妞儿道:“黑丫头,去弄些吃的送进来,君先生饿了。”
君不畏吃得很多,好像把三顿饭合在一顿吃似的。
他刚刚放下碗筷,包震天走过来了。
“老弟,你吃饱了?”
“吃饱了,我连下一顿的也吃了。”
包震天笑笑,道:“君兄弟,我有个不情之请,这一回希望你能答应。”
“我在听着。”
“船到上海,你伴着我把银子送到来人手中之后,我打算不再为官家效力了。”
君不畏道:“我上一次就是陪在你身边呀,唉,使我差点命也不保。”他拉过包老爷子低声问:“上一回那个叫于文成的家伙,你们好像是朋友嘛。”
包震天道:“多日不见,姓于的叛变了,他背叛了北王,看样子他投到杨秀清那里去了。”
君不畏道:“你肯定?”
包震天道:“南京城以东的太平军,大部分全是东王的防地,于文成往江对岸驶,正是投向东王。”
君不畏道:“这些银子……”
包震天道:“太平军不发饷,但为了士气,各王暗中筹银两,那些当年与各王有交情的人物,尤其是黑道的枭霸,便甘愿暗中出银子,有了这些现银,军士们自然会效命,只不过这可是不公开的事,你老弟知道就好,搁在心里别多说。”
君不畏微微笑了。
他终于弄明白一件事情,那就是当权的人物也免不了暗中与
黑道勾结。
这些银子不就是由“八手遮天”石不全筹的吗?
石不全难道为北王办事?
于是,君不畏发觉石不全果然不简单。
包震天拍拍君不畏,点点头道:“上一回出乎意外地上了个恶当,差点老命也留在江里,所幸老弟出手,这一回应该不会再出问题,老夫在北王面前也有了交代。”
君不畏道:“我实在弄不懂,包老呀,你的身份……”
包震天哈哈一声笑,道:“我亲爱的老弟,我们已经生死与共了,老夫便实话对你说,我当年乃是横山山大王,也可以说是坐地分赃的寨主,人称‘坐山虎’的便是老夫。这以后遇上金田起义的韦昌辉,是他拉了我一把,只不过老夫不耐军中日子,就在幕后为他干些事,暗中筹款便是老夫主要的任务。老弟,我说这话你懂吗?”
君不畏道:“懂,包老,原来你还是有身份的人,我也算是高攀了,哈哈……”
包震天道:“不,凭老弟本事,北王面前必受重用。”
君不畏哈哈一笑,道:“可惜我与包老一样,军中日子过不惯,我喜欢的是三十二张牌九玩玩。”
包震天道:“且等咱们交了差,老夫陪你赌三天。”
君不畏的精神来了。提到赌牌九,他便眉飞色舞地笑了。
两人正自说着话,黑妞儿过来了。她站在破舱口低声道:
“君先生,我们小姐有话对你说。”
君不畏走出舱外,他问黑妞儿,道:“小姐找我?”
“有话和你商量。”
君不畏转身走到后舱门,他看看小刘在把舵,冲着小刘点点头。
“君先生吗?请进来坐。”
君不畏犹疑一下,因为这间小舱也算得是姑娘家的闺房,不宜贸然进去。
但苗小玉却又道:“请进来,我们有事商量。”
君不畏低头进去了。
他发现这舱真干净,几件小型家具也精致,两尺宽的长桌放在正中间,茶水已经倒满杯了。
君不畏冲着并不高兴的苗小玉点头一笑,道:“苗小姐,你有什么打算要和我商量?”
苗小玉似乎两眼含着泪,她先是盯着君不畏瞧,然后又咬咬唇。
君不畏木然地等她开口了。
苗小玉猛提一口气,道:“这次海上遇到风,怕是把我们的‘跨海镖局’毁了。”
君不畏同情地叹口气,道:“小姐,天有不测风云,谁遇上也难逃。”
苗小玉道:“我哥哥,还有罗副总镖头,怕是完了。”
君不畏道:“那也不一定,咱们不是好端端的吗?”
苗小玉道:“大海茫茫,已无他们的踪影,我真的已经不抱希望了。”
君不畏道:“小姐,你有何打算?”
他等的就是苗小玉的几句心里话,仔细地听着。
苗小玉再一次看看君不畏,道:“君先生,如今镖局只有这么一条破船,如何能再经营下去?便是回程也十分艰险。”
君不畏道:“苗小姐指的是什么?”
苗小玉道:“君先生,我没忘记丁一山那一批海盗,他们是不会放过我们的。”
君不畏道:“我以为还要加上一个田九旺。”
苗小玉道:“我们陷于孤立了,君先生。”
君不畏道:“苗小姐,你打算要在下干什么?”
苗小玉道:“我求你,随我一同回小风城,到时候如果仍然没有我哥哥的消息,我关门大吉,也就不再麻烦你了。”
君不畏想了一下,点点头道:“好,我答应你一同再回小风城。”他顿了一下,又道:“我忘不了杀田九旺这个可恶的大海盗。”
苗小玉道:“希望我也能回报,帮你出刀。”
君不畏道:“你有这番,心意就够了。”
他准备要出去,却被苗小玉拉住了。
君不畏道:“小姐,到了上海你打算怎么办?”
苗小玉道:“先修好船。”
君不畏道:“那需一大笔银子的。”
苗小玉道:“也只有欠着了。”
君不畏伸手自怀中摸出银票,他的银票用油纸包得好好的,大海上未湿掉。
这些银票可是来自“石敢当赌馆”少东家石小开的,如今尚有四千多两,这个数目几乎够苗小玉再买一条新船。
“苗小姐,你拿着,我还用不到这些钱。”
苗小玉怔怔地道:“君兄,你……”
“收下吧,到了上海先修船。”
苗小玉还未有所表示,君不畏一晃身便走出舱外面。
他抬头看远方,舟山群岛已出现了。
小刘在船尾叫:“大小姐,咱们去不去沈家门呀?”
苗小玉走出来了。
这时候天上已不见乌云,天空中有不少海鸟飞到船上面,大风暴过后,这些海鸟便又出现了。
苗小玉只看了一眼,便对小刘道:“咱们不去沈家门,抄近路过舟山。”
小刘把船改航向,却不料远处出现一条快船,双桅上满帆驶得快,好像是往沈家门去的。
苗小玉也发现那条船了,她看得一怔,因为这条船的船体特别高,听人说,大海盗田九旺的船体就特别地高,而且船头上似乎还特别安装有尖锥。
苗小玉走近君不畏,她指着远方的船,道:“君兄,那条船好像是属于田九旺的船,咱们今天躲远些。”
君不畏道:“你确定那是田九旺的船?”
苗小玉道:“我确定那是海盗船。”
包震天急忙道:“快,咱们躲着它,千万别被他们盯上了。”
苗小玉道:“是的,船上还装有镖银二十万两。”
君不畏恨得直咬牙,却也不能叫船迎上去。
他这里正在发火,只见远处的双桅快船掉头往这面驶来了。
小刘大叫:“糟了!他们朝咱们过来了。”
包震天道:“希望它是官家的船,阿弥陀佛。”
他乃“坐山虎”,如今也叫起阿弥陀佛来了,其实包震天不是怕事的人,怕事就不会当山大王了。
他担心的乃是船上的二十万两银子。
苗小玉气忿地道: “听我哥说过,这种船正是大海盗田九旺的船。”
小刘道:“大小姐,咱们怎么办?”
苗小玉走近君不畏,叹口气,道:“君兄,看来今天免不了厮杀了。”
君不畏道:“该来的躲也躲不过,苗小姐,且看来的是谁
了。”
大船上不见旗帜。
大船上却站了不少人,这些人正在船边指指点点地不知说些什么话。
于是,大船追过来了。
船头上站了两个人,苗小玉一看心一软,因为那人正是沈文斗。
沈文斗一边站着一位又粗又壮、又黑又高的大个子,虬髯发光,双手箕张似蒲扇,龇牙咧嘴地看这面。
苗小玉身子靠近君不畏,她还在君不畏耳边嘀咕着,不知说些什么。
沈文斗已大声叫:“苗姑娘,欢迎你来沈家门呀,快跟着我们进港吧。”
苗小玉尖声道:“今天不去了,回程一定拜见沈老爷子。”
沈文斗道:“哪有过门不入的道理,走吧。”
苗小玉道:“这回海上遇到风,我们失踪两条船,我至少得把一船的镖银送到地头上,沈公子,再见了。”
沈文斗还是不放人,他叫船往前面拦。
这时候,沈文斗一边的大汉吼声如雷,道:“什么?船上装的是镖银呀,哈哈。”
他这笑声似打雷,回身大手猛一挥,道:“兄弟们,去他娘的,你们不是聋子吧。”
有几个大汉哈哈笑,其中一人道:“船上都是银子啊,财神爷跑错地方了。”
在一边的沈文斗猛一怔,他拉住大汉道:“侯二当家,他们也是自家人啊。”
姓侯的手一甩,道:“人情归人情,银子是银子,我们把银子搬上船,卖你的人情不杀人。”
沈文斗道:“对我爹也无法交代呀。”
姓侯的面皮一紧,道:“咱们这是干什么的?能看着白花花的银子从眼皮下面溜走?”
沈文斗指指苗小玉的船上,道:“侯二当家,你不知道,我暗恋那位苗姑娘三年了。”
姓侯的哈哈一声笑,道:“更好了,我们抢银子,你过去抢老婆,各取所需,各拿所好,妙!”
他大吼一声,又道:“撞过去!”
沈文斗大声地道:“侯二当家的,我答应送你们银子两万两,这是带你们回沈家门拿银子的,这也是认捐,我爹知道你们和捻党连上线了,你如今又何必……”
姓侯的仰天哈哈笑,道:“沈少东,你省省力气吧,镖银我今天要定了。”
沈文斗没奈何,他指指“跨海镖局”的船上,又道:“侯二当家的,我为那位姑娘请命,如何?”
姓侯的一拍胸脯,道:“我保管不伤她一根毛发,她是你的了。”
沈文斗总算不再吼叫了。
小刘很会躲,来船的船头上有个尖锥五尺长,撞上船身不得了,有两次蹭着船边一闪而过。
君不畏发现,来船上的十五个人,个个半赤膊、光着脚、手上的刀全都一样的。
君不畏不由冷冷笑对苗小玉道:“苗小姐,你可认得对面船上那大黑个儿吗?”
苗小玉道:“曾听说大海盗田九旺手下有个狠角色,一斧头能砍断大树,不知是不是这个人。”
君不畏道:“那一定是他。”
苗小玉道:“我未曾看到这个人手上拿兵刃。”
君不畏道:“这黑汉旁边站的人肩上扛着一把斧头,至少有三十斤那么重。”
苗小玉道:“君兄,今天仰仗你了。”
君不畏道:“我尽力。”
便在这时候,那巨大的船一个半旋撞过来,“轰”然一声,直把镖船撞得几乎大翻身。
小刘拼命稳住船,却已看到十几个汉子举刀扑杀过来了。
这些人边杀边吼叫,气势上就不得了。
小刘所带领的十一人分成两拨迎上去,大伙这里拚了命,那姓侯的大汉仍然站在大船上直瞪眼。
沈文斗跃近苗小玉,他也看到他最不喜欢看到的人—— 君不畏。
“苗姑娘,跟我过去吧,咱们一齐回沈家门。”
苗小玉冷冷道:“原来你们和海盗一伙的。”
沈文斗道:“苗小姐别误会,我们只不过认识他们,我们怎会当海盗?”
苗小玉叱道:“你如今就和海盗在一起,我问你,你们这是干什么的?想抢我的镖银?”
沈文斗道:“也是侯二当家的临时起意,与我无关。”他逼向苗小玉,又道:“你的船已烂了,还是跟我去沈家堡,我不会亏待你的呀。”
苗小玉冷哼道:“谁希罕你们沈家堡,你滚!”
船上人干得凶,已有人挨刀倒下了。
姓侯的闻得苗小玉要沈文斗滚,他哈哈大笑了。
沈文斗却把气出在君不畏身上,道:“王八蛋,你站在这里惹爷的眼!”
君不畏道:“原来,沈家堡与海盗一个鼻孔出气呀!”
沈文斗道:“我提醒你,话多的人死得快!”
君不畏道:“是吗?”
沈文斗陡然出手,一招“黑虎掏心”打过去。
君不畏哈哈一声笑:“去!”
沈文斗真听话,身子平飞而起,“咚”地一声跌在大船一边,正是姓侯的站的地方。
沈文斗撑身而起,戟指君不畏对姓侯的道:“二当家,杀了他!”
姓侯的沉声道:“看来还真要我出手。”
他把右手一摊,身边那人便把一柄板斧送去了。
姓侯的接过斧头猛一抡,另一手对着君不畏招几下,道:“小子,小子,过来!过来!”
君不畏指着自己鼻尖,道:“你叫我?”
姓侯的道:“我不叫你难道是你叫我?”
君不畏闪过两个拼命的汉子,他缓缓地走到大船上。那船高高的,上面还有架子,想是海上打斗用的。
他走到姓侯的身边,道:“干什么?”
姓侯的道:“小船上那漂亮妞儿是你什么人?”
“什么也不是。”
“沈少东要你死,大概你有对不住他的地方了。”
“我们第二次见面。”
“第二次见面他就想你死,可见你人见人厌。”
君不畏叱道:“你放的什么屁,乱七八糟,胡说八道,我问
你,你和沈家堡是什么关系?”
姓侯的一瞪眼,道:“就算是坐地分赃吧。”
君不畏道:“你们是不是田九旺的人?”
“田当家正是俺们头儿。”
“他人呢?”
“你太多话了,你不需要知道,你就快死了。”
君不畏道:“你以为你一定能收拾我?”
“你他娘的马上就知道了。”
只见他双目看着斧刃,光景就好像在评鉴一把好斧头似的不动。
姓侯的这动作不奇怪,奇怪的是他那平推一斧够阴毒,斧刃反射,斧身已到君不畏胸前,姓侯的只需手腕加力,君不畏就会被开膛。
君不畏当然识货,他上身一个铁板桥,后背尚未沾地,右足已踢到敌人的身上。
姓侯的板斧举一半,立刻无力地忙收回。
他猴叫着以左手掩紧裤裆往后闪,君不畏“懒驴打滚”站起来。
只这么一交手间,沈文斗看清楚了,人家姓君的果然够高明,难怪苗家大姑娘看中,再看两边人马,镖局的人似乎还能撑住场面,但却已伤了不少人。
沈文斗的反应尚未明朗,君不畏好快的身法,他已斜着身子箍住姓侯的粗脖子。
别以为姓侯的个头大,被君不畏手臂一夹,立刻憋得脸发青。
姓侯的斧头未砍中君不畏,早被君不畏右膝顶撞在他的腰眼上。
君不畏一声吼,姓侯的力道尽失,斧头也掉了。
这些连串动作只不过刹那间,沈文斗急忙走上来。
“君兄,你干什么?”
君不畏松开手,姓侯的一跤跌坐在船板上。
“操你娘!”
姓侯的似乎常骂人,他张口三个字,三个不受人喜欢的字。
沈文斗奔到姓侯的身边,道:“二当家,你怎么了?”
姓侯的身上不见伤,实际上他伤得真凄惨,因为只要看他左手在裤裆下揉呀搓的就可见一斑。
沈文斗上前问,姓侯的只是吸大气。
沈文斗抬头问君不畏,道:“君兄,你……”
君不畏道:“沈大相公,你好像不喜欢我这个人,你叫这大狗熊杀我。”
沈文斗道:“我承认,我也真的想杀你。”
“为什么?”
“你自己应该明白。”
“我如果明白就好了。”
“你装糊涂?”
君不畏指指正在搏杀的苗小玉,道:“是不是因为苗小姐她不喜欢你?”
沈文斗道:“那只是原因的一半。”
怔了一下,君不畏道:“还有另一半?”
沈文斗道:“你又装胡涂。”
君不畏道:“你明说吧。”
沈文斗道:“我妹子的事,君……”
君不畏咬咬唇道:“你妹子怎样了?”
提到沈娟娟,确实令君不畏吃一惊,不错,他曾和沈娟娟一
张床,但那也是沈娟娟诱惑他,他实际上并未主动求什么。
他也很清楚,沈娟娟不是守璧的姑娘,而他又是个浪子,两人在一起,会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君不畏道:“令妹到底怎么了?”
沈文斗道:“她恨你,她更爱你,而你……”
君不畏道:“什么意思?”
沈文斗道:“你见了她就明白,而你……你还赖在苗小玉身边不离去。”
事情大致明白了。
沈文斗把妹子交给君不畏,君不畏也别缠着苗小玉,各有所取,各取所爱。
但他却不知道,君不畏也没有纠缠苗小玉。
大船上,沈文斗与君不畏争论着,镖船上却正杀得凶,那一边,姓侯的突然平飞而起,张开双臂抱向君不畏双腿,君不畏如果被他抱中,大概是要往大海中滚去了。
衣袂飘风,君不畏浑身一个大车转,他的人刚站定,姓侯的仔长一声嗥叫。
“唔……噢……”
仔细看,才发现姓侯的背上连到大腿开了一道血口子,约二尺那么长。
一挺身只站起一半又坐下来,姓侯的咒骂了:“操你三代老祖奶,你最好再给老子加一刀,否则,你个王八蛋走到天边也要你死无葬身之地!”
君不畏淡淡地道:“我给你个机会,所以我不取你性命,我想……”他转而怒视沈文斗,冷冷道:“沈大少爷,你们干什么我不管,只是我要你们马上滚!”
沈文斗咬咬牙,道:“好,你狠,只不过沈家堡不是好欺的。”
他对满身是血的二当家侯子正道:“侯二当家,这仗就不用再打了。”
姓侯的出气有声,道:“娘的,这笔帐咱们改日算,王八蛋们,回来吧!”
他这一声吼叱,奔杀在镖船上的十几个恶汉,纷纷退回大船上,他们这才发现他们的二当家重伤流血不能动,张口吸气还带哆嗦。
君不畏跳回镖船,那小刘拨开大船往北驶,苗小玉大声叫:
“姓沈的,原来你们和海盗有勾结,我恨你们!”
沈文斗也大声叫:“苗姑娘,误会,误会。”
两船分开了,只见大船上几个大汉把姓侯的往舱内抬,姓侯的还在骂不绝口。
镖船上的人可真惨,大伙的衣衫刚凉干,如今七八个人身上在流血。
包震天也免不了流血,他背伤才好两天,如今肩头上又挨一刀。
苗小玉的头上在流血,有一刀砍上她的头,真幸运,被她的银簪子挡住,但还是流了不少血。
黑妞儿坐在舱门口直喘气,她的眼睛看海面,也不知她在想什么,半天不说一句话。
君不畏对小刘道:“咱们伤了多少人?”
小刘也在流血,闻得君不畏的话,粗声地道:“数了一下,我所带的十一人只有三个没受伤,君先生,你知道刚才大船的黑汉吧。”
君不畏道:“他姓侯。”
小刘道:“对,他叫侯子正,乃田九旺的左右手,也是那股子海盗的二当家,大海上他杀人就像砍西瓜,尤其他的水中功夫了得,听说他能在海中搏鲨,半个时辰不换气,凶得很啊。”
君不畏道:“他还等着要我命呢,哼!”
小刘道:“君先生,要多加小心啊。”
君不畏道:“我还会再来。”
小刘道:“再回来?”
君不畏道:“是呀,我饶不了田九旺。”
小刘道:“君先生,你看看咱们这船,别说是个子小,便是互撞一下也会碎掉了,你要找田九旺,我看你得找个大船。”
君不畏道:“我不找大船,小刘,叫那没受伤的快弄些吃的,受伤的也得治一治了。”
小刘道:“君先生,我们小姐……”
君不畏回头看,附近舱内传出饮泣声,敢情苗小玉忍不住地哭了。
君不畏也明白,女人就是女人,苗小玉经过这一连串的折腾,她当然会伤心。
苗小玉虽然很坚强,这时候也吃不消了,她的大哥下落不明,镖船又如此残破,主桅杆也断了,还得在上海找人先修船,地只是个姑娘,怎么办?
遥遥地望向北方,海面上出现两条快船。
君不畏看得一瞪眼,还以为是苗刚他们的船。
包震天站在船头仔细看,忽然他哈哈笑了。
他对掌舵的小刘道:“快,快把船迎过去。”
小刘道:“包老爷子,咱不应该靠岸呀。”
包震天道:“不用了,接我的人在那船上。”
苗小玉走出来了,君不畏没有,他仍然躺在船舱内,因为他正在思忖一件事情。
镖船往来船迎去,只见来船落了帆,只剩下主桅上一面长条旗。
那旗子是金黄色,一看便知是北王韦昌辉的后勤船。
苗小玉来到包震天身边,低声地道:“包老,你可要认清楚,别像上一回。”
包震天道:“我看得很清楚,船上两个人,我们时常在一起饮酒。”
他低头拍舱门,叫君不畏快出来。
君不畏无精打彩地走出来了。
苗小玉立刻走过去,道:“君兄,我在上海要修船,多则十日,希望你尽快赶回来。”
君不畏道: “这次海上遇难,我希望你多打听,也许还可以找到你哥哥。”
提到苗刚,苗小玉眼眶有泪水,她在抽噎。
君不畏道:“苗小姐,你放心,我自会帮助你,只不过我有个提议。”
苗小玉道:“君兄,你请说。”
君不畏道:“如找不到令兄,我以为这镖局子也就别干了。”
苗小玉道:“我也是这么打算。”
便在这时候,两条船已靠拢上来了。
那包震天大声呼叫:“喂,铁兄呀,咱们在这儿相见,太令我高兴了。”
来船的船中央站着一个身披淡蓝色长披风的大汉,这大汉的手上提着刀。
“包兄,久违了,哈哈……”
两船绳子套牢,另一船上也过来一人,是个矮胖子。
包震天一瞪眼,道:“你……”
矮胖一声哈哈,道:“包兄,许久未见了,你仍然神气十足呀。”
姓铁的拉住包震天一只手,笑道:“等你好久了。”
君不畏还未曾走过去,包震天却忙着和人打招呼。
只见姓铁的哈哈笑道:“前后应该二十万两银子了,包兄,你弄齐了?”
包震天面皮一紧,道:“二十天以前我押了十万两现银,但遇上了于文成那奸臣了。”
姓铁的道:“于文成投靠东王府了,你怎么把银子送姓于的?”
包震天道:“我还挨了他一刀,差一点老命不保。”
说着他对这两人抱拳道:“铁兄、林兄,我把二十万两银子押回来了,也总算在北王面前有了交代。”
姓铁的道:“包兄,这批现银来的也正是时候,咱们自江北撤回来的两万大军,正要去抄敌人后路,缺的就是这批饷银。”
另一大汉姓林,他倒提着一把刀,沉声道:“就在江面上交割,包兄,你的任务也完成了。”
包震天点点头,道:“银子来之不易,我命他们开舱,当面清点。”他高声对苗小玉道:“苗姑娘,千辛万苦,银子总算到了地头上,你这就命人开舱吧。”
苗小玉道:“这是应该的。”她对小刘点点头,君不畏淡淡地站在一边不开口。
包震天又对苗小玉道:“押镖的费用在风城已与令兄清过帐,苗姑娘,你怕是要辛苦修船了,只可惜我帮不上你的忙。”
苗小玉道:“我不会再向包老要求什么,二十箱银子搬完,我们就靠岸了。”
舱门打开了。
两船上的大汉们一窝蜂似的围上来搬银子,有几个还哈哈地笑。
当然,有银子总是惹人高兴的。
姓铁的抚髯点着头。
姓林的斜眼望向包震天。
包震天笑道:“铁兄、林兄,你们不打开一箱查验一下吗?”
姓铁的道:“有你包兄在场,我们信得过。”
包震天到了这时候才伸出手来了,他把手伸向姓铁的,道:“铁兄,二十万两银子没有少,该把北王的收据给我吧?”
姓铁的道:“你要收据?”
包震天道:“也好向北王交代呀。”
姓林的哈哈一笑,道:“我们都是自己人,我看这收据免了吧。”
包震天立刻警觉到他上次吃的亏。
他的背伤才刚刚好,戒心当然还在,只见他双目一瞪,道:“两位仁兄,交情归交情,公事归公事,两位如果没有北王的证据,这二十万两银子你们不能搬。”
姓铁的一瞪眼,旋即哈哈一笑,道:“包兄,进入长江七十里,你就会看到自己人了,我们又跑不了。”
包震天没有忘记上一次于文成的去向,那不也是往长江去的吗?
包震天一念及此,立刻摇头,道:“不,我宁愿在此等两位,你们取了收据再回来,这银子……”
姓林的大吼道:“怎么找起自家人麻烦来了?”
他这话好似打暗语,姓铁的突然出掌。
姓铁的掌上功夫高,只一掌便把包震天打落江中。
水花四溅,包震天载沉载浮的,可也离死不远了。
事情太突然了,君不畏看得一瞪眼。
苗小玉要拔刀,镖局的人都要抄家伙了,就在这紧要时候,姓铁的手一挥,两条船上又冒出十七、八个恶汉,加起来就是三十多人,这些人手上均提着刀,如果镖局的人动手,他们三个杀一个。
姓铁的哈哈笑道:“你们识相,别动手,哪个想动手,放火烧了你们的船。”
姓林的也得意地道:“押镖已到,你们已没有责任了,我们把银子搬走,你们也可以回小风城了。”
君不畏怔怔地在想,他怎么知道押镖是来自小风城呢?
苗小玉一看没了主意,包震天的人已不见了,也不知是死是活,回去如何对石不全交代?
她的烦恼又来了。
一箱箱的银子搬得很快,分两批分别抬到两条快船上。
姓铁的走向苗小玉,道:“咱们早已投靠东王了,只有包震天,他太不识时务了。”
苗小玉道:“我不懂,我们只保镖。”
姓铁的道:“你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东王府的人是不会亏待外人的,呶,拿去吧,算是给大伙吃红的。”
他递了一把银子并不多,算一算也有三十多两重。
苗小玉本不欲伸手的,但她现在太需要银子了。
她接过来,只淡淡地道:“谢谢。”
很快地,两条船一前一后往长江口驶进去了,好像是往江北岸去的样子。
这时,君不畏开口了:“苗小姐,咱们暗中追上去。”
苗小玉愣然道:“咱们追上去干什么?”
君不畏道:“我以为这两个人有问题。”
苗小玉道:“他们由北王转而投入东王府,这些天谁都知道南京城中各王不和,这种事咱们少去惹。”
君不畏道:“苗小姐,至少咱们应该弄明白一件事情。”
苗小玉道:“君兄,你发觉什么不对了?”
君不畏道:“天下没有那么巧的事情,上一回包老挨刀,这一回又被人打落江中,我以为这个中必定有阴谋,也许前后两批人……”
他没有说下去,因为他还不敢确定。
苗小玉道:“君兄,就算我们发觉有什么不对,又如何?我们能出手吗?”
君不畏道:“如果我们把事情弄明白,小风城你也可以在石老爷子面前交代了,你该知道包老与石老的交情,石老会问你的。”
苗小玉一听,点头道:“对,我们是应该暗中追上去看个明白。”
她对小刘道:“追上去瞧瞧。”
小刘道:“大小姐,天都快黑了。”
君不畏一笑道:“天黑好办事,追上去。”
小刘点头道:“他们的船快,咱们的人要加把劲,找两支桨划起来。”
果然,胖黑在船边抽出两支大桨,四个人用力划,还发出哼呀咳的声音来。
江面上归帆真不少,樯林巨帆之外,还有几艘洋船在江面上。
船多,前面的两条船当然也不会注意有什么船暗中追踪他
们。
那两条船并未驶远,进入长江口三里地,便掉头往南岸这面靠过来了。
这时候,苗小玉也吃一惊,他们要把银子送往哪里?
她抬头看看君不畏,这时候晚霞已落,孤雁不见,江风微微带着一股子凄凉味。
“果然是有阴谋。”
“而且是大阴谋。”君不畏再看远处,两条船靠在一起了。
小刘低声问:“君先生,咱们要不要靠过去?”
君不畏道:“暂时别靠过去。”
苗小玉道:“这一段江岸是什么地方?”
君不畏道:“我只知道这附近有一条大道,可以通往上海。”
苗小玉道:“你以为他们把银子运往上海?”
君不畏道:“很难说。”
苗小玉看看江面,又道:“这地方很静。”
君不畏道:“天黑以后更静。”
苗小玉道:“君兄,你打算怎么办?”
君不畏一时间没回话,但他的眼睛睁大了。
君不畏似乎发觉情况怪异,先是他不及出手去救包震天,因为姓铁的与姓林的两船人几乎把他们围起来了,等到君不畏往江中瞧,已不见包震天的影子。
包震天的生死,实际上对君不畏而言,那是无关重要的小事一件。
君不畏只想杀田九旺,只不过他发觉事情越来越复杂,因为田九旺又与沈家堡勾结,这件事太出乎意料。
他在思忖良久之后,便对苗小玉道:“苗小姐,你把船开到上海去修理,三五天后我会去找你们。”
苗小玉道:“你去哪里?”
君不畏道:“我也不知道,只不过我一定会去找你们,还有,我得去查看那靠岸的两条船。”
苗小玉道:“好,我这就找地方送你登岸。”
苗小玉很快把君不畏送到一大片芦苇岸边,君不畏立刻登上岸直往下游奔去。
现在,君不畏来到那条大路旁,往江边瞧,只见两辆大车在岸边停着,船上有人在抬箱子。
君不畏当然知道箱子里面的是银子,只不知道这大车是什么地方来的。
天已灰暗下来,岸边的人渐渐模糊,就在君不畏快要潜到大车附近的时候,忽见远处飞驰来几匹快马。
仔细数一数,一共是六匹。
六匹马上坐着五男一女,各人还带着家伙。
东升的月亮虽然不太亮,但还是能大略地看到来人的模样。
君不畏一看吓了一跳,他几乎要叫出声来了。
他的眼睛睁得大,他的嘴巴也合不起来。
他在心里大声叫:“那不是小风城‘石敢当赌馆’的少东家石小开吗?”
他把身子贴地面,匍伏在矮草丛仔细听。
天下还真有狠毒的人,要不然天下怎么会大乱?
一箱箱的银子往大车上抬,君不畏可不管那些,他静下心来仔细听。
那边有人大声说:“少东家,你怎么亲自赶来了?办这点小事还用不到少东家操心,一切十分顺利。”
又听得石小开一声笑,道:“上一回十万两银子,是不是已
全部送到我大伯的手上了?”
那人笑笑道:“翼王很高兴,十万两银子当场就发放给兄弟们了。”
石小开道:“上一次差一点误事。”
“怎么了?”
“包震天被一个混混救了,我爹便来个顺手推舟,答应再送二十万两银子,哈哈,包震天……”
“包震天落人大江中了,他中了我的铁砂掌,狠狠地印在他胸上,他便是牛也会重伤,少东家,我出掌有分寸,不能叫他马上死。”
“他死了,有谁去对韦昌辉报告是东王下的毒手。”
“哈哈……”
“哈哈……”
一群人全笑了,君不畏愣然了。
笑是开怀的大笑,爽快极了的人总是掩不住那样地大笑,也可以说是狂笑。
便在这些狂笑声里,君不畏放眼过去仔细看,这一看之下吓了一跳,也令他想发笑。
君不畏既吓一跳,又想发笑,便也露出一副哭笑不得的怪模样。
原来这些人当中竟然还有莫文中、李克发与尤不白三人,至于另外的一男一女,其中那个女的君不畏也见过,就是在“石敢当赌馆”后面耳房中侍候过他的那个年近三十的女子。
君不畏心中想:“石小开怎么把这些人也带来了?而且看每个人的样子,风尘仆仆,带着些许疲惫,显然他们只是刚刚来倒。”
君不畏躲到暗处仔细听,他越听越心惊,可也带着些许喟叹。
他可以肯定一件事,太平天国完了。
银子全部搬上大车,只听得一人向石小开道:“少东家,我们这就绕道赶往翼王军营,少东可向令尊报告,翼王大军这就要进入湖湘了,胜利指日可待。”
石小开拍拍那人肩头,笑道:“去吧,带句话我大伯知道,我们等着变天了。”
这几句话是什么意思,君不畏听了也不懂,只不过他相信,石小开的大伯必然是翼王石达开。
他们原来是一家人,而阴狠的乃是石不全的嫁祸东王之计。他明着出银子支持北王韦昌辉,却又命人改扮东王的人劫去银子,而实际上银子却到了翼王手上。
君不畏总算弄清楚这件事,原来他们的险恶用心是要挑拨太平军的内部团结,以便搞垮太平军。君不畏又怎能容忍!
两辆大车驶走了,江岸边立刻只剩下石小开六人站在那里,这时候从船上奔来两个汉子,其中一人对石小开道:“少东家不打算上船?”
石小开道:“告诉我,运镖银的船去哪里了?”
那人指向上海道:“少东,我好像听他们说是去上海修船。”
石小开道:“几条船?”
那人立刻应道:“只有一条。”
石小开一怔道:“他们一共三条,为什么只有一条船,另外两条呢?”
那人看看身边的汉子,道:“兄弟,咱们只看到一条,没有看到另外两条。”
石小开吃惊地急问:“船上可有女人?”
那人立刻笑笑,道:“有,一共是两个女的,一黑一白,白
的比较漂亮。”
石小开面皮一松,道:“她还活着,我便放心了。”
那人立刻又道:“少东,前几天那场暴风雨,传言海上沉了,不少船,也死了不少人啊。”
石小开笑笑,道:“你不觉得世上的人太多了?”
他只是淡淡的一句话,听得人却也不太舒服。
石小开的笑声突然停下来,换了一声雷吼:“苗小玉不死,那个王八蛋必然也在,这几天马不停蹄,为的就是那小子!”
他大声对那人吩咐:“秦不老、苟在耀,我们大伙住到船上去。”
姓秦的躬身道:“是,少东家。”
石小开看看身边几个人,又对姓秦的道:“这次前来,我们是要杀人的,你们两条船慢慢往上海驶,找到镖局的船以后别去惊动它,我们设法把人诱上岸,找个机会干掉那小子!”他重重地哼了一声,又道:“石家的银子也是他那个狗杂碎花用的?”
姓苟的道:“少东家,像这种小事情,你只要派个人来知会一声就成了,又何必顶风冒雨亲自前来?”
石小开道:“听说那小子的本事大,我们当然要小心,你们应该明白我爹的作风。”
于是,这六人顺序地登上船,石小开加以分配,他和那女的住在姓秦的船上,另外便是中、发、白与那个精壮矮汉一齐住在苟在耀的船上。
君不畏渐渐地明白了。
他大概也猜得到,原来这些人是为他而来,他还以为是银子的事情。
他笑着摸摸脖子,道:“玄,想不到有人在暗中打我的主意,要我的命了。”
不就是白银五千两吗?如今他除了身边一些零花的,有几百两在船上输给小刘他们,四千两送了苗小玉去修船,他如果今夜未遇到石小开,还以为好朋友找来了。
君不畏拍拍身上的灰与草,迈开大步往南走,他要去上海了。
他是去找苗小玉的,因为他既然发现这件秘密,就要告诉苗小玉多加小心了。
君不畏大步往街上走,迎面奔来一辆拉车,这种拉车两个轮,一个人可以睡在车上,车顶还有个白布顶,那当然是为了遮太阳。
如今天黑没太阳,拉车的汉子走得快,快得差一点撞向君不畏。
君不畏闪一步,拉车的回头骂道:“操你娘,你走马路中央呀!”
君不畏笑笑,道:“谁该走中央?”
拉车的又骂道:“操你娘,土包子呀!”
君不畏一瞪眼,他还未开口,从白布篷下伸出一个人头来。
是女人,而且头上还插着花,耳坠子叮叮铃铃响。
君不畏不由望向那女的,她已经笑出声了。
“哎呀!是你呀!你怎么在这儿呀?快上车来嘛!”
君不畏本来不想坐车的,但见拉车的凶巴巴,便不客气地坐上去了。
拉车的心中想,怎么如此巧,偏就遇上自家人。
原来车上坐的是沈家堡大小姐沈娟娟。
君不畏往车上一坐,他冲着拉车的扮个鬼脸。
拉车的真会表现,他也向君不畏点点头,但君不畏心中在
想:“好小子,你出口就骂人,我非整整你不可。”
他还真的整人。
君不畏何许人也,他不但武功高,歪点子也不少,只见他伸手拉住沈娟娟的手,笑呵呵地道:“我们又见面了,你可把我想死了。”
女孩子通常听到男人说这两句话,总是十分温柔地靠向男的身上。
沈娟娟也一样,笑眯眯地便把头放在君不畏的胸前来,她还半闭上眼。
君不畏暗聚气,由气转力,力贯全身便是一个千斤压。
拉车的才拉了十几步,忽觉车子沉甸甸的,好像一下子车上放了几百斤的东西一样。
回头看,车上两个人抱得紧紧的,如果此刻去打扰,准会挨骂。
拉车的又拼命拉,也倒霉,偏就又是一段上坡道,这更叫他吃不消了。
没奈何,拉车的把车一停,仰天直喘气。
沈娟娟挺身而起:“车为什么停了?”
“小姐,我拉不动了。”
“才两个人你就拉不动呀?”
“真的拉不动了,小姐,你们换车吧,这些钱我也不要了。”
沈娟娟指指前面,道:“就在前面了,你不拉?”
拉车的一看,咬咬牙道:“好,我拉。”
真轻松,拉车的觉得车上好像少了几百斤,这是怎么一回事?
果然,没多久便到了,沈娟娟下了车,她当然付车钱,君不畏却对拉车的道:“老兄,你这车子有问题。”
拉车的一怔,道:“有什么问题?”
君不畏指指天,道:“天黑了,你看看。”
“看什么?”
“有鬼呀。”
“鬼?”
君不畏笑得不甚好看,当然是他装出来的。
他拍拍拉车的肩,又指指车上,道:“我坐在你的车上全身不自在,起鸡皮疙瘩,那一定有鬼,你老兄可得多加小心,别惹上那东西,会倒霉的。”
拉车的双目圆睁,君不畏却跟着沈娟娟往一座三合院中走去。
这是一座四周花圃、中间三合小院的宁静住宅,奇特的是正面房子大。房子后面两边有客室,沈娟娟就好像怕君不畏跑了似的,紧紧拉住君不畏不放手。
沈娟娟拉住君不畏走进后面客厢中,关上门,她的动作便使出来了。
她双手攀住君不畏脖子,俏嘴翘起,美眸闪烁,半歪着头等着君不畏吻她了。
君不畏没有吻,她低声地道:“我知道你恨我。”
“嗯。”
“我也知道你喜欢我。”
“嗯。”
君不畏看看出气有声的俏嘴,又道:“沈大小姐,我想知道一件事。”
“你问吧。”
“你哥哥呢?”
“他回沈家堡了。”
她说的是实情,沈文斗果然回沈家堡了,而且是与大海盗田九旺的二把手侯子正一同回去的。
君不畏把双手搂紧沈娟娟的柳腰,又道:“令兄为什么突然回去?”
沈娟娟道:“你问这个做什么?”
君不畏道:“就算是关心吧。”
沈娟娟道:“不关自己的事就少去关心。”
君不畏哈哈一笑,道:“你说得对,事不关己少关心,我应该关心的是你,哈哈……”
沈娟娟主动地吻上去了。
君不畏当然回应,但在他心中却想着另外一件事,那便是沈家堡与大海盗田九旺怎么会勾结在一起的?
这间客厢好像是沈娟娟的闺房一样,里面的设备有一半很洋气。
什么叫洋气?洋人用的东西很多,也很新奇,单就那张大床就不一样,人坐上去还会晃,人站上去也会颤动,当然,人若在上面滚动就更会令人觉得柔软舒适。
沈娟娟趴在君不畏身边,她的指头拨弄着君不畏的嘴巴,一边还吃吃笑道:“上一回你一句话不留就走了,留下我一个人多寂寞啊。”
君不畏道:“你永远也不会寂寞。”
沈娟娟道:“谁说的?”
君不畏道:“我知道,你不是一位寂寞的人,你会自己制造快乐的。”
沈娟娟吃吃笑了。
君不畏可不是要干这种事的,他本来是想去找苗小玉的,却在途中碰见沈娟娟。
已经半夜了,外面一片死寂。
沈娟娟低声问君不畏道:“想吃消夜吗?”
君不畏不知道什么叫消夜,他头也不动地道:“你说的什么话?”
沈娟娟一笑道:“就是你想不想吃东西。”
君不畏道:“如果此刻摆上一桌上好酒席,只有你我两人对酌,那光景必然令人愉快异常。”
沈娟娟挺身而起,她拍拍君不畏,吃吃笑道:“我总是不会叫我所爱的人失望的,嘻嘻……”她走出房间,不久之后便又愉快地走进来。
不旋踵间,沈娟娟拉起君不畏,道:“起来吧,外间的酒莱摆好了。”
君不畏披衣而起,两个人一路来到外厢房,只见六样莱一碗汤,两只酒杯一壶酒,碗筷也放在一起,再看六样冒热气的莱还真齐全,天上飞的、地上走的、水里游的,每一种两道,香味扑鼻,还未吃口水便快流出来了。
君不畏笑笑,坐下来就是一杯酒下肚,盘中菜他挑着吃,也不管身边的沈娟娟了。
沈娟娟陪着吃,只不过她吃得并不多,还夹菜往君不畏的口里送。
两人边吃边聊。
沈娟娟道:“咱们已是自己人了,我有句话倒想问问你,可以吗?”
君不畏道:“我在听。”
沈娟娟道:“你的口音不对劲,你为了什么要一而再地往小风城去?”
君不畏道:“为生活。”
沈娟娟道:“做什么营生?”
君不畏道:“像我这种人还能有多大本事,只要有银子赚,我什么也干。”
沈娟娟道:“你别再去小风城了,行不行?”
君不畏道:“我不去小风城你管饭?”
沈娟娟一笑道:“你就那么怕饿肚子,如果我把你推荐到我爹身边,你这一辈子也饿不着肚子。”
君不畏直想笑,在大海上他便碰上她大哥沈文斗了,沈文斗同姓侯的在一起,这说明沈家堡的“铁臂苍龙”沈一雄与大海盗田九旺有关系。
如今沈娟娟想把他介绍给沈一雄,就事论事已经是太晚了。
君不畏酒足饭饱了,他愉快地双手按在桌子上,就要站起来了。
沈娟娟却伸手勾住他的腰,满面桃花似的吃吃笑。
君不畏道:“这是外厢房呀。”
沈娟娟道:“外厢房又怎样?”
君不畏道:“想起初次在沈家门见到你的时候,你的表现就是一位淑女,而如今……”
沈娟娟道:“这里是上海,不是沈家门。”
君不畏道:“上海又怎样?”
沈娟娟道:“上海是个洋地方呀,你看看,洋人在街上还亲嘴哩。”
君不畏道:“那是洋人,我不是,我……”
君不畏突然不说了,双目直看门外面,果然,只见一个穿大褂的中年人,急匆匆地走来了。
沈娟娟也看到了,她的眉头一紧,道:“西门风,你干什么?”
“大小姐,场子上来了几个家伙,老千架式十足,咱们的庄推不下去了。”
沈娟娟道:“我哥哥怎么还不回来?”
西门风道:“大小姐,你是知道的呀,少东家前天才回沈家门的。”
沈娟娟道:“他应该快回来的。”
坐在一边的君不畏心中好笑,沈文斗与侯子正在大海上还想劫镖船,沈娟娟却还以为她的哥哥快回上海了。
西门风道:“大小姐,你得打定主意啊!”
沈娟娟看看君不畏道:“君兄,我要你陪我去,好不好?”
君不畏道:“玩几把牌九我愿意,帮你稳场我不敢,沈大小姐,你自己去吧。”
沈娟娟伸手拖住君不畏道:“你不去,我不依,你去压阵,我出赌资。”
君不畏心想:“沈家与大海盗有勾搭,我今天就去输他几个也未尝不可。”一念及此,君不畏大咧咧地站起来,道:“走,我跟你过去瞧瞧。”
沈娟娟吃吃笑,伸手搂紧君不畏的腰,两个人大步往外走,那位西门风已先奔到大门外了。
门外面他招来两部车,君不畏与沈娟娟分别坐在车上,拉车的便跟着西门风往大街上走去。
君不畏发觉,上海这地方真热闹,没事干的人全都挤在街上来了。
拉车的左转右拐了几条街道,很快地停在一个大门外,君不畏抬头看,有个牌上面雕刻着大金字:“沈家赌馆”。
沈娟娟已跳下车,他拉住君不畏道:“走,进去看看是什么样的牛头马面王八蛋。”
君不畏却低声道:“沈大小姐,我只能站在一边看,不能下场去打拼。”
沈娟娟道:“为什么?”
君不畏道:“腰里没钱不敢横行呀。”
沈娟娟道:“你忘了,这儿是我家开的赌馆,你还怕没赌本?”
君不畏道:“输了怎么办?”
沈娟娟道:“算我的。”
君不畏心中在笑,立刻又问:“赢了呢?”
沈娟娟道:“全数是你的。”
君不畏就觉得妙,小风城的“石敢当赌馆”,石小开也曾邀人陪他赌牌九,赢了全部是自己的,如今又遇上同样的事,怎能不言妙?
当君不畏与沈娟娟两人从正门走进偏庭的时候,中央牌九桌上竟有人仰天笑起来了。
君不畏也哈哈的笑。
沈娟娟怔怔地问君不畏道:“怎么了?你们原本是认识的?”
君不畏道:“他们四位,其中三位乃是我的旧识,我们也是牌上见的对手呀。”
其实他心中在想,怎么不见石小开与那个女子?他两人怎么没有来?
君不畏大摇大摆地走过去,只听得莫文中笑道:“有缘,有缘,今天咱们又遇上了,哈哈……”
君不畏也笑了,他还看着一边的矮壮汉子,道:“这一位是……”
莫文中道:“这位是尹在东,都是场上的好朋友。”
君不畏往正面站,那位原先推庄的汉子拭着汗水往一边站,他还喘了几口气。
原来沈家赌馆来了四个人,正是小风城石不全身边的大杀手。
别以为他们只是杀手,赌牌九也有一套。
君不畏淡淡一笑,道:“怎么样,可要我推几庄?”
尤不白嘴角冷冷笑道:“咱们忘不了输给你的那么多银子。”
君不畏笑笑,道:“那点银子不够花,早就没有了,如今再碰上四位,财神爷来了,哈哈……”
李克发哈哈笑道:“我们不是财神爷,财神爷见了我们也会被吓跑。”
君不畏道:“那么咱们别耍嘴皮子,我这就出牌了。”
他洗牌的动作漂亮,出牌更是干净利落。
李克发四个人的银子并不多,真正多金的是石小开,他们四个人加起来也不过一百多两银子。
他们并非是来赌的。
他们是在找寻君不畏,因为他们知道,要找君不畏,就得往赌馆去找。
现在,他们果然找到了。
“下下,下的越多越好,下呀?”君不畏大声叫。
李克发瞪眼了,道:“一百五十两,你掷骰子吧。”
君不畏道:“李老板,我的毛病你知道。”
“你喜欢输?”
“对,我喜欢输,赢你们的五千两银子我早输光了。”
“你输给谁了?”
“不知道。”
他掷出的骰子是五点,君不畏取第一把牌,他吃吃一笑,
道:“气死我了。”
他身后的沈娟娟低声道:“憋十?”
君不畏两张牌往桌上砸,满面不高兴地道:“操,我喜欢输,它偏偏来个猴子王。”
下注的全直了眼,君不畏把所有的银子扫到他面前来,叹口气,道:“王八蛋喜欢赢,我要输呀,下!”
莫文中举着一个小布包,道:“这是咱们刚才赢的一百来两银子,君先生,你就看着办吧。”
君不畏道:“我祝你们大家赢!”
“哗!”他把骰子又掷出去了。
出现的点子是八个点,末门先取牌。
君不畏把牌放在门前直瞪眼,他心中在想,莫文中这些人是冲着他来的,什么大老板,全都是石不全的杀手,只不过自己实在不想和这些人干一架,又不知如何才能令面前这四个人离开。
三家的牌掀开来了,掀出的点子都不大,李克发四人的点子最大的是八点。
君不畏手压牌上淡淡地道:“我实在不想赢,我最爱输几个,你们大家要相信,所以这一把我就不用掀开来了,大家交个朋友吧。”
这是什么话,别说对面的尤不白等四人不答应,另外两门也摇头。
尤不白冷冷笑道:“君先生,少来这一套,你掀开牌再说风凉话吧。”
君不畏把牌按压得紧,摇摇头,道:“何必呢?银子输光叫人痛苦的。”
莫文中冷声道:“君先生,你不掀牌也可以,照数把银子赔大伙。”
君不畏的手松开了。
只见两张牌完好无缺地放在桌面上,但君不畏就是不去掀牌。
李克发道:“掀牌呀,操!”
君不畏叹口气,对一边的赌馆汉子道:“麻烦你去取个铲子来。”
一边的沈娟娟道:“要铲子干什么?”
她伸手去摸牌,却被君不畏挡住了。
很快地,那人在灶上取了个铲子走来,道:“你先生要的铲子。”
只见君不畏接过铲子,小心翼翼地用铲子去铲桌面上的牌。
这光景大伙全都直了眼。
李克发骂了一句:“娘的,弄什么诡计?”
莫文中也冷笑道:“鬼名堂可不少。”
矮壮的尹在东沉声道:“咱们这是干什么来的?”
只有尤不白未开口,他注视着铲起来的两张牌。
君不畏把牌铲起来,然后小心翼翼地把牌翻转在他的手掌上。
赫然是地牌一对,一共四个红点。
君不畏道:“既然各位一定要看,我只好痛苦地统吃了,对不起啊!”
莫文中惊怒地道:“你他娘的真会摆谱,为什么还要人找个铲子来?”
君不畏把牌摊送到莫文中面前,道:“你仔细看。”
君不畏张口对着两张牌吹。
他吹的并不用力,但两张牌却变成粉状腾飞,莫文中急忙闭眼睛。
惊叫声发自人们口中,刹那间两张天九牌化为灰烬消失不见。
“这是什么功夫?”
“神呀!”
“说给谁会相信?”
人们惊呼中议论纷纷,李克发一声冷笑:“君先生,你真高!”
尹在东怒目而视,道:“什么东西?”
尤不白却向君不畏笑笑,道:“君先生,咱们能不能借一步说话?”
君不畏道:“不能在这里说吗?”
李克发道:“不太方便。”
君不畏心里明白,他们这是想找地方围杀他,还以为他是傻瓜蛋。
莫文中抹去吹进眼中的灰尘,目眦欲裂地沉声道:“姓君的,这是什么意思?”
君不畏道:“我没有打算赢你们的钱呀!”
“你已经赢去了。”
“看了牌只有分输赢了。”
尤不白道:“君先生,我们在门外候教了,你是人物,大概不会钻进女人裙子里不出面吧?”
尤不白说完还拿眼看看沈娟娟。
君不畏侧转身,对沈娟娟道:“沈小姐,我出去一下,你就别再等我了。”
沈娟娟道:“他们好像对你不善,君兄,这是咱的地盘,岂容得他们撒野?”
君不畏看着走去的四个人,他笑道:“如果我想往女人的裙
子里面躲,你便也不会喜欢我了,是吗?”
沈娟娟道:“我陪你去。”
君不畏道:“我不要喜欢我的女人看到血腥,沈小姐,我想我会很快再回来的。”
沈娟娟点点头道:“君兄,你的高傲令我不敢苟同,他们是四个人啊!”
君不畏伸手摸着沈娟娟的面颊,对桌边的人点点头,道:
“各位,希望你们都是赢家,再见了。”
君不畏也把桌上的银子用手一拨便拨进袋子里,他觉得沉甸甸的,但还是哈哈一笑。
沈娟娟送他到大门口,却发现莫文中四人正大步往东行,而且边走边回过头来冷笑。
那时候上海东面还没有街道,好像是外白渡桥附近,黄浦江的帆船有一大半从太湖驶出来。
这附近还有几家造船的,如今正在赶工忙着,君不畏很想找到苗小玉,但他没有时间仔细找。
现在,江边上并肩站着四个恶汉。
莫文中四人耸动着鼻子看着走过来的君不畏。
君不畏刚站定,李克发已冷冷道:“有种!”
君不畏道:“四位有什么指教?”
李克发道:“姓君的,咱们不穿大褂装老板,你也别故作傻瓜二百五,打开天窗说亮话,你这大老千找上爷们头上了!”
君不畏干干一笑道:“四位,你们之中有三位原是什么银号的掌柜、骡马站的老板呀!”
尤不白沉声道:“别装了,你小子早就知道了。”
双方从先生、老兄,如今成了小子,君不畏便也不再客气了。
他不笑,但看上去似笑道:“我到小风城,原本与各位没过节,大家见面一场喜,只不过当我发觉被你们摆我一道,我的心里不舒服。”
李克发道:“所以你诈了五千两银子便大摇大摆地走了。”
君不畏道:“那是赢,怎说诈?”
莫文中道:“你很高明,不错,咱们未曾看出你玩诈,但事实上你玩诈,姓君的,你如果识相,就把五千两银票一个崩子不少地拿出来。”
君不畏道:“行,我答应送还,只不过我有个条件。”
敷中道: “你没有条件,你所面对的就是四对一的局面,你还琢磨什么?”
君不畏道:“听口气,已无商量余地了?”
莫文中道:“不错!”
李克发道:“石爷的银子你也敢诈,也不打听打听,石爷是干什么的。”
君不畏一笑,道:“你们说那石不全吗?”
尤不白道:“大胆,要叫石老爷子!”
君不畏道:“他是你们的老爷子,我没拿他的肮脏钱,他凭什么是我的老爷子?”
他此话甫毕,但闻“呛郎”拔刀声,四个人便把君不畏围起来了。
君不畏哈哈一笑,道:“群殴呀,哈哈……”
“你应该哭。”尤不白冷声道。
君不畏道:“江湖险恶,人心诡诈,姓石的原来与石达开是一家子呀!”
他此言一出,四个人几乎跳起来了。
李克发沉声吼道:“小子,你说什么?”
尤不白也加上一句:“我们不懂你说什么。”
君不畏道:“我的话你们真不懂?”
尤不白道:“你把话说清楚。”
君不畏道:“有时候话说得太清楚,听的人反而会糊涂,四位,你们还等什么?”
莫文中道:“姓君的,你都知道些什么?”
君不畏道:“小风城石不全和冀王石达开乃堂兄弟。”
四人闻言大惊,也彼此一瞪眼。
君不畏哈哈一笑,道:“石不全真是老奸巨猾,我可以称他一声老狐狸了。”
李克发道:“你听什么人造这谣言的?”
君不畏道:“不是谣言。”
李克发道:“必是道听途说,胡扯一通。”
君不畏道:“有什么比亲耳听到的还正确?”
“杀!”
“杀”字由莫文中的口中吼叫出来,尹在东已抱刀滚向君不畏的左侧,十七刀激射出一片刀芒,凌厉至极的刀杀向君不畏的下三路。
君不畏双眉一挑,见这人身材矮小,刀法怪异,单足点地腾身一丈八尺高下,半空中前后两把刀平削斜杀。
这四个人好像具有一套特异杀法,不用呼应而能联手合击。
君不畏半空中嘿然有声,真快!他人未落地,几点寒星已陡然射出,随之便闻得几声惨叫。
几声惨叫出自紧守一边的那人口中。
那是李克发,他惨叫着抛刀弯腰,双手捧着自己那张泛红的脸,血已自他的指缝中往外溢了。
君不畏怪异的身法空中旋,就落在李克发的身后面,他不但
闪过地上的一片刀芒,更把围杀的两人抛在两丈外。“叭!”他出腿,直把受伤的李克发踢了个狗吃屎。
“飕飕飕”的衣袂飘飘声,三个人立刻奔到李克发的身边看。
“老李,你伤在哪里?”
莫文中把手去掀李克发的肩只一半,李克发已转身挺腰坐起来了。
天啊,只见他的一只眼睛在流血,另一边脸上也有三个坑,那当然是血坑。
李克发双手摊开来,几块碎银子和着鲜血出现在他的一双手掌上。
还真有拿银子当暗器的。
其实打暗器的高手,到了出神人化境界,什么样的东西也能当暗器发射,至于有人说摘叶伤人,到现在只听说过,可没有人见过。
君不畏自称老镖客金刀胜英的后代传人,从他打暗器的手法看,大概也没有吹牛了。
李克发的眼睛毁了一只,但他另一只眼睛瞪得怕人,他咬牙切齿地抖着手掌中的碎银子,破口吼骂:“狗娘养的,你拿银子伤你家李爷!”
君不畏道:“李大老板,你不开绸缎庄了,却干起杀人的勾当了,我可以告诉你,我最讨厌别人对我用刀,这一点你们大概还不知道。”
其实这只不过是君不畏的几句逗人话,这世上任何一个人都讨厌有人对他们出刀。
李克发又骂道:“他妈的,这些银子……”
他还未吼完,君不畏已笑道:“哟,你提这些银子呀,这也是在各位面前赢的呀,在小风城赢的,如今所剩无几,也只有三二十两的了。”
莫文中大怒,因为他们本就打算好了,杀了君不畏,带着那五千两银票返回小风城,如今听得君不畏说只余不过三二十两,他火大了。
“干你娘,这才几天,你就把五千两银子折腾完了,你娘的,难道你一天三顿饭煮银子吃呀?”
君不畏淡淡一笑,道:“四位,你们怎么如此健忘,我是个喜欢输几个钱的标准赌徒,赢银子对我是痛苦的事,我赢了各位,我心里痛苦极了!”
尤不白怪叱道:“你真的痛苦吗?”
君不畏道:“我可以证明呀!”
这时候李克发自怀中摸出刀伤药,双手掩在伤处,还吁着大气。
那矮矮的尹在东厉声道:“你怎么证明?”
君不畏指着他们四人道:“我若是那天输给你们,我相信如今咱们还是拍肩搭背、握手言欢的好兄弟,可是,不幸得很,我赢了你们几个,可好,你们追上来要杀我,你们想一想,我痛苦不痛苦?”
尤不白冷冷一笑,道:“娘的,还是个油嘴滑舌的可恶家伙!”
莫文中斜视李克发,道:“李兄且在一边,我三人必为李兄讨回这血债。”
尤不白道:“也许是咱们把这小子估得太低了。”
君不畏道:“三位,你们还等什么?狠话不如狠杀,要见真章,不能单凭说说就完事。”
“杀!”
真快,也够狠,尹在东像个肉球似的一头直往君不畏的怀里
撞去。
直侍尹在东快碰上君不畏的时候,才发现一溜冷焰闪射出来。
就在尹在东扑杀的那一刻,尤不白左掌按在刀背上,右肘弯成半圆形,大叫着也往上冲。
那莫文中却抖出一个旋风身法,把君不畏的三个方位也堵住了。
这三人已把真才实学全部抖出来了。
君不畏冷冷一笑,他的身法更妙。
他好像缩地三尺似的,看上去如蚯蚓入泥,就那么腰身一扭又缩,自三人的围杀刀芒里溜出三丈外。
“嗖嗖嗖嗖嗖!”君不畏几乎就没回过身,他的一把碎银子又出手了。他好像真的不喜欢银子,随便一把撒出去,可也听得几声“哎呀”。
尹在东落地直抖手,他的刀已交在左手上,那一对愤怒的眼神,真想把君不畏吃掉。
尤不白的清瘦面皮有个血洞,他一手按住脸,气得全身在哆嗦。
莫文中的左腿上有血沁出来,他好像一瘸一瘸地站不稳当。
君不畏侧目一看,沉吟道:“各位,得罪了!”
莫文中叱道:“好小子,你想走?”
君不畏道:“你们拦得住?”
莫文中道:“你非死不可!”
君不畏道:“大话说多会闪舌头的。”
李克发大叫:“不能放他走,他知道的事情太多了,咱们不能放过他!”
尤不白道:“不错,今天只有豁上了!”
君不畏道:“只不过五千两银子,有什么了不起,一定得拚个你死我活?”
尤不白道:“五千两银子没什么,你小子却知道得太多,你不能活着走!”
君不畏哈哈一笑,道:“我才懒得过问那些窝里反、狗皮倒灶的事情哩。”他冷声又道:“去告诉石小开,叫他放心,我不会过问他的阴险勾当的。”
尤不白道:“如要少东家放心,只有你死!”
君不畏愤怒地道:“可恶!真想知道我的作风吗?老实说一句,石不全的勾当我也知道,好叫你们吓一跳。”
君不畏知道的不只是石小开的这些杀手,他更知道石不全与翼王石达开的关系。
莫文中听出君不畏话中有话,他心中一动。
“小子,你知道石老爷子什么事?”
君不畏道:“既然你要问,我就告诉你们,我知道的事情就是有关镖银……”
他“镖银”二字出口,莫文中四个人齐吃一惊,四人好像忘了伤痛,一个个往君不畏逼过来。
君不畏双手连摇,道:“各位,你们千万放心,我自是守口如瓶,不会张扬。”
李克发道:“你说镖银,什么镖银?”
君不畏道:“镖银就是镖银,打什么哈哈?”
李克发急问道:“你知道镖银怎样?”
君不畏道:“何必明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不已经够了。”
尹在东道:“小子,我们想明白,你知道镖银怎么了,快告诉我们!”
君不畏道:“如果我不说呢?”
尹在东道:“你非说不可!”
君不畏道:“强人所难?”
尹在东道:“就算是吧!”
君不畏淡淡地道:“我忽然觉得我的作风要改变一下了。”
莫文中叱道:“什么意思?”
君不畏道:“你们知道,我赌牌不求赢,输了才高兴,我搏斗也一样,输不起,但赢了也受气,你们已经是我手下败将,却仍然口口声声地逼我说出心里话,就好像你们是赢家,像话吗?所以……”
莫文中道:“你想怎样?”
君不畏道:“杀掉你们!”
李克发怒道:“杀人灭口啊!”
君不畏道:“这话应该我说,你们四人不就是要杀我吗?那么我再告诉各位一件非杀我不可的消息。”他顿了一下,又道:“我就告诉你四位,你们的石老爷子好手段,他把镖银送到他堂兄石达开处,而又以嫁祸手法,叫东王与北王互斗,各位,我这些话不是造谣吧?”
他的话音甫落,莫文中四人全愣住了。
李克发独自闪射着凶芒,溜溜地转个不停。
尹在东突然大叫一声,道:“杀!”
四个人再一次挥刀欲杀,突然传来一声喝叱:“住手!住手!”
这叫声来得突然,但声音却很熟悉。
君不畏本要搏杀四人的,但他也在这叫声中住手了。
莫文中四人齐回头,只见来了两个人。
两个人君不畏都认识,一个是石小开,另一个乃是那个女
的,那个曾经在“石敢当赌馆”后面耳房侍候人的三十多岁的女人。
这两人来得突然。
当然,这两人也来得太巧了,及时拦住一场拚命的搏杀。
说句实在话,石小开等于救了莫文中四人。
君不畏便有这种想法,石小开怎么会在此时出现?
他冷冷地注视着石小开。
李克发迎上去,满面鲜血地道:“少东……”
石小开道:“别说了!”
尤不白指着君不畏道:“少东他……”
石小开再喝叱:“别再多说了!”他转对君不畏笑笑,道:
“君兄,怎会发生这种可怕的误会呀?对不起。”
他再对李克发四人道:“你们走吧,受了伤还不快去医治。”
莫文中四人还想再说什么,但见石小开满面怒容,便齐齐回身离去。
君不畏心想:“昨日石小开和这女人住在船上,莫文中四人住在另一条船上,想不到如今石小开也来了。”
石小开伸手哈哈笑道:“君兄,天大的误会呀!”
君不畏心中明白,石小开这一回到上海,也全是冲他来的,他岂能不防?
他哈哈一笑道:“石兄,是我得罪了,只不过可并非是我先动手,我完全出于自卫。”
石小开笑笑,道:“也怪他们学艺不精,活该!”
君不畏道:“石兄,你这回前来,莫非……”
石小开忙道:“另有公干,也是我爹指派。”
“哈哈哈……”君不畏仰天一笑,石小开也跟着笑,一边的女子却对君不畏斜视又微笑,仿佛十分欣赏君不畏似的。
君不畏抬头看看天色,他收住笑。
当然,石小开也不再大笑,他换成一张愉快的脸。
君不畏道:“石兄,有件事情我要明说。”
石小开道:“我早把君兄当成自家兄弟了,自家人当然应推心置腹呀。”
君不畏笑笑,心中在骂:“有个老狐狸,就有你这小狐狸,果然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你石小开是臭虫,还以为我是傻蛋,哼,你听了我的话如果还能笑出来,我君不畏就佩服你。”他仰天哈哈一笑,道:“石兄,我已经知道那些镖银的真正下落了,啊哈,你们真好计谋呀。”
石小开一瞪眼,道:“你知道得太多了,你不应该知道一些与你无关的事情。”
君不畏道:“石兄,我把我知道的事情告诉你,就是表明我并不想出卖你,只不过我心中明白,你是不会放过我的,是吗?”
石小开哈哈一笑,道:“我有本事杀你吗?”
君不畏道:“你没有。”
真会气人,石小开听得如被刀割,他在咬牙。
一边,那女人举起手上丝帕迎风抖,她吃吃笑着向君不畏身前走。
她一边走,一边笑道:“都是自己人嘛,君先生,我们少东最爱交朋友,只要君先生说一声,要什么也不会叫你失望呀。”
她就快去摸君不畏了。
石小开一闪身,那女的手帕用力一抖,便也抖出一股香风扑鼻。
君不畏还以为女人的东西本就这种味道,但当女的又在他面前抖不停的时候,他警觉了。
君不畏暗中运气只一半,忽觉头有些昏沉沉。
他的反应快,暴喝一声拔身而起,掌风便也打得那女子尖叫一声,仰面吐出一股鲜血,歪歪斜斜地昏倒在地上。
君不畏暴旋身,右手并指疾点,指风过处,石小开猴叫着左闪右躲七八丈,右肩头以下已被君不畏指风扫中,右臂立刻垂下来,吓得他脸也白了,抱头便往来路跑。
他跑了至少四五里远才回头看,早已不见君不畏了。
君不畏没有再追赶,他已知中了迷魂药,才突然对石小开与那女子下重手。
石小开见君不畏未追来,他喘气如牛地甩动着右臂,只可惜他的右臂越甩越痛。
君不畏未追他,这倒令石小开升起一股子阴毒的希望,他相信君不畏可以抵挡迷药一时,却不能维持多久,也许君不畏已昏倒在地上了。
石小开想到这里,不由冷笑连声。
他又回过头来了。
他也得把女的救回来,那女的对他十分重要,当然,如果君不畏昏倒在地,那正是杀死君不畏的最好时机。
石小开面上露出笑容,左手五指箕张,光景他正准备要杀人了。
现在,他又走回来了,他发现地上躺着女的,但君不畏却不见了。
石小开这时候才确信君不畏着道了,他更相信,君不畏那最后一击完全是为了救他自己。
有了这念头,石小开立刻往四下里寻找,当然希望能找到君不畏。
他也想好了,只要找到君不畏,他一定立刻出刀,绝不叫君不畏再活。
只可惜他找了很久,附近什么也没有。
石小开忿忿地又走回来了。
石小开也发觉他带来的女子坐在地上满面泛白。
石小开奔过去,道:“兰儿,你醒过来了。”
兰儿撑坐着四下瞧,道:“姓君的呢?”
石小开道:“没找到,他一定着了你的道,才会出手对付我两。”
兰儿道:“少东家,我真心地佩服姓君的。”
石小开道:“你是说他的反应?”
兰儿道:“我佩服他的武功,少东,我的迷药你清楚,中的人立刻会倒下,可是姓君的吸了不少,但他还有力量使出来,这就表明他的武功过人。”
石小开道:“只不过姓君的逃了。”
兰儿道:“他也许可以抵挡一时,时间一久,必然还会倒地,我们四下再找找。”
石小开道:“你还能动吗?”
兰儿道:“我躲得快,未被他拍中要害,活动一下筋骨就会没事了。”
石小开道:“我以为咱们还是先回船上去。”他怒目直视大江,又道:“他们传说姓君的武功高,我也只是疑信参半,如今交手,才知不假,想杀这小子,怕得一番手脚忙了。”
兰儿道:“如再遇上,咱们正面出手,就不信收拾不了这姓君的小子。”
石小开道:“走,咱们到江边去。”
两个人缓缓往江边走着,只走了半里地,迎面奔来一个人。
这个人长得美,也打扮得洋气,引得石小开的眼睛也看直了。
这女人非别人,沈娟娟是也。
沈娟娟在赌馆久等君不畏不归,她急得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
她实在等不下去了,便也不管君不畏气不气,便匆匆地奔出来了。
沈娟娟出门就问人,一路问到这儿来,他发现了石小开与兰儿走过来。
附近没有人,沈娟娟不认识石小开与兰儿,两下里刚要错肩走过,沈娟娟忽然回身问。
“喂,你们两位可曾看到几个人?”
石小开回过身来看看沈娟娟,道:“什么人?”
沈娟娟道:“好像是……五个人。”
石小开道:“姑娘,你能不能说得清楚些?”
沈娟娟道:“是这样的,有四个人在我赌馆玩牌九,同我的一位朋友几句话不对味,便相约出来了,我担心出人命,才出来找他们。”
石小开立刻知道这女子是找君不畏的。
石小开道:“五人中有一个是你朋友?”
沈娟娟道:“是呀。”
石小开道:“好像见过这五个人。”
“在哪儿呀。”
“他们在那面打架,打完了分开各自走了。”
“我那朋友呢?”
“也走了。”
沈娟娟一急,又问:“他去哪儿了?”
石小开道:“我不知道,不过,如果我再遇到他,我会对他说你在找他,只不过……你是……”
沈娟娟立刻回道:“我叫沈娟娟,我住在四马路一家赌馆后 院里。”
她还冲着兰儿笑笑,笑得兰儿也点点头。
沈娟娟又道:“本来大家玩得挺愉快,怎么说翻脸就打起来了。”
石小开道:“姑娘,男人们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便是打一架,这年头谁有劲谁有理。”
沈娟娟一怔,也冷冷地笑笑。
石小开扶着兰儿便往江边走,他两人再也未回头。
沈娟娟找不到君不畏,垂头丧气地又往回走。
她以为君不畏大概受了伤,不好意思回赌场。
她猜错了,君不畏如果真受伤,他一定回赌场,有什么地方比在沈娟娟那儿养伤妥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