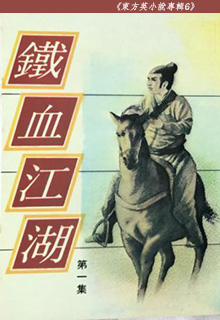沈家堡很快便到了。有个中年大汉自堡门内迎出来,对着愉快而回的沈文斗深施一礼,道:“少堡主,咱们有客人来了!”
沈文斗道:“总管来得好,快见过苗总镖头与苗姑娘。”
那人一双锐利的眼神一亮,立刻走近苗刚,哈哈一笑,道“原来苗总镖头来了,欢迎!”
苗刚点头一笑,道:“打扰了。”
沈家堡总管沈焕打个哈哈,当先在前面带路,一行人往堡内走。君不畏抬头看,这儿还真气派,堡墙三丈八尺高,堡墙上还有人在了望,正面一座大宅院,丈高的石狮子有两座,分别守在大门的两边,有个横匾是金字,上面有金光闪亮的四个大金字“霸海雄风”。
走进大门,里面是个大院,院子一角有一口大井,两边耳房,房檐下挂的是风干了的鱼,耳房内有人在工作,只不过这儿不是正厅,沈家堡的正厅还在后院。
绕过这大院,啊,景物立刻就变了。这座院里种着各种花卉,鸟笼子就有七八个,挂在两棵树下,这时候正有个锦袍老者在逗鸟呢。
“爹!”
老者闻声回过头看,他发现苗刚了。
苗刚立刻横跨一步迎上前,双手抱拳施礼道:“沈老爷子金安,苗刚打扰了。”说着,自怀中摸出一个大红包,双手递上。
那老者正是“铁臂苍龙”沈一雄。
沈一雄哈哈一笑,道:“来了就好,何必送礼。”
苗刚道:“怕是不成敬意。”
沈焕打横接过苗刚手上红包,那沈文斗已对他爹道: “爹,苗姑娘也来了。”
苗小玉已盈盈向沈一雄施礼,道:“沈老爷子金安。”
沈一雄上上下下仔细看过苗小玉,点头道:“果然巾帼英雄也,哈……”他笑着,立刻吩咐沈焕,道:“备酒,今天好生同苗总镖头喝几杯。”
沈一雄看看君不畏,他似乎怔了一下。
君不畏面带微笑,紧紧地跟在苗小玉身边。
他也回头看沈一雄,只不过他带着几分不屑,当然,沈一雄似也看出来了。
“这位老弟台是……”
苗刚忙回道:“我局子里的镖师,不过……”
沈一雄点点头,道:“他这年纪当上镖师,武功必然不错,将来定大有前途。”
沈文斗道:“快进厅上坐吧,爹……”
他当然不愿意这时候提别的,他只希望苗小玉能多留些时候,又何必把宝贵时间在此浪费。
君不畏仍然微微笑,他跟在苗小玉身后走进沈家堡这座豪华大厅上,马上惊讶了。
这座大厅真气派,只见玻璃门窗琉璃灯,檀木椅子铺锦缎,有两个大花瓶半透明,足有三尺高下,分别搁在大台的两边,里面插的大花有锅盖那么大,正中央还放着一尊弥勒佛像,挺着个光肚皮直发笑,好像在欢迎客人来临似的,只缺笑出声音来。
沈一雄笑出声音来了。
他伸手让座,哈哈笑道:“你们坐,别客气。”
苗刚三人按序坐在客座。沈文斗就坐在苗小玉对面,那一双眼神直冲着苗小玉瞧,光景他是越看越起劲,越瞧越入迷,便是他老爹沈一雄也瞧出来了。
只不过沈一雄看到苗刚带有伤,皱皱眉头,道:“总镖头这伤……”
苗刚一听,忿然道:“就在南麓外海,遇上一股海盗,少不了一场厮杀。”
沈一雄一瞪眼,道:“莫非你们碰上丁一山了?”
苗刚重重点头,道:“不错,正是丁一山。”
沈一雄道:“丁一山原是太湖水寇,想不到他把人马拉到海面上了,可恶!”
一边坐的苗小玉咬牙道:“近岸水路原本是太平航道,田九旺也很少在近岸下手,如今多了个丁一山,太出意外了。”
苗小玉话甫落,沈文斗便也点着头道:“干上海盗,六亲不认,沈姑娘,在下真为你担心啊。”
苗刚笑笑,道:“还好,咱们把姓丁的打跑了,想他再也不敢拦劫咱们‘跨海镖局’的镖了。”
他还转头看看君不畏,带着几分安慰的眸芒。
君不畏却木然地坐在那里,好像不太喜欢说话,他心中想什么?只怕谁也不知道。
沈一雄道:“总镖头,听说太平军闹内讧,南京城那边不太平,你的这趟镖……”
苗刚笑笑,道:“押镖只到上海,老爷子,太平军闹内讧,大概是气数吧。”
他这话甫出,君不畏的目光一厉,只不过别人未曾注意他。
沈文斗却接口道:“听说直鲁豫那面又起了捻军,大清朝有得忙的了。”
君不畏的目光再一厉,他直视沈文斗。
沈文斗根本不看君不畏。
沈文斗只注意苗小玉,他轻松地又道:“苗姑娘虽然英勇,终归是女子,我以为苗姑娘能留下来暂时住在沈家门,等镖局的船回航,再回小风城为好。”
苗小玉尚未开口,苗刚已粗声道:“镖未押到,她怎好留下来?”
沈一雄笑笑,道:“总镖头,由此到上海,老夫敢说那是我沈一雄的天下,你放心吧!”
苗须小玉道:“老爷子,你多体谅,非是小玉不想留下,实在咱们也无奈,‘跨海镖局’是有纪律的,怎好中途退出,对兄弟们难有交代……”
沈一雄点头道:“老大最是佩服有原则的人,苗姑娘,老夫不勉强了。”
沈文斗似是失望地道:“爹,至少容我陪着去上海,咱们上海的生意也要去看看了。”
沈——雄道:“你去可以,可别多事。”
沈文斗道:“爹,你放心,我又不是孩子。”
他特意对苗小玉笑笑,苗刚却对沈文斗道:“船上怕是招待不周呀。”
沈文斗道:“总镖头,我是随遇而安的人,你别特意招待,哈……”
他得意了,苗小玉却周身不自在。
苗小玉不自觉地看看君不畏,发现君不畏仍然一副木然的样子,便暗自有些发火。
她以为君不畏根本不注意她,这对她的孤傲性子是一种挑战,苗小玉暗自在咬牙。
苗小玉如果不孤傲,君不畏自丁一山手上救了她,她早应该奉君不畏为救命恩人了。
沈一雄的酒席是丰盛的,但吃的人并不见得愉快,因为在苗刚心中,他这是拜码头,心中一千个不愿,却非要前来不可。
苗小玉更是无奈,她吃得很少。
君不畏不一样,他吃得很多,而且也喝了不少酒。
沈一雄开始注意君不畏了。
“年轻人,你出道不久吧?”
君不畏道:“我年纪不大。”
“师承是……”
“家传小技而已。”
沈一雄笑笑道:“江湖上不乏出类拔萃之土,他们也部出自名门,君兄弟的来历……”
君不畏道:“沈堡主,如今天下荒乱至极,太平军、捻军……很多人的家早已不存在了。”
沈一雄道:“那么你的家……”
君不畏道:“在劫难逃!”
这真是叫人摸不着边际的回答。君不畏到底什么来历,一时间沈一雄也不便再问下去。
没有人专挑别人痛苦的事情追问个没完没了的。
沈一雄是老江湖,他当然更不会再问。
他干声一笑,道:“来,大伙干杯!”
大厅上众人正在饮酒,门外面不带声息地走进一位妙龄姑娘,这姑娘的模样长得俏,柳叶眉,杏仁眼,樱桃小嘴一点点,两个耳朵挂翠环,头发上还插了一朵马英花,落地裙上绣珠花,粉红上衣也贴身,便把姑娘的曲线完完全全地衬托出来了。
姑娘这一身打扮很时尚,这正是上海开埠以后,女人最爱穿的那种迷人裳。
沈一雄眼一瞪,沉声道:“娟娟!你来做什么?”
原来这位妙龄姑娘乃沈一雄的女儿沈娟娟。
“爹,我搭便船去上海呀。”
沈一雄道:“你哥去上海有事办,你也去?”
“爹,咱们上海的买卖我最清楚不过,我是去查看他们的进出帐呀。”
沈一雄尚未开口,苗小玉已笑笑道:“沈小姐去上海,那就同我一条船吧,沈公子搭乘我哥的快船,这样便也有个人在船上说说话。”
沈文斗愣然无言以对,苗刚已点头道:“好,就这么安排,老爷子也放心了。”
一边的沈姑娘不动了。
她不但未动,更未说话,因为她正在盯视着君不畏,那眼神就好像发现令她吃惊的人似的。
君不畏低头夹菜,沈一雄以海鲜招待,他吃得似乎十分愉快,当然也未多看沈娟娟。
沈文斗终于开口了:“大妹子,我去上海你在家,咱们的买卖我比你更明白,还用得着你也去?”
沈娟娟回眸向她哥沈文斗道:“哥,你休想撇下我一人去上海。”
她轻盈地走近苗小玉,道:“苗姐姐,我们说定了,我收拾收拾便随你上船了。” 真大方,她再一次看向君不畏,还抿嘴微微一笑,沈一雄大不以为然,好像无可奈何的样子。
“跨海镖局”的快船启动了,三艘快船穿过舟山水道,往北直航上海,海面上一片平静。
那苗刚很放心地热情招待着沈文斗,只不过沈文斗却不时地遥望着另外一艘快船,因为那艘快船上不只有他的大妹子沈娟娟,更要紧的是船上有个苗小玉。
苗小玉把沈娟娟招待在她住的后舱内,只不过沈娟娟很少在舱内。
她好像兴致高,站在船面上微微笑,尤其当她看到君不畏的时候,更露出愉快的样子。
现在,君不畏又自舱内出来了,手中正捏着两颗骰子。
沈娟娟发现了,便吃的一笑迎上去。
“哟,你好像喜欢赌呀。”
君不畏道:“沈小姐,我只喜欢赌牌九。”
沈娟娟吃吃一笑,道:“三十二张牌九?”
“不错。”
“那好,我们到上海,我带你去个地方赌牌九。”
君不畏眼一亮,道:“你也赌?”
沈娟娟笑笑,道:“我家在上海有场子。”
君不畏心中一沉,面皮一紧,道:“太可惜了。”
沈娟娟道:“怎么说?”
君不畏道:“正逢我袋中空空之时呀!”
沈娟娟吃吃笑了。
君不畏不笑,面皮拉得紧,捏着两颗骰子,道:“沈小姐,你知道我为什么闹穷?”
沈娟娟道:“我怎么会知道?”
君不畏却也笑了。
沈娟娟道:“你笑什么,告诉我你为什么闹穷?”
君不畏道:“很简单,我喜欢输银子,一个爱输银子的人,当然会时常闹穷。”
沈娟娟撇撇俏嘴,半叱地道:“胡说,还有喜欢赌输的人!”
“我就喜欢输。”
“少见!”
“你已经见了!”
沈娟娟道:“我知道,那些进入赌场去的人,没有一个不是打定主意去赢银子的,而且赢得越多越高兴。”
君不畏道:“可惜走出赌场的人大多数愁容满面,可怜兮兮。”
沈娟娟道:“你喜欢可怜兮兮?”
君不畏道:“我不同,如果我赌输,反而高兴。”
“为什么?”
“个中滋味很难言喻。”
沈娟娟笑笑,道:“你好像是个怪人嘛。”
君不畏道:“我比正常的人还正常。”
沈娟娟道:“船到上海,我借银子给你去赌。”
君不畏道:“你叫我去送银子?”
沈娟娟道:“你如果喜欢,你就送吧!”
君不畏道:“沈小姐,你喜欢我把银子赌光?”
沈娟娟道:“我说过,只要你喜欢。”
君不畏道:“我忘了,我喜欢赌大的,输个三五千两银子很平常。”
沈娟娟怔住了。
她以为君不畏只不过赌上三五十两银子,而且她把君不畏带到她家开的赌场,赌输了也无所谓,银子还是沈家的,然而……
然而君不畏的口气太大了,沈娟娟不由愣住了。
君不畏一看沈娟娟的表情,哈哈一笑,低下头又回到舱中了。
如今的君不畏是不会再洗船板了。
他被招待得就好像个贵宾,黑妞儿对他说话也先是一声笑,客气极了。
君不畏坐进舱中,“坐山虎”包震天伸手一把扣住君不畏的手,低声道:“君老弟,你打算留在上海?”
君不畏一怔,道:“我打算杀了田九旺再去上海。”
“为什么?”
君不畏淡淡地道:“苗小姐替我担保的一千两银子尚未清还呀。”
包震天道:“君兄弟,如果包某拍胸脯呢?”
君不畏道:“包老爷子,我仍然要杀田九旺。”
包震天道:“田九旺和你有仇?”
君不畏道:“我不认识田九旺。”他不得不说谎。
包震天道:“为何一定要杀田九旺?”
君不畏道:“我说过,我需要赌资,而我又爱输几个,哈哈……”
包震天摇摇头,道:“君老弟,你到底是什么人物?我有些糊涂。”
君不畏笑笑,道:“难得糊涂。”
包震天道:“君老弟,算我聘请你,我们押着这批银子绕道南京城,只一到你就回头,如何?”
君不畏道:“我得问问苗小姐,如果她点头,我就跟你去南京。”
包震天哈哈一声笑,点头道:“好,咱们就一言为定,我去对苗姑娘说。”
便在这时候,舱外面传来黑妞儿的声音:“君先生!君先生呀!”
君不畏伸个头出来,道:“你找我?”
“小姐找你……不……我忘了,是小姐请你。”
君不畏笑笑,走出舱门,道:“请我?干什么?”
黑妞儿哈哈笑道:“当然有事了。”
有什么好笑的,但她仍然哈哈笑,笑得君不畏也有些不自在。
他跟着黑妞儿绕到船尾舱门口,那黑妞儿已低声道:“小姐,君先生来了。”
妙影闪动,苗小玉已站在君不畏面前,这时候沈娟娟也过来了。
沈娟娟冲着君不畏瞧,嘴角微微撩,似笑不笑的样子,就好像一肚子话不知如何说出来似的。
苗小玉看着海面,道:“过午船就到上海了。”
君不畏道:“真快。”
苗小玉忽然回过身,面对君不畏,道:“船到上海你要走?”
君不畏道:“如果苗小姐叫我走。”
苗小玉道:“我改变心意了,如果你愿意,就留在船上。”
她的脸上略带羞涩的样子,那也是一种不好意思的表情,君不畏当然看得出来。
君不畏道:“有关那一千两银子……”
苗小玉道:“我说过,那是小事,不必挂齿。”
君不畏道:“我却难忘怀,所以我听你的。”
包震天使在这时候也过来了。
包震天对苗小玉道:“苗姑娘,有件事情要你担待了。”
苗小玉道:“包老爷子,你别客气,有什么吩咐,尽管明说。”
包震天拍着君不畏肩头,道:“为了路上安全,我想借重君老弟,陪我走一趟南京。”
苗小玉怔了一下,她把目光移向君不畏,却见君不畏遥望远方。
前方水线上有山峦的影子,海面上的帆船似乎也多了,看上去宛似樯林。
苗小玉道:“包老爷子,我不能勉强君先生。”
包震天哈哈一笑,道:“苗姑娘放心,我们还有第二批、第三批银子,我决定都借重‘跨海镖局’押送,君兄弟只一到南京,我立刻放他回小风城。”
君不畏哈哈一笑道:“苗小姐,我算是‘跨海镖局’的人吗?”
苗小玉一愣,道:“我待慢了。”
君不畏道:“苗姑娘,撇下千两银子不提,至少我欠你一份人情。”
苗小玉道:“你已为我们出过力了。”
君不畏道:“我仍然听你一句话。”
苗小玉心中可乐了。
她的脸皮却不动,妙目闪烁地道:“如果君先生喜欢,‘跨海漂局’欢迎你。”
一边的沈娟娟开口了:“怎么,他原来不是你镖局的镖师呀?”
苗小玉未开口,君不畏开口了:“至少我现在是。”
沈娟娟道:“如果你想找差事,留在上海嘛。”
君不畏道:“我只会赌,而且喜欢输。”
沈娟娟道:“你真是个怪人。”
君不畏哈哈笑了。
包震天愉快地道:“好了,咱们就这么说定了,船到岸,君老弟与老夫一同押着银子去南京。”
苗小玉看看君不畏,发觉君不畏也在看她,便不由得把头低下了。
沈娟娟却对君不畏道:“你真要去南京呀?”
君不畏道:“有什么不可?”
沈娟娟道:“那里局势不好,南京城有杀声呀。”
君不畏淡淡地道:“沈小姐,像我这种人,只有在杀戮中才生活得快活,你以为呢?”
沈娟娟怔怔地道:“唯恐天下不乱吗?”
君不畏道:“天下已经大乱了,沈小姐。”
沈娟娟不说了。
沈娟娟低头进入舱内,因为她知道留不住君不畏,就算她出高价雇用,君不畏也不会在上海,一气之下,她躺在舱内不出来了。
苗小玉也进入舱中了,黑妞儿没有,她站在君不畏面前挡住他的去路。
包震天拍拍君不畏,转身往船头走去,他很关心上海接船的人,还远呢,他已遥望着远方露出一副焦急的样子。
君不畏没动,他淡淡地看着黑妞儿。
“你去南京?”
“你已听到了。”
“还回来吗?”
“你说呢?”
他这是在逗黑妞儿,果然,黑妞儿有些不知所措的样子,急得直咬牙。
君不畏却哈哈笑了。
“跨海镖局”的快船,并排在黄浦江外,三条船刚摆好,便见一条快船从岸边飞一般地驶来,船头上有个黑衣大汉双手叉腰站稳,有四个黑衣人正准备把船靠过来。
总镖头苗刚过来了,苗刚的身后还有个沈文斗。
苗小玉和沈娟娟也过来了。
沈文斗迎上他大妹子沈娟娟,但目光却落在苗小玉身上直打转。
苗小玉当然知道沈文斗在盯她,但她只是淡然地站在包震天身边。
君不畏在前面船头和伙计们打招呼道别离,只见小刘拉着君不畏半晌不听他说上一个字,一边的胖黑好像快掉泪似的愣着,另外几人也点着头,有个汉子开了口:“君兄弟,你可得早早回小风城,大伙都等着你,等着同你……同你……”
“赌几把,是吗?”君不畏笑着。
那位仁兄道:“不,是喝几杯。”
“对,大伙在小风城喝几杯!”小刘也这么回应着。
君不畏点头一声哈哈,回过身来,正与苗小玉的目光碰个正着,于是……
于是沈娟娟也看到了。
来船打横驶过来,船上的黑衣大汉一跃三丈远,稳稳地站在包震天面前。
包震天有些愣然地道:“大将军呢?”
黑汉看看左右,低沉的声音对包震天道:“南京城不太平,大将军人马拉往通州,兄弟们急于饷银,命我在这儿等包兄,不知银子……是否已运到?”
包震天道:“不去南京了?于将军,十万两银子已在船上,你打算……”
姓于的点点头道:“那就马上交割,然后我进长江口转通州。”
包震天伸手道:“也好,请拿出大将军命令。”
姓于的一怔,道:“难道包兄信不过于文成?”
包震天道:“只是手续问题。”
于文成道:“包兄已募到饷银,咱们一齐回军中,大将军面前自然明白。”
包震天似是带着无奈,他忽然眼睛一亮,因为他看到君不畏了。
他把手一挥,对一旁的苗刚道:“总镖头,马上交割银子。”
苗刚当然照办,镖银交割完,他们就算任务完成,如今上海这地方在发展,原来是渔村,自从来了洋人以后,立刻变了,变得比个县城还热闹。
包震天眼看着一箱银子抬到于文成的快船上,便伸手拉过君不畏道:“君兄弟,南京不去了,咱们上通州。”
君不畏道:“你去通州回大营,我去通州干什么?”
包震天一笑,道:“咱们说好了的,你陪我把银子送到大营的。”
君不畏指指来船上的人,道:“你们人马已到,任务已完成了,还用我帮什么忙?”
包震天转头看看正在指挥的于文成,低声道:“我心里总觉得不对劲,君兄弟,算我求求你。”
君不畏有些木然地道:“你……这不是叫我少赌几天牌九嘛。”
包震天哈哈一笑,道:“君兄弟,事成之后,少不了和你大赌一场,绝不令你失望。”
君不畏道:“我帮了你的忙,还得送你银子呀。”
包震天道:“这话怎么说?”
君不畏道:“你明知我爱输呀。”
包震天道:“爱说笑了。”
君不畏道:“更何况我也没有银子。”
包震天道:“多了没有,三二百两我奉送。”
君不畏淡淡地笑了。
十万两银子已搬到于文成的快船上了,“跨海镖局”总镖头苗刚特别吩咐弟兄们置上一桌酒席,明着是为了替包震天送行,实际上却是对君不畏的一番感谢。
大伙正在吃着酒,忽见一条小船靠过来,原来是沈家的船看到沈文斗兄妹了。
沈家兄妹要走了。
兄妹两人真大方,沈文斗走近苗小玉,十分文雅地对苗小玉道:“我诚心邀你上岸玩玩。”
苗小玉淡淡地道:“以后再说吧。”
沈文斗不算丢脸,至少他还有希望。
沈娟娟走近君不畏,道:“君先生!”
君不畏一愣,道:“有事吗?”
沈娟娟伸手往君不畏手中塞了一张字条,道:“这是我的地址,你到上海一定找我。”
君不畏道:“除了赌馆……”
沈娟娟笑笑,道:“上海最大的赌馆就是我家开的。”
君不畏愉快地笑了。
于是,沈家兄妹跳上小船,很快地往黄浦江划去。
包震天拉着君不畏,两人就要上于文斗的快船了,苗小玉突然走过来。
苗小玉不开口,她只是看着君不畏。
她此刻心中想着什么,连她也不清楚,很乱,也很无奈,她只把手往君不畏袋中一塞,回身便往舱中走去。
黑妞儿没有回舱中,她看着君不畏与包震天并肩跳到于文成的快船上。
“跨海镖局”的人站在船上直挥手,君不畏愉快地微微笑,但当他自袋中摸出一个荷包时,他不笑了。
他以为苗小玉送了他几两路费银子,万万料不到会是一个小荷包,她这是代表什么?
君不畏愣然了。
快船已往长江口驶去,君不畏发觉,快船上的黑衣人似乎多了一倍,数一数至少有十七八个之多。
刚才他未注意,为什么一条小小快船上,有这么多人?
于文成陪着包震天在船头看风景,君不畏无聊地坐在船边养精神。
如今他想得多,沈娟娟、苗小玉,这两个女子似乎都对他有了情愫,他……
一念及此,君不畏笑了,他怎么会和她们……
烟波浩瀚的长江口,船只原本往来如梭,不知为什么这两天很少有船活动。
于文成的快船已行驶在江中了,便在这时候,夕阳余辉中,突然电光激闪,随之便闻得包震天高吭地一声厉嚎:“啊!”
“扑通!”水声甫起,水花四溅,便闻得于文成戟指吃惊的君不畏,厉吼:“杀了他!”
君不畏甫挺直身子,落水的包震天又叫:“君……”
迎面,五个黑衣怒汉直往君不畏杀来了。
三枝红缨枪加上两把大马刀,在这空间极小的快船上,君不畏闪避不易,他除了一飞冲天,别无余地。
君不畏没有往天空飞,横着肩便往水中跃,他人尚未入水,两枝红缨枪已往他身上掷来,只不过君不畏看也不看,随手往后甩臂,已把两枝红缨枪拔落水中。
紧接着“扑通”一声水花四溅,君不畏落入水中,抬头看,哟,那包震天己在数十丈外了。
如今正是落潮时分,加以自长江流下的水势,包震天自然早已飘出很远了。
君不畏再看于文成的快船,却早已往江中驶去了,他猛提一口气奋力向包震天游过去。
他发觉江水中有血,那当然是包震天身上的血,君不畏知道,包震天这一刀不轻,只怕……
君不畏游近包震天了,他发觉包震天除了把一张脸平仰江面之外,全身不动地飘着。
“包老爷子,我来了!”
没有反应,包震天好像昏过去了,君不畏伸手抓住包震天衣衫只一提,便不由一惊。
“这一刀……”
包震天从右肩头连上背,衣破肉绽似乎骨头可见,如果在岸上,这一刀也会叫人不能动弹,如今又在水中,那血还在流不停。
君不畏抓住包震天便往岸边游,事情偏就那么巧,一条快船过来了。
快船上有人大声叫:“有人掉进江里了!”
于是,快船半调头,落下帆,五个大汉挤在船边看,其中一人大声喊:“喂,那不是君先生吗?”
君不畏抬头极目瞧,快船上竟然是沈文斗,那么沈娟娟也许就在上面子。
君不畏忙把手举起来,一把抓牢伸来的长竹竿,于是,船上的绳索也抛下来了,君不畏忙将包震天拴牢,大伙用力拖起包震天,沈文斗又急问:“怎么了?怎么了?”
君不畏跳上船,一阵子大喘气之后,道:“快救人!”
只见包震天已昏死在船板上,沈文斗立刻叫掌舵的道:“改期再去崇明岛,现在回上海。”
那崇明岛本在上海外,乃长江口的一个岛,沈家有生意在岛上,沈文斗把他妹子送到岸上,他原船改去崇明岛,想不到中途救起君不畏与包震天两人,也算巧合。
沈文斗仔细看包震天的伤势,不由紧皱眉头,道:“真狠,这一刀是要他老命。”
君不畏道:“八成他们窝里反,自相残杀。”
沈文斗吃惊道:“他们是什么人?怎会……”
君不畏笑笑道:“把他救活再说。”
沈文斗当然想不到,包震天的身份是什么。
他也想不出君不畏的身份,他只明白一件事,那便是他的妹子沈娟娟似乎看中君不畏了。
就凭这一点,沈文斗便决心把这两人送去一个地方,那便是他大妹子住的地方。
沈文斗的快船拢近岸,有个大汉已奔往附近小村上找大车了。
如今上海这地方已开埠,骡马栈房不少,那大汉很快便叫来一辆车子,帮着君不畏把包震天抬上大车。沈文斗吩咐一声,大汉便陪着往上海驶去,沈文斗这才又开船往崇明岛驶去。
君不畏很替包震天担心,因为包震天挨的一刀半尺长,好像肩胛骨也裂开一道骨缝。就在大车的疾驶中,包震天有气无力地翻开眼皮子,当他看到身边坐着君不畏的时候,立刻露出个微笑。
那种笑是十分复杂的,君不畏就觉得包震天笑得不太自然。
不自然当然不好看。君不畏忙问:“包老爷子,你觉得怎么样?”
包震天只是两唇翕动一下,没声音。
大约半个时辰,马车停下来了,只见大汉当先跳下车来,高声叫道:“过来几个活的人!”
当然是活人,死人怎么会动?
三个青衫汉子奔过来,其中一人问道:“嗨,林老二,你不是陪少爷去崇明岛吗?怎么……”
姓林的大汉叱道:“少废话,把受伤的抬进去,我去向小姐禀告一声。”
君不畏跟在三个青衫汉子身后面,他这时候才看清楚,原来这地方是一条小街道。别看是小街道,四匹马并排一样可以通过—— 这以后上海有一条四马路,大概就是这一条街道。
一行人走进一座大院内。迎面,沈娟娟像个花蝴蝶似的自屏风后面奔出来了。
沈娟娟看到君不畏了,脸上一片喜悦;但当她看到重伤的包震天之后,惊住了。
“怎么……这样……”
君不畏道:“沈小姐,快请大夫来为包老爷子治伤吧。”
沈娟娟当即命姓林的快去请大夫,又命人把包震天抬进客厢中,这才问君不畏,道:“是谁下的手?”
君不畏摇摇头,道:“那要等包老爷子清醒之后,才会知道。”
“包老爷子好像请你保驾的呀。”
“所以我把老爷子救回来了。”
“那么多箱银子呢?”
“能捡回一条命,在那种情况下已经不错了。”
于是,君不畏把当时突发的情形说了一遍。沈娟娟听了君不畏的话,也吃一惊。
“他们八成是自己人内讧。”
君不畏道:“大概吧。”
沈娟娟渐渐高兴了。
只要君不畏来,她就会快乐。
“君先生,你怕是要在我这儿住些时日了。”
君不畏道:“我去找‘跨海镖局’的船。”
沈娟娟道:“不用找了,苗姑娘坚持,他们没靠岸,所以他们立刻折回小风城去了。”
君不畏一想,这大概是苗小玉不想被沈大公子纠缠,苗刚知道妹子的意思,这才未往上海靠岸,就回小风城了。
他也对沈娟娟淡淡地道:“走得真快。”
沈娟娟笑笑道:“君先生,你猜我这儿是干什么的?”
君不畏道:“白天不开门,夜来喧闹声,八成是赌馆。”
沈娟娟道:“算你猜中了,你不是喜欢赌几把吗?你来对地方了。”
君不畏拍拍口袋,记得口袋中还有在他离开的时候,苗小玉
塞给他的几两银子。
摸着口袋,君不畏哈哈一声干笑,道:“腰里缺银,不敢横行,我得压一压老毛病了。”
沈娟娟道:“我说过,在我这儿你尽管下场赌。”
君不畏道:“输了怎么办?”
“有我。”
“哈……”君不畏笑了。
便在这时候,姓林的领着一位戴金边眼镜的大夫匆忙地进来了,那大夫的药箱子由姓林的提着。
沈娟娟指指房中斜躺着的包震天,道:“快救这人!”
大夫走上前,仔细撕开包震天的衣衫,不由一瞪眼。
“真是要命的一刀!”说着,他再低头看,又道:“泡过水了。”
当然泡过水,包震天的衣裤还是湿的。
君不畏的衣裤也湿,沈娟娟已命人去买新衣了。
那大夫取出一应药物,很细心地为包震天疗治刀伤,又留下一些内服的药,总算把包震天又救活了。
沈娟娟派人专门侍侯包震天,只因为包震天是君不畏带来的人,为了君不畏,她得有所表现。
沈娟娟把君不畏招待在另外一间客厢中,有个女仆为君不畏送吃的用的,这光景就好像要把君不畏留下来似的,一切招待都是最好的。
果然,这天夜里,君不畏正与沈娟娟在后院亭内闲话,前面传来呼幺喝六声。君不畏闻得洗牌声,立刻搓搓双手,笑对沈娟娟道:“沈小姐,我到前面去瞧瞧了。”
沈娟娟皱眉头,她以为凭自己的美色,仍然留不住他,可知赌瘾多么厉害了。
她真的以为君不畏是个陷入泥淖的赌徒了。
沈娟娟站起身,大方地对君不畏道:“走,我陪你去前面看看。”
君不畏道:“去看我输银子?”
沈娟娟道:“你喜欢输银子?”
君不畏道:“不错。”
沈娟娟道:“输得少了心痛,输得多了要命。”
君不畏道:“我不一样。”
沈娟娟道:“你也是人。”
君不畏道:“我这个人与别人不一样,我喜欢看别人赢了钱的模样。”
沈娟娟道:“那是什么样,还不是高兴?”
君不畏道:“这你就不懂了,当有人赢了银子,便不由得会露出一副贪与馋的模样,那才是人的本性。你只要略加留意,那些赢了银子的人,还会把眼睛盯住别人手中的银子,恨不得伸手去抢过来,人啊,就是这副德性。”
沈娟娟道:“就为了欣赏人的本性?”
君不畏道:“人生各有乐趣,我就是喜欢这样。”
沈娟娟道:“那么,你便是有一座金山,也不够如此挥霍呀!”
君不畏一笑,道:“不是挥霍,是偏爱,沈小姐,如果你喜欢,会慢慢发觉个中滋味还真不错。”
沈娟娟道:“如果我只输不赢,只有痛苦。”她顿了一下,又笑笑道:“如你所言,我家这座赌馆,当把你列入最受欢迎的赌客了。”
君不畏哈哈笑了,他笑着拍拍口袋,道:“可惜呀,我的袋
中银子不多,便是输完了,也对我不痛不痒。”
沈娟娟道:“如果你抱着快乐输的主意,便永远是个穷光蛋。”
君不畏呵呵笑道:“你又错了,我若要银子,太简单了,而我很少似现在这样穷。”
沈娟娟半吃惊地道:“你还常富有呀!”
君不畏道:“怎么,你不信?”
沈娟娟道:“你怎么弄银子到手?”
君不畏道:“你休大惊小怪,我的银子来路正,比如我赚官府赏银。”
他冲着沈娟娟一耸肩,又道:“这一回我本是去捉拿田九旺的,不料这老海盗他……”
沈娟娟的面色似乎变了。
君不畏只装没发现,又道:“可惜只碰见个姓丁的,令我大失所望,便也未曾赚到半分银子。”
沈娟娟忽然冷冷一哂,道:“君先生,你不是在和我开玩笑吧,就你呀……”
君不畏道:“我怎么?”
沈娟娟道:“我爹也不敢说能杀田九旺,你……”
“那是你爹,不是我。”
“你知道田九旺的本事吗?你知道田九旺在大海上的实力吗?”
君不畏道:“田九旺仍然是个人。”
沈娟娟道:“田九旺单足在船上跺,大船也会被他跺个大窟窿,你八成害了妄想症。”
君不畏一笑,他指指前面,道:“咱们不提田九旺,到前面去赌几把。”
沈娟娟道:“我陪你。”她边走边问:“君先生喜欢赌牌九?”
君不畏道:“我好像对你说过。”
两人走过后廊,前面豁然一亮,院子四周的房子全是落地大窗。这儿赌的花样真不少,有单双,有骰子,洋赌也有好几样。左手边厢赌牌九,沈娟娟当先走进门,迎面便走来一个瘦汉,挽着长衫衣袖,笑道:“小姐,你……”
沈娟娟立刻在那瘦子耳边低声细语几句,只见那人点点头挤进人群中去了。
君不畏不在意地随着沈娟娟站在一张长桌边,只见他伸手猛一摸,嗨,摸到了个小荷包。
他忘了苗小玉塞给他的不是银子而是荷包。
君不畏手托那只锦绣荷包问沈娟娟:“这玩艺儿值多少银子?”
沈娟娟道:“你没银子?”
君不畏道:“我只有这个。”
沈娟娟接过手上看:“很细工,这里面是……”她打开荷包看,只见是一个鲜红的宝石鸡心,沈娟娟立刻怔怔地道:“谁送你的?苗小玉?”
君不畏也看到了,马上拿过来装入口袋里。他的心却一沉,女孩子把这东西送人不简单,苗小玉莫非……
只不过一念之间,君不畏笑了。
沈娟娟道:“那多扫兴。”
沈娟娟把手一招,又见瘦汉挤过来了。
“取五十两银子来。”
瘦子正要走,君不畏开口道:“要嘛,就借我一千两。”
沈娟娟愣然道:“一千两?”
君不畏道:“赌就赌个过瘾。”
一顿,沈娟娟便对瘦子点点头。
于是一千两银子筹码,用个红木盘子送到君不畏面前来了,最大的筹码为百两一个的,小的只有一两。
“足够你赌一夜了。”
沈娟娟浅浅一笑。
君不畏摇摇头,道:“那多累人呀。”说着,他双手一推盘子,一古脑推在末门前,看得大伙直瞪眼。
沈娟娟也瞪眼了。
君不畏愉快地抖抖双手,道:“这把牌我来看。”
他当然有资格看牌,因为桌上最大的银子也不过十两重的两三个,即便四周全部加上,也不过百两多些,他老兄一把上千,庄家的脸皮立刻绷得紧了。
“你全部下?”庄家问的是君不畏,眼睛看看沈娟娟。
君不畏道:“不可以?”
沈娟娟只不过叹了一口气,庄家的脸色好看多了。
只见庄家对君不畏笑,立刻掷出骰子,出现的点子是四,君不畏伸手便把牌取上手。
庄家抓了第二把牌。这时候总有十七八个人围在桌边观看,大家都看着君不畏手上的牌了。
庄家先翻牌,啊,竟然翻出猴王一对来了,这就不用再看了,庄家来了个通吃。
立刻,四周哄然一声,君不畏笑笑把牌扣按在桌子上,转头对沈娟娟道:“我欠你一千两银子。”
他正要走,庄家开口了:“小姐!”
沈娟娟吃惊地回过身:“干什么?”
庄家指着桌面上的牌道:“小姐,这牌……”
沈娟娟低头看,只见君不畏的两张牌已嵌入桌面,与桌面平齐,一时间不容易取出来。
沈娟娟把柳眉皱紧,指着桌面道:“君先生,这……”
君不畏道:“输了银子的人不都会发发火吗?”
沈娟娟道:“君先生,你忘了你说过的话了。”
君不畏道:“没忘记,我喜欢输。”
“可是你却发火了。”
“虽然发火,心里还是满高兴的。”他指着桌面,又道:“换一张桌子吧,沈小姐。”
沈娟娟突然一掌拍在桌面上,两张牌立刻跳起来,她只低头一瞧,立刻命人换桌子。
那瘦子指挥几个汉子,匆忙地换桌子,沈娟娟与君不畏并肩往后院里走。
“你真有一套。”沈娟娟斜睨君不畏。
君不畏道:“我欠你一千两银子。”
沈娟娟道:“真会说笑,我应该感激你的。”
君不畏笑笑,道:“你要感谢我?”
沈娟娟道:“你没有当面戳穿我的人弄诈,否则……”
君不畏道:“原来你看到了。”
沈娟娟道:“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一副天九牌,不会有两个丁三出现的。”
原来庄家亮出一对猴王,一般人生气得连牌也不再看了,然而君不畏虽未看牌,他却暗里摸牌底,他摸出其中一张是丁三,当然会生气,但却因沈娟娟的关系,便暗中运力,把牌嵌入桌面中,印了个丁三出来了。
沈娟娟一看便明白,立刻命人换桌子。当然,她也不会再同君不畏索还千两银子了。
君不畏露了一手绝活,沈娟娟惊于君不畏的武功,立刻又对
君不畏另有评价,也许他真有杀田九旺的能耐,有道是“不是猛龙不过江”,姓君的不简单。
沈娟娟吩咐摆酒,酒席设在她的房间里。
沈娟娟的房间是诱人的,锦罗帐子象牙床,一应家具都镶白玉,这光景正是那时候最豪华的。
所谓酒席,却是精致的小菜七八样,美酒只有一壶,只不过酒却是洋酒,君不畏头一回喝这样的酒。
柔柔的灯光,轻轻的细语,偶尔一声浅笑,君不畏仿佛身处温柔之乡似的。
其实这与温柔乡差不多醉人,几杯酒下肚,君不畏的眸子里充满淡淡的红色。
只是淡淡的红,便已瞧进沈娟娟的眼里了。
沈娟娟吃吃笑着再举杯,却被君不畏把手握住了。
“沈小姐,我快醉了。”
沈娟娟笑笑,道:“你醉了?”
“我醉了会有不礼貌举动的。”
“会吗?”她试着把手抽回来,但君不畏握得紧。
“你以为我不会?”
“我以为君先生是君子。”
“君子也是人,酒色财气免不了呀。”
沈娟娟道:“如果我不答应,只怕……”说着,她暗中运力挣脱,只可惜仍然脱不出君不畏的手掌,本能地另一手并指疾点对方脉门,指风凌厉带着咝咝声。
君不畏淡淡一笑,左掌轻拂,巧妙地拨在沈娟娟手背上,看上去就好像摸了对方一下。
沈娟娟双目一亮,斜过身子横肘疾撞,撞向君不畏的胸膛,这一招如被撞中,君不畏就惨了。
沈娟娟也认为君不畏非闪不可。
君不畏坐得更稳当,只见他拨出的手回收中途,只在沈娟娟的肩上又推一把,果然沈娟娟又撞个空。君不畏便在这时另一手握着沈娟娟的手用力一带,“噗”,沈娟娟已倒在君不畏的怀中了。
君不畏双目精光一现,道:“沈小姐,你这几招算得上乘功夫,一般人难以抵挡。”
沈娟娟直直地瞪视着君不畏,道:“可惜仍然逃不出你的手掌。”
君不畏道:“那是因为我非泛泛之辈。”
沈娟娟道:“你这样抱住我意欲何为?”
君不畏道:“你以为我会对你怎样?”
沈娟娟反而不开口了。
她微微地闭上眼睛,甚至还把巧嘴微微翘着,好大方的架式,准备迎接另一种挑战了。
君不畏低头看着,伸手轻轻地抚摩着沈娟娟的微红面颊与秀发,也把握住沈娟娟手松开了。
这时候自然地不必再握住对方,他把手托住对方的背,似乎听到沈娟娟的呼吸声了。
“沈小姐!”
“叫我娟娟。”
“娟娟,好听的名字,好美的姑娘。”
“你开始甜言蜜语了。”
“我从不轻易夸赞女人。”
“苗小玉呢?”
“一位冷傲的女子。”
“我发觉她对你也不错呀。”
君不畏道:“那种不错是不一样的。”
沈娟娟道:“怎么说?”
君不畏道:“那是因为我救过她。”
沈娟娟道:“他们在海上遇到丁一山,你从丁一山手上救了她,这事好像苗刚提过,但我却发现,苗小玉对你的表情是爱。”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是女人……”
※※ ※※ ※※
如果此刻有人来打扰,沈娟娟定把此人当仇人。
嗨,还真有人来打扰,前面客厢中就有人在呼叫。
这声音很大,使君不畏也醒了。
“包老爷子在叫……”君不畏一挺便坐起来了。
沈娟娟心中发火,为什么包震天会在此刻一声吼?
她见君不畏起身,当然无法再睡。
沈娟娟发现君不畏一心只想快穿衣衫,对她似乎不加理会似的,令她多少有些不快。
君不畏穿好衣衫,这才笑对沈娟娟道:“一夜风流,此生难忘,咱们彼此要珍惜呀。”
沈娟娟道:“不畏,我会的,你可别口是心非。”她贴近君不畏,又道:“我不会放过你的。”
君不畏道:“你不怕我把你的家产赌光?”
沈娟娟道:“我怕吗?”
君不畏愣了一下,旋即“哈哈”一笑,两人便往客厢那面走去。
包震天的声音又吼起来了:“人呢!”
君不畏推门而入,急急走近床前,道:“包老爷子,你醒了。”
包震天见君不畏与沈娟娟两人前来,脸上一片愉快,忙伸手拉过君不畏,道:“快备车。”
君不畏道:“备车?干什么?”
包震天道:“马上赶回小风城。”
君不畏道:“可是你的伤……”
包震天自己披衣裳,急忙道:“伤不要紧,快备车。”
沈娟娟道:“包老爷子,大夫说过,你至少要三天时间才可以下床。”
包震天道:“来不及了,沈小姐,麻烦备车吧。”
沈娟娟看看君不畏,发现君不畏冲着她点头,便不由得对包震天道:“老爷子,何不多休养一日再走?”
包震天道:“我的时间就是命,沈小姐,命比银子值钱多了,我得尽快地回小风城。”
包震天已咬牙苦撑着要往外走了,沈娟娟无可奈何地摇摇头,道:“你们等着,我去命人备车。”
她转身便往前院去叫人备马车了,内心中却正自大骂包老头不是东西。
君不畏扶着包震天往前走,他经治疗,再休息一夜似乎又好多了,背上一刀未中要害,只不过流了不少血。
“君老弟,我请你护我回小风城。”
“我也正要回小风城。”
“这一劫我算逃过了,多亏得你老弟援手。”
“我能不援手吗?”
两人绕到前院,前院不见有人,赌了一夜早就有喜有忧地回家睡大觉了。
什么叫有喜有忧?
赢了当然喜,输了自然忧,只有一个人输了还喜,那就是君不畏。
君不畏这一夜风流够快活,那当然是因为他的能耐高。
他现在就微微笑,如果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任谁也就明白他为什么如此快乐了。
大门外走进来沈娟娟,她走到君不畏面前来。
“车去雇了,我还派个人中途侍候包老爷子。”
包震天却摇摇手,道:“谢了,我有君老弟相陪已经够了。”
沈娟娟伸手拉住君不畏,道:“你要走?”
君不畏道:“我已答应包老爷子了。”
沈娟娟眨动美眸,道:“那我们……”
君不畏道:“有缘总会再见面的呀!”
沈娟娟道:“看你说得真轻松嘛!如果等你不来,我会找你的。”
包震天却急得在嘟哝:“为什么大车还不来?”
大车便在这时驶来了,双绺拉车有篷顶,旧垫子车上铺了三张,人躺上面够舒服的。
包震天真怕君不畏变卦改变主意,拉住君不畏便往车上登,也回头对沈娟娟道:“容后图报!”
简单四个字,沈娟娟心中真不是味道,不过她仍然对君不畏道:“你要回来哟!”
君不畏重重地点点头,道:“会的,你保重。”
还真像情人分离,有一股难割舍的样子。
其实,君不畏心中明白,沈娟娟不是头一回,这对他在心理上就少了一份负担。他坦然地登上车,赶车的长鞭一挥,两匹马拖着篷车便朝南驶去。
包震天强忍着背痛,连声催促,快!快!快!
赶大车的长鞭抽得叭叭响,累苦了拖大车的两匹马,头一天赶路一百三十里,第二天差不多也是这个数。
君不畏这时候才问包震天:“包老爷子,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如此急着赶回小风城?”
包震天道:“十万大军等饷银,君兄弟,你说我急不急?”
君不畏道:“为什么不设法追回失银?”
包震天道:“如何追?于文成早就不知去向了。”
君不畏道:“这位黑心的于文成,他是干什么的?”
包震天咬牙道:“姓于的可恶,我想八成他造反了。”
君不畏道:“他造谁的反?”
包震天一把扣住君不畏,道:“君兄弟,你以为我是何许人呀?”
君不畏怔了一下,笑笑道:“老爷子,你不说我怎么会知道?”
包震天道:“于文成本与包某在北王帐前共事,不料于文成他……”
君不畏强自镇定地道:“北王韦昌辉韦大将军?”
包震天道:“不错。我原打算把你推荐给韦大将军麾下的,真不巧,于文成叛变了。”
君不畏道:“再回小风城,十万两银子非小数目。”
包震天道:“我相信‘八手遮天’有办法。”
君不畏道:“就是那位神秘的石不全?”
包震天道:“不错,石不全如果不是身残,他应该是追随在北王身边的红人物了。”他放开手,拍拍君不畏,又道:“你年轻,武功高,我必然在北王面前保举你。”
君不畏笑笑,道:“我不是料,赌牌九我才会觉得愉快,而且……”
包震天道:“赌能丧志,改了吧。”
君不畏道:“谈何容易,我如今到处找财源,为的就是赌几把。”
包震天道:“我想你跟着我,赌瘾犯了我供你银子。”
君不畏哈哈笑了。
他心中可在想:北王、东王、翼王,大家各自心里在弄鬼,如果想把各人的心亮出来,实在不容易,最后总免不了一场火并了。
君不畏也有些无奈,权势与金钱,总是驾御在刀兵之上而永无平静之时,他现在不正是跳在这一场斗争的大漩涡中吗?
包震天当然不会知道君不畏的真实身份,总以为君不畏是一个难逃骰子控制的赌徒。
别以为重伤的包震天坐在狂奔的大车上有问题,车快到小风城的前一天,他已经可以舒展筋骨打哈哈了。
只不过他还不知道,小风城的“跨海镖局”就快要出事了。
只差一天,是的,“跨海镖局”快出事了……
然而他们也马上出事了。
他们坐在马车上会出什么事?
呶,就快发生怪事了。
一片林子里传出曼妙的小鼓与小锣声,路便在林子的正中央往左转,事情就出在这个转角处。
蹄声宛似擂鼓,包震天催着大车要赶快,赶大车的长鞭抽,两匹健马发疯奔跑。
突然,前面传来了马蹄声,也传来了锣鼓声。
两下里猛古丁遭遇上,谁也无法闪避,就那么“轰”地一声,撞成一堆了。
只见马匹交互压,两辆大车也翻在路上。
来车上一阵莺燕尖叫声,那五个女人摔得真不轻,那跟在车后的还有一辆更豪华的大车,却及时地收缰刹住了。
包震天倒霉,他在车里叫惨了,直“哎呀”!
君不畏耸耸双肩,他去扶住包震天。
“老爷子,这是车祸。”
包震天道:“老弟呀,屋漏偏逢连夜雨呀!”
便在这时候,忽听得女子声音叱道:“把那个不长眼睛的赶大车的杀了!”
“跄!”这是拔刀声。
连着又是几声拔刀声,显然对方要杀人了。
君不畏在车内刚坐直身子,他一手还扶着包震天,闻得拔刀声,便把头伸出去看。
他看见对面一共两辆篷车,前面一辆歪道边,拉车的马跌在路上起不来。
再看后面大车,哇!真豪华,上面赶车的女子也长得白,那篷车的布幔是缎子的,上面绣着大红花,四角金穗垂一尺,上面还挂着响铃当,就不知车内坐的什么人物了。
君不畏见三个女子持刀直奔来,他不再犹豫了。
就在赶大车的一声叫:“要杀人了!”君不畏已跃在三个女子的正面,伸手拦住。
“怎么杀人呀?”
三个女的怒视君不畏,其中一人道:“滚开!找死不是?”
那女子说完当头一刀劈,君不畏错身甩肩,左手已抓住女子右腕往后一送,正好把另一女子的刀砸飞。
三个女子吃一惊,前面篷车中已爬出个白净女子。
这女子只一看到君不畏,她全身的骨头又轻三斤,戟指君不畏,道:“别打了,都是自己人呀!”
君不畏除了他的小百合花儿之外,想不出还会有谁是他的自己人。
他侧过头去看,这一看便也明白了。
原来这些人全是胭脂帮的人,那么……
他心念间,便多看那豪华大车一眼,而叫声中只见一个披着绣金边白披风的女子,俏生生地站在君不畏面前。
这女子先是一嘟俏嘴,道:“没良心的,你还认得我白荷花吗?”
君不畏一笑,道:“这一辈子也忘不了。”
“那夜你为何点我睡穴,不告而别?”
是的,那女子正是十万大山的蝴蝶谷野店的白荷花。只见她上前抓住君不畏,道:“走,去见我们帮主!”
君不畏一怔,道:“你们帮主御驾亲征呀!”
白荷花道:“全是为了你才出山的。”
“为我?”
“是呀!”
“我怎么?”
“你太妙也,来!”
白荷花似是遇到了亲哥哥似的,拉着这位浪子君不畏走到那辆豪华大车前。
便在他刚刚站定的时候,只见一个女子伸手撩起车帘,哟!那车上真豪华,银器金穗照人面,车中央的厚毯上坐着一位妙龄女人。
这女人真美,那双妙目闪着光,两道眉毛柳叶一样尖,只是太过浓了。
有人说女人眉浓必淫,这个女人一定淫荡,要不然她也不会为了追踪君不畏,而跋涉千里率众追来了。
车上的人正是胭脂帮帮主紫牡丹。
只见这紫牡丹的一身紫衣绣金花,她上下看了君不畏一遍,缓缓地点点头。
“你姓君?”
“我叫君子!”
“哈……姓君的人不一定是君子。”
“我是君子!”
“你狗屁,君子还会捉弄我三名手下呀!”
君不畏一笑,道:“那也是出于无奈呀!”
正在这时候,包震天已高声呼叫了。
“兄弟,回来,咱们把车弄正,上路了。”
紫牡丹看看受伤的包震天,道:“他是你什么人?”
“路人!”
冷冷一哂,她对白荷花道:“去,叫那老小子安静下来,别穷叫!”
包震天果然大声叫:“君兄弟,快回来呀!”
白荷花俏生生地对包震天道:“老爷子,君相公遇上自己人了,当然要说几句话的,你忍耐了。”
说着,她猛抖手中的手帕。
她也把手帕往赶车汉子面上舞。
于是,传来“咚咚”声,包震天与赶大车的相继倒在地上了。
君不畏回头看,不由怒道:“你们干什么?”
车上的胭脂帮帮主紫牡丹道:“别担心,我只是叫他两人安静。”
君不畏心中有主意了。
他笑着道:“帮主南来为了我,我十分感动,只不过我还有
要事,等我办完事,你给我地址我找你。”
紫牡丹吃吃一笑,道:“总得先试一试,你是否如她三人所言呀!”
君不畏道:“如何试?”
“上车呀!”
君不畏道:“就在这儿?”
忽听得十几个女人全笑了。
君不畏看看每个女子,她们长得各有千秋,白荷花已俏生生地贴着他,道:“你跑不掉的!”
君不畏心想:“不是顾及包老爷子,你们谁也别想拦住我。”
他立刻变得坦然地道:“好,我答应,只不过咱们把大车往林子里面躲起来……”
紫牡丹一听乐透了。
“车赶进林子里!”
两个女的走过来,一人拉着两匹马,另一人坐上车辕去赶车,大车立刻钻进林密处。
大车就在几丈外停下来,紫牡丹对两个女的道:“两位使者,去帮着把两辆大车扶正,不听吩咐不许来。”
两个使者掩口笑着走了。
两人去得很轻巧,两人也回头看,只见君不畏已登上大车,车帘已扣起来。
君不畏坐在紫牡丹对面,淡淡笑了。
紫牡丹也笑,她缓缓地伸手去摸君不畏的面颊,好一股香味令君不畏心神荡漾。
君不畏仍然不动,他看紫牡丹要对他如何下手。
紫牡丹自一边取出个小瓶子,她倒出两粒药丸,道:“快服下去!”
君不畏摇摇头,道:“用不着!”
紫牡丹吃地一笑,道:“你会后悔的。”
君不畏道:“就叫我后悔一次吧!”
紫牡丹道:“别拿我同她们比,我不同,是异于人的。”
“是吗?”
“她们是羊,我却是猛狮。”
“那就有意思了!”
紫牡丹道:“你不服下这壮阳补阴丸,我服,因为我要对你加以考验。”
她果然张口把两粒红丸吞下肚。
君不畏心中想:“你总咬不了我吧?”
紫牡丹稍作闭目,顿时满面红霞,呼吸也加快了。
她不去脱自己的衣衫,却双手去抓君不畏。
君不畏真怕被这紫牡丹把他唯一的一套衣服扯破,但他更明白,这女人有强暴狂。
君不畏疾伸手,握住紫牡丹的手腕,他笑笑道:“我自己来……”
紫牡丹吃吃一笑,双手抽回来……
君不畏倏然起身,往车下面跳去了。
“轰……”
君不畏已往大道上奔去,只不过他刚走五六丈,身后面传来一声吼叱。
“围住他,别叫他逃了!”
这声音听得君不畏吃了一惊,猛回头,只见大篷车上面的人影一闪,紫牡丹扑过来了。
君不畏立刻明白一件事情,那就是胭脂帮帮主果然有一套。
其实,紫牡丹正在魂游巫山太虚的时候,身边的白荷花一声
尖叫,她才醒来的。
紫牡丹一旦醒过来,立刻伸手去抓身边的人。
当她抓不到君不畏时,便大吃一惊伸头看,正看见君不畏要逃走。
七个女的提刀围上来了。
紧接着,紫牡丹双手提着一条白色缎带也赶到了。
君不畏不动了,他对着紫牡丹一笑:“帮主,你醒了?”
“废话,你打算走?”
“在下有要事待办呢。”
“别爱管闲事了,随本帮主去吧。”
君不畏摇摇头,道:“不行,非走不可!”
紫牡丹指着七个握刀女子,道:“你走不了啦,还是跟我回去快乐吧。”
君不畏道:“没兴趣。”
紫牡丹一声怒叱:“你敢情找死了!”
君不畏道:“你强人所难呀!”
紫牡丹一声叫:“杀人!”
七个女子举刀便往君不畏扑去。
君不畏暴喝如虎,旋动身子拔空三丈高下,他的手脚便在空中施展开来,只听得“砰砰”之声连续起处,七个女子已纷纷甩手往外闪不迭,七把刀便也往草丛中落去。
君不畏刚站定,忽然头上紫影闪晃,一条白缎带宛似一溜白云把紫牡丹拱托到他的头上。
君不畏立刻想到,这女人要对他用毒了。
他以为紫牡丹那条缎带上就有毒。
想归想,动还是要快动,君不畏憋住一口气,突然冲上天,一头钻进那片白云里,口也微张开。
只见一道电芒一闪而逝,带起一声尖叫:“哎……”
“咚!”紫牡丹叫了一声落下地,她的脖子上见血了。
她一片吃惊之色,道:“你……就是江湖上传言的‘地龙’呀!”
君不畏仰天一声大笑。
这种气势,已经表示他承认了。
紫牡丹大吃一惊,她厉叫:“快……咱们撤……”
真快,她的人齐动手,驾着两辆篷车,刹那间消失在暗夜中了。
君不畏不怠慢,匆匆地把赶大车的与包震天两人救活过来。
包震天立刻拉紧君不畏,道:“怎么一回事?”
君不畏怎能说呢?他只笑笑道:“咱们快赶回小风城吧!”
包震天道:“对,快赶路了!”
车子动了,君不畏却睡着了。
他太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