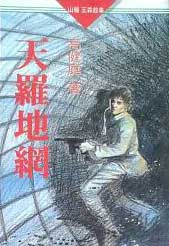三月中旬,在江南已是绿满天涯、群莺乱飞的深春时节。可在京畿的永定河畔,树叶柳丝还是一片嫩绿,垅里的麦苗也才刚刚拔节,尽管天空的太阳照得暖融融的,拂面而来的春风里,却还带着微微的寒意。
太阳已经偏西,永定河边通向西去的古道上,蹄声哒哒,有一骑从东缓缓驰来。那马矫健异常,全身一片乌黑。马背上坐着一个后生,头上绿绸束发,背后背一顶青纱遮阳笠帽,身穿淡蓝色短衣,鹿皮腕套扎袖,酱色丝带紧腰。那后生生得细眉入鬓,眼朗如星,秀俊中隐隐露出一种使人难近难犯的英气,悠然里微微含带着几分机警戒备的神情。鞍后两旁配挂着两个鼓鼓囊襄的褡裢,鞍旁悬挂着一柄长长的宝剑。
这后生不是别人,正是在妙峰山投崖未死,乘机出走的玉娇龙。
玉娇龙投崖前,确也经过一番精心缜密的安排筹划,虽然意图侥幸,却也抱了个宁死的决心。当她在半崖中竟然抓住了树枝,并顺着藤蔓平安地下到崖脚以后,就在那一瞬间,她真是有如绝处逢主,悲喜交集,不禁合掌仰祷,感谢上苍。
十日来,她将从破庙里偷偷牵来的大黑马寄养在永定门外一家马栈里。一直混迹在京城中办理她在投崖前无法办理的事情。
白天,她一反江湖上那些秘传戒忌,或跻身于上等的歌馆书坊,或踽踽于闹市茶楼;夜晚则或潜回玉府,仍宿在旧日居住的楼上,或隐入舅父黄大人府里,寄住在他花园书房,她知道自己从此已经不能再获得父亲的荫庇,一切只有全靠自己去闯。因此,她渴望能有一件像罗小虎那柄宝刀一般可恃以横行天下的利器。她便于初七深夜潜入王府,偷来了王爷那柄她久已羡慕的宝剑。玉娇龙把一切事情均已准备妥当,决心次晨离京,当十四晚上她最后去拜辞父亲时,她久久偷立窗外,听到了父亲对她那番祝告,她完全理解父亲那祝告中的一切暗示,对玉府那荣极一时而又岌岌可危、众口争夺而又危机暗伏的处境,她哪能不悚然心动,哪能不惕惕于怀。为了不使父亲为难,她本已决心立即将剑送还王府,但正当她要抽身离去时,忽又听到父亲说出了李慕白来,说王爷为了寻剑,已派人去九华山聘请李慕白去了,并说“此人难犯”,要她“务宜回避”。这却有如针一般地刺着了她的旧痛,重又挑开了她那屈辱的伤疤。玉娇龙一咬唇,猛然间,将一切顾忌全抛脑后。心里只闪起一个念头:“我正想找他李慕白去哩!”随即愤然离去。
这时玉娇龙正策马驰向王庄。她现在在马上的心情,是既感到自由自在,又感到陷阱重重。她有如逸脱铁笼的囚兽,又似离群的孤鸿,一路行来,瞻前顾后,警戒着任何一点凤吹草动。当她看到周围都无人迹的时候,她那暂时缓驰下来的心境,却又激起一阵述醉的颤动。计程越近王庄,心头的蜜意也越酿越浓,甚至另有一种莫名的情怯,又紧紧扣住她的心头。
玉娇龙策马行着行着,道旁出现了一片广阔而平坦的草地。
远远一丛树林中,露出一排绿瓦红墙,她的心不禁怦然一动,暗自惊呼了声:“啊,王庄到了。”
幽燕的春风里,总是带有凉意和夹着尘沙。玉娇龙经过一天的奔驰,已经是风尘仆仆,脸上亦蒙上一层薄薄的轻沙。她可以这样在四处驰奔,但却不能这样去进入王庄。
再说,赶了一天路,也该饮马了。她立马沿河畔张望,准备选个好的所在,坐下来洗一洗脸,让马也饮个畅快。突然,她看到上游不远处,有两个营卒模样的人正坐在河边掬水解渴,靠近道旁的一徘杨柳树上拴着几匹雄健的骏马。玉娇龙留心察看片刻,料定那两人必是王庄的营兵马卒,她正好借此探询一下罗小虎的情况,于是便翻下鞍来,牵着马缓缓地走上前去。这时,那两人正在打趣,没注意玉娇龙已经来到他二人身后。玉娇龙开口刚说出“劳驾”二字,那两人猛然回过头来,就在一瞬间,三个人都全愣住了。
玉娇龙立即认出了这二人原来是乌都奈和艾弥尔。他两人只觉站在背后这人有些眼熟,却想不起曾在哪里见过面来。两人四只眼睛,滴溜溜地望着玉娇龙转了一会,又把眼光移向她牵着的那匹大黑马身上去。突然,他二人一下站起身来,迅即向旁退开两步,惊疑而又警觉地打量着玉娇龙。玉娇龙毫不在意,只略带笑意地瞅着他二人,不再吭声了。
艾弥尔又看了看大黑马,问道:“请问客官从哪里来?又到何处去?”
玉娇龙并不回他问话,却反问道:“这儿可是铁贝勒玉爷的王庄?”
艾弥尔:“正是。客官问王庄何事?”
玉娇龙仍不回话,只说道:“是铁贝勒王爷的王庄就好了。”
说完,将手里缰绳一松,大黑马就径直走到河边,悠游地饮水去了。玉娇龙也跟着走到一块半浸在河里的石头上,从容掬水洗起脸来。
艾弥尔、乌都奈站在一旁注视着玉娇龙,两人不时还互相眨递着眼睛。艾弥尔示意乌都奈要他注意着玉娇龙,他便走到那大黑马身旁,轻轻吹了,一声口哨,伸手去抚拍着那马的项脖。那大黑马停住饮水,回过头来不断地用它的鼻梁碰擦着艾弥尔的肩膀,显得十分亲昵。艾弥尔和大黑马亲热一阵,他顺手拾起缰绳,牵着马来到玉娇龙身边,说道:“这马真骏!不知客官是从哪里买得?”
玉娇龙已经洗过了脸,站起身来漫不经心地说道:“从一个朋友那里暂借来的。”
乌都奈在旁给艾弥尔投来一道警惕的眼神,随即把眼光落到鞍旁那柄长剑和鞍后那两副鼓鼓囊囊的褡裢上。
玉娇龙走到艾弥尔面前,突然问道:“请问,王庄里可有个驯马手?”
艾弥尔迟疑来答。一直在旁冷然不语的乌都奈却接过话去,问道:“客宫问他何事?”
玉娇龙:“我听说他是条好汉,想见一见他。”
乌都奈,“客官和他有亲?”
玉娇龙似笑非笑地摇摇头。
乌都奈:“有旧?”
玉娇龙还是摇摇头。
乌都奈狡黠地笑了笑,用手指着站在她身旁的艾弥尔说道:“不识远在天边,相识近在眼前,他就是咱王庄里的驯马手。”
玉娇龙回头瞟了眼艾弥尔,她忍俊不禁宜想笑,可仍强忍住没笑出来。又问道:“请问王庄里有几位驯马手?”
艾弥尔已经会意,忙接过话来答道:“就我一个,怎么样?”
玉娇龙转过身来,似奉承又似认真地说道:“听说你骑木高超,深受王爷赏识,特来向你请教如何选马的见识。”
艾弥尔:“不敢!我哪有什么高超骑术和选马见识,感王爷恩典,不过在王庄混碗饭吃罢了。”
玉娇龙也不和他客套,岔开话题问道:“庄宅管事拉达可在庄里?”
艾弥尔:“他奉王爷召唤:已于前日动身到王府去了。”
玉娇龙瞅着艾弥尔看了看:“啊,有这等巧事!我既远道而来,就请让我进庄住宿一宵,我还有些事要问问你呢。”说完就从艾弥尔手里接过缓绳,牵马欲行。
乌都奈冷冷地说道:“王庄从不留宿外人,客官还请自便。”
玉娇龙回眸瞅着乌都奈:“你俩不也是外人?!我时在王府进出,怎从未见过你二位来?!”
乌都奈不禁一怔,回头望望艾弥尔,脸色也有些变了。
玉娇龙只微微地笑了笑,也不理他,牵着马径直走上河岸,缓缓向王庄行去。
乌都奈和艾弥尔赶忙交换了眼色,解下拴在抑树上的那几匹骏马,也跟着赶了上去。
在快走近王庄大门时,艾弥尔赶到玉娇龙身旁,为难地对她说道:“王庄的确不准外人进出,拉达老爷回来会怪罪我俩,客官有话就请在这里谈谈。”
玉娇龙:“拉达果真不在?”
文弥尔:“确是不在。”
玉娇龙眼里闪起一丝亮光,唇边顿露出一道浅浅的笑容:“不在更好。他如回来怪罪你俩,自有我去承担。”又牵马向庄门走去。
乌都奈忙将马往树上一拴,赶上前来,对艾弥尔说道,“既然这位客官和王府也有来往,我看不妨事的。”又回头对玉娇龙略带央求地说道,“大门进去多有不便,就请走那边后门好了。那儿离我兄弟住房又近,出入也方便些。”
玉娇龙点点头:“也好。就劳二位带路。”
于是,艾弥尔在前,乌都奈随后,转身向东,沿着墙外林中小道向前走会。
一路上,玉娇龙只默默地走着。艾弥尔虽不时回过头来问她几句,她也只是或点点头,或淡淡一笑应付了事。乌都奈在后,不时吹起口哨,都是一些西疆的歌调,玉娇龙听了特别感到亲切,但她却并不回过头来望他一望。
王庄真大,沿墙足足走了约一里来地,才又绕向北去。转过弯去,只见那边树林更加茂密,小道也显得愈更荒静。走着走着,乌都奈突然吹起一声尖厉的口哨,随着哨声,他猛地跳到玉娇龙身后,使出全身力气,一把将她紧紧抱住。说时迟,那时快,艾弥尔亦同时迅即转过身来,从怀中拔出一柄锋利匕首,直向玉娇龙胸口刺去。就在这快似闪电迅雷、势如千钧一发之际,玉娇龙却不慌不忙,只将两臂一分,随即侧身一抖,便将乌都奈甩出一丈开外,同时伸出左手,握住艾弥尔持刀的右腕,只轻轻一扣,他手中匕首便即落到地上去了。乌都奈突又猛扑过来,正俯身去拾那地上匕首,玉娇龙早已一脚将匕首踏着,乌都奈急了,腾跃起身,一拳向她迎面击来,玉娇龙一伸右手,轻轻将他拳头接住,乌都奈想收回拳头,却任他如何用力,那拳头竟似被钳住一般,挣脱不得。
从他二人开始动手,只不过几眨眼工夫,一个右腕被扣住,一个右拳被抓着。艾弥尔和乌都奈都拼命挣扎着,玉娇龙只是站稳不动,脸上也毫无怒容,只是略带好玩地看着他二人。艾弥尔满面涨得通红,乌都奈铁青了脸,两双眼睛怒视着玉娇龙。
乌都奈边喘着气,边恨恨地问道:“你是谁?究竟来干什么?”
玉娇龙笑了笑:“来找你们的驯马手。”同时将两手一松。
不料他二人刚一脱手,又立即同时猛扑上来。玉娇龙迅即闪身往后一退,低声喝道,“住手!”就趁他二人突然停住的那一瞬,玉娇龙紧瞅着他二人,又低声喝道,“艾弥尔、乌都奈!怎么,不认识我啦?!”
艾弥尔、乌都奈像被烙着一般,猛然连退几步,瞪圆了眼瞠直视着玉娇龙。玉娇龙睬视着他二人,不禁嫣然地笑了。
艾弥尔就在她这嫣然一笑中,突然将她认出来了。他赶忙抢前两步:“你是玉小……”
玉娇龙迅即用话将他截住:“我姓春,名龙。”
艾弥尔也立即警醒过来:“啊,是春个……春大官人。你来得正好,我们那位虎哥正……正烦恼着,你来……来劝劝他就好了。”
乌都奈仍站在原地,惊诧地打量了她一一会后,仍不冷不热地问道:“不都说你在妙峰山跳崖死了吗?”
玉娇龙有些不快地说道:“那投崖的是玉小姐,死的也是玉娇龙,与我何干!”
乌都奈揉揉他那还在发痛的手,不再吭声了。
艾弥尔忙接过话去:“死了的就休再去提了,我们那位虎哥见了你定会把冷脸变成热脸的。走,快到庄里再说。”
玉娇龙又跟着艾弥尔向前走了一段路,才来到一道小门前。
门是紧闭着的,艾弥尔边捶着门,边大声地呼喊了几声,才听到里面远处有人应声。
趁着等开门之机,玉娇龙低声问道:“有个名叫梁巢父的梁大爷是否来过?”
艾弥尔:“来过。梁大爷已同哈里木哥哥和香姑一道到西疆去了。”
说着,一个马夫模样的庄丁把门打开了。他见到玉娇龙那身打扮和她牵着的那匹大黑马,显出一些惊诧的神色。艾弥尔对男庄丁说道:“这位官人是来请咱驯马大哥给相相这匹马的。”那庄丁把大黑马打量一番,面露惊羡之色,说道:“好一匹骏马!简直可以和王爷身边那赤龙驹和白龙驹比美了。”
艾弥尔把玉娇龙让进门后,趁庄丁关门时,又问道:“驯马大哥可在舍里?”
庄丁:“到马场驯马去了,还未回来。”
玉娇龙跟随艾弥尔经过一徘整齐的马厩,又穿过一片柏林,来到一个小院门前,艾弥尔指着院内左边那间房说:“咱大哥住在院内那间房里。”
玉娇龙站在门前向院内院外一看,只见一道矮矮的土墙围着那个小院,院坝里摆了一张桌子,桌上放着一把茶壶和一个酒罐。正对石级上是一排三间房舍,正中是堂屋。
院坝左侧还有两间敝房,一间房里堆放一些柴火,一间房里备有锅灶。墙外种着一些不高的龙柏。四周是一片杂草丛生的旷地。小院在这旷地里虽显得孤零零的,但住在这里却有如置身世外一般,倒也十分安静。玉娇龙心想:“这确也是个安全所在,不过,他怎能禁得这般闲寂!”她站在门口,把周围环顾一番之后,又望着罗小虎住的那间西屋,一瞬间心里不禁感到一阵微微的颤动和羞涩,眼前又浮现了草原上那小小的帐篷,那充满了焦悔和柔情的一夜。在这漫长的两年多来,自己朝思暮想,梦绕魂牵的,都是那草原上的相依,都是那林中分手的誓言;在这漫长的两年多来,自己含苦茹辛,历尽艰险,以至宁可九死一生来换取的,正是这割不断的一缕柔情,正是这曾使自己那么醉心的蜜意。而这一天终于来了,就在这间小屋里,自己将以身相许,成为他的妻子,并将终身跟随着他,回到那一望无垠的草原,回到那恬静温暖的帐篷,把自己这颗一直担惊受怕着的心,揣进他的怀里,去享受他那有力的抚爱,自己也将竭尽一个妻子应有的温柔,去酬谢他的情义,让他那苦难的一生,得以度到和美幸福的时光。
玉娇龙想得呆呆入神,她脸上也不知何时泛起了朵朵红晕。
艾弥尔站在一旁不时向乌都奈挤眉弄眼,乌都奈却不加理睬,仍在抚揉着他那还在发痛的手。那马不知为了什么,却突然不安静起来,不住刨蹄的同时,还昂起头来发出一声长长的嘶鸣。玉娇龙这才回过神来,将缰绳递给艾弥尔,由他牵到堆放柴火的那间敝房里去了。
玉娇龙移步登上石阶,进到罗小虎房里,见房里零乱异常,一张大木床上,被盖未叠,换下的衣衫丢满床头;靠窗处摆了一张长条桌,上面只放着几个陶瓷杯碗;墙壁上桂着一柄刀和两副驯马用的高轿马鞍。她再一巡视,见屋角靠墙处,也摆有一张方桌,桌上端端正正地井放着两只门似盛有食物的碗,碗旁还放了两双筷子和两只酒杯;桌上正中,并立着两块木削的牌位,牌位前还有插香泥座,泥座下撒满香灰。玉娇龙十分惊诧,正欲近前细看时,艾弥尔提着褡裢和剑进屋来了。他把那两件东西放到桌上后,说道:“你先歇息。乌都奈取马料去了,回来就弄饭;我这就叫咱大哥去。”
玉娇龙还不等他转身,忙叫住他说道:“一会儿他自会回来的,你就不用去叫他了”。她看了看桌上那些怀碗,问道:“这附近可有村店酒家?”
艾弥尔:“倒有一户酒家,只是离庄太远。”
玉娇龙:“多远?”
艾弥尔:“来回约五六里路。”
玉娇龙立即从身边取出一些散碎银两,放到桌上,说:“你骑大黑马去,多多买些酒莱回来。”
艾弥尔高高兴兴地拿起银两就向门外跑去。一会儿,从院坝里传来了他说话的声音:“你呀,为啥这样不安分,兴许是闻出咱大哥的气味来了!难怪咱大哥也那么念你,你也通人性,比有些人还强。”
玉娇龙忙走到窗前一看,原来他是在对着大黑马说话。她不禁想笑,但心里却又渗出一股凄酸,把笑意抑止下去了。她等艾弥尔牵着马出了院门以后,才又转身去到屋角那张桌前,俯身往那两块牌位上一瞧,见一块刀削的木牌上写着“亡弟之灵位”五字,虽然写得无名无姓,她一望而知是祭的罗豹;另一块上写的却是“亡妻之灵位”五字。
玉娇龙一阵骇然之后,一种人伦之念在她心中油然升起,情随义发,不觉满怀怆楚,抱牌于胸,泪下如雨。
玉娇龙站立桌旁,悲怆许久,感到罗小虎对她的一片深情厚义,没想到自己出于无奈的一场险举,竟给他引来这般悲痛,甚至还给她设了灵位,对她寄托如此哀思。灵牌虽削得祖糙,碗里奉祭的也只是几个馒头,比起设在玉府里让公卿世宦前去祭吊的那种排场,简直有如天壤,但在玉娇龙心里,这才真使她沁心感肺,满怀幽怨一泻都消。这时,她心里泛起的已经不是自己所遭的凄若,而是对罗小虎身世的悲怜。她想到他幼遭不幸,少泊江湖,长年呼沙饮露,时时冒死犯危,从未得到一夕安宁。而今,她已效法了《封神榜》上的哪吒,“割骨”还了父,“割肉”还了母,她已不再是玉门的闺秀,也不再任父兄的拘束,从此可以自由自在,随心所欲,她决心为罗小虎献出全部柔情,让他从此甘食安枕,日子过得欢畅恰然。
玉娇龙甩了灵牌,换了衣衫,取镜理鬓,还复女妆。她卷起衫袖,将屋里零散什物略加理检,又走到床前去叠好被盖,收拾起那些换下未洗的衣衫。当她掀折着那些衣被时,一股带着马革的汗味,阵阵沁人她的心头。这略带酸涩的气味,对她是那样的熟悉,又使她是那样的动心。她沉入一片情漪,感到一阵无法自持的神摇。
正在这时,院坝里响起了一阵沉重的脚步声,玉娇龙顿感一阵心跳,赶忙放下揉抱在怀的衣衫,隐身窗旁望去,却是乌都奈提着一桶水正向敝房走去。他将要生火做饭了。
玉娇龙虽感有些怅怅,却也定下心来。她趁此举目向院坝四周凝望,贝树梢嫩叶被已快落士的阳光洒染成一片金黄,整个小院显得异常宁静。
玉娇龙那久已张绷得欲裂的心,这时竟已如小院一般的静宁。
玉娇龙正伫立出神,突然院门口映出来一个长长的身影。那身影虽被落日拉得变了模样,但玉娇龙却一眼就认了出来:罗小虎归来了。她赶忙隐身窗后,心里又是一阵扑腾。影子爬上墙壁,罗小虎已出现在门前。玉娇龙睨眸睇视,见罗小虎青布包头,蚕眉微锁,圆圆的大眼里隐露着一种黯然的神情;颌下密密须茬,掩映着他那张红润的嘴唇,更显出一种特别祖犷的气概。他肩披酱色罩衫,内穿白色排扣紧褂,胸前钮扣敞开,那鼓耸的胸肌,闪着古铜似的光彩。在玉娇龙眼里,他还是那样的虎虎英姿,还是那样的堂堂威武。
罗小虎迈到院坝中央,警觉地向四周看了一看,向正在灶旁煮饭的乌都奈问了一句:“饭可已煮熟?”乌都奈也是闷声回了一句:“快了。”就不再吭声了。
罗小虎这才跨上石阶,向房里走来,玉娇龙忙站到房屋中央,迎面向着房门,一任心头咚咚直跳。
罗小虎一步迈进房门,猛然一惊,手里的马鞭也落到地上。
但他却毫无转身退出之意,只大睁着惊疑的圆眼,紧紧地盯住玉娇龙。玉娇龙再也按捺不住那久已积萦在心的思念,只低低地唤了一声“小虎”,便扑到他的怀里,贴着他那宽厚的胸膛,低低啜泣起来。
罗小虎默默抚拥着她,过了许久,才说:“我还以为你已经死了。”接着,又用手抬起她的脸来,为她拭去眼泪,也略带哽咽地又说道:“其实我也疑你未死,果然如此,这就好了,还哭什么!过两天我就带你回到西疆去。”
玉娇龙带娇地:“为什么要过两天?明天就走不成?!”
罗小虎:“去来总要说个明白。拉达老爷不在,哪能偷偷离去。”他把玉娇龙带到床前坐定,他也挨坐到她身边,二人又说了一些那晚在鲁府分手后各自的情景。真是各有各的悲酸,各有各的艰险。
玉娇龙在谈了她决心犯险投崖的那段情景以后,忽又问道:“你然何也疑我来死?”
罗小虎:“你跳崖的消息传到王府,那已是你跳崖后的第五天了。我当即赶至谷口,躲在密林丛中,见他们正把你的内棺从谷里抬了出来。直到他们又将它启运下山去后,我又沿着那条洞道进入峡谷,在棘丛中寻遍谷底,都不曾见到一些血迹。出谷后,我又去到破庙,却连马匹和老道都不见了,我见到墙上留字,心里就犯起疑来。”
玉娇龙娇嗔地:“你既疑我未死,然何又给我设了灵位,这岂不是存心诅我!”
罗小虎憨然一笑:“论情论理你也早该来了。灵位也才刚设了两日,害得我也减肉十斤。”
玉娇龙笑了,笑得满含酸涩。罗小虎也笑了,笑得也带有余悲。
恰在这时,院外扬起一声长长的马嘶,罗小虎一下掀开玉娇龙,猛地站起身来,欢呼一声:“我的大黑马!”便冲出房门去了。
玉娇龙懒懒地走到窗前,但见那大黑马一看到罗小虎时,挣脱艾弥尔手里的缰绳,快步跑到罗小虎身旁,刨蹄抖尾,一阵紧挨紧擦,亲热已极。玉娇龙看到这一情景,不禁感到有些怅然若失。
一会儿,艾弥尔提着酒,端了一大盘羊肉进房来了;罗小虎跟在后面也端来了一大碗炒肝和葱饼;乌都奈也拿来了碗筷。玉娇龙见乌都奈在桌上摆了四副碗筷时,她觉得十分惊诧,不禁问道:“怎么,都在一起用饭?”
罗小虎毫不在意地:“都是自己兄弟,吃饭何用分开!”他抬头望望玉娇龙,眼睛里又闪露出她所熟悉的那种略带嘲弄的神色,他把玉娇龙拉到自己身旁坐定,又半打趣半认真地说道:“都是自己的兄弟,以后回到西疆,有时说不定睡觉还得困在一起呢!
你又何必见怪!“玉娇龙顿时羞得红晕满颊,她脸上虽然是火辣辣的,但心头却顿觉有股凉气透满全身。
罗小虎双手端起满满一碗酒来,高举过额,又似向着苍天,又似对着在座的三人说道,“没想到我罗小虎也有今天!我能娶得玉娇龙为妻,何异于身插双翅。从今后,我不须铁骑三千,也能横行沙漠。这不仅是我罗小虎的福份,也是西疆弟兄们的好运!”
说完,他仰起颈项,把满碗酒一气喝了下去,埋头望着玉娇龙得意自豪地笑了。
艾弥尔也端起碗来,说了一些既讨罗大哥高兴又不惹玉娇龙羞恼的吉利话,也把酒一饮而尽。
乌都奈也徐徐端起酒碗,说道:“愿玉小姐象文成公主那样永留西域;莫学蔡文姬那样一心归汉;我只望罗大哥早日动身,免西疆的弟兄们望眼欲穿。”
玉娇龙听乌都奈说得不伦不类,不禁想笑,但对他竟也知道这些史实,不觉诧异起来。
罗小虎说道:“等我辞过拉达老爷,立即就走。”接着,他又打趣地问道,“乌都奈兄弟,你从哪里听来这些故事?”
艾弥尔:“还不是在这次来的路上,从那些在客栈里卖唱的瞎子那儿听来的。”
罗小虎放下碗来,对乌都奈说道:“我是汉人,你是回人,艾弥尔兄弟是回回,咱三人都不同种同族,咱们却成了生死兄弟。管她文成文姬,何用和她相比。”
一直微低着头,含羞带愠默默不语的玉娇龙,忽然抬起头来,正色说道:“玉娇龙已投崖身死,此事已传遍幽燕,我乃春龙,今后你二人就叫我春……”她一时说不上来,艾弥尔立即接过话去:“干脆就称嫂子好了,这样更亲热些。”
罗小虎:“若讲亲热,还是称她姐姐为好。”
玉娇龙羞中带愧,总觉不是滋味。
大家又商量了一阵如何上路以及如何闯关过卡等事后,酒饭已足,艾弥尔和乌都奈便收拾起碗筷退出房门去了。
屋里又只剩下罗小虎和玉娇龙两人。这时,月光正照满花窗,无端添起一种融融的春意。玉娇龙那局促不安的心情也逐渐又归平静,她需要的就是这样的境地,就是这样的时刻。十天来,任何一张似曾相识的面孔都使她惕然心悸,自从投崖之后,在她心里,除了罗小虎和香姑,任何人对她都是累赘。
罗小虎拉着她并肩坐到床上,抚着她的肩问道:“那么高的崖,你可曾伤着哪里?”
他声音里充满了怜惜。
玉娇龙低声答道:“只手上挂破些儿皮,不妨事,早已愈口了。”
罗小虎:“那么幽深的荒谷,你一个人在乱棘丛中独行,该多惊心!”
玉娇龙仰起脸来:“想着你,我把命都豁出去,也就什么都不怕了。”
罗小虎笑了,笑得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齿,眼里又闪出那略带嘲弄的神情,他埋下头来,紧瞅着玉娇龙那脉脉合情的眼睛说道:“你已承认了马贼是好人?!”
玉娇龙不做声,忙将脸紧紧躲入他的怀里,一任罗小虎那充满柔情的爱抚。一时间,房里是那样的安谧,她又好象回到了郊静静的草原,回到了那也是这么安谧的帐篷,也是这么令人醉心的夜晚。她不觉移过手来,轻轻抚着罗小虎的胸脯,低声问道:“还疼吗?这儿。”
罗小虎低头在她耳边轻声说道:“疼,疼在心头,疼的是你!”
玉娇龙闭下了眼睛,她感到一阵颤动,心头浸透了蜜意。
月光已移过床头,灯也不知何时熄灭,静静的房里,只响跳着两颗相印共鸣的心。
半夜,玉娇龙从迷蒙中醒来,她张开眼,周围一片幽暗,触目的却是窗外一片晴朗的夜空。一瞬间,她恍疑卧身幽谷,心里不由一怔,她略一镇神,耳胖却正响起罗小虎那均匀而低微的鼾声,鼾声中还散发出一缕微微的酒气。蓦然间,玉娇龙心头无端感到一阵莫名的烦乱,她有如过去在荒原失马一般,好似突然又失去了一件足以自恃和赖以自持的东西,心头只觉空荡荡的。她正烦乱着,忽听院坝里响起一阵轻微的脚步声。她不由一惊,忙翻身下床,侧身窗旁一看,却原是艾弥尔正在给大黑马加夜草去。玉娇龙不知为何,竟突然想起了香姑,她心里又是一阵无端的烦乱。她已无心回到床上,只站立窗旁,让微微吹来的带有露意的春风,理一理自己的思绪。一时间,不断闪现在她眼前的已不是草原沙漠、荒村帐篷,而是元君庙里那庄严的道场,玉府里为她设立的那肃穆而悲沉的灵位,以及高奉在灵前那副御笔亲书的挽联。玉娇龙不禁一阵阵感到寒栗起来。
艾弥尔加过马草回到东屋去了。过了片刻,玉娇龙蹑脚出房,来到院坝,瞥见东屋里还亮着灯光,乌都奈和艾弥尔还在窃窃交谈。她想,月已西斜,他二人还在做甚?于是便轻轻走到窗前,侧目望去,见艾弥尔正在收拾行囊,乌都奈却坐在灯旁缝补汗褂。
艾弥尔在旁打趣地说:“针在你手里都变成拨火棍了,还能补好疤!还是明天拿去请新嫂子给你补吧!”
乌都奈把嘴一撇:“哼,你想得多美!她能给你我补衣服?!若是香姑嫂子倒还差不多。”
艾弥尔:“乌都奈哥,你总是对谁都不顺眼!今晚大家都高兴,你却在旁马着脸嘴,新嫂子会怎么想呢?还说你我见外她。”
乌都奈:“随她怎么想去,反正我不象她,心里脸上都假不来。”
艾弥尔有些不高兴了:“你说话总带刺,她刚来,义对你假了什么?”
乌都奈也有些激动起来:“你总护着她!明明没死,却当着我弟兄的面硬说自己死了;她本来姓玉,却偏说姓春;自己原是个女人,却要装成个男子像,这还不假!可笑她那位当年威镇西疆、四处追剿你我弟兄的帅父,假得更认真,明明知道她未死,却一本正经地把她装进一口棺材里,给她大开祭奠,大做道场,还讨了个什么‘孝烈’的封号,真是捏着鼻子哄眼睛!他哪知道他这位‘孝烈’却在这儿和咱罗大哥成亲了!”乌都奈说到这里,也不禁咧嘴笑起来,“我看,他们真叫假得出了奇,假得比真的还真!
那位皇帝老官也是麻扎扎的。“玉娇龙屏立窗外,由羞变恼,由恼变怒,几次都想闯进房,把他打个半死,可她终于紧咬嘴唇把自己强抑住了。她最后心里只感到一阵无比的难堪和屈辱!她不禁暗暗思忖道:”原来我在这些人中却已无可存身之地了!“她正煎熬着,艾弥尔在房里又说话了:”乌都奈哥,你也说得未免过偏,人各有各的难处,哪能一点都不假一下。你和我现在不都换了名姓,罗大哥也不姓罗了。听香姑嫂子说,玉小姐确是个好人,她过的日子也是够可怜的了!她来奔投罗大哥,我看是真心,哪能不把她当自己人看待。“
乌都奈还是冷冷地:“不是自己身上的肉,总是生不拢的,咱们走着瞧吧!”
艾弥尔摇摇头:“那也不一定。再说,她也只有这一条路了!”
玉娇龙不觉一震,心头感到一阵刺痛,她忿然转过身来,走回罗小虎的房里去了。
玉娇龙一下坐到床上,她刚想躺下身去,可却又突然停住了。恰在这时,罗小虎已被她微微地一动惊醒过来,伸出他那巨大的手,一把拉着她的爰臂:“你怎么不睡?”
接着又用力一带,就把她拥入怀里去了。玉娇龙也没有挣扎,只木然地任他温存。罗小虎带着怜爱责怪她说道:“看,浑身都是凉凉的,你不比我壮,谨防受寒。”
玉娇龙不吭声,心里还在为艾弥尔那句话隐隐作痛。
罗小虎拥着她,默默地过了一会,却突然发出数声微微的笑声。玉娇龙漠然地问道:“你笑什么?”
罗小虎在她耳边低声说道:“我想,如果你给我生下个小子来,咱们就把他好好抚养成人,把你的剑法传给他,让他随着我横行西疆,狠狠地收拾收拾那些巴依、伯克,为那些受苦受难的弟兄扬眉吐气!”
玉娇龙虽感到脸上一下变得火辣辣的,但心里却又不禁打了个寒战。她猛然一惊,想道:“天啦,我竟会为他生个儿子,而且仍然是个马贼!”她甚至不禁为此感到惶恐起来。
又是一阵沉默之后,玉娇龙伤心而又无可奈何地问道:“你回西疆后仍然去作马贼?”
罗小虎:“那里的弟兄们需要我,我也别无他路了。”
玉娇龙恳求般地温声说道:“我已交香姑带去了一些金银,这次我又带来了许多值钱的东西,足够我二人过一辈子了。我们去寻个幽静的所在,隐姓埋名,平平安安地过一生,岂不更好!”
罗小虎:“哪有那样的乐土?!那些巴依、伯克们,就连狼不能去的地方也能去,鹰飞不到的地方也能来,哪能容你平平安安地过日子!”
玉娇龙默然片刻,又试探地问道:“你可知道虬髯客这个人物?”
罗小虎:“莫不是说书人说的《风尘三侠》中的那位好汉?”
玉娇龙急切地:“正是他。你认为他怎么样?”
罗小虎:“说书人把他吹得神玄,我看他也是一名巨贼,不然,他哪来那么多财宝送给李靖。”
玉娇龙:“你难道就不能学他那样,远离朝廷王土,自己去建立一番功业?!”
罗小虎:“远离朝廷王土?!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官,就有王;要去建立功业,就是取而代之,自立为王;我恨的正是这般东西,我也不去立这样的功业。”
玉娇龙默然了。
罗小虎也带着闷闷不乐的声音说道:“好啦,睡吧,别胡思乱想了。回西疆,仍当马贼去,我们都只有这条路了。”说完,他翻过身去,一会儿便又响起了微微的鼾声。
玉娇龙却张着双眼,毫无睡意。她只感到眼前一片茫然,心里又是空荡荡的。她耳边不断响起艾弥尔和罗小虎那句“只有这条路了”的话音,她心里也不断暗暗自问:“难道我真的就只有这条路了?!难道我命里注定了就是贼妇?!”她的心在隐隐作痛,时而感到羞愧难禁,时而又感到悲愤、屈辱。不知不觉间,窗上已渐渐露出曙色。她穿好衣裳,蹑脚走出院坝,但见晨星来隐,露挂树枝,不远处,王爷偶来居住的府第,绿瓦红墙,雕栏玉砌,在晨雾隐隐中,显得特别庄严雄伟,别有一番尊荣气概。玉娇龙若在平日看来,亦只如山上望岭,不觉其高,可她此时望去,却竟似渊底看峰,高不可仰。
一种卑微和自惭形秽之感突然袭上心来,她的心又是一阵隐隐作痛。
玉娇龙怅然若失地回到院里,正碰上乌都奈睡眼惺松地提着水桶出来,他和玉娇龙擦身柏过时,既未给她请安,也不给她让道,只冷冷地说了句:“王庄人多嘴杂,你休去乱走!”便扬长地出院打水去了。
一股无名的怒火,蓦然升上玉娇龙的心头,她一咬嘴唇,恨恨地想道:“我岂能和他们一道,又焉能与他们为伍!”她疾步回到房中,站在床边,默默地凝视罗小虎片刻,俯身将半落床下的被盖拉起给他盖好,然后,又轻轻呼唤了声“小虎”说道:“你多珍重,恕我不与你同行了!”说完,她毅然提起褡裢、宝剑,返身去到敝房,匆匆备好大黑马,牵着它沿旧路出了王庄,然后翻身上马,一挥鞭,立即响起一串清脆的蹄声。那蹄声穿过树林,越来越小,渐渐地消失在林外的晨雾中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