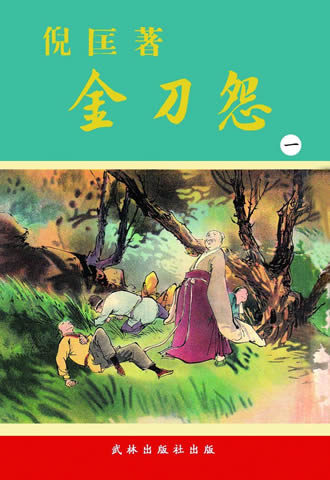春雪瓶蕴蓄着满腔忿恼,穿过草原,向西南方向一路寻去,只要遇上有牧民居住的帐篷,或是农家聚居的村庄,她都前去打听一番。她穿过一片草地又是一片草地,跨过一座山丘又是一座山丘,寻遍了周围二百里地,大红马却是踪迹全无。饥渴和劳倦不但没有使她松懈下来,反更激奋了她寻回大红马的决心。在她心里,她已经认定了盗马贼是日前在沙湾驿站门前看大红马马蹄的那个汉子,她还认定了那汉子准是姚游击军营的暗哨。春雪瓶突然想起她母亲曾对她说过的“不人虎穴,焉得虎子”的那句话来。蓦然间,她下定了重到乌苏一探军营的决心。春雪瓶主意已定,便迈开大步直向乌苏方向走去。她刚过奎屯不远,便发现道路上不时出现一队一队的巡骑,一会儿驰进树林,一会儿又绕过山丘,好似在戒备着什么,又好似在搜寻着什么。春雪瓶不禁暗暗疑诧在心,只寻能够避开他们的小道走去。从奎屯到乌苏本来只需半天的时间,春雪瓶在路上绕来绕去,却从早晨一直走到傍晚,方才来到乌苏东城关口路旁的那片树林。她隐身在林边一株大树后,探头向关口望去,见木栅门前站着八名军校,个个手按刀柄,注视着古道上的一切动静。古道两旁那些店铺已是家家闭户,门前冷冷清清。春雪瓶正惊疑犹豫间,忽见她不久前曾去拣药那家药铺的门轻轻开了一线,随着便从里面探出一个头来向关口那边望望,很快地又缩回去了。春雪瓶只在这短短的一瞥中,便已认出那人正是梁巢父来。她在林里又呆了一会,这时天色已渐渐昏暗下来,忽从城楼上传来一声号角,随着那声号角,木栅门关了,八名军校也退进城去。
又一阵沉闷的叽嘎声里,城门也紧紧地闭合拢来。春雪瓶趁此走出树林,来到药铺门前,用手轻轻将门一叩:“梁……梁爷爷,开开门!”
铺里立即传来了梁巢父的声音:“你是谁?”
春雪瓶:“我是春雪瓶。”
门立即打开了。春雪瓶忙闪身进入铺内,将革囊往桌上一放,回过头来望着梁巢父笑了笑,说道:“梁爷爷,你没想到我又会来吧?!”
梁巢父又惊又喜地:“没想到,真没想到!”他把春雪瓶打量了一下,又显得惊诧不安地说道,“你在这个时候来乌苏,该不是又来拣药吧?!”
春雪瓶:“梁爷爷,你先说说,这乌苏究竟出了什么事情?”
梁巢父:“我也还未弄清,只见军营里的人打从今早起,突然巡骑四出,关口也增多了守卫,对进出的人也盘查得紧。我猜他们兴许是听到了什么风声。”
春雪瓶:“什么风声?!”
梁巢父忽然一愣,盯着春雪瓶问道:“姚游击是否打探到了你来乌苏的消息?!”
春雪瓶忿忿地:“他自己做贼心虚,大概已料到我会来找他的。”接着,便将她在去乌伦古湖途中大红马被盗的事,以及她心里的猜疑,一一说了出来。
梁巢父听后,沉吟片刻,说道:“兴许这也只是姑娘的猜疑,我看那盗马贼未必就是姚游击军营中人。因昨晚有两名军校到伍掌柜店里饮酒,也未说起马已弄回的事,还说姚游击因输了刀马,情性变得更加凶暴,就在他们来饮酒前,还毒打了一名军校,如此看来,大红马并未在这军营。”
春雪瓶低头思忖着,脸上露出失望的神色。
梁巢父:“姑娘也不用着急,我这也只是猜测,等我明天设法打听一下再说。”说完,他犹豫片刻,忽把话题拉开,迟疑地问道:“春姑娘,你前番拣去的那剂药,病人服后情况如何?”
春雪瓶含糊应道:“似有好转,只是不见大效。”
梁巢父充满关切地说道:“病既是久积而成,药也非几剂就能奏效。这样的病重在调摄,切忌寒侵,更不宜久处深山,孤寒自苦,贻误一生!”
春雪瓶已经听出梁巢父话外有话,意在劝她母亲离开天山,重返尘世,但她知道母亲最厌恶的就是有谁谈起她的事情。因此,春雪瓶只默然片刻忙把话题一转,忽然问道:“梁爷爷,你可知京城里有个名叫德秀峰的官儿?”
梁巢父感到有些诧讶:“姑娘为何问起他来?”
春雪瓶:“几天前,我在玛纳斯河边大路上,碰到了他,随他一路的还有他的儿子和儿媳,我和l他们结伴同行了两天,听他们谈了许多京城的事情。”
梁巢父若有所思,忽又若有所悟地惊呼一声:“啊,原来是他!”
接着又说道:“十日前有两位从这里过路的蒙古朋友,曾对我谈起过一桩怪事,说他们在迪化城外遇到一位从京城来的官员,曾向他们打听一个人的下落。那官员还说,他们只要能将他打听的那人的下落告诉他,他愿赏银千两。我一直在琢磨这官员是谁,这才明白过来,原来却是这个德秀峰!”
春雪瓶听得无头无脑,只困惑不解地望着梁巢父。
梁巢父忖度片刻,才又意味深长地望着春雪瓶说道:“那德秀峰打听的不是别人,就是早已杳如黄鹤的驼铃公主!”
春雪瓶吃了一惊,心想:这不正是八年以前母亲居住在艾比湖时,那里的人们对她的称呼吗?这德秀峰与母亲何关?又为何要打听驼铃公主的下落?春雪瓶尽管心里生起许多疑问,可是,由于事情又涉及到她母亲,她只好闷在心里,不便问出口来。
梁巢父也因春雪瓶的沉默而更加审慎起来。他也不敢再深谈下去了,只仍似闲聊般地说道:“我那两位蒙古朋友只对德秀峰说,驼铃公主已于八年前只身带着她的女儿离开了艾比湖,至今下落不明,多已不在人世的了。”梁巢父瞬了瞬春雪瓶,又不禁充满感伤地说道:“听我那两位蒙古朋友说,艾比湖那些蒙古乡亲,一直都在惦念公主,把公主的房宅、财物都保管得好好的,都祈望有一天公主能重新回到艾比湖去。”梁巢父那苍老的声音也带着些儿哽咽。
他停了停,又轻轻地补了一句,“那艾比湖的气候更比天山宜人!”
春雪瓶的心深深地被感动了。她从梁巢父的这番话里,感到了尘世的温暖,重唤起她记忆里的童年,以及对艾比湖那些童年伙伴的怀念!春雪瓶眼里闪着一种异样的光彩,凝望着梁巢父,含糊地但却是真诚地说道:“天山上的千年积雪也有融化的时候,一个心灰意冷的人也会有回心转意的时候的。梁爷爷放心,我一一定把你的好意带回天山去。”
梁巢父欣然地一笑,点点头,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当晚,春雪瓶便在梁巢父铺里留住下来。
第二天一清早,梁巢父便进城去了,直至快近中午,他回到铺里,告诉春雪瓶说,他已向军营里几个他熟识的人打听过了,都说不曾见过大红马,只说姚游击已于今早率领着二十余骑急急忙忙地向北驰去,不知是否有关大红马的事情。梁巢父还从他们口里探知,军营加强巡逻,是由于姚游击得报,在车排子一带发现了马贼的踪迹。梁巢父谈到这里,不禁皱起眉头,搔首踱步,自言自语地说道:“他们来干什么?来的又是何人?”
春雪瓶:“兴许是日前在草原上妄图抢劫我们的那帮游骑!”
梁巢父也不禁哑然一笑,说道:“兴许真是如此!军营里也常有这样的事情:当官的最怕马贼,往往将游骑误认为马贼;军校们最怕游骑,又常常把马贼故报为游骑。”
春雪瓶寻马心切,见自己来到乌苏扑了个空,不禁更加气恼起来。她听说姚游击向北驰去,便决心随后跟去看个究竟。春雪瓶提起革囊,辞别梁巢父就要动身,梁巢父忙位着她,说道:“姑娘,你本领虽高,毕竟是孤身一人,又无坐马,怎能和他周旋!依我之见,不如暂回天山,作些准备,再下山来。”
春雪瓶:“我这次下山,就是为给罗大伯送还刀马去,如今失了大红马,我还有何面目回天山!至于那位姚游击,除非盗马果然与他无关,不然,我定饶他不得!梁爷爷放心,我岂把他和他那二十余骑放在眼里!”说完,她便出了铺门,沿着道旁小路向北走去。
春雪瓶在乌苏城北野外游荡了整整一天,不但未见姚游击到来,却连一个骑校的影子也没看见。守候又落空了,她只好又转身向东,阳蔚石河子方向一路寻去。春雪瓶忍着饥渴,熬着疲劳,在荒原上东寻西找地又走了一天一夜,她除偶尔碰到几个赶骆驼的汉子和几个结伴同行的挑担脚夫外,还是连个巡骑的影儿也没见到。第三天中午,她穿过一片灼热的砂砾地,来到通向玛纳斯的古道旁,春雪瓶这时已经感到闷倦已极,很想找个凉爽的地方歇息了。她举目一望,忽见前面不远处,道旁出现了一丛茂密的树林,便忙走进林去,选了一株枝叶繁密的大树,爬上高高的树桠,将身斜靠枝上,一会儿便沉沉睡去。
春雪瓶也不知睡了多久,正迷朦间,耳边忽然响起一阵急骤的马蹄声,她猛然一惊,迅即张开眼来,探头循声向林外看去,倏见一个身着骑校装束的汉子,纵马如飞,从林边一闪而过。时间虽只一瞬,但她已认出那军校骑的正是她的大红马!同时也只一瞬间,春雪瓶便已从绣袋里取弓在手,只见她扬手一扣,一支短短的弩箭好似闪电般脱弦而去,一眨眼间便插到那骑校的右臂上去了。那骑校中箭后,只略略摇晃一下,便猛然勒住奔马,那边即回过头,圆睁着一双惊异带怒的眼睛,向林里搜寻着。春雪瓶正想跳下大树扑去夺马,蓦然间她看到了一张她熟悉的面孔,和一双她熟悉的眼睛,特别是那深沉中带惊带怒的眼神,不知曾多少次把她从梦中扰醒。一刹那问,春雪瓶已经明白过来,她又干了一桩比天还大的错事!被她射伤这人,正是八年前曾经被她射伤、并因而被官兵所擒的半天云,也正是她要去乌伦古湖寻访、给他送去刀马的罗大伯。
春雪瓶一阵锥心般的难过,悔、愧、羞、悲一齐绞在心头,她木然无措,不知该如何是好了。极度的难堪竟使她对林外又响起的一·片蹄声也失去觉察,只呆呆地看着罗小虎用右手困难地拨出腰刀,再哆嗦着交到左手,随即便又看到约有二十余骑军挥刀围上前去,只见刀光马影,立时杀成…团。春雪瓶忽地打了个寒战,她也忽地从寒战中清醒过来。恰在这时,她看到姚游击j立玛林边,正搭箭开弓,准备伺机向罗小虎射去。春雪瓶哪敢褥误,迅即扬手一箭向姚游击右臂射去,只听他“啊唷”一声,一松手,弓已随声坠地,箭也斜飞出去,正好插在一名军校的腿上。那军校也几乎是与弓I司时坠落地上。春雪瓶随即一连放出数箭,紧紧围着罗小虎的几骑,有的带箭窜开,有的坠马,有的伏在鞍上惨叫。姚游击和军校们都惊呆了,只仓皇四顾,不知箭从何来。罗小虎趁军校惊散四旁之际,勒马横刀不住向林里探望。他眼里只充满了惊愕,怒意竟已全无。
春雪瓶趁那班军校正在惊惶万状、六神无主之际,突的又连连发出数箭,随即又有几名军校中箭嚎呼。其余十几骑军校被吓得魂散魂飞,拨马乱转,挤成一团。罗小虎见状,不禁发出一阵震耳的笑声,挥动腰刀,一纵大红马,猛向他们冲去。军校们哪里还敢抵敌,吓得一阵惊呼,各自勒转马头,争先逃去。姚游击正想喝住他们,忽见罗小虎又回马向他驰来,他也慌忙拨马,跟在那些军校后面,向乌苏方向逃去。.
古道上又沉静下来。要不是地上遗下几柄腰刀和一张弯弓,简直看不出这里曾发生过战斗的一丝儿痕迹。
罗小虎仍立马道上,向树林里张望,他那疑讶的神色里,已带上了些儿凄伤。
春雪瓶从革囊里取出短刀,跳下树林,慢慢来到罗小虎马前,双手捧刀,低头跪倒地上,意语不连地说道:“我错认人了,不是有意射你!我是来还刀的。还望罗……罗大伯宽恕!”
罗小虎没说话,只俯下身来,久久地盯着她。
春雪瓶见罗小虎久无动静,便怯生生地抬头来向马上望去,她看到一张虎虎有威的面孔上,充满了惊喜,布满了慈祥,一双闪闪发亮的眼里,正耀起一层泪光0春雪瓶仰望着那张充满慈祥的面孔,又低声说道:“我真的不是有意伤你!”
罗小虎仍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你是雪瓶!”
春雪瓶点点头:“是的。我正要去乌伦古湖找你……。”
罗小虎还不等他说完,翻身一跃下马,抢步来到她的面前,接过刀,伸手扶起她来,为她拂去膝上的尘沙,说道:“我也正在到处寻你,因此才碰上那班官兵的。”说完,他举目向四野望一番,忙去拾起那些兵器,回头又对春雪瓶说道:“走,到林子里去再慢慢细谈。”..
二人进入树林,罗小虎扔了那些拾来的兵器,将大红马拴在树上,选了一片干净的地方坐下。春雪瓶早已注意到了,她射去的那支短箭还深深地插在罗小虎的臂上,以致罗小虎每一举动,都痛得微微皱了皱眉头。她等罗小虎刚一坐定,便忙移坐到他身旁,充满愧疚地说道:“罗大伯,这箭我来给你拔出。”
罗小虎欣然一笑:“好,让你拔。”
春雪瓶小心翼翼地伸过手去。可那手还没触着箭便情不自禁地颤抖起来。罗小虎见她那般情景,又笑了,笑得很开心。他看春雪瓶迟迟不肯动手,又说道:“拔吧,雪瓶!你也别怕,你拔我不会痛的!”
春雪瓶一咬牙,握住了箭,手虽然不颤抖了,可心却急剧地跳动起来,她还是没敢往外拔。
罗小虎回头看着她,充满怜爱地摇了摇头,说道:“仁慈也须手狠!你能懂得这点就敢拔了。”
春雪瓶听了,迅即将手一抬,箭也随手而出。她偷向罗小虎瞟去,见他不但连眉也未皱一下,反而发抖一阵爽朗的笑声。他笑过以后,.又回头说道:“这就对了!你要记住:为人行事,该狠时,杀人也.无须眨眼;不该狠时,蝼蚁也休伤它性命。”
春雪瓶从革囊里取出母亲给她的金创药来,给罗小虎的伤口敷上,又细心地替他包扎起来。
罗小虎拾起那支带血的短箭,默默地玩了会,忽又举起它来,充满感慨地对春雪瓶说说道:“你这弩箭的射法原是我教给你母亲的,你母亲又教给了你,没料到你却两次用它来射我!”
春雪瓶羞愧得赶忙低下头去,难过得几乎哭了起来。
罗小虎忙伸手扶起她的头来,对她说道:“雪瓶,我这不是在责怪你,也不是在怨你母亲,我是在想:我从不信天意,但从这事看来,莫非果有天意?!”
春雪瓶不懂得他这话的意思,只困惑地望着他,忙又解释道:
“不,不是天意,是无意!一个装扮成百姓的官兵盗了这大红马,我气极了,正在四处找寻这马和那盗马的贼,我走倦了,正在这林里的树上打盹,恰巧你从这儿跑过,我没看清就放了箭。当我认出是你时,我悔极了!这都是我的错,不是天意。”
罗小虎又是一阵开心的朗笑后,说道:“好啦,别再提这一箭之事了!只要我能见到你,再中一箭也是值得的。”他瞅着春雪瓶,眼里充满了宽慰和喜悦。
春雪瓶:“这大红马怎会到你手里来了?”
罗小虎:“盗走你这大红马的那人不是官兵,是你乌都奈叔叔。
他去迪化办完了事回乌伦古湖,在沙湾的驿站门前见到了这大红马,他便打定主意要把这马盗回来。他不认识你,见你和几骑官兵一道上路,还以为你是军营里的亲眷哩。他一路跟在你们身后,进入草原的那天夜晚,他便下手了。他骑着大红马刚进沙漠,正碰上我从乌伦古湖赶来,他把盗马的经过告诉我后,我便已知道他是干了桩蠢事,那位被他误认为是军营里亲眷的姑娘一,定是你了。”
春雪瓶忙截住罗小虎的话头,问道:“你怎知那人是我?!”
罗小虎:“你在乌苏东城关口和姚游击对刀赌马的事你马强叔叔都已经告诉我了。我知道这刀和马在你手晕。”他又接上刚才被春雪瓶截断的话,继续讲下去,说他断定那个失马的人是春雪瓶后,便和马强赶到车排子去,守候在通向塔城去的大道旁,想在那里见她一面,并把乌都奈误盗大红马的事告诉她,好使她放心。不料他和马强刚到那里,便被乌苏军营的巡骑发现,他不想和军营的官兵冲突、纠缠,只得离开车排子,避开了那些从乌苏军营赶来拦截、搜索他们的官兵。后来,他又听一位牧民弟兄说,有位年轻姑娘在这一带找寻她被盗失的大红马,他猜出这准是春雪瓶,便也在这一带到处寻她,这才引出刚才那二十余骑官兵追赶他的事情来。
春雪瓶听完罗小虎谈了这段经过以后,这才明白过来。她立即又不安地问道:“你离开乌伦湖时,就只孤身一人上路?”
罗小虎点了点头。
春雪瓶:“你真不该这样行事,这太危3ǔωω.cōm险了!”
罗小虎:“人多了反易惹眼,再说我也不便多带人来!”他停了停,又不禁感叹地说了句,“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
春雪瓶十分诧异地:“甚么不得已的事情?!你单身一人离开乌伦古湖出来干什么?”
罗小虎:“到天山,寻你母亲去!”
春雪瓶一怔,愣住了,一时竟说不出话来。
罗小虎忽然俯过身来,紧紧盯住春雪瓶,着急而又深沉地问道:“雪瓶,告诉我,你母亲是不是生了病?她近来情况如何?”
春雪瓶不由吃了一惊,甚至有些慌乱起来。谈论和探询她母亲,这在她心里已成为一种禁忌。多年来,谁也不曾在她面前这般放肆地提过她的母亲!可眼前这位罗大伯,在提到她母亲时,竟毫无敬畏之意,全不把禁忌放在眼里!春雪瓶心里不禁暗恼起来,说道:“我不能告诉你。我母亲也决不允许别人谈及她的事情!”
罗小虎:“那是别人!这是我,是我在问,是我要你谈!”
春雪瓶被罗小虎这激动的神情和不同寻常的语气怔住了。她抬起头来,紧紧盯着罗小虎,问道:“你是我母亲的什么人?”
罗小虎盯着春雪瓶,眼里闪耀着一种奇异的光彩,胡须也颤动起来,他沙哑着声音说道:“我是你母亲什么人?!我是你爹!”
这对春雪瓶来说,真如晴空霹雳,她惊诧得张大了眼睛呆在那儿不动了。
罗小虎很快又平静下来,意味深长地补了一句:“我和你母亲原是结发夫妻。”
春雪瓶虽没说话,可罗小虎一句话在她心里激起的思绪,却有如惊涛拍岸,又似风卷残云,她被搅得乱极了。她愣了许久,才困惑地说道:“我怎从未听母亲说过这事?!”
罗小虎:“就因为我是马贼!”接着他又沉痛地说道:“你母亲纵然因此不愿随我,难道你也不能叫我一声爹?!”
春雪瓶一时间竟没有了主张,只喃喃地说道:“这事我得回去再问问母亲,要她把真情告诉我。过去我也问过她,可她说你‘不是’,说你‘决不是’。”
罗小虎突然笑了起来。尽管他眼里还噙着泪水,可笑得却是那么开心。他瞅着惶然无措的春雪瓶说道:“不管你母亲说是也好,不是也好,也不管你叫也罢,不叫也罢,反正我是你爹!好,你也别为难,随你怎么叫都行,不过,还是得把你母亲生病的情况告诉我。”
春雪瓶只有顺从了。她告诉他说,母亲一直患有咳嗽症,近年来病情日益加重,每到冬天,常常咳得透不过气来,就在二十多天前,母亲的病又发了,她劝母亲下山去看病,母亲不肯,经她苦苦劝求,母亲才自己开了张药方,交她拿到乌苏去买药。药买回去后,母亲服了几剂,病情虽稍有好转,却仍未见有多大起色。现在她又已离开母亲十来天,也不知母亲的近况如何了。
罗小虎听得紧皱眉头,显得心情十分沉重。春雪瓶刚一说完,他便带着责备的口气说道:“你就不该在这时离开她!”
春雪瓶:“我原说等她病好后再给你送刀马去的,可母亲性急了,说也许你这时正需用它们,便不由分说地把我催走了。”
罗小虎站起身来,默默地在林里走来走去。他沉思片刻,又走到春雪瓶身边,满怀凄楚地说道:“雪瓶,你知道你母亲是为何离开艾比湖的吗?”
春雪瓶摇摇头。
罗小虎:“好,我告诉你:就是为你八年前在塔城射我那一箭,这才把她逼到那人不知、鬼难寻的地方去的!”
春雪瓶的整颗心、整个身子都立即颤抖起来。这虽是她心中曾经猜疑过的事情,但也只不过是猜疑罢了。此刻由罗小虎口里说了出来,猜疑便立即成了真实。春雪瓶的心又.一次被震撼了!
她万万没有想到,母亲那么宠爱的自己,却竟是害了她的罪人!一向很难流泪的春雪瓶,这时也不禁伤心地饮泣起来。
罗小虎让她哭了许久,才将她拉近身边,为她拭去泪水,充满爱怜地对她说道:“好啦,别再难过了!这也不能全怪你,要是你母亲早告诉了你,我是你爹,你也不会对我放那一箭了。”他叹息了一声,又说:“许多苦还是她自己讨来的!我这番上天山去寻她,就是为去看看她的病,把她劝下山来。她纵然不愿随我去,也不能让她再那样去折磨自己了!”
春雪瓶忧虑地:“那地方很隐秘,你寻不到她的!”
罗小虎盯着她:“你难道不给我带路?!”
春雪瓶不安地:“我不能。我答应过母亲,还在她耐前起过誓,我这么做,她会生气的。”
罗小虎:“好,不难为你,只要知她在天山,我踏遍天山总能寻到她的。”
春雪瓶沉凝片刻,忽然抬起头来,指着大红马对罗小虎说道:
“罗大伯,你要上天山去寻我母亲,可向这大红马问路去!只有它才能告诉你了!”
罗小虎(炫)恍(书)然(网)大悟,一刹间,只见他眼发亮,脸上也泛起红光,连声说道:“对,对,老马识途!我怎就未想到这点!这大红马准能把我带去的!”
二人正说着,不知不觉问,一缕阳光透过疏枝射进来,恰恰照到春雪瓶的脸上,她眨眨眼睛,又伸出舌尖轻轻舔了舔嘴唇。罗小虎掉头看看林外,说道:“天色已经不早,看你似已饥渴,不能再逗留在这林里了。此去不远处,住有一个我的熟人,我们可到他那儿去喝喝水,吃点东西,今晚就在他那儿借宿一夜再说。”
罗小虎脱下他身上所穿的官兵服装,露出平时惯穿的那件白色排扣短褂,这才拿起短刀,看看试试,又试试看看,只深情地说了句:“伙计,你终于又回到我身边来了!”说完便将它藏进怀里去了。
春雪瓶瞅着他,不禁猛想起马强对她说过的那句话来:“你罗大伯见到你,准比他重得刀和马还高兴!”她心里蓦然生起一阵莫名的欣幸,不禁又闪起一个念头:罗大伯刚才说的那番话,莫非果是真的!
罗小虎收拾停当,又把春雪瓶的革囊提去挂在马鞍上,然后就牵着大红马和春雪瓶走出林子,一直向东走去。走了大约十来里,前面忽然出现一片草地。草地虽不算大,草却长得又青又茂,好像从不曾受到过成群牲口的践踏。草地左边是一一脉长长的灌木林丘,那簇簇的矮树,把草地衬得更加幽宁。进入草地不远,就在靠近林丘的边际,搭着一一座小小的帐篷,那帐篷在这荒无人逊的草地上,显得孤零零的。罗小虎带着春雪瓶来到帐篷前,将大红马拴在帐篷旁边的林栅上,便一同跨进篷内。罗小虎把春雪瓶安顿在一张牛皮毯上坐定,便去取来一罐水、一些烤羊肉和几个饭团,两人便不急不忙地吃了起来。春雪瓶早已渴极、饥极,吃得更是水甜饭香,十分快意。她一边吃,一边打量着帐内的一切,见这座小小的帐篷,篷顶篷壁都打满补丁,帐内放置的什物也很简单,一望而知是个穷苦牧民的篷窝。春雪瓶不禁有些纳闷,心想:这么荒野的地方,怎会有人住到这里来了?坐在她对面的罗小虎,只闷闷不乐地吃着,好像有什么心事似的。帐篷里一时显得很沉闷。春雪瓶瞅着他忽然问道:“这是谁住的帐篷?”
罗小虎:“布达旺老爹。”
春雪瓶:“布达旺老爹是个什么样人?他怎会住到这么荒僻的地方来了?”
罗小虎:“他是位十分令人尊敬的老爹。他为躲避那些伯克、巴依的迫害,多年来只好带着这小小的破帐篷,东飘西荡,拣这样连人迹都少到的地方隐住下来,担惊受怕地过日子。”
春雪瓶的心被触动,对这可怜的老爹不禁充满了同情:便又说道:“这老爹难道一个亲人都没有了?”
罗小虎的神色黯然起来,眼里也满含了哀伤,说道:“老爹本有两个最亲最亲的亲人,一一个已经死了,一个虽然还在,可也和我一样,是个有家归不得的马贼,老爹还是连一个亲人也没有。”
春雪瓶十分难过地说:“这老爹也孤独得真可怜,比我母亲还可怜!”
罗小虎不以为然地:“雪瓶,你想错了!老爹并不孤独,他也从不感到自己可怜。他虽死了一个亲人,另一个亲人也不在他身边,可他却到处都是亲人,不管他住到什么地方,还是常常有人去看他。你母亲哪比得老爹!”
春雪瓶不解地:“老爹怎会有那么多亲人?”
罗小虎:“老爹为人正直,能急人之急,不计个人安危,热心助人。除了在穷苦的牧民中,有许多他的亲人外,我和我的弟兄都是他的亲人。”他忽然瞅着春雪瓶笑了笑,又说道,“还有你母亲和你,也应算是老爹的亲人。”
春雪瓶大出意外,忙问道:“我母亲也认识老爹?”
罗小虎:“不仅认识,你母亲还曾和老爹的孙女结成患难姐妹,并曾在这小小的破帐篷里安过身呢。”
春雪瓶惊讶万分:“我母亲曾在这座帐篷里住过?”
罗小虎:“住过,还是两次。她第一次住进这帐篷,那已是十九年前的事了。那时,她也不过像你这么大,我也是在这帐篷里和她以心换心的。她第二次重进这帐篷,亦已是十六年前的事了。那时她正带着刚出世才几个月的你,拖着一身病,在这帐篷里度过了一段十分艰难的日子。要不是老爹和他亲人的照料,你恐怕也活不到今天了!”
春雪瓶又一次被震撼了。她对母亲和自己过去的身世,全陷入一团迷雾。她想问个明白,又不知从何问起。她愣了片刻,突然仰面来,望着罗小虎急切地央求道:“罗大伯,请你把我母亲过去的一切全告诉我!我只知道她心里装满了许多悲痛许多愁,只知道心里时时都在惦挂着另一个亲人,其他的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罗小虎望着春雪瓶,眼里充满惆怅和凄凉。他茫然地说道:
‘‘我和你母亲已分手十六年了。八年前在塔城虽打了个照面,却连一句话也未曾交谈。因此,她的有些事我亦弄不清楚,有些事就是给你讲了,你现在也不会懂得,还是让她以后慢慢地告诉你吧!”
春雪瓶时时惦挂在心,也是她最急于想知道的,还是她母亲曾几次对她提到过的那个尚在关内的亲人。她沉凝片刻,猛然灵机一动,忽又问道:“罗大伯,你可知道我母亲在关内还有什么别的亲人?”
罗小虎犹豫了会,肃然说道:“雪瓶,你打听这个干什么?你母亲在关内早已没有任何亲人了。”
春雪瓶不觉一怔,又问道:“罗大伯,你呢?你在关内可还有亲人”
罗小虎毫不迟疑地:“有一个。也只剩下这么一个亲人了。,’春雪瓶:“谁?”
罗小虎:“我的妹妹。”
春雪瓶不觉一愣,这虽不是她心里想要探出的那人,却不由使她猛然想起罗燕托过她的事来。她急忙说道:“罗大伯,你妹妹是不是罗燕姑姑?”
罗小虎略感惊诧地:“你母亲把这也告诉你啦?”
春雪瓶:“不,是罗燕姑姑自己告诉我。不几天前我曾见到过她。”
罗小虎猛然站了起来,圆睁着一双惊奇的眼睛,一把拉着春雪瓶,急切地问道:“你在哪儿见到她?她又是如何对你说的?快讲,快讲!”
春雪瓶这才将她如何碰见罗燕,如何与她认识,又如何谈起她和罗小虎是兄妹的经过,原原本本地讲了出来。罗小虎听得心里是时悲时喜,脸上是忽阴忽晴。春雪瓶也讲得娓娓情真,描得细细入微。当她讲到罗燕索看短刀的那般情景,罗小虎也忍不住滚出几颗泪来。春雪瓶讲到最后,说道:“罗姑姑知道我要去乌伦古湖找你,十分高兴,要我告诉你,她在德家一切都称心如意,请你不要惦挂她。她还再三要我转告你,说罗家就剩下你…人了,要你……
要你……”春雪瓶不知该怎么说才对了。
罗小虎迫不及待地:“她要我怎样?”
春雪瓶:“要你多保重!”
罗小虎虽然眼里还含着泪水,却不禁又咧嘴笑了,说道:‘‘怎说只剩我一人呢!她不也是我罗家的人吗!”他见春雪瓶那欲言又忍的神情,忙又问道:“她还说了些什么?”.
春雪瓶:“罗姑姑说,你不要……不要断了罗家的香火。”
罗小虎默然了。他仰头望着篷顶,眼里充满怅惘的神情。过了一会,他忽又埋下头来,看了看春雪瓶,自语般地说道:“女儿不也是一样吗!”
正在这时,帐外忽然传来一声呼唤:“小虎回来了吗?’罗小虎忙对春雪瓶说了句:“布达旺老爹回来了。”他随即就跨出帐篷去了。
过了一会,罗小虎又回到帐篷里来了。布达旺老爹跟在他身后。春雪瓶还不等罗小虎开口,便忙走上前去,亲亲热热地叫了一声“老爷爷”。布达旺老爹笑了,笑得很亲切。他盯着春雪瓶打量一番后,点点头,惊叹道:“真是俊美极了!没想到当年的小雏鸟竟长成了一只金凤凰,又飞到我这破窝里来了!”他随即又回头对罗小虎说道:“我敢说,人们传说的飞骆驼准定就是这春姑娘!”
罗小虎张大了眼,惊奇地注视着春雪瓶。
春雪瓶只腼腆地笑了笑,没吭声。
罗小虎咧开大嘴笑了,笑得是那么得意,又是那么自豪。他边笑边又自言自语地说道:“有了这样的女儿,还要儿子何用!”
罗小虎又和布达旺老爹谈了一些乌伦古湖那边的情况后,眼看天色已晚,就把帐篷留给春雪瓶,他二人便抱着一卷布幔到灌木林里过夜去了。
第二天天刚亮,罗小虎便提着一篮食物进帐来了。春雪瓶心里惦挂着母亲,吃饭时也显得心绪不宁。罗小虎已经看出来了,便对她说道:“你兴许是在惦挂母亲了。一会儿等你乌都奈叔叔回来,我就送你上路。”
春雪瓶一听他提到乌都奈,便想起失马的事来,心里总感有些不快!说道:“那夜算他走运。我要不是倦了,岂容他盗得马去!
兴许他今天也回不来了。”
罗小虎笑了:‘你这就有些像你母亲的情性了。常言道‘吃一堑,长一智,这对你今后行事也有好处,你就别老记在心上了。”他见春雪瓶没应声,又说道,“再精明的人也有失误的时候,就连你母亲早年也曾被人从她身边把马盗走过。”
春雪瓶又一次感到惊异了。母亲在她心里简直有如不容稍犯的天神一般,谁敢从她身旁盗走坐骑?!她正想问个究竟,帐外忽又传来一串蹄声。罗小虎闻声而起,说道:“你乌都奈叔叔回来了。”他随即匆匆走出帐去。
一会儿,他和乌都奈一同回到帐里,乌都奈瞅了瞅春雪瓶,嘴角微微弯了一弯,也分不清是笑是讥,他只举了举手,淡淡地说了句:“误会,误会!”随即便转脸和罗小虎谈他这次去给布达旺老爹筹粮的事情去了。
春雪瓶只冷冷地盯着他,心里已经消失了的不快,又被他那似笑非笑、似讥非讥的神态引了起来。
乌都奈和罗小虎谈了片刻,又回过脸来瞅瞅春雪瓶,说道:“你也别介意。听说你也是为还马而来,只当我代你还了,也省去你再到乌伦古湖去的许多路程。”
罗小虎将乌都奈的肩膀一拍,半打趣半认真地说道:“乌都奈,你行事也人粗心,动手前也不打听她是谁来!你要是早知她是飞骆驼,我量你也不敢下手了!”
乌都奈不禁将舌头一伸,惊异地望着春雪瓶,顷刻问,他脸上那冷冷带刺的神情竟一扫而光,换上的却是满脸钦佩的笑意。他用手摸了摸自己的脑袋,也半搭汕半认真地说道:“我要早知她是飞骆驼,我就当面向她讨还,也不用去盗了。”
春雪瓶也不觉笑了起来。一瞬间,她心里的不快竟又消失得无影无踪。
罗小虎走到帐篷门前探头看看天色,又回头对春雪瓶说道:
“天已大亮,你也该上路了。”
春雪瓶便提起革囊跟他走到帐外,见大红马身旁拴着一匹又高又大的大白马。那马通身无一根杂毛,胸宽腿曲,蹄颈细似蜂腰,项上鬃须未剪,散垂飘拂,神采非常。春雪瓶正在惊讶,罗小虎已牵着白马来到她的面前,对她说道:“这马是我从界外来犯的一个头目手里夺来,我已骑了它三年,脚力不比这大红马差,让它送你回天山去,你就把它留在身边,也算我的一点心意。”罗小虎也不等春雪瓶应声,又伸手拍拍白马,对它说道:“跟这姑娘去,比跟我更强!我也放了心,你也走了运。”那白马也好像听懂了他的话似的,点点头,又刨刨蹄。.
春雪瓶刚刚闪起推辞的念头,但她还未说出口,却立即又感到这情意是不能推辞的。她迅即将犹豫转为灿然一笑,随即一躬身,说道:“雪瓶就拜领了!”
春雪瓶辞过罗小虎,正要纵马离去,罗小虎忙又来到她身旁,拉住她手里的缰绳,眼里含满了眷眷之情,仰望着她深情地说道:
“雪瓶,好好侍奉你母亲,凡事别惹她生气,不用多久,我随后就会寻来的。”
春雪瓶也觉心里有些难过起来,只点点头,随即一纵马飞驰过草地,直向天山驰去。
春雪瓶在马上一会儿惦念着母亲的病体,一会儿又琢磨这些天来发生的种种事情。她一念及母亲,便心急如焚,把马催得快如流星;一想到罗小虎要去天山的事来,却又忧虑重重,心里也忐忑不安。她暗暗思忖着:反正自己又没有将住处泄告给他,等他寻来也将是许多天以后的事情,自己不如就在这些天里,相机试试母亲,只要母亲不愠不恼,便索性将真情告她,劝她回过心意:若母亲一听便发起怒来,自己只好装着不知,等他来时再作道理。春雪瓶主意已定,便一路兼程进发,不两日便已穿过河谷,来到天山脚下。
春雪瓶一阵心喜,抬头向那最高的一一座峰顶望去,忽见那皑皑的雪峰顶上,站立着一个人影,正在向山脚眺望。春雪瓶知道那人准是母亲!她立即高兴得在镫上站了起来,挥舞着手臂,向着那遥遥的峰顶高声呼唤着:“母亲!母亲!我回来了!母亲!”她明知这声音还远远传不到母亲耳里,可她还是不停地挥着手,高声呼唤着!
白马驰上山腰,又绕进山谷,雪峰被眼前的山崖挡住了。春雪瓶也不顾山道崎岖险滑,只催马向天山深处的那间木屋赶去。又经过长长一段难熬的时刻,春雪瓶终于回到了木屋门前。她一边呼唤着“母亲”,一边匆匆将马一拴便向屋里奔去。屋里却不见母亲身影。她又返身跑到林里,也未见母亲踪迹。春雪瓶忙又绕过树林向峰顶跑去。她来到峰顶,果见母亲仍然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好像已成冰冻一般。春雪瓶不觉心里一颤,忙轻轻走到她的身旁,又轻轻呼了一声“母亲”。母亲仍然一动不动,竟好似气息都已全无。春雪瓶吓得心里直抖,忙转过头去察看母亲的面孔,只见母亲那雪白的脸上,挂着两行晶莹的泪水,一双好似浸在清泉里的眼睛,正凝望着山下远远的地方。春雪瓶忙顺着母亲的视线望去,蓦然看到远远荒原上一匹红色的大马,马上骑着一人,正扬鞭催马,直向天山上驰来。
春雪瓶不禁在心里暗暗惊叫一声:“呀!他来得真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