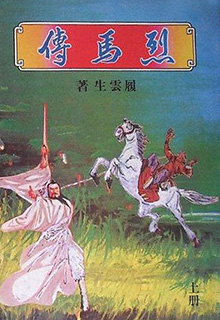看剑厅,顾名思义是“看剑”的地方。
嘱咐马小雄“看剑”的,并不是等闲之辈,而是天工堡主太叔梵离。
老太叔曾经疯疯癫癫三十年,那是一段悠长的岁月。但当这段岁月过去之后,回首一顾,一切仿如只是昨天发生的事情。
看剑厅中,再无别人,除了马小雄之外,便只有巨案上几百把长剑。
在每一把剑的背后,都曾经有不同的主人,不同的故事。有些剑,剑鞘比剑的本身贵重百倍,那是权贵中人、富家子弟藉以炫耀的装饰。
其中一把剑的剑鞘,上面总共镶了二百三十六颗大大小小的宝石,就算在白天携带着,都足以令人为之目眩,眼花撩乱。
但剑鞘里的“宝剑”,仅比一般凡铁略胜,跟“无坚不摧”四字,相差千千万万里,又有一把剑,剑鞘要是沉重,原来是用“赤焰乌金”铸造,但剑刃只余下半截,显然在决斗之中给敌人的兵刃削断。
这几百把剑,每一把都很有来历,但马小雄是绝不可能就此看得出来的。
正午,送饭的人来了。
饭菜不好。
饭是用劣等糙米煮成的,下锅的时候水太少,饭粒很硬,要是牙齿不够牢固,也许会给这些硬饭震得连牙齿都松脱下来。
因为饭粒不但生硬还混杂着砂子。
菜也不好,两三块炸得焦透了的猪肉,伴着一堆不知道是什么菜的菜,咬下去又咸又苦,很不是味道。
但马小雄还是很快就把这些饭菜扫光,然后把碗筷放在饭蓝里。送饭的人冷冷地瞧着他的脸,马小雄又再专注地在看剑。
送饭的人,正是脸上是一直戴着面谱的姹紫。
姹紫忽然道:“在这巨案上面,有一把剑,原本是属于我的。”
马小雄立刻在巨案上取出一把剑,端起仔细地看了又看,道:“是不是这一把?”
姹紫默然片刻,问道:“你怎知道就是这一把?”
马小雄道:“剑鞘上有你的名字?”
姹紫颔首道:“不错,这是我的剑,嫣红便是给这把剑刺死的。”
马小雄道:“为什么要杀她?”
姹紫道:“你已问过。”
马小雄道:“但你从没回答过。”
姹紫道:“你若想知道真相,除非能在剑法上击败我。”
马小雄吸一口气,缓缓道:“我是东蛇岛主水老妖的义子,义父教我练的是刀法。”
姹紫道:“堡主曾经问你,你可知道,刀和剑的分别?你心中是否有了答案?”
马小雄摇摇头,说道:“我不知道。”
姹紫道:“你不知道,那是因为你真的不知道,但就算有一天你知道了,也不一定愿意说出来。”
马小雄笑道:“何以见得?”
姹紫道:“因为剑道出于人心,而人心,永远都是最难捉摸的。”
姹紫的面谱,并不是狰狞可怖的。她的脸谱,眉毛细而弯,鼻骨高挺,嘴唇小巧,色泽有如年月久远摆放了几十年的象牙。
她接着又道:“除了我这个送饭者之外,这座看剑厅已被列为堡中禁地,谁也不能擅自进入,就连你师姊也不例外。”
马小雄道:“太叔堡主是个怎样的人?”
姹紫道:“在他离开堡垒之后的三十年,我不知道他变成怎样,但在天工堡,人人都知道,堡主的命令,就像是一座大山,永远深沉、有力、绝对没有人敢违抗。”
马小雄道:“要是有人违命又怎样?”
姹紫道:“赠‘违命词’一首,必须立刻吞服。”马小雄听了,为之莫名其妙。
姹紫忽然曼吟:“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马小雄微微皱眉:“这是南唐李后主的‘虞美人’,意境甚是悲凉。”
姹紫道:“李煜战败之后乞降,被宋太祖封为‘违命侯’,这种爵号,明显是在侮辱这位末代皇帝。因此,后世也有人称李煜在亡国后所著作的词,谑称为‘违命词’。”
马小雄长叹一声,道:“要是在天工堡违抗堡主的命令,便会获赠‘违命词’,并且必须立刻吞服,那么,这一首词,恐怕必然是淬上剧毒了?”
姥紫道;“不错,而且是一种非死不可,但偏偏却又死得很缓慢很痛苦的毒药。”
马小雄道:“你恨不恨堡主?”
姹紫道:“你知道我恨太叔堡主吗?”
马小雄道:“太叔堡主要你戴着面谱做人,你憎恨他也不是奇事。”
姹紫似是怔呆良久,才慢慢地点了点头,说道:“不错!我很憎恨太叔堡主,但却不是因为脸上罩这块面谱。”马小雄没有再问下去。
但他总算在这年华老去的婢仆身上,知道太叔梵离过往的威严和手段。
然而,马小雄并不感到惊讶。在他心中,老太叔从来都不是宅心仁厚的长者。诚然,他已疯疯癫癫的活了三十年,在这三十年中,给他残酷地撕开五大块的武林中人,着实不知凡几。其中固然不乏罪有应得之辈,但却也有一些死得不明不白,极是冤枉。尤其是拜他为师的徒儿,全都一一惨死在他的手下。
姹紫提起饭蓝,默默地离去。
马小雄怔呆了很久,把姹紫的剑看了又看,仿佛要看穿当年姹紫何以要刺杀嫣红的秘密,但一把长剑,永远都是冷冰冰的,而且永远不会说话。
如此这般地看剑,又有什么用处?
及至黄昏,马小雄想起了“大盈若冲五楼”内兵器架上一束一束的死人头发,一想及此,自然而然地朗吟:“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诎,大辩若讷。躁胜寒,静胜热,知清静以为天下正……”这是老子真言,也是东蛇派练功根基心法要旨。
其时,马小雄曾问义父水老妖:“为什么要用这些头发来练功?”
水老妖当时答道:“一束属于人的头发,乃是世上最柔韧之物事。本门练功心法,看似刚阳一路功夫;实则刚柔并济,甚至是以阴柔为本,刚强辅之……发在手中,便如执大象。
执,守也。象者,道也。须知道本无象,此言象者,以万象皆由是而兆见,故曰大象也……”
在那时候,马小雄对义父的解说,是不大明白的。
他实在无法明了,天天抚摸一束又一束的死人头发,对练功会有什么样的帮助。
同样地,到了这一天,他也不明白老太叔为什么要自己呆在这里独自一人“看剑”。
但马小雄的江湖阅历,正在一天比一天加深。到了这时候,他最少知道,无论是义父也好,是老大哥太叔梵离也好,绝不会让自己在练武的时候,做一些白费力气毫无意义的事情。
抚摸一束又一束死人头发,和观看一把又一把的长剑,骤然看来,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事。
但只要细心一想,却不难体会得到,在两者之间,其实是颇有共通这处的。
执大象,象者,道也。
同样地,“看剑”也是一种“入道”的法门。既要练剑,又怎能对“剑”这一种兵刃毫无认识?马小雄渐渐明白了老太叔的心意。
老太叔不但要马小雄认识“剑”,更要他比任何人都更深切地认识“剑”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兵刃。
黄昏,送饭的人又来了。送饭者仍然是姹紫,她的脸上仍然戴着那副色泽有如古老象牙的面谱。
这一次的饭菜,饭很软滑甘香,菜肴更是炮制精美,极是可口,和正午的一顿饭截然不同。
但很奇怪,马小雄只是扒了一两口饭,吃了一点点菜、肉,便把碗筷放回饭篮之中。
姹紫道:“为什么不再吃?”
马小雄道:“胃口不太好,不想吃。”
姹紫道:“这便是剑道。”把饭篮提起掉头便走。
晚间,看剑厅灯火通明,如同白昼。把灯笼一盏一盏燃亮的,是不再发笑的笑童。他道:
“我只负责点灯,其余事情,不要追问。”马小雄果然沉默不语。
哭童不再哭,笑童也不再随便地笑。还有,天工堡主已不再疯癫……倒是马小雄,忽然有着啼笑皆非的感觉。
人人都在变,他自己又怎样?
巨案上,百剑纷陈。
一把巨剑,连剑柄以至剑刃,呈金黄色泽。细看剑锷,镌有“王者”二字。
竟是王者神剑。(二百年后),此剑落入白眉神捕谭四之手,凭藉此剑,群邪辟易,成为六扇门中最备受触目之风云人物。
又有一剑,名字十分怪异,曰:“奘奘。”这便是二百年后,权势堂八大长老中,排名第六“请你杀了我”魁王“铁剑入臂”的“奘奘大铁剑”。 (详情请阅<三少爷的刀>卷六。)
这两把都是巨剑,尤以王者神剑更甚。
马小雄左手执王者,右手拿奘奘,臆胸间似在卷起千丈怒涛,豪情洋溢不能自己。
在看剑厅看剑,看的不只是剑,还有江湖人、江湖事、江湖情。
一把剑,在它的昨天,曾经发生过什么事?到了明天,又会如何?
将来是否一沉不振,金剑沉埋?
还是剑气盘龙,押一手惊天动地震人心弦的赌注?
马小雄睹剑沉思,进入了冥想境界。在这境界中,人剑已溶为一体,从眼睛向前直望,那是平滑、冰冷、寒芒四射的剑刃,剑刃末端,是剑尖,剑尖以外,是三山五岳、五湖四海,既是杀戮战场,也是群临天下,无人能与争锋之王者气象。
不知不觉,马小雄沉沉入睡。
梦中,梦见一个总是忘不了的女孩。
但这女孩,并不是一般的女孩。她的一双小手白净嫩滑,动不动便双手擦着眼睛哭得十分起劲。
她便是小尼姑小霜。
虽然只是在梦里“遇见”小霜,但马小雄还是嗅着一种令他心神一荡的少女体香。
既在梦里梦见小霜,这一觉也就睡得很是香甜。梦醒后,也嗅到一阵少女身上散发出的醉人幽香,睁眼一看,却不是小尼姑小霜,而是阿玫。(本篇小说可在公开免费的网站自由转贴。如果读者是在收费会员网站看到这篇小说,说明该网站寡廉鲜耻,把免费的东西拿来骗钱。共唾之。)
马小雄真是“如梦初醒”,失声道:“怎么是你?”
阿玫道:“为什么不是我?你在梦里看见的是谁?”
马小雄讪讪一笑:“除了阿玫师姊,又还会是谁?”阿玫怔怔地看着他,轻轻叹了口气。
这时,天色已渐渐明亮。
马小雄看着她的脸庞,道:“你不相信我的话??
阿玫道:“我相信与否,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自己是否感到愉快。”
马小雄沉默下来,随手在巨案上拾起一把看来平平无奇的长剑。
阿玫忽道: “这里已被太叔堡列为禁地,除了给你送饭的人,任何人不得擅进。”
马小雄道:“就连你也不可以吗?”
阿玫道: “本来是不可以的,但我曾经见过太叔堡主,亲口答应了一个条件,始能破格通融。”
马小雄一凛,道:“你答应了什么样的条件?”
阿玫道:“从今天开始,三年之内再也不能跟你会面。”
马小雄听了,又惊又怒:“怎能这样?不!这话作不得数,我要见老太叔!”
阿玫冷冷一笑,道:“就算你跟太叔堡主怎样说,事情早已铁定。我虽然是个小女子,但既已答应了太叔堡主,就一定不会反悔。”
马小雄怒道:“这是什么道理?”
阿玫道:“师父传授我的剑法,我不能每隔三两天随便练练便算,在这三年之内,我必须在一处清静的地方潜心苦练,不能辜负师父的期望。”
马小雄呆了半晌,道: “是你自己要练剑?还是不想阻扰我在这里练武功?”
阿玫道:“随便你怎样想更怎样想。总而言之,我既已答应了太叔堡主,在三年之内,绝不会偷偷的和你见面。”
马小雄握着她的手,欲言又止。
阿玫深深吸一口气,忽然用力把他推开,道:“男子汉大丈夫,切勿拖拖拉拉,优柔寡断,三年之后,咱们再见吧!”掉头便走,走得比鹿小更急更快。
阿玫窈窕的身影甫自看剑厅外消失,戴着面罩的姹紫已紧接着走了进来。为马小雄送上一盆热水,让他好好的洗个脸,漱漱口,然后再吃早点。
姹紫道:“今天大清早,你已看过美丽的师姊,如今便是全神贯注看剑的时候。”
马小雄苦笑一声,道:“很好!师姊练剑,师弟看剑,三年之内,师姊师弟不相往来,保证天下太平,诸事大吉。”
闽北丐帮分舵舵主,已于日前往一场战阵中身亡,把这位舵主杀害的,是豪门金庄之中,号称“太原太岁”的葛绝户。
依照惯例,立刻由副舵主暂时递补舵主空缺。
这位暂代舵主的丐帮弟子,背负六袋,年约四旬,个子矮小,但练的却是丐帮外门武功“钢臂斩”。
此人外号“钢臂神乞”,姓徐名仲豪,性子火爆,不畏强权。
这一天,徐中豪在分舵破屋之中,出奇地冷静布置阵势。
两日前,一个少女,咬紧牙关;筋疲力竭地把“公子丐”濮阳天背到分舵,才抵达分舵破屋门外,二人已双双一齐倒地。
濮阳天是丐帮帮主,身份是何等地尊崇。谁也想不到,丐帮帮主竟然会给一个妙龄少女背着,更身受重伤,生死未卜。
徐中豪这一惊非同小可,急急调动帮众,一方面全力抢救帮主性命,另一方面严阵以待,唯恐敌人趁机侵袭。兹事体大,分舵中众弟子,不论地位高低,也不论年纪老嫩,谁也不敢掉以轻心。
阿婉背着濮阳天,艰苦支撑,终于到了丐帮分舵,始全身虚脱倒下。
但她只是疲累过度,很快已复原过来。
但濮阳天饱受重创,甚至一度心跳停顿。
其后,阿婉把忘忧谷中最具灵效的救命丹药嚼碎喂服,濮阳天方始恢复了微弱的呼吸和心跳。
阿婉苦苦支撑,她告诉自己,也告诉濮阳天:“不要死在这里,也不要今日便死。丐帮逾万弟子,全仗你一人支撑大局,你若死了,丐帮怎办……我又怎办?……”她没有哭,没有掉泪,只是拼命背着濮阳天,咬紧牙关一步一步向前走。
前路茫茫,但她有信心,一定可以熬得过去。终于,在八个时辰后,她憔悴地来到了分舵。
徐仲豪立刻延召名医,无论如何一定要保住帮主性命,一连两日,方圆三百里的老医士、神医、妙手大夫统统都给拉到分舵,群医会诊,七嘴八舌,药方堆积如山。
但无论怎样,濮阳天并无起色,始终气若浮丝,群医人人摇头晃脑,面有忧色。
又过了半天,夜幕低垂,分舵破屋门外,忽然响起阵阵磨刀之声。
磨刀的是一个白发老道士。他背负长剑,腰间挟着一根拂尘,佝偻着背在破屋门前磨刀。
白发老道士磨的是一把小刀,全刀长仅四寸,柄寸许,刀刃两寸许,而且看来锈迹斑斑,绝不锋利,若在平时,如此一名老道,绝不会令人感到大惊小怪。
但此际非常时期,分舵群丐,谁也不敢掉以轻心。徐仲豪闻讯,亲自出门看个究竟。
白发老道士蹲在门外,双目半开半合,似乎除了磨刀之外,世上再也没有任何事情值得关注。
徐仲豪瞧了半晌,忽然抱拳道: “这位道长,敢问是否来自武当山?”
白发老道士继续磨刀,但却点了点头,道: “不错,贫道何五冲,徐舵主果然好眼力。”
徐仲豪道:“原来是何真人,俺早已久闻大名,不意今夜有缘相见,但未知真人何以在此地磨刀?”
何五冲道:“贫道是武当派中人。武当剑术,天下皆知,但是否用剑之人,便不能用刀?
磨刀?”
徐仲豪道:“真人此举,必有深意,尚祈明言。”
何五冲这才缓缓地站直身子,道:“这一把刀,虽然又细小又生了锈,但徐舵主可知道它的来历?”
徐仲豪道:“请恕徐某孤陋寡闻。”
何五冲道:“贫道虽然是出家之人,但却喜欢喝酒吃肉,二十年前,贫道的一个好朋友生日,邀约贫道在黄鹤楼头,生火烤肉大快朵颐。
“贫道生平最重信诺,任何大小约会,绝不迟到。但那一次,贫道在途中遇上契丹铁骑,更目睹契丹武士屠村杀害无辜之惨剧。
“贫道无法袖视,仗剑冲入村中跟契丹武士周旋。一场血战,贫道虽然杀了二十余名武士,左臂却也中了一箭,敌人更是另有援手,自村庄另一方奔杀过来。
“贫道寡不敌众,本拟逃之夭夭,正如江湖中人常道:留得青山在,那怕没柴烧。但说句实话,心里很不愿意就此一走了之,只恨老牛鼻子不曾长出三头六臂,跟敌人拼命到底。
“便在这时,一人从横里杀出,手持一根打狗棒,神勇无匹,那些辽狗在棒下无不脑浆四溅,咽喉洞穿,心脏爆裂一一惨死。
“忽然天降强援,贫道立时精神大振,也仗剑杀入敌阵。
那一场厮杀,真是说不出的痛快。不到半个时辰,所有契丹武士都已给咱们二人杀个片甲不留。
“直至最后一名辽狗倒卧下去,贫道也已支撑不住,原来那一支箭,竟然是喂上毒药的。
“贫道以为死期已届,心想最好立时晕迷不醒,就此长眠呜呼哀哉去也,免得饱受毒发折磨之苦。
“岂料贫道虽已倒卧在敌人尸首旁边,但却并未就此死去,甚至不曾晕倒,只是眼睁睁地瞪着辽狗的尸首在苦笑。
“不久,那辽狗的脑袋给一把大刀砍了下来,取而代之的,是另一张粗犷可笑的脸。
“当时,我不知道这人是谁。普天之下,也许只有我这个老牛鼻子认为他这张脸十分可笑。
“这张脸为什么会令我感到可笑?是不是因为在这张脸的脸颊上,有太多辽狗的脑浆和辽狗身体上进裂出来的肉碴子?
“我很疲倦,疲倦得不想活下去。但这张可笑的脸对我说道:‘要是不立刻把毒箭拔出,不到今晚,你便是变成一个死道士。’
“我哈哈一笑,从身上掏出一块又干又硬的炒米饼放入口中。这种炒米饼虽然干硬得像是冬天的石头,但却香甜可口,比烧鸭烤肉还更好吃。
“但才放入口,贫道就知道自己的舌头完全麻痹。我完全感受不到炒米饼的香气和甜味,只觉得舌头以至舌根,都比平时肿胀一半以上。
“这人给了我一壶酒,叫我一口气把它喝掉。我闻了一闻,这壶酒也和炒米饼一般,毫无香气可言。但我还是喝了,因为我虽然闻不到酒的香气,却还是可以用眼睛看得出,这确是一壶好酒。
“就在我仰首喝酒的时候,这人已把毒箭拔了出来。只见箭镞上的血是黑色的,看来不像是血,只像是磨得浓浓的墨汁。
“我是武当派的牛鼻子,在武当派中,不乏治疗伤毒的灵药,但我知道,单是靠武当派的灵丹妙药,绝对救不了自己。
“这人瞧瞧我的伤口,说道:‘毒药已渗入肌肉,要把毒力消解,除了要服一些解毒灵丹这,还得用刀子把伤口内的肌肉剜掉二三两。’“我立刻在地上抓起一把辽狗使用的大刀,递给这人,道:‘快动手。’他把大刀抓在手里,哈哈一笑,刀刃忽然寸寸碎裂。
“他道:‘这种刀,只能用来切割猪肉。’我叹了口气,道:‘贫道太瘦,配不上这种猪肉刀。’这人大笑,亮出了一把四寸小刀,不由分说便向我身上伤口剜割下去。
“关云长刮骨疗毒的事迹,贫道是耳熟能详的。要是这人也用刀子刮一刮贫道身上的骨头,贫道宁愿立刻死掉。幸好这人只是剜割贫道的肉,要不曾在骨头之上用刀子刮来刮去。
“这人并不怎么老实。他分明说只是剜掉我身上二三两肉,但照贫道看,最少给他剜了五六两。
“徐舵主,这便是当年为贫道剜肉疗毒的刀子,幸好那时候它还没有生锈。”何五冲说到这里,把四寸长的小刀递给徐仲豪。
徐仲豪深深吸一口气,道:“这是濮阳帮主的‘四寸割狗肉刀’……当年,为何真人剜肉疗毒的,便是濮阳帮主!”
何五冲叹道:“二十年来,一直不知道这把小刀的名宇,如今总算是真相大白,嘿嘿……
好刀!真是好刀!”
徐仲豪道:“既是帮主故人,请道长内进一叙。”
何五冲进入破屋,穿过天阶,右侧有一池绿水,池边站着一名少女,神情委顿,面色苍白。
何五冲趋前问道:“姑娘怎生称呼?何事愁容满面?”
少女欠身道:“我叫阿婉,是濮阳帮主的……朋友。”
何五冲“哦”的一声:“原来是阿婉姑娘,贫道武当山何五冲,也是濮阳帮主的朋友。”
阿婉道: “濮阳帮主身受重创,道长可愿意救他一命?据说武当派的炼丹本领十分了得,想必有办法把他救活过来。”
何五冲道:“你吃不吃烤肉?”阿婉不明所以,瞠目不知如何对答。
何五冲又问道:“你可知道什么地方有最好的蜂蜜?”
阿婉道:“距离此地三百里,有一座花蜂谷,谷主花甜儿。名字像个女孩,却是须眉男子。擅养蜜蜂,该谷所产之蜂蜜,种类繁多,味道特别甜美。”
何五冲大喜:“好极了!且待贫道把濮阳帮主救活过来,然后咱们一起到花蜂谷找寻最好的蜂蜜。”
阿婉心中嘀咕,忖道:“一会儿要吃烤肉,一会儿要找最好的蜜糖,完全风马牛不相及。”她可不知道,何五冲找寻最好的蜂蜜,正是要用上等的蜜糖醮在肉食之上,然后烤火烧熟来吃。
武当派道士之中,以何五冲的性子最是奇怪。尤其是在这二十年来,他绝少在武当山逗留,总是四出云游,喜爱结交天下豪杰,有酒便喝,有肉便吃,有祸便闯。
在徐仲豪引领之下,何五冲终于看见濮阳天。
平时,相貌堂堂眉目凛凛的“公子丐”濮阳天,在此刻似已变作了一具尸首。
何五冲在破烂的床边怔怔地瞧着他,脸上的神情似笑非笑。
阿婉心中焦急,忍不住追问: “道长,要怎样才能把他救活?”
何五冲反问道:“阿婉姑娘,你可知道贫道怎会找到这里来?”
阿婉一呆,摇摇头道:“不知道。”
何五冲道:“今天清晨,贫道在一条村庄里喝茶,茶馆中的顾客,人人都在谈论丐帮帮主身受重伤,丐帮弟子四处找寻名医之事,因此才会急急赶来。”
何五冲说到这里,目光一转,瞧着徐仲豪的脸:“如此说来,相信已有不少名医为濮阳帮主把过了脉吧?”徐仲豪连连点头称是。
何五冲道:“既有无数名医为濮阳帮主把过脉,也有无数药方一一开了出来,事到如今,境况怎样?”徐仲豪没有开口回答,只是摇了摇头,一脸无奈。
何五冲又道:“一个人若是生了病,最重要的,首先是要很清楚地弄清楚,病人患的是什么病。要是连患病的情况都糊里糊涂,又怎能对症下药?”
徐仲豪道:“帮主并不是患病,而是给敌人暗算中了一指。”
何五冲道:“天下间有多少种指法?”
徐仲豪道:“拈花指、一阳指、迦叶指、六合指、合一指、太阳指、凤凰指、白玉指、飞虹贯日指,还有咱们丐帮要饭的手指指……”
何五冲挥了挥拂尘,道: “够了!够了!说了一大堆,还没说出贵帮帮主中了的是什么指法!”
徐仲豪苦笑一下,道:“普天之下,练武之士所练的指法可算是五花八门,种类繁多,一时之间,又怎能逐一细说?”
何五冲道:“普天之下,毒性猛烈的毒蛇,种类也同样多得不可胜数,要是给毒蛇一口咬中的人,连毒蛇是那一种都不知道,又怎能立刻对症下药,及时抢救?”
徐仲豪面红耳赤,汗流夹背地说道: “真人所言极是,咱们帮主中的是那一门那一派的指法?”
何五冲道:“我也不知道。”众人闻言,都不禁为之呆住。
徐仲豪性情火爆,再也按捺不住,粗着脖子叫道:“道爷,这岂不是耍玩咱们这些穷叫化吗?”
何五冲奇道;“我什么时候说过知道濮阳帮主中的是什么指法?濮阳帮主头上又不曾留下字句,贫道又怎知道他中的是什么指法?只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照我这个老牛鼻子看,要救活丐帮帮主,倒也不是什么难事。”
徐仲豪沉声道:“道长有何妙药?请快快告知。”
伺五冲道:“徐舵主可算是妙人,贫道究竟是真人?道爷?道长?还是个连屁也不如的老混蛋?尚祈徐舵主爽快直说。”显然对徐仲豪前恭后倨的态度甚为不满。
徐仲豪闷哼一声,一言不发。
何五冲嘿嘿一笑,道:“实不相瞒,以濮阳帮主刻下沉重的伤势,便是找到了天下第一流神医开方抓药,也不济事。”
徐仲豪怒道:“这岂不是药石无盐,非死不可吗?”
何五冲道:“若用一般的药草,以至是天下间最神妙无方的仙药仙草,都不济事。要救活濮阳帮主,只能用最普通的药,配以最痛快淋漓的法子。”
徐仲豪两眼翻白,怪叫道:“老道爷,求求你别卖关子,究竟要怎样才能把咱们的帮主救活?”
何五冲道:“贫道要用的,既不是药,却也是药,而且是世间最好的一种。”
徐仲豪本来并不是个笨人,但这时候,他忽然感到自己真是笨得不能再笨,恨不得一头把自己的笨脑袋砸在石壁上活活撞死。
他完全没法子想得出何五冲说的是什么药。
既不是药。
但也是药。
更是世间上最好的一种。
这算是什么样的一种药?这道爷又是那一种稀奇古怪的道爷?
但阿婉却已明白过来。
她对这位徐舵主说出了一个字,那是“酒。”
------------------------------
drzhao 扫校, 独家连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