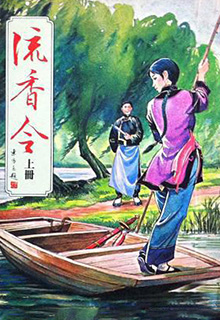局势令人惶然,惟大英雄泰然置之。
笑谈用兵,决非徒然把千万将土性命付诸一笑。只是镇静行事,凭籍才干、见识、胆量、武功、智谋亲自与敌人短兵相接,又或者是决胜干里以外。
杨缺无惧黑木堂。只是,长久以来,神鹫是明教羽翼,黑木却是祸路。
杨缺目注着神色森冷的神鹫教主齐布辛,道:“黑木堂倘有异动,本教在燕京、太原府、以至长安分坛兄弟,应有警觉。”
齐布辛道:“自从三十年前,本教西北十三分堂于煎茶溪大破黑木堂六旗魔军后,黑木堂中人的行踪,更是隐秘,要洞悉今之黑木六旗军行藏,恐怕绝非易事。但老夫却自丐帮济南分舵那边,获悉萧博已到了采石矶一带,事态并不寻常。”
杨缺道:“采石矶虽与济南相距甚远,但丐帮消息灵通天下第一,犹在本教之上。要是丐帮济南分舵万者叫化获此喜讯,在丐帮而言,绝不是什么匪夷所思的怪事。”
齐布辛道:“采石矶原名牛渚矶,位处长江东岸,江面狭窄,形势险要。”
杨缺缓缓地点头,道:“自古江南有事,由此渡江者十居七八。萧博本是契丹高手,但其父母妻儿,皆丧命于辽帝之手。虽已事隔数十载,但萧博痛恨耶律氏族极深,立誓投身于金人之下,终于成为黑木堂中身份最是尊崇之老供奉。”
齐布辛叹道:“萧博虽是契丹人,但少年时跟随兄嫂在江南定居,更迭有奇遇,既习武也修文。其人博古通今,武功盖世,可借此人投身黑石堂,未能为你我所用。”
杨缺微一沉吟,道:“萧博固是良材,但生性桀傲难驯。黑木堂有这样的一位老供奉,究竟是祸是福,恐怕尚是言之过早。”
齐布辛道:“据探子回报,完颜亮近来集结大军,厉兵袜马,前锋营战将矛头,已直指淮河彼岸。”
杨缺道:“江淮守将王权,谋略不足,胆色犹弱,金人大军掩至,势难抵御。”
齐布辛叹道:“一旦淮河军土望风而逃,江南危矣。”
杨缺道:“事已至此,策将安出?”
齐布辛道:“朝纲腐败,好党满朝,以老夫愚见,如此江山,姓赵的狗皇帝根本无法稳守。”
“最痛快的法子,莫如杀入京师,把狗皇帝乱刀剁成肉酱,继而号召天下豪杰重组文武两班大臣,把完颜亮这条金狗赶回长白山去。”
说得慷慨激昂,神鹫教麾下战将,无不喝采叫好。
只有杨缺,神情淡漠,轻轻咳嗽两声。
齐布辛不由苦笑,接着说道:“但以当年方腊起义声威,尚且不免惨淡收场,老夫适才之言,兄弟们听过便算,休要放在心上。”
杨缺道:“说到造反,我身为明教之主,那是丝毫不必忌讳的。自本教于中土立足以来,那一朝的皇帝老子不欲啖吾人之肉,喝吾人之血?只是,女真铁骑凶残暴戾,一旦席卷江南,少说也有千万生灵涂炭。为了这无数家园无数性命的生死存亡,咱们决难袖视。”
齐布辛低声道:“杨教主所言甚是。”
杨缺沉吟半晌,说道:“萧博既已到了皖南,黑木堂六旗魔军少说也有一两旗高手左右相随,这一场热闹,咱们不妨走去瞧瞧。”
齐布辛道:“教主主意既决,务当召集四坛坛主,齐赴皖南翠螺山麓。”
杨缺道:“青龙坛、白虎坛、失雀坛三位坛主,相距皖南之地极远,不必强行召唤。只须告知玄武坛之彭真人便可。”
彭真人,本名彭复生,生性豁达,喜欢云游四方,救济众生。
彭真人在少年时已属明教弟子。年四十三,成为玄武坛主,剑法独树一帜,江湖上罕逢敌手。
翌日清晨,杨缺带着戚雪珍,联同神鹫教主暨一众高手,向东南方进发。
三日后,首先到了洛阳。
泪阳位于豫西,历史悠久,有“九朝古都”之称。
洛阳又是著名之牡丹花都,“洛阳牡丹甲天下”,千百年以来一直闻名遇迄。
其时,金兵南下犯家之消息,已在洛阳城中不径而走。但市面仍然平静,杨缺带着众人,来到了城北金叶胡同左侧一间大屋,原来这里便是明教洛阳分坛所在。
洛阳分坛头目,姓吕,名锦棠,年约五十出头,每口皆以一人之力,把一项紫缎软轿当作兵刀一般,在屋内天天舞来典去。
这一日教主亲临,吕锦棠大是亢奋,在杨缺面前把软轿抛上半天,然后纵身一跃文二,把软桥一脚飞踢至屋檐上。
杨缺哈哈大笑,身如流星,紧贴着紫缎软轿追上屋檐。软轿斜斜地挂在屋蓬瓦顶间,杨缺也斜斜地坐在轿兜之中,似乎连人带轿立时便要堕下,但过了中,但笑不语。
吕锦棠恭请众人进入大厅,杨缺是教主,自是位居首座。
此时,已近黄昏。吕锦棠嘱咐门下第子生火送饭,煮的都是素菜,泡制功夫粗枝大叶,仅堪糊口。
饭后,杨映在偏厅掌灯聚众,商讨近来形势。吕锦棠道:“两三日前,洛阳城内出现了一些来历不明的武林人物,有些似是正道盟中人,有些似是黑木堂的兔息于,也有些身份神秘,谁也瞧不出究竟是什么名堂。”
齐布辛冷冷一笑:“在这兵荒马乱时候,居然还有这许多灰孙子老王八来凑热闹,真是莫名其妙。”
成雪珍心中暗自好笑:“你老人家也不是来凑热闹吗?这算不算是其中一个老王八?”
转念一想,杨缺说不定也可算是个灰孙子,不禁忍俊不禁,“嗤”一声失笑起来。
齐布辛脸色一沉:“戚姑娘,什么事情值得发笑?”
戚雪珍心中有气,这神鹫教主,果然是说不出的老气横秋,侍老卖老,一气之下,便道:“每逢看见喜欢凑热闹的老王八,我便会忍不住笑起来。”
齐布辛双眼一翻,正待发作,杨缺忽地一声猛喝:“是谁在窗外鬼鬼祟祟?”他才说出了三个字,齐布辛已破窗而出,一掌击向窗外鬼祟地窥听之人。
那人阴恻恻一笑,毫不退避,轻描淡写的挥掌相迎。
齐布辛是神鹫教主,他这一台便是威力无伦的“惊王金翅神掌”,只消用上五成力造,已足以横扫半边武林。
岂料窗外那人,竟是武林一代大宗师,两掌相交,齐布辛淬然后退,他破窗而出,却倒转过来破墙倒退回偏厅之内,霎时间砖石横飞,泥屑有如烟雾般四下弥漫。
这一着变化,大出众人意料之外。又有谁能料到,神威凛凛的神鹫教主,竟会在一个照面间弄致如斯狼狈境地?
但齐布辛不愧是临敌经验老到的江湖巨擘,虽然这一掌相拼的结果大大出人意表,但在倒退破墙之后,仍能抱元守一,神情冷静地稳住脚步,既不急于反扑,也不惊煌失措目乱法度。
尘屑渐渐落定,偏厅砖墙已坍塌了一大块,在碎砖之上,缓缓地踏出一个人沉稳的脚步。
只见这人身穿态皮衣帽,五绺长髯,气度不凡。
杨缺,齐布辛陡地双双吸一口气。
因为这人竟是萧博。
萧博,博古通今,文武汉全,身为黑木堂惟一老供奉,论江湖地位,绝不比扬、齐二人逊色。
但谁也想不到,萧博竟在络阳城明教分坛现身,更一掌震退神惊教主齐布辛。
齐布辛持须斜眼相视,说道:“萧兄一掌先声夺人,不愧是黑木堂第一高手。”
萧博神色木然,道:“齐教主若知道窗外之人便是在下,又岂会只用上两成掌力?这一掌,算是在下捡了一个天大的便宜。至于孰优孰劣,那是全然不足以作准的。”
齐布辛脸色一沉,道:“萧兄不在采石矶,却又到了洛阳城,未知所为何事?”
萧博道:“在下只是数日前在翠螺山麓走了一遭,想不到竟把明教、神鹫教两大教主引向皖南,真是罪过!罪过!”
齐布辛道:“萧兄神机妙算,知道杨教主与老夫,必然在洛阳分舵盘桓一两天。只是,萧兄此番前来,未知有何赐教?”
萧博蓦地舒了口长气,缓缓的道:“我是契丹人,更投身于黑木堂中,齐教主何以萧兄长萧兄短相称?”
齐布辛道:“战场上的死对头,夫必便是鄙劣小人。只是各为其主,不得不拼死一战吧了。若以尊驾的才智武功,这‘萧兄’二字,我是心悦诚服地叫出来的。”
萧博道:“江湖传言,当今神鹫教主齐二,胸襟狭隘,目无余子。
但也就只有我这样的契丹人,才知道齐教主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对手。“齐布辛脸色转趋郑重,道:“闲话都已表过,你潜入明教分舵,究竟有什么图谋?”不再称兄道弟,说到底,始终是针锋相对的敌人。
萧博默然半晌,才道:“在下受人之托,要向杨教主讨取一人,尚乞杨教主能够成全。”
此言一出,众人都是不禁面上色变。
要是这番说话,出于他人之四,众人必然视为疯子。
但来者却是黑木堂中弟一高手萧博!
萧博既敢孤身犯险,必然胸有成竹。杨缺不禁悠悠叹了口气,道:“未知萧老供奉要带走的是谁?”
萧博目光一转,倏地盯在戚雪珍脸上,道:“我要向畅教主讨取的,便是这位戚姑娘。”众人听了,都大感诧异。
杨缺眉头一皱,道:“这位戚姑娘,是峨嵋剑派苦月师太座下高徒,萧老供奉何以有此一着?敢问又是受何人所托?”
萧博道:“在下曾答应那人,决不把对方身份说出。但萧某可以保证,决不会伤害戚姑娘分毫。”
杨缺冷笑道:“你要在本教主身边带走珍儿,莫非真的现我明教无人吗?”
萧博干咳一声,道:“普天之下,即今是执掌武林牛耳之少林派,也绝不敢对贵教稍有轻忽,萧某又岂有资格在杨教主面前乱吹法螺?
只是,那人曾对萧某大有恩德,今日纵使在杨教主掌下粉身碎骨,也非要冒险一搏不可。“
杨缺尚未答话,齐布辛已然厉声喝道:“你要用语言套住杨教主,逼他与你单打独斗么?”
萧博道:“明教和神鹫教若要联手合力对付萧某,原本也在我意料之内。”
齐布辛森然道:“你要讨人,我来会你!”
萧博道:“要是齐教主败在我掌下,是否会让戚姑娘跟我走?”
齐布辛陡地一呆,一时间竟是无言以对。
杨缺却在这时纵声长笑,道:“能与黑木堂第一高手公平较量,实属快慰生平之事。萧老供奉若能把我击败,大可带走珍儿。”
萧博道:“杨教主千金一带,就此一言为定!”
二人都是当世武林顶尖高手,既是有言在先,就再也不能反悔。
这一战,二人各展生手绝学,总共激烈地拼搏了七十余招。
结果,竟是杨缺败了。
就是这样,萧博在明教和神鹫教高手环伺之下,带走了戚雪珍。
戚雪珍竟是连眉头也没皱一下,便跟着萧博走出这大屋的。
在大屋子门外,早已停放着一项轿子。
在轿分左右,竟有三百余名劲装武土,垂手分立!
黑木堂绝非只有萧博一人孤身犯险!要是双方展开激战,黑木堂也许会大战上风!
但萧博此行,似乎只是为了威雪珍而来,其中真相,着实耐人寻味。
萧博离去后,杨缺、齐布辛双双走入一间密室,闭门商议。
齐布辛道:“杨教主故意败在萧博掌下,未知有何深意?”
杨缺神色凝重,道:“黑木堂萧老供奉受人之托,必须要把珍儿带走,以伯父之见,原因何在?”
齐布辛道:“黑木堂素与峨嵋派毫无瓜葛,戚姑娘与萧博应该素未谋面。但却有人委托萧博公然向杨教主讨人,可见那人必与峨嵋大有渊源。”
杨缺缓缓点头道:“说不定确是大有渊源,但也说不定是大有仇怨。要是不幸而言中,戚姑娘的处境,便会十分危险。”
语声一顿,又道:“但萧博曾作出保证,决不会伤害珍儿分毫。”
齐布辛眉心一紧:“杨教主竟对萧博之言,深信不疑吗?”
杨缺道:“萧博虽然是敌非友,但其人自有一代大宗师风范,这敌人的说话,我信得过。”
齐市辛试探地:“难道杨教主不怕这是‘兵不厌诈’之道吗?”
杨缺道:“对付一个峨嵋小辈,以萧博的身份,决不致于轻易食言。
齐布辛叹了一声,道:“说句实话,萧博是一个值得尊敬的敌人,正如他对杨教主,也同样是尊崇已极,大概,这便是识英雄者重英雄吧。”
杨缺道:“话虽如此,我总不能任由珍儿像是断线风筝般,一去无踪。”
齐布辛道:“以‘闪电蝙蝠’益名城针梢本领而言,咱们决不致失去戚姑娘行踪的下落。”
原来杨缺早已暗中命令分舱中轻功绝佳之孟副舵主跟着戚雪珍,虽然这是兵行险着,但已是惟一可行之策。
可是,三日后,盂名城竟然双目被人挖掉,更连一双来去如风的快腿,也被齐膝砍掉,由一名神鹫教弟子护送回来。
杨缺、齐布辛齐齐僵住,当世两大教派教主,同时呆若木鸡,作声不得。
往事如烟,任小琳的叙述,并未完结。
杨破天听到这里,不禁神驰物外,既是向往心仪,也是黯然迷们。
杨缺是一代大魔头?还是一代大英雄?直至如今,江湖中一直都在议论纷纷。
在温州对开江心小岛上,任小琳把杨缺、戚雪珍当年一段情史娓娓道来,其间也夹杂无数江湖英雄事绩,这一席话还没说完,已是玉兔东升,在凉如水时候。
杨破天在白天探摘了一些野果,这时候自己吃一颗,也给“美娘”
吃一颗。野果是甜的,但也是酸的,甚至是苦涩的,百般滋味,如同人生。
任小琳说到这里,把一双纤美的小足放入江水之中,轻轻洗濯。
杨破天由衷地赞美:“美娘,你是世间上最好看的女子。”纯粹出自一片赤子之心,绝无丝毫亵渎之意。
却在这时,忽听一把阴恻恻的声音,自江水中传了过来,道:“要是把她身上的衣裳剥个精光,那才是最好看的。”声音尖细恐怖,在此夜闯入静时候,不禁令人毛骨惊然。
杨破天大怒,叱道:“是谁鬼鬼祟祟在说话?”江中蓦地冒出一个人湿淋淋的身子,在银白月色之下,这张脸看来一片惨青,如同鬼魅。
任小琳吃了一惊,一掌推开杨破天,另一只手已抽出长剑,向那人的咽喉直刺过去。她这一剑,是神武宫久负盛名之“无边丝雨剑法”,剑势阴柔巧妙,凡是神武宫的女弟子,入门后三年内,必习此种刻法。
任小琳是任不群的女儿,几乎在牙牙学语之际便由父亲口授剑决,还未曾站得稳己手执木剑舞来舞去。对于这一套神妙无形的剑法,她在神武宫中素来允称第一。
但自江水里突然杀出之人,竟是身手奇高,对任小琳这神妙剑法,全然没放在限内,欺身抢前戟指一戮,已把她右肘手掌侧凹处的尺泽穴戮得连剑也拿不稳,长创立时叮一声响跌落地上。
任小琳自知武功跟对方相差太远,但仍然全力护住杨破天,叫道:“你是谁?是人是鬼?是男是女?”
那人嘿嘿一笑,道:“我是来自峨嵋山的老太婆,这小子,就交给我来好好栽培吧!”
任小琳“啊”的一声叫了起来,失声道:“你是……金顶婆婆?”
那人冷笑道:“不错,我便是你嘴里描叙得阴险毒辣、麻木不仁的峨嵋至尊金顶婆婆!”
任小琳勉力镇定心神,道:“这小子只是一团烂泥,正是朽木不可雕,不劳前辈费心。”
金顶婆婆哈哈一笑,道:“老身要怎样栽培这小子成材,你是做梦也做不来的。念在神武门与峨嵋派同属正道盟一脉,只要你不碍手碍脚。老身决不会把你为难。但要是你不知好歹,我只好把你撕开十七八块,抛入江中喂鱼。”
任小琳大声道:“金顶婆婆,别人怕你,我不怕!有种的便把我杀了,否则,你休想带走杨破天!”
金顶婆婆道:“以为大呼小叫,就可以把魔教余孽叫唤过来吗?真是做梦!”
任小琳脸色一变:“你在聂坛主那边做了什么手脚?”
金顶婆婆冷哼一声,道:“姓聂的原本还该闭关练功,却为了这小子而破关强自出头,他以为这样做便是魔教中的大英雄,简直是可笑的蠢材!”
任小琳怒道:“你究竟把聂坛主、金秀才和老状元怎样了?”
金顶婆婆嘿嘿一笑:“你放心好了,老婆子已很久没有杀人,只是在那些合人的饭菜里放了一些‘酥筋化功散’,在十二个时辰之内,不但功力尽失,就连想爬过来瞧瞧魔教的少主,也是难比登天。”
任小琳听了,额前冒汗,掌心冷冷地紧紧握住杨破天的手,沉声道:“这老妖婆吃人不吐骨,我们万万不是她的对手,惟今之计,只有向这老妖怪投降。”
杨破天一怔,没料到“美娘”竟会说出这种丧气的说话,正要大声反对,任小琳已左手一扬,一蓬青芒直向金顶婆婆脸上撒过去。
一蓬钢针撤出,任小琳立刻牵着杨破天的手,毫不迟疑地跃入江中。
杨破天给任小琳拖入江水,他不懂水性,全仗任小琳维护,方始得以间歇地在江面上呼吸。
任小琳虽然略懂水性,但却难以长久地在江水中照顾杨破天。二人漂浮至江心,水流越来越是湍急。墓地一块尖石迎面飞来,不偏不倚,把杨破天的额角砸爆。
这一击极是沉重,杨破天网哼一声,登时昏倒,任小琳大惊,只见金顶婆婆阴霾可怖的脸,就在眼前不足咫尺狰狞地暴现。
金顶婆婆目露凶芒,一爪便向任小琳迎头直抓下去。任小琳虽际此生死关头,但仍紧紧握住杨破天的手不放。
金顶婆婆这一爪之威,着实可怖可畏,任小琳把脸颊向左一侧,虽然堪湛闪开这一击,但右肩已给金顶婆婆一爪插入,登时疼彻心肺,手一松,杨破天已给湍急的江水直冲出去。
任小琳急叫:“前辈,快救他!只要前辈把他救回来,无论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不等她说话,金顶婆婆早已运起内力划水,直追杨破天。
“姓杨的小子,老婆子还没把你折磨够,怎能就此死掉!”
金顶婆婆功力湛深,水性犹佳,转眼间已追及杨破天,正要把他抓回来,深黑江水中突然又再冒出一人,更声如裂帛地历吼:“霸王在此,谁敢猖狂?”
竟是来自楚地之江东霸王——楚江东!
霸王来了。
他是冲着金顶婆婆而来的。“霸王裂岳拳”轰然出手,这一种拳法,在当年谁也没见识过。
直至很久很久以后,江湖上才有一个浪子,把这一种拳法练至炉火纯青境界,这便是鼎鼎大名的三少爷叶虫。
但在这一刻,就连金顶婆婆那样的武林前辈峨嵋至尊,也看不通透这势道如此凶猛的一拳。
金顶婆婆在滔滔江水之中,竟然不敢硬接霸王这一拳,这时,二人都已渐渐靠近江畔,双足站在江底砂石之间。
但回头望去,月色下再也瞧不见畅破天的影踪。
金顶婆婆大怒:“霸王?你便是楚江东?你今年春秋多少?才活了三十个年头,不及老婆子三分之一,但已命中注定,要——死——在——这——里!”
江底下脚步错动,呼的一掌,便往霸王胸口直拍,竟是直压中宫,径取要害。
霸王不避不让,“霸王裂岳拳”后发先至。
“蓬”然一声,拳掌相交,在胜负尚未分明之际,江上突然火箭有如蝗虫乱飞,十余艘快舟直漂而至。
在最前端,一艘快舟,船首上位立着一人。他神色深沉,瞳孔寂寞。郁郁寡欢。
这人,年二十八,一身黑色长袍,一脸秀气,手挽“百石魔龙金弓”,箭已在弦,箭铁直指霸王两眉中央,倏地弓弦一崩“声大作,一枝”纵横四海天龙血箭“直射出去!
箭已射出。
但黑袍人怨毒的眼神,比这一箭更毒辣千倍万倍。
他道:“我是你生命中惟一的男人,也是惟一的女人,你竟负情负义,我要你不——得——好——死!”
箭仍在飞。霸王已和黑袍人的眼睛仿如箭矢巨戮,一起鲜血淋漓。
在此同时,江畔东方,罗裙飞舞,七十二口飞刀自裙装底下连环飞出,九位彩裙冶艳女郎,人人发出八口飞刀,狂袭江心十二艘快舟。
还有第十位女郎,口咬三尺青锋,赤足露腿,坐在一头万斤大象背上。
既有霸王,自有妖姬。
霸王妖姬,千秋佳话。
-------------
坐拥书城 扫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