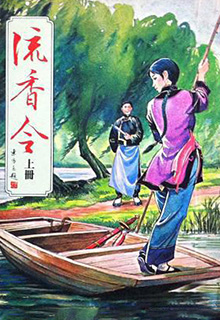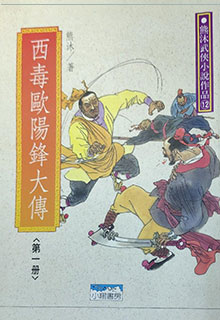铁笔书生沉思半晌,把那包纹银递给了老船夫道:“这儿一共纹银百两,足应今晚之急,你掣去,赎船还债的事,明儿老夫再给你琢磨!”
老船夫千恩万谢地接了过去,叫道:“小妞儿,还不快快过来给恩公叩头!”
这名叫小妞儿的年轻船娘,正是老船夫的孙女儿,老船夫晚年丧子,媳妇早给那些杀千刀的凶徒掳去,只剩下这一弱孙。祖孙两人,端端正正地向二位老人叩了三个响头,赤城山主细看这女孩子一眼,口里称:“罢了!起来吧。你叫什么名字?”
小妞儿回道:“小女子贱名洁馨,姓氏朱。”
老人展颜一笑,道:“好,好!”
陡然间,赤城山主把手向铁笔书生一招道:“尤老弟,附耳过来,我有话说!”
铁笔书生一怔,果然把耳朵凑到赤城山主的唇边,但听赤城山主低声道:“你瞧这女孩子如何?”
铁笔书生诧异地望了赤城山主一眼,说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赤城山主低声道:“没有什么,你没有徒弟,就收她做女弟子吧,我刚才细看她的骨骼,是个天生练武胚子,这孩子也怪可怜,只是年纪稍稍大些!”
“收她做徒弟,不行,我们还没有摸清她的来历呢!”铁笔书生移开了身子,坐到椅上,闭目沉思,过了半盏茶工夫,忽地双目下垂,叫道:“小妞儿,不,馨儿,你过来,老夫有话问你!”
小妞儿移挪着呆滞的步伐,慢慢地走了过来,十三四岁的女孩,本该天真活泼才对,只为长受贫困折磨,变成阴沉地悒悒寡欢的一副性格。
跑到铁笔书生跟前,垂手而立,却不做声,铁笔书生想了一会,问道:“你今年几岁啦?”
“十三岁不足!”小妞儿回道,就是这么简短一句。
铁笔书生暗里点头,寻思:“当真是难得的练武资材,连性情也对劲。”又问:“你的爹娘呢?到那里去了!”
小妞儿哭将起来,呜咽道:“我爹死在恶人手里,娘给拉去了,那是上个月的事!”
铁笔书生一听便明白,笑道:“那么你想到什么没有,徒然伤心有什么用,有了主意没有?”
小妞儿似懂非懂,摇摇头道:“我从没有想什么!”
陡然间,铁笔书生脸色一整,严肃地道:“冤有头债有主,谁害了你的爹娘,你就得设法报仇,这才是有志气的孩子!”
哇的一声,她又哭了,幽幽道:“报仇?谁不懂得,我是个孩子,打不过人家,他们人又多,又凶,这仇怎报!”
铁笔书生苦笑道:“傻孩子,君子报仇不在一时,待长大了才报也可以,你报不报此仇?”
“怎么不报?我也时时想着,一定要练武,到时长成了,就好报仇!”小妞儿哭得更厉害。
铁笔书生鼓掌道:“对,这才是有志气的孩子,喂,馨儿,如果你想练武报仇,咱可以帮你忙!”
小妞儿红肿的眼儿一亮,凝眸细视当前这位陌生老人,怔怔不语,神情中流露着不相信的样子。
静默了半晌,铁笔书生突地伸出右手,向里一弯,倏地望舱窗外拍出,但听吱的一声,半空中掉下一件物事来。小妞儿急定眼一瞥,一对小眼儿瞪得圆圆地,满脸惊奇的颜色,铁笔书生此时掌中多了一只夜枭,这夜枭也合该倒霉,铁笔书生一掌拍出,意在炫技给小妞儿看,好教她相信自己的话,恰值夜枭飞过,便给他用劈空掌力震跌下来。
铁笔书生平伸右掌,就让夜枭瘫在掌心,那扁毛畜牲几次鼓翼振翅,想飞向天上,脱离他的掌握,但那里能够,已然给他一股内劲牢牢黏上,动弹不得。小妞儿年纪虽少,但久居龙蛇混杂的李家沟,倒也看过江湖上人物逞技炫露,只是从未投师习艺,不知就里而已。
小妞儿吃了一惊,心下琢磨道:“这位老人家的玩意倒不错,鸟儿在他掌上就飞不出去,当真可怪,还没有人耍过这玩意呢!”觉得又惊奇又有趣,还不知是武技!
铁笔书生见小妞儿满脸奇诧,怔怔不语,不由哑然失笑。暗自运气掌上,这时在他掌心里那鸟儿,忽地啁啁哀鸣,状甚痛苦,几翻挣扎,终是白费气力,小妞儿一瞧便瞧出端倪来,已然明白是铁笔书生捣的鬼,心中不忍,颤声叫道:“老人家,这鸟儿怪可怜,放了它吧,别为难它,它也有爹有娘!”小小年纪,语出却是宅心仁厚。铁笔书生心上一乐,低低呼道:“去吧!”呼地一声,那夜枭振翼欢鸣一声,两翅一鼓,连连幌动,自舱窗中疾掠而去。
小妞儿惊疑未释,问道:“老人家,你有法术?”
铁笔书生笑道:“这是武功,不是法术,你可知道?”
小妞儿想了想,明白过来,她也端的冰雪聪颖,举一反三,已然便能了然,只见她欢然叫道:“老人家,我知道了,这叫内功可对?是什么内功,可肯教我?”
铁笔书生惊奇地望了她一眼,问道:“不错,是内功,你怎知道?要我教你,得先说明白!”
小妞儿道:“本来我是不懂的,有一天,我渡着一个客人,他也这么做,我看了心里奇怪,问他他又只是微笑不说,不久爹回来了,才告诉我!”
铁笔书生一怔,吃惊问道:“你爹怎知道,他也会武?”
小妞儿毕竟是个孩子,口没遮拦,放低声道:“他不会内功,只懂得几手拳脚,不过他却懂得什么叫内功,因为他在龙蜃帮里混过!”
语出骇人,铁笔书生脸色一沉,目中棱光一射,小妞儿给唬得全身索抖不已。过了一刻,铁笔书生神色稍霁,曼声道:“你爹叫什么名字,在龙蜃帮里干什么?告诉我老人家,才教你内功!”
连哄带唬,小妞儿已自知失言,却是不能不说,嗫嚅道:“爹叫阿牛,是龙蜃帮的跑腿,但他老人家已给杀了!”
铁笔书生自座中一跃而起,震得那小舟不住地在水面打涡漩,倾倾斜斜,老船夫在舱外船首,惊叫道:“客官,你老别乱跳,把船翻了不是当耍的!”
铁笔书生一跃起,大袖一拂,已然把小妞儿搂进怀里,颤声问道:“好孩子,你说实话,你爹可是长瘦身材,左额上有个大疙疤?怎么给杀死,谁杀的?”
小妞儿惊疑地瞧了铁笔书生一眼,却不挣扎,任由他紧紧搂着,点了点头道:“不错,爹正是这个样子,老人家怎知道?他是给龙蜃帮舵主杀的,却不知怎地杀他!”
一点也不假,这女孩子年纪还少,怎能知道这许多事,但在铁笔书生的心中,已经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想起前事,不由悲伤起来,怆然道:“好孩子,老人家是你爹的朋友,正想见他,可惜他已遭歹人毒手!”
小妞儿的爹,正是那个与南星元史三娘做一路的阿牛,阿牛秉性正直,是个好人,荒山传话,野镇送信,这一切,历历如在眼前,怎能教铁笔书生不悲怆难禁?
赤城山主不知这段原委,知之也不详尽,诧然问道:“谁是阿牛,老弟怎与他相识?”
铁笔书生音哑回道:“南老弟的朋友,野镇送信,正是此人!”
赤城山主哦了一声,也忆起前事来,叹道:“人死不能复生,伤悼于事无补,不过,阿牛的死因,却不能不追究,或者他们已闻风知讯,那就添增麻烦了,老弟,现在你总明白这孩子的来历吧,收她为徒可没干系!”
舟中收徒,已成定局,铁笔书生毫不犹豫,把脸朝向舱外船首,清呼一声:“老丈你过来,我们有请!”
老船夫移着蹒跚的步伐,慢慢地挪了过来,问道:“客官,你老有何吩咐?”
铁笔书生陪笑道:“老丈,不瞒你说,咱二人是江湖上人物,武功虽不算怎样了得,却还会几手,你这孙女儿天赋奇骨,如习武功,必有大成,咱想成全她,收她为徒!”
说到这儿,顿了一顿,续道:“老夫已然知你家深蒙血海奇冤,你孙女他日习技有成,也可报仇雪恨!”
老船夫一闻言语,不禁多瞧两人一眼,苦笑道:“小老儿荷蒙老英雄慨助多金,解了倒悬之困,此恩此德,何日或忘,今更错爱,允收孙女为徒,正是求之不得,焉敢言辞,不敢动问二位老英雄法讳,孙女拜师,做爷爷的也该知道她师傅是谁!”
倒也说得有理,铁笔书生暗道:“方才劈空捉飞鸟一手,这老儿在外边没瞧见,大抵此刻还不大相信咱吧!”也不打话,便自背上卸下一只长长的皮囊子,这皮囊子像个剑鞘,里面却非装上宝剑,打开囊袋口,刷地一声,抽出一柄用精钢打成的大毛笔来,原来他这次下辽东,生怕给人认出庐山真面目,特制一个大皮囊,盛着这枝大毛笔,深藏不露,只缘此笔乃是他的一生招牌,江湖人物一瞧便知。
大毛笔才亮出,老船夫惊叫一声道:“你老是铁笔……”
可也怪道,这村野老儿,怎地也知江湖上有个铁笔书生的人物?原来上次铁笔书生大闹辽东,剧战南史二人的事,已然闹哄哄地传遍山东一带,道路传说,把铁笔书生描绘成一个如神仙般的人物,于是,大家都知道他有一柄大毛笔,加以老船夫的儿子阿牛本来便是铁笔书生的朋友,闲里也曾提过。当前这客官,手擎大毛笔,江湖上可没有第二人使过毛笔的,不是他还有谁呢!
老船夫一喜非小,连声道:“能拜在老英雄门下,小孙女不知几生修为,才能得到!”当下,便在船舱里行起拜师仪式来,这艘舟本来就是香烛常备,用以拜祭天后娘娘的,据说天后娘娘是海上之神,专管舟楫之事,水上人家,没有一人不祀奉她的。
燃上香烛,老船夫便请铁笔书生上坐,叫孙女儿过来,以便行拜师大礼。猛地里,铁笔书生站了起来,把手频挥,叫道:“忙什么?你须先谒过祖师,才能列入天山门墙!”
这时,小妞儿已走到跟前,闻语一愕,不即跪落,楞然想道:“祖师在那里,什么叫天山门墙?”小妞儿年少无知,那知武林中天山名号,老船夫一听便明白,又是连声欢叫:“老英雄原来是天山门派,怪不得武功如是之高,小孙女何幸,竟也能列在代出英豪的武林名门之下!”
铁笔书生却不打话,面容庄严肃穆,一卸身便把背上一个小行囊轻轻摘下,倏地一探手,伸进那囊中,取出几般事物来。
他这番动作,赤城山主瞧在眼里,怪在心头,忖道:“尤老弟拿这些东西出来做甚?”
那老儿寻思未已,铁笔书生手里拿着的是一卷卷起的书画,几片檀香,另外一个锡制的小煊炉,略一移身,别转过去,翘首向背后舱壁上端详过去,便把书画挂上了去。但见画中是幅绣像,绣像上绘着一个形貌清奇的老头子,五绺长髯,飘拂胸臆,神情绝俗清逸。虽说是幅画像,却写得神肖之极,只那一对眸子,仿佛神光四射,炯炯可畏,端的栩栩若生。
铁笔书生挂好了神像,又挪过一张座台子,把那锡制小煊炉摆上,引火燃点檀香,插进煊炉里去。一时间,火引香发,香烟袅袅,弥漫一舱。
铁笔书生望着冉冉轻烟,出了一会神,突地翻身自行跪下,口中喃喃祷告,朗声叫道:“启禀本门祖师,兹有忠义之后,小女子朱洁馨前来乞求收列门墙之下,朱洁馨出身虽属平常之家,而童心仁厚,天资敏悟,乃可造之材,前途定然无可限量,弟子尤文辉经代师门考核完竣,认为此子不辱本门,故敢斗胆收她为徒。祷告祖师在天之灵,予以庇佑,肃此虔诚祷告!”
把祷词一念完,一直身形,陡地喝道:“朱洁馨还不快快跪下,谢过本门祖师恩典!”赤城山主这才恍然过来,转念间心中又有疑问:“尤老弟怎这般精细,时刻准备收徒,用物准备得这般周全。”
赤城老儿那里知道,铁笔书生随身携带本门开山祖师神像,煊炉檀香拜祭各物缘故,要知铁笔书生为人笃守师训,对本门祖师最是敬重,所带各物,乃是用以晨昏祀拜之需,并非只为收徒之用。
陡喝之声才过,小妞儿也当真聪颖,此时灵台已是空明,依言跪下,磕了三个响头,口里祷道:“弟子朱洁馨,谒见祖师在天之灵,望祖师赐佑,早日学成绝艺,报却仇冤!”
说来竟是条理不紊,赤城山主一旁点头暗暗赞许。
小妞儿谒祖完竣,正待爬起,陡然间,铁笔书生身形一掠,只一晃已然遮在小妞儿与天山祖师神像之间,和颜悦然地低声道:“馨儿且慢站起!”
话声虽轻,却是威严无比,小妞儿一怔,那敢违命,只好跪着不动,铁笔书生微笑颔首,慢慢伸手到那行囊中,又掏出一道小金牌,面色跟着一端,口中喃喃道:“睹金牌如睹祖师!”
小妞儿怔怔望着,莫名其妙,兀是不知她这位未来师傅在耍什么玩艺。铁笔书生把那道金牌朝小妞儿面前一晃,说道:“你在祖师之前,起个誓遵守戒规,才列入门墙!”
那道金牌,闪耀在小妞儿的眼际之前,她放眼朝那牌子上一瞥,但见金牌上刻着一行行的文字,小妞儿识字本不多,那些字又小又密,看觑一回,还是莫名其妙。
铁笔书生见此情景,才启口道:“馨儿不懂这面金牌么,你没有念过书?唉,让我告诉你,金牌上面刻的条文便是本门戒律,凡列入门墙的人都要遵守,嗯,你这孩子,将来除习武之外,还得好好读点书,不读书不明理的!”
小妞儿仰首坚毅地道:“弟子愿遵本门规戒,请师傅赐示!”
铁笔书生脸色凝重,手擎金牌,口里喃喃自语:“种善因,收善果,天山一派向来忠义,一入我门,任侠行义,锄恶扶弱,武林豪杰如是,本门戒律如是,善善恶恶,好自为之,休生异心!”就如矗立祭坛祭师,祷咒什么似地。
小妞儿似懂非懂,心知师傅所说的话,必是善言,料答应了也无妨碍,因朗声应道:“弟子谨遵!”
铁笔书生点点头,忽地里大喝一声:“朱洁馨听着!”
这声喝,如焦雷之起半空,震得小妞儿耳鼓嗡嗡不绝,在余音娓娓之际,不暇细想,急叩下头去。铁笔书生乃依金牌上所刻条文,一一念下,每读一条,问道:“知道吗?”三字,小妞儿必回:“弟子敬遵!”之语。
金牌上所载一共十二条戒律,无非是一些要门人扬善去恶,禁止奸邪盗杀行为之意,眨眼间铁笔书生已然把十二条戒律念完,这才轻轻叫道:“谒祖之事已完,起来,再行拜师之礼。”说着也不客气,迳自移身到当前的一只椅子旁,一屁股大马金刀地坐了下去,再受小妞儿三拜,闹了整整半个时辰,拜师礼总算草草完成,从这时起,小妞儿便是天山门下,铁笔书生的高足了。
拜师之礼一完成,余下的是袅袅轻烟,漂渺其间。这时小舟溯流而上。舟行甚慢,不远处已见灯火通明,喧声起自耳际。
前面那片光亮和喧声,正是老船夫口里所说的“连溪里”,这地方是李家沟唯一给人们的消遣所在,水上秦楼,画舫楚馆,夜夜欢乐,夕夕笙歌,管弦不辍,非常热闹。赤城老人慨叹道:“想不到穷乡僻壤,也有这般丧人心志的去处,我们既非此道中人,不如回舟休息去吧!”
铁笔书生笑道:“老兄说那里话,既来之则安之,好歹观光一会再说!”一别头,向老船夫道:“老丈,连溪里除了婊子花寨,尚有什么好去处?”
老船夫陪笑道:“去处多哩,尤老师不玩妓不赏歌,也可找艘酒艇坐地,喝杯酒乐乐。”
大凡有歌妓赌场的地方,自然附有吃喝去处,自不待言,赤城山主纵声笑道:“老丈说的对,咱不爱冶游赌博,喝酒解闷,虽非正事,倒是无碍清誉。”
舟越行越近,连溪里已现眼前,但见一排排的画舫,髹刷得堂皇美丽,金碧辉煌,舟连着舟,中间剩出一条条的水走廊,以利渡客小舟往来,而那些画舫,却是固定不动。
老船夫轻轻道:“到了!到了!”
蓦地里,但听一阵少女清歌,歌声铿锵如同金玉交鸣,因风传送,娓娓悦耳。赤城老人倾耳一听,心念一动,皱眉道:“想不到此地也有这般人物?”
这阵传来清歌,浑圆如珠玉震荡,清而不大,内蕴刚劲,赤城山主是何等人物,一听已然听出高歌的少女是个不寻常的人物,竟用“传音入密”内功歌唱,虽然不近,却如在各人耳畔,缭绕不散。铁笔书生也吃了一惊,低低道:“那话儿来了!”他已然疑到歌唱人必是长白山阴阳门的人,只缘除了二怪门人,谁能有此内劲?
一抬头,铁笔书生望了老船夫一眼,叫道:“老丈,撑咱到唱歌人的所在去!”
老船夫嘻嘻笑道:“尤老师也有此雅兴?这姑娘真难得,年纪轻轻,倒唱得一腔好曲儿!在这儿推她第一!”
铁笔书生惊奇地看了老船夫一眼,急切地问道:“老丈认得此人?”
老船夫点头道:“怎不认得?这女娃子是衣蕙坊新夹的歌妓,不但曲儿哼得挺有名气,人也长得漂亮极了,只是性子不好,常常无缘无故闹别扭,据说还是个黄花姑娘哩,卖歌不卖身,不知多少豪阔子弟拜倒石榴裙下。”
赤城山主搭腔道:“她叫什么名字?”
老船夫道:“芳名赛雪儿,本姓耿,真名小老儿可不知道,你老有兴致,可到她的画舫去,召她一见,依酒献歌!”
赤城山主哈哈一笑道:“好,咱就前去瞧瞧!”
小舟行如蚁蛭,逆水行舟,最是费力,老船夫鼓桨力划,兀是速度不增,铁笔书生一瞥,呵呵而笑,两袖陡挥,荡起了一阵劲风,风推船前,去势如离弦之矢,把老船夫吓得呆了。
展眼间,已到达连溪里,在如鲫画舫之中,找到了“衣蕙坊”这画舫。舫颇宽敞,舱里间隔成厅房,一共有六间布置雅洁的厅房,这些厅房正是供给召妓侑酒高歌之用。
小舟傍衣蕙坊拴着,铁笔书生赤城山主两人,登过彼舟,舟内自有老鸨堂倌过来招呼,赁得一厅,点下几式精美小菜,要了二斤高粱酒,当即挥下花笺,便待把名歌妓雪儿召来。
久久不见来人,丽人何故避面不见?两老头初时还以为雪儿顾曲周郎太多,分身不暇,又过顿饭光景,才见那横肉满面的鸨儿前来禀告,说雪儿已然被人赎作归家娘,蒲柳有寄,从昨晚已停止鬻歌。适才引吭清歌,不外一时兴起,并非卖唱等语。
两老头自然不是为风月而来,目的不过想看雪儿究竟是什么人物,他们知彼姝身怀绝技的人,琢磨之余,已怀疑其中必有不可告人缘故,同时,也断定非阴阳门手下党羽,设其是阴阳门之徒,二怪定然不肯任令操此贱役。
二位老人一闻鸨儿的话,不胜诧异地问:“作归家娘?嫁给谁,何家儿郎有此艳福?”
鸨儿姆指一翘,强笑一下,叫道:“不瞒达官说,雪姑娘的主儿非是别人,乃江湖上鼎鼎闻名的俞公典官人!”
二人同时一楞,俞公典纳妾之事,早自老船夫口中得悉,却不知所纳丽人,竟是这位隐身风尘的雪儿,以雪儿这般人物,怎肯许身下嫁一个万恶邪帮,年垂迟暮的老贼?心中益发疑虑万端。
铁笔书生想了想,倏地探手入怀,便想掏出银两来,一探手才觉所有带在身上银两,早已赠给可怜的老船夫,一转身对赤城山主道:“老兄台,身上有银两没有?”
他这番举动,赤城山主已自瞧料得到,连声回道:“有、有、有,要多少?”随说随在怀中掏出一大包银子来。一打开,哗喇喇地撒了一桌,黄澄澄的是金元宝;白雪雪的是纹银,光辉夺目,闪闪生亮,令人眼花缭乱,数日足有二百两之谱。看得那鸨儿也呆了,处此穷乡,虽说花事当旺,似此多金豪客,委实罕见,鸨儿瞠目结舌之余,嗫嚅道:“达官惠顾,盛情奴才拜领,可惜雪姑娘已不见客,抱歉良深,敝坊漂亮姑娘多的是,待奴才给达官召两位来陪伴陪伴如何?”这奴才还道当前两人是老尚风流,一心以为鸿鹄将至。
铁笔书生冷笑一声,随手一抓,便抓了一碇重约五两的纹银块,朝桌面一挞,叫道:“你这奴才瞧老爷子是何等人物,岂是随便召妓的,这些银子赏给你,快教雪姑娘来厮见,回头再重重赏你!”
雪儿艳帜高张,名闻辽东一带,鸨儿深信当前两位豪客,当真慕名而来,转念一想,庸脂俗粉,难当贵人之意,也是道理,但她心中却另有顾忌,取赎雪儿的人若是寻常贵富人家,暗里让她来陪伴一下倒也无碍,只缘那人乃是俞公典,这魔头轻易招惹不得。眼巴巴看着金光灿烂的黄金纹银,心里委实有点舍不得。
正踟蹰间,铁笔书生已明其意,笑道:“我们也不过想见一见面而已,料也无碍雪姑娘前程!”
鸨儿还未答话,蓦地里,烛影摇曳之际,帘帘启处,一个艳色迫人,美丽无俦的美人儿,莲步姗姗,掀帘而入,来人正是那名妓雪儿。她已得其他堂倌传达,知今晚来了两位陌生老者,豪阔异常,指名召见,不由心中怦然一动,跟着便自行过来。
一跨进厅中,裣衽为礼,鸨儿一瞧,面上变色,颤声叫道:“雪妞儿,你……”雪儿颜色自若,秋波一转,瞧了两人一眼,笑道:“难得两位贵人莅临,雪儿这厢有礼!雪儿已谢绝交游,不知贵人相召,何事见谕!”
原来铁笔书生和鸨儿对语,早已绐雪儿听去。铁笔书生略睨了她一眼,笑道:“姑娘就是雪儿吗?嗯,久仰芳名,只恨缘悭,未尝识荆,素闻姑娘擅音律,我老头今晚来此,非为别的,乃为一聆天曲为荣!”
雪儿嫣然一笑道:“雪儿粗晓皮毛,恐怕不足以当尊意,过誉之奖,愧不敢当!”旋沉吟道:“今晚放歌,恐有未便,愿献秦筝一阕,以娱贵人,还望指谬则个,未知尊意以为如何?”
这风尘奇女,不但芳华绝代,且擅音律,清歌鼓琴,人称双绝,此刻竟以秦筝自荐,也有考核当前客人之意,她只一瞥眼,已然知道两老头绝非寻常之辈。
铁笔书生呵呵一笑,霍地站起,说道:“你也会秦筝?”要知秦筝,俗称十三弦筝,乃古乐音之一? 只缘筝上一共十三道线索,弹时一手按拍,五指纷弹,便可发出乐音,据说古楚大夫俞伯牙遇钟子期时,伯牙所弹的便是这种乐具,流传近代,能者已鲜。难怪铁笔书生有点不信。
雪儿不答,一别头,对跟在后面的随从丫环喝道:“喜儿,还不快把秦筝取来?”
喜儿应诺一声,身形微晃,已飘出房去,两老人又同时一愕,赤城山主自忖道:“小妮子是什么人物,怎地连她的丫头也会武技?”心下嘀咕未已,喜儿此时已然手挟一具秦筝,漫步跑到跟前,手抖处,那具秦筝凌空飞起,朝着雪儿面前抛到。
也不见雪儿怎样作势去接,双掌横拍,那具秦筝给她击出掌风一撞,在半空中打了个旋转,不偏不倚,已然落在一张小茶几之上,却是声息不闻。
雪儿连看也不看它一眼,自顾取下檀香焚上,又挪过一团锦塾,摆在秦筝之前,香烟袅袅中,盘膝上坐,伸出两只柔荑般纤手,一掌按拍,五指一拨,陡听玉盘滚珠之声迸发,铿锵悦耳,只亮这一手,已知不俗。
铁笔书生暗自赞叹,赤城山主却喝起采来。铁笔书生眼波一横,制止赤城老儿发声,这位老人武功虽高,要称雅人还够不上,弄琴调筝,正到妙处,那可胡乱相扰?
雪儿那秦筝,而音调缓缓,其声幽怨,如泣如诉,一忽儿调亢韵高,如急水湍流,飞如狂涛,一厅之内,余音回旋,宛若仙乐之奏。
铁笔书生边听边轻轻击节,喃喃低语:“意在高山,其声自亢;意在流水,其意自逸!”这老人竟下品评,话声微不可闻,雪儿耳聪目灵,却听得分明清楚。
猛可里,陡听哗喇喇一阵响,弦断琴碎,赤城山主立吃了一惊,定睛细看,先是雪儿张口一吹,那十三道琴弦,叮叮当当自行断去,又见她左掌微抬,轻轻向筝琴上一捺,便把那具秦筝捺成数块。赤城老人见雪儿这突如其来的举止,虽吃惊却不明就里,频呼道:“雪儿姑娘,你好端端地怎么发脾气啦?”
秦筝摔破,雪儿慢慢地从锦塾上站起来,惨然道:“罢了,今生也休弄此不祥之物!”
语出含糊,当前两老人那会得知底蕴?铁笔书生也为雪儿这番举动弄得莫名其妙,惊道:“姑娘绝艺,世所罕见,奈可碎筝,何事伤怀至此?”
一抬头,雪儿已然泪痕披面,目中莹然欲滴,噎咽道:“小女子命薄,湖海飘泊至今才遇知音,可惜迟了,还要它来做甚?今后知音难觅还好说,负此雅具,空对俗物,徒招伤怀而已!”
话还是说不明白,但语意中以铁笔书生为知音,自可聆悉,铁笔书生脸上暗然,古来红颜白发,久称佳话,那不过是好色之徒,文饰其非而已,铁笔书生是何等人物,岂可概括以论,何况他这次抵此,实非为美色而来,雪儿语存暧昧,宁不使他吃惊赧颜?但一瞬间已然消失,英毅之气陡现,沉声道:“孩子,你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