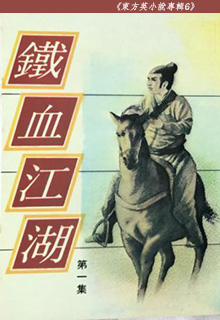单世骅久闯江湖,见多识广,一眼瞧出来人身手不弱,在敌友未判之前,岂敢留下痕迹?”立时抱起韦宗方身子,一提真气,跃上一棵大树,藉着枝叶隐住身形。
这原是一瞬间的事,他堪堪藏好身子,那两条人影也已奔近林下!
只听前面一个道:“他们明明从这个方向来的,怎会不见踪影?”
此人这一开口,单世骅暮然一惊,这明明就是九毒教主门下玄字三号的口音,心念方动,只听稍后一个说道:“天色已黑,他们自然赶宿头去了,那会呆在这里?”
这是黄字四号的声音,果然是他们!
单世骅心中一动,暗想:“听他们的口气,极似跟踪自己两人来的了!”
只听玄字三号又道:“教主算定那姓韦的小子,身中寒毒,武功再高,三日之后申牌时光,必然发作,教主说出来的话,几时不应验过?”
单世骅听说韦宗方是中了九毒教主的寒毒,心头不禁大怒;但因此刻韦宗方全身僵冷,昏迷不醒,一时只好强自忍耐。
只听黄字四号道:“你说的虽是不错,但这韦的小子,可非比寻常,试想教主的安息香,何等厉害,若不预先口含解药,武功再高,只要闻上一点都会昏睡过去,那天他闯进清心轩,居然行若无事。还逼着教主取出解药,把姓单的救醒,依小弟看来,只怕区区寒毒,也奈何不了他。”
玄字三号道:“安息香纵然厉害,怎能和寒玉尺相比?教主不是说过,就算大罗天仙,只要被寒王尺击中,也管教他冻得从云端里直跌下来,姓韦的小子究竟不是神仙。”
黄字四号道:“但教主可没有直接击中姓韦的小子,哦,听说教主的寒玉尺,还被这小子凿穿了几个孔呢?”
玄字三号冷笑一声道:“你是听荒字八号说的?这小丫头什么话都告诉你,总有一天会犯了教主的忌讳!”
黄字四号吃惊的道:“不……不是她说的。”
玄字三号道:“不是她还有谁?你总该知道地字二号是如何死的了?”
黄字四号听得头皮发炸,惊慌失措,央告道:“三师兄,求求你念在同门之谊,这话千万不可在教主面前说起。”
玄字三号冷哼道:“只要你们以后别再听天字一号的,我自然不会多说。”
黄字四号连声应道:“是,是,小弟以后一切听凭三师兄吩咐。”
玄字三号道:“其实我和天子一号,也并无什么私怨可言,只是他太娇横了,平日除了教主,谁也不在他眼里,嘿!洪字七号这丫头,听了他花言巧言,居然信以为真,一心只想去做云南蓝家的媳妇了,其实这小子那会有什么真心?据说他早已和南海门的表妹订了亲了。”
黄字四号道:“这话从未听荒字八号说过。”
玄字三号道:“你回去不会把这话告诉你的心上人,再要她露些给洪字七号听听,只是不要说是我说的。”
黄字四号连声应道:“小弟知道,小弟就说在江湖上听到的传言就是了。”
玄字三号拍拍他的肩膀,笑道:“好,你别忘了。”
黄字四号道:“这些小事,小弟一定办到。”
玄字三号道:“咱们快走吧,别误了正事。”
两条人影,话声一落,立即如飞而去,单世骅暗暗吁了口气,暗想:“自己原想抱着韦少侠到镇上去找个大夫瞧瞧,但如今这玄字三号和黄字四号跟踪而来,在这一带找不到自己两人,想必也赶到镇头去了,万一途中相遇,自己双拳难敌四手……”
想到这里,立时解下腰间束带,把韦宗方的身子,放到枝叶浓密的树桠杈上,然后用带缚好,才跃下大树;一路朝镇上赶去,这时不到初更,他赶到一处市镇,向人讯问,才知镇上住着一位名医张济万,医道极精,当下问明住处,敲门而入。
那张济万已是六十开外的老人,瞧到单世骅一脸焦急的模样,刚问了句:“尊客可是看病来的?”
单世骅道:“先生就是张济万么?”
张济万点点头道:“正是老朽。”
单世骅急忙抱拳道:“在下有个朋友,生了急病,特来请先生前去诊治。”
单世骅道:“就在前村,劳驾先生一行。”
张济万问道:“尊客可曾备了轿来?”
单世骅听的一怔,连忙道:“就在外面了。”
张济万点头道:“好,那么咱们就走。”
单世骅走在前面,很快退出门中,等张济万一脚跨出门槛,单世骅一指点了他哑穴低声道:“委屈先生了!”
一把挟起了张济万,立即展开脚程,飞奔而去,不消片刻,便已赶回原处,放下老人一手拍开他穴道。
张济万一阵喘息,眼看自己被人挟到效外来了,吃惊道:“好汉要把老朽如何了?”
单世骅道:“先生放心,在下有一位朋友,要请先生救治。”
说完,纵身一跃,飞上树去。
张济万见他飞身上树,一跃两丈来高,心头暗暗吃惊,暗想:“今晚自己碰上了江洋大盗!”
但听单世骅的口气,只是替他朋友看病,似乎无恶意,稍定了定神,只见黑暗之中,树后倒卧着一个人影。
只当就是要自己来看的病人,没待单世骅开口,就走到树底后蹲下身去,替那人把了把脉。摇摇头、抬头道:“贵友身中剧毒,业已发作,非老朽之力,所能解救……”
单世骅迅速解开束带,抱着韦宗方纵落地面,说道:“先生看都没看,怎知没有救了?”
张济万道:“老朽已经切过脉了。”
单骅道:“人在我手上,先生几时切过脉了?”
张济万奇道:“那么不是他么?”
单世骅闻言瞧去,只见树后果然躺着一个人,心中不由大奇,暗想不知此人是谁?一面把韦宗方轻轻放到地上,说道:“先生快替他瞧瞧。”
张济万盘膝坐下,取过韦宗方手腕,吃惊道:“好冷的手!”
单世骅道:“敝友中了寒毒,先生仔细看看,可否有药治?”
张济万三个指头,按上韦宗方脉腕,奇道:“奇怪!脉倒还在跳……”
单世骅看他闭起眼睛,在替韦宗方切脉,一时不敢惊动,悄俏走到树后,凝目瞧去!只见躺在地上的是个白发白须的老人,此刻双目紧阖,业已昏死过去,想起方才张济万说他身中剧毒,已经无救,凝足目力仔细察看,只觉得这白须老人,全身找不出什么伤痕,果然像是中毒模样,不由伸手把他翻了过来,这一翻动,瞥见老人右肩,月光斜照,依稀看到一点闪烁蓝光,心头一动,急忙低头瞧去,老人肩后果然露出三支极细的针尾,那是淬过剧毒的飞针!
当下随手撕下一片衣袖,裹着针尾,起了下来,这三支飞针,每支只有一寸许长,通体发蓝,心中暗暗忖道:“好歹毒的暗器,只是江湖上用淬毒飞针的人不多……”
正待站起,瞥见白发者人右手握拳,好像紧紧捏着一件东西,一时好奇,忍不住伸手过去,轻轻扳了开来,只见老人掌心握着的竟是一个白磁小瓶,打开瓶塞,里面只有一颗绿豆大的药丸。
单世骅见多识广,一看就知白发老人这粒药丸,准是解药无疑,敢情他取出药瓶,来不及吞服,就毒性发作了。想到这里,不管他有没有救,随手拔开老人牙关,把那粒药丸,纳入口中,在他原是无心之举,却没想到挽救了一位武林怪杰。
就在此时,只听张济万长长吁了口气。
单世骅急忙问道:“先生,我这位朋友还有救吗?”
张济万摇摇头道:“难……难……。”
单世骅道:“那是没有救了?”
张济万搔搔头皮,道:“老朽行医济世,不是说贵友没有救了,只是已非老朽之能,可以解救。”
单世骅道:“先生素负盛名,还望免为其难,但得治好我这位朋友的寒毒,自当重重酬谢先生。”
张济万道:“重谢倒是不敢,老朽可以医治的自当尽我心力,只是贵友这种寒毒症,老朽行医几十年,从未见过……”
话未说完,树后那个老人陡然坐了起来,张目问道:“老朽一条命,就是这位先生救治的么?”
张济万方才按过这老人的脉,明明已是快死的人了,此刻突然坐将起来,开口说话,怎不把他骇得失措,连连后退,脚下一绊,一个身子往后便倒。
单世骅慌忙伸手把他扶住,道:“先生怎么了?”
张济万大着舌头道:“他……他明明毒发无救了,怎……怎会坐将起来……来的?”
单世骅心知自己方才喂他那粒药丸,准是解毒灵药,还没说话。
那老人已经站了起来,拍拍衣服,笑道:“不错,老朽确是毒发将死之人,不知是那一位喂了老朽解毒药丸?
单世骅抱拳道:“在下瞧到者丈手上握着药瓶,想是来不及服食解药,就毒性发作,在下替老丈把药丸喂了下去,如今老丈剧毒已解,还宜稍事调息……”
那老人双目精光如电,呵呵大笑道:“老朽误中毒针,以致昏迷不醒,如今剧毒已解,自然就痊好了。”说着一面朝单世骅拱拱手道:“多蒙老弟相救,还没请教如何称呼?”
单世骅还礼道:“在下单世骅。”
他因韦宗方病势沉重,那有心情和老人多说,立刻回过身去,朝张济万道:“先生想想办法?可有疗治之策?”
张济万道:“老朽不会武功,依脉理而言,贵友之病,和风邪中寒不同,老朽实在说不出来,病情不明,就难以下药。”
那老人站在一旁,插口道:“单老弟,令友是什么病,让老朽瞧瞧!”
单世骅久走江湖,见多识广,早已看出这老人决非常人,这就说道:“敝友是中了寒毒!”
那老人道:“寒毒?如何会中寒毒的?”
张济万插口道:“据老朽从脉象上看来,少说也有三四日了。”
单世骅点点头道:“已经三日了,只是今天才发。”
张济万自诩精通脉理,得意的点了点头。
那老人道:“老朽是问他如何中的寒毒?”
单世骅道:“不瞒老丈说,敝友中了寒玉尺的寒毒。”
那老人奇道:“寒王尺?你们遇上勾漏毒君?奇怪,勾漏毒君已经有十几年没听到他的消息了。”说到这里不觉哈哈笑道:“你们差幸遇了老朽……”
单世骅听他口气,似是他懂得治疗之法,忙道:“老丈如能赐救,在下感激不尽。”
那老人道:“老朽一条命也是老弟救的,那也不用说什么感激不感激了,只是令友被寒玉尺所伤,已经过了三日,只怕寒毒业已入骨,那就麻烦了……晤,先让老朽瞧瞧再说。”
一面俯下身去,朝韦宗方脸上仔细端详了几眼,道:“令友可是易过容么?”
单世骅心头一惊,但此时救人心切,连忙点头道:“敝友确实易了容?”那老人道:“他身边可有洗容药物?”
单世骅伸手从韦宗方怀中,取出一个小小木盒,递了过去,那老人打开木盒,拈了一颗密色药丸,在手掌中轻轻滚动,然后朝韦宗方脸上抹去。
张济万听说这老人会治寒毒,自然触动好奇,静静的站在一旁,用心细瞧,此刻看他双手抹动,月光之下,转眼间,一个紫膛脸的中年汉子,忽然变成了一张清俊脸孔,心头不禁大感惊奇。
那老人拭去韦宗方脸上易容之药,突然身形一转,探手扣住了单世骅的脉腕,双目精光电射,哈哈大笑道:“老朽差点受了朋友的骗,嘿嘿,你对韦相公如何了?老老实实说出来吧!”
单世骅被他一把扣住脉门,但觉手腕上了一道铁箍,丝毫动弹不得,心头一惊,忙道:“老丈快请放手,这是误会。”
那老人嘿然笑道:“放开手,老朽也不怕你逃上天去,误会,这有什么误会?”
说话之时,果然松开五指,放了单世骅手腕。
单世骅搓搓手道:“在下单世骅……”
那老人道:“老朽早已知道你叫单世骅了,老朽问你究竟把韦相公怎么了?”
单世骅道:“在下方才说的,确是实情,在下和韦大侠同行,原是找人来的,不想韦大侠在黄昏时分,突然寒毒发作,昏迷不醒,在下赶到前村,去请这位张老先生,前来治病。”
那老人道:“你和他同行已有几天了?”
单世骅道:“在下和韦大侠由铁笔帮动身,今天已经三天了。”
那老人自言自语的道:“这就奇了!……”
他目光突然落到韦宗方左手无名指上,见他赫然套着一个铁环,不觉伸手把韦宗方左手取了起来,翻过一瞧!只见那铁环戎指在靠近掌心这一面,果然镶着一颗黄豆大的黑珠,正是江湖瞩目的引剑珠!再看韦宗方身边,还悬着一口长剑,他放下韦宗方左手,就伸手把长剑拔了下来,那老人抽出七修剑,只看了一眼,顿时脸色大变,猛一跺,怒喝道:“好小子!”
单世骅迅速从身边取出判官笔,喝道:“老丈要待怎样?”
那老人没待单世骅说完,业已返剑人鞘,急急说道:“单老兄弟,快抱起他跟我去,韦相公的寒毒,只有温玉能解。”
单世骅瞧他举动奇突,迟疑的道:“老丈……”
那老人急道:“快跟我走,老朽万年温玉就在咱们姑娘身上。”
独守南天门金臂神将,单世骅自然听人说过,不觉大喜过望,一面说道:“老丈原来是欧老前辈,只是在下还要先送这位老先生回去。”
欧老头从韦宗方身上发现了引剑珠、和七修剑,证明确是真正的韦宗方,那么昨晚自己从林中救回去的,只是个冒充的韦宗方了,他前后一想,心头顿时大急,顿足道:“事迫眉捷,这点路他自己不会回去?你快跟我来。”
张济万忙道:“单大侠救人要紧,老朽自己会回去的,不劳相送了。”
束小蕙醒来时,但觉身子不住的颠簸,耳中听到一阵又一阵的车轮转动的辘辘之声!
她仿佛做了一个恶梦,还记得昨晚……自己迫出寺外,根本没有贼人的影子,但在回身之际,却看到一条黑影,一路朝寺后山上飞掠而去,韦宗方要自己朝南追,他自己是朝东去,那么这黑影说不定准是贼人,于是自己就朝山上追去,赶到山顶,韦宗方竟然先在那里了,高声叫着:“老人家。”
自己觉得奇怪,问他:“欧伯伯人呢?”
他神色似乎显得不对,反问自己:“你看到欧伯伯了么?”
自己方觉他间的奇怪,他突然一指点了过来,自己穴道受制,心头却是清楚,他匆匆忙忙的抱起自己,连夜赶路……
如今果真已在车上了,他要把自己带到那里呢?她突然想起韦宗方明明告诉自己朝东追去的,那么不可能会在山顶现身。
她又想到前晚韦宗方被人暗中下毒,昨晚又有人在窗外暗算于他,如果山顶上出现的真是韦宗方,他何用匆匆忙忙的带着自己连夜赶路?”
她心头蓦地起了一阵颤栗,他莫非不是韦宗方?显然,他是怕被韦宗方和欧伯伯赶来,才劫持了自己连夜逃走。想到这里,不觉转眼望去,只见韦宗方赫然坐在自己身边。
他那张英俊的脸上,浮起亲切笑容,温柔地抚摸着柬小蕙的脸颊、低低说道:“姑娘醒来了么?”
束小蕙一双目光,只是盯在他脸上,她竭力想找出他的破绽来,但她却是找不出来。不过,她坚信他不是韦宗方,虽然他脸孔长得和韦宗方如此相像;但可从他眼神不正,举动轻佻,找到了结论。她只觉得他的手指像是毒蛇一般,要想把他推开,那知双手软绵绵的连抬都抬不起来。
束小蕙又惊又怒,要想大声叱喝:“你莫要碰我……”那知嘴唇张了张,却是一个字也说不出来,自己竟还被点了哑穴!
她只有从眼中闪出愤怒之色来表示她的憎恶,心中骂着:“恶贼,你究竟是谁?你为何要劫持我?”你究竟要把我怎样?”
韦宗方还是那么温柔,他轻轻替她掠着散乱的鬓发,柔声道:“你还要再歇一回,咱们还有两天路程呢!”
说着在她脸颊上亲了一下。
束小蕙心头发抖,她想嘶声大叫:“恶贼莫要碰我,恶贼,我不要去。”
一点没有声音,她急,她羞,她更怒愤欲狂,她不敢想落在这恶魔手里,以后会有什么遭遇?她竭力的想坚强起来,不让眼泪流起来,但终于急的流下泪来了。
韦宗方又怜又爱,捧着她娇躯,道:“好妹子,你是生我的气,我几时得罪了你?好妹子,快别伤心,我一辈子都不会亏待你的。”
还说一辈子,束小蕙简直连一分时光都忍受不住!
韦宗方在说话之际,竟然低下头来,用他炽热的嘴唇,吸着她脸颊上一颗颗泪珠,好像黑熊在舔着她脸颊,她可以听到咻咻犬息,她颤抖,竭力的扭动着身子,漫漫长途,她只好闭上眼睛,不再看他,也不再看到一切。
车轮不停的朝东北方向滚动,午牌时光赶到宁都,车子在一家饭馆前面停了下来。
束小蕙依然闭着眼睛,假装困睡,她听到韦宗方下车去了,吩咐赶车的好好守护:一回工夫,饭店里的伙计替赶车的送来了饭菜,那赶车的就在车上吃饭。
又过了一回,韦宗方回来了,他敢情买了一大包馒头,卤菜之类的东西,一面轻轻抚着自己肩头,柔声道:“好妹子,你大概早已饿了吧,快睁开眼来,将就着吃一些吧!”
“恶贼,谁是你的妹子?”
束小蕙心中暗自盘算;吃东西的时候,你总要替我解开手肘上的穴道,只要你一拍开穴道,我就用“突穴斩脉锁龙手”,先制你穴道再说。
她心中忖着,但却没有睁开眼来望他一下。
韦宗方温柔的道:“好妹子,你快醒醒,瞧,我替你买来了卤菜、包子,还有馒头,来,快睁眼来,我喂你吃吧!”
恶贼,好狡狯的恶贼!”
束小蕙心都快气炸了,暗想:“他喂自己,那是不肯解我穴道了,哼,谁要你喂?我宁愿饿死,也不要你喂我。”
她紧闭着眼睛,死也不睁。
韦宗方道:“好妹子,你还在生我的气,好,现在不想吃,就等一回再吃吧!”
车前,赶车的回过头,低低问道:“老大,咱们可以上路了吧?”
韦宗方接道:“也好,咱们赶到广昌下店,路程不远,这条路颠簸不平,走得漫一点,车子就稳得多。”
赶车的道:“咱们今晚可以赶到南丰。”
韦宗方道:“不、到广昌就好,大家也好早些落店休息。”
赶车的轻笑着应了声“好”,“早些落店休息”,这几个字听到束小蕙耳中恍如焦雷,他为什么要早些落店休息?显然这恶贼没安好心!
她又气又急,如今她只盼望欧伯伯和韦宗方早些赶来,照说,他们昨夜找不到自己,就该一路迫下来了,以两人的脚程,怎会赶不上马车?莫非他们追到前面去了?真是糊涂,路上发现马车,总该瞧上一瞧才对!她不知前晚救回去的韦宗方,就是劫持她的人,还在一心盼望韦宗方来救他。
车轮又在滚动了,但行没多久,只听前面赶车的压低声音,叫道:“老大,好像有人追上咱们了!”
韦宗方急急问道:“老五,是什么人?”
原来赶车的是他同党,一个叫老大,一个叫老五。
那赶车的道:“是个老头。”
束小蕙心头一喜,暗道:“是欧伯伯赶来了!”
“老头?”韦宗方声音有点嘶哑,吃惊的道:“他……他是怎样一个人?腰背驼不驼?”
赶车的道:“不驼,不过个子不矮!”
韦宗方道:“穿的是什么衣服?”
赶车的道:“穿着一件灰布长袍。
束小蕙感到失望,心想:“那不是欧伯伯了。”
韦宗方吁了口气,也在暗想:“自己真是庸人自扰,老匹夫中了自己三支掌中针,那会有命?”
只听赶车的续道:“这老头子方才就在饭馆前面徘徊,小弟早就怀疑他路数不对,咱们一动身,他就一路远远迫了下来。”
韦宗方阴哼道:“只有一个人?”
赶车的道:“只怕他还有同党,啊!老大,要不要在路上给他留些香料闻闻?”
韦宗方道:“也许是行路的。”
赶车的道:“行路的人,干么一直要追着我们,不即不离的。”
韦宗方道:“你赶快些看看他还跟不跟?”
赶车的答应一声,长鞭在空中发出“劈拍”声响,抖抖经绳,马匹带着篷车,突然加速往前冲去,辘声轮声,顿时大响,身子不停的左右摇摆,颠簸得更厉害了,显然驰行得极快!
束小蕙心中暗想:“就算跟踪的不是欧伯伯,但有人跟踪,总是好的。”
马车在崎岖的山路上加速飞驰,盏茶工夫,就驰奔出几十里路,前面已是胡岭嘴,南边山势不高,但路可着实隘狭!
突然一声“希幸幸”的马嘶,疾驰中的马匹,陡地刹住,车身起了一阵急骤的摇摆。车轮擦过沙石上,呐起尖锐拖曳之声,骤然停住!
韦宗方大声问道:“老五,你怎么了?”
赶车的道:“前面有一方大石,阻挡了去路。”话声方落,忽然低“啊”道:“这老头好快的脚程,坐在大石上面了!”
束小蕙听的心头暗喜:“事情果然来了!”
韦宗方掀开车帘跳了下去,果见山路上矗立着一方比人还高的巨石,正好挡住了去路。
这方巨石,少说也有几千斤重,一个人决难搬得动它!
石上踞坐了一个灰衣老人,面情森冷,不言不动。
韦宗方剑眉一挑,正待开口!
赶车的回过头去,突然“咦”道:“老大,追着我们的也赶来了。”
韦宗方奇道:“难道不是他?”
赶车的道:“是后面一个。”
韦宗方急忙转过身去,只见后面果然又有一个灰衣老头,急急赶来。
这人和大石上的灰衣老人,身材有几分相似,他奔到车后两丈来远,便自停了下来。
韦宗方脸上闪起一丝冷峻的笑容,伸手朝前一指,回头道:“老五,问问他阻挡咱们去路,意欲何为?”
赶车的答应了声“是”,挺挺腰,大声说道:“老朋友,你阻挡咱们去路,想干什么?”
踞在大石上的灰衣考人重重哼了一声,冰冷的道:“谁挡了你们的去路?”
赶车的道:“这方大石,不是你搬到路上的?”
石上灰衣老人一无表情道:“你搬得动?”
这话不错,你年轻人还搬不动,一个老头如何搬得动?
-------------
幻想时代 扫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