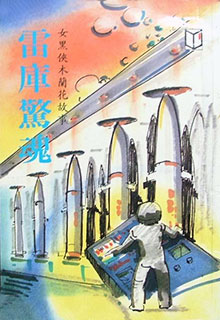木宇真冷冷的道:“借与不借,权在主人,不过……如蒙赐借,兄弟必有以报……”
他说到这里,口气微微一顿,又道“兄弟说的这个‘报’字,诸老可别误会兄弟有什么酬劳,而是咱们两不吃亏而已!”
诸文齐目光深沉,特须道:“老朽倒想听听两不吃亏的解释。”
木宇真轻笑一声,摇摇头道:“这个不能说,只能看,不能言传,只能意会,兄弟的意思,就是让请老借令之后有个交代。”
诸文齐听得微微动容,笑道:“老弟真是越说越使老朽糊涂了?老弟要老朽看的什么?
如何意会法子?”
木宇真含笑起身,说道:“一点也不糊涂,诸老看了这个,自然明白!”
他伸出白润如玉的左手,掌心舒处,摊着两颗黄豆大小晶莹生辉的明珠,轻笑道:“请老看清了吧?这叫做掌珠在握,你老赐借旗令,不是有所交代了吗?”
诸文齐脸露惊诧,憬然若有所悟,口中懊了一声,张目沉声问道:“老弟是说……”
木宇真收起明珠,傲然道:“请老猜得不错,敝师弟容有得罪贵帮帮主之处,兄弟是请诸老卖个交情。”
诸文齐干笑道:“好,好,老朽答应你了,只是如何……”
木宇真不待他说完,接口道:“兄弟信得过诸老,自然先奉明珠,后借旗令,明日一早,诸老以为何如?”
诸文齐嘿然道:“一言为定!”
木宇真满意的笑了笑,拱拱手道:“那兄弟告辞么,请老也好休息了。”
身形一闪,飘然朝门外走去了。
邻房的赵南珩,又何尝睡着了?他只道昨晚没有事故,今晚当然也不会有事,是以就在床上瞑目运功。
小天井中雷电交加,风雨打窗,使他对隔壁一老一少的谈判,丝毫没有察觉。
连宵大雨,但到了翌晨,却是个晴朗的好天气。
旭日东升,阳光普照。
赵南珩刚一起身,就听有人剥落叩着房门,接着木宇真的声音在门外问道:“赵兄起来了吗?”
赵南珩连忙应道:“是木兄?”
开门出去,只见木宇真满脸春风站在门口,向自己使了个眼色,一面朗笑道:“天气已暗,兄弟想起一件急事,立刻就要起程,赵兄昨天曾约兄弟结伴同行,不知赵兄走是不走?”说到这里,忽然低声道:“赵兄快收拾行囊,此地不宜久留。”
赵南珩对这一老一少,自己盘算的结果,一直认为木宇真嫌疑较重,他既邀约自己结伴同行,自是正中下怀。这就朝他点点头,表示同意,一面故意高声说道:“兄弟原因尚有俗务待办,天晴就想动身,木兄既然也急于要走,结伴同行,自是最好不过。”
木宇真笑了笑,就返身回房。店伙送来脸水,赵南珩匆匆盥洗,仍由店伙提着行囊剑铁,跨出房门。
诸文齐敢请听说两人要走,也从房中踱了出来,脸露惜别之容,捋须道:“老朽原想邀两位老弟去寒舍住上几日,略尽地主之谊,不想老弟们走得如此匆促,既然两位有事待办,老朽也未使勉强。”
木宇真一身之外,并无行装,此刻已在檐前等着赵南珩,闻言拱手道:“诸老盛意,兄弟只好心领,有暇当专程奉谒。”
赵南珩朝诸文齐拱手辞行。
诸文齐两道目光,只是打量着店伙手上的倚天剑,一面呵呵笑道:“两位老弟慢走,老朽送你们一程。”
赵南珩还待谦辞,却被木宇真一把拉着,朝前走去,口中爽朗笑道:“赵兄,你不用客气了,诸老的脾气,说过要送,哪肯待在那里,这样吧,就让他送到门口,咱们再告别不迟!”
诸文齐跟在两人身后,大笑道:“木老弟真是深知诸某者也!”
跨出店堂,赵南珩抢在前面,到柜上结算店账。
木宇真只是笑了笑,并没和他客气,一面很快转过身去,朝诸文齐低笑道:“诸老可以验收明珠了,点的只是黑甜穴,大概用不着兄弟代劳了吧?”
诸文齐哼了一声,从大袖中取出一个三寸来长朱漆圆筒,递到木宇真手上,冷冷的道:“老弟果然言而有信。”
木宇真迅速把朱漆圆筒收入怀中,低笑道:“多谢诸老。”
赵南珩付过店账,诸文齐和木宇真也缓步走了过来,跨出门口,小厮已替两人牵着马匹,在门前伺候。
大门右侧,另外停着一辆马车,竹帘低垂,敢情刚从远处她来的。
此时晨曦照耀,虽然隔着一层竹帘,还可隐约瞧到车上的人。
赵南珩无意之中,目光一瞥,发现坐在车中的人,竟是小玫儿,她敢情赶了一夜路程,显得有点困倦,阅着眼皮,斜倚在车座之上。
赵南珩几乎想开口叫她,但立刻想到自己身上有事,还是不招呼的好,何况自己又易了容,她也认不出来。
他心头微微感到怅仍,终于随着店伙,走近马前。
木宇真回过身子,拱手道:“诸老请留步,兄弟就此告别。”
诸文齐站在阶上,手捋柳髯,洪声笑道:“后会有期,两位老弟请上马吧!”
两人从小厮手中,接过缰绳,跨上马背。
赵南珩只听诸文齐的声音,在耳边细声说道:“赵老弟路上留神些才好。”
赵南珩听得一怔,急忙抬目瞧去。
诸文齐一手负背,正在含笑瞧着自己,他连嘴唇都没有动一下,只是两道眼神,在这一瞬之间,竟然深邃前宛如两点寒星,在晨曦之中,闪烁着异彩。他是以“传音入密”的功夫,向自己说的,那么他的意思,当然是要自己防范木宇真了!
木宇真坐在马上,神彩飞扬,轻轻一带缰绳,朝诸文齐拱拱手道:“请老再见了!”
赵南珩也朝诸文齐拱拱手,和木宇真并辔离开客店,朝大路上驰去。
出了归州城,赵南珩再也忍耐不住,偏头问道:“木兄,这位老丈到底是什么人?”
木宇真朝他露齿一笑,道:“兄弟就料到赵兄有此一问,哼!他化了姓名,瞒得旁人,可瞒木过兄弟,他就是南天七宿中的文判诸葛忌,昔年江湖上出名的一笔勾魂……”
赵南珩想起他书僮曾在店门口画笔之事,口中不禁哦了一声。
木宇真又道:“兄弟因为发现他们南天七宿中的老四翻天印单光斗也已赶来归州,说不定有什么阴谋。而且诸葛忌又已对赵兄和兄弟起了怀疑,兄弟走后,可能会对赵兄不利,所以才劝赵兄结伴同行。”
赵南珩听他说得极为自负,心中不觉大是不服,暗想自己若非想在你身上,查究几件公案,哪会和你结伴同行。一面却故意笑道:“这么说来,兄弟多蒙木兄照顾!”
木宇真人本聪明,自然听得出赵南珩口气,连忙解释道:“赵兄不可误会,若论南天七宿,二三十年以前,就纵横江湖,威震湖广,没一个不是绝顶高手,区区兄弟即使十个人也难是文判诸葛忌的对手,何况翻天印单光斗也在归州出现?”
赵南珩奇道:“他对咱们既然起了疑心,又怎肯轻易放过?”
木宇真笑道:“不瞒赵兄说,诸葛忌自诩成名多年,从不对后生小辈动手,后来他又投鼠忌器……”
话声未落,只见前面大路上,铃驾齐鸣,三匹快马,蹄声急骤,像风驰电卷,迎着奔来。
眨眼工夫,业已由远而近,一匹毛色全黑和两匹黄源健马,泼刺刺直冲到赵南珩与木宇真身前两丈来远!
赵南珩眼看对方纵马疾驰,来势极速,好像没把自己两人放在眼里,脸色方自一变!
就在三匹健马快要冲到面前的刹那之间,陡听一阵希聿聿长鸣,当前黑马,忽然人立而起,一下刹住前冲之势。
稍后的两匹黄瞟,也同时骤然停了下来。
骑在黑马上的是一名身穿墨绿长衫的瘦小个子,他勒住马疆之后,立即朝木宇真抱拳道:“大哥可是已经得手了?”
木宇真早已停马等候,闻言点头,朗笑道:“诸葛忌自视甚高,怎肯食言,四弟何用急着赶来?”
身穿墨绿长衫的瘦小个子瞥了赵南珩一眼,才道:“小弟遵大哥吩咐,早晨把人送出之后,又怕不妥,才赶来的。”
赵南珩听两人口气,才知道这三匹马是接应木宇真来的。
细看那人年约二十五六,紫膛脸,浓眉细眼,但个子瘦小,和他长相极不相称,只是人却极精干,光瞧他适才那一手骑术矫捷刚落,身手之高,已可想见。他身后两匹马上,是两个黑汉子,也只是中等身材,武功似也不弱。
正在打量之际,木字真已含笑道:“赵兄,这是我四弟任宗秀!”一面又朝穿墨绿长衫的瘦小个子说道:“这位是愚兄新交的赵兄……”
赵南珩连忙抱拳道:“原来是任兄,兄弟久仰得很!”
任宗秀神态倔傲,横了赵南珩一眼,勉强点点头道:“久仰……噢,大哥,东西既然到手,救人如救火,迟了只怕有变,咱们……”
他拖长语气,眼珠一滚,瞧瞧赵南珩,便自停顿下来。
木宇真会意地颔首道:“这位赵兄,是愚兄约化一起从归州出来的。”
说到这里,稍微沉吟了一下,忽然转过身子,朝赵南珩拱拱手道:“不瞒赵兄说,兄弟此行,实因师门有人落在南天七宿手中,目前虽已探出眉目,但人还在对方之手,为恐夜长梦多,兄弟急于去营救,此地离归州已远,兄弟就此和赵兄别过。”
赵南珩眼看任宗秀神色倔傲,说话又吞吞吐吐的,好像得着自己一般,心里已感不快。
此刻再听木宇真的口气,说什么“此地离归州已远”,好像自己没有他保护,就出不了归州城似的。一时不由激起傲性,不加思索,脱口说道:“木兄既有急事,只管请便。”
木宇真歉然的拱手道:“赵兄后会有期,请恕兄弟先走一步。”
话声一落,立即一抖缰绳,率同任宗秀等三人,纵马绝尘而去。
赵南珩目送四骑去远,心中陡然想起自己此来,原是为了想从木宇真身上,查探一连串冒用东怪“血影掌”,北怪“归元指”的杀人凶手。
据自己从种种迹象判断,觉得水宇真的嫌疑,远较文判诸葛忌为重,才和地结伴而行,藉机接近,岂可因一时气愤轻易放过?想到这里,心头一急,哪还怠慢,两腿一夹马腹,匆匆朝前追了下去。
但前面四骑总究先走一步,而且人家也在一路急驰,就算双方马匹,跑得同样快速,也已落后一大段路。
赵南珩衔尾急追,奔了将近顿饭光景,依然没有追赶得上。
一过雾渡河,大路有了岔叉,一条朝南去的,较为宽阔,另一条朝东去的,看去不像大路。
赵南珩先前没有注意,仍想顺着大路追去,但临到路口,忽然发觉朝南去的路上已只有两匹马的足迹。
心下一动,立即勒住马头,回身瞧去,果然另外两骑,是抄东首小路去的,皆因连宵大雨,路上还是相当泥泞,马匹经过之处,足迹极深。
这下可把赵南珩看得犹豫不决起来。
暗想,对方四骑忽然分成两拨,当系为了分散追踪者的注意,他们是故意规避自己?还是为了文判诸葛忌?
从木宇真和任宗秀两人的口气听来,他们好像弄到一件什么东西,才能救人,那么他们可能是遇避诸葛忌成份较多。
何况救人如救火,抄小路总比走官道大路要近,由此推想,两个黑衣汉子走的准是大路,水宇真和任宗秀可能朝东首小路去的,自己当然也以抄小路为是。
心念电转,立即拨转马头,朝东首小路奔去。这一带已接近荆山脉,远山起伏,村落稀少。赵南珩只是跟着两匹马的蹄迹,一路紧追。
不多一会,前面又有了岔路,一条是朝荆山方向,道逦往北,另一条却是继续向东。再一注意,两行马蹄,到了叉路,果然又分道场镰,各奔一路。
赵南珩略一打量,暗想这条往北去的,似是深入山区,莫非他们要救的人,就在山中不成?他不再多想,跟着朝北奔去,哪知走没多远,马蹄印突然中断。
这里既然无树林,又不靠山,一行马蹄,甚是清晰,当然也没有回转,就是忽然没了影子。
这一人一骑,生似走到这里,突然平空飞上天去了!
赵南珩在马上瞧得暗暗奇怪,这一路既然追丢了,再追下去,也是徒然,他迅速循原路退回岔口,再朝东首小路上寻去。约摸走了里把小路光景,路上蹄迹,也突告中断。
赵南珩越瞧越奇,这两匹马既没回转,怎会手空失踪?他跳下马背,凝目瞧着地上蹄印,怔怔出神,虽在片刻之间,他已经想过许多种假设,但怎么也想不出一条理由,能把两人两骑的神秘失踪,得到满意的解释。
他一手牵着马匹,缓缓朝前走去,目光只是注视泥泞而有碎石的路面。忽然,他在路边草丛中,发现一行断断续续的足尖迹印。
因为这足尖印杂在草丛之间,如非低头细看,决难看到,即使看到了,路上当然会有行人。行人怕路中间泥泞,靠着草丛走去,也是寻常之事,谁会去注意它呢?
赵南珩也是心中疑团难释,默默的踏着这行足尖,朝前走去,又走了差不多一里来路,前面已有一道大河,挡住去路,当然这行足迹,也是及河而止!
不,河边上突然有了一堆零乱的马蹄迹印!
“是了!”
赵南珩蓦然若有所悟,双袖一掳,功运两臂,蹲下身去,两手轻轻托起马腹,点着足尖,施展轻功,走了几步。
然后放下马匹,把自己在地上留下的足迹,和对方比较,显然自己的足尖印,还比对方浅了许多,可见木宇真和任秀就是这般过来的。
他们如此做法,自是为了混乱追踪者的眼目,好让别人疑神疑鬼,猜不到他们下落。
而且这大河边上,敢情早已预备好了船只,看来他们这一行,当真行动诡秘,一路都有人接应!
哼!木宇真……任宗秀……这两个名字,可能都是假的啊!赵南珩突然想起月前误闯东华山庄之事,他们的香主,不就是姓木?难道木宇真就是东华山庄的香主不成?自己先前怎会一直没有想到?
东华山……
西宁山……
-------------
幻想时代 扫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