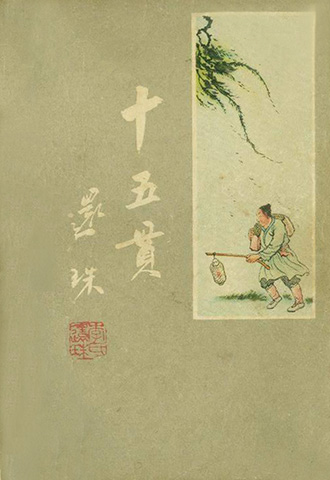三天之后,管一见刚吃饱晚饭倚在椅背上品茶。他本身嗜茶,对茶叶之色、香味都颇有研究,而对煮茶的火候控制造诣亦甚高,连带他不少手下亦染上茶嗜。
端木盛就是其中一个佼佼者,不单只对于茶道,其他一切他都刻意学他。
此时他正在陪管一见喝茶。
管一见呷了一口,皱一皱眉,道:“你这水煮得太熟。”
“头儿不是说水应该煮到冒起蟹眼才是上佳的火候么?”
“但是,你煮了水才去准备茶叶,虽然熄了火,但炉中尚有余温,是以这水就太熟了。”管一见一说到茶道,就滔滔不绝,他改一改姿势正想再说下去,楼梯上却响起一阵“砰砰砰”的脚步声。
“盛老弟,你猜是谁?”
“一定是夏四弟,他性较急,不过他轻功还不错,但这脚步却显得异常,定是发生了什么急事,而又经过长途奔驰。”
管一见面露满意之色。果然楼梯处出现一张国字形的脸,满头汗珠,正是夏雷。
夏雷喘了一口气,道:“头儿,城外发现杜一非的尸体,是自杀的。”
“您怎知道他是自杀而不是被杀?”管一见霍地站了起来。
夏雷喘息未定:“上吊……”
管一见道:“走!”三人迅速披衣下楼。
路上,管一见道:“叫你们在项府门口监视,为何让他死后才知道?”
夏雷说道:“杜一非释放之后,立即回去项府,直至今日不见他离开过项府一步。”
“那他又怎会跑去城外上吊?”
夏雷不禁默然。
管一见骂道:“你做事就是粗心。”
夏雷做事已算细心,只是在管一见的四大猛将中,他显得较粗心而已。
此时他心中亦是疑团难释,却不敢吭声。
“他的尸体谁发现的?”
“是……是属下碰见苏捕头,他告诉我的!”
管一见更怒:“饭桶,还不如一个小小的捕头!”一会又问:“项府的人知道了没有?”
“半路上碰到项家四兄弟带着一些护卫赶去。”
管一见哼了一声,脚步更急,一掠便是丈三,不一会已出了北城门。
没有一点灯光,幸好明月如轮,银光照路。
前头一株大树之下,黑压压地围了不少人,一会,风火轮叫道“不要争了,头儿到了。”
管一见与项家兄弟略一打招呼,旁人已让开一条路来。
杜一非的尸体已从树上解下,放在地上。
管一见看了一会,道:“苏捕头,谁发现的?”
苏捕头指着一个农夫道:“这人发现的。”
那农夫见来了大官,忙跪下道:“启禀大人,小人今天挑了一担菜到城内去卖,黄昏回家时经过才发现的。”
“当时,附近有没有人?”
“没有。小的吓了一跳,奔回城中遇到一个公差大人才告诉他的。”
管一见道:“把尸体移去殓房,大家散开。”
项平东道:“管前辈,你这就走了?不再调查一下?”
“调查什么?”
“调查杜叔叔为何会自杀嘛。”
管一见道:“到衙门里再说,你们四兄弟跟我去衙门一趟。”言毕头也不回地走了。
衙门内苏捕头的房中,管一见跟端木盛坐在椅上,项家四兄弟坐在床上,夏雷守卫于门外,严禁任何人走近。
管一见道:“项平东,刚才管某听你说话的语气似乎表示你略知杜一非自杀的原因?”
项平东说道:“杜叔叔素来好赌,不过他为人十分重信诺,而又十分光棍——愿赌服输,因此,他虽然经常输得囊空如洗,依然很多人喜欢跟他赌,而家父生前亦依然重用他,而且,他虽然好赌,但办事却十分尽力,故此,先父亦曾替他还过十万两的赌债,而咱兄弟亦依然十分敬重他。”
他低下头,声带悲戚:“两个月前,他找晚辈说有件事要跟我商量,原来他欠了人家五十万两银子,给人追得很急,便想向晚辈挪借一下,因为寒舍的钱财是晚辈管理。可是,家父素来严厉,公款晚辈是万万不敢擅取,只得把历年来自己的私蓄借与他,但也只得三十万两。临走时晚辈便对他劝戒一番。可是,前一阵他又要求再借二十万两,晚辈实在已没有,因此,只得向他实说,当时他好像颇颓丧。三天前,他回来后又向我说他把债权人杀死了。晚辈问那人是谁,他说是云天赌坊的姚老板。晚辈大吃一惊,便道姚老板是‘一指勾魂’霍老头的心腹,你杀死他时可有人看见,他接声说已让管前辈知道了,当时晚辈大怒,于是严词责他,并说如果霍老头知道后,少不免要生了一场风波,而家父及三弟刚过身不久,大局未定,实不宜在此时招惹强敌。”
项平东喘了一口气,才道:“大概因为如此,才令他出此下策,对于他的死晚辈甚感不安,当日晚辈可能斥责过严……其实即使霍老头兴师问罪,咱项家亦不惧他。”
管一见不语,半晌方道:“你没有苛责他,还不起债而杀人,本就是大错。不过,有一件事要再问一问你们,杜一非真的是上吊自杀么?”
众人一怔,道:“亲眼所见,自是真的。”
管一见望住端木盛,道:“你又如何看法?”
端木盛心头一动,脱口呼道:“果然有疑!”
“你把你的疑点告诉他们。”
端木盛兴奋地道:“对,一定是,杜一非一定是被人杀死的,凶手杀死了他然后才把他吊在树上。”
项家兄弟又惊又难以置信,项平东笑道:“这位英雄莫非亲眼所见?”语气中揶揄之意人人都听得出。
管一见沉声道:“管某肯定地说,杜一非的确不是死于自杀,而绝大可能是被人杀了,然后挂上树枝,布下假局。”
项家兄弟,都是心头大震。项平北道:“前辈据何理由,下此定论?”
“很简单,如果一个人是颈部被捏、绞、吊、勒而死的,有个特征,死者舌头必然伸出嘴外。杜一非死得很安详,那绝不是一个因吊颈窒息而死的表情。”
管一见站了起来,踱着方步道:“通常在上述情况下死亡的人,表情必显得异常辛苦,而且,经常有挣扎过的情况。杜一非死得如此安详,又没有伸出舌头,内行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凶手布下的假局。”
项平东脱口道:“为何苏捕头看了这么久也没有发觉?”
“因为他不够冷静,被假局所迷。管某还敢断定凶手机心虽深,却绝非老手。”
项平东道:“那么管前辈怀疑凶手是谁?”
管一见道:“管某若然知道,又岂会叫你们来此商量?”
项平东道:“前辈说的是。”一转腔,“会不会是‘一指勾魂’手下所为?”
“绝对不是。若是‘一指勾魂’霍凌的人杀的,他何必布下此假局?凶手布下此假局,无非是要别人不要怀疑到他身上。”
项五郎颤声道:“那是为了什么?”
“因为,杜一非与杀项天元及项平南的凶手有关,又与‘降龙伏虎’有关,而这凶手又是项家熟悉的人,因此,在他们还未达到目的之前,不能暴露身份。杜一非已被管某思疑,他们势必知道,故此杀之以防秘密外泄。”
项平西怒道:“这是些什么人?让咱知道了,不把他一刀一个才怪!”
“好,你们回去吧,有需要的话,管某会派人去找你们。”
项家兄弟心情忐忑,告辞而出。项平东道:“希望前辈早日破案,免项家再受不幸。咱兄弟亦感激不尽!”
×
×
×
管一见又在小楼里踱方步,杜一非之死使他对案情有进一步的了解,如今他几已肯定凶手在项府之中,而且大有可能是项家四兄弟中的一个。
“高老弟,烦你再去项府调查一下,他们这一二天有没有马车之类的出入。”
高天翅随即道:“他们每日都有三架木板马车出入。”
管一见目光一亮:“哦?怎地没听见你们提过?”
“那三架马车是用作购买鱼、肉、菜疏及日用品之用的!咱每天都有派人跟踪,都没有发现异样。”
管一见道:“杜一非的尸体一定是藏在木板马车之下运了出去。这些日子来每日如此,也因此而引起跟踪的人麻痹,从而疏忽了。去,去找项府那三个驾车的人来。”
“是。”高天翅应了一声,趁着月色赶去。
高天翅带来的消息并没有令管一见有太多的奇怪。
“那三个人回来之后都立即辞别而去了。”
“项府没有监视他们?就是这样凭一句话让他们离去了?岂不怪哉!”
“他们是三兄弟,项天元生前已让他们退休了,因为他们都已是超过六十岁的老人,跟了项天元亦已超过二十年,而且他们在三天前已向总管董中平辞职。”
“哼,狐狸终于会露出尾巴来。明天,咱们去一趟项府便能水落石出。”
×
×
×
暖和的阳光刚照在窗台,管一见及其四大虎将便已到了项府。
项平东兄弟迎于阶前:“管前辈莫非已找到凶手?”
管一见笑而不答:“管某想到令尊生前寝室再看一看。”
项平东肃手道:“前辈请。”领着他穿舍过户到内院去。
管一见道:“你们在这里稍候,项平北你跟我进去。”
“是。”项平北推开了门,“前辈先请。”
管一见揭起席子,项天元生前用“隔山打牛”功夫以手指划下的那个“一”字,仍然那样醒目。
“把房间关掉,我有话问你。”
项平北随即把门关上:“前辈有话,但问无妨。”
管一见道:“管某只叫你一人,用意有二,一则,管某认为你是最没有嫌疑的一个,二则,你是极力主张聘请管某调查此案的。”
他吸了一口气,缓缓地道:“如今管某可以肯定的说一句,凶手就在贵府中,而且,是你们兄弟中的一人,因此才会对贵府的人与事都了如指掌。”
项平北心头如遭雷击,整个人都震动一下,但他终没有出声打断管一见的话。
“杜一非肯定是在贵府中被杀:尸体料是绑在每日购买食物的木板马车之下运了出去,然后把他吊在树上,巧布假局,可惜凶手是个新手,才会犯下这一错误,如果他把杜一非埋在地下,反而没有疑点。杜一非死得安详,那表示生前绝无反抗的迹象,这是死于何种情况?”
项平北脱口道:“死于猝不及防,而且凶手与杜一非必定关系密切,是以杜一非才会毫无防备!”
管一见颔首:“但凶手是谁?”
项平北苦笑一下。
管一见道:“叫你五弟进来。”
项五郎入了房,项平北正欲退出,管一见道:“不必。”项平北回手关门坐下。
管一见对项五郎道:“腊月八日令尊之死被金花、银菊发现,而发出惊呼,当时你在房里还在睡觉?”
项五郎道:“晚辈当时早已睡醒,不过尚躺在床上,一听见呼声,立即披衣飞出去。”
“衣服放在什么地方?”
“外衣就放在床头,当时晚辈还是穿着寝裤出去。”
“你出去时见到什么情况?”
“大哥在询问金花、银菊,三哥亦刚出房门。晚辈赶到金花、银菊面前时,大哥已抢入房中!”
“你进入此房,有没有探一探令尊的气息或身体?”
“有。晚辈曾经摸一摸先父之额头,但入手冰凉,显然已死去一段时间。”
管一见转向项平北,道:“假如令尊当夜写了些字,或者是遗嘱之类的,你们认为会写些什么?”
项五郎说道:“那自然是与继任人有关!”
管一见目光大盛:“对,但如今不见有张纸屑留下,那说明什么?”他见两人都不答便再说下去,“说明那张遗嘱的内容对凶手绝对不利,因而引起他下毒手把令尊杀死。”
项平北兄弟面面相觑,既不敢不信又不能不信。
管一见目光一瞥桌上的毛笔,心头一动,再目注床板上那个“一”字,片刻立即发出一阵大笑。
项平北兄弟大诧,问道:“前辈笑什么?”
管一见道:“这个‘一’字!哈,凶手是谁管某已推算出来了,走,到外面去!”
管一见推开房门,见只有一个项平西,不禁一怔,脱口道:“项平东呢?”
项平西道:“大哥说要请前辈及四位英雄在寒舍吃顿便饭,他去交待厨房。”
管一见脸色一变,急道:“项平北、高天翅、端木盛立即去把他找来,速速勿误!”
高天翅及端木盛立即轰应一声,项平北脸色剧变,怔怔地望着管一见:“管前辈你……他……大哥他……”
管一见沉声说道:“快去,迟则来不及!”
项平北立即带着高天翅及端木盛去!
项五郎颤声地问道:“前辈怀疑大哥是……”
“不是怀疑,而是令尊告诉我,凶手就是他!”
“大哥是杀父凶手?”项平西怪叫道,“你胡说!”
管一见冷笑不语,双眼望天,两盏热茶过去了,仍不见项平北等回来,他喟然道:“已迟了一步,项平东果然做事谨慎,难怪‘太湖龙王’项天元会派他管理账目!”
他再次转身入项天元生前寝室,项平西及项五郎旋即跟在他身后。
再过半炷香工夫,高天翅等气急败坏地奔入来:“头儿,据看守大门的人说,项平东刚才骑马出去,他说有点急事要出去一趟。”
管一见冷笑道:“哼!果然不出我之所料。”
项五郎道:“请管前辈明言,以开晚辈茅塞!”
管一见道:“你们先派人去吩咐手下全力戒备,依管某看,项平东不久将会带同‘伏虎降龙’的人前来围攻。”
项平西急道:“前辈快说,急死我了,四弟你去一趟吧,叫董总管负责布置人手。”项平北只得出去。
管一见站了起来,道:“这件事得由开始说起。起初管某也只怀疑杀害项天元的凶手是项天元所熟悉之人,也即是说凶手亦是熟悉项府的人,否则他岂能轻易潜伏到此处而不被人发现?后来杜一非因好赌欠下云天赌坊一大笔赌偾,而突然能还了三十万两,于是引起我的怀疑,怀疑这个‘一’字是指杜一非。”他指一指床上。
“可是杜一非之死又使我怀疑主谋另有别人,杜一非只是把项平南的行动泄漏出去而已,至于那个老张也是凶手布下的一个假局,目的是掩护杜一非及主谋人,否则老张既然身上有明显的特征,凶手若要毁尸灭迹的大可以把他斩成十块八块然后分开埋葬。”
项五郎不禁点了点头,高天翅等亦暗暗佩服管一见精细而又冷静的头脑,暗叹道:“看来我今生今世也不可能学到头儿八成的本事。”
管一见续道“杜一非的尸体装在袋中,利用每日购菜的木板马车运出去。马夫已经有意辞职,项平东必然知道,故而订下此一计划,花了些钱请他们把尸体还交与某人,那三个车夫一则不知内是何物,二则碍于大公子之面,当然答允。而那个人必是‘伏虎降龙’的人,便依指示把杜一非挂在树上。”
项平北此时已回来,闻言道:“且慢,前辈怎会怀疑凶手及主谋人是家兄?”
管一见叹道:“管某若不先把此关键告诉你们,谅你们也不心服。”咳了一声道:“管某头一次怀疑项平东是始于在衙门内他告诉我取了三十万两借与杜一非,既能取得三十万两为何不把剩下的二十万两借给他?不错,他说他钱不够,不过大可以先向你们挪借一下,相信你们也不会拒绝,二十万两,平均向你们兄弟每人借五万两而已,数目不算大!”
项平西道:“正是,咱兄弟每人起码有近百万两的储蓄,大哥说他只有三十万两我就不信。依我看他平日必定在账目上做了不少手脚,只怕他的钱比爹还多。”
项平北却说道:“前辈又是如何看法呢?”
管一见道:“管某当时心中立即有个念头,那三十万两不是借与杜一非的,而是送给他作为收买的,他故意留下二十万两作为鱼饵,以便到时能利用他。”
“利用杜叔叔做什么?”项五郎不禁脱口问道。
“把项平南的行动泄露出去。当然,他大可能只是告诉他一句无关重要的话,而这话却是他与‘伏虎降龙’的暗号。项平南出发前的一夜,他已要杜一非把那句话说与某个人知道,故此‘伏虎降龙’赶在项平南之前预先设伏。”
“晚辈虽然已大为信服,但前辈尚未说到关键之处。”
管一见接口道:“第二个疑点是项平东的住所比项平西及五郎的远,为何能反而先到?一个原因:他因为己经知道真相,又怕迟到会引人思疑,于是一直在蓄势以待,金花一惊呼,他便奔出。可是,他太早到达现场,反而引起我的思疑。第三就是这个‘一’字,你们看看有什么新发现?”众人看了一会都没有新发现。项平北道:“前辈不是说这个‘一’字可能是东、西、南、五这四个字的第一笔?”
管一见道:“原先管某是这样推想,后来看了桌上的毛笔却使管某另有想法,这个‘一’字笔划均匀,但落笔和收笔处都较重。”
众人再看一眼果然如此,都是暗自忖道:“管神捕目光果然不比寻常。”
项平西愕然道:“这也是线索?”
管一见颔首:“这是表示这个字已经完成。试想在当时那种紧急的情况下,项天元以指代笔写下凶手之名字,第一,绝不会工工整整的写;第二,必是以最简单最快能写成的字表示。比如说,项天元若要写个‘五’字,那么必是一笔写成,而若写了一半便咽气的,那么这一笔必是落指时较重,而尾部必较轻,因为那个字尚未写成,这就和用毛笔写字的道理一样。故此,管某断定这‘一’字已经是一个完整的字,就是个‘一’字。”
项平西更加摸不着头脑:“这一个字与大哥有何关连?”
管一见笑道:“这正是关键之处。当时危急之情况已大出我之预料,亏得项天元能想得出以最简单的字来表达。项平东是他第一个儿子,也即是长子,他便以‘一’字来代表。此际管某对令尊的能力亦不禁大为佩服。”
各人此时对管一见亦更为佩服。
项五郎道:“晚辈尚有一个疑问想请教前辈。”
管一见神情异常愉快,道:“欢迎你们提出来。”
项五郎即问道:“家兄为何要杀杜叔叔?不杀岂不是更没破绽?”
管一见笑道:“这与他的性格有关,令尊没有看错人,派他管理账目钱财,这种人必定是小心谨慎,做事精细,但凡这种人材却又非领导人材,因为容易犯出抓小节忘了大局,这种人一般又是心胸较狭,难以统率群雄,而且疑心较重,正因为疑心较重,因此一直恐怕杜一非在事后会发生思疑:大公子为何会送三十万两给我,而只不过求我带了一句无关重要的话?
“故此,他为求万一便把杜一非杀掉,以防把秘密泄漏出去!”
项平北旋即问道:“家兄又为何会动杀先父之心?”
“因为,令尊本拟在七日晚上宣布谁是继承人,可惜因为你赶不及回来,因此他欲改在你回家之后再宣布,但是,那夜他猜想你可能遇到危险,因此把继承人的名字写在纸上。
“以管某推想,令尊大概是看中你,又恐其他人不服,因此叫项平东入房陈明他的意向,要项平东助你一臂之力,说服项平南及项平西二人。项平东说令尊要他管教弟弟倒没有完全说错,不过说漏了一段。”
管一见喘了一口气,道:“项平东实在谋位已久,听了令尊一席话自然十分沮丧,不过他是个城府深沉的人,只怕他一早便已利用职位上的方便——四处收账,勾结了一批人作其他日夺位之用。
“那夜,他必然是起了杀机,因此再潜入此地,见了令尊之遗嘱,知道完全没望,便杀了令尊。至于他能够潜入此地亦非难事——偌大的一间楼宇只得蒋公龙一人巡卫,岂无空隙?”
项平西脱口道:“家父又为什么不呼声?”
“有两个可能,第一,令尊尚存有侥幸之心,以为项平东不会下毒手;另一个可能,当时令尊旧患复发,咽喉被痰封住,喊不出来。”
高天翅道:“老大,是谁告诉杜一非说姚老板使诈?”
“当然是项平东。他知道只要杜一非一离开便会受我们跟踪。而只要杜一非杀了姚老板,我们自不会放过他。他要假借我们之手,把杜一非杀掉,谁知我偏把他放了,项平东只得自己动手。”
至此众人皆无疑问。
项平北道:“时候已不早,请前辈到厅中用饭。”一行人鱼贯出房。
×
×
×
午饭之后,项平北吩咐手下送上荼来。管一见一喝,双眉锁起,叹惜道:“这茶叶是武夷名种,可惜煮茶功夫实在不敢恭维,这好像是把武林绝学拿给一个毫无基础的人去练,可惜可惜!”
项家兄弟都因知道了项平东是杀父及杀死自己兄弟的凶手,心情都异常复杂,既愤怒又悲哀,既不想接受此一事实又不能不接受,是以对管一见之话都听而不闻。突然,董中平急步入内报告:“禀公子,大公子带了好些人来,要硬闯入来,望公子指示一下行动!”
项平西怒道:“以后不准叫他大公子,他是杀死爹爹的凶手,大逆不道,弑父杀弟,还跟他客气什么!杀!”
项平北忙道:“且慢,管前辈有何妙策?”
管一见靠在椅背上,懒洋洋地说道:“这已是脱离管某的职责。你们只是聘请管某替你们查案,并没有聘请管某代为缉凶!”
“如果晚辈现在聘请呢?”
“价钱另议。”
“前辈尽管开个价。”
“有两种价格,一种是要管某全力替你们把主凶捉来,这种价格较贵起码要十万两;另一种只是聘请管某等五个人从旁协助,这价格嘛,五万两就差不多了。”
项平北看了兄弟一眼,项平西道:“就你们五个好了!晚辈若不揍他几个实在会憋死!”
管一见道:“若让管某自己选择,管某也是喜欢这一个方案。”
项平西讶道:“前辈不想多赚?”
“非也,管某那些虾兵蟹将若出来献丑,死伤难免,虽然少赚五万两,但要多付汤药费及抚恤金,可能反要亏本。”
董中平见他们尚在蘑菇,不禁急道:“公子……外面已经打起来啦。”
管一见正容道:“你们先出去压压阵脚,管某在后面看看他们的声势再说。”
项府门外是一块空地,此时双方正在混战。项平东的手下大概有四五十个之多,不过人人武功高强,俱能以一挡二三,因此双方实力倒也相埒。
项平西排众而出,虎眼圆睁暴喝一声,如同起了个霹雳,指着项平东骂道:“你还有脸来!”
项平东冷冷地道:“我如今是‘伏虎降龙’帮帮主,有何不敢来之理?”
项平西更怒:“既然断了手足之情,我第一个找你!”拔出缅刀,蓄势以待,他虽暴躁,但刀一在手,整个人便好像冷静了不少。
项五郎道:“二哥且慢。大哥,你为何要做此大逆不道之事?难道你竟没有父子兄弟之情?”
项平东嘿嘿冷笑道:“古往今来哪个大英雄大豪杰不是为权而干戈?几多大英雄为了夺权什么事未做过?弑父杀弟?奴颜屈膝?出卖师友?杀妻卖妾?毒杀亲儿?断送姐妹女儿?造谣中伤?借刀杀人?冤屈亲友?哪一项没人做过!项平东比之他们实乃小巫见大巫,只因你等是云鹊,又岂知鸿鹄之雄心壮志!”
项五郎道:“但,自古以来又有几多是忠孝双全、德智俱备的大英雄,大哥何不学他们?”
项平东道:“五弟,你不用多说,自今起你不要叫我大哥,我亦不当你是弟弟,免得阵上相见下不了手!”
项五郎垂泪叹道:“大哥你又何必如此,你要继承父位只需说出来,做弟弟的岂有不让你?”
项平东哈哈大笑,良久才止住:“你年纪还小,岂知人心叵测,这种事大概也只有你肯做,老二、老四他们肯吗?”项平北道:“只要你说出来,大家不妨商量商量。”
项平东冷笑一声道:“如何?连老四都不想放过争夺的机会,何况老二老三他们?”
项平西道:“别人叫我不争还可以,就是你我不肯让!”
项平东又是哈哈一声冷笑:“这又只不过是找不到好藉词的藉口!”
项五郎道:“大哥这样做大概因为爹爹把位传给别位哥哥,所以……”
项平东沉声道:“当然啦,要不何必出此下策!”
项五郎道:“那么请问爹爹是把位传给谁?”
项平东哈哈一笑,道:“那张遗嘱,我看过已把它烧掉了!你也太天真了,我会告诉你们吗?”声音转厉,“我要让你们自己瞎猜,让你们自相残杀,这杀弟之罪嘛,大家一起背!”
项家兄弟及项府的护卫们听了无不连连打冷颤,身子无风自动,觉得人心之险毒莫过于此。
半晌,项平北道:“你自认今日有必胜之把握?”
项平东正容道:“明知胜少败多也要来,所谓成则为王,败则为寇,不成功则成仁又有何惧?如今是骑上虎背,身不由己,不能不来。”一顿又恨声道:“不过,即使我失败了也要把你们的根基摇松,免得你们太舒服!”
项平西暴喝道:“既然如此,何必多废话!”
管一见即时传声过来道:“把他们放进来!”
项五郎迅即扬声道:“咱们退入门内,大哥你再想想,勿再陷于难拔!”
项府护卫立即依次退入门内,行动划一,不慌不忙,不急不乱,显然平日训练严格。
项平东道:“我还有拔足之机?不到最后一刻绝不甘心。”随即对手下道:“冲入去,成则人人有赏,退亦无翻身之日!”当先冲上去。
除了三几个临阵退缩之外,余者亦蜂拥而入。
一待“伏虎降龙”的人全部入来,管一见立即从门后闪出,同时把门关上。
云墙高逾二丈,门是铁铸的,门一关上,有如关门打狗。
项平东一见管一见,脸色剧变,先红后青,阴森森地道:“项平东落得如此,全是你这个老匹夫所赐!”
管一见正容道:“这种话管某已不知听过人家说了多少次了。每一个犯人被管某捉住,都有此说,老夫亦听厌了!”
项平东暴喝一声,道:“今日有你没我!”缅铁刀一扬,带着阳光疾向管一见劈下。
刀一出,人亦随之扑上,宛似一道彩虹,刹那刀只离管一见胸前半尺。
他快管一见也不慢,双脚一错堪堪避过。
项平东状若疯狂,叱喝之声不绝于耳,刀锋一偏改劈为削,刀至中途一削变成三削,“奔雷刀法”果然名不虚传。
管一见一闪再闪,第三刀眨眼即至,管一见屈起中指,指节敲在刀背上,“当”一声响,缅刀给他敲开一尺,管一见一拧腰已脱出刀势范围。
项平东急怒攻心:“老匹夫怎地不用兵器!”
管一见冷冷地道:“对付你老夫空手自信还能够收拾!”
项平东如同被剌伤的猛虎,嚎道:“那你又不敢与我面对面见个真章!”
“待老夫出手,只怕你已经是悔之莫及!”
项平东怪叫一声,刀光更盛,不顾性命般一口气劈了六六三十六刀。可是刀刀落空,连管一见的衣衫也沾不着。一阵狂攻不果,使他头脑冷静下来,手更沉稳,刀比风紧,出手颇具名家风范。
项平东一出手,项平西亦即拔刀飞劈,只三刀便把面前那人劈作两半。他踏上一步,缅刀一抡,刀光立即绕上两个贼徒!
项平北亦刀不留人,招招都是最狠辣的。
项五郎却不如两位哥哥的勇狠,不过,二十招一过招数亦渐辣。
高天翅及皇甫雪等四人更不打话,好像这样场面他们已经司空见惯,下手绝不稍作犹疑。
他们一动手,董中平便指挥一干护卫,轮番冲杀,以多制少,先行杀了十个八个,然后指挥他们以两敌一,分组各自找对手格杀。
一时之间杀声震天,中院及后宅之妇孺亦听见。甚至附近的居民亦惊动了,不过,他们平日对项府都有三分畏惧,此时更加紧闭门户,不敢出门。
再过一阵,“伏虎降龙”虽然亦伤了不少项府护卫,但对方人多,一有人伤亡立即又有人替上,实在杀不胜杀,锐气亦自馁了,况且自己这方面伤亡亦不断增加,实力相差更远。
再过一阵,项府护卫已是以三敌一,而且四周尚有不少生力军摩拳擦掌,虎视眈眈。一阵心寒之下,不知哪个先行抛下兵器求饶,此人一磕头,其他人亦纷纷效尤,不一会亦全部解决,只剩项平东及管一见,一时尚未分胜负。
管一见环顾四周一眼,道:“你手下已经全部投降,你还不弃刀受缚!”
项平东趁他说话分神,猛攻七刀:“有本事你便把我杀了!”
管一见冷冷地道:“要杀你还不容易?老夫要把你生擒,交给你弟弟们自行处理。”
项平东闷哼一声,不再说话,右手缅刀一抡,向管一见头部横削,左手一式“金龙探爪”,疾抓管一见胸前。
管一见蹲下,右手骈起双指划向项平东左手腕脉。
项平东左手一沉,自下向上抓向管一见右手腕,右手刀锋倏地一转,临到对方头上四寸,改削为斩。
这变化快迅诡异,若说他的武功在项平西之下,只怕他死也不服!
管一见猛觉头上生风,足一顿,整个人如皮球般斜弹起来,拔起一丈五尺高。
项平东缅刀急如风车,向管一见绞去,人亦狸猫般蹿起。
人在半空,面迎斜阳,丹霞如火,残阳似血。
管一见一折腰,平射半丈。
项平东刀一落空,身形去势未尽,左足尖在右足上一点,拧腰斜追管一见。
人如游龙在空横飞,众人都抬起头注视。
管一见一曲腰,一个跟斗翻下,双脚如石柱般栽在地上。
项平东猛一沉身,头下脚上,缅刀疾势而下,曳起一道红光飞向管一见头顶。
管一见气定神闲,待缅刀离头才不过半尺,右手蓦地鬼魅般伸上,双目如电,骈起双指,电光石火般把缅刀夹住。
项平东蓦觉身形一滞,猛吸一口气,挺腰竖起,同时右手刀猛使劲。刀沉二寸,尚离管一见头顶一寸半。这一寸半之距离似天际,可望不可即。
管一见双脚微弯,坐马沉腰,食中两指仍然夹实缅刀。
项平东右臂一条条青筋蚯蚓般凸起,仍然毫无寸进,额上热汗簌簌流下,热汗淌过眉毛眼盖,比蚁咬还难过百倍,项平东左手不敢去拭抹,甚至连想也不敢想。
热汗淌过鼻尖滴下,点点的汗珠滴在管一见脸上,管一见却连眼也不眨一下。
斜阳射在项平东脸上,脸如柿子,又似火烧,实际上,此时他的面色却又青又白。
两人一上一下,宛似两尊石像般僵持着。
旁人更是看得大气也不敢喘上一口,这一刻有如过了一整天般长久。
项平东与管一见心内俱知,只要稍一不慎,或者某一方内力不继,便要倒下。
项平东是有死无生,竭尽全力把内力源源不绝运向右臂,目光及处,管一见额上亦已见汗。他知道管一见两只手指要承起他整个人的重量,尽管他内力深厚亦颇难支持得长久。
项平东信心倍增,他立意在自己完全失败之前先把他毙了,这才能泄心头恨!不是他,如今项平东还不是项家的大公子?说不定已坐上那执掌项府一切的位子。
热汗淌过鼻尖,不滴下,其辛苦难过只恐不是人人知道,项平东忍不住摆一摆腰,希望藉身子的移动使汗珠滴下。
汗珠不滴下反而因项平东在身上的摆动而钻入鼻孔中。项平东鼻子一酥,不禁打了个喷嚏!
与此同时,管一见左掌疾如星火拍在缅刀刀身上,暴喝一声,右手同时向外一挥!
项平东只觉手臂一阵麻痹,跟着一股力量使他松开手指,身形即时沉下。
未待他定过神来,蓦地胸口如被巨木撞击,身子亦被撞飞数丈。人在半空,一股鲜血冲口喷出。
管一见趁项平东阵脚未稳,立即一脚踢在项平东胸口。此时他如一头大鸟随着项平东飞去。一式“苍鹰搏兔”,右手抓着项平东背后衣衫。
项平东猛一挣,“嗤!”衣裂人坠下,管一见几乎在同时坠下。
项平东跌落地上,已无力爬起来,管一见一拳往他面门击下。
项平东疾叫一声,撕心裂肺,闭起双目不敢再看。过了半晌不见动静,不禁睁开一缝偷看,管一见化拳为指,点在他身上之麻穴。
未待管一见另有动作,一个尖锐已极的叫声即时响起:“不要伤他性命!”旋即见一个中年美妇自厅上排众奔来。
管一见笑笑闪身退下。
“平东,你……你怎样?要不要紧?”这中年美妇显然是项平东的妻子,她见项平东口角血迹斑斑,不禁哭了起来,用罗帕替他抹拭。
项平东睁开双眼,怒道:“哭什么?谁叫你来?”
他妻子久在他积威之下,此时仍下意识地低下螓首,随即转头呼道:“文儿,快来见你爹爹!”言未毕两行清泪已挂在腮边。
大厅中即时奔出两男一女的孩子。大的那个大概是十岁光景,半途已急声叫道“爹爹,爹爹,你为何带这么多人回家?奶奶说你、说你不是好人,孩儿再也不理奶奶了!”
项平东无言以对,刹那之间甜酸苦辣,气恨忧愁全都涌上心头,泪珠不禁夺眶而出。
他小儿子讶道:“爹爹你怎地哭了,你平日不是教诲孩儿,说大丈夫流血不流泪呀!”
稚子无知,在场诸人心头俱是一酸。
项平东泪如泉涌,不能遏止,而他妻子已经哭出声来,她亦深知小叔们绝不会放过自己的丈夫,但仍存一丝侥幸:“文儿,快去求叔叔们……求他们放过你爹爹……要不然,你们便要成为没爹爹的孩子呢!”
项平东神色大变,暴喝道:“贱人放屁!你丈夫是个大丈夫,岜能叫孩子为我乞命!”
他妻子闻言不敢再说,只是哭泣之声更响了。
项平东又喝道:“别哭!”转首对项五郎道:“五弟,我求一事未知可否?”他手脚麻穴虽被制,但头部尚如平常。
项五郎双眼噙泪,道:“大哥但说无妨,只要小弟做得到的,绝不推辞!”
项平东脸现欣慰之色:“我虽然对不起父亲及三弟,但是……”声音突转凌厉,“但是并没有对不起自己!我已为我的理想拼至最后一刻!”喘了一口气,续道:“这三个孩子我求你替我把他们抚养成人!你大哥一生只向人求过一次!”
项五郎眼泪夺眶而出,涩声道:“大哥不用再说,小弟答应你!”
“你绝不后悔?把他们视如己出?”
“是。大哥放心!”
此时,众人俱知他在交待后事。
项平东道:“好,愿你好自为之。”转头对项平北道:“我做这件事只漏了一个细节——忘记把毛笔洗干净,以致引起你们的疑心,那天晚上你一离开,我便跟着潜入,当时才猛地发觉。可是我又做了一件错事,再潜入房把笔洗净,却更引人思疑!你果然厉害,难怪爹爹要把位子交与你!我好恨!”
项平北自然知道他所指是什么,听见他说父亲要把位子交给他,禁不住心头一阵狂喜:“你所说的是真的?”
项平东冷笑一声,道:“假的!他要想把位子给你,但终于要交给五弟!”
项平北忍不住望了项五郎一眼,目光颇有怨毒之色。
项平东又对孩子们道:“你们要好好学本事,这个家将来一定是你们的,绝不是你们堂弟的!记住了吗?”
孩子默默点头,虽无知却也猜出今日事情有异寻常。
项平西怒道:“你临死还说此种话?我绝不能饶你!”踏步上前,他听见项平东说爹爹要把位子传与四弟跟五弟,虽明知可能是他在胡言,但心中之不快还是使他抑制不住。
项平东厉声道:“不必你动手!十八年后项平东自会再来找你!项五郎你若亏待我儿子,我做鬼也不放过你!”
他说得又恨又毒,声音又凄厉,使人听了忍不住机伶伶打了个冷颤,项平西亦不例外,不禁停了步下来。
项平东猛喝道:“苍天何生我于项家!我好恨!”嚼舌自尽而死。
项平东妻子痛哭出声,孩子也跟着哭起来。
项平东虽死,但他的话却深深留在众人脑中,久久不能淡忘,权之可怕,令人不寒而怵。
项平西喃喃地道:“此逆子临死还不知悔错!”想起那位子大概已轮不到他,心中说不出的没味,一转念,喝道:“岳扬,快备马回寨!”
项平北道:“二哥何去得匆匆?”
项平西道:“我若连洋澄湖寨子也失掉,只怕也要托孤!”想到托孤连忙吩咐他妻子及儿子一同上路。
项平东的话会不会在项平北及项五郎之间埋下一包炸药?可惜这已非本文的范围了。
×
×
×
夜幕低垂,春风一反常态,吹得劲疾如冬天,呜呜地响,宛似为项平东哭丧,又宛似为人间的多少纷争而悲叹。
管一见不欲多留,道:“四公子,此案已经大功告成,公子满意否?”
项平北道:“晚辈十分满意,多谢神捕全力查办。”
管一见道:“那么,管某之聘金,请即缴付。”
项平北道:“遵命,来人!到库房支九万两银子给管神捕,另外封五包一千两的,每人加送一封谢金。”
管一见道:“多谢了。不过,这数目四公子大概算错了!”项平北愕然道:“前辈不是说每办一件案子四万两?另外协助晚辈缉凶代价五万两?”
管一见道:“高老弟,他们请咱办几件案子?”
高天翅道:“共四件。”
“念给他听!”
“四公子求我替他们查:一、杀父凶手,二、杀兄凶手;五公子求咱查齐云高是否凶手;二公子求咱查‘降龙伏虎’的底细。”
“咱是否已经全部办妥?”
“是的。四公子刚才亦表示十分满意了。”
“那为何会算错?”
项平北此时方知管一见查案是逐件细算,难怪人人请他的价钱异常昂贵。他苦笑道:“晚辈先前不知前辈如此算法,既如此,自当照付。”
管一见面色一霁,笑道:“公子下次若再用得着管某,自当九折优待。”
项五郎苦笑道:“下次再找前辈,只怕已付不起聘金了。”
管一见迎着寒风走出项府,一回首道:“夏雷,跑一趟!叫兄弟们到天香楼吃一顿饱的!嗯,还有,顺便叫齐云高一同来。”
(全书完,古龙武侠网 凌妙颜OCR、黄鹰武侠Q群7649715 →孙悟空←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