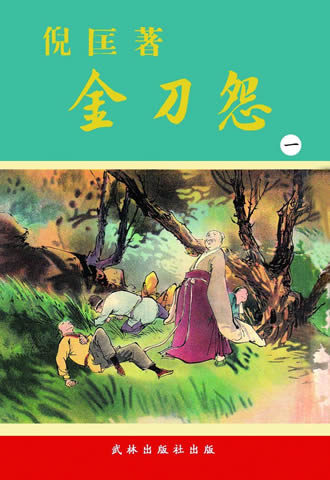不大一会儿工夫,王尚飞慌慌张张地跑回来道:“老爷子,不好了,老莫和他老婆已经跑了!”
梅晓村吃了一惊道:“你可曾仔细找过?”
王尚飞道:“据厨房的人说,他今天早上就没去烧火,因为大家本来嫌他整天醉醺醺地做事碍手碍脚,所以也没人去找他,刚才我到他住的那间房子一看,根本没有人影,连他老婆也不见了。”
梅晓村顿时气急败坏地道:“走,王大人,咱们一起过去看看!”
老莫的住处,是在厨房后侧的一间茅棚,棚内除了有个土炕和一个破衣橱及几条板凳外,只有炕上的几件破衣服。
王刚心里暗自盘算着,若这对男女是今晨逃跑的,必会被他派出去的埋伏擒住,但如果是昨晚就走的,那就真是漏网了。
梅晓村不但心里急,更感到愧对王刚,也顾不得家丑不可外扬,连忙召集所有下人,展开严密搜查。大山猫和小老鼠也配合着参与了行动。
王刚由梅晓村陪同再回到大厅,等待消息。
直到将近中午,大家马不停蹄地搜遍了梅庄前后院及花园的每个角落,依然不见老莫和路边桃的踪影。
梅晓村只急得连连跺脚。
另一方面,王刚派出去的埋伏,也不见有人回报。
事到如今,已明显地表示老莫和路边桃是在昨晚就逃脱了。
等大山猫和小老鼠回来时,梅晓村却因有事暂时离开了大厅。
小老鼠一向最为机警,趁机低声说道:“老大,您看会不会是这梅老头儿从中捣鬼?”
王刚摇摇头道:“不太可能,梅老先生已经将近七十的人了,怎会和百花门扯上关系?”
“那么王总管是否有问题?”
“也不太可能。”王刚吁了口气:“既然白来一趟,咱们只有回去了。”
谁知三人刚要起身,梅晓村却又匆匆回到大厅道:“王大人可是要走?”
王刚道:“既然找不到人,在下就不敢再打扰了。”
梅晓村道:“王大人好不容易驾临敝庄,现在天色已经近午,老朽已备下酒饭招待,不成敬意,王大人千万赏光!”
王刚欲待推却,早被梅晓村热情地牵住手臂。
小老鼠却在一旁向王刚直递眼色。
王刚只做不见,招呼两人道:“既然梅老先生诚意款待,盛情难却,咱们也就用不着客气。”
酒席设在一间雅致的净室里,一张八仙桌上各种菜肴摆得满满的,不乏奇珍异味。
宾主四人各据一方而坐,小老鼠原先本来犹豫不肯动箸,最多也是看着梅晓村动过的他才尝上一尝,但后来见王刚和大山猫都是各色菜肴都吃得津津有味,美味当前,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
酒筵完毕,王刚等道过谢后正要起身告辞,却见梅晓村忽然脸色变得异样凝重,摇摇头黯然一声长叹道:“王大人,老朽有几句话,想和你单独谈谈,不知你方不方便?”
王刚毫不犹豫地望了大山猫和小老鼠一眼道:“你们两位请到大厅等我,我和老先生谈过话后,咱们马上回去。”
大山猫和小老鼠只得告辞而出。
梅晓村站起身来道:“这里还是不方便,王大人请随老朽到里面来。”
原来这间净室只是外面的一间,推门进去,里面另有一个房间,布置得纤尘不染,十分雅洁。
两人进入之后,梅晓村掩上门去,然后招呼着王刚分宾主坐下。
这时的王刚,内心一片坦然。
其实他对梅晓村这种举动,并非不觉得可疑,而是认为越是可疑,越应该探悉究竟,若他不肯答应梅晓村的要求,那反而是平白失去机会了。
因此,他现在内心早已有了决定,那就是以不变应万变地静观其变。
梅晓村又是长长一声喟叹,许久,才缓缓说道:“家门不幸,我们梅家在短短的一个月内,竟接二连三地闹出这种耸人所闻而又见不得人的事情!”
他说到这里,竟然情不自禁地洒下了几滴老泪,接下去再道:“我们梅家,虽然算不上门第显赫,但也可称得世代书香,而最有出息的,该数舍侄雪山了,他能以不到四十的年纪,官拜御史,可以说全凭十年寒窗和自己的努力挣来的。”
梅御史本名雪山,王刚虽未见过,却知道他年纪的确只有三十几岁。
“令侄梅御史的自尽,老先生一定知道原因吧?”王刚故做试探地问,其实他自然明白是与百花门有关。
梅晓村似乎并未专注王刚的问话,还是说他自己的:“本来,以雪山的年纪,若能继续努力,在朝廷中多做些贡献,将来不难为梅家光大门楣,但他却英年早逝,断送了自己的大好前程,也断送了梅家的希望。”
“难道梅老先生不知道梅御史的死因?”
“怨只怨雪海那畜生太不争气,竟和一些叛逆组织搭上了关系,他虽然惨遭横死,那也是报应,并不值得惋惜,可是他哥哥跟着遭殃,却令老朽实在难过!”
王刚不经意地笑了笑道:“老先生请恕在下直言,目前朝中不少高官显宦,已和叛逆组织搭上了关系,又谁能担保梅御史没有嫌疑?”
梅晓村摇摇头道:“老朽可以担保,雪山不会做出这种大逆不道有负朝廷的事来。”
“即便他不是直接和叛逆组织有关系,但他弟弟梅雪海的所作所为,他却不能推卸责任,他把偌大一份家业的梅庄交给梅雪海执掌,任他在外胡作非为而不予约束或纠正,又怎能说得过去?御史在朝中是谏官,他只知弹劾别人而不能管束自己的家人,这种官吏又凭什么为自己的家庭光大门楣?”
这一番话,说得梅晓村几乎无言可对,沉默了许久,才说:“这个……老朽倒不能说是雪山在朝中公务太忙,而是雪海总是他的弟弟,由于手足关系,不便管教太严,也是人情之常。”
“老先生曾说梅御史在朝中是位好官,他若不贪渎受贿,梅庄这份家业,又是哪里来的?”梅晓村这次却毫不迟疑地说道:“王大人,这次你却真是误会了,雪山在外为官不过十几年,做御史也才三五年,而梅庄这份家业,却是二三十年前就有的,正因为雪海也可以分得一半的产业,所以雪山对他在庄上的所作所为,才不便过问。”
“那是在下错怪梅御史了。”
梅晓村叹了口气道:“老朽目前暂时接管了梅庄,这些天来,日子过得实在痛苦不堪。”
“老先生平白增加了责任,日子没有以前清闲,这是谁都可以想见的。”
“王大人猜错了,老朽绝非为了怕忙碌,而是梅庄的事情,实在不好管,下人们一个个来路都非常复杂,有时更会发生些离奇古怪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更有人在背后说闲话,认为老朽是贪图霸占这份产业,这简直是岂有此理!”
梅晓村竟然越说越激动,又长长叹息一声道:“不要说舍侄雪山有后,即便真把这份家业归老朽所有,老朽也是将近七十的人了,还有几年好活,何况老朽自己也有一份偌大的田庄。”
“可是据说梅御史的公子年纪尚小,梅庄的大事,若老先生不出面执掌,又有谁来管呢?”
“这正是老朽的为难之处。”梅晓村顿了一顿,双目中忽然泛出异样的神采:“王大人,这也正是老朽趁这机会要求和你做番密谈的原因了!”
王刚不由一怔道:“梅庄的家务事,老先生与在下有什么密谈的?”
“自然是请求王大人帮忙了!”
“府上的事,在下又能帮得了什么忙?”
“帮忙老朽早日把梅庄交还原主,不再肩负代管梅庄的责任。”
王刚越发怔住,急急问道:“在下实在不懂老先生的话中之意?”
梅晓村忽然凑近身来,神色神秘地低声道:“王大人,这事除了是你帮梅家的忙,也是老朽暗中提供了你一件重大线索,对你查办百花门的大案,一定也大有帮助。”
王刚在这刹那,两眼也闪出异样的光芒:“老先生快快请说!”
梅晓村面色有着无比的凝重,一字一句地道:“舍侄雪山并没有死!”
有如一声晴天霹雳,使得王刚顿时呆在当场,许久才说:“老先生这话有何根据?梅御史明明在梅庄事发之后,自缢在书房之中,这样的大事,连满朝文武都为之震惊,怎能有假?”
“舍侄死后的尸首,王大人可曾见过?”
“那不是騠骑营的事,在下不曾看到。”
梅晓村又是一字一句地道:“那尸首是假的,除了老朽,只怕没有第二个人能认得出来。”
王刚依然难释心头的惊疑,但却故做镇定,不动声色地问道:“不知老先生是怎么认得出来的?”
梅晓村回忆着当时的情形道:“当时雪山的妻子正在病中,雪海又已横死,老朽算是他唯一的家属长辈了,当我赶到时,刑部秦侍郎正亲率仵作在检验尸体,当时并未看出有什么疑点,因为那尸体的面貌和身材,的确和雪山完全一模一样,直到入殓之前,老朽才发觉不对。”
“老先生在什么地方看出可疑?”
“雪山在右手腕部有一颗豆大的黑痣,但那尸体竟然没有,当时他的妻子俞氏也扶病在场,似乎也未注意到。”
“在当时的心情下,只怕很少有人会留意到那种小地方,这也足证老先生的细心,老先生发觉疑点之后,为什么不当场指破?”
梅晓村黯然一叹道:“当时在场的人很多,而且各方面的人都有,老朽怎可随便开口指认。”
“人命关天,这样重大的事情,老先生竟不予当场指破,在下实在不解?”
梅晓村似有难言之隐,苦笑道:“事到如今,老朽又何敢对王大人有所隐瞒,因为当时老朽早知雪海之死,是和那叛逆组织的百花门大有关连,不消说这以假乱真的事,十有八九是百花门干的,若当场指破,他们岂能再能留下活口,只有假装不知糊里糊涂地把人埋葬,雪山才有幸存的希望。”
这话有理,到这时王刚也不得不认为梅晓村的做法十分机智。
“如果真是如此,老先生实在是帮了騠骑营一次大忙,有了这样一个秘密线索,对今后騠骑营的行动,自是助益不小。”
“不过王大人千万要守密,万一在事情未成之前泄漏出去,不但救不了雪山,连老朽的处境也十分危险!”
“老先生放心,这样的机密大事,在下怎肯轻易让人知道。”
梅晓村神色稍稍镇定下来道:“其实这事老朽早就想秘密告知王大人,因为目前真正能对付百花门的,也只有騠骑营了,可惜始终找不到机会,今天王大人前来,正好了却老朽一番心愿。”
“在下一定会尽早侦破此案,因为只要梅御史能得生还,必可从他那里得到百花门的真正内幕消息,所以救了梅御史,也等于侦破了百花门的组织。”
梅晓村喜出望外而又无限感激地道:“那就多谢王大人了,只要舍侄能安然无恙地回来,将来是否能为国继续效劳已并不重要,倒是老朽就大可不必再为梅庄的事操心了。”
王刚沉吟了一会儿道:“在下也有件事,必须提醒老先生。”
“王大人有话请讲!”
“以目前的情形看来,贵庄的下人里面,仍可能有不肖之徒混迹其中,老莫和路边桃便是明显一例,说不定他们的逃走暗中还有人协助,所以老先生必须处处留意,同时也要注意自身的安全。”
“老朽也有这种预感,好在王总管为人很能干,这些天来,很多棘手的事情,都是他代为处理的,省了老朽不少麻烦。”
王刚摇头一笑道:“在下说句话,不怕老先生听不进去,贵府的总管王尚飞,正是个可疑的人物,老先生必须在他身上多多留意,说不定会有什么发现!”
梅晓村吃了一惊道:“真有这种可能吗?王大人可抓到他什么把柄?还是以前就知道他的为人?”
王刚道:“在下还是第一次见到此人,只是由他刚才的神色和行动中见出可疑,并非已断定他如何如何,总之,老先生今后多多留意他是必须的。”
梅晓村似乎依然有些不便肯定王刚的话,吁了口气道:“既然王大人这么说,老朽今后自当留意一二,不过老朽倒想出一个可行的办法,不知王大人肯不肯答应?”
“老先生有什么办法?”
“老朽想请王大人派出一两个能干的手下,就算受雇在梅庄充当下人,由他们在暗中侦察,一有发现,随时回騠骑营报告,这样岂不很好?”
王刚想了想道:“这样做固然好,但万一事机不密被识破身份,反为不妙,这方面在下不能不有所顾虑。”
梅晓村皱下眉头道:“那么王大人可还有别的办法?”
王刚道:“老先生既然只是暂管梅庄事务,在梅庄下人中,不可能有什么靠得住的心腹,所以在下的意思,事情不必假手他人,一旦发现有什么可疑,最好由老先生直接找在下联络。”
梅晓村欣然答道:“好,老朽一定谨遵王大人的吩咐办!”
王刚随即由梅晓村陪同回到大厅,招呼大山猫和小老鼠离开了梅庄。
路上,大山猫和小老鼠不免问起王刚和梅晓村到底密谈了些什么。
王刚自然是拿别的话来搪塞过去。
这几天来,他心情之沉重,只怕除了叶如倩外,没有第二个人可以了解。
护国侯邱光超的失踪,至今连探知下落的线索都没有找到,到妙峰山百花门总坛扑了空,如今李大狗又出了事情。李大狗被人割了下体,那是罪有应得,但老莫和路边桃的溜脱却不能等闲视之,如今又从梅晓村处得到梅御史不曾真死的秘闻,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使得他简直有些难以应付。
现在唯一的处置,便是正式逮捕李大龙,既然李大狗出事时他也在梅庄花园,那他就罪证确凿了。
来到城郊,他交代大山猫和小老鼠道:“你们二位回去休息吧!”
小老鼠茫然问道:“头儿您呢?”
王刚道:“现在用不着你们了,我还另有事情。”
原来王刚是要赶到八方镖局,因为他考虑到金刀庄主李天浩在武林中是位素为同道敬仰的当世大豪,有豪中之王的美誉,而且他上次六十大寿,对自己还曾下帖相邀,那时他并不知道自己是騠骑营的副统领,可见他颇有礼贤下士之风,义气令人可感。如今要逮捕他的儿子,难免令他有些为难,因之,他决定到八方镖局找到叶逢甲和樊飘零,有他们一同前往,在礼貌上总算有个交代。
他对叶逢甲和樊飘零二人这些天来一直住在八方镖局,也有些茫然不解,因为他们各人有各人的家业,老寄居在友人处,总是费人疑猜的。
来到八方镖局,很快就会见了叶逢甲和樊飘零。
“王刚,你又来做什么?”叶逢甲一见面就先行发问。
不等王刚答话,樊飘零已抢着说道:“老叶,我看你有些不大对劲,女婿来看岳父,名正言顺,而且也可见他对你的一份孝心,如果我有这样一个好女婿,高兴还来不及,你反而有些不耐烦,当真是一个怪人!”
叶逢甲哼了一声道:“他来可不是为了向我问安,必定又有什么事请求咱们帮忙。”
王刚赔笑道:“小婿正是有事来麻烦岳父和樊老前辈。”
叶逢甲望了樊飘零一眼道:“你看怎么样,我猜的不错吧?”
樊飘零笑道:“王刚,有事只管说,老夫和令岳父都不是外人,能帮上忙的地方一定帮忙。”
王刚开门见山地道:“晚辈决定要逮捕李大龙归案,因顾忌到金刀庄主的面子上不好看,所以想请两位老人家同去,先向李庄主婉转说明,然后再采取行动,这样礼数到了,也算对李庄主有了交代。”
叶逢甲脸色微微一变道:“王刚,你为什么老是给我们出难题?上次要逮捕武重光,这次又要逮捕李大龙,偏偏这两人的父亲又是老夫的至交,也不想想看,由我们带着你去捉拿好友的儿子,这种事可是老夫和你樊前辈做得出来的?”
王刚只听得大有啼笑皆非之感。
好在樊飘零紧接着说道:“老叶,王刚固然是给咱们出难题,但你总要听他解释明白,他要逮捕李大龙,必定有逮捕他的理由,等他把话说清楚了咱们再做决定不是好些吗?”
叶逢甲没好气地道:“那就让他说说理由吧!”
王刚正色道:“昨晚小婿一个弟兄在梅庄花园被杀,那动手的人正是李大龙所指挥的,而且李大龙当时也正躲在假山之后。”
樊飘零吃了一惊道:“你那弟兄可是当场被杀死了?”
王刚道:“所幸被另外几个弟兄及时救起,虽然不曾丧命,伤势却也不轻。”
叶逢甲两眼眨动了一阵道:“梅庄自从梅雪海和梅御史死了以后,已经平静无事,百花门的人也早已撤走,你的弟兄到那里去做什么?王刚,别以为你是騠骑营的副统领,就可以纵容部下胡作非为,人家梅庄可是规规矩矩的老百姓!”
王刚轻咳一声道:“岳父息怒,小婿有下情回禀!”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我把如倩交给你,是因为觉得你身在六扇门内,却不惜规矩本分,你若仗势胡来,那就太辜负老夫的一番期望了!”
王刚神色一片肃然,缓缓说道:“小婿说话,从不会拐弯抹角,您老人家认为梅庄目前已平静无波,事实证明并不尽然,否则小婿的手下,何能在梅庄被杀?李大龙又何能在梅庄出现?”
樊飘零颔首道:“王刚这话说得有理,李大龙和梅家根本扯不上关系,他夜晚之间到梅庄花园去,显见脱不了和百花门有关的嫌疑。”
叶逢甲沉吟了一阵,再望向王刚道:“李大龙昨晚到过梅庄花园,可是你亲眼看见?”
王刚道:“若小婿昨晚亲眼得见,当时就将李大龙活捉了,何用来请岳父和樊老前辈?”
“既非亲眼看到,又怎能相信是真的?”
“小婿的手下看得很清楚。”
叶逢甲冷冷一笑道:“这就不对了,夜晚之间,如何能看得很清楚,那除非生了对夜猫子眼睛,要不然就是李大龙自己手里打着灯笼故意照给别人看,他好像还不至于傻到这种地步!”
王刚苦笑道:“岳父若硬要这样说,小婿真是无词以对了!”
又是樊飘零打圆场道:“老叶,你别只管问嘴,王刚是你的女婿,他怎能和你顶撞,既然有人看见李大龙在场,必定不会是假,谁说夜晚不能看清楚东西,难道你我入了夜都变成了瞎子不成?”
叶逢甲哼了一声道:“听你的语气,好像已被王刚说动了?”
樊飘零道:“李大龙既然有嫌疑,王刚是吃騠骑营饭的,当然应该到金刀庄找他,他一个人去,万一和他老子李天浩起了冲突,反而弄得下不了台,连咱们老哥俩以后也不好和李天浩见面,有了咱们跟去,正是给双方私下转圜的余地。”
叶逢甲一听这话十分有理,也深觉方才太使王刚难堪,不觉歉然一笑道:“既然连你都肯帮他的忙,我这个做丈人的,又岂能落后。好,不知王刚希望什么时候走呢?”
王刚一见两人都已答应,心头大喜道:“小婚先行谢过两位老人家,事不宜迟,迟则有变,最好现在就走。”
金刀庄在通州,通州就在京师东郊,虽然只有三五十里的路程,三人还是乘马前往。
三人一路上似乎都在思忖着到了金刀庄以后,该如何采取行动。
樊飘零道:“李天浩在武林中德高望重,是位人人敬仰的人物,咱们到达以后,为了顾全他的面子,事情应当尽量避免张扬。”
王刚道:“晚辈担心的是他万一不肯让咱们把人带走,又该怎么办?”
樊飘零道:“李天浩是个深明大义的人,若李大龙当真证据确凿,他绝不会为难咱们。”
叶逢甲也道:“王刚,你放心,老夫既然来了,一切自会替你做主,若李天浩不明是非,我和他也就顾不得多年的交情了!”
说话间已到达金刀庄。
经过守门人通报后,李天浩亲自迎出门来,并命下人将三匹马牵到树荫下拴好。
李天浩自从上次祝寿之日因寿桃被人动了手脚以致客人全体中毒事件后,内心一直觉得愧对武林同道,同时也自感颜面尽失,又因从那以后很多好友都不再上门,更是闷闷不乐。
如今见两位盛名卓著的武林大豪叶逢甲和樊飘零以及后起之秀的王刚进庄相访,自是高兴不已。
延入客厅坐下后,又立即吩咐下人准备晚餐。
叶逢甲道:“李兄,不必了,我们办完了事就走!”
李天浩一听语气不对,忙道:“莫非三位还有什么贵干,还是担心李某的酒饭内又有毛病?”
樊飘零怕一见面就把气氛闹僵,抢着说道:“李兄想到哪里去,兄弟等人今天前来,的确是有件事情要和李兄商量,但愿李兄千万不要介意。”
李天浩朗朗一笑道:“彼此多年老友,几位有话只管明言,只要李某做得到的,无不尽力!”
樊飘零道:“只要李兄不责怪,事情就好办了,兄弟先想问句话,令郎大龙贤侄近来在外的行动,李兄是否清楚?”
李天浩叹了口气道:“这畜生是越来越不像话,整天很少在家,有时甚至数日不归,家门不幸,出了这么一个不肖之子,真不知是李某哪辈子作的孽!”
樊飘零见李天浩并不护短,心情已大感轻松,于是直接了当地说道:“实不相瞒,昨晚梅庄花园出了一件命案,令郎李贤侄也牵涉在内。”
李天浩吃了一惊道:“真有这种事?怎么老夫毫不知情?”
樊飘零道:“事情是昨晚才发生的,李兄当然不会知道,连兄弟和叶兄,也是刚才由王刚那里得到的消息。”
李天浩脸色骤现凝重,望向王刚道:“王老弟,真有这回事?”
王刚十分有礼貌地答道:“其实李老伯早应明白,令郎很久以前就和百花门搭上关系,目前已是百花门的西路总监,上次在石榴村,晚辈已和他会过一阵,昨夜晚辈的手下在梅庄花园被人诱杀,也是他在暗中指挥,还望李老伯明察!”
李天浩的脸色青一阵、白一阵,久久不能平复,半晌,才语气沉凝地说道:“事情真有如此严重吗?老夫虽知道他在外面胡作非为,但总觉得他还不至搭上百花门的关系,而且居然担任了什么西路总监,这话似乎太过耸人听闻了!”
他顿了一顿,又道:“老夫虽然家门不幸,出了这样一个孽子,但却绝不护短,只是想问问王老弟,你刚才的话,有什么证据?”
王刚依然保持着应有的礼貌,道:“小侄但求老伯把今郎叫出来,只要当面对质不愁他不说实话。”
只听叶逢甲道:“李兄,王刚是騠骑营的人,他的话当然不是空穴来风,想你一世英名,出了个儿子竟是百花门的人,实在连兄弟我也感到不好意思,令郎如果在家,你就把他叫出来吧!”
这几句话,说得实在过分了点,李天浩脸色铁青,冷然笑道:“你们诸位听着,李某虽然不护短,但也不能让人随便在自己的儿子身上栽赃,王老弟虽然是騠骑营的人,也该讲法讲理,仅凭两句话,何能取信于人,若拿不出真凭实据来,谁也别想带走他,金刀庄也丢不起这种面子!”
顷刻间的变化,场面已弄得大有剑拔弩张之势。
叶逢甲双目圆睁,大声道:“李庄主,小婿王刚,绝不会冤枉了令郎,咱们都是武林中人,百花门正是你我的大敌,他们不但危害江湖,甚至把朝廷都搅得惶惶不安,令郎加入百花门,你反而偏袒于他,真可惜了你这一世英名!”
这场面使得樊飘零大感不安,他奇怪叶逢甲近日来为何性情变得如此暴躁,此刻虽然表现得义正词严,实际却等于在搅局,只好抢着打圆场道:“两位都是多年深交,若因此伤了和气,实在可惜。李兄,兄弟的意思,你还是把令郎叫出来当面谈谈,若真冤枉了他,我们情愿向你大礼赔罪!”
李天浩总不失是个明理之人,立刻吩咐一个下人道:“去把大少爷叫来!”
不大一会儿,李大龙便随着那下人来到客厅门口,当他看到客厅里有叶逢甲、樊飘零、王刚等人在座,立刻脸色大变,刚要转身开溜,已被李天浩喝住道:“畜生,你要往哪里去?”
李大龙只得硬着头皮进入客厅,先向叶逢甲等人见了礼,然后走近李天浩身前道:“爹!您叫我有事吗?”
李天浩扬手一掌,直掴到李大龙面颊上,声色俱厉地道:“混账东西,你把爹的面子全丢光了,昨晚到什么地方去了?快说!”
李天浩这种雷霆之怒,樊飘零等似乎还是第一次见过,他明是教训儿子,实际上等于打的三个客人。
李大龙捂住面颊,咬牙咧嘴地道:“爹,儿子昨晚一直在家里不曾出去,您干吗发这么大的脾气,儿子也是娶妻生子的人了,当着这么多客人的面,让儿子以后怎么做人?”
李天浩怒不可遏,又是一掌掴上了李大龙的另一边面颊,喝道:“混蛋,我是哪辈子烧了牛粪,才养出你这样一个没出息的东西,其实你没出息能在家里规规矩矩守着也没关系,却竟然背着我加入了什么百花门,而且居然做了什么西路总监,兔崽子,你是不是想把为父的活活气死?”
李大龙双手掩住面颊,已看不出他的表情,只是直着嗓门叫道:“爹,您是听谁说的?”
李天浩喝道:“人家已经找上门来了,还问听谁说的,你有理由去跟他们三位讲!”
他说着再对叶逢甲等三人道:“各位,我把儿子交给你们了,你们自己问吧!”
李大龙转过身来道:“叶老伯、樊老伯、王刚兄,莫非是你们三位在家父面前说了什么话,才使他老人家发了这样大的脾气?”
王刚朗声道:“李大少,事到如今,你也用不着再装疯卖傻了,上次在石榴村,你指挥十二名秋风杀手,不曾把我和贱内杀死,看在令尊的分上,事后我并未深究,目的是希望你知过能改,谁知昨晚你又指使老莫杀害我的手下人,还想抵赖不成?”
李大龙噘嘴打了哈哈道:“王刚兄,兄弟听不懂你在说些什么,石榴村的事,那只是一场误会,你用鞭伤了我的膝盖,我照样不曾追究,至于昨晚又发生什么事,我根本弄不清楚!”
“看李大少的意思,是不肯承认了?”
“常言道得好,奸情以双为凭,贼情以赃为证,不知王刚兄可有什么证据?”
“那你就把昨夜的行踪交代明白!”
“兄弟从昨天到现在,一直没离开金刀庄!”
李大龙死不承认,一时之间,难免使王刚不易处置。
樊飘零见王刚颇有为难之意,不由朗声道:“李兄,你可能担保令郎从昨天到现在一直不曾离庄?”
李天浩不愿为儿子遮掩,一来他确实弄不清昨夜李大龙的行踪,二来深恐对方提出反证,自己反而难以下台,默了一默道:“你们三位只管问他,李某不想帮着儿子说话!”
樊飘零吁了口气道:“李兄,若我们三人这样问下去,只怕问上三天三夜,也问不出所以然来。”
李天浩不动声色道:“樊兄的意思呢?”
樊飘零歉然笑道:“只要李兄不介意,兄弟希望能让李贤侄随王刚到騠骑营去趟,只要把騠骑营昨晚到过梅庄花园的两位弟兄找来双方一对质,事情便不难水落石出,兄弟可以担保,李贤侄在騠骑营这段时间,王刚绝不会让他吃苦。”
李天浩哼了一声道:“你们是想把他带走?”
樊飘零道:“为了查出真相,也只有让李贤任委屈一下了。”
李天浩两太阳穴急剧的抽动了几下,然后又叹了口气道:“好吧,随你们的便!谁让我养了这么一个不肖的儿子,不过,到了騠骑营,除非他罪有应得,否则,若你们妄动他一根汗毛,老夫绝不与你们干休!騠骑营虽然权大势大,不过是当今皇上的鹰犬爪牙而已,还没放在老夫的眼里!”
突见李大龙“扑通”一声,跪倒在李天浩脚下,哭嚷着道:“爹,您不能这样做,他们官府里做事,是照样不讲天理国法的,万一儿子到了騠骑营有个三长两短,只怕以后就没机会在您老人家跟前尽孝了!”
李天浩厉声喝道:“把骨头撑硬一点,我李天浩没有你这种窝囊废的儿子!”
樊飘零忙道:“李贤侄不必担心,到了騠骑营,只要你做得正,行得端,一切有老夫担保,还有什么可顾虑的?”
李大龙爬起身来道:“樊老伯,您不知道,不是小侄胆怯,而是騠骑营一向仗势凌人,根本不讲是非。”
樊飘零道:“难道你连老夫也信不过,他们若妄动你一根汗毛,你尽可以向老夫是问。”
李天浩扳着面孔问道:“你们可是现在就要带他走?”
叶逢甲道:“叶某等三人自然不希望再来麻烦李兄第二趟!”
李天浩一咬牙道:“好!三位就请在庄外树林边稍待,待会儿李某亲自把这畜生送过去交给各位!”
叶逢甲有些不放心,问道:“令郎为什么不能现在就走?”
李天浩双眉一耸,冷笑道:“李某在武林中的一点声名,不是侥幸得来的,金刀庄也算是块金字招牌,若犬子就这样被各位带走,李某的颜面何存?”
这倒是不得不顾虑的,樊飘零当即招呼叶逢甲和王刚道:“走!咱们就到庄外吧!”
三人出了大门,找到马匹,随即来到路旁的树林边等候。
叶逢甲有些担心地道:“李天浩会不会说话不算话?他把儿子放走了,却让咱们在这里白等!”
樊飘零语气坚定地道:“咱们和他相交,也并非一天半天了,他那侠中之王的美名不是白得的,他若不把儿子送来,我愿负一切责任。”
大约顿饭工夫之后,果然两匹骏马,由金刀庄侧门而出,直向树林奔来。
当先一人是李天浩,后面正是李大龙。
这时李大龙已换过一身衣服,神情也显得较为开朗。
李天浩来到距三人丈余外处,勒住马头,冷着声音说道:“人已经交给各位了,李某不再远送!”
说着又转头道:“畜生,你就跟着他们走吧,李家的人,算被你丢光了,看你还有什么脸面再回来见我?”
樊飘零眼看李天浩策马回庄,才望着李大龙道:“李贤侄,随大家走吧!”
李大龙苦笑着道:“两位老伯和王刚兄,这是何苦,我在庄上是这样说话,到了騠骑营照样也这样说话,干屎粘不到身上,好人是不能随便冤枉的,各位也不想想,我在金刀庄要什么有什么,享不尽的富贵荣华,干吗要靠上百花门,天下可有这样的傻瓜?”
樊飘零道:“李贤侄用不着气愤难平,到了騠骑营,若确实没有嫌疑,自然很快就放你回来,王刚不会冤枉好人的。”
李大龙无奈地摇头一叹道:“我爹也真是,竟然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儿子往六扇门里送,真是糟蹋了他那一世英名!”
叶逢甲有些不耐烦地道:“好汉做事好汉当,李大龙,令尊养了你这么个不争气的儿子,才是真正的丢人,有话到騠骑营再说吧,别耽误时间,乖乖地跟着上路吧!”
他说着当先策马向前走去。
李大龙走在第二。
王刚和樊飘零殿后。
不大一会儿,前面是一片高岗,高岗上以及周近长满了杂树,地形显得十分复杂。
就在这时,突见李大龙双足在马腹上一蹬,越过前面的叶逢甲,纵马飞快地向杂树林中奔去。
由于他发动的太快,叶逢甲等人猝不及防,竟被他溜脱得逞。
叶逢甲的马走在最前,他岂肯让李大龙逃脱,立即纵马追去,一面高声叫道:“这附近岔路很多,你们两位快到别处封住路口,千万不能让这小子走脱!”
樊飘零和王刚急急分头由两边驰出,展开了包抄之势。
这附近地形的确十分复杂,由于距金刀庄不远,除了李大龙一定熟悉外,叶逢甲等三人却像闯进了八卦阵。
王刚在杂树丛中一阵奔驰,不但找不到李大龙的人影,连和叶逢甲、樊飘零也失去了联络。
正急得满头大汗间,斜刺里冲出了樊飘零。
王刚急急问道:“樊老伯可有什么发现?”
樊飘零勒住马头,揩拭着汗水道:“什么也没见到,连令岳父也没碰上。”
“咱们不能让李大龙跑了,必须马上再找!”
“事到如今,再找也是无益,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咱们此刻不妨暂时在路口守着,等老叶回来以后,再做处置。”
“以小侄看,李大龙绝不可能再回金刀庄。”
“说不定令岳父能把他提回来,因为他追在前面,万一他也无功而返,不管李大龙回不回金刀庄,咱们只须向李天浩要人,看他还有什么话说。”
王刚只好也在路边停下马来。
樊飘零摇了摇头道:“李大龙这一着实在不够聪明,这一来正证明了他必有嫌疑,否则何必畏罪潜逃!”
“他岂止有嫌,上次在石榴村,他已公开显示了身份,当场派出十二名秋风杀手,追杀小侄和如倩,深夜间把小侄和如倩困在一座山头上,那一战如倩还受了伤,若非小侄处置得宜,只怕两人早就性命不保了。不过,如今回想起来,小侄倒是很感激他的那次行动。”
樊飘零一皱眉头道:“这话怎讲?”
“因为那一夜小侄和如倩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共御强敌,事后又悉心照料她的伤势,终于赢得了她的芳心,委身下嫁,结成连理,否则,以小侄这断臂之人,对她何敢高攀。”
樊飘零哈哈笑道:“这话倒是有理,你真该感谢李大龙才对,要知道我那如倩徒儿,自幼娇生惯养,人称武林第一美女,这些年来,多少豪门子弟托人求亲,她都不屑一顾,你能娶了她,实在是几世修来的福。”
正说话间,两匹骏马由森林中窜了出来。
樊飘零转头一看,喜出望外地叫道:“还是老叶能干,他竟把人给抓回来了!”
王刚看去,果然,马上两人,前面是李大龙,后面是叶逢甲。
只听叶逢甲怒气不息地骂道:“李大龙,你爹怎么养出你这样一个儿子来,你这一跑,显而易见是罪证确凿,老夫是甚等样人,岂能让你走脱,到了騠骑营,有你好受的了!”
李大龙满面惶恐之色,低着头,嘴巴噘得老高,却一句话都不敢说。
叶逢甲想是越想越气,纵马跟上,照准李大龙面颊,就是一耳光甩去,一面又骂道:“混账东西,在老夫面前,居然敢跑,也不想想,我叶逢甲可是你随便戏耍得了的!”
这一掌分量奇重,掴得李大龙口角鲜血直流。
樊飘零心里一急,忙道:“老叶,你是怎么了?兄弟曾在李庄主面前保证过不使他儿子受到伤害,如今连口供都没问,便把他打成那样子,这让我以后如何向李庄主交代?”
叶逢甲余怒未息地道:“这是两回事,不能一概而论,我打的是他胆敢私自逃跑,长辈教训晚辈,又有什么不对?他老子疏于家教,才养出这么个不成器的儿子,今天我正是替他老子执行家法!”
樊飘零道:“人既然已经找回来了,你也用不着生这么大的气,咱们赶路要紧。”
到达京城,叶逢甲和樊飘零径回八方镖局。
临别时,樊飘零还一再交代,不可虐待李大龙,如果嫌疑不大,希望王刚能尽速将他释回。
王刚将李大龙押进騠骑营,交代手下人将他关在一个单独房间,饮食起居并要多多照顾,绝对不可加以凌辱。
交代完毕后,他松了一口气,暂时回到住处休息。
李大龙关在騠骑营已经三天了。
在这三天里,王刚曾亲自向他问话多次,虽然大山猫和小老鼠也曾到场指证确凿,但李大龙却始终矢口否认,他看准了王刚不至于严刑逼供,不受皮肉之苦,他如何肯说实话。
------------------------------------
天马 扫描,斌卡 OCR,旧雨楼独家连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