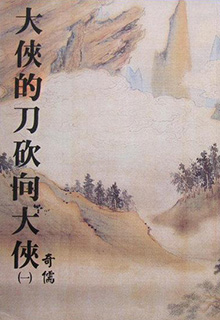河东,那原是智伯荀瑶的领地,但此刻知是属于赵襄子所有了。这是一场赌博,身家性命作孤注一掷的豪赌。
智伯是输家,也自然输掉了一切。
但赵襄子也没有赢到什么。河东经一次大战后,壮丁死亡太多,剩下的一小部份回来后,重整家园很辛苦,因为他们要养活很多孤儿寡妇。
襄子为了收买人心,特地下诏免除河东十年的赋征,他也慷慨地下诏:准许修建智伯的墓园,且决定在墓园完成之日,亲临致祭,还要带来一样珍贵的礼物智伯的人头,一只被他用来泄忿的骷髅杯,使智伯得以全骸归葬。
这对已死的智伯而言,并没有多少的意义了,但对河东的父老,却是件了不起的大事。
智伯仍然是他们心目中爱戴的领袖。死后骸骨不全,也是河东百姓的恨事。
现在,这桩大憾事总算能解决了,他们对襄子的宽大,也是十分感激。
智伯原来葬在一个荒郊,现在在一块指定的地方,兴建起庄严肃穆的墓园,大家都很尽心。
人工、民夫都是自愿前来的,他们都毫无怨言地工作着,建墓要用石头,那要从山上挖下石块,再以车马运来,襄子特地送了军马,来协助成事。
这些军卒们白天工作辛苦了,晚间总要轻松一下,那家小酒铺就成了唯一的去处。
小酒铺也是应时而开设的。智伯的墓园早先是一片荒地,连鬼都没一个,自然也没人来开设店铺了,现在有了那些军爷,以及那些民夫们,有了生意,就有人来赚残了。
小酒铺的生意好得出奇,终日不断有顾客上门,入夜时虽点了几盏油灯,照得半明半暗的,但是仍然有一大批的酒鬼挤在这儿。
酒铺的生意虽好,但卖的东西简单,除了酒之外,下酒菜只有盐水煮豆和酱狗肉。
一来是人们闲得没处去,二来是这家酒铺卖的酒很地道,最主要的是当炉的两个娘儿们都是花不溜丢的。
她们是姊妹俩,美得如同两枝花,姐姐爱穿红,妹妹喜绿,红绿交映,笑语交映,那还有不叫人着迷的吗?
不过这姐妹俩最多也只是对主顾们挺和气而已,倒不是什么不三不四的人家,她们一脸带笑,殷勤地招呼客人,如此而已。
哪个要是藉着喝多了酒,想跟她们胡调,她们的汉子就出来了。
这汉子一脸的疮疤,相貌狰狞,却又是哈腰驼背,站起来比人矮了一个头去,可是力气是大得很。
他对付那些人方法很简单,夹领一把,抓住了衣服,把人举了起来,往外一丢了事。
不管对方是多高大的汉子,到了驼子手里,就像个稻草人似的,毫无挣扎余地。
当然,也不是说这个驼子当真就没人能对付了,可是人家站在理上,谁叫那些人去调戏他的浑家的?
赵襄子遣军来助修墓是为拉拢河东人心,自然特别注重军纪,调戏妇女尤为禁例,挨了揍只好自认倒霉,吵起来不但没便宜占,说不定还会掉脑袋。再者,河东地方民风纯朴,但很骠悍,他们吃了败仗,可没有认输,更没有把赵的军爷们看成胜利者,欺负他们的女人可不行!
就因为这原故,驼子揍了好几个人,不但没事儿,反倒使别的人也乖乖的了。
虽然有些小伙子看了两个花娘们儿心里不免有些痒痒的,但是想到驼子那张可怕的脸,也就死了心。
也有人在心里不服气的,看那驼子一副猥琐的样子,深深地为两个女的伸屈。
这个丑驼子居然有两个老婆,他们怎么能平下这口气呢?因为有人问过两姐妹,她们都说是驼子的女人。
墓园快完工了,这天,从赵国又调来了一批新的军旅,他们可不是来做工的,而是赵侯的先驱卫队。
赵襄子决定在墓园完工迁葬之日,携带智伯的头骨前来致祭合葬,这一批军队是担任卫队工作的。
他们倒不敢太跋扈,也不敢太张扬,来到之前,先向河东将军王飞虎逐了照会,再一同前来,由王飞虎指定了他们驻扎的地方。
大营扎定后,除了巡逻的营卒外,其余的人都禁止出营,唯恐他们会与民众们起冲突。
因为河东的百姓们也来了不少,他们有旧日征赵的少壮,也有亲人死于战争的孤儿寡妇。
大家情绪都很激动,最易闹事,因此双方都压制一点的好。
恰好有一小队的巡卒来到小酒铺中,那个领队的十夫长是个颇为英俊的小伙子。虽然同僚们已经告诉过他这小酒铺情形,但是他却不服气,尤其是喝了几盅酒后,跟那个穿绿的小娘子又说了几句话,以为人家对他青眼独加,益发赖着不肯起来了。
渐渐的,他的话更多了,而且口齿也轻薄了起来。
驼子沉着脸出来了,走到他的座位前,只说了一个字:“滚!”
那十夫长被这一喝,看见了驼子目中的精光逼人,倒是有点怯意,可是当着十来名部下,不禁又感到脸上无光,连忙一挺腰道:“军爷是来喝酒,又不是不给钱,你凭什么叫我滚?”
驼子冷冷地道:“不凭什么,但凭这铺子是我开的,我不做你的生意,就可以叫你滚!”
“笑话!天下哪有你这种做卖买的?只要你开门,就不能禁止客人上门。”他掏了一把铜钱,往桌上一拍道:“再打两角酒来,老子喝到天黑都不走,看你能怎么样?”
驼子没有跟他多言,只走一步道:“滚!”
那小子见到来势太凶,色厉内荏地道:“老子不滚,要是敢撒野,老子就砍了你!”
呛的一声,他已经拔出了刀。
绿衣娘子见事情闹得大了,忙上来解劝,拦住驼子道:“大哥,算了吧,没几天君侯就来了,忍一忍吧!”
赵襄子来过后,此地又将归于冷寂,不会再有这么多人了,自然也没有生意做了。
这是一般人的想法,但是听在驼子耳中,又别有一种意思,他已经准备罢手了。
绿衣娘子又朝那十夫长道:“军爷,我家汉子是个粗人,不会说话,您多包涵,今天您的酒也够了,明天请再来吧!”
小子这下子占足了面子,就此下台也就罢了,偏偏他不识相,伸手抓住了绿衣娘子的手笑道:“我还早得很呢。来!再陪我喝两盅。”
绿衣娘子目视驼子,满是哀求之色。
小子更得意了,大笑道:“别怕你的汉子,小娘子,你是天仙般的人,嫁给他,真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你坐下来,他要是敢噜嗦,老子就一刀劈了他,你就可以另嫁了。”
驼子怒极上前。绿衣娘子急忙抱住他,那小子却以为这是机会,因为绿衣娘子在起身前,曾经低声道:“军爷,你快走吧,他凶得很,你会吃亏,在这儿,闹起来也是没理。”
那小子却是色迷心窍,以为绿衣娘子特别关照他,哈哈大笑道:“什么?君侯虽然严禁军队闹事,但我不同,我们是专司巡查捉拿奸人暴徒的,遇有形迹可疑的人,就能抓他起来,若敢反抗拒捕,有权格杀勿论。”说着举着刀冲上来,厉声叫道:“唉,你这驼鬼,看这副长相,非好人,看刀!”
驼子的恶名他已久闻,而且刚才接触到驼子的眼光,他忍不住有震栗之感,这时见到驼子被抱住了,心想这是机会,一刀砍了下去,只要砍倒了他,营中很多人都能作证,说驼子是个凶恶之徒。
所以这一刀他倒是毫不容情,认真砍下去的。
驼子双手一振,抛开了绿衣娘子,然后一伸手,不知怎的,刀已到了驼子手中,跟着寒光一掠,他的鼻子已经粘在刀上了,是什么样功夫?
不仅他吓呆了,那些军卒们也吓呆了,驼子把刀往地上一丢,怒声道:“滚!”
那小子鼻子被划掉都不知道痛,回头就跑。那些手下也纷纷抢着跟他跑了。
但是这批人并没有跑太远,忽而纷纷倒地,而且还有几个人过来,举刀乱砍,把那些军卒都砍倒了。
驼子大奇。那群人到了店里,首先乱踢乱打,把桌椅砍翻了,而且有一个人持刀过来,砍在驼子的身上。驼子正待反抗,看清那个人时,不动了,而且乖乖地挨了一刀,这一刀并不重,伤的部位也不重要,但是血流得不少。
跟着有一件更令人吃惊的事,就是那个穿红的娘子由后面转了出来,她看了一下道:“王将军,那家伙的鼻子是我咬掉的,他酒醉调戏我,被我咬掉鼻子,然后他砍了我一刀,以后的事就由你去说了。来吧!”
这个姓王的将军果然一刀砍在她的胸膛上,这是真砍。
红衣娘子马上倒地。
驼子大惊,上前抱住她,厉声叫道:“王飞虎,你疯了,你怎么?”
红衣娘子道:“大哥!别怪王将军,是我请求他如此的。如果不如此,事情盖不下来,你行刺的计划势必要泡汤了。小桃,你过来。”
绿衣娘子畏缩地过来。
大桃叹了口气道:“妹妹,我不怪你,我知道你有身孕,你想闹点事,使豫让的行刺计划告吹而保全他。可是你错了,豫让若是不能完成这件事,他活着也等于是死了一般,你整个地毁了他。”
小桃像是一下子崩溃了,跪了下来道:“我不管!我不要孩子生下来就没有父亲,我不要失去了他。”
大桃叹了口气,道:“也许你并没有错,但是你应该明白,豫让并不是属于你一个人的,你该明白,你不能太自私。”
她只能说到这儿,因为文姜已经伴着一位赵国的将军以及十几名亲兵急急地闯了进来。
那位将军看了满地的死尸,皱着眉头问:“这些人是谁杀死的?”
王飞虎道:“是末将。”
文姜皱了眉头道:“飞虎,你也是的,怎么杀了这么多的人,你看该怎么办?”
王飞虎道:“末将必须杀死他们,否则激起众怒,恐怕事情还要难以收抬。”
那位将军皱眉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王飞虎道:“那女子还没断气,还来得及告诉将军。”
大桃挣扎着道:“是那位军爷喝多了酒,抱着奴家要强行亲热,奴家在挣扎中,不慎咬下了他的鼻子,他就拔刀要杀奴家,奴家的汉子过来救助,也被砍伤了,那些军爷们纷纷上前要杀人,幸朽王将军来到……”
王飞虎道:“方将军,河东百姓对君侯的印象才转好一点,若是容此事宣扬出去,立即将会激起民变,所以末将只好杀了他们,以息众怒。”
文姜沉下了脸道:“方将军,河东虽已战败,但河东百姓,却不是任人欺负的,贵军到达前,我已经再三关照过,结果还是发生了这种事,你可要负全责。”
那姓方的将军道:“夫人,事情若是真如所言,自是错在敝方,可是王将军把人都杀光了,不留一个活口,全凭一面之词……”
王飞虎道:“方将军莫非认为我在说谎?”
方将军道:“我可以相信王将军的话,但是,敝方却不留一个活口,我对敝国的人又将如何交待呢?”
文姜道:“他们私出营区就已犯了死罪。”
“他们可不是出营区,他们是出来巡逻的。”
文姜道:“巡逻是为公务,如同临阵,他们却擅入民家饮酒,这就更不可恕了。”
方将军道:“他们都饮了酒吗?”
他是问小桃,小桃但哭不言。
文姜道:“有没有饮酒很容易知道,一个个检查一下就知道了,免得你又是一面之词。”
方将军挥挥手,他的部属忙分开一一检查,文姜也叫自己的手下随同去检查了一遍,赵军没有来回报,倒是一名河东的青年过来道:“夫人,他们饮酒,而且还饮得很多,个个酒气冲天。”
文姜冷笑道:“方将军,这可不是在他们死后再灌下去的,死人的肚子里灌不下酒的。”
方将军看看自己的部属,见他们没有反对,知道这项事实已无法推诿,无可奈何地道:“这是他们该死,来人哪,把尸体带回去!”
这时大桃已断了气。文姜道:“方将军,慢来,你把尸体留下,我们等君侯来看了再说。”
方将军陪笑道:“夫人,末将已自承不是了。”
“那就行了吗?这儿还有一个死的,一个伤的。”
“我们死了十来人,难道还抵不过?”
“怎么能抵呢?你的人是该死,可是这酒店夫妇死伤得太冤枉了。”
方将军只有道:“死者已矣,除非夫人还要把我也杀了偿命,此外别无他策,至于伤者,只有赔钱治伤!”
文姜道:“赔?把那十名死者的三年钱粮赔给这店主,作为伤死抚生之费。”
方将军只有道:“末将遵办,少时即将银钱送来。”
“还有,在君侯未来之前,贵军一律不得出营。”
“这怎么行?我们是来担任警戒的。”
“可是你的军纪太差,反而会出事。”
方将军沉吟片刻才道:“这件事实在难以遵命!”
文姜沉下了脸:“方将军,我这是为你好。这儿是河东地界,你们的军卒在此,极易引起反感,一点小的冲突,立可酿成巨波。像这店里的惨剧,酒醉闹事,对一个漂亮的女人调笑几句,本是很寻常的事,只是发生在你们身上就不同了,顷刻之间,就是十几条人命,若不是我赶来,他们可能会杀上大营去的。”
“夫人,最好别发生这种事,否则就会很遗憾了。”
文姜却不在乎他的威胁,冷笑一声道:“方将军,河东只是战败了,不是征服,我们还有上万的丁壮,有几万个妇女老兵,这些人都能一战的,你若是不相信,我只要一声令下,可以在一个时辰内,杀得你们片甲不留,你不妨先回去准备。”
方将军见她生气了,连忙道:“夫人,这是何苦呢?末将是受命前来担任警戒的……”
“根本是多余,凭你那一两千人,干什么都不行。我只要派出两百名甲士,足可踏平你的大营!告诉你一句话,我们之所以罢手息战,是为了心感赵侯的仁厚,若是以一副胜利者的姿态来耀武扬威,我们可不吃这一套。”
方将军只有连声陪不是。
文姜又道:“我的条件不打折扣,接不接受在你,我给你一个时辰,把你们在营外的人全撤回去,否则的话,你就准备着收尸吧。”
方将军还要说话,文姜道:“一个时辰是很快的,到了时限,我在营外看见一个赵国的人就杀一个。”
方将军总算领教到这位夫人的厉害了,他自然知道河东战士的骁勇,文姜的那些话倒不是虚伪的。更苦的是在出发之前,襄子对他一再嘱咐,要他注意军纪,万万不可跟民间起冲突。
不久之前发生了什么事,由于己方的人都死光了,已无从了解,但是那个十夫长满口满身酒气,而且杀死了一个女的,这是事实,说来总是理亏。事情闹开来,君侯一定会降罪自己,那时脑袋就保不住了。
君侯痛恨智伯,把他的头颅制成酒杯,现在却要归还,可见君侯极力在拉拢河东的人心,这时候是绝不能开罪河东百姓的,因此他一拱手道:“夫人,末将即刻就送钱粮过来。”
文姜道:“我在这儿等着,你最好快点,否则百性们看到了死者,恐怕又会起闹,我还要镇压一下。”
方将军诺诺告退。
方将军走后王飞虎道:“夫人真是了不起,败军之将,居然还能令对方屈而受命,不敢违抗,也只有夫人才能具有此等魄力!”
文姜笑道:“那没什么,也要有形势在后面作支持。形势比人强,不怕他不低头。飞虎,事情发展是如何的?怎么把人都杀了呢?”
王飞虎道:“事情是出自那个女的要求,她说形迹已经败露,必须要将来人全部杀死,否则前功尽弃。”他低声地把事情说了一遍。
文姜听了后点头道:“这位小娘子倒是很难得。小桃姑娘你过来。”
小桃过来跪下要叩头,文姜把她扶住了道:“谢谢你替我照顾他那么久。”
小桃忙道:“贱妾应该感谢夫人的成全。”
“那倒不必客气,这段时间内,我要照应河东的百姓,帮不了他的忙,还是你们方便些。怎么?在晋城一直没机会吗?”
“不,有机会的。我们行动过一次,没有得手。”
“哦?是怎么一回事?怎么会失败的呢?”
“夫人,您还是问爷吧。”
“他在哪儿?”
小桃怔住了。她相信文姜一定早已认出豫让了,而文姜居然会问出这句话。她看着豫让。
豫让笑道:“小桃,文姜夫人的丈夫是豫让,是位顶天立地的大丈夫。”
文姜也道:“我丈夫去做一件大事了,这件事没完成,他不会跟我见面的,所以刚才经过的情形,还是你来说吧!”
小桃只有把上次谋刺的经过说了一遍。
文姜点着头,听完了才道:“那倒是难怪,豫让是剑客,他看看智伯的遗骸受到了小人的凌辱,当然会受不了的。这也是他们热血男儿才有的行为,假如他能对那种事无动于衷,纵然行刺成功,也不可贵了。”
豫让微微一震,脸上带着微笑。
小桃不解地道:“为什么?夫人,这不是爷此生唯一的奋斗目标吗?”
“是的,他是一个游侠,一个剑客,游侠剑客所标榜的是一诺千金,他要刺杀襄子,不是为了私怨,不是为了国恨,只是因为他受智伯知遇太深,无以为报,而这是他在智伯生前答应过还没有做到的事,所以他要完成它。”
“那又为什么完成了并不可贵呢?”
“因为在那种情形下,还有比践诺更重要的事,那就是使智伯的遗骸不受辱。他不能在生前保护智伯,已经是万分内疚了,如果还能眼见智伯受辱而无动于衷,那就不像个人了。”
小桃点点头道:“夫人说的是,还是您了解爷。”
文姜苦笑一声道:“我宁愿不了解他。如果我不了解他,我就会像一般的女人一样,想法子去阻止他,平平凡凡地活下半辈子,因为刺杀襄子那件事已经不重要了。襄子归还遗骸,亲自致祭,善视河东百姓,这些多少也是因为他而有的改变,他就是不行刺,别人也都能谅解了,他已为智伯赢得了尊敬。”
小桃目泛异光道:“夫人,是真的吗?”
“是的。但是很遗憾,我太了解我的丈夫,他如不完成这件事,他的人活着也等于是死了,而他去完成件事后,才能堂堂正正地活着。”
“可是这一次更为困难了。”
“是的,不管是否得手,他都是死定了,行刺诸侯当灭族,他虽不死,王法也会弑死他,但那时死的只是一个刺客而不是豫让,剑客豫让从此就永恒不死了。”
“夫人作何选择呢?”
文姜的回答颇堪玩味,她幽幽一叹道:“我是豫让的妻子,我会希望丈夫死吗?我要他活千年百年。”
小桃顿了一顿才道:“我希望孩子生下来有父亲。”
文姜道:“小桃,你在做人母之前,应该先学会为人妻。假如你连丈夫都侍奉不好,又如何能教好你的孩子呢?今天幸好是你姐姐发现情形不对,立刻去向王飞虎求告,总算摆平了这件事,以后可不能傻了。”
小桃低下了头。
文姜又道:“你们是做生意的,该守本份,生意讲究和气生财,动辄找人打架,就不像是做生意了。喂!店主,你说是不是?”
豫让道:“是,多谢夫人,以后我会注意。”
“尤其你这个老婆欠庄重,该多管管。”
“是的,夫人。假如她再那样胡闹,我会管教她的,如果她太不守妇道,我就休了她。”
“别胡闹,她已经有了孩子。”
“那不是我的孩子。”
小桃脸色一变。
豫让已经沉下脸来道:“小桃,如果你那样疯疯癫癫,生下孩子来也不会好,我倒不如在他没有出世前宰了他。”
小桃掩面痛哭失声。
文姜也叹了口气道:“你们慢慢地吵吧!我要走了,还有很多事情呢。”
小桃忙止住了哭泣道:“夫人不多留一下吗?”
“不了,襄子在后天会来到,我得准备一下,因为我跟我丈夫约好了在那天见面的。”
豫让道:“夫人知道他那天准来吗?”
文姜笑道:“我对自己的丈夫有信心,不过他真要是有事耽误了,我也能谅解的。汉子,你也好好地招呼你的浑家,有身孕的人情感较为脆弱,好好地劝劝她。”
豫让只是笑笑。文姜走到了门口,豫让也送到门口。
文姜忽然道:“汉子,你说话的声音,很像我的一位故人,但他比你可高多了,若不是看到你本人,光听你声音,我真还以为是他呢。”
豫让道:“那我倒要注意,别让人当成是他。”
“你最好想想办法。要不然襄子一来,可就苦了。我那故人在赵国闹了很多事得罪了许多人,若是有人听见你说话,很可能会把你当成了他。”
豫让笑道:“那不至于,我只是个卖酒的驼子。”
“但是这儿已经闹过事了,这儿是行列仪仗必经之地,恐怕会有人来问问的。”
豫让道:“是,我会特别留意的。”
文姜又道:“我听人说,吞生炭可以使人声音变哑,你倒是可以试试看。”
豫让道:“多谢夫人,一会儿我就预备去。”
文姜叹了口气道:“这两天我没空出来了,以后我们再见吧,这两天你们别再闹事了。”
“不会了,我要办丧事,家有丧事,不做生意了。”
文姜道:“那也好,少了许多麻烦。这个死的听说也是你的婆娘?”
豫让苦笑道:“那只是说说,我一个生意人,那里养得起这么多女人,但是她死在我这儿,我倒是不能不认了,因此我打算把她算是我家里的人,到时还请夫人帮忙。”
文姜笑道:“我会安排的,王飞虎是个很义气的朋友,他会把一切做得很好,我自己恐怕抽不出空来,因为后天我要跟我丈夫一起走了。”
豫让默然片刻才道:“好吧!我就先把这个婆娘打发了,王将军,你能帮个忙吗?”
文姜已经调头走了,王飞虎仍然留下来,恭敬地垂手侍立一旁,听见了豫让的招呼,连忙恭身立正道:“大哥请吩咐,兄弟无不从命。”
豫让道:“飞虎兄,别这样,你现在已是主领河东的将军,虽然未经天子授爵,可是诸侯之间,都把你称为一个领主了,连赵襄子对你都要客气三分,而我只是一个布衣百姓,你不必对我如此客气的。”
王飞虎却恭敬地道:“大哥这么说,兄弟就太不敢当了,兄弟虽是碌碌之辈,也不是尘俗富贵所能绑得了的,兄弟之所以在河东,一则是报故主之情,二则是文姜大嫂之命,要我留下来帮她一点忙。”
豫让叹道:“你们都比我做得多,做得好。”
王飞虎道:“犬哥!兄弟以为我们目前所从事的一切,不是以成就多寡来讨功的,只要我们尽心尽力地做了,那才是最重要的,至于成功与否,已没有关系,无论事成不成,都改变不了什么。”
豫让不由得苦笑道:“是的,我也不明白何以会成这种尴尬的局势。我们似乎不为什么,也不为了什么人,更没有人在背后推挤着我们,但是却非做不可。”
王飞虎道:“是的,大哥,兄弟也有这个感觉。我们就像是扑向火炬的飞蛾那样,虽是说不出一个所以然,却会以无比勇气与毅力以赴,停都停不了。”
豫让想了一下道:“河东对襄子之来作何反应?”
王飞虎道:“他们不会反对、仇视他,但也不会去拥戴他,在河东,智伯的地位是无人可以替代的。”
“这就好,我是怕大家还记住仇恨,有所蠢动,会造成很糟的结果。”
“这个大哥放心,大嫂一直在向他们多方解说,绝不会让他们做出贻祸乡里的事来。”
豫让道:“她也没有另作部署吧?”
“没有。她说过,这是大哥一个人的事,任何人都帮不上忙,也不让任何人插手。”
“那我就是这个问题了。”他的手指向了小桃,沉声道:“她已经有了身孕,我本来也在遗憾着,怕愧对泉下的祖先,现在这个问题倒是解决了。”
王飞虎喜道:“恭喜大哥后继有人。”
豫让道:“我想请你把她送到我家乡去。”
小桃立刻道:“不,我不去。”
豫让道:“你在这儿,会碍我的事。”
“我不会了。我从现在起,不说一句话。”
豫让摇头道:“你刚才就害死了大桃,所以你一定要离开。你在这儿,我放不开手去行事。”
“大哥!我求求你,别把我送走!”
王飞虎道:“嫂子倒是必须要走,否则事后谁都无法保护你了,行刺君侯乃灭族之罪。”
“我知道,上一次不是也没事吗?”
“那是大哥没有得手,襄子又不加追究。这次大哥一定不会失手了,即使不能成功,也不会有上次的情形了。大嫂既已有了身孕,还是要早点离开……”
小桃倔强地道:“不,我们死也要死在一起。”
豫让怒道:“小桃,你要死也得把孩子生下来再死。”
“大哥,你若是坚持要我走开,我就先毁了孩子。”
豫让看看她道:“你打算这么做?”
小桃道:“你要是把我逼急了,我就做给你看,你知道我是否有这个胆子的。”
豫让顿了一顿才道:“小桃,我现在倒不想要你走了,因为我也不想要那个孩子,在你这种狠毒的母亲身上生下的孩子,必将是个恶毒的人,所以我要先毁了他。”
小桃怔住了。
豫让道:“你放心吧,才两个月左右,婴儿尚未成形,不会很痛的。”说着他的手指戳向她的腹部。
王飞虎忙将小桃推开,急声道:“大哥,你这是做什么?”
小桃已经昏倒了。
豫让道:“我要她走!”
“那也不必如此。”
豫让道:“小桃知道我对她腹中的孩子很重视,才会以此来要胁我,这是很愚蠢的事。
我就让她明白,我并不是像她所想的那么珍视这个孩子。”
王飞虎叹了口气,叫从人扶起了昏绝的小桃,并且很快地将她送走。
他很想跟豫让多谈谈,但是没多久,方将军那儿着人送钱来了,由王飞虎代为收下。
来人走了后,王飞虎道:“大哥,这钱要加何处理?”
“你看着办吧,反正我是用不着了。”
王飞虎想了一下道:“那就交给小桃吧,虽然,以后我们会照顾她的生活,但是这笔钱应该是她的。”
从人回来复命,小桃经过文姜夫人劝说了她几句,总算乖乖的上路了。
豫让笑道:“是的,我这一生中乏善可陈,但是却娶了个好老婆,交了这样的好朋友,再有就是遇上了智伯那样的好东主,这一生实在已经满足的了。”
王飞虎觉得不便再说什么,而豫让也不想问什么,这使王飞虎很纳闷,他原以为豫让会问一下文姜在什么地方或是别后的情形,但豫让没有开口的意思。
他曾在文姜那儿略作试探,文姜居然也没有见面小聚的意思,但他深知这夫妇两人感情之深,是无以言喻的。
文姜在河东时,每天都在静处对天祈祷,为豫让祝福,可是现在豫让来到了此地,文姜反而没有一见之意。
这夫妇两人都是不平凡的怪人,所以他们的思想行为,不是我们这种凡夫俗子所能理解的。这是王飞虎在心中暗自所作的结论,但他自言自语时,是充满了尊敬。
豫让弄了几块生炭吞了下去,干而粗厉的炭很难下咽,有时要用手指的力量硬往喉咙塞下去。
粗糙的炭划破他的喉咙,但他的目的达到了,他声音变得低哑深沉,再也没有以前那种嘹亮震人了,再加上他故意以叠骨法做的驼背,使他面目全非,完全看不出一点旧日的形貌。
襄子的侯驾终于来到,他为了表示他的诚意,轻纵简骑而来,但他毕竟是一国之君,不能过于草率,所以在他行祭时,仪仗军列排在两旁,亲人等被隔得远远的,不得接近。
连王飞虎和文姜她们也都被隔开,只有一个人例外,那是酒店中的驼子,因为他死也不肯离开他的店。因为在他的店里闹过事,而且还杀了他的一个女人,方将军多少有点歉意,没有办法去赶他。
赵襄子骑着马,后面跟一对步行的侍从,其中一人捧着—个金盒,盒中放着智伯的骸骨。
墓园已经做好,只等这一盒子放进去,就算是完骨全安葬了。
河东的父老百姓们都含着泪,捧着香,虽然被隔在两边,仍然是十分哀切。
襄子的马经过时,他们不见行动,但是等装有智伯骸骨的金盒经过时,每人都擎香跪了下来,低声祝祷。
襄子的骑乘跟后面的智伯骨骸柜距不逾两三丈,因此这种情形,他看得很清楚。
他的风度是很好的,一般的情形,这种清况,都会悖然而震怒,但襄子没有,他只有感慨地想着:荀瑶的确是个人杰,我能胜过他是运气。他攻进晋城,我的百姓对他歌颂仁德,我以征服者的身份来到此地,仍不如他受到尊敬,看来河东的百倒真够倔强的,他们不容易归心于一个人,但如把心交给了谁,就很难再转移。
有两名侍卫看到了这种情形,走近襄子低声道:“君侯,这些百姓们太无礼了,也太顽强了。”
襄子连忙道:“别胡说,这才是真正的义民,他们不忘故主,正是忠义的表现。”
“可是他们对君侯太不敬了。”
“他们对我并没有恭敬的理由,我杀了他们所敬爱的领主,伤了他们的子弟,他们是应该恨我才对。”
“君侯,是他们先启战端来攻打我们……”
“唉!王琮,你不懂,有些事情是不能以道理去评估的。战争已经过去了,是非就不存在了。我还活着,他们却死了,这才是事实,他们心里不舒坦是必然的。你退下去,态度放恭敬些,不要引起他们的反感。”
襄子斥退了这名王琮的侍卫,自己也下马来步行了,反而叫那名捧着金盒的侍臣骑在马上,他自己在马前牵镫而行,态度愈见庄重。
赵国的大夫子盾过来了。他是天子所委,作为诸侯的礼仪以及事物顾问,上前道:“君侯,这不可。依礼仪所定尊卑之分,君侯不可如此。”
襄子却一笑道:“智伯所授的爵秩尊于我,他是河东伯,我只是子爵而已,何况先者为大,我对他尊敬亦未逾越,我觉得应该对他恭敬一点。”
“可是君侯现已承继公侯的身份,为一国之君了,名份之所关,不能错的。”
襄子微笑道:“大夫,礼法是死的,人是活的!活人若受死法所拘,那太愚蠢了。若说要遵守成规,我们韩赵魏三姓,都是晋公的众臣,三家分晋,已失人臣之分,朝廷该对我们大申挞伐才对,可是天子却派了大夫前来,承认了我们的地位,这不也是反了礼法尊卑正名之义了吗?大夫食禄于赵已有数年,怎么未有见及此呢?”
这番话说得太直率了,使得子盾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此时诸侯割地自雄,君权早巳衰微。五霸时代,霸主还喊出了尊王攘夷的口号,对那个没多大实权的天子还保持礼貌上的尊敬,但到了三家分晋后,七雄分据,攻战时起,天子根本就管不了,朝廷也就形同虚设。
大夫子盾是太子派来的,襄子继位时,年纪尚轻,对他倒是颇为客气,他就倚老卖老起来,渐渐的言词上对襄子颇为干涉,使得襄子很讨厌他。
今天正好是个机会,着着实实地抢白了他一顿。当然,这种话也只有襄子才够资格讲,出于别人之口,就是大不敬罪了。而且襄子并不讳自己先人分晋之事,使得这位礼法权威的大夫汗流浃背,却又哑口无言。
襄子微微一笑道:“天气太热,大夫上了岁数,不宜多作步行,请上马去吧!我年纪轻,走两步没关系的。”
“不,不!君侯都在走路,老臣怎敢僭越?”
“那就慢慢的走吧!王琮,扶住大夫,若是大夫走不动了,就歇一下。今天我是以私人的身份前来致祭,不行国礼,大夫到不到都没有关系。”
他穿了私服,这也是为了避免引起反感,若是他大排仪仗,堂堂皇皇地前来,就不会草率了,而河东百姓对他的态度尚未十分转变,不是自讨没趣就是一场大冲突,那就失去他拉拢人心的本意了。
襄子是个聪明人,不会做那种笨事的,因此,他的行事也可以有适度的自由去表现他的谦逊。
而这一着还真用对了,他再向前行时,前面的河东父老不待他走近,即已跪了下来,口中呼着:“多谢君侯!”
这是百姓们表示谢意,也可以解释为他们感谢他对智伯的礼遇与恭敬,再者,也可以说他们是为智伯而跪拜,但不管怎么说,这已经是一个好的开始了。
而且,百姓们称他君侯,这已经是承认他了。国无二君,百姓们口中的君侯,没有第二个的,他们口中称他为君侯,即已自承他的子民了。
襄子心中非常得意,他终于成功地获取到河东的拥戴,这是很足珍贵的,他几乎想笑出声来。但此时此地,是不容轻慢的,他只能努力地把笑容浅浅地刻在脸上,和气地不住点头道:“不敢当,不敢当!应该的,应该的!”
这种谦和使他更为取得好感了,河东人是不易流露感情的,他们虽然还没什么进一步的表现,但是一个个热泪盈眶。襄子知道他已真正地征服了这个地方。
但是在稍前的地方,却有一个人为这种现象感到十分的焦灼不安,那是豫让。
他身在左边的桥下,过了桥就是墓园的入口,桥的两端站了不少的人,河东的重要人物如王飞虎、文姜等都在桥的那一端。
照一般的情形,襄子马到此处,必然略为加速过桥,以接受河东首要的迎接。到了这儿,他的注意力将会为对岸的人所吸引,防范较疏,也是最易下手之际。
豫让一大早就蜷伏此地,躲在桥洞中,准备等襄子过来,暴起出击。
但是现在襄子下马步行,这使他搏击较为不利,因为马上行动不便,得手的可能较大。
现在,不但襄子的行动较为利便,而且又走在马的右边,豫让从左面出来,有马身相间,直接攻到襄子的机会就更为减少了。
本来,豫让若全力一击,剑气所及,足可将马腹裂穿而不减威势,但是智伯的骨骸在马上,那是不能冒渎的。
时机稍纵即逝,如果等襄子走过去,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因为回程时,襄子必然是在扈从车骑的簇拥下行进,更没有办法得手了。
因此,当襄子走近桥头的时侯,豫让还是作了个最危险的选择,他冲出了桥洞,弓着的身子忽地弹得笔直,像飞鸟般的弹起两丈多高,越过马身,剑光下扫,发出了惊天动地的一击。
这是他在万般无奈下定的步骤,也是唯一可行之途,除了从上面越过外,没有任何的办法了。
因为襄子本人的技击极精,而且随行的护卫俱非庸手,只有突然的一击才有得手可能,若是先给他们发觉,就全无机会了。
从桥下出来,已经被人发觉,然而可以利用人们在惊愕时所生的片刻迟疑,迅速地行动,在对方措手不及的情况下得手,所以,一出来就要立刻进攻,如果他绕过马身去找襄子,那就来不及了。这不仅是找到他的问题,还要发动攻击,也不是随便的出手,而是全部劲力凝聚的一击。
豫让在很早以前就剑气蓄势,使自己像一柄拉满了弦的弓,然后再使自己再像控在弦上的那枝箭,急射而出。
箭不能拐弯,但是由高而下时,有一个弧度。
豫让也是一样,他身与剑合一,越过马身,笔直地向着襄子刺去。这雷霆万钧的一剑,应该毫无疑问的能得手,而襄子在极度的惊骇中,也不知道闪避或拔剑抵抗了。
然而,豫让那一击落了空,剑尖以两寸的偏差,刺在襄子的颈旁滑过。倒是他的冲势,把襄子撞倒了。
以豫让那样的剑手,作全力的一击时,居然会刺弯偏过,这实在是令人难以相信的。
豫让自己也无法解释。他只感觉到在将要得手时,有样东西在他脚上轻轻地一碰,只是些微的,然而使他的剑势偏了半尺。
他自己也无法解释那半空中的一触是何由而来,只有委之天意,大概是上天不让襄子死在他的剑下。
天意如此,何能违天而行?因此跟襄子一起倒地的豫让,已经放弃了努力,不想再尝试了。
其实所谓天意,却只是一只马蹄而已。
马匹被掠过的人影所惊,忽地前蹄扬起挥了一下,这是马的习性,襄子乘坐的这匹马是久经训练的战驹,它发觉掠过的黑影不过是一个人,立刻又安静下来。
这些动作都极快,但是它惊立而起扬蹄时,马蹄在豫让的靴底上轻轻地擦了一下。
若是有半分的间隙,双方都不会接触了,就是这轻轻一触,使得豫让功败垂成,也挽救了襄子一命。
襄子毕竟是经过大风浪的沙场老手,突然的惊诧过后,立刻恢复了神智,发觉这个突出的人将要不利于自己,立即握住了对方握剑的手,不让他再有攻击的机会,另一只手紧紧地勾住了他的腰,使他无法动弹。
他还没有看清豫让的脸,他的头由对方的肋下穿过,紧贴着对方,使自己的喉头,眼睛等容易受伤的部位都在无法攻击的地方,这是一个老经验的斗士常采取的方法,在贴身的肉搏中,避开要害受伤是第一要务。
而且他知道不必支持太久,他侍卫们就会来解围的。可是在他的感受中,这个刺客似乎是个很平凡的人,身上连一丝劲力都没有,也没有一点挣扎的意图。
不必等侍卫们过来,他自己就能打了。于是他手一用劲,把对方远远地抛了开去,更巧妙地,在对方身躯离去时,自己一个鲤跃翻起,呛然长剑出鞘,直刺出去。
抛人、出剑、挺身、发招,四个动作一气呵成,他不但表现了优越的战技,也借机会炫耀了一下自己的武功。
他知道此时有很多河东的人在看着,而河东的百姓尚武、崇拜英雄,这一手必可得到赞赏。
果然,很多人都为他漂亮的身法与手法响起了欢呼,大家虽然为突然出现的事件而震住了,但因为大家对襄子已经没有了敌意,因此,对这个行刺的人也没有特别的支持,当然他们也没有对刺客怀有仇意。
他们的立场是超然的,无所偏袒的,襄子表现了一招漂亮的脱身与反击,赢得了欢呼,他们也希望这个刺客能够露几手漂亮的攻击。
照他由桥下出来所作的出手一击,他无疑是个技击高手,这一战将是很精采的。
可是大家很失望,连襄子亦然,因为那个刺客虽然擎剑而立,却没有作战的意思。
但是他的剑并不是垂下或是无力战斗的样子。
他所采取的姿势仍是充满了战斗性的,只不过他听任襄子的剑长驱直入而没有抵挡而已。
这实在太怪了,也太出人意外了,襄子是个很谨慎的剑手,反而不敢深入了,剑尖已经刺中对方的胸膛,入肉分许,忽然急速拔剑退后。
刺客却一动都没有动,依然那样站着,被刺中的部位已经流出鲜血,但是他像一尊翁仲般的站着。
襄子怔住了。他不知道对方的目的何在,这时大批的侍卫都拥了过来。
有两个执剑上前道:“喂,汉子,你好大的胆子,居然敢行刺君侯,还不快快放下凶器,束手就擒!”
刺客只轻蔑地看了他们一眼,说道:“剑客的剑永不离手的,你们可以把我杀了,却不能叫我弃剑。”
声音虽很沙哑,而语气却很傲,那些侍卫正准备上前,襄子却喝止他们道:“退下来,由我来斗斗他。”
那刚上任的侍卫领班王琮道:“君侯,这应该是卑职们的责任,君候何必冒险呢?”
襄子冷笑道:“你的责任是保护我,可是在危险中,仍然是靠我自己解脱。”
王琮低下了头道:“是!是!请恕卑职们失职疏忽,但卑职们没想到他会由桥下出来,卑职等以前已经检查过那个地方,那里是绝无可能藏人的。”
“喔?绝无可能?那他是如何藏身的呢?”
“这个卑职实在难以想像,那桥头根本没有立足之处,桥下的水深逾丈,连站有水中都不可能,而桥腹处的桥洞只有径尺大小。”
“那已经够把一个人缩在里面了。寻常只要能把头钻过去的孔,身子也能跟着过去,”
“可是那桥孔却不通的,只得三尺来深,最多只能藏进半个人,有一半要在外面。”
襄子冷笑道:“武功练得好的人,能把身上的骨节松散,身躯四肢屈折合成最小的体积,有三尺多深,一尺为径的地方,足够藏身了,”
王琮讶然道:“卑职听人说过,但不信有人能练到这种境界,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襄子冷笑道:“王琮,你自己不行,却不能把别人也看成如此。别的不说,要讲藏身于那个桥洞中,在跟前就有两个人能办得到。”
王琮道:“是,是,君侯。属下孤陋寡闻,这汉子由桥下出来,藏身桥洞中殆无疑问,属下一时未注意及此,请君侯原谅,属下愿领失职之罪。”
襄子叹道:“罢了,你已经很尽心了,像那种情形,是特殊的例子,能达到那种标准的,举世也没几个人,你想不到也不足为怪。”
“多谢君侯不罪。君侯,这刺客既有那等手段,必然不是庸手,君侯更不可冒险轻斗了,还是让属下来吧。”
襄子沉声道:“你们应付得了吗?”
王琮顿了一顿,才道:“属下等当尽全力扑杀这个刺客。一人不行,就用十个人,属下等愿效死命。”
襄子笑道:“人家能运气叠骨,你连这种功夫都不知道,两下相去甚远,上去一定是送死。虽然你们仗着人多,可以用轮战制服对方,但是太不公平了。”
王琮忙道:“君候,属下等乃为护人而尽职守,不是武人争强斗胜,不讲什么公平的。”
“不行!我是学剑的人,我讲究的就是公平,在我跟前,不准有倚多为胜的事,你要是行,就一对一上前对战,不行就让给别人来。”
王琮道:“属下自承不行,但不知道还有谁行。对了,君侯说眼前就有两人擅长缩体之功,一个是这刺客,还有—个是谁呢?”
襄子脱去了身上的外衣,整理了一下劲装道:“我!”
“啊!是君侯?”
“是的。练剑到了某一个阶段,讲究身与剑合,那就必须要使肢体柔软任意屈伸,然后才能发挥某些招式的精辟之处,使对方无法想像的情况下突出奇招。我已经突破那个阶段,所以我才知道有那种可能。”
“属下愚昧,不知君侯高明若此。”
襄子微微一笑道:“我的责任在施政牧民,本不应该把精力放在击剑上的,可是我由剑道中悟出许多道理,在理政治国用兵交战时都能适用,而且还别具徵效。”
“剑道即仁道!”木立的刺客忽然开口了。声音还是沙哑的,然而语气中有着无比的庄严,使得襄子悚然动容,移目看去,豫让的脸又经过了一番改变,连声音也变了,但是他的那种内在的剑客的风标却是无法改变的,尤其是那种面对着死亡而毫无畏惧的态度,使得襄子十分熟悉。
他顿了一顿之后才道:“豫让,怎么又是你?”
这句话问出后,四下都为之震动,尤其是河东的父老们,因为豫让跟他们的关系太密切了,难道这个形貌丑陋的汉子会是豫让吗?很多人不相信,他们都见过豫让,豫让是个美男子,英俊魁伟,剑技超凡,所向无敌,视如天神。这个汉子怎么会是豫让呢?
但有些地方却又使他们无法不信。第一是这汉子的身形很像,第二是他那一剑在手,睥睨天下的气概。这个汉子虽然一击未中,但他抱剑在手,毫无恐惧,只是他也没有了杀机,没有继续动手的意思。
原野上虽然拥集了近万人,但是没有一丝声息,人人都屏息伫望着。还有不少人看着文姜,想从她的脸上找出答案,但他们也失望了。文姜站得也如同一尊石像,没一点表情,似乎那个人并不是她的丈夫,也似乎豫让这两个字与她毫无关系。
------------------------------------
天马 扫描,玄鹤 OCR,旧雨楼独家连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