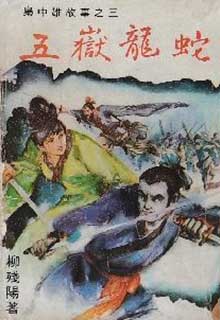(一)
这条不好看的银链子,已经勒死过二十九人,其中还包括八个女人、六个完全不懂武功的小伙子。
但余下来的十五人,却全是江湖上名气响当当的英雄好汉。
容巧辙什么酒都喝,除了毒酒。
容巧辙什么人都杀,除了自己和自己的骨肉。
幸好他的酒量不是天下第一,武功也不是天下第一,否则这一代的武林人就太遭殃了。
饶是如此,他仍然是一个很可怕的杀人者。
银链子已套在曾非禅的脖子上,就像是钩子已锁住了鱼儿的腮。
曲不方仍然站立在那里,好像根本没有看见自己的父亲正在跟别人拼命。
但忽然间,他的右手已扣着了一把飞刀,而且立刻就向曾非禅咽喉下五寸的地方射去。
这人虽然身材庞大,但五指之灵活,手法之熟练,却已足够令人看得发呆。
但曾非禅没有呆住。
他若稍一分神,这刹那间便已成为刀下之鬼。
刀光才飞起,禅杖也已飞舞。
叮!
飞刀被击落,但那条银链子却已把他的脖子缠得更紧,再缠多一刻,他的舌头就会胀大,他的眼珠子就会突出来,他的性命也得同时完结。
但曾非禅并不是脓包。
辽东双鹰虽然打不过许多绝顶高手,但他们的声名也不是白赚回来的。
他突然顺势向容巧辙冲前,单手挥动禅杖力拒曲不方,左掌却如闪电般发出凌厉的一击。
容巧辙吃了一惊。
他已知道是曾非禅已成为本教的叛徒,却没想到曾非禅还要跟自己拼命。
那是名符其实的拼命。
他仿佛根本不理会自己的死活,只求把容巧辙杀掉而后甘心。
即使是拼个同归于尽,亦在所不惜!
拼将一死的人,往往也就是最可怕的人
这种人已一无顾虑,但别人要顾虑的地方却是太多。
即使容巧辙的武功在曾非禅之上,遇上了这种情况也是大大的不妙。
而且容巧辙的武功,其实还及不上曾非禅。
他唯一占着优势的,就是他还有一个儿子,而且这里也是他的地方。
这一战才开始,四周已同时出现了十二个黑衣武士。
但他们没有动手,只是在一旁虎视眈眈。
容巧辙总算避开那一掌,但他的银链子却被逼放弃。
这时候,曲不方一爪向曾非禅迎头插下。
曲不方是一个很粗壮的人。
他的手指也和他的人同样粗壮。
但他的十指却既尖且利,就像是苍鹰的一双爪。
呼!
一股寒风,在曾非禅的面门扫过,曲不方发出来的内力竟然是阴寒无比的。
这一点倒是出乎曾非禅意料之外。
但他只是感到意外,却没有感到恐惧。
他的身子向左边一侧,闪过曲不方这一爪。
曲不方狞笑:“再接一爪!”
他第二爪又挥出,这一次他抓的是曾非禅的面门。
但这一次曾非禅不再闪避,反而张开嘴巴,狠狠咬了曲不方一口!
曲不方这爪虽快,但曾非禅的嘴巴更快,竟然硬生生的咬断了他的一只食指,曲不方的狞笑,已变成痛彻心肺的尖叫。
曾非禅满嘴鲜血,那不单是曲不方手上流出来的血,还有他的牙血。
他咬得用力过猛,居然脱掉了两颗门牙。
少了两颗门牙的人,他的样子通常都是有点滑稽的。
但曾非禅的模样并不滑稽,只会使人感到心悸,从心里冷出来。
曲不方断了一指,容巧辙连眼睛都红了。
他突然从靴子里摸出一把半尺长的刀来。
刀锋很薄,要割断一个人的喉管,那是轻而易举的事。
但他这一刀还没刺出,曾非禅的禅杖已重重击在他的胸膛上。
容巧嫌眼前一黑,身如鸢子般向后飞了开去。
曲不方怒呼不已,大喝:“你们还在呆什么鸟?上,把这杂种碎尸万段!”
那十二个黑衣武士吓得面色发青,连忙蜂涌上前,向曾非禅猛攻猛打。
血肉横飞,惨呼不绝。
倘若金松鼠在这里,一定会看得目瞪口呆。
曾非禅竟然敢倒戈相向,而且还拼着一死,以谢罪江湖!
若非目睹,又有谁能相信这是事实?
(二)
血已干。
每个人身上流出来的血,都已干透。
每个人的心脏,也早已停止了跳动。
容巧辙瞪着眼睛,仰望着天,脸上带着一种无法描述、惊惶已极的神色。
这神态已僵。
和他的身子一起僵硬。
曲不方也倒卧在他的身旁。
他不但不见了一根手指,还不见半边脑袋。
他死得更惨。
那十二个黑衣武士,平时威风八面,但是现在却横七竖八的躺在地上,没有一个还能活着。
唯一还活着的人,只是曾非禅。
他赶跑了香凤楼的翠娇,还把香凤楼中几个凶巴巴的奴才打伤,然后才去找容巧辙、曲不方拼命。
卫七龙救了他一命,也给了他一条活路。
但他却忽然顿彻顿悟,忽然发觉自己以前所做的事,全都错了。
人,毕竟还有良知。
当邱九指死后,曾非禅终于觉悟前非,决定以死谢罪江湖。
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事。
但这不是故事,而是血淋淋的事实。
回头是岸,曾非禅终于回头。
纵然他死了,他已非身在苦海,而是已登彼岸!
所以,他现在虽然已奄奄一息,心境却比从前任何时候更开朗,更愉快,也更感安慰!
曾非禅累了。
一股极度疲乏之意,笼罩着他全身。
他闭上眼睛,立刻就看见了邱九指。
他知道自己快要死了。
他甚至以为自己已经死了。
他身上、腕上、大腿上不知总共有多少处伤口,其中有些血已干,结了疤,但是也有些还在流血。
他已不能再支持下去。
但就在这时候,距离亭外二十丈的一株老树上“蓬”的一声,跌下了一个人来。
这人年约五旬,身材比曲不方还更健硕。
如此壮汉,就算是一条吊睛白额大虫看见他,也未必敢轻举妄动。
好个庞然巨物,好吓人。
这庞然巨物怎会像桶子从树上摔下来的?
(三)
这五十岁的巨汉是个大胡子。
当他从树上跌下来的时候,颔下的胡子都已湿透。
令他胡子尽湿的并不是水,而是酒。
虽然他从树上摔下来,连屁股都似要开了花,但他手里捧着的一个大酒壶,却还是那么稳定,连一点酒也没有溅出来。
这也难说,因为酒壶里根本已经没有酒了。
容巧辙喝的是汾酒。
大胡子喝的也是汾酒。
容巧辙用的杯子够大,酒瓶也特别大。
但倘跟这个大胡子手里的酒壶一比,却还相差十万八千里。
这酒壶是用铜铸成的,形状大得出奇,份量也是沉重得不可思议。
大胡子在地上躺了一会,才懒洋洋的站起来,然后走到曾非禅的身边,醉醺醺的说:“你有种,你有胆色,庞某佩服得紧!”
曾非禅没有回答,甚至连眼皮都没有抬动一下。
大胡子哈哈一笑,又说道:“起来,起来!咱们再喝他的三百斤酒,然后……然后……呃……”
他“然后,然后”之后,忽然弯下了腰,猛吐起来。
他吐得很厉害,而且吐出来的秽物,几乎全都落在曾非禅的身上。
这阵异味,当真令人难以忍受!
但曾非禅还是没有半点反应。
大胡子吐了又吐,直到吐了第三次之后,酒意有点消除了。他忽然“啊呀”一声,叫道:“不好!这厮快要咽气!”
他东张西望,最后背起曾非禅,向北而去。
自此之后,江湖上再也没有曾非禅这个人出现,人人都以为他死了。
大胡子离去后,亭外忽然悄悄的来了一个紫衣人。
他大概三十岁,走路的脚步声很轻,但十根手指却不断发出“嘞嘞”声响。
虽然他长得并不难看,但脸色却嫌苍白一点。
据说年少多金的人,往往反而身子会比别人虚弱一点。
他站在亭下,皱眉想了很久。
就在他沉思的时候,亭下出现了另一个人!
这人赫然竟是尹青霖!
(四)
“阮兄,你看那人是谁?”尹青霖忽然问。
“不敢确定。”紫衣人摇摇头,叹了口气。
“你认为他是谁?”
“庞巨龙。”
“是北三龙之一的‘醉卧中原”庞巨龙?”
“不错。”
“正因如此,你刚才没有出手?”
“也不错。”
“这人真的那么可怕?”
紫衣人冷冷的瞧了他一眼,微喟道:“中原六条龙,每一个人都有不容忽视的力量。”
尹青霖眼睛里闪过一道寒光:“现在中原六条龙已变成了七条龙。”
紫衣人道:“第七条龙是谁?是不是金陵第一剑花雨傲?”
尹青霖摇摇头。
紫衣人似是微感意外:“不是他又是谁?”
尹青霖道:“是洛阳城丁猎以前的师弟七郎。”
“洛阳城丁猎”这五个字,仿佛是五把尖刀,同时插在紫衣人的心房上。
他面上的肌肉一阵抽搐,半晌才道:“是不是那个黑衣卫七龙?”
尹青霖点点头。
紫衣人冷笑:“他配称为中原七条龙之一吗?”
尹青霖这次却摇摇头:“不知道。”
“你知道的事太少,不知道的事却太多!”紫衣人雇头打了个结。
尹青霖没有生气,却淡淡的说道:“但我却知道,卫七龙被列为中七条龙之一,有人不大服气。”
“是不是花雨傲?”
“花雨傲服气与否,我倒不知道,但我却可以肯定,他的三位师父必然深深不忿。”
紫衣人道:“他有三个师父?”
尹青霖道:“不错,卫七龙的三位师父是南三龙,而花雨傲的三位师父则是北三龙。”
紫衣人吸了口气,没有再说话。
他忽然用一种很奇特的目光盯着尹青霖。
很难形容这种目光是什么滋味。
是羡慕?是妒忌?还是在自己揶揄自己?
——“你知道的事太少,不知道的事却太多!”
这两句话,是紫衣人刚才对尹青霖说的。
现在,紫衣人似已把这两句话,贴在自己的脸上。
当紫衣人正在盯着尹青霖时候,一阵急骤的马蹄声忽然响起来。
蹄声渐近,那是一匹灰马。
马鞍上的骑士,穿着一身青红相衬的衣裳,手里提着一杆铁枪,神态异常的威武。
尹青霖目光一闪道:“是总坛枪组的武士。”
紫衣人冷漠一笑:“这个我知道。”
尹青霖立刻闭上了嘴巴!
那武士策马来到亭下,却没下马,只是说了两句话:“虎爵传令召见紫云、青衣两堂的堂主。”
灰马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瞬即又已消失在远方。
(五)
夜色茫茫,无月无星。
在一座高山下,一丛密林中,隐约传出微弱的灯光。
山名恶虎,林却无名。
很少人敢踏足恶虎山,更绝少人曾进入这丛密林内。
此处是穷山恶水之地,除了虎狼恶兽、毒蛇蝎子之外,还有妖魔出没。
虎狼虽凶猛,犹有对付之道。
但妖魔出没无常,随时随地都会把人活活吃掉,那才是真的防不胜防。
曾经有一个采药的庄稼汉,亲眼看见一个长发披肩,黑面獠牙的妖魔,在这恶虎山上活剥人皮,生吞人肉。
这庄稼汉吓得魂不附体,连跑带跌,好不容易才离开恶虎山。
此事一经传开,谁都不敢再冒这个险了。
反正这里是穷山恶水之地,又不是一座足以引人入胜的大金矿。
这种鬼地方,又有谁想来?
“虎爵传令,召见紫云、青衣两堂堂主。”
这是虎爵的命令。
令已传达,人也已到了虎楼外!
虎楼就在这鬼地方的深处,除了极少数的人之外,任何人接近这里,都必死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