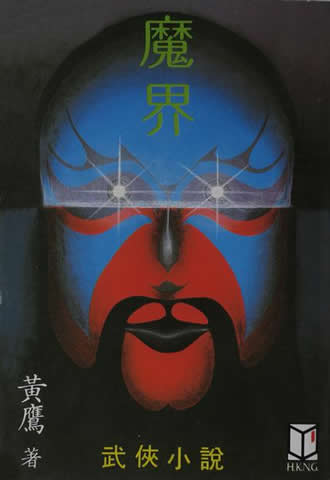这三个人头,展宁只须略为打量一眼,便将它一一认出来了——
这正是那贺天龙,菊花仙姑,与华山樵子陈亮的三颗六阳魁首!老和尚双手一合什,低声诵念道:“罪过!罪过!阿弥陀佛!”
展宁一步赶到身边,面对地狱谷主,直指喝问道:
“你既非立意逃走,你在谷口外面的丛林中现身,又为何来?”
地狱谷主,满面死灰的脸色,进出两个单音来道:“找你!”
“找我吗?哈哈!这倒是好的很!”
展宁胸脯一挺,双手在胸前一抡,无比凄厉地,吼道:
“这正好,你有非亲手杀我展宁的决心,我也有必杀你而不可的誓言,我师叔是百龄以上的有道高僧,我保证他老人家决不插手助拳,来来来,乘这江边日丽风轻,你将压箱的绝活搬出来,我俩不分强弱死不罢手,如何?”
地狱谷主不住摇头中,咧嘴一笑道:
“匹夫之勇,你小子多此一说,我邬子云要替你寒心了!”
展宁双眼猛然一翻,厉声暴吼道:
“我应该怎样说,才能使你不讥作匹夫之勇?才能不使你寒心呢?”
邬子云好整以暇地,涌起一丝干涩的笑容来,道:
“有了黄山的一番遭遇,老夫才认清你这小子当真算得是仁心侠胆,很具有几分一派大侠的磊落气度的人。直到现在,老夫方始认真探索出为什么我的一双如花似玉的掌珠,要对你这小子,深深种下爱苗的根源来……”
展宁已是不耐其烦了,怒极大喝道:
“邬子云,你用不着婆婆妈妈!也别打算用爱情的烦恼来羁绊我展宁!你指望我看在你两个女儿的份上,便能放过你一条生命么?做梦!你在做梦!”
地狱谷主鹞眼陡然一翻,也报以一声怒叱道:
“你这小子,怎地这样不知好歹?怎地又这样不能容人?老夫若是一个靠裙带关系,芍且能够偷生的人,你想,我能落个这样下场吗?”
似是有冤没处伸,地狱谷主一转头,却朝了行大师苦笑道:
“大和尚,你来评评理,我邬子云若有图逃之意,恁籍一尊蜡制人像,在地狱谷中,就连逍遥先生也被我蒙混住了!现在,那一群自命为高手的人,包围着那间破庙,尚在喋喋吵闹不休呢?大师你想,我邬子云既已潜出谷来,为什么放着一条向左能够逃生的路不走,明明看到您俩在这儿,我要送羊进虎口,为的是什么呢?”
“是呀?你为的是什么呢?……”
了行大师茫然说出这一声,对邬子云又端详了几眼,动容说道:
“邬施主,若是老衲的揣测不差,你生命之火已尽,在世的时间,可能不久了!”
“是的!”邬子云率直应承道:“我在熬……这……片刻时光!”
“你服了毒?”
“是的,最毒,而又无药可解‘亡魂鹤顶红’……”
展宁脚下一滑,一步欺进身来道:
“怎么?你服了毒?不让我亲手报仇?不让我一快心意是不是?”
地狱谷主苦笑道:
“错了!……小子你又错了!我正是让你一快心意,偿你报仇的意愿的呢……你现在割下我的首级……掏出我的心肝……又有什么两样?”
展宁猛然一跺脚道:
“我不领你这份情,我杀却一个并无还手之力的人,我胜之也不武!”
地狱谷主,鹞眼中一现希望之光,管自强笑道:
“小子!你……用不着发火,也许……老夫的用意,正是有利……与你呢?听你之言,我邬子云修得福份,临终……还可能落个全尸喽?……”
随即,他又摇摇头,幽幽一叹道:
“其实,生不认魂……死也不认尸,我要求一付整个……臭皮囊,对我?……又有什么价值?……”
了行大师,冲着地狱谷主一摇手,道:
“慢来,隐身在林中还有什么人?敢情是那凤姑娘么?”
“正是小女!”邬子云一句答完,转过头去,扬声招呼道:
“凤儿……你不用顾虑……什么,走出来吧!……”
入耳传来一声漫应,幽幽地,打林中又走出一个人来……这是邬金凤!
她,邬金凤,无精打采地,一步一步踱出林来……
螓首垂得低了又低,几乎就要垂到她的胸前,间或也微微抬起脸来,两道呆滞的眼神,既不看展宁,也不望那了行老和尚,两只眼睛,红得宛如一对熟透了的桃子,步履艰难似的,一步一步踱向地狱谷主身边……
多时不见这妞儿,确乎,她已是花容失色,显的极为憔悴的了,在她的行色之间,哪里还有半分斗双僧,闯少林的如云豪气?乔装冯锦吾的洒脱气度,更是消失无踪,而不复存在了!
为错综复杂的情感所困扰的她,今与昔比,判若两个人!
眼看恁般景物,任展宁天生一付铁石心肠,也觉鼻生酸楚,心头简直不是滋味!
邬金凤几步踱到地狱谷主身边,骇然拾起头来道:
“爹,我怎地不知道,您是什么时候服下‘亡魂鹤顶红’的?……”
邬子云一手扶搭在女儿肩头,斜睨展宁一眼,凄声笑谓邬金凤道:
“用不着……为我婉惜什么,也许,这样的结局……对于你……对于别人……俱要完美得多,我不怨天……也不尤人……这是我咎由自取,自蹈的……杀身之祸!……”
地狱谷主的话,似了而未了之际,地狱谷口,人声鼎沸,一窝蜂,有数十条身影冲出谷来,隐隐传来酒怪边跑边叫,狂吼的声音:
“不好!不好!邬子云用金蝉脱壳之计,远走高飞了!展宁,你小子站在江边又怎地?还不……咦?”
最后一声惊叫,想是他将站在江边的四个人看清楚了,步声杂沓的,一齐赶到展宁立身之处的江边来……
不一时,在地狱谷主的身前左右,围了有上数十之众,其中有逍遥先生,雪山三色童子,酒怪,贺芷青,少林寺的红衣上座,武当六道长,青城静真道长,另外还有一群,展宁辨别不出服饰来的武林健者,想必就是属于当前武林其他门派中的人了!
这一群人,赶到江边。眼看四个男女,面色凝重的站在当地,遂也喧嚣一止,无声无息地站在一边……
地狱谷主不为来人众多所动,他干咳一声,转脸望向展宁道:
“展宁,老夫最后……有一句言语,想请你证实……一下好不?”
展宁不知他有心要说什么,一蹙眉,将头点上一点。
见得这一点头,地狱谷主一露苦笑道:
“我听说……兰娘在……九顶山出了家,这话……当真么?”
“当然真的!”展宁冷峻的。
“这样……我邬子云死也瞑目了!……”
地狱俗主获得展宁的证实,状极欢愉的,在他愈变愈暗灰的尖削瘦脸上,过了一抹喜色,他,似乎在强打精神,缓缓地,向了行大师转过头来,苦笑道:
“我还有几句如骨头在喉的话,大和尚,能……容我尽情……倾吐么?”
流云和尚面色凝重的也自点一点头。
地狱谷主,原本一只左手扶搭在邬金凤的香肩上,一见老和尚点头已应允下来,精神似是陡然一震,两手在胸前一抱拳,面对站立在周遭的人,罗圈一揖道:
“木有根,水有源,我邹子云不欲多嘴……晓舌,只有三言五语……诸位同道便可对这一段公案,了如指掌了!……”
邬子云脸色一沉,手指地上的贺天龙的人头,道:
“他,贺天龙,空有一付道貌岸然……的仪表,垂涎我妻子——兰娘的姿色……在十五年前,他贺天龙来在我南海门下作客,乐不思蜀……一住就是三月有余,谁知道,……在这段时日之中,他尽情……蛊惑我妻子,而与兰娘勾搭……成奸……”
想是地狱谷主情绪太已激动,说话中,满布灰色的瘦脸上,也微微泛出了红色。
说到这里,他又自干咳两声,继续说道:
“我妻……兰娘,她是一个任性、骄傲、而主观意识……很重的人,她不自知,是她自已吞服了一粒糖衣毒药……藉着我处理不善的……几桩小事,与我闹翻脸,狼心撇下一个两岁未足的女儿……以及她怀着的三个多月的身孕,她,私奔了!
她私弃,我当时以为她,只不过是短时期的……负看行为!殊不知,她与贺天龙却长相厮守在一起,十五年流年似水……她一去,信息毫无……
贺天龙鸠占鹊巢,这也罢了,他欲盖弥彰……故意制造出许多新闻,揭我的疮疤,说是我邬子云……阴恶狡诈,行事……乖张,那兰娘也恬不知耻……不为我辩护,还在一旁帮腔……张扬!”
说到激愤处,他一伸如柴干爪,虚空抓了几抓,恨声又道:
“我也是人!人,皆有其自尊之心,一点一滴的刺激累积下来……形成了我,一股强烈的报仇……愿望,我困在南海……十五年,造成了一股错误的……变态心理,我恨,恨天下所有的人!当时只有一个想法。我要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来,来抚平我的怨气,使贺天龙,与兰娘看看……我邬子云可是一只绣花枕……头?……”
他咬一咬牙,又道:
“老天爷可是真不负我,我在青城山的……一座亘古无人足迹……的山洞里,获得了玄通子遗留……下来的‘地罗十一式’,恁藉这几招掌法……我打遍天下无敌手,造成无人能敌的态势……”
“当时,藉这地罗掌,我要杀那贺夭龙……真是易于反掌折枝,但是,我被胜利……冲昏了头,我要造成一股……万夫莫敌的洪流,不管……洪流冲激到哪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在武林之中,要形成一付南面称孤的局面,就是这个……英雄主义的想法害苦了……我,平日杀死了多少……不愿屈志的同道……也种下了今天无法邀人同情的……丧生之机!”
他摇摇头,叹息了一声又道:
“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邬子云……今日……本可逃得一死,一走……而了之,但是,我并没有……这样作,我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多行不义必自毙’,即使我能逃脱今日……之厄,可是…往后提心吊胆的日子……不好过!”
“再说,我一人作事一人当……我能够使我的女儿也……负咎一生,永远让……痛苦来噬蚀她……的心灵么?……”话象是说完了,但,他的激动心情并未稍敛,略略仰起脸来,又道:
“现在,贺天龙……先我而死,足见冥……之中,因果尚在,兰娘……悟道削发,足见她……满怀着悔意,矢志向佛前……求得解脱去了!现在,轮到……我了,诸位同……道若要……杀我雪恨……请吧……”
诚如他自己之所言,他当真是个英雄主义色彩浓厚的人,临死,他并没向人乞求伶悯,视死如归而了无怨忧!
听这邬子云一度谈,周遭原本情绪激动的人,像展宁,象酒怪,象那武当一派仅剩下来的六个道人,一个个神情凝重,反倒默默无言了!
了行大师,究竟是个年高有道的高僧,他双手一合什,道:
“阿弥陀佛,你邬施主还算是一个行事磊落的人!任你自认为罪大恶极,以死来赎前过,武林同道,还能要求个什么?老衲看你此刻仅是胸头的一口气支撑着未散,你何必不一散真气,魂登极乐呢?”
地狱谷主黯然一点头,倏然,他又象想到了什么,冲着老和尚,神含企盼的道:
“大师,我邬子云以死……赎罪,我的女儿……她是没有罪的,是不是?……”
老和尚皓首颔颔,决不犹豫地道:
“当然!理所当然!”邬金凤究竟还有父女之情,哀叫一声“爹”,哭倒在邬子云的脚前。
贺芷青神色木然,杏眼中,也渗出几滴晶莹的泪珠。
邬子云一手在邬金凤肩上拍了一拍,略略偏过脸来,迳向贺芷青招呼道:
“青儿……你过来……”
经这一喊,贺芷青似是慌了手脚,她的脚下,要动也没动,圆瞪着两只俏眼,惶然失措的,盯视在展宁脸上……
展宁一时也不知如何是好,还是逍遥先生不过意了,走近贺芷青轻声嘱咐道:
“孩子,该是你认姓归宗的时候了!你爹已是一个行将垂死的人,你要表现得热络些,让他死也瞑目吧!”
有这一言嘱咐,贺芷青禁不住珠泪夺眶,口里叫声爹,和身扑倒在邬子云身边……
二女哀声痛哭,哭声震耳,铁石人儿也伤心。
邬子云老泪纵横中,眉宇间,仍显露出一丝若有若无的欢慰之色,他,缓慢的蹲下身去,双手撑起二女的梨花玉面,仰起头,却朝展宁苦笑道:
“展宁,老夫谢谢你赐我一个……全尸,你可万不能心有……不甘,来折磨……我这一双女儿……的啊!……”
展宁也不愿做得太过火,凄然一笑道:
“这个你且放心,展某不是一个狼心狗肺的人!”
“好,好,哈哈……”地狱谷主连说两声好,本来要想引发一串长笑,奈何他力不从心,真气一散,就地撒手尘寰了。
二女哀极痛哭声中,了行大师口喧一声佛号,走上前来道:
“邬施主临死极为称心,两位女施主也节哀顺变吧,我等趁这人手众多,将他的骸骨埋在此地,不也了却一桩心事了么?……”
众人七手八脚,就此拢起一堆孤冢。一代枭雄,就此长眠地下!
江边诸事了了,一行数十之众,折回谷口的同时,地狱谷里,浓烟上冲云霄,火舌,在浓烟中上窜不已……
展宁转过头来,迳向酒怪问道:
“老哥哥,谷中的鬼卒,完全斩尽杀绝了么?”
酒怪嘻然于色,一指地狱谷口道:
“这一次,可真是逍遥老儿的计划周详!你看,就连谷口那三个用白骨嵌成的大字,也被我等扫除的荡然无存了呢?”
展宁念念不释黑白二无常,笑道:
“两个无常被谁下手宰了的?”
酒怪反手一指酒糟鼻头道:
“老叫化这次杀的最过瘾,两个无常也真是太不济事,一招‘十二天罡’下去,哈哈,他俩就魂断奈何天了!”
展宁微微一笑道:
“那条秘密甬道怎样处理了?确是不能容它继续存在着的呢!”
“那还用说吗?这一点,老叫化早就想到了的!……”
酒怪一句话尚未落音,白儿嘴快,一挺小胸脯,挤上前来道:
“穷叫化子,你一直在丑表功,那条秘密甬道,未必也是你将它堵死了的?”
酒怪舌头一伸,忙不迭地摇手道:
“啊?不是我!不是我!谁也知道那是你三色童子的功劳!老叫化纵有天大的胆,也不敢在三色童子面前,冒名邀功的呀?哈哈……”
此言一出,引起哄然一阵大笑之声……
地狱谷里,上审的烟火愈见猛烈,欢呼四起中,涌出一股人潮来……
展宁身边,口响起贺正青一声惊叫道:
“展哥哥,你看,后面是谁来了?”
“谁?”展宁惊奇不已,随同众人,俱皆转头打量过去——
果然,在江边的碎石坡道上,一条青色身影,其疾如风的滚滚而来……
那人,一身青布短褂裤,裤脚管高高扎起,背背着斗笠,尺长的早烟管,悬在腰间白布板带上,面颊清臞,须发已是花白了,只需一见这身穿着,他是九江钓叟李明了!
九江钓叟他极象是刚从水里爬起来,浑身湿沥沥水滴滴的,他双手抱着一个已然晕厥的人,那人满头白发,干瘦如柴,那不是逃走了的巫山婆婆么?
九江钓叟几步赶到人群之中,放下手中的巫山婆婆,哈哈大笑道:
“来迟了,来迟了,我没想到这老婆子,水中的造诣也了得!若非有人赶上前来助拳,不但我制不了她,我的一条老命,怕也要送在她手里呢!”
展宁心里一动,疾步迎上前来道:
“李老前辈,您说有人助拳,是谁?……”
九江钓叟不停抖落身上的水渍,欢声漫应道:
“那个人么?了不起!当真了不起!对付这巫山婆婆,至多也不过用了三招两式,乖乖,我李明痴长五十有奇,还没见过如此俐落的身手呢……”
众人听得入神,在齐口惊叫声中,酒怪已是大不耐烦了,从旁催促道:
“他是谁?你爽爽快快说出来不好?怎么,你的老毛病又发作了?……”
九江钓叟双眼一翻白,含笑叱道:
“你这穷叫化也真会冤枉人!你要我爽爽快快,我又能怎样够爽快呢?我除了知道他约莫四十多岁的年纪,一身书生打扮,其他的,我也说不出所以然来呀……”
这是谁?能够三招两式打发这巫山婆婆,这份功力了得?
逍遥先生别有心意的,上前问道:
“李兄说他最多四五十岁,你究竟看清楚没有?……”
九江钓叟摇头尚未答,逍遥先生已是哈哈大笑道:
“李兄,你走眼了!若是白某猜得不错,那书生,四个四十岁也不止呢!”
突如其来,九江钓叟,情不自禁的啊了一声。
酒怪也自恍然大悟过来,偏脸一笑道:
“敢情又是那个老鬼?……穷途书生?”
“正是!”白翔点头笑道:“那老鬼精通化装术,李兄所见,想必就是他了!……”
九江钓叟似又想到什么,面对逍遥先生,奇然一笑道:
“临行,他还特意梢个口信给你白翔,他说什么……尧龙山的陈年佳酿,味香酒醉,在五天之内,他要再上尧龙山去偷一缸……要你留心防守好了!……”
逍遥先生含笑恨声道:
“这老鬼怎地一再戏耍我,我这就赶回尧龙山,看看他究竟有什么了不起……”
话完,冲着周遭的人一个罗圈揖,转过身去就要走……
酒怪手快,一把扯住他的洁白儒衫,一瞪两只水泡眼,道:
“怎能说走就走?至低限度,你也要喝一杯,七大门派在邓都县,共同设下来的庆功宴再走,是不是?”
情不可却,逍遥先生只好又含笑站住脚来。
酒怪,两手朝天一撑,对蜂拥站在谷口的近千之众,高声发话道:
“地狱谷已除,妖气已清!七大门派联合在对江的邓都县设宴庆功,各位同道不远千里而来,务必要过江去叨扰一杯的呀!过江去!过江去!”
群众哗然一声欢呼,宛如雷动九天,响辙云霄。
欢呼声中,群众如同潮水,俱向渡船码头涌了过去……
酒怪咐咐既了,低头望一眼刻正躺在地上,被穷途书生制住穴道了的巫山婆婆,他,双眉一蹙,笑谓展宁道:
“我等也好走了!这家伙,要怎样打发她?……”
“依你老哥哥说呢?……”
酒怪,做了一个突睇的表情,挤眼一笑道:
“姑念这鬼婆子,百十年的修为得来不易,给她一个‘凭天断’吧!”
“怎样凭天断法?”
“生死由命,富贵在天!死与活,就看她的造化了……”
话末说完,酒怪他一掌电疾拍出,这一掌,不偏不倚,拍上巫山婆婆头顶的“百会”穴上。
波地一声响,巫山婆婆脑浆迸裂,血花四溅……
酒怪一脚飞起,对巫山婆婆的尸身,踢落在浪涛汹涌的大江之中,耸肩一哂道:
“这样的‘凭夭断’,许是太残酷了些,那鬼婆子若是运道好,遇上一个能够起死回生的仙人,她照样可以再活一百年……”
插浑打趣,又引起一连串哈哈大笑之声。
一行数十人,在欢笑声中,逆着滚滚东流的江水,走向渡船码头。
只有邬金凤与贺芷青,面色仍是凝重地,并肩走在最后。
来在渡船码头,已有几十条渡船,相继满载着武林豪客,络绎正摆过江去,大江北岸,只剩下一条逾龄了的大渡船,竖着一要长竹篙,停泊在那里,船梢头,坐着一个身披棉袄的老梢公,口吻一根草烟管,动也不动,口里直在冒白烟,眼看这一行男女走近船来,他,苍白而干瘦的面颊上,掠过一瞥喜色。
一见这老船夫,展宁兀自欢叫了一声,提身一起,纵身上得船去,面对面,站在老船夫的面前。
这一着,突如其来,老船夫骇然站起身来,一揉他的昏花老眼……
展宁也不欲继续恶作剧,哈哈一笑道:
“老人家,你不认识我么?”
老船夫闻言惊异不止,对展宁左看右看,最后仍是摇了摇头。
九江钓叟接着来到梢头,接过舵柄,朝老船夫一笑道:
“你休息休息吧!这趟过江,只好由我来献献丑了!”
老船夫哪知就里,伸手又待前来抢舵,展宁手快,一把拖住他走进舱里来,按住他坐下身子,这时,一待众人俱已上船坐好,在九江钓叟熟练的操舟技术施展之下,渡船掉过头来,直向大江中流驶去……
展宁幌一幌老船夫的瘦手,反手一指自己,大笑道:
“老人家,你当真不认识得我了么?你想想看……”
老船夫似是一无记亿,圆瞪着两只眼,呐呐地,没法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来……
展宁为帮助老船夫提起记亿,轻笑一声道:
“您不是一番好心,指引我说是地狱谷中有一条秘密甬道的么?……”
“哦……”老船夫这才陡然起起来了,“你就是冒雨闯进谷去的那位小哥?”
展宁笑道:
“老人家,难得您有那份好心。现在,地狱谷三个字没有了害人的恶鬼也没有了,您老,用不着担惊受怕,邓都城可以安居乐业了!”
说到这里,冲着老船夫含笑又道:
“如果说,破除地狱鬼谷,展某还有寸功可言的话,这份荣耀,应该属于您老人家。”
另一边,酒怪将这两块碧玉,一人一个分别授在邬金凤与贺芷青的手里。
二女由衷也没想到这是什么东西,接过手来,分别端详了一眼,随即红霞密布,情不自禁的,但各垂下头去……
展宁至此方始领悟过来,油然立生一股羞意,讪然笑一笑,也自没出声。
渡船,划过了急水中流,驰驰地,向邓都城码头靠泊过去……
码头上,人山人海,象是赶集会般地,那样热闹。
千百道眼神,焦点集中在展宁身上!
逍遥先生含笑站起身来,笑谓展宁道:
“邓都事完,我看你不如定居在尧龙山,与我作个伴好不?”
青城掌门人静真道长,急忙也站起身来道:
“少侠是我青城门下的祖师,他不住青城,于情于理似也不合适的!”
小红儿更是不甘后人,虎的跳起脚来道:
“你们那些残山剩景,哪有我们雪山风光奇伟,我爷爷临行吩咐下来,务必要小祖师住上雪山去的……”
红儿一跳,船身却幌了几幌。展宁一摆手,制止住还待说话的红儿,一起眼,却朝各大门派的掌门人,讪然一笑道:
“多蒙诸位先辈爱护我,展某一俟有暇,必然要一一登山去拜望!”望一眼舱中的二女,继续又笑道:“不过,展某祖籍鄂北襄阳,也该回去看看了!再说,安顿家小,也是该不容缓的事呢!”
贺芷青少不解事,闻言,茫然抬起头来道:
“家小?你要安顿什么家小?凤姐蛆,什么叫做家小呀?”
邬金凤本是悲肠寸结,满面愁容,经这一问,也自忍俊不禁,噗哧笑出声来。
这一笑,宛如一根导火线,响起了哄然一阵大笑之声。
贺芷青茫然有所不解,她,东张西望一阵,傻了!……
—全书完—
潇湘书院图档,fsyzhOCR,潇湘书院独家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