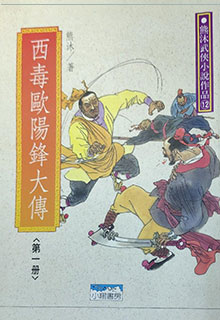毛丫头说:“我住在你方家。”
庄重惊奇地眨一下眼,但没说话。
毛丫头说道:“那一天我见到了,先是一个大汉来埋东西,他那样子,我也看不出是谁。”
庄重说道:“方顿的弟子有八个,再就是护院的壮汉、门人,在方府有千数号人。”
毛丫头说道:“我知道埋东西的地方,但我不知道他埋的是什么。”
庄重说道:“如果你知道,我们去找找看,说不定是埋的秘籍,因为在那几天,方顿的祖传秘籍没了,不知被谁拿走了。”
毛丫头再问道:“后来你来了,与你在一起的是一个男人,你们做的事儿,我都看到了。”
庄重忽地脸红了,她轻声说道:“你都看到了,那就不必说了。”
毛丫头忽地大声道:“怎么不必说?我看到你拿一支匕首,直刺入那人胸前,他就死了。你跑回去,对不对?”
桑木头不料会有这许多说法,只是直直地盯着庄重。看来方府的秘密不少,就只是这个庄重身上,就有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毛丫头再问道:“那个死去的男人是谁?”
庄重叹一口气,说道:“他是三师兄方水。”
毛丫头看着她,说道:“你为什么杀他?”
庄重笑了笑,说道:“他想离开我,我便杀了他。”
原因很简单,不知是不是真的。
毛丫头说道:“你挑了方老爷的脚筋?”
庄重说道:“不错。”
再问什么?
桑木头忽地说道:“为什么?你为什么这么做?”
庄重说道:“他只是一个盟主,从来也不是一个男人,只想着霸业霸业,怎么不想想一个十几岁的女人要什么?他忘了我,我必然也会忘了他。你说这是不是很公平?”
原来是因为这个,才有方顿的死亡。
庄重说道:“我喜欢男人,三师兄死了,我再想弄一个男人,我不愿意离开武林盟主的家,我愿意做夫人,我就在他的弟子里……”
“够了!”
桑木头大吼道:“你再胡说,我杀了你!”
庄重说道:“我能死在你手,便是快乐。你真能杀我,杀一个手无寸铁的女人么?”
桑木头叫道:“你杀了方老儿,要不是你,方老儿怎么会死?”
庄重忽地笑道:“他早就想死了,只是死在火中水里,或是被毒,或是被杀,总是一样的。”
毛丫头说道:“他死了,你要做什么?”
庄重看着她,忽地失笑:“我要替他报仇,你信不信?我告诉你,是那个郭免杀死他的,我要替方顿报仇,去那个赏善罚恶大会,替方顿报仇。”
桑木头忽地叫道:“那可了不得了,你要报仇,要杀那个郭免,可郭免会当上武林盟主,你怎么杀得了他?”
庄重说道:“匹夫怨气,可以冲天,你怎么知道我杀不了郭免?”忽地,庄重说道:“谢谢你的酒,我要走了。”
轿子抬走了,在路中间,仍坐着毛丫头与那个桑木头。
桑木头问道:“丫头,你说她与那个郭免会在大会上争雄么?”
毛丫头不语,她在喝酒,她还有许多事不明白,但她再也不想问庄重。
庄重的轿子走得很急,走得很快,看看到了一座院子,慢慢放下了。
庄重走出来,院门很沉重,在她的身后吱扭声声,关上了。
她走进了屋子。
这是一间很华美的屋子,地上铺有白毛皮,羊毛如浪翻,她走过来,把鞋扔出去,一只纤瘦的脚便踏上那羊毛。再踏上另一只脚,衣服就也扔掉,扔在羊毛上。再扔,整个人都无遮无束。
有男人沉声道:“像你这样儿,方老头儿能让你满意吗?”
她斜了一眼,显然并不惊奇那人的存在,娇声道:“他满意不满意,我不知道。可我满意不满意,你也不知道。”
那人哈哈大笑,说道:“方老儿要是真死了,你就满意了。”
庄重笑笑:“你以为他没死?”
那人眼如鹰隼:“方老儿不会自焚,他如果能自己把自己烧死,他就不是武林盟主了。我知道他。”
男人盯着女人看,看那些浑圆处。他也慢慢脱下长衣。露出他的身躯来。
他是一个男人,是一个成熟的男人,成熟而不老。
最好的当然是成熟,最不妙的当然是衰老。
男人说:“我不信他会死,你告诉我,他死没死?”
女人不说,只是夸张地抚摸着她自己,她陶醉于她自己的美妙胴体。她轻声说:“他不死,我怎么会这么自由?”
男人笑了:“算了,他就是不死,也只是一个废物,有什么关系?”
女人轻蔑地一笑:“我看你好紧张,看你那神气,像是看到了一只恶虎,哪像是看到一个废人?”
男人说道:“不是废人,他不是废人。你要拿他当废人,你会死在他手的。”
男人站立着,毫无一丝肉欲,他回顾一段往事,对他自己和对于他人都很陌生的往事——
那是在他十岁的时候,他是一个富贵人家的少爷,做少爷也没什么不好,他很快乐。但后来他就不再快乐了,当他在街上看到方顿走过时,人群前呼后拥的,便问爹:“他是谁?”爹说:“他是天下最有本事的人。”他问:“他有什么本事?”爹告诉他,天下武林的人都听他的,就是当今皇上也没他自在。他向往做那个人,听说方顿收徒弟,且把那两个徒弟当儿子待。他想了好久,跟着爹娘,他只能有钱花,不会像方顿那样一呼百诺,全天下的人都对你很敬畏。他决心去跟方顿学本事。
但这要花一点儿心思,他虽说才十岁,但也知道,方顿收下他,他才能达到那个愿望。他先是在家里找了一套破衣服,那是一个小厮的,他用新衣服与那个小厮换的,然后再弄花了脸,去街上守着。他知道方顿每天走的路,他一定会在那时走过来的。
他看到方顿了,那时他找的五六个乞丐儿正在打他。几个乞丐儿拿了他的钱,打得他鼻血直流。
他们喊:“来了,来了!”便一哄而散。
方顿看着他,很怜惜地蹲下来,对他说:“你为什么挨打?”
他睁大眼说:“我总挨打。”
他能流出泪来,泪水很委屈,一想到平生他头一次被人打,就真的委屈极了,泪水哗哗流。
果然方顿很可怜他,问他说:“你爹娘在哪里?”
他不能说爹正在钱庄里算帐,娘在花厅与几位婶娘话茶,他说谎道:“我爹死了,我娘也不在了,她在路上被人抢走。娘啊,娘啊!”
他号啕大哭。
方顿看他可怜,便说道:“你跟着我去,住在我家,跟着我,好不好?”
如果是平常的孩子,他一定会说好,也会喜出望外,但他本来就不平常,十岁时已经知道了欲擒故纵,他说道:“我去你家,我不能干什么的,我长大了能帮你做事,你要我做什么,我便做什么。”
方顿笑了,说道:“好啊,好孩子,你回去,一定高兴,你有两个哥哥呢。”
方顿当时说的是方栋与方为,他们都是十岁的孩子,但早被方顿收养了,正在家里习武。
他到了方府,看到了门上的匾额“武林第一家”,他的心扑扑跳,心道:“我到了方家,不知道爹娘是不是会找我,如果他们找我,也找不到。爹会急得叫钱庄的伙计到处去找,会在街上招招贴,会写上“失儿一名,年仅十岁,有送来者赏银十两”。依爹那等吝性,肯定不会写上二十两的。娘会哭,但几个婶娘会幸灾乐祸,她们会想着再有机会做爹的大老婆了。
他在方家呆了几天,学了几天的武功,也没什么稀奇的,只是学一些扎马步一般的功夫。
忽地一天,方顿叫他来了。
两人走啊走的,走出了方府,方顿领他到了一条胡同,说道:“你知道不知道我要带你去哪里?”
他说不知道。
方顿笑了,说道:“你吃馒头为什么扔皮儿?”
他吃惊了,说不出。
方顿再问道:“你为什么嫌衣服脏,自己还不洗?”
他也说不出。
方顿再说道:“师母给你几文钱,你都买了糖人儿了?”
他点头,这有什么不对?
方顿看着他,说道:“你只有十岁,我信。但你决不是没有家的孩子,你说,你家在哪里?”
他对方顿大声道:“我家在哪里不关你的事儿,你要收我做徒弟,我就是你的徒弟,我也会像他两人一样叫你爹,你老了,我会管你。你要不要我?”
方顿摇头,虽说他自己说得热泪盈眶,方顿可不听,他说道:“你是富人家的孩子,你知道,我只要那些没人要的孩子,我要他们做我的徒弟。”
他大声道:“我叫你爹不行吗?我叫你爹,我再也不叫我爹是爹了,我再也不回家了,行不行?”
方顿看着他,脸上带着笑,说道:“不行。”
他哭了,跪下了,给方顿跪下了,他哭着说:“我吃馒头再也不扔皮儿了,你让我回去好不好?就是再不给我零钱也行,我不要钱。”
方顿摇头,说道:“你回家去吧,你得回家去,你要不回家,我也会很快找到你家的。”
方顿走了,他摇头走了,他没看到方顿的脸,不知道方顿此时也有些伤感。如果他看到了方顿那样的大英雄也流眼泪,或许他一生不会痛恨方顿,不会对方顿有那么深的仇怨。
他回到了家,没有对爹娘讲他去了哪里,十天后,他叫来了娘,告诉她,如果不把他送到神针郜小娘那里,他就走了,再也不回来了。当时娘说:“你疯了,你疯了!”
他说:“娘,我没疯,我告诉你,那几个婶娘对你没好心。我要死了,她们一定会害死你。我去学本事,你就有指靠了。”
那时娘忽地满面是泪,答应了他。他终于到了神针郜小娘的门下学艺……
这是一个很长但也很伤心的故事。
庄重看着他,他满面是泪,看着庄重,说道:“方顿是一个很出色的人,但他没收我做他的徒儿。这是他一生最大的失策,我要告诉你的,正是这个秘密。
庄重说道:“他不知道,如果知道那个十岁的孩子就是你,他会后悔的。”
男人忽地正色,说道:“你说,他在哪里?”
庄重的双乳掐在他的手里,他用手指把两个乳头捏到一起,庄重的脸变白了,再变红了,她忍着苦痛,轻声娇柔地说:“他死了,我不是他,我只是与他住在一起。”
男人笑了,放开了她,不看她的眼泪,她的眼泪让他很满足,很刺激,他笑说:“方老儿死了,我要取代他,我是天下第一人了,我要他死后也在地狱里看看我,看看我是谁。”
他对着庄重说道:“你是他的人,凡是他的东西,我都要占有,你是他的,对不对?”
庄重娇声而笑:“我不一定是他的,他是老人。如果你会说,你只能说,他是我的。你呢,你是我的,还是我是你的?”
他笑了,眼里满是野性:“你说,你是我的,还是我是你的?”庄重柔情满怀地凑近他,再凑近他。
男人忽地呻吟一声,说道:“我告诉你我的过去,你是不是很笑话我?”
庄重笑一笑,说道:“要不要我告诉你我是怎么嫁给方顿的?”他忽地笑了,说道:“那一定很有意思。”
她说了一个故事——
她是在街上看到方顿的。
方顿对着她,笑了一笑。
那一笑决定了她的一生,她十几岁就嫁了一个近六十的的老人。
当时她很快乐,因为方顿的气质高雅,那样子不像是老人,她喜欢他。当夜里她看到他的身体时,她颤抖了,他有一个很健壮的身体。但后来……后来,他们不那么亲近了,因为他总是在练功,在练一种方家几代人也没练成的功夫。她等着他,夜里等人的心情是焦急的,她盼着脚步声。她等着那脚步声再响起来。可没有,有时一直到天亮,他也不来她的房里一次。她实在累了,便睡,到天亮时醒来,看看房里,仍是只有她自己。
她悄声道:“有时我咬自己的手臂,看我是不是在梦里?我才知道,他是像买一件东西一般,把我买到了家,再也不必关照我了,像那房间里的一切物什一样,我也该是静无声气的。你说,男人是不是都是这样?”
他笑了,说道:“不这样,我就不这样。”
庄重再笑,说道:“你骗我,你家里有许多美人,她们不光是你的,还是来侍候你家里人的。”
他笑得含蓄:“你知道我家许多的事儿?”
她叹一口气:“方顿说的,你是他时常说起的十几个人之一。”
他笑了,昂头大笑。方顿也时常说起他,方顿时常说起他。在方顿的眼里,他是一号人物,这让他很兴奋。
庄重说道:“你有女人,何必再看着我?”
他笑了:“如果我是武林盟主,我要的女人必多,你也是一个,而且是最不寻常的一个。”
他来摸她,欲望随着语言升华,更炽热。但她推开了他,推开他是很不容易的,但她做到了。
他说:“你不喜欢我?”
庄重媚笑:“我喜欢,但我不喜欢做你的美人中的一个,而且是很快就被忘记的一个。”
他再复冷笑:“你可以做一点儿事儿,让我忘不了你,让我一出门就想起你,一进家门也想起你,直到最后,我一想起你来便头疼欲裂,睡不着觉。那时,你便不须再嫉妒别的女人了。”
灯熄了,庄重滚在羊毛里,那男人像一条鱼,扑在羊毛上。他扑得太厉害了,女人被惹得发出一声尖叫。
再也没什么声息了,院里仍是那么阴森,那么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