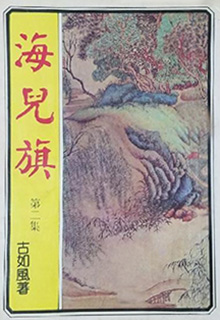鸡啼三遍,一抹淡淡的曙光,从石景山岭透射下来。
天,已经破晓了。
天寿宫前院正厅中,那盏八角琉璃灯仍然高悬未灭,灯光照映下,现出几张神情凝重的脸庞。
老魔曹克武亲率高手进窃北宫,其中现有绝世凶人“天山二臾”随行……这消息像一块看不见的大石,沉重的压迫在每一个人心上,连一向以机智沉着著称的紫燕,也惶然失去了主意。
自从欧阳天寿遇害,剑魔甘道明相继去世,她身为长女,无形中继承了北宫主人的重任,然而,顶了天她才不过二十二岁的少女,面对压境强敌,难免不忧心冲忡。
水来土掩,兵来将挡。摆在眼前的课题,已经不是“战”与“不战”?而是如何在强敌环攻之下,使天寿宫屹立元恙?这儿的一草一木,却是欧阳天寿毕生心血所置,假如被人毁损,教她何以对数十年养育之恩?何以维护天寿宫铿锵广被的英名声誉?
紫燕木然凝视着那份炸药埋置详图,思潮紊乱,久久没有出声,那图中一点一线,都会令她愧作得无地自容,若非桑琼远来告警,一旦炸药被引发,整个的天寿宫化为韭粉,大家还不知祸从何来呢?
欧阳王儿见她愁闷不语,不禁轻叹一声,道:“大姐,事到如今,也不必顾忌太多了,唯一的办法,先按图将炸药枢纽加以破坏,除去内顾之忧,然后聚全宫高手,跟曹老魔决一死战,咱们宁可毁宫战死,也不能眼睁睁束手待毙。”
紫燕摇摇头,道:“这是孤注一掷的办法,纵然拼得过强敌,天寿宫必亦元气大伤,何况制胜的机会又是那么渺茫……”
黄燕接口道:“酒痴李老前辈曾说过‘寓攻为守’的话,咱们何不先下手为强,倾全宫之力,抢攻戒坛寺,打它一个措手不及,无论胜败,至少不让魔崽子们毁我天寿宫。”
紫燕又摇头道:“徒逞意气,于事何补?咱们如果败了,天寿宫一样不保,这跟玉妹妹的办法有什么分别。”
黄燕道:依大姊这么说;“咱们已经毫无制胜的希望,空自坐着发愁,也不是办法呀?”
紫燕扬目道;“我没有说过毫无制胜希望,但咱们不能不承认敌势强过咱们,硬拼之下,吃亏的多半是咱们天寿宫。”
三燕不期同声问道:‘那大姊认为应该怎么办?”
紫燕没有回答,却反问墨燕道:“以你目击情形,那天山二臾的功力,与酒痴李前辈孰强孰弱?”
墨燕沉吟7一下,答道:“这一点很难遽下断语,不过,从侧面观察,李前辈似要略胜一筹。”
紫燕道:“你是说天山二臾功力,与李前辈约在伯仲之间?”
墨燕摇头道:“不!小妹是指以一对一,李老前辈或不致落败,若二臾联手,李老前辈恐怕难支持到五百招以上。”
紫燕骇然变色,哺哺道:“这么说,二臾功力仅不在曹克武之下,今夜这场血战,只怕凶多吉少……”
正说着,忽见飞天鼠李明疾步而人,兴冲冲道:“桑庄主回来了!”
四燕同感精神一振,忙不迭推椅而起……
欧阳玉儿情不自禁道:“谢天谢地,他总算及时赶回来了,快请——”
话犹未毕,桑琼与何冲在李明,纪浪簇拥下走了进来,两人身上都是一身尘土。
四燕迎着让坐,暗暗都松了一口气,好像桑琼一到,天大艰难都能迎刃而解似的。
桑琼仆仆风尘未歇,也无暇寒暄,刚坐卜,便问道:“魔宫有无行动迹象和消息吗?”
欧阳工儿忙将连日发生事故经过,详细复述一遍。
桑琼听说曹克武亲到,并有大山二臾随行,也不期为之震惊,默然片刻,始道;“如此说来,难免一场恶战,不知大家可有应敌的良策?”
欧阳玉儿道:“咱们正苦思不得计谋,看来除了准备背水一战之外,别无他法可行了。
桑哥哥,你有什么主意呢?”
桑琼沉吟道:“仇人相遇,一场血战是免不了的,但咱们有两点顾虑,不能不先作妥善安排。”
欧阳玉儿忙问道:“哪两点顾虑?”
桑琼道:“第一,敌强我弱,尤其是天山二臾功力深湛,不可忽视。第二,天寿宫是欧阳老伯毕生心血经营,咱们不能容魔崽子们有所毁损,宫中男女老幼的安全,也必须设法确保,否则,若遭受毁坏伤亡,虽胜亦败了。”
紫燕脱口道:“公子真是一针见血之论,方才咱们姊妹为难的,正是这两点,但却想不到解决的方法。”
桑琼微笑道:“其实,也并不困难,关于第一点,也用八个字作为解决之法:‘只宜智取,不可力敌’。关于第二点,也用八个字解决:‘争取主动,以攻为守’。”
黄燕欣然道:“妙极了,这八字真言,竟跟李老前辈赠语不谋而合…·”
桑琼诧道:“哪一位李老前辈?”
黄燕道:“就是风尘三奇中的酒痴李道元。” 于是,又将李道元戏弄人妖和火灵官陈童,诱使二臾现身等经过,—一告诉了桑琼。
桑琼听了,大喜道:“这次我与何兄在沧州中计,也多亏三奇中的盲丐青竹翁及时援手,才化险为夷,咱们既有高人暗助,大可放胆而为,不必再顾忌天山二臾了。”
紫燕慎重地道:“话虽不错,但风尘三奇神龙见首不见尾,咱们也别存依赖之心,必须自己筹思一条妥善应敌之策才行。”
桑琼微笑道:“这是当然的事,应敌之策,我已略有腹案,咱们现在先确定几项原则,便可依计行事。”
四燕齐道:“愿闻妙计?”
桑琼压低声音,将心中安排轻轻向众人解说一遍,最后道:“这是将计就计的方法,同时也可避免在天寿宫内与敌人遭遇,唯一困难之处,是纪兄已无法再往戒坛寺,必须另外设法诱使曹老魔人伏,假如果能一举击败老魔主力,趁势剿灭第三魔宫,曹克武在北五省已无法立足这地,那时,大伙儿再星夜南下,会师巢湖,魔党复灭就为期不远了。”
纪浪奋然道:“为助此计成功,纪某愿冒死再往戒坛寺诱敌。”
桑琼却摇头道:“你一次涉险,获得地形秘图已属幸运,绝不可再投虎口,那样不仅大危险,还可能引起曹老魔的警觉,破坏了全盘大计。”
何冲含笑接口道:“现存有两条鱼饵,庄主怎么反而忘了?”
桑琼讶问道:“何兄指的是——”
何冲附耳低声数语,桑琼听罢,抚掌笑道:“好计!咱们就分派人手,加紧进行吧厂大伙儿经过一番密议,俱各欣喜不已,立即分头依计而行口
口
口
一日易尽,日出、日落,转眼间,夜色又笼罩了大地。
这一天,将是天寿宫面对强敌的存亡关头,也是北宫创建以来最危险严重的一天,存亡荣辱,都将在今夜一战而决。
但是,奇怪得很,时间已经如此迫近,天寿宫却看不出有什么非常的举动。
宫中旌旗招展,宁静如常,平时供人们出人的几道门户,依然敞开未闻,堡楼等处巡逻警戒的的弟子,反而减少了人数。
看这情形,莫非天寿宫已经忘记了今夜寅正二刻即将发生的存亡决战?
不!当然不。
日暮时分,天色刚暗,天寿宫正门忽然启开,由宫中鱼贯驰出十骑快马。
第一匹马上,坐着劲装佩剑的桑琼,随后紧跟着的,是何冲、飞天鼠李明、屠龙手纪浪和另外六名天寿宫精选高手。
十人十骑出了宫门,略一踯躅,便放辔如飞向西方而去,接着,宫门又轻轻掩闭了。
他们去向何处?没有人谈起,为什么竟在天寿宫危机近迫的时候离宫而去?更属令人费解。
夜色渐浓,时间已将近午夜了时了。
蓦地,一条黑影,迅速掠过天寿宫练功密室外那座院墙,一路掩掩遮遮,直向密室而来。
来人约莫四旬左右,一身黑色劲装,肩后斜插着长剑,浓眉,短髯,一双眼神炯炯发出惧人的光芒。
黑衣人行动十分谨慎,步步为营的逼近练功密室,但在距离室门丈余处,仍然惊动了两名把守室门的弟子。
“什么人?报名——”
两名警卫弟子同声低喝,双双按剑旋身,长剑才抽一半,却被那黑衣人闪电般欺身而上,双掌齐扬;打翻在地上。
黑衣人武功显然不弱,一击得手,毫未迟疑,猛长身形,抢进了练功密室。
密室中燃着一盏昏暗的烛灯,靠壁角有一双深嵌在墙内的钢环,钢环中贯穿一条粗钱链,铁链两端,各系着一个人。
这两个人一名双尾蝎杜伦,一名火眼罗滔,原是眼于寿臣和纪浪同时奉命潜入天寿宫充任蓝衫特卫队的魔党高手,后来纪浪率众反正,其中四人不肯服从,两人被当场格毙,杜伦和罗滔却同遭生擒,桑琼不忍加害,才一直将他们禁固在练功密室中。
杜罗二人身被铁锁,穴道也都受制,但却清清楚楚听见室外呼喝之声,是故黑衣人甫人室门,两人都同感一惊。
火眼罗滔凝目望去,不禁为之惊诧万分,沉声道:“来的可是朱二哥么?”
黑衣人低声应道:“正是愚兄,罗兄弟噤声,千万不可惊动!”声落人至,已到室壁之前。
火眼罗滔济问道:“朱二哥,你来干什么?”
黑衣人道:“愚兄特来相救你们,一同逃出天寿宫……”
火眼罗滔惊道:“你……不是已经随纪浪叛宫了么?”
黑衣人道:“内情一言难尽,无法细说,愚兄好不容易冒死而来,咱们还是先脱身出宫,再说不迟。”
语声一落,抽出长剑,立将铁链劈断。
杜罗二人腕间铁链虽断,却依在墙角,没有立起。
黑衣人低问道;“你们受了伤么?”
火眼罗滔摇头道:“伤却未伤,只是穴道被他们制住,无法行动。”
黑衣人轻“哦”一声,举掌向二人背心各拍一掌,替他们解开闭穴,低声道:“快些活动一下筋骨,我去替你们弄件兵刃来。”
罗滔和杜伦双双跃起,舒展了一下四肢,发觉血气并无阻碍,不禁大感欣喜。
黑衣人去而复返,手里提着两柄长剑,分处给社罗二人,同是沉声说道:“你们跟着我来,非万不得已时,最好不要出手,如今天寿宫正在混乱,咱们趁乱脱身,不必硬闯,一旦惊动了四燕,反倒不易走脱了。”
杜罗二人连忙点头道:“咱们理会得,朱二哥请带路吧!
黑衣人当先转身奔出练功密室,一路领着杜罗二人掩掩闪闪,由花园阴暗处穿出围墙,途中果见天寿宫弟子三五成群,匆匆往来于前后宫之间,不过,谁也没有留意到练功室这一边发生了变故。
三人趁夜色掩护,意外顺利地抵达东北方一处侧门,黑衣人忽然挥手示意,矮身匿伏在一处草丛内。
窃视情势,原来侧身已开,门前共有四名弟子在黑暗中往来巡行不上。
姓朱的黑衣人轻对杜罗二人道:“出得堡门,便可脱身了,但他们共有四人把守,若不能一击全毙,被他声张起来就糟了,你们躲在这儿别动。待愚兄去诓他一诓。”
火眼罗滔低道:“朱二哥务必小心,如果不能得手,就招呼咱们联手硬闯。”
姓朱的黑衣人点点头,一问长剑,长身而起。
四名凝子听得声响,一齐按剑喝问道:“什么人?”
黑衣人应声道:“是我,特卫队的朱光权。”说着,大步走了过去。
四名守卫弟子看清朱光权的面貌之后,同时松了一口气,其中一个拱手又问道:“朱兄不在宫内值勤,深夜至此,意欲何往?”
朱光权含笑道:“姑娘们吩咐,今夜情势不比平时,特命在下来知会各处一声,要严防魔党潜人,并须提防宫内有人私自出去。”
口里说着,已行至距离四名弟子不足三尺处。
四名弟子同应道:“不劳叮嘱,咱们自会小心。”
朱光权又道:“时间快到了,这附近还平静吗?”
四名弟子答道:“平静如常,并无事故。”
朱光权点点头,道:“那就再好不过了,诸位多辛苦,在下还须去他处传话,咱们回头再见。”
四名弟子同时施礼道:“朱兄好走,回头再见…、·。”
朱光权佯作转身,忽然用手一指门侧,轻呼道:“咦!那是什么东西?”
四名弟子俱各一惊,不约而同扭头张望,刚转身,朱光权疾探右臂,“呛”然拔出长剑。
剑光一闪,横掠而过,四名弟子连哼都没有来得及,卟通倒了两对。
朱光权沉声道:“快走!
杜伦和罗消应声纵起,直扑向门前。
朱光权低喝道:“不必开门,越墙过去,快!
三人先后腾身掠出宫墙,展开身法,轻烟似的脱出了天寿宫一口气疾奔将近十里,不闻追截声息,才停下脚步略作喘息,火眼罗滔激动地握着朱光权的手臂,气咻咻道;“朱二哥,多蒙涉险解救,活命之恩,终生感戴,小弟亲眷都在总宫,他日能得重晤,皆由二哥所赐……,”
朱光权轻叹一声,道:“愚兄何尝不是一样,你我都有亲人留在总宫,又受宫主厚恩,怎甘作那叛离负义之事,无奈被纪浪那厮仗势胁迫,不得不佯为顺从罢了。”
双尾蝎杜伦也含笑道;“咱们素知朱兄忠议,绝不是背叛之人,这次多蒙解救危难,回返分宫,定将实情呈报分宫主,代朱兄报功请奖。”
朱光权道:“纪浪那厮挟众自恃,降顺天寿宫以后,已被四燕委派为天寿宫总管,他卖身投靠固然名利双收,那些被胁迫的弟兄谁不是敢怒而不敢言,依我观察;未必全是真心降敌,只等宫主圣驾一到,定然还有人阵前反正。
火眼罗滔叹道:“宫主圣驾何时才能到呢?”
朱光权道:“二位还不知道?宫主圣驾昨夜已进驻戒坛寺,亲率本宫高手,准备一举毁了天寿宫,据说,定期就在今夜发动,可恨这消息却被纪浪匹夫出卖给四燕了……”
杜罗二人齐吃一惊,忙问道:“此事当真?”
朱光权正色道:“怎么不真,昨夜宫主密令传于寿臣前往戒坛寺谒驾,被纪浪顶替前往,直到今晨返回天寿宫,据他向四燕呈报,宫主已定今夜寅时二刻发动,那厮并且把咱们从前埋藏天寿宫的炸药布置图骗到手,一并出卖给四燕,如今天寿宫已作紧急准备,炸药枢纽已被毁坏,同时布置了狡计,要诱害宫主,愚兄忍无可忍,才决心冒险救你们一同脱身,咱们无论如何得设法赶快把消息飞报宫主……”
杜罗二人骇然失色,齐道:“事情既有变故,又如此紧急,朱二哥就应该尽早呈报宫主才对呀!”
朱光权叹声道;“我虽然有此心,无奈已蒙上不白之冤,假如宫主不肯相信,岂不—
—”
火眼罗滔急道;“有小弟和杜兄亲见为证,朱二哥忠贞绝无关碍,现在方过子夜,咱们立即赶往戒坛寺报讯还来得及。”
双尾蝎杜伦也道:“朱兄侦得如此重要消息呈报,宫主非仅不会记恨前事,一定还要记朱兄一项大功哩!”
朱光权苦笑道:“我但求重获谅宥,何敢奢望功劳,只愿能保全此身再晤妻儿,死亦瞑目。”
火眼罗滔急忙慰藉道;“宫主赏罚严明,当初朱兄是格于情势,乃事非得已,如今已表白清楚了,再说若无当初佯作顺从,又怎能获得这件重要的消息,咱们别再耽误了,快走吧广
两人极力安慰了朱光权一番,重又急急动身,绕道奔往戒坛寺。
抵达寺门,时间已近丑刻,曹克武正坐候屠龙手纪浪回报不见消息,方命火灵官陈童出寺探望,恰与朱光权等在寺前相遇。
朱光权和杜罗二人慌忙拜见,将前情大略复述了一遍,火灵官登时吓出一身冷汗,愣了好一阵,才切齿骂道:“好一个匹夫,果然被夏护法料中了了’狠狠一跺脚,领着三人返回寺内,不敢隐瞒,一五一十都呈报了曹克武。
曹克武听了,脸色连变,顾不得责骂陈童,急令传三人进见。
朱光权等战战兢兢走进方丈室,远远就跪了下去。
曹克武铁青着脸,凝目逼视着朱光权,约有盏茶之久,才颔说道:“你能不忘根本,冒死送讯,姑念降敌迫于形势,本座准你将功抵罪,杜伦。罗滔临危不屈,志堪嘉勉,都站起来回话吧广
朱光权等再拜而起,垂手侧立,又把经过复述一次。
曹克武强自按耐住怒火,凝容问道:“北宫四燕获得纪浪匹夫归报之后,究已如何布署迎敌?你且详细说一说。”
朱光权俯首道;“就属下所知,四燕已首先毁去炸药枢纽,将宫中妇弱全都移往天寿宫后山一处隐密的树林中,准备倾全力与宫主对抗……”
曹克武冷笑道:“难道他们还以为除去炸药,便能跟本座一决胜负不成?”
朱光权道:“四燕亦自知不是宫主之敌,但她们冀企风尘三奇中的酒痴李道元和盲丐青竹翁曾出面相助,同时,她们撤去老弱妇孺,免除后顾之忧,准备在不敌之时,暂时退出天寿宫,却利用桑琼等进行“围魏救赵’之计。”
曹克武讶道;“何谓‘围魏救赵’?”朱光权答道:“今日入夜时分,桑琼已带领纪浪等人离开天寿宫,连夜直扑五台第三分宫,以图牵制宫主,解天寿宫之围。”
火灵官陈童大惊,不觉岔口问道:“他们带了多少人去?”去了多久?”
朱光权道:“人夜动身,距今约已三四个时辰,连桑琼共有十骑,其中更有分宫护法飞天鼠李明在内……”
火灵官陈童倒吸一口凉气恨恨骂道:“他妈的,这批贼娘养的东西,一个个全都反了,总有一天,老子剥他们的皮…”
曹克武脸色一沉,冷哼道;“你有这份威风和能耐,平时都瞎了聋了不成?”
火灵官陈童急忙躬身道:“求师父赐准,徒儿愿立率本部属下,回援分宫。”
曹克武阴阴一笑,道:“等你赶到,第三分宫早成瓦砾了。”
他语锋微微一顿,冷电般目光一扫全室,又道:“好一个‘围魏救赵’的妙计,可惜他想错了,本宫人手全在此地,就算把第三分官那几栋房屋送给他,又算得了什么?何况他轻离天寿宫,岂不等于把四燕和欧阳老儿那点基业双手奉献给老夫了!”
说到这里,忍不住得意地大笑起来。
火灵官陈童等人虽然内心焦急,却不得不附合而笑,方丈室中,顿时扬起一片高低不一的笑声。
人妖夏玉珍最会把握机会献殷勤,忙诏笑道:“宫主圣明果决,远非常人能及,可笑桑琼那个小辈自作聪明,却没有想到天寿宫覆灭之后,他在五台第三分宫又能多活几天……”
火灵官陈童也赔笑道:“那小子聪明个屁,我看他,简直蠢得可怜…·”
谁知曹克武突然笑脸一变,竟冷哼道:“你们也比他强不了多少!
群邪一愣,不由自主都收敛了笑容,一个个傻眼相对,谁也猜不透老魔此言何意?
曹克武锐目飞扫,接着又道:“本座且考一考你们,那桑琼小辈临危领众离开天寿宫,其目的是什么?”
大家又傻了眼,心道:“这还用问?不是趁虚往袭第三分官,行那‘围魏救趟’的计谋么?
可是,大家都被曹克武那一声冷哼镇住了,心里虽然明白,却不敢贸然说出来。
曹克武目观此状,冷笑着摇了摇头,目注陈童问道:“你身为分官宫主,难道也猜测不出?”
火灵官陈童腼腆一笑,躬自答道:“弟子只知道这是他‘围魏救赵’的狡计,至于其他目的,就……”
曹克武倒和颜悦色地颔首道:“不错,但本座问的是,他那‘围魏救赵’的狡计,目的何在?”
陈童壮着胆道:“自然是希望咱们回师往救第三分宫,此地之围使可解除了。”
曹克武又点点头,再问道:“可是,他怎能预知咱们一定会在今夜,得到五台山第三分宫危急的消息呢?假如咱们得不到这个消息,仍然对天寿宫下手,他的计谋莫不是要落空了?”
“这个——”陈童猛可一怔,竟呐呐回答不上来。
人妖又自作聪明,拱手代答道:“那桑琼小辈颇有机智,他当然料到咱们会在天寿宫四周预伏高手,随时侦查他们的举动
曹克武目光一闪,冷冷截口道:“那么,夏护法想必早已从伏路高手的呈报中,得知桑琼前往第三分宫消息了?”
“这——”夏玉珍不觉语塞,尴尬的笑了一笑,道:“宫主圣明,咱们的确尚未获知此项消息,若非朱护法不忘故主,及时来此呈报,咱们真要被那小辈蒙在鼓里了……”
曹克武重重哼了一声,道:“这就是你们比不上桑琼小辈的地方,他不仅使用了‘围魏救赵’的狡计,而且还用了一条苦肉计!
陈童和人妖俱皆一惊,骇然道;“宫主的意思是指——”
曹克武阴笑道:“朱光权叛逆在前,早不反正,迟不脱身,偏在此时脱身来归,这不是太巧了些?……”
一语未毕,那朱光权神色速变,急道:“启禀宫主,属下确无异心,宫主不信,可以问问社伦和罗滔,属下也曾拼死涉险闯出天寿宫,并且杀死了五六名宫中守卫弟子……”
曹克武冷叱道:“不如此,怎能邀得信任,本座料你身边一定还携带着与北宫四燕联系识别的信物,准备在咱们中计之后,通知四燕随后追击掩杀,你还敢狡赖?”
朱光权脸色大变,矢口道:“属下没有……”
曹克武喝道:“来人,给本座仔细的搜!”
朱光权突然挺身跃起,双掌一错,呼呼横劈两掌,霍地旋身向室门外冲去!
变起仓促,群邪都没想到朱光权竟敢出手反抗,杜伦和罗滔相距最近,立被掌力扫中,滚跌开去,室中顿时大乱!
朱光权,身形如电,转眼已冲到门前。
曹克武怒目一挑,冷叱道:“鼠辈还想走么?滚回来!”扬手凝势,遥向朱光权背心一抓一收。
空际“嘶”地一声锐响,只见朱光权身形一顿,紧接着,竟凌空倒撞了回来,重重掉落在地上。
两名随侍在侧的猥族野女闪身而出,一人抓住一条手臂,登时将朱光权像小鸡似的提了起来。
陈童猛跨上前,扬掌便劈,怒骂道:“王八羔子,老于就不信杀不尽你们这些叛逆!”
掌势未落,曹克武已厉声喝道:“住手!本座命你搜他身上,不许伤他性命。”
陈童愤愤的收回掌力,三把两把撕开朱光权衣衫,一搜之下,果然从贴身处抢出一枚小型号箭。
曹克武狞笑道:“姓朱的,你还有什么话说?”
朱光权昂然不惧,破口骂道:“老匹夫,你多行不义终必遭报,朱某人对你早已深痛恶绝,恨不能吃你的肉,喝你的血,此次才自告奋勇愿担任诱敌任务,未来之先,朱某人已存必死之心,早将生死置诸度处,只恨功败垂成,未能亲眼看你遭受报应,既已落在你手中,老匹夫!要杀要剐请便,朱某人若是怕死,也不来了。”
曹克武冷笑道:“好一打硬汉子,本座且问你;你在第三分官身居护法,奉禄不薄,更没有人亏待你,因何叛投敌人,更不惜冒死替敌人行此苦肉之计,你倒说说看,本座哪儿亏负你,桑琼又有什么地方厚待了你?”
朱光权朗声说道:“你这老匹夫奸诈毒辣,为一己私欲,茶毒苍生,待人以威逼离间,使人妻离子散,供你驱策凌辱,手段残酷神人共愤,纵能摄人之身,不能服人之心,大家对你敢怒而不敢言,一旦有机会,必然众叛亲离,桑庄主却对人推诚输义,襟胸磊落,豪迈感人,使人相处如沐春风;相敬如同手足,万人悦服,乐为效命,岂是你老贼所能够比拟的。”
曹克武并不生气,反微笑道:“依你这么说,他也不过仗着虚情假意,网罗人心,口惠而无实利,你却没想想自己亲人都在总宫,叛逆从敌之罪,不单关系你自己生死,更关系你的亲人!”
朱光权叱道:“老匹夫,你不必再拿亲人性命来威胁朱某人,大丈夫为义而生,活要无愧天地,死要无作祖先,人生一世不过短短数十年,纵不能流芳百世,也不能遗臭万年,为人旦求心安,区区生死亲眷,早就不在意中了,何况你老贼视人质如俎肉,肆意凌辱子取予割,何冲身为舵主,尚已被你师徒霸妻夺爱,你以为朱某人还会顾忌妻儿,甘心替你们卖命吗?”
曹克武默然片刻,旋又冷笑道:“本座不信你真的不怕死,杀一敬百,本座正愁找不到人开刀,这只怪你运气欠佳……”
朱光权昂然道:“既已失手,朱某人也没有打算活着回去。”
曹克武道:“但你可知道本应要如何处死你?”
朱光权冷冷道:“反正不外一死杀剐听便。”
曹克武嘿嘿笑道:“本座最恨不忠不贞之徒,对待叛逆向不从轻,你要想痛痛快快一死,却也没有那么容易,本座要教你亲眼看着自己的妻儿子女,遍受人间惨刑,然后将你凌迟碎割,以敬效尤!不过……”
-------------
幻想时代 扫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