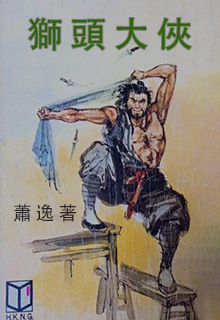凌茜对宫天宁的逸去毫不理会,凤目迅速扫视,见那人手持一根竹杖,一腿悬空,一腿单立在墙头上,整个人纹风不动,竟是用的“点萍无波”之式。
她心中一动,一摆翠袖,化着一条淡绿色的身影,一闪到了墙头之下,低声道:“许成,你好大胆子,竟敢撞到这儿来了。
”
许老二白果眼连翻数翻,笑道:“在下怕姑娘认不出来,特用出这‘点萍无波’的姿势,姑娘看看可还像样么?”
凌茜又好气,又好笑,沉声道:“你来到有什么事?快些说吧!这儿千万不能久耽。”
许成用竹杖一指远处一片竹林,道:“在下四人,现有要事欲请姑娘一谈,咱们在林边恭候。”
凌茜担心被巡夜的高手或父亲桃花神君发觉,急急道:“好吧!你先去,我马上就来。”
许成去后,凌茜四下一阵张望,未见动静,芳心却不免犹豫,暗想这四个丑人怎知道自己在这座庙里?他们夜半潜来邀约,为了什么事?
她这时大可不去应约,但想到明日一早,便要离开此地,倘若今生不能再到中原,心里的一件负荷,便永远也不可能释然了。
她本已不想再见陶羽,但自从知道他曾经来过古庙,心底却不禁又泛起涟漪!
陶羽来干什么?不用猜,只有一个理由,刃蹴是来找她。
可是,他真的带着竺君仪同来的吗?为什么原因跟爹爹闹翻动手?有没有被爹爹打伤……
她心里乱得很,唱然轻轻一叹,身形展动,奔向那丛竹林。
竹林前有块草地,“海天四丑”已并肩站在草地上,每个人面上都一片肃穆。
凌茜迷惑地问道:“你们来寻我有什么事呢?”
四丑彼此互望一眼,包天洛向前跨出数步,从怀里取出一粒龙眼般大的珠子,默默地递到凌茜手上。
凌茜接过珠子,低头细看,只见珠子色泽略显暗黄,珠面上隐隐现出机缕深红色的纹络,带着浓厚的清香气味。大惑不解,问道:“这珠子作什么用的?”
包天洛缓缓说道:“这珠子名叫‘犀顶珠’,乃自千年寒犀头顶上剥取而来,有化解面毒的功能,我等在无毛族荒岛上,费尽千苦,方才寻到,珍藏至今,视同性命……”
凌茜诧道:“那么你们把它交给我作什么呢?”
包天洛咽了一口唾味,脸上露出一抹勉强的笑容,道:“这是我们四人感激姑娘指点轻功要诀的一点心意……”
凌茜“啊”了一声,连忙把珠子又还给他,笑道:“你们的好意,我谢谢了,那天在乱山中,是我无意先惊扰了许老前辈练功,所以略陈所知,用作补偿,这原是我对不起你们,怎能再收你们的厚礼。”
包天洛面有难色,回头看看其余三人,那文士打扮的林一波忽然越众而出,拱拱手,说道:“些小之物,实在不成敬意,姑娘请晒纳了,我等还有下情奉闻。”
凌茜道:“有什么话,你们尽管请说,可是,这珠子我万万不能接受。”
林一波沉吟一下,笑道:“姑娘出身名门,玄功盖世,想必知道武林中人,嗜武若命,有些人为了习武,不惜毁家荡产以赴,有些人为了谋求功力增进,常常不择手段,做出越轨害人之事……”
凌茜点头道:“这个我不难想像得到,一个嗜武如命的人,每每会不顾一切地去争取天下第一的虚衔的。”
林一波面有喜色,忙道:“姑娘高见,明如日月,譬如区区在下等四人,生平便是嗜武若命,凡闻绝世玄功,莫不梦寐以求,唯恨福缘菲薄,至今并无成就,想起来,真是令人扼腕唏嘘——”
凌茜笑道:“你说了半天,何不把心意率直表露出来呢?”
林一波突然面色一怔,道:“姑娘冰雪聪明,难道不知我等衷心希冀的事?那日山中一晤,我们再三计议,对姑娘桃花门惊世骇俗的武功,憬慕无限。因此今夜特又冒昧邀请姑娘移驾此地,愿以这颗罕世难见的解毒珍品‘犀顶珠’,与姑娘交换,将贵门‘冲穴御神’之法,赐告一二法门,我等但得寸进,必不忘姑娘成全宏恩。”
他一口气把话说完,心里大大松了一下,回顾三丑一眼、对自己的口才颇有些得意之感。
包天洛等都一齐把的的目光,投注在凌茜身上,十分急迫地等待她的答复。
凌茜沉吟片刻,笑道:“你们的好武之情,实在使我深受感动,可是,桃花门的武功,是一向不准私传外人的
杨洋立即插口道:“只要姑娘愿意成全,我等自不会对人提起,而且,‘冲穴御神’之法,非独门招式可比,也不愁会被人看出来!”
凌茜笑笑,说道:“假如是一招一式,那倒可以传给你们了,大不了说是在对手过招时被偷学去的。唯独这种通穴增进功力的独门手法,天下只有桃花一门会使,而桃花门又只有我和我爹爹练过,将来不难一查便穿了。”
许成双目无法看见,但一直都在专心一志的听着他们的对话,此时一听凌茜执意婉拒,心里大急,肩头一晃,抢了出来,大声道:“姑娘如肯授我通穴大法,许成有生之年,必将有以报偿,姑娘但有所命,赴汤蹈火,也绝无犹豫。”
凌茜心中微微一动,脸上笑容渐渐沉敛了下来。
林一波急向包天洛递了个眼色,包天洛连忙双手捧着那粒“犀顶珠”送到凌茜面前。四丑鸦雀无声,只盼凌茜蜂首一颔。
凌茜凝目注视着那粒“犀项珠”,心念起伏,怅然无语,暗讨道:“这东西对他也许大有用处,不知他体内伤势,果然已经痊愈了没有……”
“唉!我明天一早就要跟爹爹回桃花岛去了,将来也许再无机会重莅中原,就算传了他们、又有谁会知道呢……”
转念间,又忖道:“不!不能!这四人相貌怪异,是正是邪,尚难分辨,假如错传匪人,怎对得起桃花门中历代祖先……”
“可是,我又怎甘心就此与他永诀,连最后的一面,也不能见到?”
传授“冲穴御神”之法和陶羽本是毫不相干的两件事,然而凌茜却总是把这两件不相干的事,联想在一起……
眼前这四个丑汉,是她在临去之前,唯一与外界交谈的人,良机瞬即逝,到了明天,再要寻个能把自己行踪转告陶羽的人,只怕再不可能了。
她反复苦思着这些心事,脸上也时喜时忧,阴晴不定。
“海天四丑”人人目不转睛,各人的神情,也随着凌茜的喜忧而升沉变化。
过了很久,凌茜才长叹一声,幽幽说道:“你们如能为我办成一件事,我便可以考虑告诉你们‘冲穴御神’的方法,不过,唉!这件事你们也许不肯去做……”
四丑大喜,几乎异口同声叫道:“姑娘但有吩咐,粉身碎骨,在所不辞。”
凌茜凄惋地一笑,说道:“这事说难不难,说易不易,但你们跟那人有仇,也许不会答应去寻他。”
四丑急道:“姑娘快请直说,我等断无不愿之理。”
凌茜道:“这粒珠子,我不需要,但我要你们去把它送给另外一个人,并且为我转告他一句话……”
侧丑道:“那是人谁,姑娘快说——”
凌茜道:“他就是你们心中骂他认贼作父的陶公子……”
“啊!原来是他……”
凌茜点点头,道:“不错,是他,我明天一早,就要跟随我爹回桃花岛去了,你们如果能够赶快找到他,把这粒珠子转赠,同时,要他在我离开中原以前,来跟我见最后一面,我就把‘冲穴御神’法私下告诉你们。”
四丑听了,面面相觑,作声不得。
凌茜看他们颇有难色,不觉心灰,叹道:“我原说这件事定会使你们为难的,但这是我心中最大的愿望,除此之外,虽有绝世珍宝,也难打动我的心意。”
淋一波连忙接口道:“姑娘不要误会,我等为难的,并非不愿去寻他,而是担心两点困难。”
凌茜道:“是什么困难呢?你可以说出来听听吗?”
林一波道:“第一,那陶羽现在何处,已是难寻,何况姑娘明早便要动身,我等再快,也无法在一夜之间便将他找到啊!”
凌茜点头道:“这个不难,我们虽然明早便动身,但由此地到海边,途中至少要行半个月以上,而且,我可以设法使车辆走得慢些,只要他能在一月之中,赶到海边,就可以见到那最后的一面了。”
林一波又道:“第二,不瞒姑娘说,那陶羽和我等四人,从前有些过节,我们就算寻到他,把话转告,他必然也不会相信,这却怎么好呢?”
凌茜想了想,便从颈间取下那半枚“全真金钱”,递给他道:“你们把这件东西拿去,他见了这半枚金钱,一定会相信你们的话的。”
林—波接过金钱,回头望望三人,似在征询他们的意见。
许成毫未思索,爽然道:“既是这样,事不宜迟,我们立刻去寻陶羽,但等这事完满之后,姑娘可不能失言!”
凌茜道:“要是你们相信,就不妨试试,如果不相信,我也别无他法。”
包天洛沉声道:“我等对姑娘敬若仙人,岂有不信的道理,如此咱们现在这就告辞。”
四丑一齐向凌茜拱手为礼,转身如飞驰去。
凌茜突然叫道:“等一等!”
四丑闻声停步,问道:“姑娘还有什么吩咐?”
凌茜沉思了一会,幽幽说道:“如果他不愿意来,那也不必勉强他,只请他也给我一件物品,让我知道你们的确见到了他,也就罢了。”
四丑应声而去,转眼便隐入林中。
凌茜怅然呆立许久,心里忽又懊悔起来,暗责道:“唉!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既有所恋,怎会再来见我这自作多情的女子?何况,纵算能见他最后一面,又能怎样呢?黯然相对,徒增情恨,凌茜啊凌茜,你也未免太痴了。”
想着,急忙纵身追进林中,展开身法,飞快地穿林疾赶。
但不知是她心急之下追错了方向?还是四丑已将“点萍无波”的绝顶轻功参透?追了二程,竟未能追上。
林木萧萧,长夜正浓,当她废然退出竹林时,月儿已偏向西方,遍地银练,映着她依然孤独的身影。她冥立林前,否知所做的对与不对?不禁仰对皓月,发出一声悠长的叹息。
天不久就要亮了,天亮的时候,也就是她启行离开这古庙的时刻,回忆中原数月,就好像做了一场无头无尾的梦。
她徘徊唏嘘一阵,独个儿悄悄返回古庙,当她身子刚从庙墙之上飘落院子时,却蓦闻一声冷冷的声音道:“茜儿,过来这边!”
凌茜猛然一惊,惜着月光,只见院边一片珠檐之下。放着—张软椅,椅上正坐着她的父亲——桃花神君。
她心头不觉卜卜直跳,但此时欲避已经来不及了,只好嗫嚅地走上前去。
桃花神君一个人坐在椅上,手边斜斜倚着那柄杯口粗细的纯钢拐杖,一双神目,的的地逼神着她。
凌茜连头也不敢抬,轻声问道:“爹,你老人家还没有睡?”
桃花神君“晤”了一声,冷冷道:“这样夜深,你一个人到哪里去了?”
凌茜强颜笑道:“女儿心里很烦,睡不着,到庙外去走了一会……”
桃花神君微笑道:“爹爹待你爱怜至深,哪有什么烦闷,使你深夜难眠,要独自出去散心?”
凌茜暗想爹爹因为曾经走火入魔,双腿至今无法行动,他既然独自坐在这儿,必然已不止一时半刻了,自己行踪,只怕早落在他的眼中,于是一横心,道:“爹待女儿固然不薄,可是,待外人有时比对女儿更厚……”
桃花神君一怔,笑道:“是吗?那是爹爹歪心了?你倒说说看!”
凌茜壮着胆,道:“譬如说,咱们桃花岛一向严禁外人擅人,可是今日爹爹竟会亲邀那讨厌的宫天宁同往,姓宫的心术不正,是个可卑的小人,你老人家也待他这样厚,相形之下,女儿自然要心烦啦!”
桃花神君听了,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道:“这么说,你是在生爹爹的气了?”
凌茜道:“女儿不敢生爹爹的气,可是,你老人家为什么会那样厚待她,女儿的确无法明白。”
桃花神君又是一阵哈哈大笑道:“爹爹不但厚待于他,说不定将来心里一高兴,更会把你终身许配给他,你看如何呢?”
凌茜大吃—惊,刚要开口,忽听远处的廊下,传来二声极其轻微的喘息之声。
她耳目何等灵敏,那喘息之声虽轻微得不能再轻,但一入她的耳中,便立即猜到廊下必然隐藏着一个人……
凌茜怒目一扬,方欲发作,桃花神君却忽然咳了一下,漫声道:“不用紧张,他已经走了。”
这情形,显然他已知道廊后躲着有人,只是故作不知,没有说破而已。
凌窗惊问道:“爹,你早知道了?”
“什么事瞒得过爹爹?”
“他是谁?”
“还用猜吗?”
“是宫天宁?”
桃花神君含笑不语。
凌茜愤愤地道:“你老人家看吧!这种鬼鬼祟祟的东西,你……你还要……”
桃花神君哈哈一笑,挥挥手,指着身边一张石凳,道:“来,坐下来,咱们父女许久没有谈谈了,今夜月色如洗,正该多谈一会。”
凌茜不解他用意何在,只得讪讪地坐了下来,一面倾神细听,果然四周己不再听到人声。
桃花神君忽然变得慈祥无比,握着女儿的手,轻轻拍着,道:“自从你娘去世,桃花一门,只有爹爹和你,如今爹爹双腿俱废,将来光大本门,延续香火,全在你一人身上。孩子,你不会使爹爹失望吧?”
凌茜听得心里一阵酸,连忙点头道:“女儿知道,可是,我宁死也不愿嫁给宫天宁……”
桃花神君大笑着打断她的话,道:“孩子,你太愚啦!世上还有比爹爹更疼你的人吗?那姓宫的小子是什么东西?爹爹会把你嫁他吗?……但是,你也应该让爹知道,谁是你心目中的丈夫?”
凌茜粉脸一红,旋又一黯,摇摇头道:“女儿也不知道。”
桃花神君笑道:“这就是矫揉之言了,此地只有我们父女两人,你老实对爹爹说,那姓陶的小伙子如何?”
凌茜突然热泪纷落,“哇”地一声,伏在软椅上呜咽起来。
桃花神君轻叹一声,道:“孩子,不许哭,咱们凌家男女都是硬汉,是不轻易掉眼泪的。”
凌茜忍住酸楚,收泪招起头来,颊上泪痕未干,绽出一线苦味的笑容。
桃花神君自己倒觉鼻头一酸,但他毕竟是修为多年的健者,深纳一口气,神色登时又复平静,道:“据爹的看法,那陶家孩子固是不坏,但听陆家兄弟说,他如今正陷身在错综复杂的恩怨之中,而且。他体内中有剧毒,你知道吗?”
凌茜吃惊道:“我只知他曾经受过内伤,却不知道他中了毒?这一定是宫天宁干的好事……”
桃花神君点点头道:“不错,他所中的毒,正是全真教的‘焚心毒丸’,爹起初还以为他是全真教叛徒,后来宫天宁来了,才知不是。”
凌茜愤然道:“爹,答应女儿,我要杀了宫天宁替他报仇……”
桃花神君黯然道:“杀了他于事何补?这事爹爹自有安排,明天咱们就动身回桃花岛去,天都快亮了,你去休息一会,吧!
”
凌茜急道:“爹爹,求求你老人家,咱们缓几天再走,我……我……”
“桃花神君”动容道:“你还想等他来,跟他见上一面?”
凌茜一怔,但随即爽然点点头,目中早又热泪盈盈。
桃花神君长叹一声,道:“痴孩子,他要来自会追来,否则,见又何益?”
说罢,取了拐杖,扶着凌茜的肩头,从软椅上站起身来。
凌茜深知父亲秉性刚烈,不便苦缠,扶着他回到卧房,替他安顿妥当,临行时,忽然想起一件事,道:“那么,宫天宁呢?”
桃花神君仅只淡淡一笑,道:“交给爹爹吧!别忘了,他是全真教的人。”
凌茜含泪颔首,失神地回到自己房中,和衣躺在床上仰望房顶,那里还能入梦?
不过片刻,天色便已大明,院中人语马嘶,渐渐沸腾起来。
这些声音,正似告诉她立刻便要离开这初次钟情的地方,她心烦意乱,双手掩住耳朵,—翻身,滚向床里……
车声鳞磷,马嘶阵阵,重叠阳关,消逝着苦恼的日子。
一天,二天,三天……
在桃花神君默许之下,人马行得十分缓慢。
凌茜无精打采地依坐车中,对面便是父亲桃花神君,“陆家双铃”随侍在马车两侧,在他们身边,多了一个宫天宁。
宫天宁跨着骏马,儒衫飘飘,神情飞扬,一忽儿纵马赶到前面探路,一忽儿又缠着双铃蝶蝶不休,每到一处宿夜的地方,更是忙碌着指挥筹措,替桃花神君父女准备住处,件件设想得十分妥贴。
虽然忙碌,却掩不住他内必的欣喜与满足,偶有片刻闲暇,便憧憬着到达桃花岛之后的绮丽风光。
娇美的妻子,如山的财富,绝世时武功,今生今世,夫复何求?难怪他在睡梦之中,也常常发着吃语:“……我宫天宁就是桃花门未来的掌门……全真教…竺君仪……哼!算得了什么……”
桃花神君一直很少开口,一双神目,却几乎没有片刻离开过爱女,眼看着她不时掀起车后窗帘,痴痴地向后面张望,老怀难免暗自酸楚。
日子一大天地过去,五天,十天,二十天……
凌茜望穿秋水,可是除了灰尘,车后始终未见到半个人影。
一个月无声无息地将要过完了,海口渐近,她的心,也一天天地下沉。
是许成他们没有找到他?或是他不愿跟自己见这最后的一面?她只恨马儿行得太快,恨不得这段途程,再走上十年八年才好。
可是,时光是无情的,路也终有走完的一天,张望云天,人踪俱渺,她再也忍不住情泪纷洒,柔肠寸断……
凄惶中,车声戛然遽止,陆完在窗外禀道:“启岛主,海口已经到了。”
桃花神君默默望着爱女,半晌没有出声。
宫天宁也喜笑颜开地掀起窗帘,道:“岛主,已经到海边丁,咱们落船吧?”
凌茜突然跪倒于地,哭叫道:“爹……”
桃花神君黯然向窗外挥挥手,轻抚着凌茜的秀发,许久许久,才叹了一口气,道:“孩子,他至今不来,大约是不会来了。”
凌茜仰起泪脸,用力摇着头道:“不!不!他一定会来的,爹爹,我们再等他三天……。”
桃花神君哼了一声,隐隐可以听见刚牙磨得悉悉作声,蓦地沉声道:“落船!”
凌茜放声大哭,死命扯着父亲的衣襟,哀声道:“爹,求求你老人家,再等三天,他一定会来的……”
桃花神君只是冷漠地摇摇头,道:“已经等了他二个月,他即使现在赶来,爹也不会让他再跟你见面,你们的缘份,到此已尽。”
宫天宁兴冲冲到海边雇了五艘大船,一字儿排在岸边,车辆马匹,全下了船。
桃花神君换乘软轿,也下了船,凌茜已哭得声嘶力竭,由几名侍女挽扶到舱里。陆整与船家商议一阵,进舱禀报道:“据船家回称,现在北风刚起,潮水也正涨,如要启旋,正好赶上风潮,天明以前就可以抵达桃花岛了。”
桃花神君沉吟不语,缓缓回过头去,向后舱望了一眼,舱间帘幕低垂,里面传来一声凄切的啜位!
他木然的脸上,忽然掠过一抹怜惜之色,长叹一声:竟未回答陆望的话。
陆方忍不住也望了望后舱,然后压低嗓子,悄声道:“公主与那陶公子不过数面之缘,没想竟会痴情到这种地步。”
桃花神君喟然一叹,低声喃喃道:“唉!孽障!孽障!”
陆方连忙又道:“错过午刻潮水,便要到半夜子时才会再有大潮了,岛主的意思,是立刻启旋呢?还是稍候半日,待子时涨潮再走?”
桃花神君紧皱着眉头,道:“唉!这可怜的孩子……你去吩咐船家,静待子夜大潮时启旋,无论如何,不能再延时刻了……”
凌茜在后舱里听见,号哭着奔了出来,扑地跪倒,叫道:“多谢爹爹……”
桃花神君流露出无限怜爱,抚摸着女儿宛如带雨梨花似的面庞,柔声道:“孩子,你这是何苦啊……”
话未说完,两滴晶莹的老泪,己默默顺颊滴落襟前。
海潮轻吻着沙粒,一浪消退,另一个浪花又涌了上来。
船舷边,波澜相击,发出一声声落寞单调的音响,粼粼波纹,已渐渐由碧蓝转变成金黄色,日轮悄然沉入西山。
正当夜幕扩张的时候,距离海边半里多的一处小镇上,如飞驰来—骑通体乌黑的骏马。
那骏黑马虽然神骏非凡,但此时也遍体汗迹,鼻口中吐着白气,马上一位儒衫少年骑士,也是满身尘上,显见是经过长途奔驰,刚刚赶到镇上。
一人一骑,在小镇上转了个圈,最后停在一家兼营客店的酒楼门口,那儒衫少年一闪身下了坐骑,举步走进店里,默默选了副空桌坐下。
伙计连忙上前躬身笑问道:“少爷是先用酒饭?还是先要间房间,盥洗后再用饭?”
儒衫少年略一沉吟,道:“你替我先留下两间宽敞的卧房,我还有几位朋友,等一会也要赶到了,另外给我随意弄点酒菜来,用过之后,我还得出去一道。”
伙计连声答应着,一面高声交待到柜上,一面抹干桌子,送上几样下酒小菜。
儒衫少年剑眉紧皱,似有满腹心事,自己斟了酒,一仰脖子,喝得涓滴无存,接着又斟满一杯。
他显然不是会喝酒的人,一杯下肚,俊脸上登时浮出两朵红云,可是,他却毫未迟疑,举起第二杯,一仰头,又喝得干干净净。
一连干了两杯酒,儒衫少年心情似乎略为平静了些,扬手唤过店伙,问道:“你们这镇甸,距海口还有多远?”
伙计笑道:“少爷,你或许是初次到小地来,咱们这处镇甸,唤作‘汪家集’,再向南三里多,便是海口了。”
懦衫少年“啊”了一声,又道:“这儿能雇到出海的大船吗?”
伙计道:“海边有的是海船,不知少爷雇船要到那里去?”
那儒衫少年淡淡一笑,道:“我想雇一艘快船,明日一早启碇,去桃花岛。”
伙计听了“桃花岛”三个字,眉头一动,道:“暖呀!少爷真是来迟了一步,听说今日午问,有许多客人,一口气雇了五艘大船,也是往桃花岛去的,少爷若早来半日,跟他们一路,岂不好么!”
儒衫少年神色蓦地一变,问道:“是么?你知不知道那些雇船的客人是何许人物?”
伙计摇摇头,道:“咱们只听说人很多,还有车辆马匹,看上去像是十分有钱的样子……”
儒衫少年一听这话,脸色更是大变,闪电般一把扣住那伙计的手腕,急声道:“其中是不是夹有妇女?另外有个老人,双腿不能行动,须用软轿抬着?”
伙计被他这突然的举动吓了一大跳,连连点头道:“一些也不错,少爷是来寻他们的?”
儒衫少年虎目疾转,沉声又问道:“他们什么时候启旋的?”
伙计道:“那些客人是午刻左右雇的船,说明立即启碇,赶午时大潮顺风,大约已开出半日时光了……”
儒衫少年听说船已开走半日,全身劲力这失,长长嘘了一口气,一松手,颓废地坐到椅上,两眼直视,口里喃喃自语道:“凌姑娘啊凌姑娘,我日夜不停,拼命飞赶,仍然来迟了半天,唉!要是能早到半天,那有多好………
他唏嘘半晌,突然探手抄起酒壶,对着壶嘴,一连灌了几大口,“蓬”地将酒壶放回桌上,那银制的酒壶,竟斗然嵌进桌面,足有四五寸深。
伙计看得咋舌不已,蹑足欲溜,门外蹄声骤至,转眼间,又进来了三男一女。
这四人个个满头大汗,其中一个纹脸大汉,一个英朗负剑少年,另外一个身芽绸衫,头戴皮帽的老头子和一个面形樵粹的女郎,四个人四种模样,极是显目。
他们一拥进店,直奔先来的那儒衫少年桌前,抢着问道:“怎么样?有消息了吗?”
那儒衫少年热泪盈眶地点点头,道:“途径没有错,可是,咱们都来晚了一步……”
纹脸大汉大声道:“难道已经走了?”
儒衫少年又点点头,道:“午间才走,距现在不过半日。 ”
大汉一掌拍在桌子上,道:“他妈的,想不到海天四丑这一次竟说的是老实话。”
那形容樵悴的女郎长叹一声,道:“陶公子,这都怪我牵累了你,明天我一个人赶到桃花岛去,亲口向凌姑娘说明这件事的经过……”
皮帽绸衣老头连忙摇手道:“鲁莽不得,凌祖尧那老头儿生性怪诞,他那桃花岛,外人是严禁踏入一步的,咱们指望追上他们固然好,既然来迟了一步,却得从长计议!”
负剑少年接口道:“事到如今,还有什么好计议的,无论它桃花岛是龙潭还是虎穴,咱们也要陪陶大哥去闯一闯。”
儒衫少年低头把玩着颈问悬着的半枚闪闪发光的金钱,头也未抬,幽幽说道:“我已决定于明时雇船迳赴桃花岛,是福是祸,由我一个承担,你们最好在这里候我半月,如果半月不返,那就是我已经死在桃花岛上了……”
形容憔悴的女郎忽然“哇”地哭出声来。
皮帽绸衫怪老人沉着脸道:“男儿志在天下,岂能为了儿女私情,把性命看得这么轻贱?
你纵然甘心一死,天下武林千万同道,也不会答应你如此自暴自弃,公子说出这话,不怕罗大侠在九泉之下心寒么?”
负剑少年道:“伍前辈说的不错,大哥,你肩上挑负着天下武林荣辱存亡的重任,万不可轻易涉险,我看……还是由小弟代你去一趟如何?。”
陶羽黯然无语,一直摇着头,显得内心极是痛苦。
四人见他无言,也就未再开口,大家面面相觑,枯坐了—会,伍子英站起身来道:“咱们只闻桃花岛的名字,究竟它距此有多远?快船须几日才能往返?尚不清楚,你们略歇片刻,让我去海边寻个船家打听打听,晚间咱们再定行止好了。”
他独自出了客店,一路向海边行去,肚子里却在寻思,该如何用条妙计,阻止陶羽往桃花岛涉险。他虽知陶羽此时武功业已精进不少,可是,桃花神君凌祖尧更是盛名早著,别说陶羽一人独去他不能放心,就是五个人一同去,能否全身而归,也实在叫人难以逆料。
不过,他又深知陶羽乃是个至情至性之人,假如不让他再见凌茜一面,那后果却又太令人担忧了。
正想着心事,猛抬头,却见前面海岸边,一列井排靠着五艘三桅大船,船上隐隐有许多红衣大汉,肩负长剑,在舱面往来梭巡。
伍子英心中一动,连忙停步,远远凝目向船上张望,望了片刻,忍不住心头狂跳,原来他已望见其中一艘船的船头上,正绰立着一个绿衣绿裙的少女,痴痴地面对夜空,一动也不动。
“那不是凌姑娘吗?”
他险些要叫出声来,暗自忖道:“不是说他们午间已经启旋走了?怎的仍在这儿?”
伍子英心神紧张得象崩紧了的弦,缓缓又向前走近丈许,藉着淡淡月光,揉了揉眼睛再看,果然一些不错,那绿衣少女正是凌茜。
这时月移中天,恰是于夜将临时分,浪潮拍击着海岸,层层前涌,潮水正在上涨……
忽然另一艘船上又走出一人,俯身看看海面,回头叫道:“去回岛主吧!潮已经涨了,应该准备启旋了。”
伍子英心头狂跳,意念飞转,竟无善策再向凌茜走得近些,因为这时船面上又出现了许多人,有的甚至已在开始解缆收板,准备启旋。
时机稍纵即逝,他知道如不赶快回镇驰告陶羽,凭他一人之力,决不可能在桃花岛高手云集之下,踏上船舷一步。
主意一定,飞快地扭转身子,提足一口真气,发足狂奔,人如一缕轻烟,翻翻滚滚,向镇中疾驰而回。
海边距镇街,不过三里多路,若在平时,顶多一盏热茶时间,伍子英是足可赶到的。但这时无论奔得多快,却总觉得其慢如牛,眼中早望见镇上房字,奔了许久,竟然仍未奔到。
待他气急败坏地赶抵客店,一望之下,却不见陶羽等四人的踪影。
这—急,真是非同小可,迫不及待——把抓住那客店伙计,喘息着喝问道:“他……他们呢?快说!快说!”
那伙计被他一把提住衣领,就像提小鸡似的双脚离了地,早吓得三魂去了二魂,越发语不成声,结结巴巴道:“谁……谁啊?……老……客……”
伍子英恨不得一掌把他劈死,但转念一想,也知是把他吓呆了,只得松手放他下来,急声问道:“不久前在那边桌上同桌吃酒的三个男的,和一位姑娘,他们现在到那里去了?”
伙计恍然道:“是不是两位少年公子,一个粗汉,脸上刻着花纹……”
伍子英连连点头,道:“不错,不错,他们现在那里?”
伙计怔了一怔,才笑道:“老客,你老人家险些把人吓死,那几位客人公子,多喝了几杯,现在只怕已经睡熟了啦
伍子英喝道:“房间在那几?快带我去!”
伙计不住答应、匆匆要去找灯,伍子英不耐,一把提起他的衣领,人踏步向后面客房便跑。
他已经等不及店伙计指点房间所在,所过之处,凡是房间,一律拳打脚踢,把房门轰开,一间间乱搜乱找。这一来,许多客人从睡梦中惊醒,只吓得怪叫连天,整个客店,直被他扰了个天翻地覆。
总算竺君仪尚未入睡。被叫喊声惊动,出来探视,这才带他寻到陶羽房中,却见陶羽、秦佑和辛弟都己烂醉如泥,人事不知。
伍子英奋力拖起陶羽,摇了几摇,叫道:“陶公子,快醒一醒!”
陶羽从朦胧中睁开眼来,但随又废然合上眼皮,呢喃道:“……醉乡路稳直频到,此外不堪行,来!秦兄弟,再喝一杯……”
伍子英怒从心起,蓦地一声大喝,道:“还在说什么疯话,凌姑娘还没有走,你要不要去见她?”
这一声断喝,宛如春雷乍动,不但陶羽一惊而醒,连秦佑和辛弟也都一滑碌爬了起来,竺君仪也瞪大了眼睛,几乎异口同声道:“什么?你说什么?”
伍子英道:“我在海边亲眼看见凌姑娘,桃花岛的船尚未启旋,你如要见她就赶快跟我来!”
陶羽骇然一跳,道:“有这种事,你快些带路……”
伍子英连责备他的时间也没有了,转身向外又奔,陶羽等四人随后紧随,出了店门,五人各展轻功,恍如流星赶月,奔向海边。
可是,当他们一口气赶到海边,岸边己不见了五艘大船的影子。
朦胧月光,掩映着水面碧波,波光月影之中,只看见五团暗影,冉冉向南移去。
——阵海风拂面而过,隐约可以听到船上“依呀”的橹声,和模糊不清的呼喊。黑形渐去渐远,逐渐变得一片模糊……
-------------
武侠屋 扫校, 独家连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