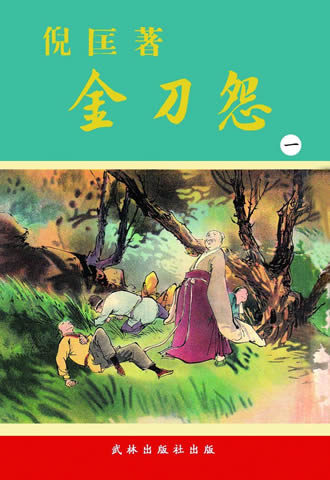秦中来现在还清清楚楚地记得第一次看见红石榴的情形。
那是三年前一个秋夜,秦中来被苦风凄雨吵得不能入睡,披衣而起,翻出本古棋谱,在灯下一把一式摆着玩。
秦中来的棋艺在江南一带负有盛名。然而秦中来自己却一直认为“弈乃小道”,玩玩还行,不能废寝忘食地去钻研。
秦中来被人称为“八方君子”,不是没有原因的,泰中来笃信孔孟之道,而且对朱程理学精研有年,造诣颇深。
仅从他对围棋的态度,就可以看出他那种”君子”本色来。
秦中来摆到第三局棋时,家人睡眼惺松地敲门说门外有一个娃郑的公子来访。
秦中来又惊又喜。光着脚就往门口跑,浑身被雨淋得透湿。
这位“郑公子”,就是郑愿。
郑愿也是一身狼狈,身后还跟着个落汤鸡般的“少年”,秦中来黑暗之中,也没在意。
那个“少年”,就是红石榴。
红石榴浑身罗衫尽湿,发育得很好的胸脯令人“触目惊心。
秦中来的脸刷地红了,心中也怦怦乱跳起来。他飞快地转过眼睛,不敢再看,而且那个晚上再也没朝红石榴看一眼。
“非礼勿视”这句古训,他四岁时就已牢记在心。
秦中来招呼家人,领郑愿和那个女孩子去更衣,自己却坐在那里发痴。
秦中来还是第一次被女人的胴体刺激得如此强烈。以前虽也免不了偶尔“非礼”女人一眼,但那些女人不能和红石榴相比,“非礼”的程度也不能和那天晚上相提并论。
秦中来发现,自己居然在想人非非,而且不可抑止。
虽然古圣贤曰:“淫于心而不淫于行,是谓圣人”。但秦中来仍觉得有点羞愧,就好像自己做了贼似的。
因为他想起了一句俗语:“朋友妻,不可欺”。他知道郑愿这小子身边向来不缺女人,虽然“非妻”,终究还是关系密切,于是秦中来觉得自己不该“淫于心”。
当郑愿换好衣裳,进来相见时.秦中来都觉得脸红。
郑愿告诉他说:自己将去高唐看看老家还有什么亲戚,顺便探访一下旧邻,请他帮忙安置一下红石榴。
然后郑愿把红石榴的身世遭遇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
秦中来听得热血沸腾,当即满回答应。
事后秦中来才知道,“安置”红石榴是如何不容易。
一看见她,他就想入非非,常常走神。而她呢,又客气又冷淡,知礼得很,一心一意念着她的“大哥哥”郑愿。
秦中来的苦恼从那天晚上开始,一直到现在还没结束,而且还不知要到何时才能结束。
他痴恋她,而她又痴恋着他的朋友。
那年他十七、郑愿十八、红石榴十岁。
去年六月,红石榴失魂落魄地回到金陵,站在秦中来面前。
秦中来几乎已认不出她来了。她蓬头散发,衣饰不整,像个女丐,一个疯了的女丐。
红石榴只说了一句话,就昏倒在地上。
她说的那句话是“大哥哥不要我。”
秦中来 接连六天守在她身边,为她请大夫,为她赶蚊子,喂她吃药,累得瘦了好几斤。红石榴却疯疯癫癫,一时哭一时笑,不住说着梦话。
秦中来 从她缠杂不清的呓语中,整理出下列“事实”——
红石榴去找郑愿,找到了;红石榴扮成郑愿的“舅舅(当然就是石榴红),住进了青州的一客栈里;那天下雷雨,红石榴和郑愿在同一个房间里换衣服,红石榴的抹胸是郑愿解开的;然后发生了男欢女爱这一类的事情;然后是郑愿又去勾引老板娘,却骗红石榴去睡觉;然后是郑愿和花深深在红石榴当面做那件事;然后是红石榴服毒自尽;然后不知道了。
秦中来的心被痛苦和愤怒塞满了,他真恨不能自己从未认识过郑愿,从未和郑愿做过朋友。
如果郑愿当时在场,秦中来 真的会和郑愿拚命。
他真的没想到,郑愿竟是这种人。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秦中来还不会苦恼到现在这个境地。
但后来偏偏出了一件事,这件事一发生,秦中来就快“万劫不复”了。
七月十七晚,红石榴好像有点清醒了,昏昏欲睡的秦中来又惊又喜。
红石榴想喝酒,于是他陪她一起喝。
那天晚上月亮很好,漫天的萤火好美好美,四周的花木散发着淡淡的酒香。
酒是女儿红。
红石榴秀雅美丽的小脸上也泛着玉一般可爱的嫣红。
她醉眼中的秋波摇得秦中来心慌意乱。
她绝口不提郑愿,他也不提,就像他们原先早就认识,是从小玩到大的伴侣。
他们谈得很开心,酒也喝了许多。
最后,红石榴醉态可掬地往桌下出溜,秦中来自然要去扶她,可红石榴浑身软得像没了骨头。
家人们都不知死到哪里去了,秦中来只得自己动手,他将红石榴刚抱起来,她已开始呕吐。
结果可想而知。
秦中来总不能让红石榴一身污秽地睡觉,偏偏家中仆妇一个也不见了。
秦中来 抱着“嫂溺叔援以手”的古训,开始收拾残局,他甚至还平生第一次下厨,亲手为红石榴烧了碗酸辣汤醒酒。
秦中来 累得满头大汗,为红石榴换衣擦洗时,更是面红耳赤,手忙脚乱,眼睛闭得紧紧的。
幸好红石榴睡得很熟,而酸辣场烧了没用。
秦中来好容易忙完了她,又开始忙着收拾桌上地下,收拾自己。
最后他用炭火将酸辣汤煨着,自己靠在椅中打吨。
四更天,红石榴醒了,口里喝着酸辣场,眼睛里渐渐溢出了泪水。
她哭了,哭得哀哀欲绝。
其后发生的事情,秦中来 事后想起来仍很糊涂,他隐隐记得当时自己冲动得厉害,发誓说他要她,他要娶她,爱护她,宠她爱她。
红石榴哭得更伤心动情,秦中来 忍不住吻了她一下。
然后事情就一发不可收拾。
秦中来充分理解了孔夫子说的“饮食男女,人之大欲也”这句话有多么正确。
如果红石榴就此清醒,秦中来 也绝对不会苦恼,他真的爱她,他不在乎她的过去。
要命的是,红石榴又糊涂了,而且很厉害,她只记得他是“秦大哥”,似乎已忘了她和他曾度过了多么美妙的一个晚上。
红石榴心心念念的,仍然是她的“大哥哥”郑愿。她很恨花深深和老板娘,但似乎并不怨恨郑愿。
她相信郑愿会离开那些狐狸精,回到她身边来,因为她肚子里有他的孩子。
秦中来看着她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简直痛苦得快发疯了。
他不相信郑愿的辩白,也不相信宋捉鬼的信.他认为红石榴肚里的孩子是郑愿的。
如果他从此对红石榴不闻不问,江湖上没人会说他不够意思,如果他只像对待朋友之妻一样对待红石榴,他也不会大痛苦。
可他真心爱她。
命中注定他要受苦。
谁叫他情有独钟?!
秦中来 很快听到街头巷尾的议论,他知道郑愿和花深深来金陵了。
秦中来知道郑愿是紫雪轩的少主人,却不知道紫雪轩的老主人是朱争而不是若若。在此之前,知道朱争隐居在紫雪轩的人实在少得可怜。
秦中来当然也猜到了郑愿和野王旗的关系。
但他不怕。
他有满腔正气,满腔热血,满身侠骨,满怀不平。
他要去找郑愿算账,为红石榴拼命。
郑愿、花深深正和朱争、南小仙等人守在若若榻边说笑,丫环进来禀报,说是金陵君子秦中来 派人送来“战表”,挑战郑愿。
郑愿的脸一下白了,花深深更是忍不住哆嗦了一下。
朱争已看出苗头不对,但什么也没说,南小仙则是满脸忧郁。
“战表”是秦中来 的书僮送来的,上面只有寥寥数语;“明夜三更。雨花台候教。秦中来。”、。
郑愿将“战表”纳入袖中,对书僮微笑着:“请回复秦公子,就说故友郑愿,谨候指教。”
一石激起千层浪,金陵武林顿时沸腾了。当天下午,秦中来 挑战郑愿的消息已传遍金陵。到晚上时,消息已到苏州、淮阴,芜湖。
正在淮阴的宋捉鬼吃惊得要命。
呆了半晌,宋捉鬼将手头的“捉鬼”活计抛下,抢匹快马,沿运河岸而下冲向金陵,沿途每逢快马,抢了就走。当然,每次都会仍下一张大额银票。
宋捉鬼一面打马疾驰,一面在心里大骂秦中来和郑愿。
在宋捉鬼看来,这两个小子都有病,都该打屁股。
好端端的四个朋友,弄得一塌糊涂,宋捉鬼真恨不能将秦中来 和郑愿捆起来,丢进运河里喂王八。
他只希望胯下马再跑快一点,他一定要赶到金陵,制止这场可笑又可悲的决斗。
拚了老命也要去。
小季自然也听到了决斗的消息。
但小季并不激动。
一场决斗早已定了胜负生死,就一点看头都没有。
秦中来 的武功虽然在江南很有名,但由于秦中来 为人端谨古板,武功也循规蹈矩,老气横秋。
秦中来不可能是郑愿的对手,若分胜负,负的必是秦中来;若论生死,死的绝不会是郑愿。
但小季已决定去看这场决斗,而且一定要瞪大了眼睛仔细看,从头看到尾,不遗漏任何细节。
小季知道凭自己现在的武功,根本不是郑愿的对手,他必须苦练,然后把握机会,才有可能一击成功。
所以他要去看一看郑愿的武功。
他要知己知彼。
那个阴郁的少年在客栈登记的名字是“芦中人”,籍贯是浙江昌化。
至于他是不是真的叫芦中人,是不是昌化人,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芦中人就坐在紫雪轩对面的一家酒楼里,安安静静地饮着酒。
他已换了身好一点的衣裳,神情也不那么忧郁了,他甚至还有钱点了几个不太贵的下酒菜,叫了两角善酿。
他的座位就靠着窗口,窗口正对着紫雪轩的大门。
芦中人的目光,根本没朝窗外看。
现在是正午,离晚上的决斗还有六个时辰,他根本不必着急。
焉知这酒楼上没有“郑愿的人”在监视他呢?
芦中人不知道给他纸条的人是谁,但他知道人家给他纸条不是为了帮助他,而是希望他帮忙杀郑愿。
芦中人知道紫雪轩是野王旗的禁地,也知道郑愿曾是紫雪轩的“少主”,所以他在金陵的活动一直很小心。
芦中人两角酒刚喝了一半,楼下忽然走上一位老婆婆,看样子很像街角摆地摊卖稀饭的穷婆子,衣裳既破且烂,脸色又青又黄,皱纹深得像刀刻的一般,头发也全白了。
她的腰都已直不起来了。
这老婆婆上了楼,所有的酒客都转头看她,几乎所有的酒客都皱起了眉头。
小二一迭声地叫着“下来下来”跑上楼来,红着脸怒道:‘’哪个叫你上楼的?”
老婆婆咳嗽看着,慢吞吞地道:“肚子,肚子叫我上楼来的。”
她的肚子里果然发出咕咕的叫声,众酒客皱着的眉头,已舒展了不少——
这老婆婆人虽穷,倒是挺诙谐的。
小二更气了:“你肚子饿,楼下有稀饭馍馍,你上楼来干什么?楼上是雅座,有钱的爷们才能上来。”
老婆婆还是不紧不慢地道:“你倒像个爷们,你有钱吗?你怎么也上来了?”
众酒客已开始哄笑。
小二想打她又怕出人命,想不动手又忍不住火,一时厦僵在那里,满脸涨得血红。
老婆婆颤巍巍地摸出一个铜子儿,晃了晃道:“我也有钱。”
芦中人忍不住微微一笑,起身相邀:“老人家请这边坐、”
老婆婆歪着头瞧着他,笑道:“你请客。”
芦中人道:“当然。”
小二悻悻。
秦中来将决斗的事瞒得很紧,严令家人不得向红石榴透露半点风声。
红石榴即将临盆,他不想让她受到刺激。
秦中来 并非不知道郑愿武功高过自己,但他认为相差有限。
更重要的是,他是为正义而战,为情而战,而郑愿理不直气不壮,必然心虚。
所以秦中来 对今晚“雨花之役”很有信心。
因为他有一腔浩然正气,而郑愿没有。
秦中来并不想要郑愿的命,他们毕竟还是朋友,他只不过希望能迫使郑愿对红石榴负起负应的责任。
就算他战败,乃至身死,他也必须去。他甚至希望能以自己的鲜血,唤醒故友身上已泯灭多时的良知,告诉人们世间仍有真情在。
为了避免面对红石榴,也为了在决斗前放松自己,秦中来悄然离家,躲在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静静地培养他的浩然之气。
正午时分,宋捉鬼快马已过扬州,正飞弛在去仪征的大道上。
一夜奔波,不眠不休,不吃不喝,宋捉鬼自己已很像是个活鬼了。
他还是嫌马跑得太慢。
朱争追着问郑愿到底为什么决斗。他虽然知道自己的徒弟绝对不会败,但决斗总要有理由。
没有理由的决斗,不可能发生;理由不充足的决斗,就是轻率;理不直的决斗,就是闹剧,会让人着笑话。
而且朱争一向听说郑愿和秦中来是好朋友,秦中来又是个志诚君子,如果秦中来认为郑愿该杀,那么郑愿或许真有该被杀的理由。
花深深知道原因,但郑愿不说,她不想多口,南小仙更是心里有数,而且绝对不愿这么早说出来。
郑愿只是轻飘飘地说了一句“是误会”,就什么也不肯再说了。
朱争气得把桌子拍得山响:“误会?什么误会?朋友之间有什么误会,尽可敞开来说个明白,为什么要决斗?”
郑愿苦笑。
“说话!”朱争又拍了一个桌子,那张可怜的梨花桌子绝不起拍,忽喇喇散了架。
郑愿叹道:“我没有错。”
朱争冷笑道:“你没有错?你没有错人家怎么要向你挑战?难道是他错了?”
郑愿道;“认真说来,他也没有错,但他对我有一点点误会。”
朱争笑得更冷:“一点点?一点点是多少?一点点误会就要拚命?”
郑愿道:“不会流血,也不会拚命,我准备尽量解释清楚。”
朱争瞪着他,忽压低声音吼道:“是因为女入?”
郑愿的睑刷地一下红了:“是。”
朱争嘿嘿笑道:“有出息!你真是我的好徒弟,真给我露脸!”
郑愿红着睑道:“我问心无愧!”
南小仙不失时机地盈盈跪倒,娓娓动听地将红石榴的事情说了一遍,她说的都是真话,连青州客栈中发生的根秘密的事情也没有遗漏。
花深深气得脸儿惨白,发现郑愿这小子没说真话,时时在哄她骗她。
她一定要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地和他算这笔账。
南小仙那种娇羞的神态,郑愿面上的尴尬,都令花深深愤怒,她饶不了他。
然而,南小仙并没有把红石榴现在情形说出来。
因为她还是想“欣赏”一下郑愿和秦中来的决斗。自己安排好的棋子不走,岂非是自己打自己的脸。
朱争听完了,愣了半响,丢了句“不许伤着人家”,扭头走了
像这种为女人打架的事,天王老子都管不了。
芦中人虽然并不富裕,但待客却很慷慨,他居然叫小二又上了八个菜,四角酒,“孝敬”那个说话呛人的老婆婆。
老婆婆金刀大马地坐着,好像芦中人天生就该请她喝酒似的,当仁不让,来者不拒。
芦中人看看自己不多的“钱”流水似地跑进她嘴里,心里很诧异,当老婆婆吃完八个菜,又抱起一角酒开始痛饮时,芦中人忍不住问道;
“够不够?”
老婆婆咽下一大口酒,笑道:‘’勉勉强强。”
芦中人道:“你真能吃。”
他并没有要讽刺她的意思。他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像她那个年纪还这么能吃的人,实在没几个。
老婆婆用很低很低的声音,慢悠悠地说道;“一个人吃饱了,喝足了,剩下的事情就是蒙头睡上一觉,也就想不起来去算计别人了。我说的话你懂不懂?”
芦中人忍不住轻轻哆嗦了一下,眼中冷光一闪而过。
她是谁?
她怎么知道他要算计别人?
她说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从这老婆婆一上楼,芦中人就明白她不是普通的老婆婆,若非有强键的身体,她不可能穿过小二们的防线,从门口跑到楼上来。
芦中人请她喝酒,并没有什么深意。芦中人在街上。
路边看到年老的妇人时,一向心怀怜悯。
这个老婆婆究竟想干什么呢?
芦中人的右手慢慢地、不被人察觉地从桌上收回腰间,他浑身每一块肌肉都涨满了勃勃的活力。
杀机已生。
如果这个老婆婆是“郑愿那边的人”,他将不惜出手一剑。
老婆婆轻轻叹道;“你在哪一家挂牌?”
旁人听见这句话,一定会一头露水。只有名优红妓才有“挂牌”一说。她这么问芦中人,好像很有点污辱他的意思。
如果老婆婆说任何其它一句话,芦中人都不会吃惊,若是“好话”,他大可一笑而去,竟是恶意,他一定拔剑相向。
他万万没料到,她说的竟然是一句“行话”。
不是这一行当中的人,绝对听不懂的行话。
芦中人尽量不让自己显出吃惊的表情,淡淡地道: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既然是同行,她就不可能来坏他的事,这是规矩,是这个行当里人人都知道的,而且,她若想坏他的事,大可不必明说出来。
再说了,除非郑愿那边的人已经知道了他的身份而请这老婆婆来的,否则地没理由于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情。
他说“不懂”她的话,是在告诫她不要胡来。
但他仍有点奇怪、他从未听说过本行当中有这样一位老妇人,难道她是某个人易了容。
如果是,她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
老婆婆摇摇头,自言自语地呼叨起来:“唉,我可真是老糊涂了,这里是金陵,你当然是扬州那一家的,而且绝对是前三号的牌子。我早该想起来才是,真是的,真是的......”
芦中人心在往下沉。
她知道得真不少。她每一句都说对了。他的确从扬州来,也的确是“那一家”前三号的“牌子”。
芦中人用阴冷的声音缓缓道:“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听不懂你的话。我不想再多听一个字,我也希望你不要再多说一个字。”
他说了四句话,这四句话的意思是:
——你是哪一家的我不清楚,我从未听说过有你这号人物。
——你违反了规矩,但我不想深究。
——我要走了,我的事不允许你插手。
――如果你胆敢泄露我的身份,坏了我的事,我饶不了你。
芦中人说完这四句话,就慢慢站了起来。
老婆婆嘟嚷道;“年轻人火气就是大,我老婆子还不是为你好,有心想帮你一个忙?”
芦中人冷冷道:“我从来不帮别人的忙,也不让别人帮我的忙。”
他缓缓离开桌子,缓缓走向楼梯、他浑身每一块肌肉都已被警觉调动了活力,他的精神和体力足以应付来自任何地方的突袭。
小季随着刑堂堂主杨雪楼及总舵的二十多名高手已经出发,
他们的任务是维持秩序,以便使决斗顺利进行。
这是韦松涛的命令。
至于韦松涛为什么要下这样的命令,绿林盟总舵的首脑们都有数——
韦松涛也接到了命令。
杨雪楼伤已痊愈,鼻尖上的青记又已开始油光发亮。
这个人就像是铁打的,受了那么重的伤,居然这么快就恢复了。
小季跟在杨雪楼身后,心里在默默算计着自己要如何出手,才能一招杀掉杨雪楼。
小季最近几年一直在琢磨如何杀人。他对自己遇到的任何人,都要这么算计一下,直到他有把握在心里把这个人“杀掉”,他才会换一个算计对象。
他对自己这种特殊的自我训练十分得意。他发现自己“杀人”的本领已越来越高,高到他已看不起绿林盟绝大多数高手的地步。
他早已算计过韦松涛。这位绿林盟的大盟主只经过他半个月的算计,在他心中就已成了一个“死人”。
他现在正算计杨雪楼。对这位新任刑堂堂主。他感到想“杀死”实在不容易。
在心中“杀人”经验一多,小季的眼力已十分老练。
江湖上的一流好手在他心里,值不得半天算计。就连威名赫赫的绿林盟主,也只花了他半个月时间。
可小季本能地感觉到,杨雪楼比韦松涛更难“杀”,甚至比鲍孝还难“杀”。
小季“杀”鲍孝,用了二十六天时间。
小季已算计杨雪楼十一天了,居然还一点头绪也没想出来。
小季这么刻苦训练自己,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杀掉毁了季家的那个,现在他已知道那个人是郑愿。
谁会想到,绿林盟主韦松涛身边的小踉班,一个诚实质朴的小伙子,心里一直在“杀人”呢?
如果那些“被杀”的人知道了,心里又会是什么感受呢?
杨雪楼突然心里一悸,后背顿时耸起了鸡皮疙瘩,麻酥酥的。
那是背后有了危险时才会有的警觉。
那是高手对带有敌意的杀气的反应。
杨雪楼没有回头,连脚步也没丝毫停滞,他用不着回头,也知道这杀气来自何人。
只可能是小季!只有小季走在他背后。
杨雪楼马上就想到了一个问题——这个小季为什么要杀自己。
小季奉了谁的密令。
杨雪楼决不动声色,诱使小季出手。
他并不知道小季不可能出手。
如果他知道小季这么做,只不过是在训练如何杀人时,他又会怎么想?
四月十五的黄昏,温暖、柔和、美丽,随处都是诗情画意。
黄昏的金陵城庄严、华丽,气象万干。
宋捉鬼过了长江,他终于看见金陵城了。
宋捉鬼跳进江水里,痛痛快快地穿着衣裳“洗了个澡”,让奔流冰凉的江水冲去他浑身的灰土汗污和浑身的酸痛。
然后地跃出水面,落到岸上,就那么湿淋淋地大步往金陵城里走去,他甚至还在路边的小饭馆里打了二斤酒,切了半只狗腿,边走边吃。
他知道急也没有用,好在他总算赶到了,郑愿和秦中来的决斗就很有可能打不起来。他只要在三更天赶到雨花台就行了,在此之前,任何举动都徒劳无益。
就算他再能耐,他也不可能现在找到秦中来。像秦中来这样的“地头蛇”,现在一定已躲在一个极其难找的地方安静去了。
而如果他事先找不到秦中来的话,决斗就不可能避免。
找郑愿是没有用的。
宋捉鬼对金陵虽不陌生,却也不很熟,他的大半捉鬼生意是在中原和西北做的,偶尔有机会到江南~行,也都是来去匆匆。
他到金陵来过两次,第一次是捉鬼来的,第二次也是捉鬼来的,只是两次的鬼不一样,其中第二个鬼,后来就成了他的好朋友。
这个鬼就是郑愿。
那是在六年前,宋捉鬼应江南大名捕苏州字文备邀请,去苏州帮忙查一件案子。
这件案子说复杂也不复杂,说困难还是真困难,案情是这样的——
杭州大绸缎商米暄晖带着管家米资和儿子米金宝来苏州进货,住在一家大客栈里。三天后,货已办齐,米暄晖准备第二天一早开船回家,当天晚上,父子主仆数人喝了点酒,就早早安歇了。第二天一大早,米贵来叫主人父子起床,却发现米暄晖已被人杀死,米金宝也昏迷不醒,但没有受伤。
就这么一件案子,字文备查了三个月,一点头绪也没有。恰巧有一日听人说起南阳有个宋捉鬼,很有两把刷子,便辗转托人将宋捉鬼请来帮忙。
宋捉鬼查阅了案卷,发现米暄晖身上的伤口很奇特,本想开棺验尸,但时隔三月,尸体已开始腐烂,也就算了,只叫来了件作细问。
“米暄晖身上的伤口很小,也很浅,虽说中在腹部,但按理说一个半寸深的小伤口不可能致命。但打开腹腔察看,才知道米暄晖内脏已全都粉碎,一塌糊涂。”
这就是仵作的报告。
那积年老仵作说完后忍不住又加
了几句:“他是被人用阴力震死的。但老朽想不出苏州地界谁有这么浑厚的阴柔内功,也想不出江南有谁能用刀尖发出如此惊人的震力,…,这个凶手简直……简直不像人。”
宋捉鬼又问米金宝的情况。米金宝是被人点了穴道,中午就醒了。在此之前,没人能解开米金宝的穴道。
宋捉鬼亲自找来米金宝和米贵,反复细问米家的家世及生意往来情况,以及那几天发生的事情。
仍然没有头绪。米暄晖是个老实本分的人,他的绸缎生意承自祖业,而且并未在他手中发扬光大。米家的人都不爱惹事生非,连米家的绸缎铺子,名字都叫“贵和”。
而且米家没人会武艺,若真有仇家要杀米暄晖,犯不着请身手如此高明的杀手。
一时之间,宋捉鬼真要怀疑这世上有鬼了。就凶手的武功而言,或许比他宋捉鬼 要高出数倍不止。
天下到哪里去找这样的高手?
这样的高手怎么会杀米暄晖这种不懂武艺的生意人?
宋捉鬼当天晚上,做了一件让字文备吃惊的事,他让字文备穿上夜行农,蒙上面去杀米金宝。
宇文备居然也真的去了。结果大出字文备意料,若非宋捉鬼及时现身,字文备差点死在米金宝掌下。
米金宝的武功居然好得出奇。
宋捉鬼的桃木剑及时刺中米金宝右腕,字文备这才侥幸躲过一劫,米金宝在宋捉鬼的“捉鬼剑法”下仍然支撑了小半个时辰,这才被捉住。
然后,米金宝证实了米暄晖也是武学高手,米金宝的武功,就是米暄晖一手教的。可那天晚上“刺客”破窗而入时,他们连反抗都没来得及。
米金宝说:“他就像是鬼。”
至于那个“鬼”为什么要杀米暄晖,米金宝一口咬死说他不知道,而他隐瞒他们父子会武功的目的,却是为了避免被牵扯进武林是非里去。
米金宝的话,显然不太可信,但他很倔强,无论如何也不肯改口。
第三天晚上,“鬼”来找宋捉鬼 ,而且没让宋捉鬼知道。宋捉鬼醒来时才发现枕边有张纸,上面写着字。宋捉鬼看完,脸色铁青,一言不发,将那张纸交给宇文备,飞也似的离开了苏州。
那张纸上写着一首打油诗:
“三十年来老米,
暗为倭奴作怅。
杀之本不足惜,
何劳阁下瞎忙?_:’
天下谁最湖涂。
南阳捉鬼宋郎。”
宋捉鬼生了一肚子闷气,他发誓要找出那个“鬼”,问个明白,否则岂非被白白嘲弄了一场?
宋捉鬼一直追到了金陵,进了紫雪轩,一把揪住了郑愿的衣袖,吼道;“是不是你?”
当时的郑愿才十六岁,是个又漂亮又斯文的贵公子。
他看见宋捉鬼冲进门的时候,就开始微笑,被揪住之后,也还是在笑:“阁下莫非就是人称‘村夫’、钦封遗玄显微真人,以一柄桃木剑打遍天下的南阳捉鬼宋郎么?
宋捉鬼气得满脸铁青:“郎、郎、郎个屁!说,你为什么要捉弄我?”
宋捉鬼的粗鲁顿时引起了公愤,紫雪轩的大美人小美人一涌而上,冲宋捉鬼大骂,燕呼莺叱,宋捉鬼也听不懂她们在骂些什么。
郑愿只微微一抬手,美人儿们都愤愤住口。
郑愿微笑道:“在下郑愿。’,
宋捉鬼渐渐松开手,觉得有点惭愧了。
郑愿又道:“我就是你要找的人,只不知阁下是怎么找到我的、”
宋捉鬼喘了几口粗气,冷笑道;“从她们身上找到你的。”
他的手指向四周的众美人儿。
美人儿们先都一怔,旅即飞红了睑。
郑愿也脸红红的道:“阁下这句话…·好像……好像有点语病。”
宋捉鬼怔了一下:“语病?什么语病?”
郑愿微笑道:“阁下进来时,我并没有…·在她们身上。”
宋捉鬼回过味来,忍不住仰天大笑。
他能找到郑愿,的确是在这些大小美人帮忙——郑愿留诗时,在宋捉鬼房中也留下了一种奇异的香味,宋捉鬼就是循着这种极淡的奇香从苏州追到了紫雪轩,而宋捉鬼一进紫雪轩,就闻到这里的大小美人们身上都有这种异香。
宋捉鬼的鼻子,比狗还灵。
在宋捉鬼 的大笑声中,他们的友谊开始了。
宋捉鬼第一次来金陵捉鬼的经历,连他自己都不愿回想,一想起来就伤心。
那时候他才二十不到,可心已老起了皱纹。
现在,宋捉鬼三闯金陵,目的却不是为了捉鬼,因为他还不知道这场决斗就是由“鬼”精心策划安排的。
宋捉鬼刚进城门,没走一百步,就看见了一个由一群美人簇拥着的端坐香车的大美人。
宋捉鬼僵住。
夏小雨!
他看见的是夏小雨。
时间仿佛在倒流,宋捉鬼的血都凉了。
他第一次闯金陵捉鬼,进的就是这道城门。走的就是这条路,而且也是走了不到一百步,就看见了同样由一群美人簇拥的夏小雨。
而且夏小雨同样也是端坐在香车里,美目流盼,微微地笑着,用一只纤巧洁白的小手招呼他过去。
怎么这么巧?
宋捉鬼已长了十岁,但还是像十年前那样,满脸通红,魂不守舍地走向香车丽人。
夏小雨瞟着他,害羞似地轻轻道:“今晚有一场很精彩的决斗,你不想去看看?”
宋捉鬼道:“我就是为这而来。”
夏小雨道:“决斗定在三更,现在还早,到我那里喝杯酒再一起去,好不好?”
当然好!
宋捉鬼简直连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