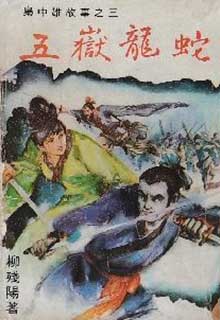月。
月笼纱。
镜一样的孤月笼在纱一样的烟雾中,月光轻得就像是情人的手,淡得就像是情人的梦。
一辆马车牵着这情人的手,拥着这情人的梦,自西而东,缓缓驶来。
车厢紧闭,就连窗户都掩上。
马两匹,人只有一个。
这个人一身白衣,一手控鞋,一手挥鞭,独坐在车厢之前,头上老大的一顶竹笠,面容尽在竹笠的阴影之下。
车声辚辚,撕破长空静寂,车轮滚滚,碾碎遍地流光。
西面是荒野,东面是山林。山林中一条小径,两旁野花杂生,披着月光,投上了满径花影。
月光凉如水,流如水,花影仿佛就幻成了水中的青苹。
周士心踏着花影,踏着青苹,徘徊水中,徘徊月下。
月照着他的剑,月照着他的手。
他的手正我在他的剑上。
每当剑在手,他的心中不由就感慨万千。
廿八年仗剑江湖,百十次浴血死战,换来他今日声名,这其中的艰辛,知道的怕就只有他手中这一只伴他已廿八年的剑了。
凭他今日的声名,若说他曾替人保镖,十个人中怕有九个不会相信。
这都是事实,今夜他的确要替人保镖,保的而且是暗镖。
能够说得动,请得起他保镖的当然不会是普通人。
普通人也根本就当不了长胜镖局总镖头。
十二载苦练的一张金背大环刀,再加上好几十处内外伤,辛奇这个长胜镖局的总镖头实在不是容易当。
辛奇的成功,声名当然还不足与周士心相提并论,长胜镖局更未在周士心眼内,但十一年前,冰天雪地中,周士心中伏负伤,十八个仇敌他奋力杀到最后的两个的时候,自己亦不支倒下,是辛奇走镖路过救了他的一命。
他并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这所以十一年后的今日,一接到辛奇求助的书信,明知是替人保镖,保的而且是暗镖,他还是昼夜赶来支援。
辛奇也不是一个挟恩求报的人,这也所以十一年来他一直没有给过周士心麻烦,到今日他可是迫不得已。
这一镖,委实太重!
整整的一大箱,无不是难得难见的珍宝。
七王爷当时得势,对于他的生日贺礼,各地的官员真还不敢草率。
准备这一份贺礼实在不容易,要将这份贺礼平安送到应天府七王爷手中似乎就更难了。
北上应天府,少不免要经过白沙坞,野云渡,赤松林,这三处向来就是绿林朋友出没的地方。
辛奇走镖那么多年,不待言心中有数。
当地的巡抚老爷似乎也知道多少,因此特别将这一份贺礼交给开业以来无往不胜的长胜镖局,还指定辛奇亲自护送。
这不由得辛奇暗暗叫苦。
长胜镖局之所以能够长胜,没有人比他更清楚,一半是凭着他那一张苦练十二载的金背大环刀,还有的一半却是由于他颇有自知之明,从来不保完全没有把握保得住的镖。
像这趟镖,他简直半分把握也没有。
绿林朋友的消息似乎灵通得很。
独行大盗花猫听说已赶程南下!
白沙坞的红娘子誓夺此镖!
野云渡的十二条龙扬言这一镖买卖非到手不可!
赤松林碧云观的道士风闻亦已倾巢而出!
这四拨人遇上任何一拨,辛奇这一趟镖都岌岌可危。
以他的行事作风,这一趟镖他是万不会接下来的,但巡抚老爷的命令可也是不容推卸!
这还是七王爷的生日贺礼!
这两个人一个都开罪不得!
巡抚老爷一向言出如山,绝无更改,他也就只好硬着头皮将这只热山芋接在手里。
他也就只有保暗镖!
保暗镖看来也不是办法,花猫、红娘子、十二条龙,碧云观的道士并不是初出茅庐的角色。
他也就只得寄望周士心。
周士心已是他最后希望!
周士心并没有令他失望!
还未到约定的时候,周士心来到约定的地方。
今夜好在有月,路旁好在有花。
缟衣步月踏花影,炯如流水涵青苹。
周士心这才领略得到苏东坡这两句诗的意境。
这未尝不是一种收获。
他似已沉醉在月中,花钟,但车马声才入耳,他的脚步便停下。
车马方近,他停下的脚步已又展开,奔出了小径。
车马一到,他立即就迎了上去。
白衣人亦立即停住了马车。
辛奇是一个彪形大汉,这个白衣人身材瘦长-------心念一动,周士心霍地收步。
“来的可是长胜镖局的车子?”他的眼中充满了疑惑。
疑惑的目光落在白衣人的面上。
他当然看不到白衣人的面庞。
白衣人并没有取下头上的竹笠,只是简短的应了一声,“是!”
“辛兄在哪儿?”
“这车内。”白衣人的语声异常的低沉。
“哦?”
“车内好说话。”
“这也是,”周士心目光一清,一转,转向车厢,“辛兄,小弟周士心来了!”
车厢内没有反应。
周士心没有在意,放步走过去。“碧云观的道士已在七里外现身,今夜看来免不了一场血战,小弟总算还来得及时!”
他说的倒也轻松,凭他的本领,的确可以不将碧云观的道士放在心上。
辛其就不同了,但车厢内竟然还是一些反应也没有。
周士心也感到有些不对劲了,三步两步走到车门之前,又一声,“辛兄。”
已然听不到辛奇答话!
周士心再不迟疑,一探手,猛地将车门拉开!
一个人连随车厢内跌了出来。
死人!
死人咬牙切齿,一面惊惧之色,双手紧握着一张黑色的帖子!
帖子上完全没有字,只是书着一双蜘蛛,白蜘蛛!
“辛兄!”周士心一声惊呼出口,剑亦出鞘。
他的反应已不能算慢,但还是慢了半分。
他的剑才出鞘,一张巨网已迎头罩下!
这张巨网也不知是用什么东西编织而成,会会白白的,轻得就像是一片浮云,一蓬烟雾,无声无息的飞来,一下子就将他笼在云中,雾中!
他一怔,剑连忙挥出。
高手的确是高手,千百道剑影刹那四方八面飞射!
剑风呼啸,剑气激荡。
这一剑的威力实在非同小可。
网若是普通的网,只怕就得被剑锋绞成粉碎!
只可惜这并不是一张普通的网。
剑未到,网已被剑风荡开,剑一收,网便又飘回!
这张网当真是一如云雾!
云雾中似乎还有一抹淡淡地红霞!
周士心并没有觉察到这一抹红霞。
又不是大白天,要非小心留意,这一抹红霞真还没有那么容易觉察得到。
网一飘回,红霞亦落到了周士心的身上。
红霞飘香。
这种香,香的来淡薄,但一经吸入,就令人心荡神旌,魂消,意消!
周士心的魂未消,意未消,心却已荡,神智已旌!
他的第二剑已准备出手,并未出手!
剑还是出手!
他在剑术的修为已到了剑在意先地步!
这一剑的威力已弱三分,还有七分!
剑风依旧呼啸,剑气已然激荡!
红霞剑风中飞散!
森寒的剑气使得周士心的心神也为之一冷,一定,一清!
他终于留意到了那飞散在剑中的红霞!
“消魂蚀骨散!”
一声惊呼,冲口而出,周士心的面色已铁!
七分威力的一剑居然未能将网荡开,剑锋已与网索相触!
网索相当坚韧,但周士心这一口剑可也不是用来切豆腐的!
七分威力已足够有余!
“嗤嗤嗤”的网索迎着剑锋纷纷断下!
剑突然收回1
周士心河横剑胸前,整个身子突然凝结在空气之中!
眼看着豆也似大的汗珠一颗颗冒出了他的额头,滚下了他的面颊,一丝丝的白烟亦从他口鼻中冒了出来!
云雾一样的那张巨网这刹那已然贴身将他罩在网中,但倏地又飞起,合成一束,一团,投入一只苍白的手中!
白衣人不知何时已下去车座,到了周士心面前1
他左手抓网右手正在解开竹笠那条在领下打结的带子。
周士心并没有合上眼睛,视线就在白衣人头上。
白衣人缓缓的取下了头上的竹笠。
周士心的目光不其而暴缩!
竹笠里面是紧裹着白巾,只露出两眼一张面庞。
这根本不能算是面庞。
这简直就像是蜘蛛的眼睛!
周士心由心寒了出来,额头上汗落更急,口鼻中烟冒更浓!
白衣人看在眼内,忽然叹了一口气,“你的功力果然深厚,凭你的功力,一时半刻,实在不能将吸收的消魂蚀骨散迫出!”
周士心没有答话,他不能答话!
一开口他凝聚的真气不难就消散!
“一时半刻,唉!”白衣人又叹了一口气,说,“只可惜,我连半刻也不会给你,不能给你!”
周士心铁青的面庞刹时苍白,忍不住喝问一声,“可是唐彪?”
“不是唐彪!”
“消魂蚀骨散乃唐门彪豹兄弟专用,唐豹早年作案为我遇上,被我剑断一手擒下,送交查七,收押应天府大牢,你不是唐彪又是哪一个?”
一口气说了这几句话,周士心的面色更难看!
白衣人不答反问,“你方才难道没有看到辛奇手中的帖子?”
“看到了又怎样?”
“帖子下有什么?”
“没有什么,”
“想清楚!”白衣人的目光更阴森,更冰冷,更诡异,更像蜘蛛!
“蜘蛛!”周士心失声叫了出来,“白蜘蛛!”
“正是白蜘蛛!”
“白蜘蛛,白蜘蛛......”周士心嘟喃自语上下的再打量眼前的白衣人,“唐豹收押在应天府大牢,我与辛奇相会在此时此次,辛奇那方面不知,我这方面,只与一个人说过,你,你......”
他第二个你字才出口,白蜘蛛右手的竹笠已出手!
呼的竹笠荡起一股旋风,车轮一样转动着飞削向周士心的咽喉!
周士心惨笑飞剑!
这一剑已不能再化千锋!
剑上的威力已只剩三成!
剑确上了竹笠的边缘!
喀唰的剑锋砍开了竹笠,直入半尺,也只能直入半尺!
竹笠的直径却尺许有余!
这一剑竟不能将竹笠斩为两半!
笠上的力道也竟比剑上的力道还大,周士心手中的剑猛然脱手,随同竹笠一旁飞旋了出去!
他脚下不其亦一个踉跄!
一道耀目的寒光,几乎同时飞到了他的胸膛!
他也看到这飞来的寒光,他也感觉到一股森冷的寒意,正袭上自己的胸膛,他也想闪避1
只可惜他已无力闪避!
白蜘蛛竹笠一飞出,手中就多了一支剑,利剑!
身形只一动,他的人已在周士心面前,寒光只一闪,他的剑已入周士心胸膛!
一剑已足够!
只一剑,白蜘蛛就将剑收回!
血,箭一样标出1
“果然是你,果然是你!”周士心嘶声狂呼,身形一晃再晃,终于到了下去!
一刹那,他苍白的面庞突然变成了朱红!
“消魂蚀骨散果然不错!”白蜘蛛凝望这周士心朱红的面庞,忽的摇了头,“你的脑袋也不错!”
“唉,最好的办法看来还是杀人灭口这个办法!”
叹息着,白蜘蛛走了过去,探手从车厢里拿出了一个包袱。
七王爷这一份生日贺礼若是一件件用盒子什么载好,的确需要一双大箱子才可以装得下,但如果盒子什么全部去掉,打一个包袱就够了。
白蜘蛛所以就只打了一个包袱,连一只盒子也没有了。
看来这一份生日贺礼他是一件也不想留给七王爷的了。
这么的一个包袱相信也不会怎样轻,但多了一个包袱,他的脚步反而变得更轻松,更从容。
脚一点,他的人就飞上了路旁一株大树的树梢!
月恰在树梢,人恰在月中。
月中的蜘蛛,白蜘蛛!
红蜡泪飘香,
烛香中还有酒香。
烛影摇红,人已微醉。
烛光还是没有灯光那么明亮,带醉的眼睛看起东西来也总是没有平时那么清楚。
珠宝玉石所以在烛光下总是比较辉煌,玉石珠宝所以在醉眼下也总是比较巨大。
有七分醉意,鸽蛋大小的一颗珍珠在眼中看来不难就变成鸡蛋一样。
孟天化的醉意还只不过四分,他的眼中已看到鸡蛋一样的一颗珍珠。
这颗珍珠本来就已有鸡蛋那么大小。
像这样的一颗珍珠,它的价值当然大得吓死人。
这不过是孟天化珍藏的七件珠宝玉石之一。
孟天化珍藏的珠宝玉石就只有七件。
这七件珠宝玉石的价值好像都不相上下。
这七件珠宝玉石如今都放在桌上。
雪白的珍珠,碧绿的翡翠,火红的玛瑙,映着烛光,醉眼中看来更见缤纷,更见瑰丽。
怪不得孟天化总是喜欢在灯光下,酒醉中欣赏这些玉石珠宝。
这的确是一种享受。
这种享受似乎是只限于有钱人。
要说到有钱人,在应天府,只怕要数到十七十八才是孟天化。
但几分醉意,烛光下独对着这七件珠宝玉石,孟天化就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好像自己已富甲天下。
这当然是一种奇妙的感觉。
孟天化下颚枕着双手的手背,猫一样伏在桌旁,人已迷离在烛光宝气之中。
只有在这时候,这地方,他的一双手才会离开腰际,其他的时候,其他的地方,他的腰际最少也按着一只手。
他的要侧左右都有一个豹皮囊,每一个豹皮囊都载着最绝,最毒的暗器。
江湖上的二十个暗器高手之中,似乎还少不了他的一份。
像他这样有钱财,有地位的一个人,当然更加珍惜自己的生命。
走江湖的人,少不免都有仇敌,他也不例外。
他一直小心防范。
他的暗器随时随地都准备出手。
只有在这时候,这地方!
这地方并不是龙潭虎穴,也没有铜墙铁壁,只不过是他寝室下得一间密室。
要找到他的寝室并不困难,要发现密室的暗门也很简单,但要瞒过庭院外他的四个心腹保镖与寝室内他的那条母老虎的耳目可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四个保镖,分成两拨,日夜逡巡在庭院之外!
河西六娘子更是一个很深闺的女人!
寝室对正庭院,密室的暗门就在床后,即使躲开当值的两个保镖,还得准备躲开河西六娘子的鸳鸯双剑1
河西六娘子的鸳鸯双剑在江湖上的名气似乎还在孟天化之上。
做丈夫的不如做妻子的本领,当然不会是滋味。
孟天化起初好像也不知道六娘子那么厉害,到他发觉娶着一个母老虎的时候就真后悔也来不及了。
其实六娘子对孟天化一点儿也不凶,相反比别的做妻子的更来得体贴,有孟天化的地方就一定见得到她。
很多人都羡慕孟天化有这么大得福气,就是孟天化的朋友也非常的佩服好像孟天化这样的一个风流人物,这几年间居然会变成了应天府知名的四大君子之一。
偏就孟天化并不见得开心。
唉,做君子,本来就不是一件轻松写意的事。
一想到君子这两个字,孟天化不由就叹息气起来。
就连叹息他也得在这密室之中。
河西六娘子似乎还放心让他独个儿留在这密室之中,她很少下来,她若是下来孟天化就酒也喝不成了。
没有酒,孟天化的兴趣就没有那么浓厚,所以一见到六娘子下来,他就像给老虎赶着的兔子一样,走也嫌慢了。
好像今日的样子实在少见。
蜡烛已烧了半截,密室外六娘子还是一点儿声息也没有。
孟天化也觉得奇怪。
六娘子一只相信酒喝多了有损身心,虽然放心让他独个儿留在密室之中,从来可不让他有大醉的时间,有大醉的机会。
这下子不知不觉他总有七分醉意了。
他已很久没有喝的这样痛快。
所以,他虽然觉得奇怪也没有去理会那许多。
这样的机会到底不是常有的。
他并不是一个不懂得利用机会的人。
他的一双手,一直都没有停过。
一杯再一杯。
酒香已浓于烛香。
酒香烛香之中忽然多了另一种香。
这种香比烛香更迷人,比酒香更醉人,香的来令人心荡神旌,魂消,意消!
宝玉,明珠,醇酒,美人,这里向来都只得三样。
孟天化一生最感遗憾的也就是这件事,但这一刹那,他却感到前所未有的满足。
这一刹那,密室之中简直就像是突然来了一个销魂蚀骨的女人。
孟天化哪能不心神旌荡?
他的目光一阵迷惑,可是一下忽又清醒过来。
他到底并没有忘记这密室之上只有一条母老虎。
果然有人来!
密室的门已打开,人正在拾级而下。
来的脚步很轻,很轻。
孟天化还是觉察得到。
一个人善用暗器,目力,听觉方面总是特别得敏锐。
他虽然觉察,却没有回头,狠狠地一下将手中的一杯酒倒入嘴里,连忙又斟上一杯,就好像这下子不喝酒没有机会再喝似地。
来人也没有作声。
孟天化斟酒的手却已开始发抖,连酒壶也仿佛拿不稳了。
莫非对于河西六娘子这条母老虎他真的是怕得要命?
香已浓,人已近。
孟天化一杯酒已斟好,但连举杯的气力似乎也没有了。
香更浓,人更近。
孟天化忍不住叹了一口气。
“你就算新买了一种花粉,也犯不着一下子用上那么多!”
话还未说完,一样东西已从他身后飘飞而来。
一张纸,只凭听觉他就分辨得出。
“唉---”他立时又叹了一口气,“这花粉好使卖的很贵,账单迟早我还是一样照付的,你何必一定要现在交给我?”
一面说一面抬手。
的确是一张纸,但不是账单,是一张帖子,黑色的帖子!
帖子上画着一双蜘蛛!
“白蜘蛛!”孟天化双瞳立时暴缩!
一声惊呼出口,黑帖突又飞起,孟天化的两手已落在腰左右的豹皮囊上,人同时转身!
一转身他就看到下来密室的那个人!
那个人已停下脚步,负手站在石级之旁,一身诡异的灰白!
白蜘蛛!
孟天化馒头冷汗直冒,大喝一声,双手暴翻!
密室中刹那寒芒飞闪!
孟天化的暗器已出手。
惊怒之下,凭他的功力,这两把暗器最少可以远击三丈!
白蜘蛛离他不过一丈!
白蜘蛛若是不闪避,这两把暗器就得将他打成肉泥!
白蜘蛛并没有闪避!
这两把暗器也并没有将他打成肉泥。
还未到白蜘蛛面前,这两把暗器就已纷纷堕地!
你信不信孟天化的暗器会如此差劲?
就连孟天化自己也难以相信!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只知道这两把暗器在出手的刹那,每一颗都好像重了好几倍!
他的面色在变!
忽然间他留意到密室中漂浮着的淡淡红霞,忽然间他省起了密室中弥漫着的阵阵异香!
“消魂蚀骨散!”他惨笑,醉红的一张脸已变成了朱红!
惨笑还留在他的唇角,白蜘蛛人已向他走来!
人与剑齐飞!
剑飞入了孟天化的胸膛!
剑锋利,剑冰冷!
孟天化浑身的热血已在凝结!
“嗤!”心深处的热血突然狂喷而出,孟天化的一个身子突然剧飞,撞在后面的墙上!
这实在是一种前所的刺激!
孟天化浑身仿佛又充满了活力,一反手,猛地抓住了墙上的一个钢环!
一阵惊心动魄的铃声随即爆发!
白蜘蛛一怔,但只是刹那,身形又展开,一闪身来到桌前,左手抖开一个布袋,右手环臂一扫,尽将桌上的七件珠宝玉石扫入袋中!
孟天化眼也红了,闷嘶一声,松开握着钢环的手,飞身扑下!
叭的他扑倒在地上!
他这哪里是扑下,简直就是倒下来的!
他倒下又爬起!
坚硬的石板撞碎了他的门牙,鲜血流出了他的口鼻!
就连他的一双手也再冒血!
十根手指在石板上擦碎,拖着十条触目的血痕,还是要向前爬去!
白蜘蛛看在眼内,他冷笑,手一按桌子,身形又飞起1
十根手指冷笑中突然僵结!
孟天化已吐了最后的一口气1
白蜘蛛这就看不到了,他根本没有再回头,掠上了石级,窜出了暗门。
密室的暗门就在房中,就在床后!
房中的异香更浓!
一个销魂蚀骨的女人下躺在床上!
河西六娘子!
六娘子的一双细细素手已在剑柄之上,鸳鸯双剑已准备出鞘。
剑到底没有出鞘!
死人毕竟是死人!
河西六娘子的鸳鸯双剑要是出鞘,这房间的东西最少得毁掉一半!
幸好她的剑还未出鞘就给裁断了咽喉,房间的东西这才落得完完整整。
房间外就是庭院。
庭院中也有死人,两个!
孟天化四个心腹保镖中的两个!
两个死人的旁边还有两个活人。
密室的铃声本来就是远达户外!
不是在今夜当值,如今还活着的其他两个保镖也应声赶到来了!
两人的目光在房门之上。
照道理这下就该破门而入,但这种事情还是破题儿第一趟!
做了孟天化的保镖那么多年,两人也还是第一次听道密室的铃声!
这实在难怪两人大感踌躇!
“老张,你看怎样?”左面的一个飕地刀已出鞘,刀已在手!
“在情在理也应该进去瞧瞧!”老张呛啷的亦自拔刀!
“好!”左面的一个连随窜出,一探手,正想将房门推开!
房门突然在里面打开!
匹练也似的一道剑光紧接从中飞出!
左面的那个不由一怔!
要命的一怔!
他一怔,再要闪避时已来不及!
剑穿心而过!
这又多了一个死人!
还有一个活人,老张!
老张的一张脸已变了颜色!
剑一吞一吐,又刺出!
白蜘蛛人剑夺门而出,飞射向老张!
剑光迅急而辉煌!
老张看来也是一个识货的人,一瞥见来势,连忙就抽身后退!
他退的已够快,但剑似乎还快!
老张也知道剑快,退着猛一个翻身,刀连随劈出!
一出手就是二十八刀!
他不求有功,只求无过!
若换是别人,他这二十八刀即使不能伤敌,也足保身!
只可惜他遇着的是白蜘蛛!
遇着白蜘蛛他就是只求无过也不成!
第二十八刀还未劈尽,白蜘蛛的剑已刺入他的眉心!
好绝的一剑,好毒的一剑!
这双白蜘蛛原来并不是完全得力消魂蚀骨散,在剑上亦有惊人的造诣!
他的轻功也不错,老张才倒下,他的人已飞越过庭院中的花树,掠上了墙头!
月已在墙头!
弯弯的,今夜的月就像是一把银钩,烂银钩!
银钩,明镜。
月缺,月圆。
月石这样的多变。
月圆的时候总比月缺的时候少,月缺的时候总是在月圆前后。
不少人将月的圆缺比喻人的离合,又岂知月缺还圆,人去未必重返,生离更不难就是死别。
落花风飞去,
故枝依旧鲜,
月缺终须有再圆,
圆,月圆人未圆,
朱颜变,
几时得重少年?
吴克齐南吕金字经的一折小令你有没有印象。
月缺还圆,年华逝水,人去即使复回,青春亦已不再。
人有情,人也会无情。
倒是月,虽然多变,还算多情。
不管是春,是夏,是秋,是冬,一任你独立在纱窗下,徘徊在空阶前,没有雨的晚上,只要你抬头,你不难就会发觉并不孤单,相陪着的还有天上的月。
唉,好一个月!
到春来梨花院落溶溶月。
到夏来舞低杨柳楼心月。
到秋来金铃犬吠梧桐月。
到冬来清复暗度梅梢月。
唉,好一个月!
可不知道,这一弯天上的银钩,这一面云中的明镜,惹出了人间多少的欢乐,多少的忧愁。
说什么,万里归心对月明,沧海月明珠有泪,说什么,更教明月照流黄,云边雁断胡天月,。。。。。。
若不是这一个月,诗人墨客那来这许多的佳句,又怎写的尽那作客的哀怨,分离的愁苦,又怎写的尽那闺妇的幽怨,边塞的凄凉......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苏东坡毕竟是妙人,谙尽此中滋味。
只是心情随人各异,感触亦自不同,残月未必令人肠断,满月亦未必令人心欢,倒是那中秋的月,酒也好,水也好,想来谁也忍不住要邀他三杯。
沈胜衣如今更就已饮下了第四杯。
他学识喝酒还是这年来的事,最初他只能喝三杯,近来却已能十杯不醉,但再添两杯,他还是非醉不可。
他清楚自己的酒量,很清楚,偏偏很多时他还是醉的一塌糊涂。
没有人强迫他,他自己强迫自己。
一个人在无聊的时候总会想起以往,他不过在设法要自己少想一些。
他也知道酒入愁肠愁更愁,他也知道酒醉还醒,愁来又依旧。
他只是无可奈何,他实在感到悲哀。
人生偏就有这许多无可奈的悲哀。
幸好他无聊的时候并不怎样多,还用不着他去制造喝酒的机会,但喝酒的机会来了,他却是从来不肯错过的。
今夜天秋月又满,岂非一个大好的喝酒机会?
月满在丹桂梢头。
丹桂正飘香。
花前,月下,小院中,酒菜一席,人却只有他一个,相伴的就只是天上的明月,地上的影子。
月既不解饮,影空随人身,他,独个儿自饮自斟。
独酒,未必无味,只是喝起来总会快上许多。
这第四杯酒他简直就是倒下去的。
不是醉,他在想起了什么?
一丝苦涩的笑意展现在他的唇边,他想起来的一定不会是快乐的事。
倏地他放下了杯,袖子里一掏,手中就多了一支短笛,半身旁边的丹桂一靠,哀哀的吹了起来。
什么时候他又学识了吹笛?
冷月凄凄,疏星耿耿,良宵院落沉沉,秋风败叶萧萧。。。。。。
原来是悲秋的曲调,怪不得这般的苍凉,又这般的幽怨。
笛声缭绕,突然一下子飘上了树梢,票入了云霄!
一道闪光几乎同时击在树干之上!
雪亮,精巧,好一把柳叶飞刀!
刀身一指宽阔,三寸短长,一击中树干就齐柄没入,力道真还不小!
沈胜衣幸好在这刹那之间,拔身飞上了树上。
他似乎只不过一时兴起,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笛声也并没有丝毫异样。
他这一拔身差不多有两丈高下,那儿正好分出一条横枝,他也正好坐落横枝之上。
这条横枝又似乎并不好坐,连随他又拔了起来。
横枝之上亦几乎同时钉入了两把一式一样的柳叶飞刀,原来真的是不好坐得。
这一次难道他仍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笛声飘得更高,更远。
笛声忽的变得出奇的婉转。
半空中沈胜衣一连竟翻了三个筋斗。
这三个筋斗实在翻得恰到好处!
四,三,二,九把柳叶飞刀间不容发的先后掠过他的双肩,两颊,腰肋,胸腹,咽喉!
不成这又是巧合?
刀飞,叶飞,人飞!
刀落,叶落,人落!
落叶舞秋风,才着地又被风吹去。
人却并没有被风吹走,飘落在一丛百日红之前。
叶还绿,花还红,但花叶都已开始憔悴。
人无千日好,花又何来百日红?
笛声始终不绝。
笛声吹入了花丛。
拔刺的花丛突然左右分开,当中飞出一簇鲜艳以及的红花!
花没有这么大朵,是人!
一个很年轻的红衣姑娘。
姑娘的手中一把柳叶飞刀!
刀光雪亮,刀锋锐利,刀光一闪,刀锋就已迎头劈下!
这一刀劈实,沈胜衣的脑袋不难一个变成两个。
沈胜衣的脑袋还是只得一个。
刀锋未到,笛声已转,他身形亦自一变,人已在刀锋之外!
到落空又挑起,姑娘冷笑,左手忽的多了一把长只尺许的柳叶短刀,左右双飞,两刀齐舞,舞得就像是蝴蝶的一双翅膀,院子中立时就像是多了一双大红蝴蝶,还有一只白蝴蝶!
沈胜衣迎着刀光飞舞,也变成了蝴蝶,白蝴蝶!
居然还有笛声!
笛声好像已没有那么婉转。
红衣姑娘的柳叶飞刀,到底也是出自名师的!
刀势越来越凌厉i!
笛声开始断断续续!
刀势更急!
笛声突断!
沈胜衣的一支短笛已在刀光中断成了两截,他左右手各执一截断笛,苦笑了一下,“好在我扬长避短手急眼快,一个人想学的潇洒一点儿,原来也是不容易的。”
话才说的一半,红衣姑娘的柳叶双刀已左七右五砍出了十二刀!
刀快,沈胜衣的身形更快!
最后的一个“的”字出口,十二刀他已避开了十刀,左右手猛一翻,两截断笛齐飞,飞入了云中,飞入了月中,人连随闪身,迎向红衣姑娘左手的第七刀,右手的第五刀!
刀光闪电,人亦如电闪!
人闪入刀光,刀光一下子突然消散!
沈胜衣空着的两手只一拍,铮的就将红衣姑娘的长短柳叶刀拍在双掌之中,挟在双掌之中!
这判断的准确,这出手的迅速,未免太惊人!
红衣姑娘也大大的吃了一惊,连忙就旋身抽刀!
她这一抽刀才发现沈胜衣的双掌简直就像是两块钢板一样!
沈胜衣也正在旋身!
两下的肩膀,不其而碰在一起,挨在一起了!
姑娘连脸也红了,红得就像是一个熟透了的大红苹果。
这样的一个大红苹果,你若是男人,你想不想咬上一口?
相隔那么近,就咬上一口看来也不是一件难事。
沈胜衣总算还老实,他只在笑,但笑得就像个贼!
姑娘的脸更红了,她瞪着沈胜衣,看样子就要生气。
哪知道噗嗤的她忽然笑了出来。
她人本来就已经够漂亮,再这么一笑,更不得了。
沈胜衣一时间也为之一怔。
姑娘乘机抽刀!
刀动也不一动!
沈胜衣的双掌已然好比钢铁两块!
这小子似乎还不是一个好色之徒。
姑娘只有叹口气,“看来,你真的是沈胜衣!”
“本来就是沈胜衣,你呢?”
“箫玲!”
“箫玲?这个名字,我好像还是第一次听到!”
“我们这也是第一次见面。”
那么说我们之间应该没有仇恨。”
“事实没有。”
“这到怪了,我就想不出还有什么原因你要狠狠地尚我十二把柳叶飞刀!”
“我只不过想证明一下你到底是不是那个沈胜衣......”
“那个?据我所知沈胜衣向来都是只有一个!”
“就只你这个!”
“你总算知道了。”
“但事前我实在不能肯定。”
“所以你就用飞刀来证明一下?”
“只有这个办法,你要不是沈胜衣也没有那么容易接下我那十二柄飞刀!”
“幸好我是沈胜衣!”
“你就不是也不打紧,我那十二把飞刀是留有分寸的!”
“哦?”
“这柳叶双刀就没有了!”姑娘的目光落在沈胜衣双掌之上。
沈胜衣微微一笑,终于松开了双掌,他似乎看得出箫玲并没有恶意。
箫玲的确没有恶意,沈胜衣松开了双掌她也就只是将刀收回。
两人的肩膀还在挨着。
箫玲似乎突然醒悟,又再红了脸,连忙跳了开去。
沈胜衣却是面不改容,“你害怕什么,我才不过十五天没有洗澡。”
“你说多少天?”箫玲吃惊的,望着沈胜衣。
“十五天!”
“真的?”
“假的!”
“你这个人原来并不老实!”
“什么?来找我之前难道你还没有弄清楚我是怎样的一个人?”
“谁说没有?”
“那么对于我你到底知道多少?”沈胜衣微笑问道。
“不多不少。”
“哦。”
“你曾经战平手祖惊虹,先后还击败了金丝燕,柳媚儿,雪衣娘,满天星,拥剑公子!”
“这已经是陈年旧事了,连我也快要忘掉了。”
“那么说最近。。。。。。”
“最近又怎样?”
“西溪一战,你一举歼灭了江湖知名的十三杀手!”
“一举?我的武功,好像还没有那么的厉害。”
“不管怎么样,十三杀手到底是毁在你的手上!”
沈胜衣一笑,没有再分辨。
“十三杀手出了名的手辣心狠,阴险狡猾,却全都不是你的对手,那么你的武功如何,机智如何,更就不必说了。”
“人也是的!”
“你这个人没有什么不好,”箫玲撇了撇嘴,“偏就是嘴巴不老实!”
沈胜衣又怔住,可不是因为箫玲的说话,而只是因为箫玲的神情。
箫玲的武功倒也不错,却一点江湖气也没有,有的只是一份女孩的娇态,纯真,像这样的一个女孩子实在不适宜单独在江湖上行走,就即使她的师长认为她的武功已足够应付,也绝不会放心,就这样让她在江湖上单独闯荡。
但像这样的一个女孩子居然就这样昼夜单独找到来,这到底又为了什么?
沈胜衣实在奇怪,正想问,箫玲已接下去这样说,“其实你也是的,你这个人要是不好,也不会跟十三杀手作对,所以我今夜就这样一个人来找你也不害怕。”
沈胜衣笑了,“你来找我莫非就是只为了试试我的武功,看看我是怎样的一个人,说说仰慕的说话?”
“才不是!”
“那到底为了什么?”
“江湖上最近发生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相信就是我决斗十三杀手于西溪!”
“你这个人原来连谦虚也不懂得的。”
“谦虚无疑是一种美德,但同样也是一种虚伪。”
“你讨厌虚伪?”
沈胜衣点头,“虚伪就是一张假面具,我是不会再戴上任何的假面具的了。”
“这是说你过去......”
“别问我过去。”
“那么第二件呢?”
“你说。”
“你不知?”
“知的话我不会叫你说。”
“。。。。。”箫玲一阵子沉默,眉宇间一下子忽的添上一抹忧愁,“应天府一带最近出现了一个独行大盗!”
“花猫?”
“跟这个人比起来,花猫简直就成了娃娃了!”
“哦?”
“花猫很少伤人,更少杀人,这个人一来就犯了十七件劫案,要了六十四条人命!”
“十七件劫案,六十四条人命!”
这到底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沈胜衣亦为之大吃一惊,“既然称得上江湖大事,这死去的六十四人,定必不是无名小卒的!”
“周士心,辛奇,孟天化,河西六娘子等人好像都不是籍籍无名之辈。”
沈胜衣面色微变,“你是说一剑千锋周士心,鸳鸯双绝河西六娘子,长胜镖局的辛奇,名列江湖二十暗器高手中的孟天化。”
“你也认识这些人?”
“不认识,只是听说过。”
“连你也有印象,这些人在江湖上看来也有相当分量。”
“那十七件劫案的损失,份量只怕就更惊人了。”
箫玲点头,“单是周士心辛奇保镖的七王爷一份生日贺礼已经价值不菲!”
“周士心似乎不是做保镖的。”
“他不是,辛奇是。”
“这有什么关系?”
“他跟辛奇就正如群七跟他一样,是生死之交,辛奇保不住的镖,他不会袖手旁观,就正如他一出事,群七虽然已退休多年,也立即重做冯妇一样。”
“群七?”沈胜衣稍作沉吟,“是不是人称天下第一捕头的那个群七?”
“恩!”
“这当差的听说实在有几下子,他出面事情相信就简单得多了。”
“周士心辛奇失镖丧命是这十七件劫案的第一件!”
沈胜衣又是一怔。
第一件劫案发生群七就出马,事情如果这就变得简单又怎会再来十六件?
“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
“六月十五,如今已是八月十五!”
“才不过两个月,盛名之下无虚士,破案在群七来说,也只是迟早问题。”
“不能再迟了,再来一个月,群七如果还未破案,他这个总捕头固然当不下去,我哥哥的一顶乌纱帽亦同样难保!”
“怎么?”沈胜衣惊讶的望着箫玲,“你哥哥是做官的?”
“是呀。”箫玲点头,“他就是应天府的巡按箫放。”
“怪不得,我看来看去,都不像是个走江湖的,原来是官府人家的小姐。”沈胜衣摸鼻子,忽然说道,“巡按这个官职好像不小了。”
“比起七王爷来还是小得多,别说三月,就即使他限期三天,我这个巡按哥哥,也应命。”
“幸好他限期三个月。”
“已过了两个月。”
“还有一个月。”
“一个月还没有两个月那么难过,在过去的两个月,群七一点儿头绪也没有,接下来的这一个月,实在令人担心。”
“我哥哥这下子想必很着急。”
“简直就不思茶饭。”
“好啊!”沈胜衣忽然瞪起眼睛,“做哥哥的不思茶饭,你这个做妹妹的居然还有心情来寻我开心?”
“那里是了,我来找你,正就是要替他分忧嘛。”
“你以为我就是那个独行大盗?”
“我没有这样说。”
“这到怪了,我就想不出你找我怎会替你的哥哥分忧。”
“江湖上最近发生了两件大事。”
“你都说过了。”
“这两件事下来,江湖上就多了一个大盗,一个大侠!”
“我就是那个大侠!”沈胜衣几乎没有挺起胸膛。
箫玲不由得噗嗤一笑,“我没有说你不是,你用不着那么大声的。”
沈胜衣也笑了,他并非真的那么自负,他只不过在将说话简化,尽可能减少废话。
废话有多种,客套的说话,正是其中的一种。
奇怪的是明知废话,还是有那么多人喜欢说。
沈胜衣总算例外。
箫玲似乎就不是了,接下去就这样说,“大侠至今未逢敌手。。。。。”
“唉----”沈胜衣好不失望。
“大盗至今亦是逍遥法外!”
沈胜衣再听这一句,连随又收住了那一声叹息。
“偏就是这样凑巧,大侠大盗差不多同一时扬名江湖,这所以很多人都希望大侠大盗有碰在一起的一天,这所以不少人都认为只有大侠才能对付大盗,这所以我来找你!”
“哦------”沈胜衣这才明白,挺起的胸膛似乎就要缩回去。
“这你说,我来找你是不是就等如替我哥哥分忧?”
“恩。。。。。”
“那你答应了?”
“答应什么?”
“到应天府去对付那个大盗!”
“......。”沈胜衣没有作声。
“你不答应?”箫玲急着追问。
“我想不出有什么理由要答应。”
“你是大侠!”
“大侠好像不是捉小偷的。”
“他不是小偷,是大贼,是强盗,你理应锄强扶弱!”
“巡按老爷也算得弱者?”
“就不算,其他的人呢?”
“你当我是会舍己为人的那种人?”
“本来你就是的,要不,你怎会去挑战十三杀手?”
沈胜衣闭嘴。
“这个大盗相信还没有十三杀手那么难应付。”
“未必!”
“未必?原来你害怕。”
“到今时今日为止,我好想还未知道有所谓害怕。”
“这-----”箫玲眼珠子一转,“我明白了,你挑战十三杀手是为了求名,如今名有了你就不再冒险。”
沈胜衣笑了,“你这种激将之法倒也高明,只可惜找错对象。”
箫玲怔住在那里。
沈胜衣只是笑。
好半晌,箫玲无可奈何的叹了口气,“你是决定不答应的了?”
“我想不答应,偏偏又想不出什么理由不答应。”
“你......。”
“反正在这里闷得发慌,闲得无聊,到别处走走也是好的。”
“那你要多少酬劳?”箫玲高兴地几乎没有去牵着沈胜衣的手。
沈胜衣却突然一正面色,“我答应是因为我喜欢冒险,并不是为了酬劳!”
箫玲又怔住,一脸的抱歉。
“我也只不过对这些劫案,对这个大盗,发生兴趣,并非对你那个巡按哥哥,发生兴趣的。”
“怎也好,你去就成了!”
“哈,你当我什么,赛诸葛还是。。。。。。”
“我只知道你是沈胜衣,也只当你是沈胜衣。”
“有意思!”沈胜衣好像是想起什么,随即问,“大侠叫做沈胜衣,大盗又是那一个?”
“不清楚。”箫玲摇摇头,“他从来不留活口!”
“心狠手辣,好一个大盗!”
“不过每一次劫案发生,现场当眼地方总发现一张上面画着一双白蜘蛛的黑帖,人们因此就称呼他白蜘蛛!”
“白蜘蛛?”沈胜衣稍作沉吟,“江湖上称龙称虎的人最少有二三百,蛇猫同样大有人在,蜘蛛似乎就只是这一个只。”
“一只就够了。”
“杀人这双蜘蛛用什么?”
“群七说是剑!”
“凭他的经验,相信绝不会判断错误!”沈胜衣目眺闪动,“周士心,河西六娘子都是用剑的高手,这只蜘蛛的确不简单。”
“你是说剑术方面?”
“嗯。。。。。。”
“这倒不一定,根据群七的报告,周士心,河西六娘子都曾中毒在先,其他的人也大多数是。”
“可知是那一种毒?”
“消魂蚀骨散!”
“群七敢肯定?”
“敢,这也不单是他个人的意见,据讲不少有经验的江湖朋友在看过尸体之后,异口同声都是这样说!”
“消魂蚀骨散,风闻乃是唐门彪豹兄弟专用!”
“唐豹三年前作案,遇着周士心,被周士心断去一臂擒下,送交群七收押在应府大牢中!”
“唐彪呢?”
“箫玲道,在唐豹入狱同时,唐彪就宣布失踪了!”
“唐彪唐豹是兄弟,三年前唐豹为周士心伤擒,唐彪失踪,三年后的今日,白蜘蛛出现,周士心第一个失镖丧命,迹象所显示,是中毒在先,这种毒就是唐门彪豹兄弟专用的消魂蚀骨散,很可能,这就是唐彪的报复行动,这只白蜘蛛也就是唐彪。”
“很可能。”
“但未必一定。”沈胜衣又笑,“对这个大盗我越来越感兴趣了,嗯,你要我什么时候出发?”
当然越快越好!
“现在呢!”
“现在?”你家里。。。。。
“这地方是租来的,这个月应付的我都已付清!”沈胜衣面上一片落寞,“我没有家,我也只是一个!”
一阵难言的苍凉的感觉不其而袭上箫玲的心头她想说什么,可是什么也说不出来。
“月也赏过了,酒也喝过了,这时不走,又待何时?”
“你......”
“我怎样?”
“很爽快!”
“亦即是不拖泥带水?”
“嗯......”
“不拖泥带水,就不会去做藕断丝连的事情?”
“你这是什么意思?”
“沈胜衣不答,漫声轻唱-----”
藕断丝不断,月圆人未圆,
月圆时枉把离肠断,
半天儿风韵愁千里,
一弄儿秋声闷几般,
难相见,
和愁和闷,经岁经年......
天上人间,当然再难相见,和愁和闷,也的确已经岁经年。
箫玲菁菁的听着,怔怔的望着。
她实在难明。
她又怎知道沈胜衣内心的感触?
歌声才歇,沈胜衣倏地回头问,“我的歌喉怎样?”
箫玲如梦初醒,还是怔怔的望着沈胜衣。
沈胜衣再问,“好不好?”
“箫玲在犹豫。
“你这个人原来并不......”
他话口未完,箫玲已大声叫了出来,“不好!”
沈胜衣大笑,“这才像是个年青人,要是连年青人都不敢率直说话,这世上只怕就更难听到率直的说话了。”
箫玲娇魇微红,“其实你的歌声也并不难听,只不过我才听过小凤仙不久,她唱得实在太好,比起来你就变得不好了。”
“有这种事,?”沈胜衣有点不服气似地,“这小凤仙又是什么东西?”
“她不是东西,她是人。”箫玲娇笑,“她一直在应天府的第一楼卖唱,一到了应天府,我就先带你去听听她。”
“我好像不是为了听这小凤仙而去应天府的。”
“我知,但这些日子以来,群七早晚都泡在第一楼的酒缸里,你要见他就只有到第一楼去。”
“我一定要先见他?”
“没办法,对于这些劫案相信没有人比他知道的更多,限期只剩一个月,你已没有足够的时间从头再来再做调查的工夫。”
“这也是,我做事向来就喜欢选择简单而有效的办法,这未尝不是一种简单而有效的办法,再其次,看看这天下第一捕是怎样的一个人亦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你以为他是怎样子的一个人?”
沈胜衣想了一下,笑道,“听说早在二十年前这小子就已经在衙门当差,这下子年纪想必已有好大一把,做这种既伤脑筋又卖气力的工作的人大概总不会胖到哪里去,再给这只白蜘蛛一气,酒缸里一泡,你这样问起,我就好像突然看到了一只干瘪了的湿水老蟑螂。”
“干瘪了的湿水老蟑螂。”箫玲皱了皱鼻子,噗哧的又笑了出来。
“你笑?难道不是?”
“当然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