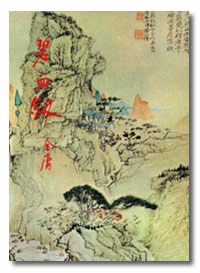站在葛仙宫的门外广场向山下眺望,目光会自然而然地落在两里外祥云庄,那座三层高顶神气的瑞云楼;那是这一带的地标,引人羡慕的权势人家代表性建筑。
失火的痕迹已经消失了,庄主邓大爷早已把楼修得焕然一新,比往昔更醒目。
荀文祥的目光移向另一边,小山的那一边,是他的家园荀庄,在葛仙宫无法看到,庄被小山的草木挡住了视线。
那里,已经不是他的故园了。
要说他心中没有怨恨,那是自欺欺人。
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半点不假。
按当时的社会结构,神刀邓国安怎么可能对他荀家造成伤害?只要他老爹往县衙递一封拜帖,早些年邓庄主天胆也不敢强买他家的百余亩地。
神刀邓国安是什么东西。一个靠吃镖行饭的第五等平民。在官府的档案中,属于刁民阶级。
而他老爹,却是书香世家的士绅,有高人一等的秀才身分,朝廷未来的治世官吏。地方官会保障士绅的权益,一封同年拜帖就可彰显特权的威力。两人走在城里的大街上碰头,邓国安必须恭恭敬敬避至路旁问安。如果不,一封拜帖呈入县衙,大不敬有辱士绅的罪名,至少会挨上几刑杖罚款若干,甚至可能枷号两三天示众。
他老爹从没使用所拥有的特权,在襄城是众所周知的老好人。结果,断送了水源充足的百余亩田地。
现在,所有的田地都没有了。
不但家破了,他也几乎死无葬身之地。
“他娘的!这那有天理?”他的目光回到瑞云楼,忍不住破口咒骂。
在陈留望牛岗,荀文祥向邓淑说,留下的田地送给邓家。那只是一时气头上的话,没有人肯把田地白送给仇人;尤其是几乎害得他家破人亡的仇人。他年轻,修真刚入门,血气方刚,那有这种豁达的修养?他不是做圣人的料。
他认了,但心底的怨恨很难一下子全部丢开忘怀,难怪他盯着瑞云楼诅咒。
经这这次血腥浓厚的惊涛骇浪,性情改变理所当然。他不再是不知人间疾苦险恶的无知青年,不再是听天由命苟且偷安的乡愚了。
遥望他生活了二十年的荀庄,他的家族在这里生活了一千年,甚至更久些。现在,可能永远不会回来了。
没来由地突然想起他老爹的话,感慨万千。
他老爹那天在田地里对他半嘲弄地说:“乌龟活上一千岁,仍然是一只乌龟。它既不能替旁的乌龟改善生活,也不能使自己乌龟升天,活一万岁也是枉然。”
另一段话,可不是嘲弄,而是当头棒喝了:“儿子,你失去的东西太多了。不要说你一天到晚苦得要死,三更灯火五更鸡,甚至三五天入关不眠不食。最重要的是,你修炼的结果,一切以自己为中心,完全忽略了身外的亲情、爱念、世俗、人的责任……”
现在,他才真正体悟出父亲的伟大。
还有,他的师父孤鹤丹士,和那头老鹤。他在心里呼喊:“你们在那里?”
孤鹤丹士的确有未卜先知的神通,不时鼓励他行走天下积修外功,多看看世俗的众生相。但由于生活优裕,根本不想离开温室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所以天涯浪客汤青,要诱胁他闯天下唱道情,他嗤之以鼻。
这次他返回葛仙宫,主要的是处理一些留置在宫的一些私人物品,对故乡投下最后一瞥。在与孤鹤丹士和他参修的秘密角落,留下他迁居的讯息暗记。十年之后,除非孤鹤丹士找他,他是无法找到孤鹤丹士的。天下茫茫,丹士不可能在通都大邑留驻,可能循迹在人迹罕至的深山大泽隐修,他那有遍搜深山大泽的能力?
在葛仙宫逗留一天,向故乡投下最后一瞥,挥挥手扬鞭策马踏上南下的旅途,难免有点依依和惆怅。
距陈留望牛岗事故结束,已经近了前后共计九日。大官道旅客络绎于途车水马龙,应该不会有人认识他是威震中州的青松道人。何况他没穿道装,只是一位穿了宽长衫的年轻旅客,身上没携有兵刃,那像个江湖之雄?事过境迁,应该天下太平了。
难怪他有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他本来就不是江湖人,根本不知道江湖人对恩怨的看法,和处理的态度。更不知道在望牛岗他放弃报复,单方面撒手不管一走了之的作法,那是形同儿戏,没有任何拘束力的个人道义行为,那是不算数的;真正遵守道义的人,早就和古代的圣人一样死光了。
神刀邓国安的名头声望,江湖朋友对他颇为尊崇。圣剑神刀,武林双豪,声誉之隆,中州武林人物无出其右。如果这位武林之豪真正讲道义,怎会横行乡里,勾通官府,大吃窝边草,一而再谋夺乡邻的田地?
邓国安甚至当着群雄的面,当着圣剑面前公然说谎,厚颜无耻说没胁迫荀文祥的父母,也与荆县丞周捕头无关。那天荀文祥被押往祥云庄,亲自经历刻骨铭心的迫害现场始末;假使当时他父母有拒绝胁迫的表示,可能永远出不了祥云庄。他一家老少的尸体,可能已被蛆虫吃掉一半了。
荀文祥还没想到,狂风巨浪之后,必定有余波荡漾,不可能突然风平浪静。
他更没想到,他大仁大义放过要把他化骨扬灰的仇敌,仇敌是否也会放过他。
由于他的出现,威远镖局的暗镖虽然保住了,但损失空前惨重,几乎精英尽失。金戈银弹本来就是一个阴险的枭雄,狐群狗党更是野心勃勃的假英雄,他们不会问谁造成这次血腥事故,只知昧着良心,要造成这次失败打击他们的人负责。
总之,荀文祥根本没想到还会有后患。
从襄城南下至遂平玲珑山,不需回头走许州,走小官道下舞阳至西平,才会合南北大官道南行。小官道旅客不多,用健马代步的旅客也不多见,沿途偶或可看到三五辆客货车往来,与及附近乡镇的人走动。
近午时分,前面鲁店镇在望。这座小镇他不陌生,走这好几次,是一个与郾城县境交界的小市集,一处歇脚站。走了老半天,才走了六十里。
乡愁早就抛开了,怨恨与惆怅也随距乡渐远而淡薄,任由健马所之,无意快马加鞭趱程。
前后不见有旅客,偏僻城镇繁荣不起来。他把遮阳帽掀高些,举目远眺两里外的鲁店镇,镇不大,四周全被树木所包围,看不到房舍。近官道的几家路旁小店,棚下好像看不见有人歇脚。
“奇怪,怎么这段路上,只有我一个旅客,顶着大太阳赶路?”他自言自语,真希望有一位同伙一起走聊解旅途寂寞。
以往他与万里鹏四男女同行,十分投缘毫无寂寞的感觉。尤其是白凤舒欣小姑娘有意亲近,有说有笑怎么可能感到寂寞?
他突然想起白凤,她该已和乃父邪剑舒徐走在一起了,舒老邪知道被他作弄了,现在是不是正在诅咒他。
他刚觉得好笑,突然神色微变,侧耳倾听。
一带缰,健马小驰进入路右的松林。
他是以神御气的行家,可以感觉出某种耳力无法听到,却可用感觉感受到的这种音波。
没错,他感觉出这种声波的撼动,而且是他熟悉的音波,是从御音同道特地向他传递的声音。
“蓬蓬!叭蓬蓬!叭蓬叭蓬叭叭蓬……”是渔鼓的节拍。在曲调旋律来说,该称为过眼。
只有一个人,与那一个渔鼓,才能击出这种除非是行家,否则无法听到的音波,若有若无特别低沉可以及远的音波。
汤青,鼍皮渔鼓。
入林数十步,他在松枝上挂上缰。
“佩服佩服,你真听到了。”前面的巨松后,闪出潦倒的天涯浪客汤青。
白凤神通广大,把汤青带到望牛岗作证,之后不等事件结束,这位浪客便溜之大吉,乘乱溜走,威远的人不敢截留,以免引起荀文祥的干预。
“老天爷,你还敢留在许州附近?”荀文祥摇头大惊小怪:“你绰号叫天涯浪客,应该远走天涯海角避祸逃灾,居然仍在他们的地盘内鬼混,未免太不聪明了吧?看你这鬼样子,好像饿了好几天了吧?”
“吃了好些日子干粮,哪能不饿。”
“那你……”
“如果我远走高飞,必须走大道,能逃这那些混蛋的监视?威远的人把河南布政使司,看成他们的后院。但在我这老江湖来说,暂时潜伏反而安全。”
“他们真在捉你?”荀文祥不愿相信。
“那能假得了吗?别忘了我是黑道最令人头痛的成精浪人。”天涯浪客冷冷一笑:“大官道附近的城镇,几乎每一里就有一个眼线,连乌龟王八狗盗鼠窃全出动了,河南本来就是他们的地盘,各门各道的人谁敢不听他们的?要活捉搏杀的主要猎物有三个人,玉骷髅、银衣使者,我天涯浪客。三个罪魁祸首,在河南休想见天日。行动总指挥,正是你那位好乡邻神刀邓国安,他的神刀,天天在磨上油防锈,磨得锋利得根。”
荀文祥一直就躲在葛仙宫,不曾与任何人士接触,这次动身又不经由大官道,怎知江湖道暗潮激荡。
“没有我?”他仍然存疑,但感到诧异,要论罪魁祸首,对方应该把他列为第一。
“没听说他们要找你,不能乱说。”汤青不是信口开河的人,无意乘机煽风点火。
“那就怪了,他们应该把我看成罪魁祸首呀!”
“明里他们不敢,暗中敢不敢就不知道了。”
“唔!应该不会。我大仁大义轻易地放这他们……”
“老弟,你大仁大义,他们用不着也大仁大义呀?我明明白白告诉你,你可不要被他们在望牛岗的示弱神态愚弄了。圣剑那一番假仁假义的话,是说给你这种读过书,明白事理想做圣贤的笨蛋听的;他那番慷慨激昂的表演,只有你这种人才欣赏,你们得罪这这些玩弄阴谋诡计的专家。你如果相信他们是方正的侠义英雄,早晚会死无葬身之地的。”天涯浪客这番话,就有挑起仇恨的嫌疑了。
“也许他们怕我……”
“他们用不着怕你,你这种人是容易对付的,明枪暗箭你能天天提防吗?我想,近期间你可以在河南大摇大摆南来北往,出了河南,你可要小心了,他们有不少外地的猪狗朋友,搞不好你将在天底下寸步难行。”天涯浪客危言耸听,说的其实也有几分真实性。
“这……”他有点相信了。
“他们不怕你,怕的是慑魂魔君。”天涯浪客诚意地分析:“那老魔有不少早年的忠心耿耿爪牙,聚集在玲珑山,那地方任何不怀好意的人接近,真的会死无葬身之地。胆敢向他们图谋不执,保证会受到雷霆报复性的袭击,屠门绝户绝不留情。祥云庄不是金城汤池,玉骷髅和银衣使者,就轻轻松松放上一把火,能禁得起老魔的毁灭性雷霆攻击?神刀也许不怕死,很勇敢;但祥云庄一两百名狐群狗党和老少妇孺,不可能人人视死如归。老魔不来则已,来则绝不会仅烧掉一角瑞云楼了事的,我保证。”
难怪邓家大小姐邓淑,劝他不要迁往玲珑山。
圣剑高高兴兴,欢迎他加入侠义道行列。
新仇旧恨涌上心头,他脸色难看。
“他们最好不要找我,哼!”本来忘了仇很的平静心湖,像突然被人投石而涌起涟漪重起波澜。
“应该暂时不会。除非你永远耽在玲珑山庄不出外走动,否则……不谈这些,我是来送渔鼓给你的,今后我不再吃唱道情这口卑下饭了,送给你这行家好好把玩。你是书香门第荀家八龙的后裔,不可能背着渔鼓走天下混口食,有这玩意在身边,威力在你手中,必定比九音魔铃厉害百倍。平时把玩,你会在其中获得不少乐趣。至少在受到人世惨重打击百劫余生之后,借这具渔鼓发泄悲痛哀伤的情怀。”
“唷!你还会说俏皮话呢!”他阻止天涯浪客取下在肋下的鼍皮渔鼓:“谢啦!你留着。这玩意如果在伤心痛苦时把玩,眼泪得用脸盆盛装。我根本不需借用乐具做武器,背在身上是大累赘。”
其实渔鼓也可以演奏一些轻快的曲调,比腰鼓优异多多,变化更复杂活泼,甚至可与最复杂的琵琶合奏。
荀文祥之所以买渔鼓,主要是为了追查天涯浪客的去向下落,用任何乐器御发神音,都没有用喉音方便,银龙就是御音高手,用的就是喉音。在乐坛的人士心目中,俗谚说丝不如竹,竹肉;肉,反映人的声音。三国时代的超级名将张飞,在当阳独拒追兵,掩护鼻涕虫刘备,带了十余万难民逃命,面对潮水似涌来的曹兵,大喝一声,当阳桥崩坍河水倒流。当然这种传说有点过于夸张,但也说明人的声音的确具有各式各样的无穷威力。
“宝剑赠豪杰,红粉赠佳人;把武林神刃送人也没人要,真是呜呼哀哉。”天涯浪客泄气地嘀咕。
“没有以神御音秘学的人来说,你这神刃比废物好不了多少。哦!你怎么在这里遇上我,这么巧?”
“你猜,这些日子我躲在何处?”天涯浪客笑问。
“西面的山区?”他向西一指。
“躲在你家后面的紫云山。”
“咦!你……”
“我知道你会返回故乡,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挥别可能一生一世不再回来的故园;所以想把这个渔鼓,奉赠给你让鼓有好主人,不至于埋没成废物。而且,祥云庄附近,是藏身最安全的地方,那位捉人总指挥,目下正在信阳州附近调兵遣将。”
信阳州,白凤应该还在信阳等她老爹的经穴解禁。
如果神刀与威远的人也在信阳州,那……
“你还要躲躲藏藏?”他眼中冷电乍现。
“往西走关中。”天涯浪客没发现他眼中的煞气:“出了河南地境,他们就无奈我何了。河南是他们的地盘,出了河南谁肯听他们的?我如果真怕他们,怎敢参加千手天尊那些邪道大家连手,对付这些假仁假义的混蛋?”
“不怕就和我走在一起,如何?”荀文祥提出邀请。
“这个……”
“咱们走在一起往南行,大摇大摆走大官道,看那一个狗娘养的杂种,敢动你一毫一发。”荀文祥口中不三不四咒骂,江湖味十足。
“免了。”天涯浪客拒绝他的邀请:“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我那能一天到晚跟在你身边?他们投鼠忌器不敢碰你,在街上用暗箭背后来一下,我难逃他们的毒手。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走也,咱们江湖上见,后会有期。”
“胆小鬼!”他笑骂,举手一挥:“汤兄,保重,后会有期。”
这里有一条大路通过伏牛山区,可以到达河南府,再西出函谷关,便可到关中。
×
×
×
他不再慢吞吞赶路,快马加鞭昼夜兼程。一天一夜,便驰抵玲珑山寨。
他父母安顿在老魔的山寨庄院中,受到贵宾般礼遇。所谓山寨,只是往昔避兵村民与匪盗留下的遗迹,名存实亡,山寨早就化为乌有。老魔另在废址上盖了庄院,采兵垒的型式建筑,隐约可以看出寨的气势。
慑魂魔君早年横行天下,结了许多仇家,退隐结寨而居,不得不作万全的准备,严防仇家上门。这一带方圆二十里地,都是他早年买下的。近邻唯一的市镇,是十里外的砂沟集。
这是说,未经允许而踏入这二十里方圆地域,死活都不会有人知道,何处土地不可埋人?
老魔不是孤军在江湖称霸的,他有一群忠心耿耿的死党,退隐之后干脆聚居在一起,放下屠刀拿起锄头,居然成为可以自食其力的朴实庄稼汉。
但他们的武功练得更勤,子侄们更是辛勤苦练,以自卫为目标,也随时准备出动应付意外。
老魔偕同几位亲眷,带荀文祥在附近走动察看形势。
上次在山寨住了几天,老魔含有深意地带他登山看形势,表示在石羊河到玲珑山麓这块地,可建一座庄院。他不知道老魔的用意,以行家的眼光告诉老魔,庄建近砂沟集比较方便些。如按风水形势看,还是倚山建造比较妥当,只是照料庄稼往来要辛苦些。他完全不知道,老魔是有心替他准备的。
工人们正在赶工,把要送给他的庄院,倚山纳入山寨的范围内,预防那些假侠义英雄找他报复。在陈留望牛岗,他已公开表明迁居玲珑山寨,如果庄建近砂沟集,早晚会出大纰漏。那些假侠义英雄阴险狠毒是不饶人的,已经把他看成心腹大患,早晚会前来报复快意恩仇,那能派子弟远出昼夜提防?所以把庄院纳入山寨的天险内。
要接近玲珑山寨袭击,得出动上千官兵,也难保证必可得手。大明开国功臣邓愈,牺牲了数千官兵才攻下山寨。
世间真正不畏死愿意死的人毕竟有限,敢前来令人丧胆的玲珑山寨送死的人找不出几个。
他父亲对这一带环境非常满意,把书房的藏书全搬来了。田地那需他老人家亲自耕种?成了山寨人人欢迎的老太爷。山寨没有一座很像样的社学,遂平县官方承认新学的学籍,不属于私塾,子弟可以参加县学的考试。老魔亲自劝驾,礼聘老太爷主持校务。老太爷那能拒绝?求之不得呢!毕竟一个书香门第的秀才公,下田地种庄稼只能算消遣而非专业,那能靠种地餬口?
一切用不着荀文祥担心,他可以放心投入莽莽红尘积修外功了。读万卷书行千万里,是清高的读书人心向往之的追求目标;修玄的人,以积修外功,来体会出世人世的循环天道,不至于因自私的修炼,完全与世俗断绝;应该活在天道循环中,人是不能远离人群与禽兽一同生活的。
修玄的人,早就发现所谓天道循环,根本与迷信鬼神的报应无关,而是指自然的天生万物中,生老病死春去秋来,才是天理循环。修长生想成仙,那是意图打破天理循环定律的努力途径。积修外功,可以从与世俗的深入接触中,找出究竟该择取何种态度,次定努力修炼的方向和目标。所行所事如果契合天理,可以增加心理上的追求信心与力量;反之,心中的罪恶感就会使修炼的意志崩渍。
他们也明白,要想打破天理循环的规律,是极为困难艰辛的。有些天理,目下不可能以人的力量来改变的,那能把寒冬改变成春天?但只要找到改变的秘诀和力量,一年四季,温暖如春这一天终必到来。
不管修那一种玄,其中不可能有利用血腥来达到目标。但他所处的恶劣环境与凶险的情势,他不可能摒绝血腥了。
他年轻,以往没有涉足鬼域江潮的阅历,不知世道艰难,根本就不是修玄的料。他不是一个对人世漠然的老朽,而是一头受到挑战而奋战的猛兽。他与孤鹤丹士的遇合,是天理循环规律中的错误运行,所错误演化出来的结果;他根本就与仙道无缘。
荀文祥正式云游修积外功,有如猛虎出柙。老魔当然不会让他丢人现眼扮成乞食道人,把他打扮成游学书生,尽管江湖道有不少以书生为绰号的人,其实只是外形扮成书生而已,肚子里是否有墨水,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书生挂剑游学是合法的,学舍里练刀剑弓马,剑是合法博取功名的“生财”器具,可以合法地佩剑公然行走,因为每天都得好好练习。
在府州城市大埠,尤其是有龙子龙孙建藩王府的大城,佩带武器是犯禁的,不能佩带在外招摇行走;书生学舍官员例外。比方说,开封。开封有周王府,佩刀剑在街上招摇,简直是活得不耐烦了。过往的武林人,必须包起来另行置放,或者藏在衣内,别让一些尽职的治安人员查获,当成携带凶器的暴民刁民法办。
这天午后不久,荀文祥出现在信阳州小南门的义阳老店。二度光临,店伙计个个心中叫苦。
这次,他所穿的宽大长衫换了玉色的,不再是青色的博衫。头上梳的也不再是懒人髻道士髻,而是正式的发结,不再不伦不类,人如临风玉树,气概不凡,与上一次半道装打扮迥然不同。随身携带的马包也大了些,表示盘缠丰裕。
感觉中,信阳的市面与往昔并无异样,街上很少看到携刀佩剑的人走动,可知近来没发生任何骚乱,早些天正邪双方大会信阳的盛况,早已烟消云散。
他逐渐了解江湖门槛,知道找同道的窍门。蛇有蛇路,鼠有鼠路;跑错了门槛,那是白费劲。
任何一座城市,邪道的人,必定比正道的人多十倍。威远镖局虽然名动天下,以侠义道自居,声威远播,把河南看成基本势力范围。口碑并不怎么好。一旦发生事故,几乎难以获得邪道人士的帮助,不出来捣蛋抽后腿,已经情至义尽了。
他这次重来信阳,主要是从天涯浪客口中,知道神刀邓国安正在布网张罗,准备对付玉骷髅三个人。天涯浪客是夜劫襄城大户的人,用意在把神刀牵制在家,阻止神刀前往威远护镖。玉骷髅与银衣使者,则是群魔派来火焚瑞云楼的代表,用意也在把神刀拖住,阻止神刀协助威远。三个人分属不同的邪道小组合,但目标是一致的。
他人的恩怨是非与他无关,但神刀亲任搜杀指挥,而且前来信阳坐镇调兵遣将,就与他有关了。
他制住了白凤的老爹,红尘双邪的邪剑舒徐。邪剑是劫镖群魔之一。
但他喜欢白凤,在结伴同行期间,小丫头对他的起居,照顾得无微不至,像一个温顺的小主妇。从小丫头投注在他身上的含情脉脉目光,可感觉出小丫头所流露的绵绵情意。直至邪剑现身,小丫头才不得不出手对付他。
他不但原谅小丫头父命难违的苦衷,而且更为喜欢这位可人的刁钻活泼小姑娘。
算期限,邪剑父女在等候经脉复原期间,神刀恰好在最后一或两天到达,是否会发生事故?
如果神刀真的有心承认错误,应该不会迁怒邪剑父女。陈留望牛岗的冲突,赶来解围的人中,白凤是关键性人物,带来天涯浪客揭开瑞云楼之谜。虽然邪剑父女,也算是图谋劫镖的群魔之一,但反而上了当,连镖在何处也没看到;白凤反而有偕同神针玉女率来解围之德。
如果神刀赶到时,邪剑还没复原,这位阴险的神刀假英雄,会不会乘机找邪剑父女泄愤?
算日期,白凤南返信阳,迄今已过了十六天,邪剑复原已有六天了,应该动身返回豫西邓州老家啦!
在望牛岗他告诉白凤,邪剑所制的经脉,自当日起,十天内禁制自解,已明白表示不需他亲自到信阳州,替乃父解禁制。所订的后会,显然是指信阳州。
他不放心,因此急急赶来打听消息,希望神刀到达时,没发生血腥事故。他要知道邪剑父女是否发生意外,是否平安离境的。
最可靠的老手段,便是向地头蛇打听消息。
首先,他必须找到银龙上次最后藏匿的地方。舒老邪化装暗藏在银龙身边,上当劫到假镖的计策,很可能出于舒老邪所订的,结果几乎一败涂地。
舒老邪的藏身处,与银龙不在一起,除非正式大举出动,舒老邪才蒙上脸跟在一旁,必要时才上阵。所以两人合作的关系,只有少数身分高的人知道。
透露舒老邪底细的人,是绝剑雷一鸣,因此荀文祥才知道,舒老邪那时藏身的地方。
他记得那处地方,师河的一处小河湾,距以前千手天尊建立指挥站的周家大宅周庄不远,众方支援策应暗中往来方便。距银龙一群人的秘站,也不过里余。这两群魔道高手名宿,目标一致,行动也相互通声气,就是无法统合在一起,谁也不肯听别人指挥,都想做司令人。结果,成了两个临时凑成的组合,力量分散,有如乌合之众。荀文祥早就料定他们必定失败,所以坚决表示各行其是,拒绝联手合作,这些乌合之众靠不住。
绕南关沿护城河向东走,河南岸有一条小径向东伸,在城角折向东南,贯连东乡一带村落。
远出里余,路右的树林前缘,钻出一位敞开胸襟,流里流气的壮汉,躲躲闪闪隐身在树后向他招手。
小径上前后不见有人行走,当然是向他打招呼。
他是步行前往的,不需用坐骑代步,距离并不远。
“老兄,你认识我?”他毫不犹豫进入树林,已看出壮汉并无敌意。
“你是青松道长,对不对?”壮汉说:“你扮读书人很神似,但没易容,脸上该用假须肌肤改色,所以一看就知道是你。”
上次信阳风云际会,江湖朋友像是有志一同前来赶集。一些参与盛会的有头有脸人物,自然成为众所注目的中心,壮汉认识他理所当然,他才是那时众所周知的人物。
“你老兄是……”
“一个在油坊充打手的泼皮。”壮汉居然调侃起自己来了,脸上也有自嘲的苦笑:“上次威远镖局的英雄好汉们,派人把本城的下九流朋友看得死死地,严厉警告不许咱们与那些黑道劫镖好汉合作,有些朋友被整治得很惨。”
“我知道。”他恍然,下九流江湖朋友,与黑道人物走得很近,这是事实:“老兄,在下有事请教。”
“我也有些事想告诉你。”壮汉躲在中途招手示意,当然有所为而来:“早些天又来了一群他们的猪朋狗友,毫不客气要求本城的下九流朋友合作,协助他们办事。他娘的!咱们被吃定了,实在心有不甘。”
“哦!要求你们办什么事?”荀文祥心中一跳,首先便想到白凤的安全。
“协助他们封锁道路,替他们留意上次和他们作对的人,何时何人经过这里。尤其是其中的三个人,看到了就必须立即向南大街沈家大宅,找沈大爷飞鸿禀报。三个人是玉骷髅毕天奇、银衣使者柳如是、天涯浪客汤青。沈大爷宅中住了几个行动诡秘的人,可能是负责抢劫的人。道长,你一个人来,太危险了,赶快走,还来得及。你虽然不是他们指定要监视的人,但我不得不将你的消息向沈大爷禀报,马上就得进城。”
天涯浪客的消息是正确的,那么,确是神刀祁国安,在主持追搜劫杀的狗屁事了,但神刀并不在信阳。
劫镖以打击威远镖局威信的事,河南地区的英雄好汉,敢参与的人寥寥无几,威远吃定了河南地区的各门各路英雄好没。下九流的混口食朋友,更是见了威远的人如鼠见描。这位壮汉的胆子不小,冒了大风险向他提警告。
前来劫镖的几路人马,几乎都是河南地区以外的人。邪剑舒老邪,可能是唯一一家在河南邓州的人。
“谢谢你老兄的关照,你办你的事好了。”他抱拳行礼道谢,伸手往路的那一头指:“上次前面罗村罗成的家,住了几个人,他们……”
“哦!道长是指红尘双邪的邪剑舒老邪。”壮汉可能是本地的包打听,消息灵通:“七天前他们还住在罗家,后来那位跟你在一起的大姑娘……叫白凤的大姑娘,冒着暴风雨从北面来。第二天,他们全走了,不走大官道,往西走的,可能走南阳,居然买了一辆轻车代步。”
他心头一块大石落地。显然白凤拼命赶路,竟然只花了七天,就从陈留赶抵信阳,大概急于将好消息告诉她老爹,把可能追赶她的人,远扔在后面。
也可能是发现有人追赶,一到就催促她老爹动身,不能再等两天,走为上策。买的马车,当是载她老爹的,她老爹还要多等两天,经脉方能复原,未复原浑身软僵,不能乘坐骑。
已经走了七天,该到达邓州啦!他放下心头重担,白凤父女的安全不需他担心了。
“威远来的人,是何时到来的?”荀文祥仍然有点牵挂,对威远派来的人有了解的必要。
“大前天来的,当天就要沈大爷用十万火急的口信,把本城的下九流朋友,稍有名气的召至沈宅,听候他们发号施令,没给我们一文钱,却要我们不分昼夜替他们跑腿。”
“难怪啦!老兄。他们是强者,弱肉强食,这是天理,所以他们理直气壮欺负你们。我如果没有几招花拳绣腿自保,早就被他们碎尸万段了。”
“道长能不能帮助我们?”壮汉终于提出要求,这才是拦路通风报信的目的。
“我现在只有一个人,真正的落了单。”他那能帮助这些下九流的朋友出头,这些人靠不住,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威远镖局吃定了他们,任何时候,他们都必须接受摆布,不然后果可怕,反抗的下场不问可知,根本没有反抗的力量。
“罢了。”壮汉也知道有困难,信阳是威远的最重要镖路,沿途州县城镇的江湖人士,包括三教九流的地方龙蛇,几乎全在威远镖局的有效控制下,确保镖路的安全,长时期的控制,敢表示反抗的人寥寥无几。一个外人,那能提供可靠的助力?
这次威远借黑道邪魔意图劫镖的机会,倾全力调兵遣将,用意就是一举歼除这些来自天下各地的高手名宿,不但可以杀鸡儆猴增强慑伏地盘内的龙蛇,更可扬威天下增加威远镖局的威望,一举两得,预计必可达成心愿的。可惜有了万全准备,却没把意外的变数计算在内。
“这里还留下那些人?我是指来自外地谋劫威远的人。”荀文祥想打听那些黑道邪魔,有那些人还没走。
“都走了,留在这里干什么呀?信阳小地方,他们都是大豪霸,不屑在这里抢地盘建势力范围。”
“我也许会逗留三两天。哦!可有神刀邓国安的消息?据说他早些天就来了。”
“没听说这。他应该不会来呀!他早已不是威远镖局的总镖头,上次也没有人在这里见这他。”壮汉所知有限,信阳的地方龙蛇,不可能知道境外的事,只知道劫镖的事无疾而终,正邪双方虎头蛇尾突然一拍两散,威远的人先撤走的,如此而已。
圣剑神刀是化装易容,暗中跟在暗镖后面走的,走的是间道,并没经过信阳。
“他是调兵遣将的司令人,按理不会这么快就抢到这里来。谢谢你老兄的消息,有事请多关照。我不到罗家去了,回客店歇息。再见。”
“道长,他们虽然没把你列为必须留意的人,但仍得小心。再见。”壮汉向林深处退走。
“再见。”他退出林,看小径前后鬼影俱无,却又哼了一声,踱出小径向西走。小径绕这一处茂林小坡,里外就是州城的东南角城楼。
仅走了百十步,他钻入路右的灌木丛形影俱消。
壮汉相当精明机警,从林右侧绕走,窜走如飞,要以树林的南端脱离现场,穿枝入伏,像在草丛窜走的狐狸,留意四周有何动静,起落不定,时窜时停。
仍然不够精明,没能及早发现凶险。
刚窜至一株大树下贴树藏身,小心地向前观察,身后突然传来一声轻咳,接着是拨枝声到了身后。
壮汉吃惊地转身,火速拔出藏在衣内的短刀戒备。
枝叶再动,钻出一个青衣中年人,身材高瘦,有一双冷电森森的鹰目,剑插在腰带上,气势慑人。
“李勇,你干了些什么好事?”中年人直逼近至丈内,冷笑令人心慌:“昨天分配监视地区时,我就知道你靠不住,心不甘情不愿,只知道诉苦推托。”
“王大爷……”壮汉脸色大变,心虚地向后退,短刀在斜动。
“那个穿长衫的人是谁呀?我要知道你引他入林,说了些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如果你有一字说谎,后果你去想好了。”王大爷一面说一面逼近,背着手毫无拔剑的准备,对几乎位于胸口那把抖动的短刀,像是视而不见。
“他……他是……是……”李勇几乎语不成声,惊骇的神情令人同情。
“是什么人?”王大爷声如沉雷:“不许说谎,小心我剁掉你的手脚,让你慢慢死,哼!”
“他……他是青松道……人……”李勇快要崩溃了,不敢不从实招出。
剁掉小臂小腿,片刻便会鲜血流尽;但如果先用巾扎紧要剁断处的上部,阻止流血,半个时辰以内死不了,痛苦绵绵十分凄惨。
“什么?青松道人?”王大爷大吃一惊。
显然王大爷偷窥处,相距至少也在五十步外,既看不清人的面貌,也不易听清谈话的字句。枝叶挡住视线,不敢接近以免惊动谈话的人;分枝拨叶偷偷接近,大白天也难免有声响发出。
“是……是的。”
“该死的东西!难怪你隐起身形偷偷摸摸引他入林,显然和他勾结,商讨图谋咱们的阴谋。好,我要你一字不漏地.把所有交谈的话吐出来。先擒下你把你打个半死,再好好盘问你。你敢走?”
生死关头,怎敢不走?李勇已惊得心胆俱寒,转身拼命飞奔。
奔出二十余步,怎么身后没有声息?居然没有人追来,这位王大爷真会吓唬人。心中一动,不由自主扭头回顽,猛然止步怔住了。
先前与王大爷打交道处,多了一个人。是荀文祥。
王大爷跪在地上,后颈被荀文祥的左手扣住,右手五指如钩,扣住天灵盖,颈部受到完全控制,只要一扳或一扭,颈骨非断不可,张口结舌叫不出声音,鹰目出现骇绝惊怖的可怕光芒。
“快走,不要回头。”荀文祥低喝。
李勇打一冷颤,一言不发扭头飞奔。
“你……你是谁?”王大爷跪在地上动弹不得,声音破碎嗓门全变了。
“青松道人。”荀文祥五指逐渐收紧。
“你……你你……”王大爷如中电殛。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在……在下奉到的指示,是不……不招惹你。”
“你准备如何对付李勇的说谎,我也要有样学样。我记得,好像是剁掉他的手脚,让他慢慢死;我没记错吧?你反对吗?现在,你不会再说谎了吧?嗯?”
“是暂……暂时不要惊动你……”头部的压力一松,王大爷说话流畅了些:“只……要求留……留意你的动静,不……不要打……打草惊蛇……”
“他娘的!把我当蛇?神刀邓国安目下在何处?小心手脚会被刹掉。”
“可……可能在陈州附近。”
“可能?”
“也可能已带了人,向东进入南京地境了。”
“他要干什么?”荀文祥大感兴趣。
“在图谋劫镖的人中,银龙和千手天尊这两股人马实力最强大。”王大爷强定心神,为自己的生命奋斗:“银龙的计策也最完备,志在必得,派玉骷髅和门人银衣使者,远赴襄城火焚瑞云楼,要拖住邓前辈无暇替威远护镖。邓前辈咽不下这口气,誓在必报。威远虽然不希望再生风波,但邓前辈有何面目面对天下英雄?因此邀请知交好友,要找一些罪魁祸首彻底了断。”
“我也是罪魁祸首呀!”
“你不同,谁也不敢招惹你,以后……”
“你们都是些欺善怕恶的英雄好汉。”荀文祥的右手,离开王大爷的天灵盖:“以后等实力够大时,再到玲珑山寨找我算总账,或者在江湖等我,他知道我要在江湖积修外功。”
“银龙那一伙人,是在这里散伙的。当天咱们有人打听出他与四五个黑道名宿,要前往南京凤阳府的宿州,去找老魔潜龙吕海,不知要办些什么机密大事。因此邓前辈在陈州附近,等候助拳的知交好友会合,要前往宿州找银龙师徒了断。”王大爷不敢不吐实,保住手脚要紧。
“这老狗要继续拖知交好友下地狱,真够朋友;陷亲友于不义,他算哪门子侠义至尊。你老兄武功不怎么样,也是他的知交好友。甘心替他卖命。”
“我是身不由己。”王大爷失声长叹。
“为何?”荀文祥好奇地追问。
“家师是邓前辈的知交,师命难违,我能不来帮着跑腿吗?”
“唔!可敬。银衣使者柳如是,可能也是身不由己的,她是银龙的得意门人。难怪天下间门派林立,阿猫阿狗也广收门徒,一旦有事,可驱策这些徒众卖命送死。你走吧!尽你的责任,把我的消息传出,我不怪你。”
“你……”
荀文祥收回左手,转身便走。
王大爷鬼迷心窍,以为天赐良机,荀文祥转身以背相向,妙极了。
不需挺身站起,身形左扭转,左手小臂的皮护套夹袋,一枚双锋针滑入掌心,顺势后甩,针去如惊电,射向相距不足五尺的荀文祥左背肋心坎部位,一闪即至。
真不巧,荀文祥恰好转身回头,恰好抬手,恰好捏住电射而来难见形影的双锋针,顺势一挥手,电芒反而没入王大爷的左肋;六寸长的双锋针仅露出一星针尾,锋尖该已贯入心房了。
“你……好阴……险……”王大爷厉叫,扭身重新仆倒,开始抽搐。
没搜掉敌人的武器,而以背向敌,让敌人有可乘之机,以便抓住回报的借口反击,确是有点阴险。
按武林规矩江湖道义,敌人乖乖招供,是不能杀之灭口的。
把尸体拖放在小径旁,留待对方同党善后。白凤父女可能已经返回邓州,他用不着替他们担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