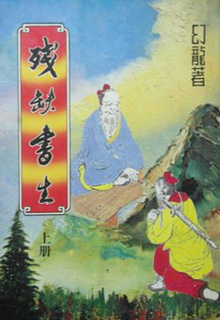经过了一阵的耽搁,已去了不少时候,谭妒非仍记起那些钟声,忙道:“方才恐怕是我师父出困,又和庄上的人厮杀了,你我得赶快去才行。”这时她再不避讳余树奇在场,当即将另外两根“碧萝剑”缠在腰间,双手各执一枝,飞走就走。
余树奇也将金精剑归鞘,捡起那根长的“碧萝剑”提在手上,与谭妒非联袂飞奔。
顷刻间,两人到达一处高峰,俯瞰碧芙山庄,但见庄外到溪边的旷地上人影翻飞,看来最少也有十几对在那边厮杀。
余、谭两人只消一瞥,便知决无平若在内,但来人是谁?怎会一下子聚得那么多人与碧芙山庄为敌?两人对望一眼,会心地微微一笑,谭妒非毅然道:“不问那些是什么人,反正他们与碧芙山庄为敌,我们就得帮忙他!”
余树奇道:“对呀!你我由这里杀奔庄后,先给他放一把火,烧他这狐狸窟,省得留下来害人!但是……”
谭妒非急道:“又有什么难处了?”
余树奇道:“这庄上端的埋伏太多,你我得走在一起,省得失陷了就难得照应!”
谭妒非芳心一颤,略一寻思,随道:“你我在一起就是!”
两人由高峰下扑,不消多时,到达一处土岗,见这山岗上正有一座小屋,谭妒非就要进去放火,余树奇曾在庄前的小屋里吃过大亏,这回自知戒心,急道:“烧这些小屋,没有多大好处,要是遇上凶事,又太不上算,还是烧大屋子才好!”
谭妒非一想,觉得他所说有理,遥指着前面数十丈处,花丛掩映中一座高阁,说道:“那边敢情使得!”
余树奇一看那边,正是平若所说的“绣阁”,沉吟道:“那绣阁原是我姑姑住过的地方,烧了有点可惜,但后来又是方芙占住,也许她正在里面养伤,烧了也无不可,我们就过去罢!”
那知正要举步,土岗上的屋门忽然打开,一位中年汉于当门而立,哈哈干笑两声道:“狗男女!你胡大爷等候多时,过这边来纳命罢!”
谭妒非听那人一开口就骂“狗男女”,粉脸一红,就要扑去。余树奇急一握她玉腕,说一声:“使不得!”谭妒非手腕被握,俏脸更红了,着急道:“你快点放手!”
余树奇道:“放手你就要跑啦!”
谭妒非恨得连说几声:“不跑!”
余树奇略一犹豫,将手一松,同时已纵上土岗,单掌发力向那人打去,立又倒跃回来。
谭妒非见他单独扑出,知他不愿让自己冒险,心里虽觉一甜,性子却等不得,也就立即起步,不料被余树奇倒跃回来,一直撞进怀中,两人一齐由山坡滚落。然而,这时山坡上“轰隆”一声巨响,硝烟沙石漫天飞舞,两人被震得由地面弹起数尺。
余树奇滚在谭妒非怀中,被她无意中搂着站不起来,谭妒非也被他压在胸上动弹不得,一任震得身子几度弹起,才能够分别爬起身来,两人都尴尬得满睑通红。
谭妒非娇羞满面,噘着嘴道:“你这人哪!要倒退回来也不先招呼一声,害得人家……”她自己也不禁好笑起来,指一指自己背上,又说一声:“你看多脏?”
余树奇苦笑一声,看她背后滚得尽是黄泥,忙道:“我替姐姐拍!”
谭妒非涨红了脸,急叫一声:“不要!”却自用那“碧萝剑”扑去身上的灰尘,嘴里依旧埋怨不已。
余树奇只好苦笑道:“当时我怕姐姐要冒险上去,只好抢先一步,要是先招呼姐姐,只怕你我两人全都不活!”
谭妒非怎不知这道理?只因跌得不好意思,才叹怪别人遮羞,这时听余树奇自己说了出来,与自己揣测他的心意不谋而合,心里只有甜蜜的份儿,深情地望他一眼,幽幽地说一声“下回不准你单独冒险!”
虽只是目光一闪,已表出万种关情,而余树奇已由她眼波里读出全部的意义,心里不禁惊喜,一时不知应该怎样回答,好容易才喊出“姐姐”两字。
这是心弦上共鸣之音,像春天的鸟儿以喜悦的歌声,取悦它的侣伴,谭妒非听他连嗓音都发颤了,那能不懂?一颗芳心竟被“姐姐”两字喊得卜卜乱跳,螓首低垂到胸脯,刚叫得一声:“奇哥!”却闻土岗上一声断喝,一条身影疾扑而下。
余树奇纵目看去,来的正是自称为“胡大爷”的中年汉子,想起方才几乎上个大当,恼怒在心,双臂一分,盈虚功的“张”字诀已经展出。
要知他这“张”字诀一发,伹见烟尘飞卷,沙石飘扬,原先被炸飞而甫落回地面的沙石,又再度如几万颗弹丸,向那人急射。
谭妒非急叫一声:“把人抓起来!”但已无及,这边声音发出,那边也惨呼一声,一条身影已被余树奇这种玄妙的奇功打飞数丈,浑身上下也被沙石钻了百孔千疮。
余树奇闻声收掌,见已变成这样,不禁苦笑道:“姐姐!人都死啦!”那知他一语甫毕,那人的尸体一落地面,立又“轰隆”一声,烟硝石雨,又再度翻腾。
幸而两人站离几丈,未被波及,但那尸体已炸得无踪无影。
谭妒非急叫一声:“快走!”一把抓住余树奇手臂,即往后倒跃,冲着扑面的硝烟,后退二三十丈。
余树奇不知她有何所见,待在硝烟外面停下身子,才茫然道:“姐姐见了什么?”
谭妒非道:“那人已经炸碎,要是还站在原处,被血肉兜头淋下,岂不脏死人啦?”
余树奇这才知道女孩子本性好洁,所以谭妒非在这种时候,还记得招呼他退后,不觉点一点头,纵目向各处一看,却见侧面又有几条人影飞纵过来。
谭妒非不待他开口,即叮嘱道:“这回可别把人打死了,要抓活的来问,有人在庄前厮杀,你我在后面救人,总要方便得多!”
余树奇颔首道:“还是姐姐想得周到!”
谭妒非羞涩地一笑道:“你就会灌人家迷汤,姐姐,姐姐地乱叫,也不问自己到底多大啦!”
余树奇看谭妒非的年纪确要比他自己少一两岁,“姐姐”两字不过是对她的尊称,否则,才一见面,怎好把人家叫成“妹妹”?这时听她一说,本要改个称呼,却又故意撒赖道:“我才出师门,还不懂事,要叫你姐姐,才肯照应我嘛!”
谭妒非花容忽然一黯,几乎是哭的声音道:“照这样说来,你是不喜欢我,不肯照应我啦?”
余树奇急了起来,也不知如何是好,轻拍她香肩道:“那里,那里?,……哥哥没说不喜欢你呀!”
谭妒非抬起头来“噗嗤”一笑。
她这一笑,端的是:“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直把余树奇看得又惊又喜,默了半晌。
谭妒非一颗寂寞的心,因余树奇自称一声“哥哥”而震响了心弦,但也因他痴痴望在自己睑上,而有点儿害羞。深情地望他一眼,立又低下头去,佯嗔道:“那有这样看人的哪?看够了没有?”
余树奇笑道:“就看一辈子也不会够!”
谭妒非年纪虽然较小,伹十五六岁的少女也是情窦已开,平若一心在水云洞等待方蓉,不欲离洞远行,所以由谭妒非代替她探查方芙的劣迹,每次出行的时日虽短,而次数却是不少,外间的事物,更令这情窦初开的姑娘增了几分阅历。
再则湘女多情而滥爱,桂女多情而坦率,湘桂边境山林旷野,不乏原始时代的情歌,那些热情而坦裸的歌词,直唱得这姑娘心跳不已,若非平日教养有素,加上自负才貌技艺,只怕早已跌进爱海,这时遇上余树奇这样一位少年郎,早就芳心默许,恨不得投入郎怀。
伹她虽不装作,仍是娇羞,轻轻“啐”一声道:“你那里学来这份贫嘴?要打你啦!”果然捏起粉拳,不痛不痒地在心上人胸前槌了一槌,接着又“噗嗤”一笑。
大抵少女娇痴憨态最易迷人,余树奇纵是不解风情,也免不了心里甜滋滋,面上喜孜孜地跟着她笑了。
这一对小情人为了表露心里的爱慕,几乎忘了身在险地。谭妒非轻敲人家一槌,见他仍然痴笑望自己脸上,还待多挝他几下,忽觉眼角边缘,人影晃动,急叫一声:“哥哥不要痴啦!敌人到了!”
余树奇蓦地一惊,举目看时,五位老人已相距不过十丈,认出来人正是要交手而来不及交手的徐概一行五老,急着说一声:“妹妹!这五个并不太脓包!”
谭妒非见心上人懂得先提醒自己留意,心里又是一甜,报之以甜蜜的一笑,立即向来人一扬蛾眉,“呔”一声喝道:“快给我站住!”
独行客徐概在谭妒非的喝声中飘然在距她两丈处一站,余下四老也分别列在徐概两旁。
谭妒非不知这五位老人是何许人也,右手的“碧萝剑”一指,喝道:“老儿报个名来,再上来受死!”
徐概早先见谭妒非用红绫罗带与宋敏、方芙交手,知她轻功卓越,艺业寻常,此时见她手里各拿有一条软带作为兵刃,还要装腔作势,吆吆喝喝,不由得好笑道:“姑娘家们还是回去学针黹罢!南岳五老不与你一般见识!”
说起“南岳五老”的名头,在江湖上确是响当当的人物,老大就是万里飘风独行客徐概,他一套阴阳掌法神奇莫测,掌力之雄,直可穿山裂石,几十年来确无人敢触他虎胡。因此,他便自高自大地诩为独行客。
另外四老是丧门吊客古熙,湘水渔人崔立,烟霞啸客朱枫,山左樵夫毛川,各有一身特异的艺业。
这五位老人既非同门,更非兄弟,也不是同乡,只因臭味相投,才占隐名山,结为五老,果然使江湖人物见南岳而却步。
徐概为了要收“先声夺人”之效,特意炫耀“五老”的名头,焉知这一对少年男女俱是初出茅庐,根本就不知老与不老,谭妒非嘴角徽徽一翘,鼻里“哼”一声道:“你们老还是岳庙的神主老?”
南岳五老竟被拿来与木偶相比,怎不教他气极?丧门吊客八字眉梢微垂,嘿嘿两声道:“小妞儿活不耐烦了,老夫先迭你终便是!”膝盖徽动,已斜里飘出,挡在徐概面前。
谭妒非抖腕一指,一缕劲风自“碧萝剑”尖发出,疾射丧门吊客鸠尾穴,同时叱一声:“亮兵刃再来!”
丧门吊客身形才定,忽感劲风临身,急挪开两尺,吊鬼眉一皱,横目向谭妒非一瞥,又嘿嘿两声道:“妞儿真还有一手,怪不得狂妄……”忽然猛喝一声:“接招!”一晃身躯,即达谭妒非面前,右臂一伸,五指透出五缕劲风扑奔谭妒非面门,左臂却由右肘下突发一掌。
谭妒非不防对方忽然大喝,吓得后跃一步,回到余树奇身边,立见对方拳形一动,掌风即到,急一挥“碧萝剑”,但闻一连串的爆音,剑上虽已充实内力,仍被震得来回弹晃,不由得怔了一怔。
但那丧门吊客更加骇异他这一招“暗渡陈仓”,原是万无一失,那知被对方一位二八年华的少女轻摇“罗带”,掌劲即全被化解,这一来,使他不得不重对敌人估价。只听他哈哈一笑道:“妞儿再来两招!”身法一变,掌动如轮,霎时闾,一阵阵劲风卷到。
谭妒非哼了一声,将一对以碧萝绦制成没有锋口的剑舞得一片青光,向掌风卷进,但闻“噼噼啪啪”一阵爆音响处,青光已直迫丧门吊客身前。
丧门吊客真料不到这少女仅用两段“罗带”作兵刃,即有恁般凌厉,一下子被攻得连连倒退。
烟霞啸客见势不好,一声厉啸,震得邻近的铁瓦飞跃,接着又冷笑一声道:“古老二!别忘了用家伙!”
谭妒非知他提醒丧门吊客古熙以兵刃对招,也就冷笑道:“朱老儿连你算上!”话声中,双剑一卷,右挡古熙,左取朱枫,居然未把南岳五老放在眼底。
余树奇暗惊道:“这妹妹也未免太过,一个还未分胜败,偏要多惹一个。”他生怕谭妒非有失,也将那枝六尺来长的“碧萝剑”在手中抖了两抖,暗蓄真力以应突变。
烟霞啸客听谭妒非一语未毕,一股锐风已朝丹田重穴冲来,骛得向上一拔,喝一声:“你找死!”一个“云里翻身”头向下,脚向上,双掌一挥,一股凌厉无比的劲风罩向谭妒非头上。
谭妒非若是剑掌并用,对于这种内家掌劲不见得不能抵御,无奈她一时好奇,把两根截下来的碧萝绦,当作两枝软剑来用,虽得真力运入“剑身”,但也只是一条直线,所以锐于攻,拙于防,一见烟霞啸客凌空下击,知他这一掌非同小可,便打定不接招的主意。
烟霞啸客这一掌已尽全力,不伹其余四老认为谭妒非无法幸免,他自己也认为那狂傲少女难逃一掌之危。
那知正在暗喜的时候,余树奇一声暴喝,一股狂飙向谭妒非头顶上一卷,烟霞啸客即觉掌劲被横力一冲,整个散去,眼底一闪,那少女已无影无踪,同时听到山左樵夫一声大喝。
原来谭妒非也恰在余树奇发掌的同时,一扭纤腰,电闪般到了山左樵夫身前,分心就是一剑。
山左樵夫与厮杀中的三人相距五丈开外,那会想到这姑娘会找到他头上?犹幸全神注视谭妒非如何应付烟霞啸客一招“寒月笼沙”,才瞥见一条纤影向他冲来。
起先还以为谭妒非为了闪避,才有此一闪,及至看到纤影一射而到,这才惊觉人家故意找他交手。因为发觉过迟,而且对方又以“罗带”作为前导,封掌发招全已落了后着,只得一闪数尺。
由得双方来去均疾如奔电,但山左樵夫到底迟了一着,被谭妒非“唰”地一剑过去,将他左边衣袖划破一道长有尺许的裂口。
谭妒非一招得势,却笑呼一声:“哥哥!你怎地还不打?”
南岳五老各有一身艺业,在江湖上大有名声,原无以多为胜的念头,却给谭妒非一阵乱攻,激得大发肝火。
烟霞啸客性子最烈,高呼一声:“徐老大!对此狂妄的贱婢,还要讲什么道义?”铮一声响,首先拔出一把寒光闪闪的锯齿薄刃刀。
余树奇尚未答谭妒非的话,即见烟霞啸客拔刀,看他那刀形奇特,刀光浮动,知是一件罕有之物,恐怕谭妒非的碧萝剑会被锯齿刀拉断,急呼一声:“妹妹!这个让我来对付!”也铮地一声抽出自己的金精剑。
前时南岳五老虽曾见余树奇用金精剑与萧恭雨交手,但因相隔尚远,看不清是什么剑,这时再见一枝软剑,徐概急喝一声:“老四且慢!”一闪身躯,抢过烟霞啸客面前微微拱手道:“请问小哥手上的是金精剑还是软晶剑?”
余树奇听他问得大有文章,怔了一怔,谭妒非已跃回心上人身旁,蛾眉微扬,抢着道:“老儿问这个作甚?”余树奇怕她又和对方闹翻,忙道:“我的是金精剑!”
湘水渔人微微一笑道:“金精剑是独孤子的随身宝剑,怎会落在你手?休得在这里骗人!”
余树奇心里不悦,大声道:“金精剑何以在我手中,你可管不着,软晶剑在方士哲手上,你们可自己看去!”
谭妒非接着“哼”一声道:“他们一丘之貉,教他看甚么?往阎王殿再看罢!”
湘水渔人脸色微变,敢情他日常钓鱼之故,仍然能忍耐得下来,独行客徐概想是与金精剑有点渊源,微微作色道:“是金精剑就好办了,老夫还要问一句,你是独孤子甚么人?”
他这一问,可教余树奇十分难答。要说是独孤老人的门下,则独孤老人未教过他一招半式,要说与独孤老人并无渊源,则须将得剑经过从头讲起。
往事从头说也并不费多少力气,只怕被夹七缠八闹个不清,庄前厮杀的声音隐隐传来,可知格斗正烈。进攻碧芙山庄的是什么人,余树奇无从知道,伹他却替他们担忧。因此,略一沉吟,毅然道:“独孤老人是我再传师父,你问这个怎的?”
万里飘风独行客仰天大笑道:“端的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好小子!你认命了罢,老夫可要你头血溅地了!”话声一落,双目凶光射出,一步步向余树奇捱近。
谭妒非娇叱一声,即待上前。余树奇急一拖她手腕,轻说一声:“且慢!”接着昂首挺胸,面对独行客道:“我余树奇决不是怕你,但我师早遭人毒手,我只是由他留下的宝剑与秘笈,而自承为它门下,师门恩怨,我一无所知,你老与我师何仇,不妨先说个明白!”
南岳五老听这少年人气概昂藏地说出这一番经过,不禁相顾愕然,独行客也微微一怔,随即道:“不论你是否获得独孤老贼授艺,你既自承为它的门下,而且承受他的艺业和宝剑,也就该填我胞弟一家七口的命来……”
余树奇先说一声:“那是当然!”接着又道:“先师杀戮令弟一家,是你亲见?”
独行客面色一沉,喝道:“虽非亲见,但他斗胆题壁留词,而且用的是独门暗器碧磷沙那还有假?”
余树奇摇摇头道:“我虽未获先师面授一招半式,但曾搜尽遗物也未见什么碧磷沙,此事大有可疑!”
独行客还在沉吟,烟霞啸客已喝道:“任你小子狡辩,还想图逃死命么?”
余树奇怒道:“难道怕你么?”
烟霞啸客一声厉啸;招过独行客身前,锯齿刀一挥,已向余树奇拦腰削来。
余树奇不闪不避,觑定锯齿刀将临身侧,闪电般反手一剑,“当”一声响,烟霞啸客身不由己被震开几步。
南岳五老见状不禁骇然。
山左樵夫毛川大叫一声:“大伙儿齐上!”一探腰后,取出一柄乌金鬼头刀就手中略为挥舞,即涌起一轮乌光,挟着劲风而到。
湘水渔人取出一个尺许长的小筒在手上一抖,伹闻“克嚓”一声,竟变成丈二长的钓竿,尖端锐利如锥,叫一声:“让我先钓一尾大鱼!”也向余树奇的期门穴疾点。
丧门吊客使的是两节蓝白相间,像哭丧棒般的短棒,但因谭妒非紧靠余树奇身侧,挡在他进击的方向,所以才喝一声:“贱婢!”双棒向她身前直捣。
独行客仍然是一双巨掌,透出两片赤光,分别劈向这对少年男女。
要知南岳五老艺冠群伦,而且同时出手,这份功劲那怕不比各自为战胜过十多倍?
谭妒非见丧门吊客一双哭丧棒势猛力沉,生怕不急出手迎战,便落后着,那知才娇叱一声,即听到心上人叫一声:“休慌!”织腰一紧,身躯已被挟退十几丈,落在土岗上被爆炸过的坑沿,不禁又羞又恼,叱道:“你怎么了?”
余树奇笑说一声:“请看!”
谭妒非一看原来站身所在,五老的掌风,兵刃,交击得“啪啪当当”怪响,不禁笑骂一声:“你就会使坏!”
余树奇笑道:“我们过那边救人去!”
谭妒非道:“怎生走法?”
余树奇道:“由芙蓉花上走没事!”
在余树奇的心意,认为南岳五老一口咬定独孤老人杀徐概家人,自己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解释,若再厮杀下去,定难免有所伤亡,岂不是没有仇也搞出有仇来?
照说南岳五老既与方士哲合伙,杀杀几个也不见得有何差错,但牵涉有师门恩怨,若不加以剖白,岂不教师门永远被别人误会,故使学过独孤老人绝学的后辈永远被人认为是邪魔外道?
因此种种顾虑,余树奇便想暂避其锋,让时间揭破这个秘密,到那时候南岳五老自然因真相已明,而有所悔悟。但他这种只是自己一人的玄想,不仅是南岳五老不明白的用意,连到紧傍在他身边的谭妒非也无法了解。
南岳五老当时因为敌人忽然飞走,以致收劲不及,自己乱碰一阵,已是又惊、又羞、又恼,再见他两人悠哉游哉站在沿坑谈笑,仿佛不将跟前的厮杀当做一回事,更加火上添油。
独行客冷笑一声道:“小子倒是滑溜、腿快,但是,今天不死不散,你两人别打算逃得了!”回头向他四位同伴扫了一眼,准备有所吩咐,余树奇已大声叫道:“徐老儿!我们不是怕你,不愿和你们打的原因,是要教你日后能查出真正的凶手,若果这时连你也打死,你也就要含冤地下,永不超生,反使真凶道遥法外……”
丧门吊客霹雳一声大喝,身子随即扑上,骂一声:“你敢胡说!”双棒已卷了上前。
方才余树奇挟有一人,尚且能逃出五老兵刃掌风之下,此时两人计议已定,正是可战、可守、可走的形势在握,那还把一个丧门吊客放在眼里?俟他扑到相距不及一丈,左手猛劈出掌,要把他迫转回头,同时还大喝一声:“只怕你就是冒名的独孤子?”
丧门吊客早知这少年男女全不易与,一见余树奇掌形翻动,立即双棒一点地面,倒翻上空中数丈,余树奇一掌落空,竟卷起一路烟尘,远达十丈开外。丧门吊客急于闪避掌劲,没听清余树奇说什么东西;伹那独行客听进耳里,不由得又是一怔。
这种神情已被余树奇看在眼里,顺手向空中一挥掌,将丧门吊客迫落一旁,却闻庄内一声厉叫。
那厉叫的声音进入余树奇的耳里,惊得他心胆皆颤,一把拖着谭妒非接连几纵,已登上芙蓉花树。
谭妒非不知他何事恁地忽忙,羞急得连呼:“放我自己走!”
原来余树奇听到那厉叫的声音绝像田毓方叔叔,所以来不及说明情由,拖得谭妒非,兀自忘了放手。这时听她娇呼,忙将手一松,说一声:“快救人!”话声摇曳中,身形直如电光飞射,冲起破空的锐啸。
谭妒非见他恁般急迫飞走,情知事出非常,也展出平生绝艺,如流星赶月般笔直追。
徐概虽自命为“万里飘风”,伹他眼看二小脚不沾地,恍若电闪云驰的轻功身法,也不禁叹一口气道:“老了—只好由他们年青人闹去罢!”
丧门吊客恨恨道:“老大恁般丧气?你不追,我追!”话音落下,身形纵起。万里风独行客说一声:“那有不追之理?”不消几个起落,已抢过丧门吊客的前头,但他心里一个疑团,终莫能解。
由庄后到达庄前的旷地,最少也有一里远近,但以余、谭两人轻功来说,还不是顷刻即到。
余树奇相距厮杀场地犹有二三十丈,即看出是十几名道士与碧芙山庄的人打得舍死忘生,道士那边已有好几人倒在地上,其余也人人显出招式凌乱,方士哲捧着一柄银光四射的宝剑站在一旁督战,看他得意洋洋的样子,不禁心头冒火,可就看不见田毓方在何处,当下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大喝一声:“方士哲!有种就敢接余树奇三招!”
方士哲早闻庄后地雷频响,所以请南岳五老赶去援助,认为以南岳五老那样艺业,定能堵住来敌,让这边结束厮拼,然后转往庄后,因此,频喝令手下人对来敌急攻。那知没有多少时候,即瞥见两条身形竟如流星换位般,先后飞掠而来,南岳五老竟零零星星落在敌人身后。
他略一凝视,即认出前面一个是余树奇,后面那少女定是萧恭雨回来报说的谭妒非,急吆喝手下人加紧歼敌。正在慌忙急乱的成败关头,余树奇已指名叫阵,方士哲记起那柄化骨的毒刃犹觉心寒,但当在手下人的面前,又不能示弱,硬起头皮喝一声:“小杂种胆敢过来!”
余树奇一瞥间又见原先诱平阿姨入彀的张向祥,这时正与几名中年壮汉,包围一名道士,打得难解难分。暗道:“要问平阿姨的消息,正要找这老贼!”心念方罢,谭妒非也恰来到身边,忙说一声:“妹妹去帮那些牛鼻子,待我擒下那狗头!”大喝一声:“余树奇来也!”即与谭妒非双双扑下。
张向祥分明听得余树奇与他庄主喝阵,那会想到人家竟找到他头上?犹在大显威风的时候,忽觉脑后风声,回头一看,即见两个指尖对正双目戳来,吓得叫出一声:“嗳呀!”迅即仰身倒下。
但余树奇取双目的“二龙抢珠”本是虚招,右剑向下一落,把张向祥的胯骨刺个对穿,又痛得他一声惨叫,仰跌地上。
余树奇一剑刺倒张向祥,生怕他的同党来救,反手一剑,向围攻道士的壮汉扫去。
他这一招迅如电射,但见毫光一闪,就听到一声惨叫,八段尸同时倒地,敢情其中有三人竟连惨叫也来不及。
剩下两名相距较远,瞥见同党死得太快,竟惊得呆在当场,被那道士一剑一个,登时了账。
在这时候,四周的惨叫迭起。惨叫声中,但是一条织影带着两道碧绿光华在人丛里穿插,每到一处,必定有几人倒地。余树奇解了这名道士的围,也就向横里杀去。
群贼见新来这对少年男女猛若天神,以为他是哪咤再世,魔女临凡,惊哗一声,即向四面逃散。
方士哲取出一面小锣,“当当当……”一阵急敲,大喝一声:“不许走!”同时扑进扬中,对准余树奇一剑劈下。
余树奇心说:“好哇!正要看你有多少能为!”奋力一剑搪去,“当”一声搪个正着,方士哲身子被震得一阵颠簸,歪歪倒倒连迟七八步远。
万里飘风头一个赶到,大喝:“小子敢狠?”双臂一伸,打出两股狂飙似的掌风,挡在余树奇前面。
余树奇因为姑姑的情面上,本来就不能对方士哲下辣手,见万里飘风掌心一到,也突发一掌挡退来势,骂一声道:“徐老儿再不自量,休怪我余树奇下手不留情!”
谭妒非娇呼一声:“奇哥哥!你留什么情,尽杀就是!”
话声甫落,花树上一声厉啸,接着骂一声:“贱婢好狠!”烟霞啸客已飞纵过来,锯齿薄双刀即迫身前。
谭妒非哼了一声,碧萝剑已迎了上去。
要知由碧萝绦截成这种怪兵刃,在内家高手用起来,无论点、削、搪、劈,都与钢铁制成的刀剑获得同等效力,当年玄女就曾用树枝为剑,与猿公搏刺,并还得过胜利。
伹那碧萝绦的外套,是编织而成,总不能像刀剑那样平滑,与锯齿刀这一类多刺兵刃对敌就难免吃亏。
谭妒非一时失算,居然刀来剑挡,那知一剑上去,立觉掌心一紧,原来碧萝剑已被锋利的锯齿钩住。
烟霞啸客喜得喝一声:“贱婢还小撒手!”
谭妒非碧萝剑被钩,虽是一惊,但她手上还有一枝,身上还有两枝,而且是不花钱的东西,也不十分着急。用力将被钩住的碧萝剑向后一扯,立即一送,同时喝一声:“连这枝也给你!”将另外一枝向烟霞啸客掷去。
烟霞啸客以为对方定要争夺兵器,不妨有此突变,以致用力过猛,身躯向后一仰,眼见一剑当胸飞来,急得往侧里翻身,那知谭妒非早有不一定要回碧萝剑的打算,抢身上前,双掌下击,一腿飞去,娇叱一声:“滚!”
此时,烟霞啸客身已将倒,仅避得开致命的双掌,被谭妒非一脚踢中尻尾骨,痛得惨叫一声,身子滚出丈余,登时晕死过去。
谭妒非一招将烟霞啸客踢个半死,南岳四老尽皆骇然,山左樵夫毛川的鬼头刀,湘水渔人的长钓竿,丧门吊客的哭丧棒,都同时向谭妒非进招。谭妒非一俯身躯,捡回跌落地上两枝碧萝剑,一招“回风卷叶”,双剑一上一下向三老扫去。
烟霞啸客一柄锯刀尚钩在碧萝剑上,被谭妒非这样一扫,竟脱而出,疾射丧门吊客身前。
丧门吊客骇得一个纵步,让那锯齿刀飞去,却被谭妒非跟着一剑扫到,恰将他一只鞋底削落。
这是南岳三老为了紧急救人,以致被谭妒非乘机弄巧。丧门吊客吃了小亏,长了见识,他在五老中排名第二,艺业岂能太弱?一招失利,定下心神,哭丧棒挥出两团异光,与湘水渔人,山左樵夫将谭妒非围在核心。
谭妒非因三老结成阵势,星眸一瞟,见心上人也被几位老人围起来打,瞥见其中一位老人手中一枝长剑几与心上人的一般,忙叫道:“奇哥哥!那使剑的糟老儿可是方士哲?”
余树奇一剑震退方士哲,恰遇万里飘风独行客到来,方士哲,溪山客安臣、青云客张骥也同时扑到。他对于独行客、溪山客、青云客的三般兵器,仗着一身艺业尽能应付裕如,惟有方士哲那枝软晶剑与及左手的“百毒塞沙”却教他有所忌讳。
以致在厮杀的时候,仍得留神方士哲的左手,才被敌方四人有攻有守。这时听谭妒非尚能从容发话,心里一宽,笑说一声:“正是!”
谭妒非道:“你过这边来打,让我去夺它下来!”
方士哲听他两人一唱一和,竟是欲夺自己的宝剑,忿怒得几乎忘了进搭,却见一道纤影飞来,急向后一退。
余树奇瞥见谭妒非话声一落,即冲破三老包围,跃身过来,心里又喜又惊,又是好笑,忙道:“当心老贼的百毒寒沙!”恰周丧门吊客三人追了过来,急挥金精剑一拦,左手一掌劈出。
丧门吊客冶笑一声道:“小贼能接我六人半刻,就准你天下第一!”
余树奇才说得一句:“这有何难?……”忽又闻一声惊呼,骇得叫一声:“田叔叔!”虚撇一剑,即向声源来处扑去,瞥眼间,即见一位道装人物已是披头散发,左臂鲜血淋漓,也不问那道装人物是否田毓方,宝剑一挥,已横断两人,这才问这一句:“道爷可是我田叔叔?”
要知碧芙山庄除了十几位老人武功卓绝之外,余下一班庄汉,个个也是强手。田毓方激战多时,先被敌人刺了一剑,由于那声厉呼才把余树奇召来。
余树奇到了厮杀的场所,见的尽是道士,一时想不到田毓方戴起黄冠,虽然自报姓名,好待田毓方先招呼他,那知田毓方神智半昏,只知奋力杀敌,再则天下同姓同名的人很多,他认为奇儿已十年前死去,纵使听到“余树奇”三字,也只道是同姓同名,怎敢相认?
及至第二次被敌人削落黄冠,再度惊呼,听到余树奇喊出“田叔叔”,又问他一句,这才悲喜半参,精神振奋,叫一声:“你真是奇儿么?”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那处来?”十年不相见,莫说生离,早疑死别,这时忽尔相逢,那有不悲、不喜、不痛、不怜之理?但是强敌当前,无暇叙旧,余树奇只说一声:“正是奇儿!”立又叫道:“田叔叔!你们带伤者过独木桥,这边由我和谭妹妹来挡!”
田毓方见奇儿不但未死,十年竟学得那样俊的功夫,不禁喜极而泪,嘶声高呼道:“韦师叔!我们退回去好么?”
余树奇正在迫杀敌人,忽听田毓方高呼师叔,纵目看去,郎见一位老道长啸一声,自己也忙叫:“妹妹过来!”
谭妒非听得余树奇唤她,嘤了一声,立即纵步回头。
碧芙山庄的人已死伤不少,见敌人要走,那里肯放?
方士哲凛若天神般大喝一声:“一个也休放走!”
那些庄汉想是在淫威之下已久,被方士哲一喝,明知是死,也得向前冲来。田毓方和他的同伴刚将伤者扶起,见状又年迫放下,待与碧芙山庄的人再厮杀一场。
余树奇急喝一声:“列位速退,这里有我兄妹便够了!”谭妒非听他当众叫唤得恁般甜蜜,也接口叫一声:“杀!”双剑反卷敌阵。
原先发出啸声的老道敢情是田毓方的师叔,这时也气概昂藏地喝道:“道通!道玄!你等率众先退,我和两位小侠断后!”长剑一挥,也反扑上去。
余树奇一看敌方除了方士哲和几位老人不算,单讲壮汉就有三四十人,方士哲先前敲锣之后,每一间的门户俱已洞开,各有三四十人小心翼翼由路上奔来,若果让那伙人到来,岂不愈杀愈乱?当即俯身抓起一把泥土,用重手法向敌阵一洒。
方士哲和南岳五老等一班高手对余树奇大有顾忌,所以余树奇一举一动尽落在他的眼中,一见沙石洒出,立即腾身而起,伹那些庄汉个个被沙石射得如同钢针刺体,在呼痛声中,登时四散。
余树奇三人趁机进击,又和方士哲几位高手打成一团。眼看田毓方一行负死扶伤,通过独木桥,忽又闻远处传来一位老妇的声音喋喋狂笑。
那人内力充沛,但双方听她嗓音十分陌生,全都为之一怔。
-------------
大补丁 扫描 一剑小天下 OCR, 独家连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