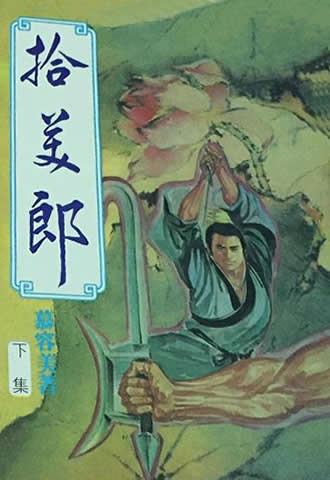关山月望着枯瘦长发灰衣人。
枯瘦长发灰衣人淡然道:“阁下,老住持太抬举,言之太重,我哪里当得起。”
关山月两眼闪现寒芒,亮如冷电,他不止心神猛震,脸色也起了变化,那是动容、震惊、瞿然。
他已经看出来了,枯瘦长发灰衣人的一双手臂,及盘着的两条腿,的确是骨瘦如柴,瘦到两只衣袖,两条裤腿几乎是空若无物。
枯瘦长发灰衣人之所以枯瘦,难道就是因为这?
很快的,关山月脸上的震惊、瞿然神色,转为一片肃穆,说了话:“老住持这菩萨、佛的尊称,尊驾应该当之无愧。”
显然,关山月相信了,而且也有同感。
枯瘦长发灰衣人依然淡然:“阁下怎么也这么抬举,怎么也言之过重?我实在是当不起。”
关山月肃然道:“从即刻起,关家存殁不再言仇,这笔血债,一笔勾消!”
老住持佛号高喧:“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枯瘦长发灰衣人一怔急道:“阁下……”
关山月道:“老住持没说错,尊驾是菩萨,是佛,我不能伤尊驾。”
枯瘦长发灰衣人道:“老住持不让我赎罪,阁下也不让我赎罪?”
关山月道:“老住持说得好,尊驾已经没有罪过了,有的只是功德,菩萨、佛一般的功德。”
枯瘦长发灰衣人仰面长叹:“不知道有阁下之前,我贩依三宝,以求赎罪,却不能剃渡出家;知道有阁下之后,我求能死在阁下手里以赎罪,却又不能如愿,这是……”
他住口不言,没说下去。
关山月道:“这是天意!”
枯瘦长发灰衣人道:“天意?”
关山月道:“这几个都是我碰上的,都死在了我手里,尊驾是我好不容易找到的,我却不能伤尊驾,这难道不是天意?这天意皆因尊驾的一念慈悲。”
枯瘦长发灰衣人道:“是么?”
关山月还没有说话。
老住持已然说了话:“霍居士,这位施主说得不错,这确是天意,这天意也皆因霍居士的一念慈悲。”
枯瘦长发灰衣人胡须抖动,脸上闪过抽搐:“以我看来,这位才是真慈悲。”
关山月道:“尊驾尽割双臂、两腿之肉合药,救一府之生灵,我不过是对一位是菩萨、是佛的三宝弟子放弃私仇,算得了什么?”
老住持又说了话:“以老衲看,施主也具大慈悲,也是位菩萨、是位佛,‘留侯庙’前后出了两位菩萨、两位佛,‘留侯庙’的三宝弟子,天大的福份,天大的造化,几世修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老住持肃穆合什。
关山月道:“霍居士当之无愧,我则不敢当,也当不起!”转望枯瘦长发灰衣人,接道:“关于孙姑娘的事,我已经告诉尊驾了。”
枯瘦长发灰衣人道:“是的。”
关山月道:“她的事,我可以不必管,但我不忍不管;尊驾的心意,是不是该有所改变?”
枯瘦长发灰衣人道:“十年都没有改变,如今又何必改变?”
关山月道:“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
枯瘦长发灰衣人道:“没有什么不可以。十年前,突然接奉密令,不知吉凶,难卜生死,不敢误人;之后,两手血腥,一身罪过,不敢害人;如今,一付槁骨,如同废人,又怎么敢误人、害人?”
关山月道:“孙姑娘都知道,她还是等了尊驾十年。”
枯瘦长发灰衣人道:“她知道的是以前的我,却不知道如今的我。”
关山月道:“十年前的理由,已经不复存在,之后的罪过也已经没有了,有的只是大功德,只剩下最后这一样。”
枯瘦长发灰衣人道:“只这一样已经够了。”
关山月道:“尊驾太伤孙姑娘的心,尊驾以为孙姑娘求的是什么?她都能为尊驾收尸,如今也愿坟边筑庐,以余生伴尊驾,她还会在乎尊驾槁骨一付,如同废人?”
枯瘦长发灰衣人道:“可是……”
关山月道:“尊驾具大慈悲,何独对孙姑娘如此狠心?今后她在‘留侯庙’后筑庐伴墓,尊驾就能高坐在这‘授书楼’上静修?”
枯瘦长发灰衣人欲言又止。
关山月道:“天意不可违,佛门高僧说尊驾尘缘未了,不给尊驾剃渡,这段尘缘不了,尊驾带发修行,又能得到什么?今世之缘不了,尊驾又打算拖到什么时候?”
老住持动容,道:“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枯瘦长发灰衣人没说话,闭上了眼。
这是?
关山月凝功传音:“‘授书楼’上,庙旁石阶往上可达,请芳驾登临一会。”
这是叫孙美英上来相见。
枯瘦长发灰衣人猛睁两眼,奇光逼人,但他没有说话,两眼奇光随也歙去,又自闭上。
一阵轻风,孙美英已然来到,一怔:“你不是已经走了么?怎么上这儿来了?这是……”
关山月抬手向枯瘦长发灰衣人:“芳驾看看,这位是谁?”
孙美英闻言转望,又一怔,旋即脸色大变,失声叫:“是……”
枯瘦长发灰衣人睁开了眼,说了话:“是我!”
孙美英道:“你、你不是已经……”霍地转望老住持:“你这个出家人……”
枯瘦长发灰衣人道:“不怪老住持,是我求老住持这么做的。”
孙美英脸色又一变:“我明白了,可是又怎么让他知道了、找到了?”
她以为枯瘦长发灰衣人是为避仇。
枯瘦长发灰衣人说实话:“我不是为避仇,我根本不知道有他这位关家后人。”
孙美英道:“那你是为……”
枯瘦长发灰衣人仍然实话实说。
孙美英脸色又变了,沉默了一下才道:“可是还是让我见着你了。”
枯瘦长发灰衣人没说话。
孙美英转望关山月:“谢谢你,你又是怎么知道、怎么找到他的?”
关山月也是实话实说。
孙美英惊急,霍地转望枯瘦长发灰衣人:“是你传音找他来的?”
枯瘦长发灰衣人道:“是的。”
孙美英道:“你……”
枯瘦长发灰衣人道:“原来到‘留侯庙’,我本不是为避仇。不知道关家有他这么一位后人之前,我皈依三宝,以求赎罪;及至知道关家有他这么一位后人,我当然想死在他手,以求赎罪。”
孙美英道:“你只知道赎罪,只知道在知道关家有他这么一个后人之后,想死在他手以求赎罪,你有没有为一个等了你十年、找了你十年的人想想?”
枯瘦长发灰衣人道:“当初我突奉密令,难卜吉凶,不知生死,不敢误人;之后我两手血腥,一身罪过,不敢害人:及圣知道关家有他这么一位后人之后,我认为该尽快死在他手,以求赎罪解脱,更不敢误人害人。”
孙美英道:“我明白了,你这是说,十年来,你从没有为我想过?”
枯瘦长发灰衣人没有说话。
关山月道:“芳驾明知道,十年来,霍居士所以躲情、避情,都是为芳驾着想。”
孙美英哀怨地看了关山月一眼:“让我不明白,让我怨他,甚至让我恨他,岂不是好,你又何必说破?”
关山月道:“芳驾是说……”
孙美英道:“我不知道能不能说动你,要是不能说动你,我就得替他收尸,让我少悲痛难过些,岂不是好?”
原来如此。
关山月要说话。
孙美英道:“如今我都不知道该不该跟你一起找他了!我后悔跟你一起找他,更后悔把你带到‘留侯庙’来:可是如今我知道,不跟你一起找他,我永远找不到他。这么看,我跟你一起找他并没有错;当初所以跟你一起找他,是怕你先找到他,让我不能再见着他,也没有机会说动你留他一命,甚至不能为他收尸;如今还是你先找到了他,你却知会我前来见他一面,也给我说动你留他一命的机会,万一不成,也能让我为他收尸,对我来说,这是恩、是义,我该……”
关山月说了话:“芳驾什么都不必,我跟霍居士之间的仇,已经一笔勾消了。”
孙美英一怔,急道:“怎么说,你跟他之间的仇,已经一笔勾消了?”
关山月道:“是的。”
孙美英道:“怎么会?你找他不就是为了报仇么?他是你众仇之首--”
关山月道:“他没有罪过,只有功德,大功德,是菩萨、是佛,我不能伤他。”
孙美英叫道:“他没有罪过,只有大功德,是菩萨、是佛,你不能伤他?”
关山月道:“请老住持告诉芳驾吧!”
老住持忙说了。
听毕,孙美英急望枯瘦长发灰衣人:“你--真的?”
枯瘦长发灰衣人说了话,淡然道:“没什么。”
关山月道:“芳驾只要仔细看,看得出来。”
孙美英闪身扑过去,先抓枯瘦长发灰衣人双臂,又扑枯瘦长发灰衣人两腿,突然,她哭了,浑身俱颤,失声悲呼:“天--”
她两腿一曲,跪倒在枯瘦长发灰衣人跟前,失声痛哭。
枯瘦长发灰衣人一怔道:“你这是……”
孙美英哭着道:“这真是大功德,真是菩萨,真是佛……”
枯瘦长发灰衣人道:“怎么你也--快起来。”
孙美英没动,只低头痛哭。
枯瘦长发灰衣人道:“既然认为这是功德,就不该哭,不该这样。”
孙美英猛抬头,泪满面:“我总是人,我心疼!”
枯瘦长发灰衣人胡须抖了几抖,才道:“这些肉救了我一条命,你还心疼?”
孙美英一怔,突然不哭了,道:“这些肉何止救了你一条命?我不该心疼。”
她举袖拭泪,站了起来。
枯瘦长发灰衣人呆了一呆,默然未语。
老住持肃穆合什:“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孙美英转望关山月:“这么说,你找我上来,不是为给我一个说动你的机会,不是为让我见他最后一面,不是为让我给他收尸?”
关山月道:“霍居士认为他如今槁骨一付,如同废人,更不敢误人、害人:我却认为他如今更需要人照顾,芳驾绝对愿意,而且我也已经说服了霍居士。”
孙美英忽然又哭了:“留了他一条命,成全我十年情,这双重的恩德……”
她就要跪。
关山月没拦,但是要走。
枯瘦长发灰衣人突然轻喝:“阁下,请留一步!”
关山月收势停住,同时也伸手拦孙美英。
隔着好几步,孙美英竟没能跪下去,她叫:“你……”
关山月道:“芳驾,我当不起。”
孙美英道:“你也是菩萨,你也是佛!”
关山月道:“霍居士救了一府生灵,比起霍居士,我这算得了什么?”
孙美英道:“他是救了那一府生灵,你是对我有双重恩德。”
关山月道:“芳驾,霍居士叫住我,一定有事,”
孙美英道:“我不拜了,也不说了。”转望枯瘦长发灰衣人,接道:“说你的事吧!”
枯瘦长发灰衣人向关山月:“我觉得我应该告诉你,那位姑娘的下落。”
关山月心头一跳。
孙美英道:“哪位姑娘?噢,我知道了,那位姑娘真是你带走了?”
枯瘦长发灰衣人道:“我不忍再伤那位姑娘,也伯别的那几个伤害她,所以我带走了她。”
孙美英道:“你怎么没告诉他那位姑娘的下落?”
枯瘦长发灰衣人道:“原先我不能。”
孙美英道:“为什么?”
枯瘦长发灰衣人道:“老侯爷要走了她。”
关山月心头震动,倏扬双眉。
孙美英一怔叫道:“老侯爷要走了她?”
枯瘦长发灰衣人道:“是的。”
孙美英道:“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枯瘦长发灰衣人道:“当年,我回京覆命的时候。”
孙美英道:“都十年了。”
枯瘦长发灰衣人道:“是的,都十年了。”
孙美英道:“你怎么如今又要告诉他了?”
枯瘦长发灰衣人道:“受人良多,我认为该告诉这位了,不该么?”
孙美英道:“该、该,你告诉他吧。”
枯瘦长发灰衣人向关山月:“阁下已经听见了。”
关山月道:“尊驾说的可是‘神力侯’?”
枯瘦长发灰衣人道:“正是。”
关山月道:“尊驾曾经跟我保证,她很好,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这是指“神力侯”要走了虎妞。
枯瘦长发灰衣人道:“阁下不要误会,老侯爷跟我要走那位姑娘,是怕有一天我会伤害她,也是防别人跟我要她。”
关山月道:“是么?”
枯瘦长发灰衣人道:“老侯爷朝廷柱石,一代虎将,盖世英雄,视姑娘如己出,我可以拿这条命担保。”
孙美英道:“我也可以拿我这条命担保。”
其实,这位“神力老侯爷”,关山月也听师兄郭怀说过,知道是位当今朝廷的柱石虎将,盖世英雄,无论朝野,莫不尊仰,连皇上都敬他三分,跟他那个儿子“威武神勇玉贝勒”不一样,绝不会对民间一个小姑娘存有什么不好念头,更不会伤害一个民间小姑娘。
枯瘦长发灰衣人当年只是“神力侯府”一名护卫,处在“京城”那么一个地方,万一有哪个亲贵垂涎虎妞,他还真无力卫护,他的话也可信。
何况还有两条命做担保?
所以,关山月没再说什么,只道:“谢谢尊驾了,告辞!”
话落,他又要走。
人在“授书楼”里,又当着这么一位菩萨、佛,还有一位高僧老住持,关山月不便施展绝世身法,打算等出了“授书楼”后再施展绝世身法离去。
是故,枯瘦长发灰衣人来得及又叫住了他:“阁下,请再留一步。”
关山月又停住了,道:“尊驾还有什么教言?”
枯瘦长发灰衣人道:“阁下能否让我知道,离开‘留侯庙’之后,要往哪里去?”
关山月连迟疑都没迟疑,道:“没有什么不能让尊驾知道的,离开‘留侯庙’之后,我要赶往京里去。”
枯瘦长发灰衣人道:“阁下是要见那位姑娘去?”
这是一定的。
关山月仍然没迟疑:“正是。”
枯瘦长发灰衣人道:“我就是为告诉阁下,阁下不必往京里去,那位姑娘如今不在京里‘神力侯府’。”
孙美英微怔,道:“那位姑娘如今不在京里‘神力侯府’?’枯瘦长发灰衣人道:“不在。”
孙美英道:“哪儿去了?”
枯瘦长发灰衣人道:“蒙古。”
孙美英又一怔:“蒙古?”
枯瘦长发灰衣人道:“‘科尔沁’旗。”
孙美英轻叫:“老侯爷那位义子,‘科尔沁旗’呼格伦王爷那儿?”
枯瘦长发灰衣人道:“不错。”
孙美英叫道:“老侯爷怎么把她放在了那儿?”
枯瘦长发灰衣人道:“老侯爷也去了,如今也在那儿。”
孙美英再次一怔,叫道:“老侯爷也去了?如今也在那儿?老侯爷是什么时候去的?”
枯瘦长发灰衣人道:“有几年了。”
孙美英道:“有几年了?怕不早回去了?”
枯瘦长发灰衣人道:“恐怕不会。”
孙美英道:“恐怕不会?”
枯瘦长发灰衣人道:“老侯爷是不满意贝勒爷的作为,贝勒爷趋炎附势,攀上了四阿哥雍王爷,以为雍王爷将来一定能夺得大位,拥立有功,将来一定有大好处,老侯爷虽然忠于皇上,心向二阿哥,但是老侯爷的脾气与为人,你是知道的,‘神力侯府’绝不介入各阿哥间的大位之争,老侯爷要贝勒爷也这样,贝勒爷阳奉阴违。儿子大了,管不了,又有个雍王爷在,雍王爷又机关到处,耳目遍布,老侯爷也不便太明显怎么样。老侯爷生气、难过,干脆眼不见为净,远走蒙古去了。”
孙美英道:“你是怎么知道的。”
枯瘦长发灰衣人道:“我在‘西安’的时候听说的。”
孙美英道:“你在‘西安’的时候听说的?这么说,知道的人已经不少了?”
枯瘦长发灰衣人道:“恐怕是。”
孙美英道:“外头都这么多人知道了,宫里恐怕也知道了。”
枯瘦长发灰衣人道:“应该。”
孙美英道:“这对贝勒爷可不太好。”
枯瘦长发灰衣人道:“以贝勒爷的脾气跟为人,他哪知道怕?又伯什么,怕谁?他只知道,老侯爷不在,禁城的禁卫禁不得他,宫里不会拿他怎么样。再说,都是自己的儿子,宫里虽严禁众家阿哥间因争大位而间墙,却不便不让臣下拥立哪一个。”
孙美英道:“这么看,老侯爷短时日内是不会回去了。”
枯瘦长发灰衣人道:“我就是这么认为。”
孙美英转望关山月:“你听见了?”
关山月道:“我听见了。”
孙美英道:“幸亏你走得不快,不然你就白跑一趟京里了。”
关山月倒不怕白跑一趟京里,他只是不愿到京里去,京里卧虎藏龙,“神力侯府”尽多好手,“威武神勇玉贝勒”本人就是个好手中的好手,再加上那位贝勒夫人胡凤栖,尤其禁城里的大内侍卫近在咫尺,他这一趟进京去“神力侯府”,要想神不知、鬼不觉,只怕不可能;不怕让谁知道,也不怕不能自保,怕的是师兄郭怀已经前来,住进“南海王府”;到时候让师兄为难,可是为找虎妞,又势必得去,一颗心正沉得很低,正暗皱眉头。
如今,心里松了,暗皱的眉头也舒展开了。
关山月道:“谢谢。”
枯瘦长发灰衣人道:“阁下客气,我不知道便罢,知道了不能不说,只是……”
关山月道:“尊驾有什么话,请只管说。”
枯瘦长发灰衣人道:“我原先不告诉阁下那位姑娘的下落,如今说了,是因为阁下对霍某人我恩高义重,再不告诉阁下,自觉实在说不过去。只是,我要请求阁下,千万不要伤害老侯爷。”
关山月道:“尊驾先前不肯告诉我,就是因为有这个顾虑,是么?”
枯瘦长发灰衣人道:“正是。”
关山月道:“尊驾放心,只要老侯爷没有伤害她,我对老侯爷只有敬重,只有感激,绝不会轻犯虎驾。”
枯瘦长发灰衣人道:“老侯爷一代虎将,盖世英雄,绝不是那种人,他是怕她受到伤害,把她要到身边之后,视她如己出,我刚才曾愿以性命担保。”
孙美英道:“我不也是么?”
关山月道:“那么两位都大可以放心。”
枯瘦长发灰衣人道:“以阁下之对我,对我俩,我知道我这个顾虑实在是多余;只是,身为人下,老侯爷也对我恩重如山。”
孙美英道:“更要紧的是,当年主持杀人事,老侯爷也是奉旨行事,万不得已。”
关山月道:“我知道,要不然我不会因为老侯爷只对她有恩,我就对老侯爷感激、敬重。”
枯瘦长发灰衣人道:“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谢谢阁下。”
关山月道:“该我谢谢尊驾。”
孙美英道:“知道‘蒙古’怎么去么?”
关山月道:“应该不难。”
这倒是,江湖上跑的人,还怕到不了“蒙古”?
孙美英道:“‘蒙古大分分三部,‘内蒙古’、‘外蒙古’、‘额鲁特蒙古’;分七部,‘内蒙古’、‘外蒙古’、‘西套蒙古’、‘科布多’、‘乌梁海’、‘青海蒙古’、‘游牧蒙古’。”
关山月道:“谢谢。”
孙美英道:“‘科尔沁旗’属‘内蒙古’‘哲里木盟’之四部十旗,那位世袭罔替的呼格伦王爷,是位‘蒙古’豪雄,马上马下一身好武艺,得自老侯爷真传,万人难敌。”
关山月道:“谢谢。”
孙美英道:“‘蒙古’人骠悍,个个勇猛能斗,这么一位王爷身边有多少百里选一的好手,可想而知。”
这似乎是提醒关山月。
关山月道:“对‘蒙古’人之骠悍勇猛,我是知之甚久,好在我只去探望儿伴,不是去骚扰侵犯。”
孙美英道:“我只是怕他们不相信!”
关山月道:“谢谢芳驾,我会让他们相信。”
孙美英道:“我就是要告诉你,能不起冲突,最好不要起冲突;一旦冲突,遭灾难的必是他们;他们一旦逃了灾难,你见呼格伦王爷就难;见不着呼格伦王爷,就更别想见着老侯爷。”
关山月道:“谢谢芳驾,我知道了。”
孙美英道:“他跟我都不能陪你胞一趟。”
关山月道:“怎么能烦劳两位?也不敢烦劳两位。”
孙美英道:“我俩该说的,应该已经都说了,不耽误你了,临别问一句,还能再见着你么?”
关山月道:“不敢说,有缘总会再相见。”
孙美英道:“不管怎么说,别忘了‘留侯庙’有姓霍的、姓孙的这么两个人。”
这么样认识,这么样相处多日,也这么样化仇为友的两个人,如今竟会有这么一句话。
关山月暗暗激动,也暗暗感动。表面上故作淡然:“不会的,想忘恐怕都忘不了。”
孙美英笑了,看得出来,笑得勉强。
关山月没再说什么,道:“告辞!”
转身外行。
没人再叫住他了。
只听枯瘦长发灰衣人道:“阁下好走,恕我不能送了。”
关山月没回头,应了声:“不敢。”
只听老住持高声诵佛:“阿弥陀佛,善哉,善哉,施主后福无穷。”
关山月也没回头,说了声:“谢谢。”
出了“授书楼”,飞身而去。
孙美英送出了“授书楼”,望着关山月飞星殒石般,飞泻不见!
旧雨楼 扫描 大眼睛 OCR
旧雨楼 独家连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