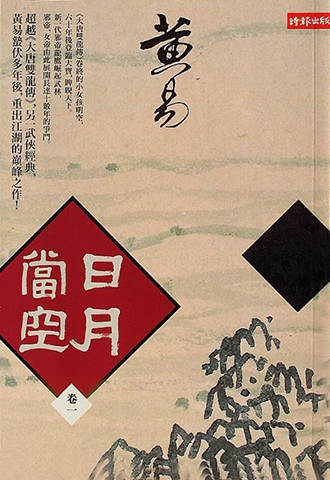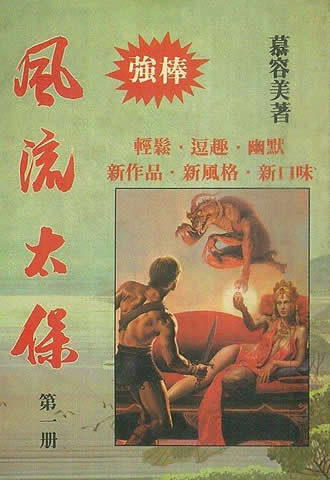水涨船高,像是起潮了。
大船摇动得厉害,尤其是那根合抱粗细、高耸当天的船桅柱子,吱吱哑哑地响着,看样子真像是随时都会倒下来。
月亮够大也够圆,只可惜才出来不久就被乌云给吞噬了,江面上浪花汹涌,一个接一个地卷起来拍打在岸上、石头上、船身上,每一次都澎湃有声,激发出万点银星。
像是有人吩咐了一声,大船就悄悄地起锚了。
大江上蒸腾着白茫茫的雾气,时见鱼群的“泼刺”。
“白头”老金一声不吭地抽着烟,不时翘起脚来,旱烟袋杆子磕在鞋底上,笃笃有声地落散着小火星子。把舵的是他儿子“金七”,挺高的个子,头上扎着布,浓眉毛,大嘴,黝黑黝黑的,看上去像是天生干船的,有一身用不完的力量。
那一边灶头上,小伙计“毛五”正在升火煎药,一把把的树枝塞进灶头里,发出劈劈拍拍的响声,火苗子不只一次地穿出来,差一点就燎着了他的眉毛。“嘿!”他嘴里嘟嚷着:“煎药就煎药吧,干吗还非得要有这么些讲究?非得用桑树枝来烧火,怎么!桑树枝烧的火是冒蓝烟儿?”
“嘿,这你就不知道了!”
老金微微咧着嘴笑,一丝丝的白烟,就像小蛇也似地由他黑牙缝里钻出来。
“岐黄谱上说过,桑是属凉的,用桑枝点火,八成儿是去火吧。”翻着两只大肿眼泡,咂了一下嘴:“噢,准是清火气,清心补肺吧!”
“清心补肺?”毛五一脸的疑惑:“这么说,他是得了肺病?年轻轻的--可怜。”
“别瞎说!”白头老金立刻又正经了起来:“这话要让人家听见,可不答应你,年轻人嘴里要积德!”
毛五嘻着一张黄脸,道:“我只是瞎猜着玩罢了,要说人家相公,还真是个好人哪!”
一面说,他直起腰来,用一根白木头药杓子在大罐子里搅着,浓重的药气随风飘散开来。接着他用一个小小的药滤子,把罐子里的药汁滤出来,不过是小小的半碗药,又浓又绿的颜色。
毛五用鼻闻了闻,皱着眉毛道:“这是什么味呀?怪里怪气的!”才说到这里,他立刻眼睛发直地注视着前方,道:“看!那个难说话的主子来了!”
白头老金一怔,赶忙站起来,烟也不抽了,把着舵盘子的金七也伸长了脖子。
在舱檐前面两盏桶状的宫灯照射下,一条瘦长的影子已来到了近前。
白头老金紧张地趋前,赔着笑脸道:“唷!这不是史老爷吗,您有什么吩咐?”
来人鼻子里轻轻哼了一声,派头十足地点点头:“这是什么地方了?”
“噢!”老金向外看了看,这地方他太熟了,当下脱口道:“五里滩,再下去是七星勾子,呵呵,还早呢!要到明天过了晌午,大概就到了汉江了!”
“哼!”来人不耐烦地听着,一双黄焦焦的眉毛,时开又合,两只小眼睛频频眨动着:“到时候记着告诉我一声,我要下去一趟买点东西。”
“是--”老金十分巴结的样子:“史老爷和贵宝眷--”
“胡说!”姓史的一下子虎起了脸:“你乱说些什么,小心我掌你的嘴!”
“啊!”老金吓得后退了一步,半天才变过脸来,一面赔着笑道:“是--小人糊涂,小人糊涂!”
“不要再说了--”
姓史的抖了一下闪闪有光的黑缎子衣裳,冷冷地打量看面前的三个人:“前舱里没你们什么事,以后不招呼不许进来,只管好好招呼着船,到了鄱阳湖我们走人,钱只有多没有少,知道吧!”
倒是后面这句话还算中听,白头老金拱着两只手连连称是。乘这机会,他才看清了疑是“官场”上的对面这个人物。
五十六七的年岁,头发虽不像自己那样的全白,却也差不多半白了,一对招风耳,小鼻子小眼睛,老金看在眼睛里,却是纳罕着对方的这副尊容,也不知是那一点主贵,值得他这么神气。
姓史的交待完了这几句话,刚要转身,一眼看见了毛五手里端着的药碗,怔了一下:“什么东西?”
“这--”毛五结巴着:“是--一碗药--”
不知是什么原因,从第一眼看见这位史大爷起,毛五就对他不顺眼,可也真怕他。
“药?”姓史的已走了过来。
毛五喃喃地道:“是药,这舱里的一位相--相公--”
“这舱里的相公?”姓史的脸上像是忽然罩上了一层霜,拧过头来,瞪着白头老金:“这是怎么回事?”
老金不安地干咳了一声,喃喃地道:“是--这么回事,船过洞庭时,上了个客人--”话还未完,只见面前人影闪了一闪,紧接着“啪!啪!”两声脆响,包括金七、毛五两个人在内,简直都没看见姓史的什么时候出的手,白头老金已挨了两记耳光。
这两下子打得还真不轻,老金“啊哟”地叫着,顺着嘴角往下面淌着血。
金七不甘父亲的挨打,一下子由舵台上跳下来,伸手就去操一根长篙。
姓史的好像是一个练家子,好快的身法!
金七的手还没来得及抬起来,已被那位史大爷的脚踩了个结实,别看他个子不大,劲头儿可是不小,没有怎么施劲儿,金七已痛得几乎咧嘴,连声“啊唷”了起来。
白头老金顿时傻了脸。
毛五更是端着碗,像个木头人似地怔着。
史大爷冷笑着道:“怎么着,还想动家伙,不要命了!”
白头老金哭丧着脸,连连打躬道:“小人不敢!小人不敢!史大爷你老高抬贵手吧!”
“哼!”姓史的缓缓松下了脚,一脸怒气地看着老金道:“不是跟你说得好好的,这条船,我们整个包下了?怎么还搭外客,这是怎么回事?”
老金自知理屈地赔着干笑道:“这--是这么回事,这位相公一个读书人,又有病,那间边舱房空着也是空着,所以就要他上来了!”
姓史的想发作,却又忍着,冷笑了一声:“你好大胆子!叫他下去!”
“这--”金七一脸为难的样子。
“没什么好说的,明天船一到汉江,就叫他下去!”
姓史的还要再说什么,就见前舱里款款步出一个细腰长身的姑娘,老远向着这位史大爷点了点头,姓史的快步迎了上去。
细腰姑娘嘘一声道:“小姐关照,叫大叔你别吵,夫人和小主人才睡着了。”
接着说话的声音就低了,那位史大爷回过头看了后舱板上的三个人一眼,就随着来的那个细腰姑娘去了,紧接着前舱的两扇舱门也就关上了。
摸着麻辣辣犹有余痛的脸,白头老金缓缓地坐下来。
金七一脸忿忿地走过去,恨声道:“他娘的,船是咱们的,咱们爱搭谁就搭谁,他管得着吗,这个姓史的,也太欺侮人了!”
老金漠漠地看了儿子一眼,叹了口气道:“也难怪,收了人家的定钱,原是不该再搭外客的--”
“只是--咱们怎么跟那位相公说呢?人家还在病着!”
毛五插嘴道:“这我可不去说。”
老金叹了口气站起来,把旱烟袋杆子插在腰上:“有什么办法,小五,把碗给我,我瞧瞧那位相公去。”
毛五一怔道:“你真--真的要赶他下去?”
老金也没说话,接过碗来,独自个地走了。
背着身子,那位先生正在写字,一头长发披散着,一袭长衫也披散着,宝蓝缎子面闪闪有光,长长地曳下来,上面连一个褶子都没有,乍看上去就像是一整匹缎子那么的平滑光洁。
船身微微地动荡着,使得悬置在他头上的那盏银红纸灯也在晃动着,是以,他修长的影子被扭曲了。
白头老金轻咳了一声道:“这位相公,你的药来了!”
“噢!”长发人缓缓地搁下了手里的笔。
老金把药缓缓地端过来,正迎着对方回过来的身子。
“何劳老丈亲自服侍,不敢当!”说话时,对方已接过了药碗,眉头微微皱了一下。
老金笑道:“大概有点凉了,再去热一下吧!”
“不必了!”回答得很干脆。
一边说时,遂即仰首把小小的半碗药汁喝了个干净。
卷金这才注意到,对方那只持碗的手,敢情与常人有些不同,包括他另一只手在内,十根手指的指尖,连同指甲,都作暗红、紫黑的那种颜色,看上去煞是可怖。老金心里希罕,却也不便出口询问--忽然一怔,才警觉到对方一双眼睛正向自己注视着。
四只眼睛交接的一霎,老金下意识又不禁打了个寒颤,白天上船时,他竟不曾注意到,敢情对方这个相公真的病了,而且还病势不轻。
苍白颜色的一张脸,显示着病魔的入侵,绝非朝夕之事,一双尚称灵活的眸子,固然是黑白分明,然而在其下眼泡处,也同他的十根尖指一样,郁积着浅浅的暗红色泽,这番奇异的色泽点缀,使得对方斯文的外表着了几许阴森、憔悴和病痛。
白头老金情不自禁地往后退了一步,若非是紧接着对方脸上所显现的微笑,他还真有点心里发毛。
“金老丈请坐,你有话要说么?”
抬起拖着肥大衣袖的一只手,指了一下舱里的座位,老金情不自禁地顺着他手指处就坐了下来。
“老丈喝茶。”
“是--不客气,不客气!”
一面说,老金就手拿起茶几上的茶壶,倒了半碗清茶,糊里糊涂地端起来喝了一口。
“茶凉了。”
“噢,还好,还好--”
“今夜的月色不好。”
口音似岭南,却又带点云中,又稍掺有一点北地京里的那种韵味。
老金自信这一辈子干船上的活儿,大江南北都跑遍了却是一时听不出对方的真正发音所属,那种低沉却富有磁性的男音,出自对方斯文冷寂之口,虽是简短的几个字,却是铿锵有力,有不听不可的强迫感。
说到月色不好,对方已踱向窗前,推开了两扇临江的轩窗,一阵江风袭来,悬在舱里的那盏“八角银红双穗”纸灯,滴溜溜地直打着转儿,文案上的纸笔书篇,俱都大有动势,一霎间,颇有飞沙走石之态。
老金“啊”了一声,慌不迭地离座站起来,想去帮着对方关上窗户。
不劳费心,来得快,去得也快。
老金身子不过才站起来的当儿,舱房里却已恢复了原有的平静,那阵风像是只进来兜了个圈子,却又出去了。
并非是风停了,眼看着窗外浪花翻飞,其势不已,这小小边舱,一瞬间,却和煦如春。文案上的纸牍书篇,当顶上的八角挂灯--俱都在同一个时候,收住了耸动之势。
白头老金狠狠地眨了几下他的一双大眼,心里透着“玄”,却是无论如何也想不通是怎么回事?
打量着当空在疾风行云中的那轮皓月,这个人深邃的目光,却转向附近水面,天是波谲云诡的,水也是波谲云诡的--连带着他的脸色也变成了那个样。
随后,他就不再对窗外感到什么兴趣了。关上了窗户,他发出了几声轻咳。
白头老金像是忽然警觉起来,打量着面前这个“讳莫如深”的人物:“这位相公,你敢是着了凉吧!”
摇摇头,对方脸上含着淡淡的笑:“你还是关心你的船吧!”
“还没请教相公贵姓?”
“我?”
一霎间,他脸上布满了凄凉,在他那双眼睛再次注视向老金时,后者顿时被一种无可名状的沉寂气势所笼罩住,真后悔自己有此一问。
“你可以叫我水先生。”
“水--先生?”
“对了,江水海水,反正离不开水!”他脸上终于泛出了由衷的笑:“我在岭南吴家庄设过馆,教过书,你要是高兴,称我一声教书先生,我也不反对。”
“这就对了!”老金咧着嘴嘿嘿笑道:“我看你相公就是个念书人的样子,水先生,你的病--”
水先生道:“夜深了!”
老金眨了一下眼,喃喃道:“是这样--前舱里住着的客人--”
水先生轻叹了一声道:“江上起风,只怕是多事之秋,老丈要注意了!”
白头老金皱了一下眉,心里真纳闷儿:这是怎么回事,不叫我说话。
“哼”了一声,老金再次开口道:“是这么回事,我来看水先生,是--”
“且慢--”水先生轻轻地摇了一下头。
老金不得不把下面的话吞在了肚子里,心里那股子别扭劲儿可就不用提了。
隐约间,像似传过来几声琴音,等到老金倾全力再听时,却又没有了。
经过了这么一搅和,老金要说的话是一句也说不出口,也没有兴趣再说了。
对方水先生这时竟然缓缓地闭上了眼睛,像是要休息的样子。
白头老金叹了口气,站起来道:“天不早了,我走了!”
水先生连眼睛也没睁,微微地点了一下头。
风浪比先前更大了。
由于受到了前舱的客人、那位史大爷的嘱咐,老金和他儿子金七,以及伙计毛五都不敢随便走动,没事的时候,只是在舵旁坐着发愣。
毛五终于打破了沉寂道:“我就是想不透,住在大舱里的那几个人是干什么的,说是官面上的人吧,可又不像,说是普通的老百姓吧,更不像,只看看那个姓史的人五人六的样子就不像,真想不透这一家子!”
金七冷笑道:“你就少管闲事吧,反正人家坐船给钱,我们管他是谁呢!”
毛五不好意思地笑笑道:“当然,咱们管也管不了啊,我只是心里纳闷儿,还有边舱的那位教书先生,也透着有点玄,怎么怪事都让我们给碰上了。”
白头老金默默无声地打着了火,点上了纸煤,吸了几口烟。
他眯着一双布满了皱纹的眼睛,正要说什么,忽然站起来道:“咦!”
金七、毛五也都发现到了,三人顺眼看过去,只见一艘双桅平顶、模样新颖的中型快船正由后方快速驰来。
金七一惊道:“唷!这是干什么?”
说时迟,那时快,不过是转念的当儿,那艘快船已来到了眼前。
三人才看清了,敢情来船备有一座看似尖猛结实的菱形船首,那种模样大异常船,倒有几分与洞庭水师的战船酷似。
老金第一个发觉不妙,忙叫了一声:“快!”
三个人同时行动,以最快速度,一个人操起了一根长篙,猛地向着右舷扑了过去。
是时,那艘看似战舟的来船,已风驰电掣地来到了近前,老金等三人三根长篙各自施出了全身之力,猛地向着来船船头点了过去。
来船突然的现身,本就有几分奇特,以如此神速硬撞前船,更给人无限扑朔迷离,一时真摸不清是何居心。
三根长篙虽说是劲力十足,奈何对方来势至猛,其力万钧,甫一交接之下,只听见“咋喳”一声脆响,金七手中长篙首先为之折断,老金、毛五二人手中篙虽不曾折断,要想阻住来船至猛的来势,却是不能,在甫一接触之初,已双双跌倒在地,摔了个仰面朝天。
这条看似战舟的来船,好疾猛的势子,由于整个船身不曾悬有一盏明灯,黑乎乎一片,更不知是否有人蓄意操纵。总之,以眼前这番猛厉来势,一旦撞着了,大船必将绝无幸免之理。
老金哑着啄子叫了一声,一个骨碌由地上翻起来,正待拼死命,再次以手中长篙向来船迎去。忽然面前人影一闪,一个熟悉的口音道:“闪开!”同时手里一阵子发热,手中长篙已被来人抢了过去。
惊慌中,老金方自看见来到面前的,正是那位史大爷,史大爷手上的长篙,已不顾一切地点向了来船的菱形船首,尽管如此,看来其势仍然是慢了一点。
史大爷鼻子里哼了一声,眼看着他手中长篙在对方巨大撞力之下,有如弓也似地弯了过来。
说时迟,那时快,就在这紧急俄顷之际,耳听着大船上传出了一声女子的清叱,紧接着一连几声暴响传自来船,眼看着高悬来船的四面风帆一齐自空中桅杆上高高坠落下来。
四面帆,每一面都有两丈长宽,加上碗口粗细的横木一齐自空中猝然落下,其势端的惊人已极。
一连串的惊人大响声中,总算阻止住了来船的冲势,这艘船在猝然失去了主力下,再加上沉重的落帆之力,一时摇摆动荡着,激起了滔天的巨浪,久久不能平息。
老金等三人目睹这番情势,早已吓得魂飞魄散,他们原以为无论如何难以躲过沉船的劫数,却万万想不到竟会在千钧一发之际,对方变生肘腋,竟会无故自落风帆,定住了来势,使得己方转危为安。
三个人只是怔怔地看着来船发傻,却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双手持篙的史大爷,想是在先前全力定船的一霎间用力过重,一张尖削的长脸,显示着沉重颜色,扔下了手上长篙,他一连咳了好几声,紧接着怒叱一声,右手一撩长衣下襟,“嗖”一声,已自腾身而起,向着对船掠身过去。
史大爷敢情身手不弱,休看他一大把的年岁,动作里却是透着“练家子”的利落。
来船上虽说是一片黝黑,却也逃不过史大爷尖锐的目光。他身子甫一落向来船,紧接着再次煞腰,第二次纵身而起,直扑向来船中舱。
猛可里两口钢刀夹着疾厉的刀风,分向史大爷左右两侧力劈下来。
姓史的脚尖才一着地,猛地来了一个疾转快翻,同时借招现式递出了右掌,“噗”一声,击中了右面持刀汉子的前胸。
这一掌,史大爷实实贯足了内力劲道,对方既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那里能承受得住?随着史大爷的掌势,痛呼了一声,球也似地被掷了起来,“扑通”一声,水花四溅里,落向江心。
另一个持刀的汉子,眼看着同伴遇难,那里还敢蛮干,猛然间一撤,递出了刀势,一拧身,“扑通”一声,自跃入水。
史大爷怔了一下,错齿出声道:“小辈!”
嘴里叱着,一面压掌前进,猛可里一道亮光直射眼前,史大爷猝然吃这道强光一照,只觉得双目生花,足下禁不住往后打了个踉跄。久走江湖的人,俱都知道这一手的厉害。
姓史的虽非江湖中人,可是阅历丰富,不假思索地向一旁猛的一个疾翻盘滚。
果然他没有猜错。就在他身子方自转动的一霎,三点金星串成一线,直向他身上招呼过来,总算他见机得早,否则强光射目之下,休想逃得开这一手暗算。
三点金星擦着他衣边直落江心。
史大爷虽说是技高胆大,却也由不住惊出了一身冷汗。
暗中人冷哼一声,手势一转,那道匹练般的灯光,又复直射在史大爷的脸上。
史大爷有了前番见地,倒也不惧他再施暗算,当下身形半矮,双掌盘错当胸,一双瞳子微微收拢,成为小小两弯月牙形状。这当口,却已经把对方打量个清楚。
矮矮的个头儿,沉绦色的两截裤褂,看上去油光水亮,多半是水衣水靠,手里端着喇叭口样的一盏长桶子灯,却在两手护肘处贴持着白光闪烁的一对锋利匕首,赤红脸,万字眉,灯光晃动时,隐约间还似可以看见脸上七上八下的几点大麻子。
就面相论,史大爷是无论如何也记不起自己印象里有这么一号人物。然而,对方身上的那绦色的水衣靠,以及手里的怪状长灯,却使他有所警觉。
一念触及,史大爷禁不住倒抽了一口冷气,自心眼深处打了个寒颤。“你,”史大爷紧紧咬着牙,压制往心里的张皇:“午夜劫舟,所为何来,好朋友你报上个万儿吧!”
“嘿嘿--史银周,光棍眼睛里可是揉不进沙子!”来人咧着大嘴,喝风似地那般笑着,那双深陷的眸子,原本就聚结着诡异莫测,再给灯光一映,更见狰狞。
“老兄你扒下了王府的那身号衣,就当我褚某人这双照子认不得你了--嘿嘿--你也太目中无人了!”
史大爷猝然被对方呼出了姓名,正如所言,那是“光棍一点就透”,刹那间,獃若木鸡,随着摇晃的船身,他身子打了个踉跄。
“褚某人?”史银周总算认清了对方的身分:“足下莫非是大内当差的人称‘短命无常’的褚氏昆仲之一,史某人眼生了!”
“好说,好说,阁下好亮的照子!”赤红脸喝风似地笑着:“不错,兄弟正是褚杰,家兄褚方来是来了,一时还不及拜候!”
史银周乍听对方亮出了字号,就知今夜绝不能善罢甘休,忖思着此行责无旁贷的重任,一时忧心如焚。
他久闻这褚氏兄弟在京畿为恶多端,为大内十三高手中之佼佼者,自己虽不曾与他动过手,料想功力绝不在自己之下。方才他出言相探,就是惟恐对方昆仲二人联手对付自己,现在既知褚方不在面前,总算少了一个劲敌,眼前说不得先把这个褚杰解决在现场,再图后算也还不迟。
心念一转,史银周两臂暗聚真力,丹田运气,外表却愈发显得持重。
“褚兄夜临江舟,有什么指教?史某洗耳恭听。”
借着双手抱拳的当儿,史银周已把他仗以成名的“一掌飞星”自袖内取到了手上。
所谓“一掌飞星”,乃是二十四粒大小如梧桐子的八角钢珠,史银周此技,得自家学渊源,其祖“巧天星”史功,正是此一暗器的始创鼻祖。二十四粒小小钢珠,妙在串成一串,平时配戴在两腕之上、用手捻指可得,一经出手,顿时在空中散开,由于数目多,照顾的范围极广,加以施功人充沛的内功掌力,如果存心伤人,对方即使身中一粒,如属要害地位,也当有性命之忧。
“短命无常”褚杰似乎不曾觉察到对方的这一手袖里乾坤,聆听之下,咧着嘴打了个哈哈:“史老哥这可就明知故问了。”
褚杰手里的灯光扬起来,照向远在咫尺的大船。
大船上的金氏父子与伙计毛五各人一把长篙,早已把对方船身钩了个结实。三个人心衔撞舟之恨,狠狠地瞪着褚杰,样子像是要把对方生吞了下去。
“史大爷,只要你老招呼一声,咱们就把这个老小子给做了,大可恶了。”说话的是白头老金的儿子金七。
史银周冷冷地说道:“用不着你们多事,只管拢稳了船,不要让大船离开了就好。”
褚杰一声怪笑道:“鄱阳王大势已去,立功论罪可全在你老兄一念之间,今夜褚某人单身会你,称得上仁至义尽,错过了今宵此刻,只怕又将是一番嘴脸了。”
史银周嘿嘿一笑:“食王禄,报王恩,姓史的要是怕死贪生,卖主求荣,也就等不到今夜此刻了。”
“哼--你的意思,是要与朝廷为敌了。”
“这,”史银周冷冷道:“桀吠尧,各为其主,史银周何许人,当不上褚兄抬举。”
“好!”褚杰点了点头道:“慢说你一个小小护卫营统领,贵主子的两卫精兵,我主一纸令下,兵不血刃,在洞庭也都缴了械了,如今叛王已押赴晋京,枭首在即,史银周--你有几个脑袋,竟然胆敢抗旨,私下里拐带罪臣孽子遗孀,哼哼--只此一罪,就足灭你九族有余--姓史的,怎么样,我奉劝你一句话,立功待罪,就在你一念之间了。”
这番话,出自褚杰之口,字字清晰,只把大船上的金氏父子等三人吓了个魂飞魄散,同时也知道了他们彼此的真实身分与来龙去脉。
史银周待对方话声甫落的一霎,一声狂笑道:“打!”
就见他身子陡地向下一矮,右掌已当胸平封而出,作为暗器手法来论,史银周这种打法可就端的称得上“高明”了。
“嘶!”一股尖锐疾风,发自他五指之间,其力至猛,其势至广,在他掌势当前的两丈方圆内外,这些暗器全都在内力控制之内。
当然,史银周绝非是想以单纯的劈空掌力伤他,而是配合在掌力内的二十四粒八角亮银钢珠,这些暗器,一经出手,迅速地扩散开来,成为扇面式的一片光雨,直向着看来毫无戒备的褚杰全身笼罩了过去。
“短命无常”褚杰岂能不知道史银周暗器的厉害,只是却不曾料到对方竟然会在如此正面相对的近距离之内施展,是以乍见此情,也禁不住吃了一惊。
他当然不是无能之辈。史银周暗器方一出手,褚杰整个身子霍地向后就倒,像是“铁板桥”,其实却又暗含着“蜉蝣戏水”的招式。
好漂亮的一式双招,配合着他的一个滚翻势子,手里那盏桶状百叶长灯,哗啦哗啦一声猝响,竟然迎着当空暗器拨打了过去。
史银周这时才忽然警觉,敢情对方手上那盏灯,竟然也能权当兵刃,这一点倒是他当初始料非及。
果然,随着褚杰抖出的势子,手里那盏桶状长灯,蓦地脱手而出,在哗啦哗啦大片响声里,化为满天飞叶,就空向着史银周所来暗器迎了过去。虽然如此,因为变生仓促,仍然不尽理想,褚杰的身式尽管再漂亮,仍然是慢了一步。
“嘶!嘶!”两缕尖锐的劲风过处,却在这位当今大内高差“短命无常”褚杰身上留下了不深不浅的两处记号,一在左胸侧,一在右腿胯边。
虽然都当不上是什么要害,可是也够他受的,随着褚杰旋风也似的身子“呼”地旋出丈许以外,落在了战舟左边船道。他鼻子里厉哼一声,怒视着史银周道:“史老儿,好,你等着瞧吧!”
史银周满以为在自己暗器之下,对方不死必受重创,却想不到依然是让他从容逃脱,心里一惊,正待腾身攻进,却有人较他快了一步。
黑暗中传过来一声女子清叱,紧接着一条俊俏的纤细人影霍地自大船后侧方拔起来,夜鸟腾空般在当空略舒二臂,遂即以飞鹰搏兔之势,直向着“短命无常”褚杰立身处直扑了过来。
“短命无常”褚杰先是一惊,却又一声怪笑道:“好!”
“叮当!”一声脆响,双方兵刃猝然接触,褚杰是一对精钢匕首,来人姑娘却是一根打制得十分精巧的“鸠形短杖”。
由于这个姑娘的凌厉扑身之势,褚杰不得不向后疾退数步,只觉得右腿胯处一阵发酸,这才想到敢情方才被史银周暗器伤了不轻。
不容他多作深思,那姑娘,已经再次地欺身过来,手上银色的“鸠形短杖”再一次当头挥落下来。
同时,另一侧的史银周也由另一个方向猛然袭了过来,史银周决计不打算让这个褚杰活着离开,身子一来到,双掌乍然向下一沉,用“双撞掌”直击褚杰后背。
“短命无常”褚杰惊惶里,双手同时撩出,姿态是一上一下,上面的匕首迎向对方少女的“鸠形短杖”,下面的一把,却反迎着史银周面门上扎点过去。
“当”的一声,顺着褚杰的匕首过处,当空爆散出一片火星,褚杰架是架住了,震得他手腕子发麻。
那个姑娘,得势不让人,“鸠形短杖”猝然向下一压,翩翩然已转向褚杰侧方,左手猝然递出,骈二指向着后者肩头就点。
史银周虽是赤手空拳,但是一经进身逼近了敌人,便能发挥出十分威力,况乎还有那个姑娘助阵,情势更将不同,再者褚杰显然已为暗器所伤,情势越发地对他不利。
果然,在史银周与那个姑娘联手攻击之下,褚杰顿时大现不支。
霍地,褚杰跃出战圈之外。
就在他奋力急跃的一霎,却着了史银周凌厉的一式“披挂掌”,顺着后者箕开的五指下拉力道,褚杰左肩头一阵麻辣刺痛,连带着半个身子俱都为之发麻。
经此一战,这位惯以称狠恃强的大内高手,一时亦不禁为之胆战心寒,鼻里哼了一声,连话也来不及再作交待,当下双足用力一顿,直向江心跃去。
“哗啦”一声大响,水花四溅中,已然掩没了他坠落的身躯。
后来现身的那个姑娘,在褚杰纵水下落的一霎,一连发出了两口飞刀,却都失之过慢,双双落空人水。望着怒涛波涌的水面,那个姑娘连连跺脚叹息,一副失望的样子。
史银周以最快的速度,一连击开了两扇舱窗,摸着黑,在这艘看似战舟的船舱里转了一转。
那个姑娘跟进戒备道:“还有别人没有?”
史银周摇摇头没有说话,看了面前的姑娘一眼。
面前姑娘瘦高的身材,细细的腰肢,两根漆黑的发辫盘结在头上,虽然时当黑夜,亦能显示出她的机灵透剔,正是日间在舱门处与史银周答话的那个姑娘。
“我本来早该出来,是小姐要我照顾着夫人和小少爷,”她忿忿地道:“要不然,这个家伙,无论如何,也别打算能跑掉。”
史银周一惊道:“你是说翠公主她不在舱里?”
细腰姑娘轻轻嗯了一声,一双长长的眼睛向四周瞟了一眼,道:“来,史大叔,咱们回去说话。”
二人双双纵过来船。
史银周走向持篙发獃的金氏父子三人,正待说些什么,却见以白头老金率先的三个人,忽地扔下手中篙,一齐向着史氏跪倒在地。
史银周一怔道:“咦,你们这是干什么?”
老金一面叫头道:“老大人,--请多--请多包涵,小人们早先是不知道大人你们的身--身分--多有冒犯,罪该万死--罪该万死,还请大人多多原谅才好!”
史银周皱了一下眉,看了一旁那个盘辫子细腰姑娘一眼,冷冷哼了一声,向着老金等三人道:“你们敢情都听见了?”
老金喃喃道:“小人该死--小人该死!”
史银周一声叹息道:“这又与你们有什么关系,起来吧。”
三人一齐应了一声,又磕了个头,才站了起来。
史银周目注着老金道:“船老大,既然你们已知道了一个大概,我也就不再瞒你,方才的情形你们是看见了,保不定他们还会再来。”微微一顿,他低头叹息了一声。
老金忽然义形于色地道:“老大人请放宽心,鄱阳王--”
史银周低叱道:“小声。”
老金立刻把话吞住,一脸惊惶失措的样子。
“大胆!”史银周轻声叱道:“你好大的胆子!”
老金后退一步,躬身颤惊道:“小人该死--”
站在一旁那个盘辫子的细腰姑娘听到这里,移步过来,小声向着老金道:“船掌柜的,你千万记住,以后无论在什么地方,人前人后,都不能再提起刚才说的那三个字--”
说“那三个字”时,她的语音带戚,像是强咽着满腹的悲伤,快要哭的那种声音。
老金等三人对看了一眼,脸上也都染了悲戚神色。
“小人该死!”老金垂首道:“小人记住了。”
史银周道:“你要说的我都知道,难得你们三个草野村夫,居然还能有这番心意,也不枉--”说到这里,禁不住仰天长长发出了一声叹息。
当空月白风高,不知何时乌云尽去,一轮明月复出云表,洒下了如银月色,将此大江内外景色映衬得一如图画,大船上的一切,更是清晰在目。
白头老金抱拳躬身道:“小人父子等三人,愿以性命,为老大人效死--”
史银周哼了一声,摇摇头道:“那倒不必,只把船早日靠到地头就好了!”
老金道:“小人遵命。”
他儿子金七看了一下天,道:“月色这么好,可以加快赶,要是再遇顺风,不出三天,一定能赶到鄱阳。”
史银周点了点头,道:“好,不过,行程也许会临时有些改变,到时候我自然会通知你们!”
老金等俱都应了一声。
史银周挥手道:“你们去吧。”
三个人应了一声,正要下跪,却被史氏止住。
“你们这是干什么?”
史银周脸上罩着一层阴森,冷笑着加上了一句叮嘱:“以后人前人后,不许带出一些特别样子,要是为此坏了我的大事,你们--”摇摇头,他情不自禁地又发出了一声叹息。
老金喃喃道:“小人知道--小人是因为这里没有外人,所以才--才不敢失礼。”
“没有外人?”史银周锋利的目光,向着船后的边舱瞟了一眼:“你敢说没有外人?”
老金顿时为之一怔,道:“不是,老大人--”
史银周哼了一声,老金立刻改口道:“史老爷--史老爷不提起来,小人却是忘了,明天船就到汉阳,小人一定请他下船就是了!”
“那倒不必了,”史银周冷笑一声:“错在当初你不该让他上来,既然来了,再赶他下去,反倒不好,你们只要严防着他,不许他往前面接近就是了。”
毛五上前一步,接口道:“史老爷放心,那位相公他身上有病,你就是请他出来,他也不出来哩!嘻嘻!”
老金叱道:“你是怎么跟老大人说话?”
毛五一怔,绷住了笑脸。
史银周脸上这时才带出了一丝笑容,连连点头道:“我就是要他这个样子。”一转脸看向老金道:“你们也要学他这个样子说话,要是带出了一丝痕迹,落入外人耳目,只怕你三人性命不保!”
三个人又是一惊,对看一眼,史银周挥挥手道:“你们下去
三个人应了一声,这才转身离开。
看看他三人回到了舵房,史银周才转过脸向着那个细腰姑娘轻声道:“翠公主--”
细腰姑娘轻咳了一声,翻着两只眼道:“怎么,你自己也忘了?”
史银周戚然一笑:“现在无妨。”
细腰姑娘努着嘴,向着那边道:“那边船舱房里不是还有人么!”
史银周皱了皱眉:“这个人暂时看不出什么动静。”
细腰姑娘道:“哼,那可不一定,不过,小姐已经注意上他了!”
把“公主”改口“小姐”,显然有深刻的意义。
“夫人和少爷呢?”
“都睡了,”细腰姑娘说:“大叔,我们进去说话。”
二人迈步入舱。
大舱里布置华丽,两名青衣长身武士分立在通向内舱的门边左右,二人虽然是便装,可是神色持重,立态庄严,一副谨慎从命,如临大敌模样,各人背后都佩着一口青鲨鱼皮鞘的青钢长剑,剑穗子一色的杏黄,一望即知就是训练有素的公门剑士。
望着史银周,两名青衣武士一齐抱拳见礼。
史银周道:“你二人可曾发现了什么动静没有?”
左面武士抱拳道:“启禀统领,这里很安静,只是适才小主人啼哭多次,现在安静了,属下未敢擅人舱内探视!”
这名武士宽额头,浓眉黝黑,三十上下的年岁,和另一位瘦长身材,授着精明干练,看来白皙的青年,恰恰相反,正是不同类别的两个典型。
史银周聆听之下,皱了一下眉,一旁那个细腰姑娘早已闪身而入,须臾,又步出。
史银周忙问道:“小主人现在怎么样了?”
细腰姑娘微笑道:“没有”事,宫嬷嬷在一旁服侍着,宫嬷嬷说小主人是吃坏了肚子,两个时辰不到,已经如厕了三次,所以才会啼哭。”
史银周轻叹一声,落寞地坐下来道:“宫嬷嬷也是太大意了,舟途之中,要特别注意小主人的起居饮食才好!”
细腰姑娘点点头,道:“我已经吩咐她了。”
“她怎么说?”
“她,”细腰姑娘挑了一下眉毛:“哼!她说这是她的事,不要我多管。”
史银周怔了一怔道:“糊涂,她太任性了,我去说说她去。”
细腰姑娘一笑道:“算了,大叔。”
史银周原要站起来的身子,遂即又坐了下来。
细腰姑娘道:“宫嬷嬷说,小主人是她从小照顾大的,若有什么差错,她用命来赔,你看,她说了这种话,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史银周无奈地叹口气道:“这个老婆子。”
细腰姑娘挑了一下眉,又轻叹一声道:“不过,要说对于小主人的关怀,这多少年来,宫嬷嬷的确是无微不至,再说她那一身功夫,即使翠小姐也对她赞不绝口呢!有她在小主人身边,倒是可以放心的了!”
史银周愣愣地道:“但愿如此,只怕--”
微微一顿,他轻叹一声道:“翠小姐呢?”
细腰姑娘沉吟了一下,欲言又止。
史银周立时会意,目光一扫那两个身着青衣劲装的武士道:“马裕、杜飞,你们两个到外面去小心看着,有一点风惊草动,立刻来通知我。”
黑硕白皙的两名武士听聆之下,各自抱拳应了一声:“遵命!”遂即双双步出舱外。
史银周还不大放心地特别去到舱门前看了一眼,见马、杜二人俱在左舱两舷,距离颇远处设岗站定,忖思着舱内谈话绝不至为二人所闻,这才又转回来。
“好了,”史银周道:“新凤姑娘,现在你可以说了,其实我手下侍卫营的兄弟,全是忠心耿耿的勇士,足足可以信得过,你也未免太过仔细了。”
被称为“新凤”的那个细腰姑娘微微一笑道:“史大叔多疑了,婢子岂敢对史大叔手下弟兄有所猜疑,只是翠公主的脾气,您是知道的,她不愿意的事情,谁也不能勉强。”
史银周点点头道:“这话倒也不假,翠公主是不愿意要人家知道她那一身杰出的功夫,其实对于王府上下来说,早已有此传闻,已经算不上是什么秘密。这倒也罢了,姑娘还是快说出公主的下落吧。”
新凤点点头道:“翠公主午时以前已出去了,说是去探察一下可疑的敌踪。”
史银周一怔:“你是说,船开了以后,公主才出去的?”
新凤点点头。
史银周脸色一变,喃喃道:“我早知公主一身武技不落凡俗,却万万想不到竟然会达到如此造诣。这么说,公主竟然能够踏波而行了。”
“这,婢子可就不清楚了。”
她说话时,脸上带着神秘的笑,虽未明言,事实上却也等于承认了。
史银周正待说什么,忽然一阵风过,半掩着的两扇窗扉忽然徐徐张开了。
就在新凤与史银周同时引目注视之下,一条疾劲纤细的人影,已然掠窗而入。
大舱内人影闪了闪,一个粉面长躯的俏丽佳人已站立当前。
史银周一惊之下,忙自起立躬身抱拳道:“卑职史银周,参见公主。”
新凤也上前行了个万福道:“小婢参见公主。”
来人少女敢情正是当今鄱阳王的掌珠,人称“无忧公主”,名叫朱翠的传奇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