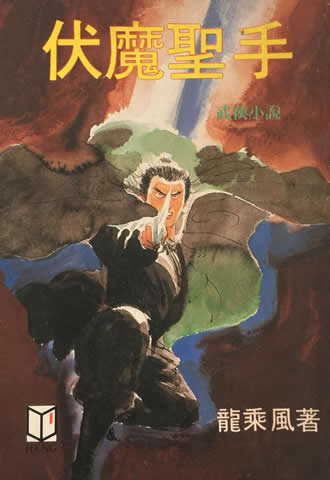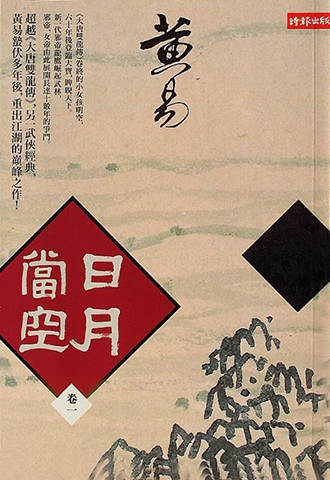褚天戈怔了一下之后,眼睛仍然注视着楼栏上二人的拼搏,嘴里说道:“为父用人一向把才能放在首位,崔教头莫非有什么胡作非为不成?”
夏侯芬还不曾说话,那位三姨娘就冷冷一笑,道:
“老王爷,这些话您老人家不自己问,哪一个人敢说呀!既然您1起,贱妾可就有一句说一句了!”
褚天戈脸上现出了一丝不悦,冷冷地哼了一声,道:“你说吧!”
三姨娘把那张朱红的樱桃小嘴撇了一撇,道:
“哼!多着呢,这金沙郡里里外外,谁不知道崔教头是老爷子您跟前的大红人,谁敢惹他呀!”
三姨娘是褚天戈跟前最得宠的一个爱妾,崔平是最得宠的一个部下。
双宠难以并立!
有时候崔平自视过高,对于这位三姨娘不那么十分买帐。
三姨娘可就有些不是味儿了。
“金沙郡除了老爷子以外,他还在乎谁呀!”
三姨娘呶着红唇道:“不要说别人了,有时候我跟他说话,他都是爱理不理的呢!”
夏侯芬道:“崔教头武功不错,这是真的;可是他心术不正,替您老人家在外面招了不少非议。女儿本诸爱护义父之心,却要提醒义父多留意点!”
这几句话,褚天戈可是听了进去!
他现在正是在走“收揽人心”的路子,希望日后一朝称帝能够得逞。陡然听到了这些话,哪能不为之震动?
他那张大红脸,一瞬间变得苍白,老半天没有说出一句话。
了解他的人,都知道话不能再说了,“到此为止”是最好的办法。
三姨娘本来还有满肚子的牢骚待发,看见他这副面色,就知趣地不再多言。
褚天戈一言不发!
三姨娘、夏侯芬也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在比武的楼栏上。
也就在他们的目光方自集中的刹那间,那场战斗已然分出了胜负。
堪称是巧妙的一式对击!
崔平身子腾在空中,像是一只燕子那样直向江浪身上袭来。
江浪却把身子猛地向下一伏。
崔平紧紧擦着江浪的背掠过,一双足尖踢了个空,江浪的身子蓦地暴伸而起。
这一掠一起,其间之微妙,设非当事人,外人可难体会!
立在窗内的褚天戈,看到这里,叹一声道:“崔教头败了!”
这个“了”字的尾声还未消失,江浪的一双手掌已经击在了崔平的后背上。
江浪显然是手下留情!
崔平却是招架不住!
他足下一跄,沉重地撞在楼栏上,只听见“喀嚓”一声,红木扶手硬生生地从中折断。只见崔平立足不稳,一头向着湖水落了下去。
“扑通”一声,水花四溅!
尽管崔平有一身极好的水功,可是无论如何,这个脸是丢定了。
他是一百个不甘心!
随着他身子一个侧滚,手掌暗聚真力,用力地向水面一击,打出了一股水箭。
白光一闪,这道水箭直向着江浪身上射来。
江浪身子一闪,这股子水花足足射出了十数丈以外,然后劲道消失,幻为一天水珠,散落湖面。
胜负已分,而且是在众人面前。
四下里爆发出一阵子掌声!
江浪向着水里的崔平一抱拳,道:“承让!”
崔平气得大叫一声,他双臂力振之下,带着大片的水花“哗啦”一声,拔身在楼廊之上。
“姓江的!”他气息喘喘地道,“小辈!”
右手向腰里一探,霍地向外一翻,只听得“铮”的一声脆响。
一杆九合金片的如意软棒,已经现了出来!
崔平在盛怒之下,想借用兵刃的帮助,为自己找回面子来。
正当他把这杆“九合金丝棒”抖了个笔直,妄图向江浪前额上点扎过去的时候,观赏的众人震惊得嚷叫了起来。
也就在此刻,楼廊内的褚天戈发出了一声断喝道:“住手!”
崔平闻声而惊,金丝棒原已递出,又硬生生地收了回来。无边的怒火,使得他抡圆了手中软棒,“叭喳”一声,重重地抽在栏杆上。
碗口粗的栏杆柱子,顿时被棍棒砸得一片稀烂,他足下飞点着纵身而出,落足在远处的荷叶上,施展起了“登萍渡水”的轻功绝技。当他落身到岸之后,头也不回地一径去了。
立在窗边的褚天戈冷笑了一声,目视着崔平背影消失了,才转向江浪道:“江壮士,请上来!”
江浪高道一声:“遵命!”
双足力顿处,起身如箭,“飕”一声足下拔起了六七丈高,向褚天戈等三人坐处楼窗扑来!
看到这里,三姨娘又发出了一声惊叫。
江浪为了卖弄身手,便把纵起的身子猛然向着楼栏前一扑,单手一按栏杆,全身向里一翻,翩若巨鹤般地让身子稳稳地落在大厅之内。
他气不喘,脸不红!
就连不懂武功的三姨娘也看出好来了,两只粉团般的嫩酥手拍了一下道:“好呀!”
江浪抱拳向着面前的褚天戈一揖道:“老王爷见笑了!”
褚天戈哈哈大笑。上前一步执起了江浪的双手。
这个亲热动作,便得江浪不知所措,倏地挣开,向后退了一步。
褚天戈微微一怔。
江浪躬身道:“在下一身肮脏,怕脏了老王爷的衣裳!”
褚天戈微微一愣,遂大笑道:“江壮士,好本事。佩服,佩服!”
“老王爷夸奖,在下这身本事,比起老王爷来,只怕差得太远了!”
“嗯?”诸天戈皱了一下眉,道,“你怎知道我会功夫?”
江浪道:“是夏侯小姐说的!”
褚天戈转向夏侯芬,问道:“是么?”
夏侯芬道:“是的,是我告诉他的。”
褚天戈哈哈笑道:“不错、不错,我是练过功夫,不过那是早年的事了……江壮士,我要问你,愿意接我一掌么?”
江浪低头道:“在下岂敢与老王爷对掌?”
褚天戈说道:“不必客气,来、来、来。”
他一面说一面缓缓地伸出一只手掌,足下八字步分开跨立,嘿嘿笑道:“说不上对掌,只是较上一掌之力,谁的身子移动,谁就算输了!”
江浪心里一转念,暗忖着:不知道这老儿如今功力到底如何,趁这个机会试他一试倒也无甚不好!
想到这里,便暗聚真力于右掌之上,抱拳道:“老王爷掌下留情!”
言罢,身子“老子坐洞”式地向下一坐,一只右掌平伸而出,抵在了褚天戈的手掌之上。
两张脸都不禁为之一红!
紧接着,两人的手掌就像是被胶粘在了一起一样,看上去纹丝不动。
这正说明双方势均力敌。
可是时间并不很长,约莫有半袋烟的时间,即见褚天戈倏地眸子一睁,右手霍地抖动了一下,江浪身子摇晃了一下,禁不住后退了一步。
他脸上一阵子飞红。
褚大戈见状,说道:“小伙子,不要张嘴说话,坐下来!”
他说得不错,凭着江浪的功力,只要不张嘴说话,静下来把这股冲关而起的气机压下丹田,就保住不会受伤;否则,只要一开口说话,气血上涌,当场就得大口吐血,内伤肝脾,
江浪当然知道这个道理。
他静静地步向一边,缓缓地坐下来,双目下垂、闭口不语。过了一段时间,才重新睁开眼睛。
这时,他的脸色已经回复如初。
褚天戈含着微笑,站立在他面前,点着头道:
“不错,这些年以来,我还没有见过比你强的年轻人。小伙了,你休息一天,明天到武术团应差去吧一崔平那个位置是你的了!”
江浪抱拳道:“谢谢老王爷!”
一时间,他内心真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当他大步走出来时,两汪热泪早已夺眶而出j
※
※
※
夜凉如水。
明月似雾。
几许秋风,兴起了一些寒意。
萧索的落叶,更不禁为客居的游子平添了尖忄怅惘。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人们惯以巧妙的智慧双手,为自己编织许多美好的未来;然而当未来成为现实时,你又会发觉现实的不尽如人意。
那是因“人”与“事”的结合而导致的。
因人成事,事左右人——这是千古不易的哲学大道理。
人人都为别人着想,固然是好!
人人都为自己着想,也不算坏!
如果想到自己,又想到别人,似乎是再好不过;如果想到自己,算计着别人,那可就不妙了!
偏偏这个世界上,竟有那么多的人是属于后一种类型一这就难怪天下大乱了……
※
※
※
江浪睡在软榻上。
那是因为他如今已经取代了崔平的位置。
岂止是一方软榻!
就物质生活上来说,他已经享有了一切,包括醇酒美人在内。
今夜,当他带着八分酒意之后,他破题儿第一遭玩了女人!
信不信由你——活了近三十年,这还是第一次。
对于所爱的人,那是“爱”和“奉献”;对于不爱的人,那就是“玩”、是“嫖”、是“作贱”!
不止是“作贱”对方,同时也是在“作贱”自己。
人们惯以“一度春风”、“几番云雨”来形容这档子事。对于大多数当事人来说,“春风”早已成了“秋风”。春变成秋,已是可悲,残余下来的一些“风”的快感,以及萧索的自慰意识,只是勉强地供你咀嚼而已。
于是,美芸众生就是这般慢性“作贱”着自己。
“童贞”与“处女”是同样的可贵。人们的快乐正是在于“保守”这种“可贵”的节操,如果一旦连这最宝贵的东西也看为平常时,你将是何等地不幸和可悲!
江浪的不幸与可悲,正是在于他虚掷了他可贵的童贞。
那个姑娘是老王爷赏下来的跟前人。
褚天戈对于自己所赏识的人,一向是采取用女人笼络的手段。那姑娘叫“芳芳”—
—属于诸天戈手下十二金钗之一。
江浪原先不打算接受。
然而,在几杯苦酒下肚之后,那个芳芳来了。
带着满脸的笑靥和无限羞涩,芳芳投入到他的怀抱里……
江浪就糊里糊涂地干了这件事!
芳芳失身子他酒后的猖狂,却在他清醒后的冷漠里悄悄地离开。
江浪后悔干了一件傻事!
犹记得那个小妮子,半赤着身子,挺委屈却无怨言地收拾着残局时,他吃惊地发觉到被单上的一抹朱痕——那是血!
一个处女宝贵的贞操,原是应该在新婚洞房之夜贡献给她所爱的丈夫,而她却这般随便地送给了他。
为此,江浪心里很内疚。
芳芳离开的时候,他的酒己醒了一大半,现在可以说是完全清醒了。
正是因为他已完全清醒,才会这般痛苦、这般深深地谴责自己!
来到“金沙郡”,已经好几天了。
“独眼金睛”褚天戈似乎还不十分相信他——虽然得到了“武术教导团”的总教头这个职位,可是却不像崔平以前那样随时可以到褚天戈的身边。
褚天戈还在暗中考查着他。
他也一直耐心地等机会。
今夜,褚天戈送来这个女人芳芳,并非是没有用意的;而江浪的接受,也并非全因酒醉,多少是含有一些心机意味在里面。
江浪隐隐约约觉察到,在褚天戈的想象里,认为一个人接受了他馈赠的女人之后,才算是死心踏地地属于他,才能算是一切听令于他的死党。
江浪真有些为自己感到可悲了。
在以往的几个晚上,他不止一次地感到热血激动,不止一次地拿起宝剑,想悄悄地潜进“心明阁”,待机向褚天戈下手行刺。
这种意念,后来终因为他慎重地考虑之后,放弃了行动。
记得初来的那一天,他与褚夭戈曾经对掌一回,也就因为那一次,他发觉到这个老头儿功力高出自己很多,所以暗暗地留下了深深的戒心。
夜风轻轻启动着窗扇,发出了吱吱的声音。
透过这扇敞开的轩窗,可以看见院子里扶疏的花木、飞檐、雕栋,看得那么清晰、真切。
这是金沙郡王的禁宫所在,入夜才会显得格外的宁静。
几盏油纸大灯笼,用高高的竹竿挑着,点缀在不同的角落里。
凡是有灯光的地方,必定伫立着一个守更的卫士——这些卫士,都是在武术教导团里经过长久训练、严格考试挑选出来的高手,所以他们每一个人都有高来高去、徒手飞搏的能耐!
褚天戈为了保障自己的安全,在禁宫部署了一个连锁反应的“十面飞魂阵”。
这其中的奥妙,江浪还不十分清楚,不过他却知道这阵势,是由一百二十九名武功高强的能手组合而成——一百二十九个人散置在一百二十九处地方。其微妙处,当然在于牵一发而动全局!
这就是说,当你惊动了其中任何一个人时,也就等于同时惊动了一百二十九个人。
那么,一百二十九人同时攻击,自是威力可观了。
况且,这么一来势必把整个禁宫的大小头目和众武士全动员起来。
江浪之所以迟迟不敢轻举妄动,对于这个“十面飞魂阵”的顾忌也是原因之一。
他披上衣服下了地,把半开的窗扇关上,正要返过身子吹灯,门上忽然“笃”地响了一声。
有人用指尖轻轻弹了一下!
“是谁?”
“我。”
说话的是个女子。
“你是……”江浪紧张地道:“请你等一下!”
他匆匆地穿好了衣服,把房间里略略整理了一下,然后开了门。
门外空空如也!
这扇门内通楼下大厅,大厅是八角形,共分四面楼梯通向楼上——整个大楼四通八达,共有石舍数十间之多!
大厅四角,各亮着一根松枝火把,火光熊熊照耀得远近清晰,在确定没有任何人时,他迅速回到了房间。
然而,当他再进入卧室时,一件稀罕事儿发生了。
一个披散着浓黑长发的姑娘坐在椅子上!
江浪怔了一下,急忙关上了门!
“你是……”
“午夜打搅,请江先生海涵!”
她的话音刚落,便倏地回过身来!
“是你……苓姑娘……”
几天不见,她消瘦多了。
倒是那双大眼睛,却并没因为忧郁而失色。深邃的目光,含蓄着潜在的毅力和智慧——一种女孩子的静态美,在她顾瞬的一刹那,展露无遗。
“对不起……”她苦笑着道,“你来了好几天,我才来看你!”
江浪道:“姑娘可好?”
“还……好!”
她轻轻地叹了一声,漠然地道:“江先生你说得不错,褚老王爷早先的名字是褚天戈。”
她紧紧地咬了一下牙齿,无限怅恨地道:“我已经查明白了,他以前的确是横行沙漠的土匪头子!”
说这些话时,她的脸色显得很苍白。
由她的语声里,可以体会出她内心蕴藏的潜在恨意。
“苓姑娘,你先安静下来,我还有许多话要问你!”
小苓默默地点了点头。
江浪仔细地注视着她的脸,叹息了一声,道:“苓姑娘,对于你小时候的事情,你一点都不记得了?”
小苓苦笑着,摇了摇头。
江浪道:“你姓郭,是不是?”
小苓怔了一下。这个瞬间的动作,只能表明,这个姓氏她听起来似乎很熟,除了这一点以外,就没有什么其他的意味了。
“你爹叫郭松明,是鲁东人氏。”
小苓不待他说完,又苦笑着摇了一下头。
“没有用,江兄!我真的一点也记不起来了!”
“你一定能够记起一点来的!苓姑娘,你总能想到一点什么,把你知道的,全说出来!”
“我……”她略似羞涩地看着他,道:“我什么也记不起来了,只记得……小时候我穿的大花鞋!”
她脸红了一下,又窘笑着道:“这不会有什么意思的!”
“不,有意思!”江浪点点头,说道,“你那双大花鞋是红色的,鞋尖上缝着一块白白的兔子毛。”
小苓顿时一呆,道:“你……你怎么知道?”
“我怎么不知道?”江浪凄凉地笑着,“你们家后面是否有一条河,河里有成群的白鹅……”
“白……鹅……白鹅,啊……是的,是的!”
霎时,她脸上绽开了笑容。
“有一只老公鹅,啄了我一下……”
“那只鹅是桑家养的……桑大爷你记得吧!”
“我记得……”小苓的眼睛睁大了,“他老人家是不是有个女儿?”
“他女儿叫小芬!”
“小芬……芬芬!芬芬……”
“你记起来了!”
江浪眼睛里噙满了泪水——高兴了!
“芬芬、二槐、长弓。”他一连串地说出了这些名字。
苓姑娘的脸上展现出极为兴奋的笑容。
“长弓!”她忽然脱口叫出了这个名字。
江浪倏地呆了一下,喃喃地道:“你记得这个人?”
苓姑娘道:“我记得!长弓哥,江家的长弓二哥!”
江浪眸子里突地流出了热泪!
他抬起手来,用手背把脸上的泪揩了一下。
“江兄,你……怎么了?”
“我太高兴了!”江浪说,“姑娘你果真是姓郭了!”
小苓脸上现出无限神往的样子,喃喃地道:
“长弓哥……我记得,我记得,他的飞刀最准了。有一天,他与人家比刀子,手被刀划破了……”
“是你母亲为他裹的伤!”
“你……你怎么知道?”
苓姑娘脸上岂止是惊喜,简直有些惊骇了!
“姑娘,你仔细看着我。”
苓姑娘把略带羞涩的眼光移到了江浪的脸上。
“你不觉得有些脸熟么?”
“我……你是……”
“我就是姑娘刚才嘴里说的长弓哥啊!”
“啊!”小苓打了个哆嗦。
“长弓是我的小名,江浪是我的大名!”
“江浪,江浪……”
小苓嘴里一再重复着这个名字。忽然,她那双美丽的大眼睛闪出了泪光!
“江浪哥,我记起你了!”
就连江浪也没有想到,她竟然会猛扑了过来——她紧紧地抱住了江浪的身子,兴奋得痛哭了起来。
十五年的谜结,忽然被人解开——眼前的人正是几时的玩侣,她怎能不喜极而泣?
“江浪哥……江浪哥哥……”
她如同梦吃般地叫着,泪如泉涌,把紧贴着江浪的胸衣都湿透了。
江浪不胜感慨地叹息着。
他的手情不自禁地摩掌着她柔软的秀发——这一刹那,使他忆起了小时候那一次她被鹅咬了的样子——也是这样地伏在他的身上啼哭不止。
恁他是铁打的汉子,心也碎了!
家破人亡,孤魂万里,上千的族人惨遭杀戮———切的一切都冷却消失之后,居然像梦幻一般,老天爷还能安排他会晤到几时的玩侣……
他的心真碎了,一时有说不出的感伤!
彼此的心里都燃烧着激情的火,包含着悲痛的压抑和热烈的放纵。
感情由死寂升华到沸腾,这其间只是一刹那!
人非圣贤,孰能无情?
当江浪抖颤的双手捧起她沾满泪水的脸庞时,郭小苓再次投入到他的怀里。
“长弓哥……噢……哥哥……”
像是梦吃,她嘴里喃喃地诉说着。
两张脸,像呢喃的燕子,耳鬓厮磨不已。
原是无波的古井,却为猝然投落下的石子,激起了轩然大波!
长年被忧郁、悲痛压抑着,只是在孩提时候才开颜笑过……
他们太需要爱了1
他们紧紧拥抱着,直到两张火热的唇接在了一块儿。
不知何时,他强有力的身子压在了她身上!
他像是一只发情的兽,吻着她的唇,亲着她的脸、颈项、秀发……
她何曾服过人?
虽然是千娇百媚的女儿身子,却比男孩子更倔强。金沙郡里上上下下,从来不曾见过她的好脸色,都说她是“水仙不开花——装蒜”。然而,这朵蓓蕾终于绽开了。
江浪简直不明白,自己怎么会有这番勇气。
他真不知道自己是在做什么!
直到她赤裸的身子,呈现在他眼前时,他才像触了电似的,震惊不已。
她柔弱的就像是一只羊。
一只小羔羊。
那么娇声地喘着。
星星似的剪水瞳子,似乎失去了昔日的威凌,无限乞怜、求助地看着他。
淙淙的情泪,溅满了粉颊香腮。
羊脂般的娇柔身躯,散发着处女的芳香,像浪女那样,放纵地扭曲着……
“不,不能!”江浪挣扎着跃起了身子。
她用一只手紧紧地抓住了他,尖尖的五个指甲,深深地陷进了他的肌肤里!
他转过脸来。
她一言不发地看着他。
那抹白玉般的酥胸,剧烈地起伏着!
“江哥……我……我……”
江浪用力地摇着头说:“我们不能这样!”
“为什……么?”
“因为……因为……”
她把他用力地拖过来,江浪不由自主地把她赤裸的身子抱了起来……
老天爷像是有意促成这一件好事!
不知什么时候,那盏灯自然地熄灭了。
漫长的一夜……
※
※
※
正如同那些使人厌恶的日子一样,任何美好的时光也终究会过去的。
几番蜂狂蝶浪,几度交颈呢喃……
在生命呈现半休止的状态时,他如同烂醉,沉沉地睡着了。
天色接近破晓。
第一只雄鸡由畜场鸡笼里拍打着翅膀跃上篱笆,方自啼了半声,小苓就悄悄地翻身下了床。
她脸上带着醉人的晕红——羞答答地回过眸子瞄着他。
蒙胧的意态里,那张脸,那张唇,赤裸着的胸肌……
这一切都是属于她的!
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既感到欣慰,又觉得仟悔;明是喜悦,却又感伤……真是“宿粉残香随梦冷,落花已上燕巢泥!”
她轻轻地叹息了一声,摸索着将散落在各处的衣衫穿好了。
女孩子家在任何情况下,都较男人要细心一些。犹记得倒凤颠驾间,落红缤纷……
那些见不得人的污秽,她都小心地归置在一起。
倾耳细听了听,室外没有半点声音。
她再次悄悄地走近床前,像是责怪却又爱怜地细细打量着他。
伸出手把他那根粗黑的大辫子掂起来,轻轻地放在枕边。
她定定地对着他,心里暗自虔诚地许了个愿。
“今生但把檀郎守,恁他东风、西风,毫不改这寸心相思!”
嘴角牵动起一丝微笑,轻轻掠了一下长过肩头的秀发,她悄悄地开了门,闪身而出……
江浪来到练武场的时候,已是日上三竿。
只见赤膊着上身的小子们,早已经拉开架势,捉对儿厮打着,拳来脚往,实打实摔!
总教头来了,大伙儿肃然起敬,紧接着爆发出一阵子掌声。
那天在“心明阁”江浪与前总教头崔平比武的事,大家都亲眼看了个痛快。对于江浪那身功夫,一个个佩服得五体投地。现在江浪接替了总教头这个职位,除了崔平与桑二牛二人以外,人人,心服口服。
江浪装模作样地在场子各处转了个圈儿之后,便来到了“总教头”的“督练房”,小厮过来递上手中肥皂,泡上了热茶。
这就是他每天例行的公事。
而昨夜,他竟干了一件毕生最荒唐的事儿!
郭小苓的来去,对他来说,真有梦幻的感觉。
只是哪有这么真切的梦境?
憧憬着那些片段,他真有些恍恍然。“这毕竟是他平生从来也不曾尝试过的感受,此刻想起来,心中禁不住卜卜乱跳,像是倒了个五味瓶儿一般,说不出的酸、甜、苦、辣……
他这里正自意乱情迷,就见方才倒茶的小厮入内道:“总教头,大小姐有请!”
“哪个大小姐?”他说了这句话,立时就觉出多此一问,即道,“是夏侯小姐么?”
小厮欠身道:“是……大小姐请您去一趟!”
“她在哪里?”
江浪心里透着希罕,自从那一天在“心明阁”见过她以后,到现在还一直没跟她照过面儿,忽然承她召见,不知是个什么路数!
“小的也不知道!”小厮道,“大小姐那个使唤丫头小红在门口等着您呢!”
江浪道:“我知道了!”
说完就站了起来,步出“督练房”。
小红约莫十五六岁,像是挺机灵的样子,她老远看见了江浪,就急忙跑过来请安。
江浪道:“是夏侯小姐要你来的?”
小红说:“大小姐在后院驯马,说请总教头去一趟!”
江浪怔了一下,问:“驯马?”
小红道:“是老王爷早先赏的两匹蒙古马,性子烈得不服人,这一回总算让大小姐制服了!”
江浪原本提心是不是有关郭小苓的事,听她这么说,倒放下了心。
当时就由小红在前带路,穿过了一大片草地,来到了一幢大楼房前。
这地方,也属于禁宫的一部分。
从这里穿过上道长廊,绕到这座大楼房的后侧方,便是一大片草地。
江浪的脚刚踏进,即听得一声嘹亮的马嘶。
一匹棕红色的骏马,上面骑着一个紫衣少女,迎面奔驰过士不。
马上的少女,正是夏侯芬。
今天看上去,她出落得极为标致!
她一身紫色劲装,脚着鹿皮长靴,小蛮腰紧紧地扎着,背上还背着一面长弓,皮鞍前侧箭槽上插着十来支雕翎。
那匹棕色大马,像是很不驯服,一路颠伏着跳跃而出!
招展的夏侯芬在马上笑着道:“啊哟,大哥!江大哥快来,这匹马我可怕了……”
随着那匹马不时地跳跃,夏侯芬更是叫个不停。这一刻,她真像个小女孩子那般夭真。
江浪嘴里应了一声,肩头微晃,来到了马身跟前。
那匹大棕马,果然是好烈的性子,唏聿聿长嘶一声,倏地扬起前蹄,直向着江浪身上踏来!
昔年,江浪有很长一段时间是与拜弟裘方靠着擒捉野马变卖为生的。所以对于任何类型的野马,他都有信心驯服,眼前这匹马,当然也不例外。
只见他喝叱一声,双手同时递出,左右各一,抓在了面前这匹烈马的口环上!
随着他双手用力拉下的势头儿,右面膝头霍地抬起,只一下就击中了大棕马的口鼻要害处。
说也奇怪,只是这么一下,那匹马顿时老老实实地安静了下来。
夏侯芬惊讶地道:“咦,你是怎么制住它的?”
江浪笑道:“过去,我捉过一个时期野马,懂得一点马性子!”
说时,夏侯芬翻身下马,笑嘻嘻地道:“老王爷出远门去了,没人管我,我想找大哥一块儿打猎去!”
江浪心里顿时一惊,道:“老王爷出去了?”
“今天早上走的。”夏侯芬说到这里,声音变得低低的,道,“没人知道!”
“他上哪去了?”
“去呼鲁兹,见海酋长!”
“谁是海酋长!”
“是个蒙古人。”她笑了笑道,“这个人很滑稽,自称是元朝开国皇帝成吉思汗的第六代孙子,可他偏偏不叫成吉思汗……”
“老王爷去找他干什么?”
“谁知道?他又不跟我说!”
说到这里,笑了一阵子,又道:
“我巴不得他老人家离开几天,没人再在我身子后面老嘀咕。江大哥,我们好像好久不见了,听说你当了总教头以后好神气哟,连人都不理了!”
“姑娘说什么笑话!”
“我说的是真的。要不然,怎么好几天连你的人影儿也没见到……”
江浪道:“姑娘身居禁宫,我岂能随便出入?”
夏侯芬瞅着他,微微笑道:“算你会说话,现在我把你请来了,总没借口了,巴!”
江浪道:“姑娘想去哪里打猎?就姑娘一个人?”
“不,两个人!”
“还有谁?”
“你呀!”
她说着,把马缰交到江浪手里,道:“你等一会儿,我牵我的马去!”
江浪说道:“姑娘的马,不是在这儿么?”
“这是给你骑的!”
说着转身就跑了。
不知怎么回事,江浪觉得心里挺不自在。
如果这件事在昨天以前发生,他不会觉得丝毫不自在。可是,只是一天之隔,就全然不一样了!
因为什么?
郭小苓!
直到现在为止,郭小苓的影子始终在他脑子里晃着。男女之间在发生过那种感情以后,必然是心心相印——那是什么力量也分不开的!
他的目光四处搜索着。
小红在一旁睁着一双大眼睛看着他。
江浪向她点点头道:“苓姑娘是不是住在这里?”
“早先是的,后来不知为了什么苓姑娘搬了出去,住在后院里啦!”
“她一个人?”
“嗯!苓姑娘怕吵,最喜欢安静!”
“夏侯小姐跟她来往不?”
“常常来往,刚才我们小姐还找过她呢!”
“找她去打猎?”
“不是!”小红摇着头道,“好像不是。找她做什么,我也不太清楚!”
江浪还想1些什么,夏侯芬就策马而来了,便把到嘴边儿的活吞了回去。
一刹那,他脑子里全让郭小苓占满了,迎面而来面如春花的夏侯芬,在他眼里反倒是黯然无色了!
夏侯芬策着马,鞍辔弓箭齐全地来到了面前。
“快上马呀,跟我去个地方,包你玩得好!”
说着,她已抖开缰绳,一马当先地冲在前边,江浪只得策马跟上去。
两匹马跑过了面前的这片草地。
前面是一片生满了高高芦苇的坡地。
夏侯芬兴趣很高地回过头向江浪招着手——她的马已窜进了芦苇丛中……
江浪催马过来,陡地发觉眼前一片开朗。
好大的一片原野!
原野几乎全为芦花占满了,白色的花穗形成了一片白色的海。天风压下来,大幅度地起伏着,形成了类似怒海中的巨大波浪——一眼看上去有说不出的美丽、说不出的心旷神怡!
在那里,有几只展翅的大秃鹰低空盘飞着。声声鹰鸣,逗挑着人类先天具备着的潜在野性。
芦花波浪里,能够清晰地看见纵横的陌道——像是几条巨蟒,游行在怒海惊涛里。
原来不开朗的江浪,也变得开朗了。
真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这么豪迈的句子,没有身历其境的人是绝难道出来的。
“怎么样,美不美?”
夏侯芬在马上回过头来看着他,大风把她散开的长发吹得飘拂着。一瞬间,她那种狂放与任性的禀气,让江浪尽收眼底一她是个很可爱的女孩子啊!
曾几何时,她已把昔日的忧郁愁结解开了。
像她这种年岁的少女,原是应该这样的。
不等到江浪说话,她已催骑纵入大片的苇丛之中。
江浪的坐骑自动跟了上去。
两匹马穿行于大片苇丛之间,首尾相衔地奔驰着。
一列野鸡拍翅而起,五彩的羽翼在晴空翱翔着。
夏侯芬手持雕翎,取下弯弓。张弓搭箭,“飕”地一箭射出!
一只野鸡顿时应势而落,在芦丛里拍打着翅膀。
夏侯芬策马上前,弯腰抬起。
江浪道:“姑娘好箭法,想必暗器上的功夫更高。”
说到暗器,夏侯芬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情。
她把野鸡套在鞍后的绳套上,催骑来到了江浪跟前,伸出一只素手,道:“拿来!”
江浪一怔道:“什么?”
“你欠我的东西。”
“我欠姑娘什么东西了。”
“哼,还装蒜呢!”她眼睛一转,道,“你可真会逗着人家玩儿,明明赢了我,竟装着输了。”
说到这里,她脸上红了一下,信手折了一截芦花,向着江浪丢过来,江浪信手抄住。
江浪忽然明白过来了。
夏侯芬所指,乃是江浪把她由赤峰牢房里救出来的那一次,两个人在坟场里曾经比斗过一回。
“姑娘说的是那一对耳环?”江浪问道。
夏侯芬向他一笑,道:“还说呢,真丢人,直到第二天我才发现,你怎么摘下来的,我可是一点也不知道!”
江浪随即探手入怀,取出一个小皮囊,从里面把那一对收藏的银耳珠递了过去。
夏侯芬笑了笑,道:“真在你这里!算了,既然被你摘了下来,干脆送给你算了!”
江浪笑着收了起来,道:“姑娘这对耳珠,可是一种厉害的暗器?”
夏侯芬微微一怔,说道:“你怎么知道?”
她痛痛快快地大笑了一阵子,又说:
“反正什么也瞒不过你,即然你知道了这是暗器,我倒要认真地暗你一下,这种暗器,依江大哥看,该是怎么一个打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