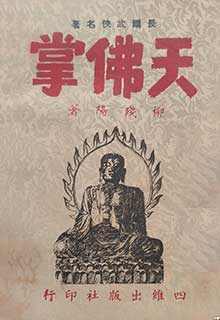已经是阳春二月了,照说该是春暖花开的季节,然而在北国的山区里,仍刮着凛冽的西北风,大风依旧带着刺骨的寒意,冻得人们簌簌发抖。高山上的积雪非但未开冻溶化,反而更坚实,更滑溜。因为积雪的上层表皮在冒水,也就那么湿湿的薄薄的一层水,却在稀薄的冷空气吹袭下,反而把下层积雪结结实实地冻了起来,而使得急着上山的张博天与戈正二人,不止一次地走到半途又不得不又重折回到景阳镇的“悦来小客店”里。
张博天与戈正二人,如果是在一年前,那可是人见人怕的两头豹,因为他二人可是李闯王身边的两个贴身悍将;只是二人万幸,当李自成被吴三桂搬来女真大兵,赶出北京的时候,二人正好押了一批珍宝在川陕道上,因此盛会未碰上,却把李自成的私藏,埋在了这终南山的“叫天岭”绝峰上面,埋得严严实实的。
不过张博天与戈正二人也够狠的,因为同他们一起爬上这“叫天岭”绝峰的二十个押宝亲兵,正挖了一个大岩坑洞,又把金砖珠宝坑入这个十丈深洞之后,却一个个被二人守在洞口,一刀一个,全都劈砍在洞口的万丈悬崖下面,大部份全都脑袋离位,就算有人在谷底收尸,恐怕多一半得张“头”李戴了。
单就这件事来说,二人甚感满意,因为在二人来说,既不要,也没有在清兵入关的时候,搏命于缰场而为闯王尽忠,更没有任何人知道他二人干了这趟买卖。
本来嘛!原本就叫流寇,寇者,盗匪也,而盗匪干的就是刀口舐血的活儿,东杀西砍的,为的就是金银财宝。
如今,天全变了,天变成大清的天下,如果二人当时把这批珍宝,双手再捧到北京,那才叫货真价实的傻蛋。
张博天,人长得一副端正相,浓眉大眼,直直的胆鼻,只是头尖而圆,宽而厚的大嘴巴四周,长了一半寸长的黑胡茬子,肥耳下面光溜溜的,看上去像是个富贵相。只因李自成没成气候,否则必是一个方面大员之流的人物;再看他身材也相当魁伟,白净净的,如果是蟒袍加身,玉带腰围,谁见了也会低头哈腰地侧退一旁。
至于戈正,更是一副张飞相,虎臂熊腰,豹头环眼,绕腮胡子连到胸膛上,六尺大汉人前一站,还真是让人以为天神下凡呢!
看来二人全是“大将之材”,却没有跟上时运,到头来变成丧家之犬,躲躲藏藏地窝在老河口附近的武当山里面。
一年多来,二人还真的够安份守己,没再干他们的老本行,当然二人全有自知之明,一份价值连城的宝物,正等着二人去分享分用,只等山上积雪溶化,挖开山洞,二人这大富翁肯是当定了,谁还会放着富贵的日子不享,再去干那淌血掉肉的刀口日子!
张博天与戈正二人在年一过完,就急不可待地沿着汉江西进,而到了这终南山下附近的景阳镇。
年刚过完,二人都在正月二十的中午,就赶到了景阳镇,半个月里,前后往终南山的叫天岭,爬了三次,却都无功而返。
倚着客房门,一颗脑袋几乎顶着门框上梁,戈正抓着他那毛森森的络腮大胡子,嘿声不绝地道:“他奶奶个熊,那么大的日头,竟然晒不化山上的积雪,惹得哥儿俩这儿穷急躁。”
坐在一张四方桌上喝闷酒的张博天,往嘴巴里一连丢了四五个花生,把个放在一张板凳上的大脚一收,起身走到戈正身旁,斜着头往远处的山峰上仔细瞄了一阵,才又回身缓缓地走回座位,狠声道:“他娘的还有得等的!”一面招呼仍然倚门望山的戈正,道:“老戈,喝酒吧。急有个屁用!”
就在当天晚上,这家“悦来小客店”中,又来了一位年不过三十的健壮男子,但在外貌看来,却是一派斯文,穿了一件蓝大褂,外罩兔毛坎甲,一条天蓝长裤,裤管分别由两条指宽的黑带子扎着,黑布面鞋子,肩上搭了一个褡裢帆布袋,袋子的两端还有系带露出那么两三寸。
论他的长相,一看是个老实人,一张四方脸,大耳宽嘴巴,眉清目秀下面吊了个悬胆鼻。他一进门掌柜的就哈哈笑道:“约莫着白大官人也该来了。”
只见这姓白的就着店中一张方桌子,放下肩上的褡裢袋,一边坐下来,一边笑着道:“王掌柜这个年过的可好?”
“好,好,如今不闹流寇,地方上平静就算是福。”
就着一张凳子,王掌柜一手拎着他那支长年不离手的旱烟袋,坐下来道:“今年山里的雪好像化得特别慢,三两天恐怕白大官人还不能往山中走啊。”
喝了小二送上来的茶,这位被称作白大官人的笑道:“明天一早,我得往山上去踩踩路,不行再折回来,如果还要等上个十天半月的,那就再回白家堡,总不能就在你这家小客店里干耗着。”
店掌柜换装着旱烟丝,哈哈一笑,道:“说的也是,这儿到大官人的白家堡,也不过一天的脚程,没有必要窝在我这破落的小店。”
这位白大官人,就是安康以西不过十里的白家堡少堡主白中天,川陕道上谁都知道,安康白家堡是个武林世家,老爷子白慕堂年已六旬,膝下两儿一女,大儿子白中天,除了子承父业,学了老父一身本领外,更是醉心岐黄之术,每年开春,总是要攀上终南山的各大高峰,采摘一些嫩枝草药,几年来从未中断过。
景阳镇的悦来客店那扇大门,掩上了半边,因为天色已黑,从终南山顶吹刮下来的西北风,仍然是那么的刺骨。店外面的那条泥巴小街上,已不见了人影。就拿悦来客店来说,住店吃饭的人,才不过五成,数一数也只有十七八人而已。
悦来客店门口的两盏西瓜大的纸糊灯笼,在油座底下各坠了一个包在布里的石头,为的是怕风吹得晃晃荡荡。
屋子里,七八张四方桌子,看起来全坐了人,只是没有一张桌子坐满人。那些赶驴运粮或拉着矮不唧的小川马往东运川盐的贩子们,大多只是吃了一碗辣汤牛肉盘子面,干净的凑着洗脸水再洗个脚,就倒在那个通铺上睡了。不爱干净的,甚至脸也不用洗,就睡下去。如果有人问他们,走了一天的路,赶了一天牲口,怎么连脸都不洗一下,他们准会说,一脸油泥可挡风刮日头晒,洗了那多可惜。
安康白家堡的少堡主白中天,据了一张桌子,一边吃喝着,一边与掌柜的闲聊。
“我到山上所要找的宝物,还真的要等雪全化了才能找得到,总不能瞎子摸象,挖出来不一样吧!”
店掌柜眯着眼笑道:“赶明儿一早,我叫伙计给你准备家伙,你到了高山顶上刨起来也方便多了。”
“那就谢谢你了。”
“哪里话,白大官人你可不是外人,说谢可就见外了。”
二人这么有一句没一搭的对话,却把附近一张桌子上正在大吃大喝的戈正与张博天两人,给说得扭结在了一块儿,那股子吃惊的样子,只就看着戈正手举着酒杯,半天停在空中没有动的表情,就可以知道。
于是,张博天与戈正二人,对于白家堡的这位少堡主,算是盯上了。
戈正心想:上山挖宝,什么宝?敢莫是老子们的那个山洞里的“无价之宝”吧!
张博天也在琢磨,这个王八蛋,可能就在打老子们的那些金砖珠宝,好在让老子碰上了。
然而,戈正与张博天二人却有个共同的想法……
其实,二人的想法也就是令他们费解的迷惘……
那就是这小子怎么会知道的?
上山挖宝还有在人多地方嚷嚷的?
还有就是这小子是什么来路?
疑问的结果,对于戈正与张博天二人来讲,却全都变成了问题,而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先盯牢这小子,当然必要的时候,就在深山先做了他。
当天夜里,戈正与张博天二人还真的一直商量到二更以后,方才睡去。
就在二人紧邻的房间里,白家堡的大少堡主白中天,早已是鼾声大作,睡得十分香甜了。
当太阳光还未从悦来客店正对面的斜坡上冒头的时候,白中天已收拾妥当,背了一应上山用物及一把十字镐,手上抓着一把宝剑,沿着景阳小镇北边的一条蜿蜒山道,迤逦着朝终南山的高峰方向走去。
相距不到一里多地,戈正与张博天二人,也朝着这条上山的小径走去。
从东边洒落的一片金霞,把个天空照射得相当美,美得就如同一张崭新的蓝被单一般,在高山白雪的互映下,人们的心中是应该舒畅,恬静的……
然而,这时候跟在白中天后面的戈正与张博天二人,却并不舒畅,更不恬静,因为前面的白中天,竟是与他二人同道。
一连翻过“三道土地岭”,那是攀上终南山高峰必须经过的地方,每道土地岭上、面,均有一座丈高的土地公庙,据说那是因为这一带山区里面,野狼特别多,而土地公却专管这些畜牲,不准它们越过这三座山岭,也因此,人们只要翻过这“三道土地岭”之后,再也不会看到任何住家的人了。
白中天一到了第三道土地岭,就在土地庙前的老松树根坐下来,歇腿塞肚子,因为这时候已快近中午,吃饱喝足以后,还得有一段好长好长的山路要爬呢。
三道土地岭的高度,全都差不多,因此戈正与张博天二人站在第二道土地岭上,还真的把正在第三道土地岭上的白中天,看了个一清二楚。
张博天边啃着一块酱肘子边道:“老戈,如果苗头不对,咱们俩可得狠着点。”
戈正边吃,边仰头往白中天处望,慢吞吞地道:“只要看到他往咱们那个地方爬,咱们就把他剁了,大山里没有人看到,谁知道是咱们哥儿俩干的?”
张博天不由地摸摸背上的大刀,他那把砍刀可是喝过不少人血的锋利钢刀。
于是,就在白中天翻向第三道土地岭下方的时候,戈正与张博天二人也急急忙忙地朝着第三道土地岭上冲去。
白中天脚步相当快,因为戈正二人才登上第三道土地岭的时候,他已沿着碎石草径,直往正面高峰上走去。
看了这情形,戈正与张博天急忙紧脚步追去。
翻过第三道土地岭,戈正二人知道,再往山里进,顶多再有个四五里,就连那尺宽小径也没有了。
一连转过三个山凹,跨过两次山溪,戈正二人已看不到前面的白中天。
“快!”张博天当先展开身法冲去。
戈正也急道:“咱们直赶朝阳峰去。”
二人施展轻功,快得如两头黑豹,不过一个时辰,已经攀岩跨崖冲到朝阳峰偏西的那个悬崖上面。
一棵向下垂的合抱老松树,是特有的,也是主要的记号。另外,一溜长藤,严产实实地自老松树根处垂下来,遮了一大片岩石。
戈正与张博天二人对望一眼,没有异状。
张博天想笑,因为,宝物就在一片藤蔓下面,只要搬离堵塞洞口的岩石,二人这就成了富翁,连下辈子也闻不到“穷”味了。
戈正仰天哈哈一笑,道:“老张,还等什么?下手吧!”
张博天手一拦,急道:“慢着!”
一面环视一下四周群峦绝峰,道:“不要忘了,上山来的可不是只咱们哥儿俩!”
戈正一听,不由点头,道:“对!要不要找那小子去?”
“不必,咱们暂时不要把这洞口附近盖上的积雪移除,藤上的积雪依旧,就算那小子摸来,他也不一定知道咱们是干啥子的。”
“有道理,不过……不过咱们总不能就守在这儿不动,岂不引起那小子的疑心?”
张博天一边挥去身上的雪痕,一边冷笑道:“他最好别冒失,也最好别叫咱们碰上!”
“你的意思是……”戈正比划个杀头的模样。
“嗯!”张博天在他那胖嘟嘟的脸上冒出一个笑,只是那个叫人起鸡皮疙瘩的笑,却被一层寒霜所掩。
哥儿俩有二十年的杀戮生涯,彼此也太了解,因此,只要是任何一个动作,任何一个表示,不用开口,心里全都明白。
于是,戈正又摸摸背的大砍刀,环视一下四山。
时辰在二人觉着是慢了些,但等下去似乎毫无意义,因为既然决定要对那小子下手,就算他真的遇上,也还是死路一条,顾忌对二人来说,似乎已成了多余。
二人一打商量,决定开始动手。
“呛”的一声,戈正抽出大砍刀,对准附着一层几有半尺厚的雪,开始劈砍那层藤蔓。
一堆堆的积雪,笔直地落向老松树下面的万丈深崖,还未落到谷底,已被从谷里吹来的阵风,吹得无影无踪。
于是,一大片藤蔓条,一下子连雪全都落下深涧,沿着山壁,带起大片的雪花与碎石。
一大块足有磨盘大的岩石,歪歪的却正紧紧地堵靠在山崖上。
二人相视一笑,立刻动手推那块大岩石。
戈正则把垫在大岩石下面的几块碎石除掉。
也就在二人低头拆除大岩石周围碎石的时候,张博天忽地“噫”了一声。在这种令人窒息而又兴奋的时刻,任何异样的表情,都会令人吃一大惊。
戈正身材高大,急忙垫起脚,伸头看过去,不由也是双眉一皱,因为他也发觉,就在大岩石上方,断藤的下面,还有一个足可爬进去的洞口。
对望一眼,戈正与张博天二人立刻“哼咳”有致,施出全身力气,急急地推开那块巨大岩石。
就听一阵雷声般的巨响,巨岩在不断撞击着岩壁的响声中,滚向峰底。
然而,巨岩离洞却带起一股极为腥臭的味道。但这时候对二人来讲,已管不了这么多。
不打招呼,且又是争先恐后,二人甚至连个松枝火把也没有点燃,立刻朝着数丈深的洞中冲去。
头前两三丈,距离洞口近,尚可看见,但过了三五丈,洞中却一片漆黑,尤其人在明处,一旦走入黑暗,双眸尚不能适应,还真的是有伸手不见五指的感觉。
也就在二人刚刚人洞五六丈深的时候,就听一阵“沙沙”巨响,那声音就如同人行沙滩上一般。
二人一惊,张博天人在后面,正要掏出来的火折子,立刻被划落地上,人也斜撞到洞壁上。
而走在张博天前面的戈正,却大叫一声拚命在洞中左冲右撞,他那高大的身体,不断地发出撕裂声与撞击声,以及他手中那把大砍刀的碰壁声。在拼命挣扎中的戈正,粗哑着声音,只低而沉地迸出一个字来:“蟒!”
张博天头撞岩石,尚有些七荤八素,闻言以为戈正叫自己帮忙呢。
于是,他奋不顾身地挥动双手,朝着戈正跟前抓去,却在他尚未摸着戈正人的时候,左臂陡然火攻一般的疼痛,大叫一声,急忙用力收回,于是巴掌一块大的臂肉,几乎被撕下来。
到了这个时候,张博天才发觉,这洞中原来窝藏了一条水桶般粗细的巨蟒。
就在这么一阵翻腾中,张博天似已适应洞中的情形。
不错,那确实是一条巨蟒,一条花斑大蟒,正把戈正缠绕在地上滚动。
再看戈正,由于洞内窄小,根本没有躲闪余地,仅看到戈正的一条手臂不停地在挥,在抓。
本来,戈正的身体粗壮,却不料这条蟒更十分凶悍,它不但死死地把戈正缠住,甚至不断地张开巨口,对戈正的头脸咬去,
也因此使得戈正没有再开口说出一句话,甚至一个字来。
要知道巨蟒缠人或任何动物,一旦被它缠住倒在地,那就算是死定了,因为人要用上力,全得要站稳脚步,如果倒在地上,又如何运用得出任何力道?
相反,对蟒蛇而言,只要能把人撂倒在地,它便立刻缠咬自如,更显出它的力大无穷。
其实对戈正而言,也是想不到的事,如果明着发现洞中这头巨蟒,戈正一刀在手,他是毫无可惧的,然而……
张博天一看戈正被巨蟒掀翻在地,顾不得自己左臂滴血,立刻拔刀,劈杀过去。但由于人蟒不停地滚动,他又怕砍到被缠绕的戈正,所有竟显得有些无所适从。
渐渐的,人蟒已翻滚到距洞口三丈距离,张博天这才看了个仔细,他知道戈正真的完了,因为戈正的那个粗脖根,已变了方向,那样子何止是面目全非,简直就是被千刀万剐,但却全招呼在他的那颗脑袋上一般。而戈正的头,如果不是被巨蟒绕着脖子,一准会垂下来。
张博天如今是一喜一忧。
喜的是戈正这么一死,自己算是放下了设计已久的心机。当然,那是在二人分宝时候,施之于戈正的计谋。如今岩洞已开,宝物将露,自己这往后就算是富甲一方的张大财主了。
忧,当然是忧,因为这条巨蟒,看样子还真难对付,自己是躲一躲呢?还是挥刀而上?
就在他的一念尚未决定的刹那间,突见那头巨蟒,昂首吐出一尺多长的叉形毒信,滑溜不唧地朝他扑来。
这时候就算想逃,也已迟了。
张博天大吼一声,不等毒蟒扑近,立刻挥刀向它劈去。
却不料毒蟒的尺半长蟒头一缩,已疾快无比地绕向紧靠洞壁的张博天,那种扑击绕缠动作,直叫张博天大吃一惊,而急忙朝洞内纵去。
他才刚刚跨过戈正倒在地上的尸体,巨蟒的尾部却已拦住他的去向,急切问,张博天挥刀狂劈。
有如金铁交鸣,又像砍在碎沙石地上一般,张博天的那把大砍刀几乎有不着力的感觉。
就在这一刹那间,脑际出现了一群人影……
人影在浮动,全都是没有脑袋的样子……
那不正是亡命在崖下面的那二十名被他与戈正劈杀的手下吗?
眨巴着双眼,张博天极力想把那种令他惊心的幻觉抹去,但却愈眨巴愈明显。
就在他这种惊吓中,巨蟒的扑缠已即将上身,张博天拚命地大叫一声,一连又挥去四五刀。
虽然,刀刀都中在巨蟒的身上,虽然,每一刀全都发现巨蟒有血被大刀的刃芒带出,但却无法一刀挥断这头巨蟒,更何况巨蟒似通灵性般的,只把七寸以上的部位,尽量地躲过张博天的刀锋。
因此,张博天眼见快要步上戈正的后尘,去统领崖下面的那二十名“阴兵”了!
就在张博天危机重重,生命已将奔向丰都城的刹那间,突然间,洞口的人影打闪,只听一个人大喝道:“畜牲!竟躲在这儿!”
只见那人冲进洞来,先是抖手洒出一把十分香醇的粉末,紧跟着就在背的袋中,抽出一根银色丝绳。
那巨蟒正要把张博天扳倒,突见来人,似是遇到煞星一般,就在那把香醇的粉末疾洒而来的时候,“咕咕咕”的一连叫了好几声,御着一阵腥风,急急地扔下张博天,一冲而扑向洞口。
“哪里逃!”
来人手中的银色丝绳刚刚举起,正要奔向毒蟒的头时候,毒蟒已擦着来人的身边,一冲而过。来人急用双手去抓,但却抓了两手蟒血,那巨蟒已滑出洞外。
来人急追而去,但在仰头看时,阳光下,那条巨蟒,已驾云腾雾般,朝着朝阳峰顶上冲去。
来人正要追去,突闻洞中“哎呀”声,只好把身形煞住。
缓缓地又走入洞中,来人这才发现,地上已死了一人,而另一人则歪坐在洞壁上,正大口喘气。
于是,他从肩上褡裢中掏出火种,燃起一只小小火把来。立刻间,洞中的一切,尽入眼底。
先是走向戈正的尸体旁,探手一摸,摇头道:“他死了。”
火把照向张博天,但见他已脸色泛青,耸肩喘气,口中低叫着:“我……”
就在火把的照射下,发现张博天的一条左小手臂,正在往外冒血,而冒出来的全都是黑色的血液。
来人摇着头,从褡裢中掏出四五个纸包,边敷药边低低地埋怨道:“怎么不看清楚,随便就往山洞中钻,应该知道,大山里荒泽中,狮狼虎豹,毒蟒巨蛇,全是以山洞为家,硬闯进来,岂不拿自己性命开玩笑。”
张博天似是喘过气来,但也才只说一个字:“你?”
“把这包药快吃下去!”
张博天保命要紧,几乎连那包药的纸也塞入口中。
一面低头看来人替自己熟练地把伤口敷上一层淡红色药粉,且又掏出一块丝巾,包扎起来。
张博天的痛苦慢慢地在减轻,但随着痛苦的减轻,而恶念却又在胆边滋生。
因为这时候他想到了洞里的宝藏。
他不能因为这人对自己的施舍援手,而丧失价值连城的宝物,因为那些是他来此的真正目的。这人如果不是为了寻宝,怎么会在这雪尚未化完而又寒风刺骨的时候,一个人扑上这叫天岭来?
张博天暗暗地抓起跌落在地的大刀,他要像巨蟒偷袭他与戈正二人的方法,再加诸于这个外表斯文的家伙,为了那堆宝物,他不得不如此。
本来这世上就是这种样子。为了财,什么他娘的父子之情?为了宝,又管他什么朋友之义!只要有钱,老子就是老子中的老子。就算比我张博天大上个三五十岁,照样也会叫我一声张大爷。当然,如果我张博天是个穷光蛋,就算是小之又小的小辈,自己还得称一声少爷,甚至小爷的。
这一切,这一切全都是“银子”在作祟,于是,张博天不得不再为洞中的那堆宝藏,而昧起良心,再施杀手。
但他也发现,来人身手不俗,还抓了一把宝剑,显然武功很高。
于是,他必需要一击而中,否则……
就在他这一连串的意念中,却发觉这人手举着小火把朝着洞中摸进去。
“你要干什么?”张博天挤出一句吼叫。
来人一迟疑,回头道:“寻宝呀。”
张搏天跌跌撞撞暴伸右手,眦牙咧嘴地把大刀一阵挥动,叫道:“不可以!你不能!”
那人一愣,立刻联想到张博天的“善意”吼叫,不由一笑,摇着头道:“你不要担心,不要白不要,岂可轻易放弃?”
张博天大怒,咬牙切齿道:“你他娘的原来早就觊觎那堆东西了?”
来人似是一愣,但旋即笑道:“也可以这么说,白某人上山来,多一半为的就是这些可遇不可求的宝物。”
张博天似是喘过劲来了,因为他已经能背顶着洞壁,慢慢地站起身来,再加上洞中的那般含有雄黄的味道,使他有清醒作用,帮助他恢复活力不少。
暴怒而无法自己的张博天望着姓白的长驱直人而深入洞底,他也一步半尺加三晃,跌跌撞撞如酒醉般地朝洞底移去。
十丈距离,张博天就着灯亮走过去……
到了,那不是洞底吗?因为岩石挡住去路。
伸手触摸,岩石冷凛而坚硬。
洞顶,洞壁,全都是一样,全都是岩石,全都是灰黑色带黄土的洞穴。
那四支铁箱子呢?
六只帆布袋呢?
为什么洞中是空的?
张博天几乎昏了过去,巨蟒没有要了他的命,但失去这些价值连城的宝物,才真的会要了他的命。
因为他张博天与戈正,为的就是这些宝物,才摸到这深山里来的。
如果真的宝物失了,张博天觉得,倒不如像戈正,两眼一闭,离开这个比他张博天与戈正二人的心更丑陋的世界,因为他们再丑,也丑不过这世上那些心机更奸诈阴险的恶人。
张博天几乎要哭起来,胖嘟嘟的脸上,一下子充满了汗珠子,如果用手去摸,一准觉得他的那一脸汗珠子比山谷下面的泉水还凉。
猛然看到那个蹲在地上的“救命恩人”,张博天心中在激荡,先杀了这个姓白的,出出这口鸟气再说。
只见他在这一恶念中,缓缓举起了手中的大刀……
“你看,你看,这就是无价之宝!”
姓白的回身仰头,目注张博天,那份得意的样子,根本忘了张博天的举刀是“为什么”。
也算是一种得意忘形吧!
姓白的,正是安康白家堡的大少堡主白中天。
白中天本来并未登上这个朝阳峰来,他是在另一峰上,寻找他的各种草本中药材料。但他在一连听到两声大叫中,发觉高峰之上的另一面,有人呼叫,便折转过去,却发现是在对面的朝阳峰上。
于是,他立刻奋力冲了过来,这才在这洞中,及时把张博天救了下来。
但他心中不无疑惑与遗憾。
疑惑的则是这二人身材魁伟,身上带着大刀,上到这高山上来于什么?
而遗憾的,则是他冲来救人,但还是晚了一步,因为戈正已遭蟒咬而气绝当场。
白中天救治了张博天的伤势以后,就急急地深入洞中,就着洞底,沿着石壁,用手挖挖刮刮的,而且是极为专心地在每块岩石上刮……
他根本忘了还有个张博天,已磨蹭到他的身边,他的身后,甚至已把大刀举起来。
因为,白中天找到了“蛇片”。
“蛇片”,那是中药中的无价之宝。它几乎无毒不治,无病不除,保养的药中,加上少许“蛇片”,连病人的气色也变得除浊而清爽;尤其是治病方面,五毒七痨,只要加上少许这种“凉中之王”的“蛇片”,那必然是效果立现。
“蛇片”这种可遇而不可求的药中之宝,乃是因为冬眠的巨蟒大蛇,在蛰居的洞穴深处,蟒嘴对着某一岩石,不断呼出体内之气,天长日久,它所吐的蟒涎与腹内呼出的气,在那个岩石上面,结成一层层的晶体白片,天寒地冻,形成了这种得之不易的药材。
张博天本来要举刀劈下,一看白中天专心一致,拿出一块白布,铺在地上,就着那块岩石,拼命地用一把匕首,在那块岩石上面铲刮。
张博天看得很真切,一层层,如大拇指甲的白霜似的薄片,落在白中天铺在地上的布里,火把的照耀下,发出晶莹的闪光,十分惹人眼。
但张博天可不懂这些,他所关心的,只是他的宝藏,如今成了空中消失于无形的楼阁,而他的希望,也成了一场春梦。数年跟着魏阉卖命,如今年已四十,得到的只是一场空欢喜。
他想起一年多以前,戈正与他二人,在杀了那二十名手下之后,为什么没有多带一些出去先花用,二人只不过各塞了几个金元宝,就趾高气扬,意满志得地下山而去!
突然间,张博天想到了一件事,难道会是他?
张博天想到谁?
张博天在衡情量势以后,缓缓放下了手中的大刀。
张博天正准备移步走向洞口的时候,突然间,他眼睛一亮,洞中石缝里有金光一闪。张博天不经意地弯下腰去,拾起那个令他吃一惊的金片来。
他太清楚了,那可是闯王玉带上的饰物,怎么会掉在这洞中?
那么来人又是谁?
不可能是戈正吧?他一直都是陪在自己身边的呀!
于是,他收起那个如牡丹花一般的金片,倒拎着大刀,缓缓朝洞口移去。
朝阳峰自太阳东出到日落,全都看得到,因而称做朝阳峰。
过了盏茶时候,白中天哈哈笑着走出洞口来。
“你好多了吧?”
“谢谢救命之恩。”
“谢什么?只不过举手之劳,而我却要谢你呢。”
“谢我?”
“是啊!”白中天扬一扬手中的白布小包,又道:“这就是我白中天寻找的无价之宝,如果不是二位的叫声把我白中天引来,又如何能够轻易找到这些‘蛇片’?”
张博天一头雾水,总算被一扫而光,当即问道:“白仁兄是做什么行业的,难道是郎中?”
白中天哈哈一笑,道:“并非悬壶郎中,只不过热衷岐黄之术而已。”
张博天立即又道:“白仁兄上山来,为的是……”
“寻宝,就是……”他得意地又挥挥手。
张博天一声极为苦涩的笑,道:“我二人也是来寻宝的,只是人的运气,天的邪气。”
张博天一顿之后,又道:“人若运气不济,老命都不知道是怎么丢的!你看我这位戈兄弟,如果他站在任何人前面,谁都会说他至少还能活三五十年的,可是……,这就是那句话,霉运罩头。”
张博天又指指天,接道:“天要尽冒邪气,天下可就大乱了!”
白中天笑着道:“你这话一点不错,李自成那个魔王,就那么一阵搅和,汉人的天下变了样,变成‘清’的了。”
张博天一声苦笑,他能说什么?
就听白中天继续道:“本来,我还要往上面攀去,可是越往上雪越深,我找的那几样宝贝,恐怕还得个十几二十天的才能刨得到。”
张博天心想,你小子挖药材草根之类,就说找药材,却偏偏说成找宝贝,娘的这也算你走狗运,如果不是遇上巨蟒,如果不是戈正身亡,就你这一句话,就叫你死在这荒山野岭之上。
突听白中天道:“走吧,翻过第三道土地岭,有户人家,咱们去那儿借一宿,明儿一早再折回景阳镇去。”
张博天想说什么,但他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人却对洞中躺着的戈正一摇头,跟在白中天的后面,朝第三道土地岭方向走去。
山路是难行的,尤其在没有山径的野岭上,更难行。
张博天的伤本来很是不轻,如果不是白中天及时赶到,如果不是白中天的药效好,张博天至少也要痛苦得折腾个三五天的。
然而他还是够幸运的,因为他遇上了白中天,叫他死里逃生,捡回一条命来。
如今,他甚至还能强忍着左臂伤痛,跟着白中天,一路朝三道土地岭走去。
山谷下面的水声,渐渐清晰可闻,也许白中天正在高兴中,当二人跨越谷溪的大石头上时候,白中天又掏出几粒药丸,对后面跟着的张博天笑道:“就着溪水,把这几粒药丸吃下去,提神醒脑,兼而补补元气。”
张博天急忙接过来,一下子全塞到口里,就着大石头,他爬下去“呱嘟呱嘟”猛喝两口水。
二人一劲攀上三道土地岭,平着望去,前面还有两道,土地岭上土地庙,老松树下灰蒙蒙的。
望望天,真的快要黑了,因为人在深山中,天亮天黑那可是绝对的,也就是天亮一定见到太阳,天黑必然日落山,太阳的余光比其平地来,至少要少上一半。
白中天领着受伤的张博天,连停都没停一下,两个心情不同,志趣相反,黑白道分明的“天”字号人物,一溜烟地翻过了第三道土地岭,朝着一座相距山溪不过二十来丈远一处山凹的茅屋中走去。
茅屋中,正中间已有了灯亮,灯亮不大,但在这黑漆漆的夜里,看得仍然相当远。
有灯亮就有人在,白中天已是喜形于色。
而张博天却并不高兴,他在想着他的宝藏,究竟是谁把那么多的宝物取走了?
当在他没有找出宝物之前,任何这儿的人,全都带着洗不干净的嫌疑,自然,这位救他命的白中天白大少爷,也脱不了干系,因为一个常年尽在深山高岭中寻他心中“至宝”的人,也包不准没有动了他那宝藏的手脚。
就在白中天隔溪呼叫中,张博天又回到了现实。他看到茅屋里走出一个壮汉,而壮汉的后面,又跟了一个女人,还有个十来岁的孩子,也从屋里跑出来。就着屋里灯亮,他看得一清二楚。
张博天跟着白中天,跨过山溪,来到那户人家前。
“真是稀客,大少堡主今年这么早就上山了。”
“老吴,你们这个年过的可欢畅吧?”
只听那个壮汉笑着走向场边,道:“流寇不造反,百姓好过年嘛!”
张博天一听,心里还真不是滋味。
白中天笑着走近茅屋,一边摸着那孩子的头,一边对一旁笑迎的妇人,道:“大嫂子这一向可好哇?”
“好!少堡主你也好?”
白中天边笑着,回身指着张博天,对姓吴的道:“这仁兄在山上遇了麻烦,我把他也带来你这儿,歇一宿,赶天亮我们就回景阳镇。”
姓吴的立刻招呼他老婆,道:“快弄些吃的,远来的贵客,可不能慢待。”
姓吴的还真够热情的,一直把白中天二人礼让到茅屋里坐下。
边喝着茶,白中天把张博天的遭遇,对姓吴的说了一遍,更把自己得的“蛇片”也毫不隐瞒地说了一遍。
姓吴的一听,立刻兴高采烈地道:“那畜牲又在山上造反了,我正准备找它呢?它竟还是害死一个人。”
白中天笑道:“如果你们再遇上,算是第三仗了,望你得胜而归。”
姓吴的一笑,也道:“如果收拾了那条千年巨蟒,就它那张蟒皮,就值上百两银子,比起我猎上三头老虎,还值钱哪。”
张博天这时候才想到,原来这姓吴的是个猎户。
当然猎户的嫌疑也最大,因为他们长年就在山中混,财宝说不定真的被这姓吴的弄走了。
于是,张博天有了一个令人可怕的意念。